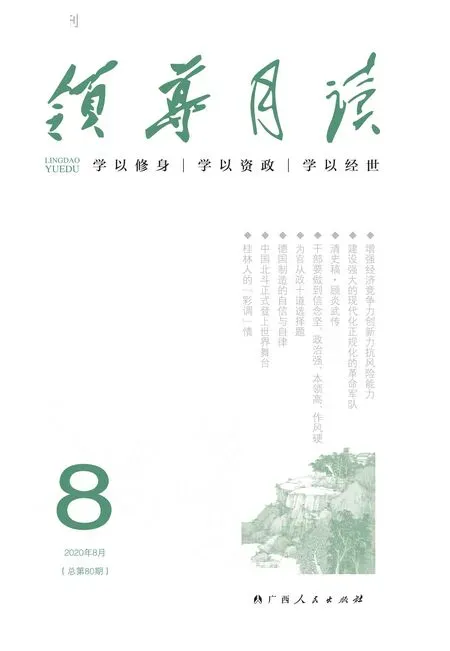桂林人的“彩调”情
黄捷文
彩调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的地方戏曲,她的内容谐趣、形式活泼、表演风格非常接地气,是桂北地方群众都喜爱的一个剧种。
对于出生在桂北的农村人来说,听唱彩调就是他们享受生活一种方式,彩调是一种自然的腔调,是一首谁都可以随口哼哼的歌!“哪嗬咿嗬嗨呀!”“我没拿着你的鞋(孩)呀?”“哪个讲你拿了我的鞋(孩)!”“你唱的呀:你拿了我的鞋(孩)呀!”“哦,那是唱调的调音,衬词!”“这样的呀,那就走吧。”“走吧,咿吆拐咯,夜夜哪嗬咿嗬嗨呀。”我小时候的生活,每天都是在这样愉快的小调中度过。
还没上学之前,我最喜欢跟着奶奶走亲访友。奶奶是个彩调迷,只要哪个村有“彩调”演出,她就会去那里的亲戚家住上个三五天,看得不亦乐乎。不懂世事的我也一天屁癫癫地跟在奶奶后面,嚼着硬邦邦的糖蔗,嗑着自家炒的葵花子,颇有兴趣地欣赏着舞台上流光溢彩的变幻。
奶奶的娘家是隔壁一个叫上炉的小村子。舅公的房子旁刚好是村子的大剧院、大戏台。这个大剧院应该是当时我们乡里最豪华、最宽大的了。那时候每个村时兴建戏台,记得有一首山歌:湖(复)里梁山好秀才,砍败长山起戏台,搭起戏台无人唱,哄起好多亲友来!可见当时彩调风非常流行。舅公屋边的剧院,青砖白粉墙,黑瓦房,大门口迎客的亭就有4 根大柱子支撑着,里面也有,都是粗大的原木。戏台也是木板搭的楼台,很结实,后面还有化妆间,古香古色的,和现在电视里常看的古戏台一般模样。
那些唱彩调的都是外地人,以邻县平乐的戏班子居多,都是住在舅公家里,因此我就有很多的时间跟他们接触。那些小生、小旦、小丑都是农村人,为人和善好说话,对我很好,常教我唱戏、化妆,也教我跳舞。
那时候,最流行的就是《王三打鸟》《娘送女》《阿三戏公爷》《四九问路》。我们那里“王”和“黄”是不分的,都是念“王”,我刚好姓黄,在家也是排行老三,所以他们经常插科打诨地称呼我“王三”。

彩调剧《王三打鸟》片段
“王三,来唱打鸟喽!”我就会乐滋滋地跑过去:“我王三,刚来到,端起鸟枪乒乓一声响,打得麻雀一大堆,数了一数,四十四双麻雀尾巴八十八……”一唱到这我马上就会笑场了!因为,每当数到这里,我就吐字不准了。直到现在我一口气也唱不下去这一段“四十四双麻雀尾巴八十八条麻雀腿”。还有,就是《阿三戏公爷》里唱“正月里来花里又花开”盘花那段我也唱不下去,真是缺少天赋。那时候的人淳朴,演出很卖力,虽然道具简单,但唱腔却是现在好多人学不来的。
我喜欢彩调,或许跟父亲也有点关系。父亲是村里队上戏班的长笛手和二胡手,经常吃过晚饭就拿着他的“弦子”出来拉两段。母亲没事就哼上几句,但母亲哼的是山歌居多。我其实很希望父亲教我吹笛或是拉弦子,但是不知怎么回事,我一样也没学成。
我喜欢彩调,喜欢那诙谐幽默风趣的唱腔,唱词简短、旋律简单、容易接受。就像我最喜欢的《阿三戏公爷》,阿三一出场就是:“公爷叫得急,阿三我来得慢,我在后堂煮早饭,一筒米,两筒水,煮出了三样饭:高头生,中间烂,底下成了锅巴炭,走出堂前看一看,原来是个乌龟王八蛋,王八蛋!”非常有个性的唱腔,极适合当时没有电视、手机等传播工具的情况下茶余饭后的娱乐消遣。
我喜欢彩调,喜欢她声张正义,追求完美爱情的曲意。一部《地保贪财》活脱脱地演活了民国时期一个农村地保的丑恶嘴脸;《四九问路》则是把梁祝那美好的爱情故事用幽默的对唱戏谑开来,叫人感受到一种纯朴爱情的美好。来源于乡村的生活故事,爱憎分明的故事情节,彩调其实就是农村惩恶扬善的形象代言。
彩调是一首古老的歌,彩调是一部通俗的剧,用心去聆听,去感受,你就会明白,彩调就是将人生的五味酝酿进去,通过历史的发酵而诞生的一种人文写意。
我想我老了,坐在轮椅上的时候,还想听到“哪嗬咿嗬嗨呀”那低回婉转的音调,而不是整天对着手机在孤独中悄无声息地消亡。

彩调剧精彩剧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