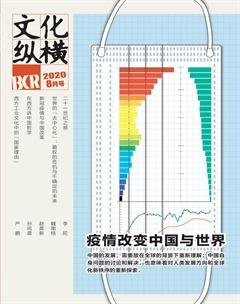西方工业文化中的“国家理由”
[重述世界史·栏目导语]
今天人们对世界近代史的理解,多多少少都会受到西方历史叙述的影响。这种“西方中心主义”是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对世界长期而深入的扩张留下的一层深厚的“观念地层”。然而,任何一种观念体系,当它深埋于思维的地层之中,就成为人们开始思考的前提,而鲜少被反思、质疑。这既遮蔽了历史叙事的复数可能性,又模糊了西方历史自身的丰富细节。为此,本刊开设“重述世界史”栏目,希望突破目前流行的世界史叙事的单一面貌,回到历史原本的丰富性中重新讲述,挖掘新的思想。
本期刊发的严鹏的文章正是重述世界史的一次尝试。长期以来,我们都相信西方国家是凭借私有产权、自由竞争、企业家精神、市场理性这些制度文化,才开启了工业化进程。然而严鹏指出,工业革命并非是在一个理想的自由市场环境中出现的,恰恰相反,它是与国家力量交织、在强大的国家力量干预下的产物。然而,那些已经借助国家力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又刻意隐去国家的作用,對外兜售一个跨文化的、普适的“自由市场”神话,从而压制其他国家的工业化。以此观之,今天一些西方国家为了国际竞争而公然放弃自由市场,也就不足为怪了。
工业文化是一个含义复杂的概念。作为中国工业主管部门推行的一种政策,“工业文化”一词指向了一种与工业化进程相伴生又推动了工业发展的价值观体系。[1]自亚当·斯密后,西方工业文化被主流经济学赋予了自由竞争及与之相关联的企业家精神等一般性意象,以成本、收益为考量的市场理性成为西方工业文化的显性标识。然而,考诸历史,哺育了工业革命的西方工业文化其实早于工业革命出现,[2]而“国家理由”在工业文化的形成中长期起着支配与支撑作用。进入20世纪后,西方工业文化中的国家理由逐渐被市场理性所遮蔽,在某种程度上被逐出了相关话语场域,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理由从西方工业文化中消失。相反,国家理由一直是西方工业文化的隐秘内核,并不时通过贸易战等极端形式重返视线。
国家理由的诞生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西方工业国家的基本制度,与之相联系的私有产权、自由竞争、企业家精神、市场理性等要素往往被认为是促使西方成功踏上工业化道路的原因,还被写入了开给非西方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药方中。然而,工业革命并非在历史的真空中横空出世。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工业革命经历了漫长的经济积累,[3]而这一积累过程与西方国家政治上的国家建构(state building)进程是同时发生、相互交织的。虽然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国富论》,正好与英国工业革命开启的时代一致,但是《国富论》所抨击的各种国家干预政策直到19世纪40年代后才真正取消。换言之,英国的工业革命是在一个广泛干预了市场的重商主义政权下发生的。[4]这是探讨工业革命起因时无法回避的一个历史次序。
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工业革命与工业发展的确依赖于竞争机制,竞争及其观念也的确是西方工业文化最重要的内核之一。不过,对西方世界的工业革命而言,竞争具有层次性。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只是西方工业革命的一个层次,而在市场之上,国家之间的政治与军事竞争则构成了更高层级的竞争,它既激励了工业革命,又宰治着工业革命。如果说市场经济是企业间的竞争在西方工业文化中的投射,那么国家间的竞争在工业文化中则反映为“国家理由”。
“国家理由”(英reason of state,法raison d'?tat,或被译为“国家理性”[5])指的是一种为实现国家利益而不惜采取一切手段的价值体系。它是西方政治学自文艺复兴时代以来形成的重要观念,是西方世界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时期特殊政治形势的产物。在欧亚大陆的主要文明中,西方文明自古罗马帝国崩溃后长期分裂的状态是比较特殊的。15世纪以降,欧亚大陆出现了一系列广土众民的大帝国,如东亚的明、清帝国,南亚的莫卧儿帝国,以及西亚的奥斯曼帝国等。这些大一统帝国的实际政治统合程度存在差异,对广袤疆域的控制力亦时强时弱,但在形式上能够将多种民族与多元文化置于一个统一政权的管理下。而欧亚大陆西侧的欧洲不仅在政治上缺乏大一统帝国,在思想文化上也因为基督教的宗教改革运动陷于分裂和对立。哈布斯堡王朝、波旁王朝以及后来拿破仑帝国恢复大型帝国的野心,都因无法突破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限度而无一例外地破灭了。在漫长的中世纪历史中,由于不存在一个强大的国家势力,天主教道德对国家行为起着规范、约束的作用。统治者要发起战争,需要首先证明自己在宗教或道德上的合法性。然而,随着近代国家的兴起,欧洲各国陷入纷乱的战争中,而罗马天主教会的伪大一统无法为欧洲各政权提供事实上的安全保障。为了不亡国,以生存为首位的政治体需要以非道德化的手段追求非道德化的目标。当中世纪道德已不能满足近代国家的需求,就必须出现新的价值观为国家在现实政治中采取的有违旧道德的行为做出辩解。此时,国家理由学说为新兴的主权国家挣脱中世纪大一统的文化与制度束缚提供了武器。

马基雅维利是第一个宣扬国家理由的思想家
国家理由学说认为,国家为了谋取公共福祉和权势,在必需时可以运用不合法律和道德的手段。第一个宣扬这种冷峻的现实主义新价值观的人是意大利人马基雅维利。在以城市国家为单位展开列国竞争的意大利,不仅在文艺上启蒙了西方世界,在政治上也因为长期持续的纷争状态而率先进行了关于政治体制与政治学说的各种试验。国家理由的观念就是这一政治试验的成果之一。马基雅维利教导君主“要保留那些不会使自己亡国的恶行”,称“如果没有那些恶行,就难以挽救自己的国家的话,那么他也不必要因为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6]。他大胆地宣告:“一位君主……不能够实践那些被认为是好人应做的所有事情,因为他要保持国家,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7]后来的德国史家梅尼克(Fridrich Meinecke)将欧洲思想史中的国家理由系谱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8]梅尼克如此界定国家理由:“‘国家理由是民族行为的基本原理,国家的首要运动法则。它告诉政治家必须做什么来维持国家的健康和力量。国家是一种有机结构,其充分的权势只有依靠允许它以某种方式继续成长才能够维持,而‘国家理由为此类成长指明途径和目的。”[9]梅尼克指出,“权势属于国家的本质”,因为“没有权势,国家就无法贯彻自己维护正义和保护社会的任务”[10]。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谋求更大权势,是国家理由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从本质上说,国家理由是对列国并立格局在思想上的承认,也为列国竞争格局下各国追求国家利益的行为提供了辩护。直到20世纪前,这种国家层面的马基雅维利主义都是西方列强奉为行动准则的指导思想。譬如,为了维护法国的国家利益,身为天主教红衣主教的法国首相黎塞留不惮与新教国家结盟,对抗与法国同属于天主教阵营的哈布斯堡帝国。这是最标准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也是国家理由的范本。不过,正如行动上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腓特烈大帝在宣传上对马基雅维利口诛笔伐,国家理由并未能在西方世界的政治思想领域确立绝对霸权。相反,梅尼克敏锐地意识到了现代西方世界的某种精神分裂,即国家理由与继承自中世纪天主教的伦理与法律之间强烈而痛苦的冲突。他将这种思想上的紧张状态描述为“一种不断被唤起的感觉”,那就是“冷酷无情的‘国家理由确实有罪——忤逆上帝、违背神规之罪,破坏往昔美好时代法律的神圣和不可亵渎之罪”[11]。这种精神分裂使国家理由成为一种具有原罪的思想观念,对于现代西方的政治文化有着深远影响。
如果说国家理由为国家间竞争提供了合法性辩护,那么制造业就是这种竞争的具体手段。制造业对于国家间竞争的作用体现在:国家间军事斗争的武器是由一部分制造业直接提供的,而另一部分制造业则通过创造财富,为国家供养纯消耗性的军事组织提供了财政收入。因此,虽然民间的制造业经营者是以市场竞争、成本与收益为核心关切的理性人,但对国家而言,制造业是权力斗争中的重要手段。相对于制造业经营者之间的竞争,国家间竞争的层次更高,这是因为任何制造业经营者都必须接受特定国家的统治。所以,在现实世界中,一旦制造业被国家视为竞争工具,则国家理由将从政治领域延伸至经济领域,对市场理性起着决定作用。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理由会时时干预市场理性,也不表示国家理由与市场理性是对立的,相反,国家理由很可能会放任或利用市场理性来为自己服务。但国家理由的决定性给了国家理由在其自认为的关键时刻或适宜时机凌驾乃至压制市场理性的权力。换言之,从理论上说,国家理由在经济领域里同样会奉行为赢得竞争而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
国家理由在西方国家经济领域的渗透是在思想观念的漫长交锋中逐渐发生的。这一过程中有大量问题必须从思想和理论上予以回应,比如:在一个农业社会里,如果农业经济足以自我循环,为什么必须将资源导向制造业?发展制造业要采取何种手段,是指望市场自发诱导还是依靠政府投资培育?当政治上的国家理由明显与经济上的市场理性相违背时,要如何取舍选择?……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与辩护过程中,一个新的观念体系形成了,这便是西方工业文化的母体——一种关于制造业的文化。而马基雅维利主义则是这一文化的内核之一。
知识与权力:一种关于制造业的文化
制造业是工业的主要组成部分,工业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制造业的现代化。虽然制造业远自人类文明鸿蒙初辟就已诞生,但是在古代,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农业都是古代各大文明经济体系的基础,并被赋予了文化上的重要性。比如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武器的制造对于各诸侯国兼并战争的成败有着重要影响,“耕战”思想被最终取得胜利的秦国付诸实践。在“耕战”思想中,农业具有基础性的战略意义,工商业受到限制,以免与农业争夺劳动力等资源。古罗马帝国的工程技术和武器制造技术也是帝国扩张的利器,但工匠在罗马的地位并不高,而且被社会报以敌视态度。[12]这种轻视、鄙夷制造业从业者的心态,在诸多文明中持续了很长时间,形成了结构性的文化。因此,文艺复兴之后西方世界逐渐形成的新的关于制造业的文化,就和日后的工业革命一样,既是西方世界率先迈出的历史脚步,也为西方世界一度领先其余各文明奠定了观念基础。
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产生了关于制造业的新观念,将制造业视为知识与权力相结合的一个载体,以及国家赢得国际竞争的重要手段。14世纪末,一位希腊出身的红衣主教在意大利写信给拜占庭帝国统治者,称:“制铁技艺,如此之有用,对人类如此必要,缺了它将无法顺利地从事战争或政治。”并建议派遣年轻人到意大利学习机械、冶铁、军火制造和造船技艺,将其引进希腊。[13]这种对制造业的推崇就是文艺复兴时代新知识的物化显现,而这位主教主张学习这些知识的目的之一,正是为了增强国家的权势。这种国家理由驱使下对制造业的重视,逐渐在西方世界内部造成与崇尚农业的古典思想之间的文化断裂。
英国文艺复兴思想家弗兰西斯·培根对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做出了理论表述,其“知识就是权力/力量”的思想广为流传。培根大力推广的新文化礼赞知识,宣扬由知识探索带来的进步。在培根眼里,知识的重要性只在于知识揭示了权力赖以运行的规律:“人类知识和人类权力归于一;因为凡不知原因时即不能产生结果。要支配自然就必须服从自然;而凡在思辨中为原因者在动作中则为法则。”[14]这种通过知识探索得到规律、并将其转化为人类支配自然的力量的逻辑,正是现代经濟发展的思想条件。因此,培根虽然没有对西方科学做出研究层面的实质性贡献,但他推动了一种有益于科学发展的文化的形成。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认为,培根可以被视为一名“文化企业家”(cultural entrepreneurs),其最大的遗产,“就是在文化上接受将有用知识的拓展视为经济增长之关键因素的观念”[15]。
培根对科学知识转化为实践力量的提倡,使得他高度肯定制造业的价值。在《新工具》中,培根认为科学“真正的、合法的目标”是“把新的发现和新的力量惠赠给人类生活”,但他同时指出,绝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偶然有“智慧较敏,又贪图荣誉的工匠”投身于新发明。[16]这一判断将制造业的从业者工匠抬高为将知识与实践结合起来的先驱。培根在其极具影响力的著作中为有用的知识与工匠式的实践提供了辩护,赋予了制造业更高的社会地位,营造了有利于制造业产生革命的社会心态。这为后来英国工业革命提供了理念和文化层面的准备。工业革命中大量的技术发明正是来自工匠在生产实践中的经验积累。值得指出的是,对于作为国务活动家的培根来说,有用的知识首先是一种国家权力的工具,而非为了全人类的福祉。[17]因此,培根对制造业的重视从根本上是基于巩固国家权力的动机。
培根高度重视制造业中的劳动。他写道:“往往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劳动比产品更宝贵,即工作和运输比原材料更宝贵,更能使一个国家致富。”[18]他看到了制造业创造财富的本质是劳动,并认识到施加于原材料之上的劳动能够提升商品的附加值,使国家获得更多财富。与培根相仿,一些同时代的英国作者也强调制造业的本质是劳动。他们肯定劳动中的实践性知识与技艺,并赋予了制造业以勤奋、自立等美德。这种观点在16、17世纪的英国商业界和思想界很有市场。托马斯·孟(Thomas Mun)在1621年出版的著作中将财富分为两种:“一种是天然的,国土本身的产物;另一种是人造的,靠人们的辛勤劳动创造。”进而指出:“如果要生活得好,要繁荣和富裕起来,我们必须想方设法地通过贸易来出售我们的多余产品,换回外国货币和我们需要的物品。这里,辛勤的劳动开始起作用,它不仅增加了海外贸易并支配其方向,而且还保持并提高了国内技艺。”[19]孟的论述在国家富强、劳动、勤奋、技艺和制造业之间建立起了逻辑关联,构建了一种将制造业赋予崇高道德意义的新文化。在18世纪工业革命爆发前,英国的许多关于制造业的论说都采用了上述培根和孟的基本的逻辑,它们与旧有制造业文化的区别如表1所示。

表 1 工业革命前英国制造业文化的结构
扶持制造业:经济领域的马基雅维利主义
在上述制造业文化中,不仅制造业服务于国家,国家也开始扶持制造业。而近代早期西方国家扶持制造业的具体方式,可谓极尽马基雅维利主义之能事。
直到1570年,英国海外贸易的结构主要还是出口原材料、进口制成品和奢侈品。这种处于劣势的贸易结构引发了许多商人、政客和知识分子的不满。对他们来说,制造业的发展被视为国家间竞争的一部分。例如,16世纪前期的一位作者写道:“这个王国有三种物产:羊毛,锡和铅;只要它们能在王国里被加工,所有人都将有口饭吃。”[20]
正如政治领域的国家理由观念从意大利向整个欧洲扩散,经济领域内重视制造业的文化同样起源于意大利,并逐渐传播至欧洲其他国家。今天英语中表示制造业的词语“manufacture” 源于意大利语“manifattura”,它正是在16世纪英国对意大利制造业文化的学习中,逐渐取代英语中原来用于指称制造业的词语“artificialtes”和“artificial wares”的。[21]为了扶持本国的制造业,欧洲各国的统治者先后采取了被亚当·斯密称为重商主义的政策。这类政策通过扭曲市场,将资源要素导向国家所看重的产业部门。15世纪后期,英国都铎王朝的亨利七世已经开始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培根的《英王亨利七世本纪》记录了当时重商主义政策的内容及动机:“国王希望他想支配和维护的和平……带来财富和繁荣……我们的民众要从事技术和手工艺工作,国人要更加自立,避免闲散,不再花自己的钱买外国人制造的物品。但仅有这些还不够,还要规定凡从海外带回来的商品,都可用来生产国内的商品,这样国内储备的财富就不会因贸易逆差而减少。”[22]在介绍亨利七世的另一项政策时,培根指出了扶持本国造船业和航运业与增强国家军事力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为了使海军更强大,国王还规定……来自加斯科涅和朗格多克的葡萄酒和靛蓝只能由英国船只运回国,将英国古老的关注富裕的政策调整为关注强大。”[23]可见,重商主义政策是十足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它将经济视为发展军事力量的手段,并且以压制别国经济势力的方式扶持本国产业,即使有违市场理性和国际性的商业伦理也在所不惜。

17 世纪起,英国开始通过海上贸易挑战意大利、荷兰这些制造业强国
为了扶持本国的制造业及其配套产业,西方各国的政府和学者想到的手段主要是关税。从15世纪后期到17世纪后期,英国存在着持续不断的鼓吹国家以关税等手段扶持制造业的思想潮流,也产生了包括《航海法令》在内的相关政策。17世纪后期的经济学家威廉·配第称:“对于已经加工完成马上可以消费的一切商品课税时,税率不妨高到使其售价稍稍高于国内生产或制造的同类商品——假如其他条件相同而能够自行供应的话。”[24]这是明确主张用提高进口关税的手段来扶持本國制造业。在这种马基雅维利式扭曲市场交易的政策背后,是英国对意大利与荷兰这些先行于英国的西方制造业强国或地区的羡妒与敌意。1672年爆发的第三次英荷战争,便起因于英国对荷兰“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指控。[25]然而,率先采取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其实是英国人:早在1660年及1662年,英国就为了打击荷兰毛织业两次通过了禁止羊毛出口的法案。此外,英国人也警惕地关注着同样采取重商主义政策的法国制造业的兴起。1697年,英国国务活动家约翰·波列芬(John Pollexfen)写道:“我们从前只盯着荷兰,将其视为唯一的竞争者;现在,法国人靠不屈不挠地发展工业来推动贸易,这附带增强了他们的海上力量,明显要比荷兰人危险。”[26]同样的威胁论论调也用来指责从中国进口的瓷器和从印度进口的棉纺织品。[27]可见,由国家理由支配的英国制造业文化,为萌芽中的西方工业文化的内核注入了一种强烈到近乎狭隘的竞争心态,用包括战争在内的一系列重商主义政策打击其他国家。这种政策有违市场理性和公平贸易,但促进了英国制造业的发展。英国正是凭借长期的马基雅维利式政策,从西方世界制造业的追赶者变为领先者。
以国家之名:西方工业文化未中断的传统
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基雅维利式的经济政策遇到了基于市场理性的经济思想的反对。英国国内对自由贸易的呼声日益高涨,主张废除用于扶持本国制造业的保护性关税。在李嘉图之前,作为自由贸易理论根基的比较优势学说已经以较为粗陋的面貌问世。活跃于18世纪初的英国人达维南特(Charles Davenant)指出:“不同土地和国家出产不同的产品是一种迹象,表明天意要它们相互帮助,相互供应必需品。”[28]达维南特并不排斥制造业或国家竞争,他排斥的是在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中使用扭曲市场的马基雅维利式政策。用他的话说,贸易“就其本性而言是自由的,它自行寻找航道”,而政府对待贸易“应当在总体上像上帝那样加以仁慈的照管……其他一切则应听其自然”[29]。达维南特对于成本控制有着执着的追求。他认为,如果英国毛织品生产能做到“低价向所有国家出售”,自然可以“打消一切人建立毛织品制造业的念头”[30]。而在达维南特眼里,产品的低价取决于劳动力与原材料成本的低廉。所以,他一方面积极鼓吹英国废除《济贫法》、设立“贫民习艺所”以便“强迫贫民从事劳动”[31],另一方面又反对发展原材料不产自英国的制造业如丝织业,因为这种产业无法在英国生产出廉价商品。[32]他举出的例子是:“荷兰人最近将法国光亮绸盖上他们的印记运到我国,尽管交付了运费和关税,仍能廉价出售,击败了我国的光亮绸制造商。”[33]这个例子批驳了重商主义者们马基雅维利式政策的有效性。
达维南特实际上建构了一个与培根和孟等人不同的增长模型。在培根等人的增长模型中,制造业依靠知识驱动,国家权力为制造业降低外来竞争的冲击,制造业以其出口巩固国家权力。在这一模型中,知识是竞争的关键。而在达维南特的增长模型中,成本是竞争的关键,国家权力对制造业采取放任态度,而制造业依靠本国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降低成本。最终,制造业的出口是为了财富的增长而非国家权势的扩张。两种增长模型的本质区别在于对增长动力的判断不同。尽管达维南特举出了保护政策失败的例子,但正如孟等人指出的那样,一些资源贫乏的国家如荷兰也发展出了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制造业,这与达维南特模型的预期并不相符。究其原因,制造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源的成本是动态的,而知识是一种可以改变资源成本的变量。从机制上说,权力所起的作用与知识相同,尽管权力更多的只是为知识改变资源成本的过程创造便利条件。然而,知识的生产与应用具有不确定性,不像天然的资源禀赋具有更高的可预判性,这就使得培根式增长模型较之达维南特式增长模型具有更高的实施成本。两者的比较如表2所示。

表 2 近代早期兩种经济增长模型的比较
由于种种原因,18世纪的英国在工业革命的展开过程中,自由贸易思想慢慢取代了保护主义思想,其最终形成的工业文化更偏向达维南特式增长模型而非培根式。19世纪的亚当·斯密在强调市场理性支配下的自由贸易这一点上,就完全承袭了达维南特等早期的自由贸易论者。
但是,自由贸易论者达维南特却是支持英国建立海上霸权的,[34]这一点也被斯密继承了。正是在这一点上,斯密露出了其马基雅维利主义的马脚。斯密虽然主张市场理性、反对国家扶持制造业发展,却在《国富论》中对英国用于排挤荷兰的《航海法令》赞不绝口,称这个法令的有些条目虽然是基于“民族仇恨”制定的,但“却是像深思熟虑的结果同样明智”[35]。斯密支持《航海法令》是因为它“以削弱唯一可能危害英格兰安全的荷兰海军力量为其目的”,进一步说,“由于国防比国富重要得多,所以,在英国各种通商条例中,航海法也许是最明智的一种”。[36]一个鼓吹道德情操的自由主义者对“民族仇恨”如此公开地褒扬,即使是最大胆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闻之亦会瞠目结舌。被斯密称赞的法令条目包括禁止使用荷兰的船舶与英国贸易,以及对非英国的捕鱼业课以重税。此外,斯密对于重商主义者惯用的补贴政策,也基于国家理由而给予肯定:“如果某一种制造业确是国防所必需,那么靠邻国供给这种制造品,未必就是聪明的办法。如果这一种制造业非奖励即不能在国内维持,那么对其他一切产业部门课税,来维持这一种制造业,亦未必就不是合理的。对于英国制造的帆布及火药的输出奖励金,也许都可以根据这个原理来加以辩护。”[37]在《国富论》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表述:“在战争或政治上,邻国的财富,虽对我国有危险,但在贸易上,则确对我国有利益。”[38]不经意间,斯密暗示了《国富论》的核心主张是不考虑“战争或政治”条件下的贸易问题。事实上,整本《国富论》都散发出一股不易察觉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气息。斯密不仅不否定国家理由,还将国家理由置于市场理性之上。
从近代早期的制造业文化向19世纪古典工业文化的过渡,就是这样一个“去马基雅维利化”的过程。培根宣扬的知识与权力的结合依然是其核心,然而在“知识”被阐发为以创新为特征的企业家精神的同时,“权力”则被有意识地淡化了。国家理由隐而不彰,工业竞争在观念上被局限于市场层次,马基雅维利主义被更为道德化的自由贸易说辞取代。然而,这种转向只是一种伪善的伎俩,其本质是英国通过马基雅维利式政策取得工业化优势后寻求道义上的制高点来压制其他国家的工业化。且看英国人李嘉图畅想自由贸易如何“把文明世界的各民族结合成一个大同社会”:“葡萄酒得以在法国和葡萄牙酿制,谷物得以在美国和波兰种植,而金属制品和其他商品得以在英国生产。”[39]问题在于,金属制品是武器装备的基础,当金属制品只在英国生产时,对其他国家意味着什么?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促使其他国家的部分精英不得不以竞争心态推测英国的实际意图。于是,美国的汉密尔顿提交了《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呼吁新生的合众国以培根和孟鼓吹过的方式扶持制造业;德国的李斯特则直接控诉英国人说一套做一套,一如当年英国人对荷兰人的指责。[40]这种后来者指责先行者言行不一的戏码在后来的历史中一再上演,而关税、补贴等实践中的马基雅维利式政策却从未停止过,只不过新的西方工业文化代言人已经少有如斯密讴歌《航海法令》那般率直了。
小结
当市场理性的话语支配太久后,隐藏于行动中的国家理由偶一登上观念的前台,还是不免令人惊骇与不适。在学界,主流经济学将达维南特式增长模型和斯密传统发扬光大,视“贸易可以使每个人的状况都变得更好”这一信条为经济学的“十诫”之一,[41]避而不谈国家理性支配下的马基雅维利式残酷竞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意识到这个世界仍然是利维坦们争斗的舞台。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今天美国对中国威胁论的渲染,正如波列芬当年拿法国制造业的威胁来恐吓英国人;今天美国在高科技产业上的对华封锁,与17世纪英国禁止羊毛出口荷兰如出一辙;而今天美国企图通过关税战来转移产业链,不正是英国《航海法令》曾经干过的事情?

今天美国对华为的打压,与 17 世纪英国禁止羊毛出口荷兰如出一辙
作为西方工业文化的内核,“国家理由”的观念诞生于西方近代国家长期纷争、始终无法实现大一统的状态中。它深植于西方文化的观念体系中,对国家行为有着长期、深刻的影响。因此,我们大可不必惊诧于当前中美乃至世界其他经济体之间有违市场理性和商业道德的贸易争端。反过来说,正是由于西方工业文化的这种本质性特征,我们也不应就工业论工业、就经济谈经济,而应该认识到在西方工业文化所塑造的全球工业竞争格局下,国家之间马基雅维利式不择手段的竞争随时可以凌驾于遵循市场理性的公平竞争之上。自由竞争、市场理性、企业家精神、勤奋伦理……不管西方工业文化呈现出何种样貌,一旦国家间竞争的强度高到震裂了这一文化的外壳,国家理由这一隐秘的内核就会显露出来。
(责任编辑:王儒西)
注释:
[1] 对工业文化官方化的解释见王新哲、孙星、罗民:《工业文化》,电子工业出版社2018年版。
[2] 较新的通论性史著可参考:William Ashworth,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State, Knowledge and Global Trade, Bloomsbury, 2017。
[3] Graeme Donald Snooks, eds., Wa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Necessary?, Routledge, 1994, pp. 21~23.
[4] 贾根良:《重商主义、工业文化的诞生与英国工业革命》,载彭南生、严鹏主编:《工业文化研究》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5~26页。
[5] 周保巍认为,从“reason of state”在意大利产生的“论辩语境”及其在欧洲扩展的“社会语境”看,应将该词译为“国家理性”而非“国家理由”。不过,他也指出,大多数中文论者均将该词译为“国家理由”。见周保巍:《“国家理由”,还是“国家理性”?——三重语境下的透视》,载《读书》2010年第4期。
[6] [7] 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4~75;85页。
[8] 在当前中文论著中,梅尼克或被译为迈内克,马基雅维利或被译为马基雅维里,本文采用更普遍的译名,但在引用中文文献时则据其原译。
[9] [10] [11] 弗里德里希·迈内克:《马基雅维里主义》,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51;66~67;86页。
[12] 爱德华·露西-史密斯:《世界工艺史》,朱淳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31页。
[13] Carlo M. Cipolla, Clocks and Culture, 1300-1700,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3, pp. 15~16.
[14] [16] 培根:《新工具》,許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8;64页。
[15] [17] Joel Mokyr, A Culture of Growth: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Economy, p. 98;p. 84.
[18] 培根:《培根随笔全集》,蒲隆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51页。
[19] 托马斯·孟、尼古拉斯·巴尔本、达德利·诺思:《贸易论(三种)》,顾为群、刘漠云、陈国维、吴衡康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6~37页。
[20] [21] M. Beer, Early British Econom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p. 158~159, p. 160.
[22] [23] 弗朗斯西·培根:《英王亨利七世本纪》,王宪生译,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年版,第131;143页。
[24] 配第:《配第经济著作选集》,陈冬野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8页。
[25] [26] [27] William Ashworth,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State, Knowledge and Global Trade, p. 28;p. 77;p. 113.
[28] [29] [30] [31] [32] [33] 查尔斯·达维南特:《论英国的公共收入与贸易》,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01~309页。
[34] 大卫·阿米蒂奇:《现代国际思想的根基》,陈茂华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4页。
[35] [36] [37] [38]亚当·斯密:《国富论》,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436;436~437;495;467页。
[39] 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周洁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94~95页。
[40] 近年来,关于西方国家发展工业在思想层面与政策层面的言行不一,国内外已有较多论著。比较系统的梳理可参考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肖炼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41] 曼昆:《经济学基础》,梁小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