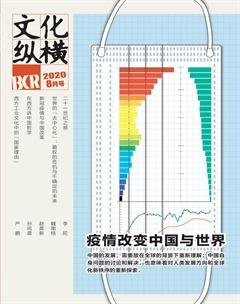城市病是一种什么病?
谭纵波
所谓“城市病”
20世纪80年代后期,“城市病”(有时也被称为“大城市病”)这个情绪化、拟人化的表达词语出现后,就被广泛应用到了媒体、专业论文乃至政府文件中,形成了汉语语境下的一种独特表达方式。[1]它指的是“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交通拥挤、住房紧张、供水不足、能源紧缺、环境污染、秩序混乱,以及物质流、能量流的输入、输出失去平衡,需求矛盾加剧等问题”[2]。学术界更倾向于把城市“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城市贫困”等问题归结为“城市病”。[3]也有的将其归结为“自然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交通拥堵”“生活成本上升”“公共资源供给失衡”“公共安全事件频发”等更加宽泛的范畴。部分社会学研究者也把“城市冷漠”“青少年问题”“乞丐”等也归入“城市病”的范畴。[4]更有甚者,有人把“狗患”“空巢青年”等现象也作为“城市病”一股脑都算在城市头上。[5]
本质上,“城市病”是伴随城市化,城市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大城市的出现而产生的。西方国家对伴随城市化所产生的城市中的一系列问题采用了一个更为中性的名词——“城市问题”(Urban Problems)。它与我国“城市病”的话语有明显差异:首先,针对工业化和城市化不同阶段所出现的城市问题进行论述,而不是笼统地作为一种抽象的问题,例如早期工业城市的城市问题主要集中在劳工阶层生存环境、城市基础设施不足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公共卫生等方面,而被我们称为“城市病”的交通拥堵、空气污染、房价上涨、公共服务不足等问题则是到20世纪80年代才作为主要城市问题提出来的;其次,城市问题的着眼点更多聚焦于生活在城市的社会问题上,如贫穷、暴力犯罪、无家可归等,而“城市病”更多提及的是城市空间和设施问题。[6]换言之,城市问题本质上是“人”的问题,而不是城市的问题。
从以上的区别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如何看待城市问题的基本思路:其一,城市问题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不同的发展阶段乃至不同城市的问题都有可能存在差异,讨论问题须界定范围,并具有针对性;其二,城市问题源自人类的活动,通过城市中的某些表征体现出来,所以解决城市问题归根结底是要解决人的问题;其三,即使认识到城市问题是由人类活动而引起的,仍有必要区分达到城市问题程度的原因是否是由城市这种特定的空间形态所造成的?还是一种人类活动的普遍性问题。有了这个看待城市问题的基本框架,就可以具体来看一看城市问题是如何产生的,以及怎样才能缓解这些问题。
“成长的烦恼”
如果一定要用“城市病”这种拟人化的方式来论述城市问题的话,笔者更愿意将被称为“城市病”的种种现象称为“成长的烦恼”。事实上,即使一个健康的有机体在其成长过程中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烦恼。一个人在婴儿时代大约只需要完成三种本能的行为:会吃、能睡、不无故哭闹,就会被视为是完美的。但是好景不长,一旦他到了进幼儿园的年龄,也就意味着好日子结束,开始进入了被各种“问题”和“烦恼”包围着的日子。进好的幼儿园需要竞争,与小伙伴需要比拼智力和才艺,入小学、小升初、中考、高考,一路下来,要求越来越多、越来越高,问题涌现,烦恼不断。这还没有完,大学毕业即便不考研也要步入社会,参加工作,恋爱、结婚、买房、生娃,没有一件事是可以轻轻松松搞定的,哪一件事情没有做到位,抑或只是没有达到预期,都会被当成“问题”而受到他人的指责,也许是自责。所以,人的成长必然伴随着烦恼,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正常的人绝不会因为出现问题而拒绝长大。
“城市问题”也与之类似。“城市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是大量的人类活动聚集在一个异常狭小的空間中所产生的各种不适及其连锁反应。“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住房紧张”“公共服务不足”等问题皆是如此。随着人类聚居点规模的逐渐扩大,从小型村落到集镇,从城市发展为大城市,进一步成为特大城市、超大城市、都市连绵区,城市问题正是伴随着城镇规模的扩大而出现,并愈加多样化和复杂化。
那么,为什么人类给自己创造了这么一个问题繁多、看上去并不适合生存的聚居形态呢?在笔者看来,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效率”。城市产生了社会分工,带来了生产的规模化效益,促进了技能和知识的传递、积累乃至创新,并使得开展大规模社会组织行为、实现共同目标成为可能,同时也使得个体生活的多样化选择成为可能。人类的城市史正是这样一个不断追求生产效率的自然演进过程,而城市问题则是发展的必然代价。
“生态城市”的悖论

大量人类活动聚集在狭小的空间中,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种种“城市问题”
既然聚居规模的扩大会带来负面效应,那么有没有办法在聚居的正负效应之间取得某种平衡呢?20世纪70年代起,对现代城市的批判逐步演化出一系列“另辟蹊径”的规划理论,“生态城市”就是其中的代表。[7]虽然“生态城市”也承认城市的资源和能源使用效率要远比郊区或乡村高,但其主导思想仍是希望城市可以融入自然。在“生态城市”之后,“绿色城市”“低碳城市”“景观都市主义”“生态都市主义”等类似的概念不断出现。然而,这些理论通常存在三个致命的软肋:第一,无法提供与其批判内容相对应的解决方案;第二,任何利用自然力量来解决城市问题的方法均需要付出占用更多自然空间的代价;第三,缺少具有说服力的实践案例支撑。以“生态城市”为例,首先,“生态城市”的12项原则只是一些局部的改善和仅存于设想中的对策,仍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城市与生态系统间的冲突和矛盾;其次,这种过分依赖自然力的“生态城市”由于占用了更多的空间,实际上对生态系统的破坏更大;最后,“生态城市”好像举不出太多被实践证明成功的案例。从阿布扎比的马斯达,到上海崇明岛上的东滩,理念可以很完美,规划设计也可以很酷炫,但建设工程的停滞和项目流产反而证明了“生态城市”的理论是无法普遍付诸实践的。
那么怎样才有可能破解城市与生态系统的矛盾?其实答案很简单,就在城市本身,或者说城市的发明和发展虽然在主观上是为了追求效率,但在客观上却形成了有利于生态系统稳定的模式。在城市人口规模一定的前提下,相较于“生态城市”所提倡的低密度、富绿色的空间模式,其实圣吉米尼亚诺(San Gimignano)那样的中世纪欧洲城镇和纽约等现代大都会才是更加“生态”的聚居模式。格莱泽的《城市的胜利》[8]、陆铭的《大国大城》[9]都在试图证明这一点。从个体角度看,人们看似悲惨地被局限在拥挤的城市里,忍受着诸多的“问题”,但无数个体选择的集合却在客观上形成了较为合理的人类居住模式。与其他形态比较,城市在整体上仍然是解决人类生存与生态系统之间矛盾的最佳方案,可以说是一项“有瑕疵的成就”。

圣吉米尼亚诺这样拥挤的中世纪城镇,其实比生态城市更加“生态”
“城市恐惧症”
在演化史上,食物链高端的动物通常繁殖能力较弱,不同物种之间总是趋于相对平衡的状态。但人类是一个例外。无论是数万年前采集和狩猎时期对大型哺乳动物的灭绝式捕杀,还是刀耕火种的农业对原有生态的毁滅性破坏,直至工业革命开始大规模开采亿万年积累下来的化石能源,人类在不断打破生态系统平衡的同时,种群的数量也在持续增加,远远超过了维系种群延续所需的规模。城市正是为了容纳这一物种的庞大人口而出现的。
虽然城市及其雏形已伴随着人类存在了数千年,但是聚集了上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却是工业革命之后的事情。人类面对从未经历的现象和问题难免产生心理上的恐惧,进而加以否定和排斥。历史上,空想社会主义者所提倡的“新协和村”(Village of New Harmony)就是面对工业革命后城市问题开出的一剂乌托邦式药方。霍华德提倡的田园城市虽然在城市规划理论界被奉为圭皋,但究其本质或多或少也透露着作者对大工业生产时代大城市的忧虑和逃避。
由于我国长期处于专制的农业社会,在近代既没有经历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没有发生工业革命这种原发性的社会变革,对城市这种聚居形态既无原生的现实需求,也缺少系统和全面的认知,潜意识里仍将城市作为传统社会的统治中心,与乡村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10]即便是新中国成立后,对城市的认知依然停留在“消费”与“生产”相对立的观念中。[11]“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适度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原则一度被列入1989年颁布的《城市规划法》,直至2007年。可见,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传统社会对大城市有着天然的恐惧和由此而生的抗拒。
事实上,“城市问题由城市规模过大而引起”这一判断本身就存在争议。施益军、陆铭等学者的研究发现:无论是“城市病指数”还是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均与城市的人口规模无明显的相关关系。[12]英国物理学家杰弗里·韦斯特(Geoffrey West)更是基于对统计数据的分析告诉我们:在相似的社会背景下,城市的规模越大,其所创造出的人均财富和创新越多,所需要的人均基础设施越少。当然,该研究也没有回避犯罪数量和传染病传播率也同样是人口规模的1.15次幂。[13]
可见,人类出于对未知事物的本能恐惧,凭直觉判断而得出的对“城市病”病因的诊断,事实上是不可靠的。在着手解决城市问题之前,人类首先要解决自身的“城市恐惧症”。
城市问题的对策
既然我们知道了形成城市问题的原因一部分与城市人口规模有关,而另外一些则关系不大,那么解决城市问题就有可能对症下药。首先,对于犯罪率和传染病等与城市规模成正相关的问题,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降低城市人口的规模。理论上,限制甚至疏解城市人口就可以缓解这些问题。但是这种方法会带来另外多个新问题,一是分散的人口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更大;二是无法享受大城市所带来的经济、创新及基础设施的高效。同时,还要承担限制人口的道义负担。显然,如果仅仅是为了解决犯罪率与传染病传播率这些问题而限制城市人口的话并不是一个理智的选择,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本末倒置、因噎废食的思维方式,或可称为“城市病”的“休克疗法”。与之相反,采用技术和管理上的手段将这一类的城市问题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或许是一种更为明智和现实的“保守疗法”。[14]
另一方面,类似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已被证明与城市人口规模并非成明显相关关系的问题则涉及另外一个与城市密切相关的话题——城市治理能力。虽然限于本文的主旨和篇幅不在此展开来论述,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对这一类的问题,单纯依靠限制或强制疏解城市人口规模是无法解决的。
城市规划大概是社会治理工具箱里面最容易、也最频繁被想到用来应对城市问题的工具。起源于公共卫生政策的近代城市规划也的确扮演了缓解城市问题,帮助实现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角色。但在现实中,城市规划的角色又时常扮演着“背锅侠”和“万能药”的双重角色,许多严肃的论文都会将城市问题的产生原因归结为“规划不合理”,但同时在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时,又将“合理规划”作为重要的手段,仿佛只要规划做好了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但事实上,城市规划只是城市治理政策工具的一种,城市问题的解决,还取决于城市规划之外的多种因素。仍以城市的人口规模为例,虽然目标年限里的城市人口规模通常是城市规划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时还会为此开展专题研究论证,但有多少时候这个人口规模是由城市规划专业人员客观测算出来的,又有多少时候是由包括政治决策在内的其他因素所左右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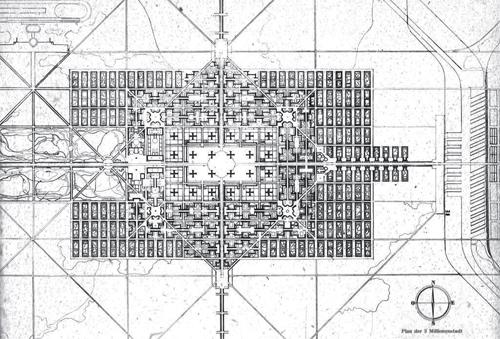
城市规划应该顺应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不是追求英雄主义的宏大叙事
城市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它很大程度上遵循着市场规律。而由于市场不是万能的,需要代表公权力的政府使用诸如城市规划的政策工具对市场的失灵部分进行纠偏,因此城市规划的基本态度应该是把握并顺应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纠正明显的“市场失灵”部分,而不是越俎代庖、想象着完成英雄主义的宏大叙事。具体而言,城市规划一方面为包括城市开发在内的各种利益的博弈提供了一个相对公正的平台,并监督、执行博弈的结果;另一方面,城市规划是政府利用税收等财政收入为市民提供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引导城市发展的蓝图。由此可以看出,按照客观规律合理编制的城市规划在整体上一定是顺应城市发展的需求,并通过对规则的执行和公共产品的提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部分城市问题的严重程度,而非主观意愿的强势推进,也绝不是治疗“城市病”的“万能药”。
现代城市中存在的问题,形式多样,成因复杂,不宜笼统地将其称为“城市病”。這种笼统的称谓或许无意中掩盖了某些因果关系,久而久之形成错误的思维定式。城市问题的缓解,需要建立在尊重城市发展与运行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人口规模大、建筑密度高是城市的宿命,也是城市的优势。限制城市人口规模乃至疏解城市人口的方法无助于从根本上消除城市问题,甚至可能适得其反。或许,城市问题本身不是“病”,而对城市与城市问题认知的误区,以及城市治理能力的不足才是“病”。
(责任编辑:王儒西)
注释:
[1] 较早使用“城市病”这一名词的论文,如吴复民:《医治“城市病”的关键何在?》,载《瞭望周刊》1986年第28期。
[2] 邓伟志:《社会学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
[3] 参见石忆邵:《中国“城市病”的测度指标体系及其实证分析》,载《经济地理》2014年10月刊。
[4] 陈哲、刘学敏:《“城市病”研究进展和评述》,载《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2年1月刊。
[5] 参见《当狗患成新“城市病”》,载《三秦都市报》2017年07月30日;《空巢青年盛行也是“大城市病”》,载《中华工商时报》2017年04年12日。
[6] 诺克斯、麦卡锡:《城市化——城市地理学导论》,姜付仁、万金红、董磊华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
[7] 瑞吉斯特:《生态城市——重建与自然平衡的城市(修订版)》,王如松、于占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8] 爱德华·格莱泽:《城市的胜利——城市如何让我们变得更加富有、智慧、绿色、健康和幸福》,刘润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
[9] 陆铭:《大国大城——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与平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10] 费孝通先生在描绘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城乡关系时说:“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乡村和都市(包括传统的市镇和现代的都会)是相克的。……乡村没有了都市是件幸事,都市却绝不能没有乡村。”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11] 建国初期在讨论北京未来建设设想时提到了须遵循“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的方针。参见北京建设史书编辑委员会编:《建国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内部资料,1986年。
[12] 施益军、翟国方、周姝天、刘宏波、鲁钰雯:《我国主要城市的城市病综合测度及特征分析》,载《城市研究》2019年2月刊;陆铭、李杰伟、韩立彬:《治理城市病:如何实现增长、宜居与和谐?》,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9年1月刊。
[13] 杰弗里·韦斯特:《规模》,张培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
[14] 例如大数据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公共卫生和犯罪预防等城市管理领域,参见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盛杨燕、周涛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