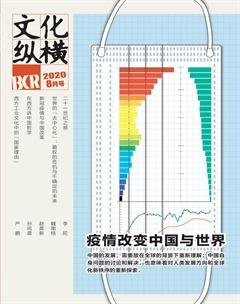本土传统慈善文化的价值与反思
一、“慈善”界定及研究困境
中国本土善行义举资源丰厚。自清末引入“公益”和“慈善事业”词汇以来,经民国激荡接续,再至改革开放前30年的官办化、贬义化和后40年借鉴与发展,本土慈善事业跌宕起伏。“慈善”概念至今仍很模糊。甚至《慈善法》立法者所面临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界定慈善。最终,立法者将扶危济困赈灾等传统慈善事业称为狭义慈善或小慈善,将包括小慈善以及促进教科文卫体等增进社会公共利益在内的活动称为广义慈善、大慈善或公益,[1]并把现代组织化慈善作为该法的基础,将互助互济以及慈善组织以外其他组织开展的慈善活动放到附则之中。
鉴于这种既按领域又按组织分类的不周延性,笔者从组织唯一标准出发,将面对面的赠予以及小地域共同体范围内各种组织的施善称为基础慈善或传统慈善;各领域内按现代非营利组织[2]运作的活动称为组织化慈善或现代慈善。前者带有更强的地域性、文化性、多样性、特殊性和非正式性,后者则强调组织标准的相对普遍性、管理的规范性和正式性。
《慈善法》的重心显然在后者。然而,从2016年9月1日该法实施后的效果来看,社会组织对认定“慈善组织”的热情并不高。该法精心设计了社会组织—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募平台的制度,但民政部和中国慈善联合会在2016~2018年统计结果均显示,社会组织接受捐赠总额并未大幅增加。例如,被视为现代组织化慈善主力军的基金会接收捐赠分别为625.5亿元、658.04亿元和645.88亿元。那么,基础慈善状况是否更为糟糕?若否,将证明本土慈善文化别有价值,进而深化我们对慈善的理解。
叩问慈善的文化之根,是在探索人类同情文化多样性基础之上实现慈善自觉的根本途径。然而,在交流频繁并相互借鉴的当下,寻找慈善文化基因的道路注定崎岖。基础慈善和现代组织化慈善的张力同样体现在学术研究。当前大多本土慈善史和慈善文化研究在具体历史人物、组织或空泛观念等方面取得硕果,但因缺乏社会科学概念而难以形成反哺实践的整体性理论方案。而当前更盛行的一些慈善实证研究,常因缺乏情感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导引而水土不服,甚至因刻意追求量化而陷入集体无意识之境地。为此,本文希望通过鲜活的案例研究,关注本土基礎慈善在生活世界中的象征性运用、价值与困境。为了选择组织存续时间较长、同时历史上声名显赫至今尚未消失的慈善组织,[3]汕头存心善堂就这样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二、存心善堂:一种基础慈善类型
(一)存心善堂及其发展史
明清至民初的善堂是近现代慈善的重要过渡。近代善堂虽然不能代表中国本土慈善资源的全部,却天然地保有慈善文化的因子,并饱含着中西慈善文化的碰撞与调试。19世纪中叶以后的善堂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在传统救济基础上还增加了维持政治秩序等功能。这些非传统因素导致研究难度倍增。[4]但这恰好符合笔者透过变迁考察本土基础慈善延续与叠加的用意。
该组织的前身是明末清初的一所弃婴堂。1899年,汕头暴发瘟疫,潮阳棉安善堂念佛社的大峰祖师信众恭请神像至弃婴堂设堂祈福,一时皈依者众。随后,当地二十行商在念佛社基础上发起成立存心善堂,并创建了存心义冢和存心掩埋队(1901)、存心施粥局(1911)、存心水龙局和存心善堂医院(1929)、存心小学(1942)和儿童教养院(1943)等附属机构,形成综合性善堂。1950年,善堂被认定为迷信组织,次年被政府全面接管改造。20世纪80年代善堂开始复苏,90年代初,一些曾在民国时期受到善堂恩泽的老者在善堂旧址旁行善。渐具规模后,存心善堂慈善会成立。1996年,该组织再度被撤销。[5]2001年,经市民政局批准,该组织成为市慈善总会分支机构,对外名曰汕头慈善总会存心善堂福利会,并渐次成立了念佛社、存心慈善医院、养老服务中心、爱心免费快餐厅、义工队、文武学校、特教学校等机构。2009年,该组织以汕头存心慈善会为名独立登记并使用至今。此后,陆续兴建了存心陵园、存心残疾人工疗站、存心安老庇护院等。该组织虽名称屡换,但无论碑文、组织出版物、官网还是当地人,均惯称“存心善堂”(下文也予以沿用)。[6]

存心善堂在民间信仰的强烈驱动下成立,图为善堂大殿(韩俊魁 /摄)
(二)延续与叠加
纵观存心善堂发展史,除了组织名称,不难发现存心善堂在组织形式和业务上的延续性。比如,当前官网上的组织架构[7]中有些表述仍大致沿用民国时期的旧称,如民国时叫交际股、法事股,现在称交际部和法事部;儿童救助、养老、陵园、医院等业务板块也几乎如出一辙。此外,从组织业务和组织宗旨[8]都能看到存心善堂综合业务特征的延续性。这些业务均为基础慈善,因为和大型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综合项目群相比,善堂综合业务不仅缺乏现代项目管理制度,业务之间也缺乏逻辑关联。
从“不可见”的文化角度来看,存心善堂的延续性依然清晰可见。
存心善堂在民间信仰的强烈驱动下成立,这一信仰具有弥散性、复合型特征。其最早施善的领域是义冢和掩埋。这种善举可溯至古老的传统。[9]该组织至今仍有火化设施和陵园,百年来收尸逾百万具。很多当地民众甚至政府部门发现无主尸骸时,第一反应就是通知善堂前来收尸。我们甚至发现政府部门请善堂收尸的函件。由此可见这一观念烙印之深。今天的现代非营利组织中,即使在那些致力于临终关怀的组织中也难寻这种善举的踪影。居于善堂信仰核心的大峰祖师所开创的“白衣派”大峰宗门融合了儒家伦理。19世纪中期,潮州东门善堂的释可声大和尚开启了人间面向的善门法脉。此外,善堂还供奉三山国王和华佗仙师等。这种弥散性、复合型的民间信仰使善堂被神祇香火和人间烟火所环绕。善堂收入构成折射出民间信仰文化的影响。例如,民国年间存心善堂的经济来源就包括堂前捐助、社员年费、社员进社金、吉穴捐助、柩厝寄柩、法事供款捐助等,[10]今日存心善堂的财务报表中亦常见到敬佛师收支、香油箱收入、莲花座收入等科目。总之,民间信仰为善堂“预装”了使命,并赋予组织以坚韧的生命力,故善堂在被迫两次停止活动又能很快重生和壮大。信仰驱动的捐款具有稳定性特点,捐款额和信众数量一般存在正相关关系。

存心善堂在组织形式和制度上均有延续性,图为善堂正门(韩俊魁 /摄)
然而,因为鲜明的地域性、民俗性、民间性和多神崇拜等特点,善堂慈善文化又表现出相对封闭性的特点。和历史上的民办义仓和义庄相比,善堂要开放得多。位于经济中心的善堂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原籍地收养主义,并超越了宗族和狭小地域之限制。[11]例如,民国时期的存心善堂基本在汕头中心活动,只在乡镇层级设了一个办事处。这与社会转型时乡居地主向城居地主的转变密不可分。但这一转变并不彻底,因为1921年广州市区从南海县分离出来之前,中国的城市从未独立地以政区的面目出现。[12]所以,这种开放性又受地域性的信仰、语言和宗族文化影响,表现出一定的封闭性。
和现代非营利组织的外向交流与合作不同,今天的存心善堂业务基本在本地,外出交流也多限于同根同源的海内外善堂。与清末民国善堂多在经济中心活动不同,存心善堂近年来一个明显的发展趋势是向基层发展并使之网络化。办事处已在濠江、澄海、潮阳等地生根。同时,存心善堂从2007年开始在乡镇建设义工队,并多采取为既有义工队冠名并让其缴纳会费的方式形成庞大的松散联盟,义工队最多时达330支。
总之,在成立之初,众商贾能跳出狭小乡土格局,且因地处通商口岸而受到基督教、天主教影响,但善堂文化仍难开显出超越性。
我们还可以从会员制看到显著的内敛性。民国时期的《存心善堂组织章程》规定,只要持身清白、热心慈善、赞成善堂宗旨并经两名社员推荐、审核后即成为社员。[13]同时又规定:凡社员逝世,其社员资格由其法定继承人继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与会员资格绑定的会员福利制度。例如,社员福利仅包括其家属丧故时,得享善堂礼忏及社员之祭吊或执绋。也就是说,其会员制的内敛性使其带有浓厚的互助色彩。
按理说,现今的存心善堂并非基于会员制的行业协会或商会类社团,其互助性应当较弱。但令人惊讶的是,其互助功能反而日益增强。2004年,会员福利扩展到15项,除殡仪服务,还有免费体检、托养、教育、医保自付部分补贴等。2020年合并为8项,但主要内容变化不大。基于这种文化基因,2012年起,存心善堂拿出部分会费为会员办理意外险、疾病险和身故险的做法就不奇怪了。这种做法比国内很多基金会开展的保险项目起步要早,但不同的是,前者的受益对象是会员,呈封闭性特点;后者的受益对象是不特定的救助对象,呈开放性特点。这种内敛性互助文化使善堂会员数量和会费收入快速增长。
另一个重要的延续性特征是,存心善堂在很多业务中坚持古老的款物使用而非占有原则。[14]例如,义工队和办事处开办免费凉茶点,免费为户外工作者及过往市民发放茶水等。笔者就在善堂门口目睹路人无须任何登记而免费领取面包牛奶的场景。义工队的收入来自义工月捐、日捐以及企业赞助等。收入由义工队支配,无须上缴存心善堂,主要用于义工队所在镇域的扶危济困。义工队不断随访鳏寡孤独,并赠之以粮油等用品,所有票据账单及发放情况由义工在微信群晒照片为证即可。义工没有补贴。也就是说,其服务“成本”由纯粹志愿服务而化之于无形。多年来,国内围绕做慈善是否有成本而颇多争论。其实,持有成本者是用逐利原则中的“成本”一词定义使用原则下志愿付出的时间、技术等。而在基础慈善中,使用原则支配下的慈善的确“无偿”。
总之,无论组织名称、组织形式、制度还是慈善文化,存心善堂都表现出极强的延续性。近年,除了组织向基层发展而内敛性趋势明显,以及随着会员福利不断扩大而组织的互助性增强,该组织最大的变化要属互联网众筹了。存心善堂2016年和轻松筹合作发起存心筹,并在官网开设“在线求助”专栏。这改变了以往面对面求助或由义工主动寻找弱势群体的工作模式,求助者被迫“主动”地、无尊严地在陌生的互联网世界展示各种细节以获取更多帮助。于是,被救助者从社区中脱嵌而出,面对面构建社会资本的方式被打破,还透支了传统慈善资源。例如,存心善堂2009~2017年的捐赠总收入呈上升趋势,尤其是2016~2017年捐赠从26473283.90元攀升至2017年的47547614.32元。其中,敬佛(师)活动收入、香油钱等增幅不大,最大增幅来自存心筹。将这部分从捐赠总量中剥离出来重新统计,会发现自从存心筹上线以来,除了敬佛、师活动收入之外,其他收入都明显下降。[15]
由上看出,存心善堂鲜明的本土基础慈善特征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中[16]变化不大,尽管组织在适应外部环境时叠加了一些新内容。
三、本土基础慈善的可能洞见
经过上文考察、分析,我们可以将存心善堂的特征总结为民间信仰驱动型、志愿性、内敛性、网络结构松散和专业性弱。[17]笔者发现,存心善堂的组织结构与明茨伯格论述的使命式(Missionary)配置方式[18]惊人地相似。
不同于简单结构、机械式官僚结构、专业式官僚结构、事业部制结构以及变形虫结构等配置方式,使命式配置方式的组织特征如下:(1)有强大的信念体系和道德规范。这可以驱动组织开展激动人心的任务,但也存在根深蒂固的不灵活性。(2)结构松散。(3)劳动分工不清晰。组织规模要想扩大,就须将自身分为更小的单位。(4)几乎不存在任何直接监督以及工作输出和技能的标准化。明茨伯格得出一个令人振聋发聩的结论,他认为,这种在西方从未风行过的使命式配置方式将在有效的组织构成中占据重要地位,并注定流行开来。
仅仅接近或相似而已!然而,即使相似性,也足以驱使我们思考存心善堂案例所蕴含的理论价值。那么,这些用于企业组织或许更为妥当的判断是否适合慈善和慈善组织呢?
还是继续从慈善史中去寻找灵感吧!慈善(charity)不管在古拉丁语还是基督教传统中,本体意义就是爱(love),当然比love的文化意义要复杂得多。现代组织化慈善运动在启蒙运动后期才形成。在号称“仁慈时代”(Age of Benevolence)的18世纪及19世纪初,社团的时代终究来临:在英国,几乎所有人都加入了某个协会(association)。[19]这些组织的存续主要依赖筹集款物,尤其是志愿服务。基礎慈善与现代组织之间张力的真正凸显是在稍后的19世纪下半叶。
一百多年过去,现代组织化慈善似乎成为公理般的存在,然而什么是慈善却日益模糊。20世纪90年代,萨拉蒙等开展的一项跨国比较研究发现,收费收益和政府资金在非营利部门的总资金中分别占53%和34%,包括个人、基金会和公司等捐款在内的私人慈善占比仅为12%。只有将志愿服务时间折算在内,私人慈善在非营利部门12个领域的7个之中才能成为收入的第一大来源。[20]萨拉蒙曾在更早的一项研究中对私人捐献(private contributions)的重要性进行辩护:“私人捐赠(private giving)在非营利组织的收入中份额虽少,但任何危及它(的行为)都意味着动摇非营利部门之本质。”[21]然而,他并未从正面解答之所以重要的真正原因,而是借助托克维尔式的非营利部门之逻辑先行及非营利部门与政府在公共目标取向上的契合性,主张政府扩大资助,防止商业化和收费收益比例攀升带来消极后果。与此不同,佩顿等认为,这种管理的路径显然忽视了慈善本质。只有从人文视角,优先考虑志愿服务,才能保证非营利部门必要的可辨别性(distinctiveness imperative)。
这样一来,佩顿等将萨拉蒙的“私人慈善对保证非营利部门独立性至关重要”这一命题转换为道德和政治参与命题,即慈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与每个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22]换言之,如果没有仁慈、爱邻里、公民性、宽容等美德,如果忘了非正式慈善所呈现出个体性、日常性、体验性等特征,就无法真正把握慈善本质。仅凭统计数据,只会产生私人慈善日益萎缩的错觉。佩顿等人进一步推论:“组织化慈善(organized charity)比民主和资本主义更为悠久,要早于基督教、佛教,甚至要早于那些消失在历史之中的社会和传统。”[23]如果该说法不是略带夸张的话,这里的组织化慈善其实是指更具本体性的基础慈善,而非现代社会的组织化慈善。

近年,存心善堂的互助功能日益增强,图为存心慈善医院(韩俊魁 /摄)
这给认识存心善堂的价值提供了一种视角。存心善堂在民间信仰的驱动下,其使命感、组织的稳定性和公众参与的志愿性都很强。和其他类型的组织相比,没有高度专业化和科层化的存心善堂反而印证了人际关系学派的观点。由于信仰驱动所产生的强烈志愿性,以及保留着古老的财物使用原则,所以人与人的关系优于人和物的关系。义工队这种基础慈善恰恰成为慈善的沃壤。面对面的志愿服务和古老的互助传统相得益彰,在生活世界中充满活力。与此相比,明茨伯格所说的简单结构组织风险更高,因为难以将个人追求有效转化为组织使命。许多个人精英创办的草根组织所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难题已证明了这一点。
再反观所谓现代组织化慈善。现代非营利组织似乎更能提供规模化绩效,但也不免丢掉了慈善的本质。在提供所谓专业服务的同时,其运作成本也随之增加。因此,“慈善有成本”这种现代说辞在不断否定基础慈善无“成本”古训的同时,也为了招徕更多捐赠者而不断借用这一古老的修辞术和志愿服务,以压低行政成本。于是,鼓吹慈善专业化和倡导人人慈善这对看似矛盾的现象出现了。然而,无论多么鼓吹慈善专业化的人也不敢反对“人人慈善”这句更具本质性的响亮口号。当慈善最核心的要素——志愿服务开始用并不炫目的服务小时数以及折算后的金钱精心打扮,并以专业志愿服务的名义吆喝自身存在价值的时候,慈善选择了一种屈服的方式,仰仗货币市场和科学主义的检阅和度量。现代非营利组织尽管苦心打造了多种劝募方式以筹款,但捐款者或许仅关注自我感觉是否良好,而对这些组织是否真的帮助目标人群未必感兴趣。[24]现代非营利组织付出移山心力,试图在弱势群体的“飞地”中重建社会资本和社会保护机制,但仍像西西弗斯般止步难前。有研究者发出警示,随着现代非营利组织形式的复杂化和捐款者—受益人之间的组织链条不断延长,“捐赠者和受助者失去直接联系,慈善将失去其实践效能及道德目的”[25]。
难道基础慈善就没有不足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将未经历理性发展阶段的存心善堂作为现代慈善的标杆为时尚早。我们需要的是借鉴、转化而非简单复古。存心善堂在项目管理、成本核算、网络运营等方面同样存在风险。传统征信录的做法转化为现代慈善的信息披露和审计制度也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信仰驱动并不意味着信仰能自动杜绝一切有违教义的行为。若不汲取现代组织管理方式及其经验,小慈善实践一旦出了问题,势必反过来影响信仰。这或许是以信仰为本的慈善组织(faith-based charity organization)登上历史舞台的重要缘由。
制度性个体主义下的现代人总是处于自由选择的欢欣与难以抉择的两难之中。[26]通过人类学的并置比较发现,我们需重新赋予基础慈善以意义和价值。慈善组织化似为当下潮流,但若缺乏对多样化的本土基础慈善文化的洞见与借鉴,就会遇到开篇所说的挑战。幸亏,《慈善法》第110条和第111条留下可以发挥的空间。慈善在未来是否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空间如何深化和拓展。
(责任编辑:张文倩)
注释:
[1]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内务室:《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第15~19页。
[2] 本文对“社会组织”“非营利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未加区分。
[3] 这里的“慈善组织”是广义的历史概念,而非《慈善法》意义上须经认定后获得特定身份的“慈善组织”。
[4] [9]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278页。
[5] [6] [7] [8] [17]《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的一篇文章称存心善堂1995年被强制取缔,见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n/news/2010/03-19/2180337.shtml。内部印刷物《存心堂务》第136页则说1996年被政府撤销;这段简介从《存心堂务》(1899~2014)136~145页归纳而来,需注意的是,在该资料中,组织发展脉络中的一些重要细节并不清晰,甚至有出入。此不赘述。官网上的组织结构图未能反映该组织的真实运作情况,和《存心堂务》第48页的架构图也有差异;《存心堂务》第43页的民国时期《存心善堂组织章程》第三条为“本堂以博爱、和平、力行劝善、施棺、赠葬、赠医、施药以及各项救护赈济为宗旨”。官网上的表述是:“存心善堂的主要服务宗旨是,救死扶伤、赈灾恤难、赠医赠药、布衣施食、敬老安老、兴学助学、办医院、造桥梁、修路等福利事业,惠民宏愿、任务不分巨细艰易,皆尽心尽力、善始善终加以实现”;其官网中看不到组织章程、年检结果、财务审计报告、组织具体架构、分工和实体机构、义工队关系以及项目管理制度等,更看不到筹款的实时更新。我们在调研时试图获取更多信息,未果。從前文描述中,已看到不少细节不清楚甚至互相矛盾的例子。
[10]林悟殊:《潮汕善堂文化及其初入泰国考略》,载《海交史研究》1997年第2期。
[11]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 伍跃等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55,161~162页。
[12]周振鹤:《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35页。
[13]有意思的是,该章程并未明文规定社员的年龄限制。
[14]卡爾·波兰尼:《大转型》,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7~51页;路易·迪蒙:《论个体主义:对现代意识形态的人类学观点》,谷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3页。
[15]该数据来自赵小平和笔者撰写的案例,载韩俊魁、邓锁、马剑银等:《中国公众捐款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即出。
[16]其间50多年活动停滞。
[18]亨利·明茨伯格:《卓有成效的组织》,魏青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83~385页。
[19] Gertrude Himmelfarb, Poverty and Compassion: The Moral Imagination of the Late Victorian, Vintage Books,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1991, pp.3~4,186.
[20] 莱斯特·M. 萨拉蒙、S. 沃加斯·索可洛斯基等:《全球公民社会:非营利部门国际指数》,陈一梅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4~63页。
[21] Lester M. Salamon, Partners in Public Service: Government-Nonprofit Relations in the Modern Welfare Stat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68.
[22] [23] Robert L. Payton and Michael P. Moody, Understanding Philanthropy: Its Meaning and Missi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5;pp.13~14.
[24] 彼得·辛格:《行最大的善:实效利他主义改变我们的生活》,陈玮、姜雪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10~11页。
[25] Lawrence J. Friedman and Mark D. Mcgarvie, eds., Charity, Philanthropy, and Civility in American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48.
[26] 乌尔希里·贝克:《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张文杰、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