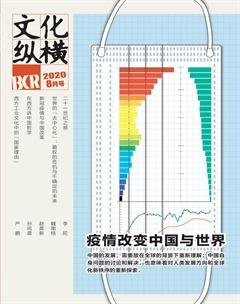在西方讲中国哲学
孙向晨
[文章导读]
如何向世界诠释中国,是今天中国思想界难以回避的重要问题,但如何在当代世界语境下确立中国思想的价值,却是一个难点。中西思想有着截然不同的传统,建立在相互尊重与欣赏基础上的中外交流对话,既要避免以“西方中心论”弱化自身的主体性,又不能陷入“中国中心论”的自说自话,这就需要一种新的“中国与世界”的哲学思想。
本文作者通过在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讲授“中国哲学”的经历,对中国哲学如何在现代语境和西方思想框架中建立自身的叙述主体,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当 “以西释中”“以中释中”两種常见策略都已不足以改变西方人难以理解中国哲学的困境时,作者提倡对中西哲学作“框架性的对比”,回归中国价值自身的根本框架,在坚守中国思想传统主体性的前提下,面对现代性,面向世界,从自身思想传统中发展出制衡现代世界缺陷、开辟未来可能性的思想力量,进而构建起当今中国哲学的世界意义。
在欧洲,一般讲授中国思想的课程都只在汉学系或者中国学系(China studies)开设。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近年来倡导“全球哲学”的理念,颇有前瞻地引进了“中国哲学”“印度哲学”“非洲哲学”等课程。2019 年 9月,笔者受德国 Cluster of Excellence SCRIPTS- Contestations of the Liberal Script 和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 Stefan Gosepath 教授与 Hans Feger先生的邀请,在 2019~2020 年冬季学期开设了一个学期“中国哲学的现代阐释”课程。
这样一门主要针对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讨论课,究竟能有多少人来听课,笔者并没有把握。毕竟在大学里 3~5 个人的讨论课比比皆是。一个学期下来,听这门课的人始终保持在 25 人左右,至少说明德国同学有了解中国哲学的热情。尽管只上了一个学期的课,在欧洲大学哲学系讲中国哲学,笔者还是有颇多感受:这其中既有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异,又有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更折射出在现代语境下探寻中国哲学意义的复杂性。
汉学系,抑或哲学系
同样一门中国哲学的课,在哲学系与在汉学系(或中国学系)开设究竟有什么不同?
事实上,这背后有很大的差异。对于德国学生来说,当他进入汉学系学习中国思想传统或者中国哲学时,已经预先准备接受一种异质文化;在他的知识框架中也会为这种异质性预留一个空间。他愿意将一些在日常中不太理解、不太能接受的内容,纯粹作为一种异域文化的概念接受下来。在这方面,西方世界有很强的传统。西方不仅有悠久的汉学(sinology)历史,也有卓越的埃及学、巴比伦学、希伯来研究以及印度学等学科,形成了非常优秀的非西方研究的传统。但这些学科比较偏向于古典学研究的范畴,偏重古代语言与历史文献的研究。现在,许多西方大学的汉学系改为中国学研究(China Studies),更偏向于区域文明与国别研究,这一名称的改变,背后是范式的转化,会带来研究上的新变化。但总的来说,这样一种局限在某个区域或国别的系科,更多地受到其他学科包括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影响,在现有大学的学科体系下并不具有主导性。

哲学在西方是独一无二的,至今仍有很多西方人认为哲学是单数的
当“中国哲学”这门课是在哲学系而不是在汉学系(中国学系)开设时,它进入的是主流系科,遇到的挑战会更大。它所预设的学生的学术背景就与汉学系大不一样。在这里,学生首先看到的是“哲学”两个字,其次才是“中国哲学”。狭隘意义上的“哲学”来自古希腊(海德格尔曾说过“哲学讲希腊语”),西方传统中形成了非常独特的“哲学式”运思方式。哲学在西方是独一无二的,时至今日,在西方很多人依然认为哲学是单数的。当中国的思想传统以“哲学”的名义进入西方大学哲学系时,“哲学”也就成为某种复数的概念。学生们之前所受到的哲学训练,自然也就成为一种质疑与批判“中国哲学”的力量。在上课时,笔者就遇到了各式各样的质疑与挑战。比如,有一位德国女博士生在一次课上就激动地站起来提问:儒家学说中充斥了圣人、君子、小人等等级性观念,在《孝经》中也满是这些等级性的思想,显示了巨大的保守性,把这些与西方哲学传统相比较有意义吗?在现代世界再来讲授这些内容还有价值吗?除去这种带些情绪化的表达,学生们更多的反应还是具体的困惑:比如如何定义“卦”?“卦象”为什么能解释我们周围的世界?“象”究竟是什么?怎么来界定“阴阳”,为什么会有“否”与“泰”之间的变化而不是一种直线变化?具体怎么来评判“中庸”,“中庸”的标准是什么?很多文献的论述不是一种“论证”而是像诗歌语言一样充满跳跃,没有规范性的解释似乎什么都能解释,这还有意义吗?在德国大学教授中国哲学,遭遇这样的场面,实属情理之中;如果得到一片认同与喝彩,反倒是要令人生疑。无论是博士生在课堂上的情绪化表达,还是学者们在学术会议上的学术化表达,本质上都反映了一种对“中国哲学”的疑惑。在西方大学言说“中国哲学”的真正挑战在于,“中国哲学”在什么意义上是一种“哲学”?在什么意义上,这种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
西方学人的“前见”及其演变

真正的挑战在于,“中国哲学”在什么意义上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一种“哲学”
在西方语境下,谈起“哲学”会有其固定范式。在西方主流看来,哲学是一门非常专门的学科,专指西方哲学。黑格尔对于孔子的评价,已经透露出某些端倪。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中说:“在孔子与他弟子们的谈话里面所讲的只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能找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能找到,可能还要更好些,这是些毫无出色之处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教训,从里面我们并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我们根据他的原著可以断言: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言下之意,孔子的学说根本算不上什么哲学。原因很简单:孔子的哲学似乎没有一个形而上学的框架,更不是一种体系性哲学。
黑格尔对于孔子的评价多多少少反映出西方哲学对于中国哲学的看法。尽管今天在西方哲学界,这种充满赤裸裸偏见的话也许不会再有。但自近现代以来,哲学也进入了某种学术工业化的形态,有着非常专业化的分工。从积极的角度讲,这是一种讲究规范的研究。比如,现在研究正义问题,基本上都会从罗尔斯的范式开始,然后一步步拓展出去,有研究全球正义的,有研究环境正义的,有研究代际正义的,等等;从消极的方面说,一旦形成某种范式,范式本身常常就成为某种非反思的构架了,很多思想资源与传统,在这样的学术框架下就很难进入西方主流学术的视野。于是,西方学术就形成了一系列的内在规范,也形成了自己认为天经地义的坐标。在这个前提下,任何非西方主流范式的思想、方法、路径突然闯进来,就会让人觉得相当不适应。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文明体来说,其哲学框架从根本上说就是不同于西方的,那么讲“中国哲学”遭受某种形式的排斥也就非常正常。西方社会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现代性的代表,而所有非西方世界都是要迈向“现代”社会——这一说法,虽然现在认为是一种“政治不正确”,逐渐为 “多元现代性”的观念所替代,但在现实世界中,这样的思想痕迹无处不在。当中国哲学“进入”时,实际上会对西方的传统规范造成某种冲击。
伽德默尔说,对他者开放,就意味着要接受某些反对我自己的东西,接受起来也并不那么容易;虽然德里达从反对西方哲学逻各斯中心主义出发,让“中国没有哲学”在后哲学时代的语境中,似乎也不再那么刺耳。无论怎样,要在哲学系统中确立某种“中国哲学”的位置,依然是一项艰巨的挑战。
基于这样的文化背景,从学生的角度来看,就会对中国哲学传统观念持强烈的质疑态度。在学生们眼中,德国哲学传统几乎就是康德传统(中世纪哲学以及古希腊罗马的哲学传统也被隐去),康德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现代哲学的样态,因此“哲学”就被看作是论证性的,理性至上的,就应该强调个体的自主性。事实上,西方哲学传统并非从来如此,其本身也有一个古今变迁的过程。从 17 世纪西方近代哲学开始一直到当代社会,西方的传统则越来越隐到了“现代”的面目背后。从历史看,现代世界毫无疑问首先是在西方社会中确立的,以致西方社会在秉持某种“现代”理念时,也时常“遗忘”其自身的“西方”根源。因此,学生更多会以一种现代“普世”的眼光来看待某种“文化”传统,而没有意识到这种“普世”的背后,可能只是一种“西方”的眼光。因而,任何一种非西方的观念,它进入“现代”社会有多难,那么它让“西方”人理解也就有多难。
有个来自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的学生,主修哲学和物理,在柏林洪堡大学做交流生,每次都会赶过来听课。他有一种非常标准的科学化思维,对于周易的演绎性表示了极大兴趣,同时以物理学标准对周易系统提出很多疑问。但他始终对于“卦”的变化非常疑惑,认为这种“卦象”的变化没有任何理性依据,对于世界有过度解读的嫌疑。他的疑惑与质疑让人印象非常深刻。从现代科学的角度去理解周易自然会出现这些疑问,3000 多年前出现的“周易”系统是“经不住”科学拷问的;但作为一种不同于西方哲学传统的思维方式和生存经验,它揭示了某些中国人思考问题的特点,对于这种“根本性差异”的敏感可能在学习中更为重要。
作为“过程哲学”创始人的怀特海曾说过:西方两千多年来的哲学是对柏拉图哲学的注解。尽管前苏格拉底哲学中有各种流派,有毕达哥拉斯派、元素派、原子论派,也有赫拉克利特的哲学,就像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但并不是每一种哲学都在西方思想传统中起着同样的作用,真正起主导作用的是“巴门尼德-柏拉图哲学”,就像在中国思想传统中真正流传下来的是“儒家与道家”。如果以“巴门尼德-柏拉图哲学”来看,他们的哲学是以“存在”为主轴的,是以“范畴”方式来展开的。根据他们对“存在”的界定,“存在”是永恒不变的,两千年西方哲学传统就是从这个“不变”的存在为起点来理解“变化”的世界。中国哲学的传统,是以周易的“生生之谓易”作为理解世界的起点,与不变的“存在”根本不同。因此,笔者经常跟学生讲:如果要打个比方来说的话,西方哲学两千年来是对柏拉图哲学的注解,那么你们想象一下,另一个文明,如果他的哲学两千年以来是对赫拉克利特哲学的注解,那会是怎样一种情形?
因此,我们需要从根本上去了解,哪些哲学思想为这个文明提供了某种框架性思想,哪些哲学家只是提供了某种具体思想的可能性。这就要求我们在西方大学讲授中国哲学时,在懂得中国哲学主流立场的同时,还需要懂得西方哲学传统,尤其要懂得他们的“根本性思想框架”,由此才能针对性地讲解中国哲学。与西方进行对话,相比语言上的流利,更重要的是要懂得他们的思想框架。讲出自己的故事是远远不够的,能让人听得懂才是更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讲中国哲学,讲中国故事,前提是懂得听故事人的故事。只有理解接受者的视域,你的讲解才可能是有效的。
除了西方哲學传统的根本性框架,西方基于自身的立场,面对中国思想时存在着三种模式:第一种是黑格尔式的,背后有着强烈的“哲学”标准,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都是以西方哲学的普遍“标准”来衡量世界哲学。这种观念以某种潜在的方式,至今依然强烈地存在于西方各学科中。第二种是“多元”式的态度,尽量让更多声音进入西方的学术平台,颇有些“百花齐放”的感觉。但是,这种态度并不在意不同的声音以什么方式进来,不同声音究竟能发挥多大作用。“多元”常常成为符号般“政治正确”的体现。第三种才是真正具有挑战性的,倾听一种“他者”的声音,并不仅仅在于建构某种“多元”的体系,而是意识到这个“他者”有自身的主体性,有自身的逻辑。如何能够超越自己的框架去理解“他者”存在的合理性?更为困难的是,自我的框架常常是潜意识的、隐蔽的,在自以为放下的同时,依然会起阻碍作用。只有当“他者”的根基性内容能够得到澄清时,才会迎来一个真正的全球时代。
如何定位中国哲学
就现在而言,人们是如何来定位中国哲学的?在笔者看来,关于中国哲学的研究与讲授主要有两种范式:一种是“反向格义”的方式,由胡适、冯友兰开创的大致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解说中国哲学。冯友兰先生主要是从一种实在主义立场来阐释中国哲学,比如用共相殊相来理解“理一分殊”的问题。他说:“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这种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把中国的学问“选而述之”的做法,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是中国哲学研究中非常普遍的一种模式。它使中国哲学借助西方哲学的某种框架而呈现出一种系统性,但这不可避免会失掉中国思想本义的丰富性。

在现代世界,用任何理论方式解释中国思想传统都难免于“以西释中”
另一种是“以中释中”的方式。由于在现代世界,用任何一种理论方式来解释中国思想传统,都有某种“以西释中”的嫌疑,很多学者主张“以中释中”。但这种姿态在传统语境下常常形成某种“内循环”。姑且不说现代汉语已经深受西方语词影响,很难实现真正的“以中释中”;即便可以实现“以中释中”,这种保守心态很容易变成一种自我证成的形态。比如中国人读《中庸》一定会觉得很有道理,那是因为我们从小就是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很多来自《中庸》的成语、习语渗透在汉语中,这些语言实际上规范着我们日常生活。我们只是身在其中往往不知其所以然。因而重复孔子讲过什么或孟子讲过什么,很容易发现我们日常思维的来源,但这种思想史的做法,却并不能让西方人真正理解其所以然。
两种策略似乎都难以奏效。无论自己主动运用西方范畴来理解中国思想传统,还是坚持自身传统但事实上依然被动地以西方范畴来理解,这些都没有走出理解中国哲学的困境。有人建议运用“比较”方法,通过“比较”的方法来衡量中西哲学。“比较”本身也常会是一种陷阱,笔者称之为“比较陷阱”。比如中西绘画的比较,强调西方绘画是焦点透视,中国绘画是散点透视。“散点透视”概念本身是德国学者的发明,用以凸显中西绘画的差异。它看似强调了中西文化的差异,其实只要你用“透视”去理解中国绘画就已经是一种误导了。西方艺术追求“模仿”,“透视法”可以说是模仿艺术的最高境界,但中国绘画从一开始就讲究“气韵生动”,追求以形写神,重在神韵。由此可见,中西绘画完全是在不同的框架中展开的,中国绘画从来就不用“透视法”来衡量。因此,当“比较”不能彻底反思自我与他人时,就会陷入另一种遮蔽。

一种文明如果依然有活力和生命力,就一定能让另一种文明的人理解
“比较”的前提在于确立“他者”的主体性,在于理解“他者”自身的逻辑和合理性,从而在那个“真正的分叉”点上做出“比较”,而不是在“虚假的分叉”点上做出武断的判断。对于“他者”的“合理性”的理解,一如黑格尔对于西方历史传统自身的解释,在历史细节和习俗背后隐藏着某种“合理性的内容”,我们需要在现代以一种新的“合理性的形式”将其再现出来。来自“他者”的概念常常同样地被淹没在陌生性下,我们需要以新的形式将其挖掘出来。在当代讲解中国哲学,远远不是一种独白,而是需要在理解西方传统的背景下,敢于以一种“新的形式”表达出来。事实上,这一直以来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特点:朱熹与郑玄对于经典有着不同的注释,说明中国思想传统从来不墨守成规,而是敢于面对时代性的要求,给予一种新的“合理性形式”。在现代社会,一种文明如果依然有活力,依然有生命力,就一定能让另一种文明的人理解。这要求我们能突破边界,能够在不懂得中国文化的人面前,把中国思想传统的道理讲明白,讲清楚背后的逻辑,而不只是重复孔子讲过什么或老子讲过什么。正如我们一再强调的,这需要既懂得西方人的哲学方式,又能以现代方式来阐释自身传统。
由于“比较”的双方各有其主体性,因此“比较”就需要对于中西文化的根本性框架有“双重”敏感性。在讲授中国哲学的课堂上,想让西方学生对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概念有比较深切的理解,就要努力把他们从自身的框架中拉出来,但同时又要借助他们自身的理解框架来做某种相应性的对比,笔者称之为一种“框架性的对比工作”。这是一种非常艰难的工作。举例来说,“亲亲”,在中国哲学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人者,仁也,亲亲为大”,在西方哲学中却找不到类似概念。古希腊哲学中有 philia 的概念,要比“亲亲”的内涵宽泛得多,在汉语中常被翻译为“友爱”,亚里士多德常在这同一个概念下来讨论“友谊”“亲情”以及其他“爱”的情感。更狭窄一些的,则是 Eros 在希腊哲学中的地位以及 Agape 在基督教世界中的位置。因此,虽然在西方哲学中没有完全對应“亲亲”的概念,但借助于其自身哲学框架中的这些情感性概念,我们还是完全可以把“亲亲”在中国哲学框架中的作用讲清楚,他们也能理解“亲亲之爱”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基础性地位。它们都是一种“爱”,渊源不同,特点不同,但对于切近与他人的关系,都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源初性力量。基于这些不同的源初性概念,中西哲学会发展出不同的思想体系。
直面中国哲学自身的特点
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常会在“中国哲学”的论述中,看到“朴素的×× 主义”“自发的 ×× 精神”“直观的 ×× 观念”—总之,给人“低一等”的印象。在这里,西方哲学不是以“他者”而是以一种“普遍面目”出现的,这严重制约了对于“中国哲学”的理解。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学者,常常以“中国没有哲学”来抵御这种所谓“哲学性”的侵害。中国思想传统的研究固然有多重路径,古典学的、文献学的、学术史的、思想史的,但是,哲学毕竟是极为重要的路径。哲学以更加鲜明的论说方式呈现中国传统的思想内涵,中国思想传统的“哲学性”不可或缺。
如果我们不那么拘泥于狭隘的哲学标准,而是以一种更加宏阔的方式来理解哲学的话,那么中国思想传统当然是一种哲学,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哲学传统。在各个文明体中,试图以理性的方式来回答关于宇宙、世界、人的生存、道德起源等根本性问题的学说,都是哲学。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哲学有着丰富的思想传统;而且在不同时代,它在不断地提升其理性化的水平。我们不仅要强调中国思想传统的“哲学性”,同时还要努力创造出其在现代世界的“合理性的形式”。
此次在德国讲学,受限于时间,主要内容聚焦在儒家思想传统。但是,笔者为学生选取了三个非常不典型的古典文本——《系辞》《中庸》和《孝经》。笔者的用意,是要通过这三个文本为他们搭建一个理解中国哲学的框架。在不同的文明体中,哲学远远不是一种个体性的行为,具体哲学的讨论常常是基于一种更大的逻辑性框架。中西哲学的“对照”首先是一种“框架性对比”的工作。为了强化这一点,笔者在进入具体文本讨论之前,花了6周课时的时间,为日后文本的研读与讨论建构一种“本体论框架”。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一样,都是要直面人类的根本性问题;只是不同哲学传统,他们建立起来的“根本性框架”完全不同。漠视这一点,随便拿起中国的哲学概念非反思地置于西方哲学的框架之中,那么黑格尔对于孔子的评价就难以避免。如果不强化“总体性框架”上的差异,无论用哪种西方哲学的模式来看待中国哲学,甚至在枝枝蔓蔓上突出中西哲学的差异,都未免隔靴搔痒。
笔者之所以以《易传》为开端,就是要让西方的学生了解,如果说西方哲学传统的第一个概念是 being,那么中国哲学的第一个概念就是“易”;西方哲学的“being”传统是从“不变”的“本质”去理解世界;中国哲学是从“变易”中去把握天地“大道”。这就是一种本体论上的根本差异。中西哲学从开端处就“分叉”了。这样的起点,给习惯于从“巴门尼德-柏拉图”创立的二元世界观的德国学生以一个极大的反转。如果说我们面对的“本质”不是永恒的,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去把握?如果“本质”不是永恒不变的,那么亚里士多德式的逻辑与范畴是否还有效?我们知道《周易》重在变化的“天道”,经首“乾坤”讲的就是“天道”如何变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庸》被认为是“准《周易》而作”,由天道而人道,讲的是如何在这个“变易”的世界中保持“中庸”;人人都有配天之责,尽人性、尽物性,赞天地之化育。《孝经》则将《周易》中“天地之大德曰生”,具体化到人伦世界,并进一步阐发了《中庸》中所讲“道不远人”的道理,“人之为道,孝而已矣”,由此落实下来,并基于此建立起中国人传统的生命观、伦理观与政治观。当然,这个哲学性框架并不够全面,它还缺失了道家哲学显示的中国哲学中人与自然连续性的另一面。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在现代语境下阐释中国哲学传统概念的合理性
有了这种“框架性”的理解,接下来最重要的是在这种框架中,如何把中国哲学自身的“概念”呈现出来。现代汉语长久沉浸于西方的术语概念,以致我们遗忘了自身的“概念”;在“透过现象看本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之类的概念中,中国哲学自身的“概念”体系被隐没了。比如“孝”,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哲学观念,对于中国文化传统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在全世界唯有中国有《孝经》。但现代社会对于“孝”的观念有强烈的排斥感,五四以来我们对于“孝”的观念也有很大的污名化,“孝”被认为是制造等级制的,是专制主义的基础,是对“个性”的压制。从历史上的各种“机制化的表达”来看,确实有很多问题需要现代的检视与澄清。即便在孔子时代,孔子的弟子宰予也对三年服丧表示不满。但我们并不能由此剥夺“孝”作为一种哲学概念的内在合理性。
究竟如何来理解“孝”呢?这就需要在中国思想传统的大框架中来定位。中国文化传统讲“大道流行”,在中国主流文化中,没有人格神的概念,也没有拯救的概念。那么如何来理解生命的不朽呢?在柏拉图哲学中,他提出了“灵魂不朽”的概念,这一概念不仅在希腊哲学,而且在基督教传统中发挥着很大作用。对于中国文化传统来说,在这个“变易”的世界中,是通过“生生不息”来保持生命的不朽。因此在中国文化中就特别强调“世代”之间的延续,“孝”就成了首要德性。“孝”这个字本身就是“上一世代”与“下一世代”的结合,是“老”与“少”的结合。中国文化传统强调“孝,德之本也”,既不是古希腊的“智慧、正义、勇敢、节制”,也不是基督教的“信、望、爱”。不同文化传统中的德性体系有其自身的缘由与合理性,需要在这个框架性体系中来理解。同时,“孝”虽是至德要道,却是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造端乎夫妇,这充分体现了《中庸》“道不远人”的原则。
中国人恰恰是在“孝”中抓住生命意义。在没有人格神的世界中,通过“孝”给自己在宇宙中一个位置,通过“孝”实现生命的不朽。因此“孝”不单纯是一种伦理概念,也是有着终极意义的精神概念;如果说路德是通过“因信称义”来界定基督教信仰的,那么可以说,中国人是通过“因孝称义”来面对终极性意义的。
但凡在自身框架中被凸显出来的“概念”,在另一个文明体系中都非常难以翻译。通常英语里把“孝”翻译成“filial piety”,安乐哲先生将“孝”翻译成“family reverence”,还有其他种种不同的翻译。在这门课中,类似难以翻译的中国哲学概念不胜枚举。比如“象”:“易道”之“象”或者卜筮之“象”已经很难理解,而“意以象尽,象以言着”这样的“言、象、意”三重结构就更难解释。在西方的思维结构中,由于没有这种概略性“象”的概念,因此翻译起来同样困难重重。在英语翻译中出现了一系列不同的译法,如 image、figure、emblematic symbol、semblance 等,都不太能准确地表达“象”在中国哲学中的意义。在论述中国哲学时,一旦确立了这些概念自身的自主性,而不是淹没在西方哲学的概念中,那么這种概念的“不可翻译性”恰恰体现出了中国哲学自身的特点。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努力在现代语境下阐释这些传统概念的合理性。
在现代世界如何探寻中国哲学的意义
作为现代智人的后代,人类的智商大致就在 85~115 之间,都有着喜怒哀乐的基本情感,面对的也都是人类处境类似的根本性问题,这就是人类能够相互理解的生存论基础。但在不同的文明体中,积累了各自面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经验,在解决根本性挑战上也给出了各自不同的路径,不同的文明各擅胜场。这是人类在不同文明之间相互交流、对话与学习的意义所在。
尽管只是简单的一堂课,如何面对课堂上的种种困惑,其背后也折射了在现代世界如何探寻中国哲学意义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首先要澄清两个基本的出发点。首先,当我们面对西方文化传统讲授中国哲学时,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一种西方文化,一如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那样,一种与中国完全相异的文化。我们还必须认清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是脱胎于西方文化传统的,而不是脱胎于其他文化传统。西方文化常常以“现代性”的面目出现,构成了现代社会运作的基本逻辑;它同样是现代社会价值“本体”的来源,而我们自己也身处现代世界。“西方”的双重性,使得中国哲学在受到“西方哲学”质疑时,这种质疑常常是以现代性名义出现。在这里,既呈现出中西哲学在文化空间上的对峙,又显现出现代与传统在精神时间上的张力。
另一个基本出发点,则是中国哲学自身的主体性问题。自张之洞的“中体西用”之后,中国思想传统的主体性就开始遭到质疑。于是,我们总是把自己定位为“具体实践”“特色国情”“国际接轨”的对象,虽然表述不同,其间无不透露出同样的思路:面对“普遍”,自己只是一种“特殊”;这与以“西洋哲学”标准对中国思想传统“择而述之”的做法如出一辙。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其实大可不必费尽周章地去西方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因为它只是更普遍、更纯粹、更彻底的哲学的一种“特殊体现”。讲授“中国哲学”,其背后坚守的理念就是坚持中国思想传统的主体性,坚持其“本体”地位。我们同样需要以这样一种认真的姿态来提升中国哲学在现代世界的严肃性与庄重性。
笔者觉得这“双重出发点”对于在现代世界探寻中国哲学意义非常重要,也体现出在西方大学讲授“中国哲学”时的基本“情形”:一方面,作为中西方文化的思想传统,它们之间有着对等的“本体”地位,有一种在结构上相互理解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则依然存在着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面对的不仅仅是一种文化上的相互的“理解”与“欣赏”,更会受到一种来自现代价值的“质疑”。只有从“双重本体”出发,在“中西”与“古今”两个层面上来应对这种挑战,才能以一种更为成熟的心态来面对中国哲学在现代世界的处境。
中国哲学讲究“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只有以一种“诚恳”的态度,才能“明了”问题的复杂性;也只有对周遭世界有透彻的“明了”,才能以“真诚”的态度,面对大家的疑惑与质疑。
在中西差异的层面,言说“中国哲学”的同时,其实也是一种倾听,也是一种理解;在他人的疑惑与质疑中,会更清楚自身的特点与所长。只有真正理解他者,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才能客观地评价自己。理解了他人的长处,才能理解自己的宝贵之处。自己的“所长”并不是通过贬低别人来获得的;自己的“所短”,也是在一种比较中才能呈现的。在人类文明中,并不存在某家的独“长”,而是各擅所“长”,各苦所“短”。这背后是一种相互理解,相互开放的过程。在“双重本体”的前提下,一种成熟的交流,是要有能力去理解来自对方的误解,有能力去理解那种不理解。真正的交流与对话,不是宣传与输出,不是自炫“高明”,而是基于相互的尊重与欣赏,为的是一种相互的学习与提高。
在古今张力的层面,现代世界尽管有种种的问题与危机,但现代价值观念在“尊重每一个人的自由、权利与尊严”上取得了巨大进步,康德哲学所达到的“人是目的”的哲学理念已经成为人类共享的价值理想。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哲学所达到的现代价值观念,也不仅仅是西方世界的,同样为人类世界所共享。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哲学的传统存在着现代“转型”的问题。但“转型”并不是要去成为“差一等”的西方哲学,而是在自身的思想傳统上发展出制衡现代世界缺陷,开辟未来可能性的思想力量,这才是中国哲学在现代世界的意义所在。
作为来自不同文明传统的人类,最终要思考的是相同的问题:我们亟须以这样或那样一种传统所积累的智慧来质询自己,我们还能为人类贡献什么?就此而言,中国哲学在现代世界的意义,才刚刚起步。
(责任编辑:张文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