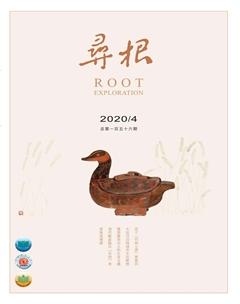柳沟碑刻节孝碑中的女性问题
刘文科 周蜜


2015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郑州市中原区须水镇附近清理搬迁了一批明清到民国时期的古代和近代碑刻。这一批碑刻原分别立于须水镇各个村庄,后因农田水利建设,被集中于现在中原西路与须水河交会的柳沟村西,称为柳沟碑刻群。为配合郑州西部村镇的拆迁安置,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柳沟碑刻群进行了搬迁和整理。
须水古属荥阳,交通位置重要,其人口众多、农商发达,四方辐辏,是中原地区重要的商贸中心和交通枢纽。这一批碑刻为我们了解清末民初的乡村社会提供了资料,其中民国14年和民国21年的两通节孝碑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女性问题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通过对两通节孝碑的释读,初步了解碑主人生平事迹及其所体现的女性生存状态,结合同时期的其他柳沟碑刻资料,我们得以管窥这一时期的女性问题。同时,也为我们研究当时荥阳地方社会与家庭关系打开了一扇窗。
节孝碑释读
碑刻存立之日起即受日光照射、风雨剥蚀,恶劣的保存条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碑刻文字的释读。加之一部分柳沟碑刻在集中和作为水库堤坡基石的建筑过程中也受到过损坏,现在已无法看到碑刻文字的全部内容。
此次共发现节孝碑三通,其一碑名为“登仕佐郎方二公讳文祥德配李孺人节行碑”,其二碑名为“清故处士方三公讳象离德配朱氏节孝碑”,其三为“皇清处士方大公讳锦文德配赵氏节孝碑”。第三通石碑仅见少许文字,本文只对前两通较为完整的石碑略作释读。
“登仕佐郎方二公讳文祥德配李孺人节行碑”。碑刻为青灰石质,通高1.64米,宽0.57米,厚0.14米。碑首为圆弧形,碑额上书“鹤发冰心”,左右两侧为龙纹浮雕。碑文为小楷,共计8行,每行52字,共计378字。由于年久,部分文字漫漶不清。
登仕佐郎方二公讳文祥德配李孺人节行碑
从来有守者必有为,有为者必出于有守,是以人生天地间,有守尚焉。夫守孰为大,守节为大,然节之守也,求之于妇女,难求之于幼年,妇女尤难者,余族祖母李孺人者可谓幼年守节者也。
原孺人及笄,适方文祥君,不数年而方君夭损,孺人则哭天号地,势不欲生,继又思夫尚无嗣,徒以一死塞责,罪戾滋甚,不得已,收泪含痛,勉裹家政于一人,则唯勤惟俭,对兄嫂则毕敬毕和,对侄辈则有恩有威,以治先人旧业愈进愈盛。后来人众,析居,孺人仅取薄田六十亩,住宅一处,余尽归侄辈享用。比时,孺人乃择兄之第六子同生为嗣,而理家后振刷精神焉。孺人视同生有大材,令其深入商界,家中琐务,一己独任其劳。孺人生一女,适孟君金铃,于适时,嫁妆不甚丰厚,恐于家之财政有妨也。现今家业兴盛,时因孺人之留守而有为也。昔孺人到方门时,翁姑已谢世耳,其孝不知若何也。今孺人弃世已五六年矣,村人群思树碑,光前人以劝来者,嘱玉为文。玉不获辞,特即所知者缕续述之云。
铭曰:山明水秀兮,钟毓异常,有女丈夫兮,才节无双,后人□□□,前人有光。是为铭。
清优廪生 愚族孙 方贡玉沐手撰文
师范讲习所毕业 愚甥 孙奉先书丹
第四师范完全科毕业 愚孙 方 男 书额
同族:国子监 方锡蕃 清国子监 方今生 方□寅 方□□ 方锡明
副官 方贡瑞 方同科 方□
□ 方锡□ 官校毕业 方福林等
中华民国十四年六月仲浣旦
这一通节行碑是方氏族人为了彰显李氏的优良操行而合族共立的。碑文描述李氏在年轻时守寡,“原孺人及笄,适方文祥君”,李氏在刚刚成年时嫁与方文祥为妻,当时公婆均已过世,所以碑名节行,并未注明她的孝道。丈夫几年后去世,只留下一个女儿。李氏痛失丈夫而不欲生,但觉得自己没有给丈夫留下子嗣不能用死来逃脱责任,于是便“收泪含痛”,开始生活。因为李氏没有男丁不能成嗣,于是过继了方文祥大哥的第六子同生为自己的儿子。家族中李氏所在的这一支家业渐大,人口渐多,在“析居”即分家时,其仅仅取薄田少许,住宅一处,其他的家产都让给了众多的侄子。李氏“唯勤惟俭”,所有琐事都一人承担下来,在培养子女方面,她对过继而来的同生视为己出,让他外出从事商业活动,自己在家承担所有家务。李氏与方文祥只有一个女儿,在女儿出嫁时,并没有给予太多的嫁妆,害怕“家之财政有妨也”。
“清故处士方三公讳象离德配朱氏节孝碑”。碑为青灰石质,通高1.82米,宽0.56米,厚0.15米。弧形碑首,石碑正反两面皆有文字。正面碑额上书“流芳百代”,两侧为高浮雕龙形纹饰。碑文为行楷。共计11行,每行33字,共计328字。石碑北面碑首位置为一松鹤形浮雕纹饰。碑身部分书写“乡友亲族仝立”,且记录有参与立碑的所有人员的姓名。该碑出土时已经被严重破坏,碑首与碑身断为两截。
清故处士方三公讳象离德配朱氏节孝碑
益闻男□□,尤山河倚以為重,妇人节孝,门第因之生辉,此乃间气所钟而风化攸关者也。若吾族婶母者,朱公启元之女也,十八适方门。斯时也,翁姑在堂,但知殷殷以事老,弟兄在侧,恒知怡怡以悦亲,且亲疾亲侍汤药未尝废离。方冀夫倡妇随永享天年,不意清光绪丁酉年,其夫象离公竟夭逝焉。生四子一女,长锡朋,仅十二岁,其他幼且弱,不问可知。况前已析居,田无人耕,事无人理。婶母几不欲生,又思翁姑尚在,不得不勉强支持,以书孝道。于是柏舟矢志,菽水承欢,昼夜纺织以食其十指。又为四子计划,长子朋四□钦留在家耕□,次子珍、三子党令出外学习职业,后来各知勤俭,家有余粮,外进多□,二十余年置地近八十亩,家中称少有。呜呼,婶母七十竟去世矣,何受其苦者久、享其甘者蹙也。村人欲树碑以彰其德、表其苦,乞文于玉。玉陋甚,只按事序之云尔。
铭曰:檀山在其后,长河在其前,妇女有完人兮,节孝双全。吾始信钟毓有灵兮,可作巾帼之山巅。
清优廪生族侄方贡玉斋心撰文
邑人赵道一沐手书丹
铁笔孙绍源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岁次壬申秋九月上浣榖旦
这一通节孝碑是方家后辈为家族内一位德行高尚的长辈朱氏所立。朱氏18岁时嫁方象离为妻,她伺候公婆尽心尽力,与方象离的兄弟关系和睦。丈夫方象离早年过世,留下了白发高堂和四子一女,长子年仅12岁。丈夫去世,朱氏痛不欲生。但因失子高堂和幼年丧父的孩子仍需仰仗她的照顾,朱氏支撑这一个即将崩垮的家庭。通过勤俭持家,精心打理,儿子各有成就。20余年来,置地多达80亩,家庭殷实。朱氏中年丧夫、吃苦受罪,晚年乐享天伦、家业有成,于70岁去世。
柳沟碑刻中记述女性的特点
上述两通碑记载翔实,保存状况相对较好,同时在柳沟所发现的其他碑刻中也有少量关于女性的记载,这为我们研究清末乡村女性问题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材料。
柳沟碑刻群共发掘有字碑刻59通,其中有33通碑刻提到女性,共计56人。尽管人数不少,但对于她们的描述多惜墨如金,通观对这56人的记述,发现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有姓无名。在柳沟发现的碑刻中,包括合葬墓碑和节孝碑,均未发现女性的完整姓名。在合葬墓碑中,仅有丈夫名讳,女性均以姓氏区分。
第二,描述简略。在柳沟碑刻中仅有少数关于女性事迹的记载,在合葬墓碑中除姓氏外,基本上没有女性的任何信息。在节孝碑中,出于对人物具体功绩表彰的需要,一般则有较多关于女性事迹的记载。
柳沟碑刻中的女性社会问题
柳沟碑刻群中可以观察到的女性事迹较少,以节孝碑为基础,结合其他碑刻中零散的信息资料,窥探清末民初荥阳地区的女性评价标准和其所处的社会地位,这些无疑都是研究这一时期社会结构与社会环境的重要资料。柳沟碑刻尽管文字记述较少,却反映出了许多女性的社会问题。
1.对女性的评价标准
在柳沟出土的所有石碑,有具体女性事迹描述的不过6通,叙述详尽的则只有上文所提的两通。通过对上述碑文人物形象的刻画,我们可以归纳出当时社会对于女性的评价标准。
在“登仕佐郎方二公讳文祥德配李孺人节行碑”中认为女性“守节为大”,评价李氏在生活中“唯勤惟俭”,在人际关系上“毕敬毕和”“有恩有威”,在治家上“以治先人旧业愈进愈盛”,对下一代培养时“视同生有大材,令其深入商界”,面对家庭琐事“独任其劳”,至于对待长辈的态度则因“其孝不知若何也”。
在“清故处士方三公讳象离德配朱氏节孝碑”中认为女性“妇人节孝,门第因之生辉”,丈夫去世后,二老双亲和未成年的四子一女是朱氏唯一的牵挂和责任。朱氏对待老人“但知殷殷以事老”,用行为“以书孝道”,处理妯娌兄弟关系时则“恒知怡怡以悦亲”;在治家上“昼夜纺织以食其十指”,辛苦劳作终有回报,“二十余年置地近八十亩,家中称少有为”;在培养下一代上“为四子计划”,子女们在她身体力行的感召下“各知勤俭”。
柳沟碑刻中其他碑文中也有少量关于女性评价的记载,例如《清从九品茹二公讳秉文及原配王孺人继配常孺人墓表》提及茹秉文原配“柔嘉维则”。《清太学生茹太公讳有神暨德配赵孺人墓表》中对于赵氏的评价则是“柔顺若贤,十八岁归内助,家政力肩无废事,子能成立,女能宜家,使公得绵延烟祀不坠家风者。”
通过对上述碑文的释读,我们不难归纳出清末民初对于女性的评价标准。这一标准首先要立足于妇德之上。“节孝”是妇德的第一个标准,“守节为大”,同时恪守孝道也是妇德的一个重要的标准。在处理人际关系上要求恭敬平和,温柔待人,温和处事。
这一时期对妇女评价有一个较为明显的特征是“有所作为”。李氏年轻守寡,在治家上,亦使先人旧业愈加兴盛,家业兴旺。朱氏中年丧夫之后,精心治家,20年置地80亩。
这些记述共同体现出这一时期对于女性的要求除了能够守节,还必须有所作为,能够使家族昌盛、家风不坠。
2.女性的社会地位
从柳沟碑刻中的女性事迹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对于女性的评价仍以传统标准为主,要求非常高,甚至可以说近乎苛刻。女性在整个社会和家庭体系中无外乎三种身份和地位:母亲、妻子、女儿。这三种形态在柳沟碑刻提及女性的碑刻中均有涉及,但是,对她们的介绍寥寥无几,只说明女儿人数、嫁与某家;妻子是否有嗣;母亲这一属性也更多附在妻子的身份之下,大多数没有事迹可供查考。
柳沟碑刻一如常制,女性在墓碑中只有姓氏而没有完整的姓名,大部分女性也没有较为完整的生卒年月。表彰女性德操的节孝碑上也仅有姓氏,但却往往在其上书写有其丈夫的完整姓名。女性在当时的社会中只是男性的附庸,并没有占据较高的社会和家庭地位。
3.节孝的阶层性
宋元以来,由于“三从四德”的观念渐深,对于女性便提出了更为苛刻的要求,重“节孝”的社会风气日益昌盛。但是,通过两通节孝碑以及相关碑刻的释读,我们可以明确感受到节孝应该是具有一定阶层性。
两通节孝碑中均提及两位女性能够守节且勤于持家,使家庭面貌为之一新。两者共同的特点是具有较好的经济条件。这一基础不但是评价女性有为的标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女性得以守节义的基础。《清从九品茹二公讳秉文及原配王孺人继配常孺人墓表》中提及的“公姊适同岗铺罗姓,少寡,无子,且贫,励以节义养于家。委以家政,殁具棺衾遂送归葬”。茹秉文的姐姐家贫且无子,茹秉文则鼓励其节孝养于家,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经济条件是女性节义的必要条件之一。没有较好的经济实力,传统社会中孤独贫穷的妇女也难以完成其节孝的心愿。
节孝观念在现在看来是女性的社会和家庭枷锁。但是,在古代社会却被认为既是传统女性個人价值的实现,也是家庭荣耀的展示。于是,越是庞大的家族,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越会支持家族内女性的节孝实践,也会把这种节孝行为当作家族共同的成就。
4.女性社会地位的时代性变化
在柳沟碑刻中关于女性的碑刻依据年代先后进行排列,我们发现了一些非常细微的差异,如所有提及墓主姐姐和墓主女儿(包括孙女)的碑刻全部立碑于民国,所有清代碑刻中,无论墓主有无继承人,都没有提到是否还有女儿的存在,可得出从清代至民国这段时期内女性地位在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的转型中,正与时代变革同步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
方文祥妻李氏节行碑与方象离妻朱氏节孝碑中除了提到守节和与同辈和睦相处、自立自强、但取所需这类传统节孝类女性的普遍事迹,还重点突出了她们在治家和经济上的努力,如擅长财富的积累与支持继子投身商界,脱离了一般称颂列女事迹的标准模式。说明在清末及民国时期,单一的节行碑已不能容纳新时期女性的奋斗事迹和人生贡献,社会舆论对于这类突破了传统评价标准的女性也表示了认可和称赞。
——————————————————————
作者单位: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郑州市文化遗产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