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苦中西交通四十载
张西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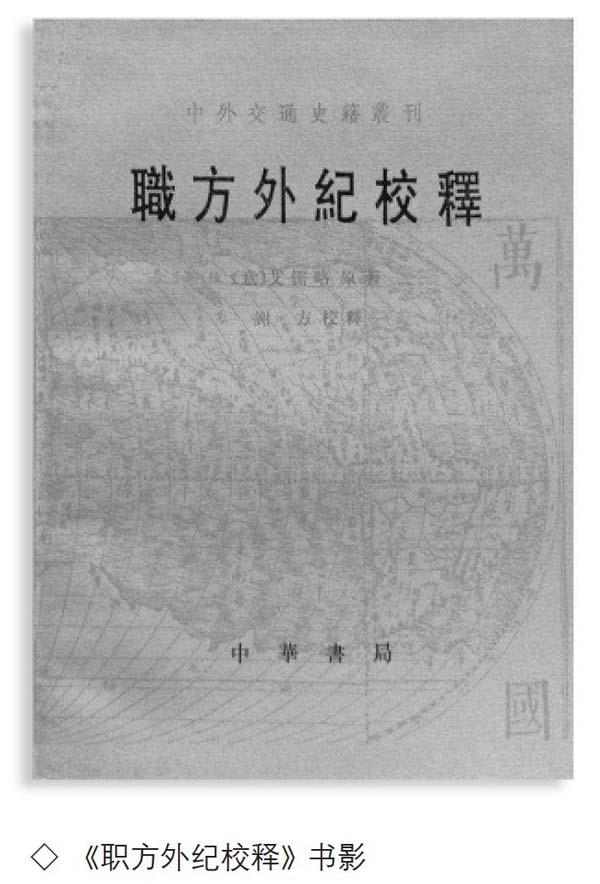

在我们回顾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外关系史学科的发展与建设时,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谢方先生对这个学科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我们是不能忘记的。谢方先生1957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1957年9月开始在中华书局工作,1994年1月退休。他在中华书局40多年,最为重要的贡献就是编辑了“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和“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两套丛书,从而为中外关系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奠基了文献学基础。
编辑出版“中外交通史籍丛刊”
“中外交通史籍丛刊”这套书是向达先生最早提出的,这个想法得到了当时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先生的支持,这套书也得到了当时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齐燕铭先生的认可,将其列入了由翦伯赞先生主持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历史部分”。中华书局的金灿然先生把这套书的出版编辑工作交给了从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不久即进入中华书局工作的谢方先生。金灿然先生对这套书也寄予很大希望,尽管当时向达先生仍戴着“右派”的帽子,但他仍安排谢方先生去找向达先生约稿,并告诉谢先生“稿来后可以先发排付型,等到他帽子一摘,书就可以马上出版”。(谢方:《忆我和向达先生的首次见面》,《谢方文存》,中华书局,2012年)
由此,在中华书局领导的支持下,在向达先生的带领下,谢先生开始进入中外交通史研究领域。这套书从1961年出版向达先生的第一本书到1996年,历经35年,共出版22种,为中外关系史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这套书的奠基人是向达先生,最初的42种书目也是向达先生列出来的。他为做好此书曾专程从北京前往广州向陈寅恪先生求教,陈先生写下《甲辰春分日赠向觉明》一诗:
慈恩顶骨已三分,
西竺遥闻造塔坟。
吾有丰干绕舌悔,
羡君辛苦缀遗文。
这套书出版之艰辛,可以以《大唐西域记校注》出版为例,此书的出版前后历经26年。向达先生的计划出版目录中就有这本书,中华书局后来接到上海章巽和范祥雍两位先生的来信,提出整理《大唐西域记》的计划,范祥雍也曾亲自来北京和向达先生商量此事。1961年,北大历史系在章、范两人计划基础上也向中华书局提出了一个整理计划,后来由于当时高校正在“拔白旗”,这个计划就流产了。1962年向达先生重提此事,决心以余生独自来完成它,并建议可以先出版敦煌残卷、福州残卷和赵成藏残卷三个古本。1965年,向达先生也受到了“大批判”的冲击,他于1966年11月去世。《大唐西域记》整理的第二阶段结束了。
改革开放后,由季羡林先生牵头,张广达、耿世民、杨廷福、朱杰勤、孙毓堂、张毅、蒋忠新等人参加的整理小组,在充分利用向达、周连宽等人的成果和充分吸收国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到1983年完成了全部编辑工作,《大唐西域记校注》正式出版。“《校注》的成就是空前的”,书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这个过程中谢方先生作为编辑,在联络学者、整合书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外交通史籍丛刊”每本书的作者都是从事中外关系史的前辈或者知名学者,如《岛夷志略校释》的作者苏继先生是商务印书馆的老编辑,从20世纪40年代看到日本学者藤田丰八的校注本后,就开始研究这本书,并对书中的地名、物产、商品名逐一考证。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东起澎湖,西至阿拉伯半岛、东非海岸,书中有200多个地名。冯承钧先生曾认为可以考证出53个,但苏继先生逐条考证,学问之大令人敬仰。姚楠先生认为苏继先生的《岛夷志略校释》对地名、物名的考证“比藤田、柔克义等的考证,应该说是前进了一大步”。
谢方先生不仅是这套书的编辑,同时也是这套书的作者之一。他点校出版了《东西洋考》《西洋朝贡典录》《职方外纪校释》。他还为《咸宾录》《海外记事》《殊域周咨录》写了前言。他对意大利来华传教士艾儒略(Jules Aleni,1582-1649)《职方外纪》的研究多有贡献。首先,他首次明确更正和批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关于艾儒略词条的错误,指出艾儒略并未到过江西,也没有写过《基督传》八卷,同时《职方外纪》这本书虽然涉及到天文学,但主要是地理學著作。其次,艾儒略在出版《职方外纪》时说此书是由他和杨廷筠“增辑”而成,那么《职方外纪》是以何为底本来增辑呢?以往学术界都认为艾儒略是在利玛窦等的《坤舆万国全图》基础上加以增补而成。谢方先生依据原始文献指出,这样的看法都是无根据的。《职方外纪》实际上是福建税官献给朝廷的两幅西洋地图,由当时的庞迪我(Didace de Pantoja,1571-1618)和熊三拔(Sabbathin de Ursis,1575-1620)两人将这两幅西洋地图翻译成中文后,由艾儒略和杨廷筠编辑而成。同时,谢方先生通过对照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和《职方外纪》的地名译名,进一步说明《职方外纪》并不是在利玛窦地图的基础上增补而成。这个研究成果直接深化了对艾儒略的研究。
在校注《职方外纪》时,谢方先生显示出他深厚的历史学养和丰富的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知识。例如,在《职方外纪》卷一有神秘良药“的里亚加”,谢方指出,这就是唐高宗乾封二年(667年)由拂国遣使献给中国的“底也伽”。在卷四《孛露》中有“拔尔撒摩”的万能神药,谢方指出,它在唐代名为“阿勃参”,此药名在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有记载,就是今天英语中的Balsam,即香脂。
谢方先生还分析了《职方外纪》的贡献,他在《艾儒略及其〈职方外纪〉》的长文中对艾儒略的这本书做了全面的分析,提出重要的学术结论:
1.《职方外纪》是我国第一部世界地理,也是西方地理学最早的中国版。
2.《职方外纪》的内容并非“荒渺莫考”,它基本上反映了15世纪以来的世界地理的最新成果。
3.《职方外纪》对中国新旧世界的地理观念的革新,起了深远的影响。在经历了250年之后,中国最终接受了新的世界地理观念。
4.《职方外纪》强烈地反映了西方的宗教观、历史观和殖民观,这是中国人所不能接受的,也是新的世界地理观念长时间内被排斥的重要原因。
“中外交通史籍丛刊”这套书目前已经成为治中外文化交流史的案头必读之书,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代表中外关系史学科取得实质进展的经典之作。谢方先生为这套书的出版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这套书至今出版30多种,其中多数文献有详细的校注:《西洋番国志》《郑和航海图》《两种海道针经》《岛夷志略校释》《真腊风土记校注》《西游录》《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往五天竺国传笺释》《经行记笺注》《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诸蕃志校释》《职方外纪校释》《诸蕃志校释》《回回药方考释》《法显传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日本考》等,其余为校点本,如《殊域周咨录》《清朝柔远记》等。
“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内容丰富,多部书籍除此无其他铅印版本。但也缺少一些重要的中外交通史文献,如明代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等。
编辑出版“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谢方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组织出版“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初期,就萌生过出版一套国外中外交通史研究著作的翻译丛书,但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个想法很快就被他自己否定了。改革开放以后,这个计划再次被提起。当时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有所分工,翻译著作大都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征得社里和商务印书馆的认同后,谢先生先后拜访了翁独健、孙毓棠、夏鼐、季羡林、张广达、朱杰勤、姚楠、韩振华、何兆武、陆峻岭等学术界前辈和同行,这个想法得到了学术界的大力支持。翁独健先生当时就推荐了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三卷本《马可·波罗游记札记》。恰逢当时孙毓棠先生和马雍先生在筹备中外关系史学会,这样谢先生就把这套书的名字定为“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并确定下来了“一、古典中外关系史名著,即16世纪以前阿拉伯人和欧洲人有关中国的著作和资料。古代日本和朝鲜、越南方面的著作都用汉文,因此不包括在内。二、16世纪欧洲传教士、商人、政治使者来华的著作及资料。三、18世纪后外国学者对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成果。外国汉学家对中国的其他各种研究,因为数量太多,不包括在内。”
经过多年努力,目前这套书已经成为与“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并驾齐驱、在学术界受到广泛好评、产生重大影响的学术丛书。目前已经出版20余种。
这套书对中外关系的研究,特别是对16世纪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学术影响。201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意大利文版《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201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意大利文版《利玛窦书信》,在此之前中华书局版《利玛窦中国札记》成为这个研究领域的热点,而《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成为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明清之际历史与西方汉学史的必读之书,所有学者都案头必备。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谢先生组织出版的这套书,就没有今天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的研究热。
这套书的另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为新一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学者,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学术舞台。谢方先生去拜访孙毓棠先生时,孙毓棠先生就给他推荐了刚刚调到历史所的耿先生。从此,耿与谢方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学术友谊,耿先生的《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刊》《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开启了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和西方汉学史的翻译事业。谢方先生对耿先生的翻译事业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他翻译法国汉学名著硕果累累,不但补充了冯承钧去世以后的空白,而且在翻译的数量上和内容的广度上,都超越了前人,成为近年来出现在汉学译坛上一员少见的骁将。”他在《为了法国与中国文化因缘》一文中详细地列举了耿在敦煌学研究、藏学研究、基督教传教士来华研究、中国社会史研究、法国汉学史研究等多个方面的成绩,耿先生的译著在近40年的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学术影响。关于这点,季羡林先生说得好:“我读了耿译《丝路》(耿译:《丝绸之路——中国与波斯文化交流史》)以后,眼前豁然开朗,仿佛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丝路。我原来根本没有想到的问题,书中提出来了;我原来想的不深的问题,书中想得很深了。这大大提高了我对‘丝路的认识。……我手不释卷,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几乎是一口气读完。我应该十分感谢阿里·玛扎海里先生,我应该十分感谢耿同志。”
《古代南海地名汇释》的学术价值
谢方先生不仅为“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中的各种图书出版时写了大量的学术性前言和介绍,他还和陈佳荣先生、陆峻岭先生合编了《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以下简称《汇释》)一书。这是研究中外关系史的重要成果和重要的工具书。因为中外关系史中中国典籍的记载具有重要地位,但中文典籍里的地名还原问题一直是一个难题,50多年前冯承钧先生编辑了《西域地名》,书虽然简略,但受到学者的欢迎。冯先生曾设想编一本《南海地名》,可惜没有实现。谢方、陈佳荣、陆峻岭三人所编的这本书填补了学界空白,实现了冯承钧先生当年的理想。
这本书有两个显著特点:
第一,资料翔實。书中不但囊括了中国古籍记载中的南海各国地名,而且在每条释文后,全部列出所见书名、卷数,具有索引工具书的性质。“据统计,《汇释》全书共收录中文地名4697条,外文地名800多条;引用古籍217种,包括了‘二十四史‘十通及《永乐大典》等卷帙浩繁的大型古籍,参考现代学者著作达一百多种。”由此可以看出,几位编者所投入的巨大劳动和学术心血。
第二,《汇释》的学术性很强。它不仅在资料上突破前人,在研究上也很有特点。在书的每条释文中,凡是学术界在释文上有不同意见和说法的,《汇释》都逐一列出,并提出自己的意见。这样,使阅读者既了解学术界以往的研究进展,也能看到新的解释。例如,关于“赤土”一条,学术界以往分歧较大,有人说是在泰国的渭南河流域,有人说是在马来西亚半岛或者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的巨港。《汇释》在释文中纠正了《星槎胜览》和《西洋朝贡录》中的错误,并明确指出“赤土”应在马来西亚。
目前,学术界出现了“一带一路”研究热,但基础性学术工作进展并不理想,这本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著作,我们当十分敬佩谢方、陈佳荣、陆峻岭三位先生的远见卓识和出色的学术研究,更应该继承谢方先生等学术前辈的事业,做好中外关系史基础文献的整理与翻译工作。
谢方先生在中华书局工作四十年,编辑出版了“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两套高质量的学术丛书,为今天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奠基了学术基础。从他们的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外关系史研究从张星、冯承钧开创以来,到向达、张维华、方豪、陈垣、季羡林、张广达、耿世民、孙毓棠、马雍等前辈的不断努力,现在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从前辈的学术成就中,我们得出一个基本的经验,做好中外关系史研究,一定要把基础文献的整理与翻译做好,没有这一条,研究进展就是不扎实的。
1999年,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与杭州大学历史系和中外关系学会共同举办的“中西文化交流史(1500-1840)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谢方先生代表中外关系史学会做了总结发言,他指出:“要大力加强资料的调查研究。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由于起步晚,中间又出现30年的空缺时期,因此大量资料还来不及做出调查整理,特别是外国的文献和资料未能利用。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研究人员要多出国,到国外去找资料,进行整理研究。”杭州会议后,我与谢方先生开始有了较为密切的接触,我按照他所说的思路,开始在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资料整理、翻译和研究上下功夫。我和任继愈先生在大象出版社主编“国际汉学书系”,将翻译西方早期汉学名著作为重点,谢方先生亲自参与了这套书的书籍挑选和部分编辑工作,例如《耶稣会中国书简集》就是谢方先生亲自编辑的。“国际汉学书系”目前已经出版20余种,包括《耶稣会中国书简集》《中国近事》《中国图说》《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来华耶稣会士传教士马若瑟研究》《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父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中国近事报道》《中国新史》《中国来信》《利玛窦:凤凰阁》《中国的使臣:卜弥格》《十六和十七世纪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传教士与法国汉学》《张诚: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五位数学家之一》《奇异的国度:耶稣会的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中国近事》《斯洛文尼亚在中国的文化使者:刘松龄》《汉学先驱巴耶尔》《清初西洋传教士满文档案译本》《南怀仁的〈欧洲天文学〉》《历史上的北京俄国东正教使团》《中国通典》等,明后几年我们还将陆续出版《中华帝国全志》、《中国哲学家孔子》、《莱布尼茨中国书信集》、《雷慕沙至洪堡书信集》、《白晋文集》(四卷本)、《纪理安传》、《罗明坚文集》(九卷本)等书。
在谢方先生的指导下,我们用了7年时间在梵蒂冈图书馆搜集、整理复制回来了30万页的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基础性中文刻本文献,2014年已经出版了“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第一辑(43册)和第二辑(32册),未来两年将出版字典篇20余册,估计到2025年左右出版150冊。我还参与了谢方先生主持的《利玛窦中文著作》的点校工作,书稿交给商务印书馆,至今没有出版,书稿也下落不明。
回想起我进入中外关系史研究这个领域对我帮助最大的有两个人,第一个是谢方先生,第二个就是不久前去世的耿先生。现在谢方先生已经重病,卧床不起,耿先生已经驾鹤西去。中外关系史学会不应该忘记这两位优秀的学者,正是他们为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奠基了基础。
——————————————————————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