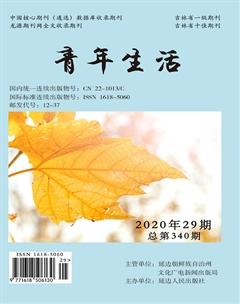基因编辑婴儿生育权的法理分析
陈斌
摘要: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引发了舆论与法学界的热议。按照我国法律和国际法的规定,这两名婴儿属于自然人。从从法律规范的角度看,两名基因编辑婴儿依法享有生育权,但默许政府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干涉她们生育权的实现。从法律思想的角度看,自然法学派支持剥夺两名婴儿的生育权,而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和社会法学派则反对剥夺两名婴儿的依法享有的生育权。
关键词:基因编辑;生育权;法理学
2018年11月26日,中国科学家贺建奎宣布一对基因编辑双胞胎女孩露露和娜娜近日在中国健康诞生。[1]此事一出,舆论一片哗然,法学界也在激烈讨论与此实验和两名女婴相关的法律问题。本文将从法理学的角度出发,从法律规范与法律思想的两个维度和不同法学派的多个视角,浅析两个女孩的生育权问题。
一、两名女婴的身份界定
(一)我国法律的看法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由此可知,要获得“自然人”的身份应当满足两个条件:其在生物学定义中属于“人”这一物种;其现有的状态是存活(已经自然出生并且尚未死亡)。
在本次事件中,一方面,这两名女婴庞大种类和数量的基因中仅有两处被修改,显然不足以改变她们是人类的事实;另一方面,这两名女婴目前已经自然出生,目前其身体状况总体也比较健康稳定。因此,这两名女婴属于我国法律上认为的“自然人”。
又,根据目前透露出的信息,这对婴儿的父母都是中国公民,且婴儿出生于我国深圳,根据我国《国籍法》的有关规定,这两名婴儿依法具有中国公民的身份。
(二)国际通行的看法
根据联合国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规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All human beings are born free and equal in dignity and fights.)”可见,国际社会公认自然人身份的获得基于两个因素:“人类(human being)”和“出生(born)”,这一看法与我国法律的规定基本一致。可见,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这两名女婴同样属于自然人。
二、从法律规范的角度审视基因编辑婴儿的生育权
(一)我国法律的规定
我国《宪法》和法律确立了对公民基本人权的保障制度,其中就包括对公民生育权的保护。[2]基因编辑婴儿作为中国公民,其依法享有生育自由与生育权利,任何人不能剥夺。
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法》推行计划生育,提倡“优生优育”。据此,通过医学检测认为胎儿可能患有严重疾病时,一般应建议夫妻避孕或终止妊娠。但具体到基因编辑婴儿,仍存在两个问题:
其一,计划生育,对公民来说不是强制性义务,是倡导性义务,主要采取国家指导、群众自愿,因此必须从鼓励和提倡入手。[3]因此,在法理上,国家对公民的生育权的限制并不具有强制效力。
其二,缺少CCR5基因并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严重疾病”等不适合生育的情况。如果孕检显示胎儿具有智力缺陷,那么我们基本可以肯定其出生必然伴随智力缺陷,并预测到这对胎儿自身、家庭和社会带来怎样的负担,其危害范围、危害形式、危害程度都是明确的。但基因的修改造成对个人人和人类的影响尚不得而知,我们不清楚它会引发人体结构和和性状表达的怎样改变。编辑基因对人的影响既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甚至可能根本没有影响。这难言“有严重缺陷”。
综上所述,虽然笔者认为国家可能会采取补偿等手段换取这两名基因编辑婴儿自愿放弃行使其 “实施生育的自由”,但这显然是行政层面的问题而非法律层面。在法律上,这两名基因编辑婴儿的生育权依然享受合法保护,不能剥夺。
(二)国际法的规定
1968年国际人权会议首次明确了生育权是基本人权。这一认识在196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社会进步及发展宣言》同样得到了确认。而197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更是首次将生育权明确写入国际公约。由此可以明确,国际社会公认生育权是人固有的基本权利,不容肆意剥夺。
但同样,基于第三代人权的思想和人口超载危害的现实,国际社会普遍认可各国结合本国国情对生育权采取一定的限制。1974年联合国布加勒斯特世界人口大会通过的《世界人口行动计划》首次明确提出夫妇在行使生育权利的同时,应当承担起对子女和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基于这一“责任和义务”,我们可以自然推导出公民应当自觉控制生育数量和控制生育质量(亦即“少生优生”),以保障后代的幸福生活和人类的和谐发展。《墨西哥建议》进一步提出:“各国政府可以做出较多努力去帮助其人民以负责的态度做出有關生育的决定”。这为公权力对生育权的介入提供了法理依据。
由此可见,国际法给予公民的生育权以更高的地位、呼吁更切实的保障。但考虑到基本权利具有的内在界限和外在界限,又普遍允许各国对其采取合理的限制。但具体适用到这两名“基因编辑婴儿”的身上,同样受到上文中提到的“危害的不确定性”和“限制效力较弱”的掣肘。因此,笔者认为,国际法和国际公约在原则上保护这两名婴儿的生育权不受侵犯,但默许政府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干涉她们的生育权的实现。
三、从法律思想的角度审视基因编辑婴儿的生育权
通过上文的研究,我们发现,现行法律在适用到本次事件时存在明显的障碍和缺陷。原因有二:一是社会和科技发展的高速性与法律固有的滞后性间的冲突,二是法作为社会规范的一种其效力所能限制的范围不足。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从法律思想的层面探究是否能够对基因编辑婴儿的生育权进行限制。
将这一特殊问题进行剖析,可以归结为三个普遍性问题:
其一,能对不确定的风险采取行政干预?
其二,集体(人类)利益能否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
其三,是否存在高于法的人类准则?
考虑到法学界对于这些问题看法不一,笔者将尝试分别从新自然法学派、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和社会法学派这三个主流法学流派的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解答。
(一)是否能对不确定的风险采取行政干预?
在传统的法律思想中,人们强调的并非“风险”而是“危险”。为了防止公权力的滥用,人们要求政府扮演“守夜人”身份。[5]此时,政府权力大多仅限于事后的反应,即使有时允许政府事先采取行动防止危害的发生,也要求政府对于损害的发生拥有充分的根据方可行动,这种根据就是“危险”的出现。但随着科技与社会的快速发展,很多时候我们对新兴事物仅能得出一个模糊的预测。在并不存在明显而现实的危险,却又无法排除危害可能性的情况下,如果仍以“危险”作为干预的起点,可能会过于束缚政府的行动。为了更好的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社会安全,现代各国要求政府发挥主动性,国家的安全任务由消极的危险防卫转变为更为积极的风险预防。[4]
综上所述,政府能够对不确定的风险提前采取行政干预。这一超前行为不仅基于政府的权力,同时也是公民保护个人权利的需要。
(二)集体(人类)利益能否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
公权与私权的界限与划分是法理学的重要议题。对此,不同学派的看法不一。
古典自然法学派认为,在国家的实在法之上存在永恒正义的“自然法”。[6]而人固有的基本权利是自然法所赋予的,先于制定法存在,因此,国家不得侵犯自然法赋予个人的权利。新自然法学派肯定个人权利的重要性,但同时也提出了个人权利的边界。如法国学者J. 夏蒙便提倡“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利在理性和正义的制度下相互结合”,[7]这实际上是承认了公共利益的重要性。可见,新自然法学派在原则上主张个人权利,但也允许公权力在正义原则下,出于公共利益对个人利益进行适当干预。
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反对将正义和道德带入法学领域中,认为法学研究的目光仅着眼于实在法。[8]而现实的情况是,虽然各国在其法律(特别是宪法)中对公民的基本权利进行了保护,但同时又普遍强调了权利的内在界限和外在界限。因此,新分析主义法学派虽然并没有在公私权利领域专门提出看法,但他们认可了现行法律规范,自然也就认可了出于公共利益而对个人利益的侵犯。
社会主义法学派认为法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秩序,强调法律的社会作用和效果。他们否认自认法学派所提倡的“自然法”的存在,又反对分析法学派的法律教条主义,主张将法律现象作为社会现象的一种进行比较研究,强调法律的社会作用和效果。[9]基于这一理念,社会主义法学派重视法律对社会秩序的保护,进而肯定了公共利益对个人利益的驾驭。
综上所述,不同法学流派基本认可政府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适当损害个人利益。
(三)是否存在高于法的人类准则?
法是社会规范的一种。然而,诸如“人类整体利益”、“人类未来发展”等话题并不由社会来调整,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社会的存在。由此我们感受到法律的局限性。那么,是否存在高于法的人類准则呢?
自然法学派肯定了高于法的准则的存在。他们认为在国家制定的实在法之外,还存在着一种“自然法”。自然法代表着法律的理想状态,是对法律的终极价值目标的追寻。[10]因此,如果我们将“法”这一概念限制为“实在法”,那么,按照自然法学派的观点,“自然法”即永恒不变的最高道德和最高正义才人类的最高准则,是法律之上的规则。
而包括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和社会法学派在内的分析法学派则否认了公平正义等高于法的准则,着力分析真正的法或“严格意义的法”,即国家制定的实在法。他们认为,道德等因素凌驾于法律之上,会使法律有失公正客观进而失去权威性,还会助长无政府主义。需要明确的是,分析法学派并未否认道德的意义,也未否认道德与法律的联系,只是反对道德对法律的直接影响。社会主义法学派将法律作为社会调控的方式之一来理解法律,这本身就是对道德、宗教等其他社会规范重要性的承认。而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家哈特承认道德对法律的影响,只是反对直接以道德或正义作为检验检验特定法律的法律效力的标准。[11]
(四)小结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知,三大法学派均认可对风险的行政调控和必要条件下公共利益对个人利益的适度损害,但对于强制性行政干预公民生育权的根据和正义性存在不同看法。新自然法学派认为,虽然剥夺两名婴儿的生育权是违反了现有法律规范的,但这一做法是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的,因此它为高于现有法律规范的“自然法”所允许,不仅是正义也是必需的。而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和社会法学派则认为,“非法即不义”,反对剥夺两名婴儿的依法享有的生育权。
四、结语和反思
回顾上述研究,我们发现,在处理基因编辑婴儿的生育权问题时,法律规范自身的效力存疑,难以适用;而不同学派的法学思想又尚未达成统一,得出的结论不同甚至相对。这种矛盾混乱的局面不利于我们从法律的层面处理基因编辑这样的新兴问题。
因此,笔者呼吁有关部门以处理本次“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为契机,加强基因编辑领域的立法。一方面,我国在基因编辑的和基因治疗方面存在“法律空白”,目前对类似行为进行规制的依据仅有《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两部部门规章,法律位阶较低,且处罚较轻。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发展,在未来必然存在更多对于人生殖细胞和胎儿进行基因编辑的行为,如果这些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这样既不利于保护受害者的权利,也有损法律的权威。
总而言之,科研机构和医疗单位应当自觉遵守有关规定,而有关部门也应加强相关领域的立法,避免基因编辑技术的滥用或不正当使用。只有双方共同努力,才能让科技真正造福人类,保障人类未来发展的和谐与稳定。
参考文献:
[1]仲崇山. “基因编辑婴儿”打开了潘多拉魔盒?[N]. 新华日报,2018-11-28(015).
[2]许婧婷. 论公民生育权的法律保护[D].南京师范大学,2017.
[3]张春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释义[M]. 法律出版社, 2003.
[4]赵鹏. 《风险、不确定性与风险预防原则——一个行政法视角的考察》[J].行政法丛论,2004,21(1):187-211.
[5]王春英,庞明.从守夜人到管理者──西方国家政府职能的演变[J].中国公务员,1996(08):46-48.
[6]廖然琴,邱太昌.论卢梭的自然法思想[J].信阳农林学院学报,2018,28(02):8-10.
[7]储有德.当代西方新自然法学派评述[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7(04):90-95.
[8]邓春梅.论古典自然法学与分析实证主义法学[J].求索,2007(09):114-116.
[9]庞德.法律与社会控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04.
[10]刘云林. 自然法学派和实证法学派论争的法伦理启示 [J].伦理学研究,2012,57(1):01.
[11]陈应珍. 关于哈特和庞德法律思想的比较[J].荆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04(1):8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