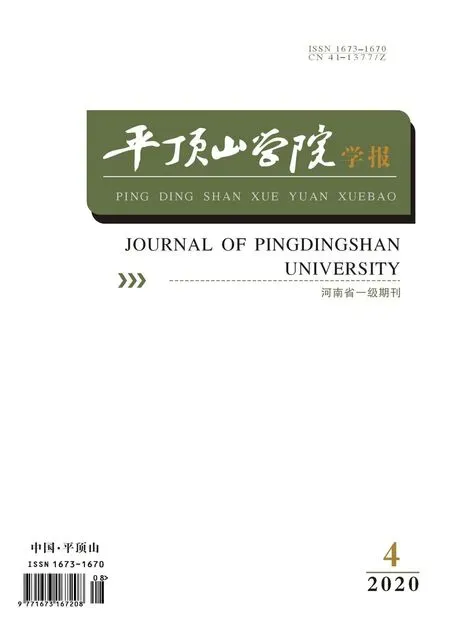《野有死麕》诗旨考辨
李颖燕
(复旦大学 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野有死麕》为《诗经·国风·召南》第十二篇。自来解此诗旨者众多,莫衷一是。本文举要各家观点,考证诗中名物,探究诗旨本原。
一、诗旨举要
古人对《野有死麕》诗旨探讨颇多,其中较有影响力的观点集中于以下几点:
第一,恶无礼。此说认为天下无序,多淫欲之风,女子仍恪守礼节,劝阻吉士无礼之行径,如吕祖谦言:“此诗三章,皆言贞女恶无礼而拒之,其辞初犹缓而后益切。曰‘有女怀春,吉士诱之’,言非不怀婚姻,必待吉士以礼道之,虽拒无礼其辞犹巽也。曰‘有女如玉’,则正言其贞洁不可犯矣,其辞渐切也。至于其末,见侵益迫拒之益切矣!”[1]55—56
女子所处的大乱之世究竟为何时,学者有两种看法。一说纣王之世,如孔颖达言:“作《野有死麕》诗者,言恶无礼。谓当纣之世,天下大乱,强暴相陵,遂成淫风之俗。被文王之化,虽当乱世,其贞女犹恶其无礼。经三章皆恶无礼之辞也。”[2]615一说平王东迁之时,如王先谦言:“此诗为东迁后西都畿内之人所作无疑。虽时当衰乱,犹知见不善而恶之,斯周初礼教之遗、圣主贤臣之化,入人为至深矣。”[3]111但无论创作于何时,持此观点者都强调王政教化之功用,认为女子于乱世恪守礼仪,是因文王礼乐之治让“恶无礼”的观念深植于人心。
第二,刺淫奔。此说认为士与女均失礼节,行淫奔之事。这一观点始于欧阳修:“纣时男女淫奔以成风俗,惟周人被文王之化者,能知廉耻而恶其无礼,故见其男女相诱而淫乱者,恶之曰:‘彼野有死麕之肉,汝尚可以食之,故爱惜而包以白茅之洁,不使为物所污,奈何彼女怀春,吉士遂诱而污以非礼。’”[4]
“恶无礼”与此说之差异在于前者认为男子失礼、女子守礼,而后者将男女双方均视为礼节背叛者。如黄櫄《毛诗集解》言:“前一章为责男子之辞,次一章为责女子之辞……白茅之洁,惟恐为物所污,况吉士可以诱怀春之女哉?此深责男子之辞……野有死鹿之肉,以其可用可食,而束之以白茅,况如玉之女,其可以不自爱乎?此深责女子之辞。”[5]
在此观点下,女子被塑造成接受吉士诱惑,欲拒还迎的形象。如季本《诗说解颐》言:“此淫风也。女子有为吉士所诱者,而不忍绝以竣辞,谕使徐徐过从,故诗人乐道之也。”[6]而“有女怀春”便是此说评定女子淫秽之关键证据,如许谦《诗集传名物钞》言:“此淫奔之诗也。错简在此,气象与二南诸诗不同,虽欲曲说,归之于正,终恐有碍。盖‘有女怀春,吉士诱之’两句是一诗大意。麕之自死者遗于野,人尚以为可食。以白茅之洁者包之而去,此有女子怀春则吉士其诱之矣。谓之怀春,固非贞静之人,而又曰诱之,非淫辞而何哉?”[7]
第三,言杀礼。杀礼,即简化礼节,《周礼》言:“凡礼宾客,国新杀礼,凶荒杀礼,札丧杀礼,祸灾杀礼,在野在外杀礼。”[8]1949此说认为天下大乱,凶荒积年,男子以“死麕”“白茅”做聘礼,简化婚嫁礼节,如《毛传》曰:“凶荒则杀礼,犹有以将之。野有死麕,群田之获而分其肉,白茅取洁清也。”[2]615
诗中杀礼是否象征礼乐崩坏,学者又持不同看法。一则认为杀礼亦是遵循礼节,为礼正之行,如顾广誉《学诗详说》言:“昏姻必有媒氏道成之,白茅包麕是纳采之杀礼,舒而脱脱是亲迎之杀礼。六礼为礼,礼之正也。杀礼亦为礼,礼之变而不失其正也。”[9]一则认为杀礼之举,使二人婚礼不正,亵渎礼节,如王安石曰:“昬礼,‘死’贽不用。今用‘死’,则非礼之正也。然犹不为无礼……‘野有死麕,白茅包之’者,礼之薄也,而犹愈于无礼。”[10]
第四,赞贞女。此说认为女子反对男子强暴行为,具备坚贞不屈之品性,如朱熹《诗集传》:“南国被文王之化,女子有贞洁自守、不为强暴所污者,故诗人因所见以兴其事而美之。”[11]15梁寅《诗演义》言:“贞女不为强暴所污,故诗美之。”[12]

第六,寄托言。此说认为《野有死麕》为比体诗,借女子形象言志。然其所喻之人有两:一喻炫才求用者,“女子怀春”即为有求于人,文末拒绝男子媾和之行,又指其不愿被逼迫,如章潢言:“炫才求用于人,又欲人勿迫于求己也,可乎哉?诗人不过托言怀春之女以讽之耳。”[15]一喻隐逸高士,“有女如玉”表现其人洁身自好,不妥协于吉士又象征其不愿与世俗同流,如方玉润《诗经原始》言:“愚意此必高人逸士抱璞怀贞,不肯出而用世,故托言以谢当世求才之贤也。”[16]113
二、“麕”“白茅”“朴樕”考证
“麕”“白茅”“朴樕”为《野有死麕》名物,探究三者的文化内涵,有利于辨析诗旨。
第一,麕。麕属鹿类,朱熹言:“麕,獐也,鹿属。”[11]15鹿被古人视为神兽,具有浓厚的文化色彩。
首先,鹿为先民崇拜之物。第一,视鹿为太阳使者。鹿角在夏天自然脱落,《逸周书》提道:“夏至之日,鹿角解。”[17]先民认为这是鹿角在传递太阳的旨意,鹿也就成为沟通人神的神兽。第二,视鹿为繁殖之象征。鹿与人类生育特征相似,且繁殖能力旺盛,故被赋予繁衍崇拜的色彩,如《山海经》记载一种叫“蜀鹿”的神兽,相传佩戴它的皮毛,可保子孙昌盛:“有兽焉,其状如马而白首,其文如虎而赤尾,其音如谣,如人歌声。其名曰蜀鹿,佩之宜子孙。”[18]4674
其次,鹿为婚娶之礼。《仪礼·士婚礼》将婚礼分为“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其中纳征所用之礼就是鹿皮,如《说文》言:“《礼》:‘丽皮纳聘。’盖鹿皮也。”[19]790传说这一礼节始于伏羲,《世本》载:“伏羲制以俪皮嫁娶之礼。”[20]“俪皮”即成对的鹿皮。因此,鹿皮便为重要的婚嫁之物,以鹿为贽符合婚嫁礼仪之道,如孔颖达疏《礼记·月令》:“按《世本》及谯周《古史》,伏犧制以俪皮嫁娶之礼,既用之配天,其尊贵先媒,当是伏犧也。”[21]值得注意的是,将鹿作为嫁娶的聘礼,一因鹿结伴而行之特征,如《说文》言:“鹿,旅行也。鹿之性见食急,则必旅行。”[19]790二因鹿生殖繁衍之色彩,表现先民对生命延续的重视。
第二,白茅。白茅为一种草本植物,《本草纲目》载:“白茅短小,三四月开白花成穗,结细实。”[22]洁白柔软之特征,使白茅成为祭祀、分封的重要工具。
首先,白茅用于祭祀。第一,白茅是缩酒道具。“白茅缩酒,灵巫拜祷”[23],缩酒为古代祭祀方式,祭祀者洒酒于白茅之上,酒渗入其中,寓意神灵饮酒,黄庭坚曾有诗记载这一活动:“栾公千岁湖冥冥,白茅缩酒巫送迎。”[24]白茅为这场祭祀仪式不可缺少之工具,如《左传·僖公四年》载:“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25]第二,白茅为祭祀草垫。古人祭祀时,会将祭品置于白茅之上。《周易》言:“藉用白茅,无咎。”[26]83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26]83白茅既洁且柔,将其置于祭品之下,体现出祭祀者恭敬、虔诚的态度。如此谨慎,自然“无咎”,如孔颖达疏:“柔处下,心能谨慎,荐藉于物,用洁白之茅,言以洁素之道奉事于上也。‘无咎’者,既能谨慎如此,虽遇大过之难,而‘无咎’也。以柔道在下,所以免害。”[26]83
其次,白茅为分封工具。《尚书》曰:“厥贡惟土五色。”[27]311孔颖达疏:“王者封五色土以为社,若封建诸侯,则各割其方色土与之,使归国立社。其土焘以黄土。焘,覆也。四方各依其方色,皆以黄土覆之。其割土与之时,苴以白茅,用白茅裹土,与之。必用曰茅者,取其洁清也。”[27]311-312天子授命,在国中建太社,以五色土筑坛,东青、南赤、西白、北黑、中黄,分封诸侯之时,取对应方位的土,用白茅包裹,授之。蔡邕称此为“茅社”,可见白茅对这场仪式的重要性。
值得注意的是,白茅裹物具有真诚郑重之色彩。“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术也以往,其无所失矣”[26]164,祭祀与分封,均为国之大事,白茅虽轻,此举却重。《野有死麕》中吉士用白茅裹麕,亦是体现对女子之重视,如王先谦言:“诗人览物起兴,言虽野外之死麕,欲取而归,亦必用白茅裹之,稍示郑重之意。”[3]142

薪柴为古代婚礼仪式的重要工具。首先,迎亲时以薪烛照路。“士昏礼,凡行事必用昏昕”[34]2095,古人于昏时迎亲,需薪柴作火把照光。《仪礼·士昏礼》言:“从车二乘,执烛前马。”[34]2078注云:“使徒役持炬火,居前照道。”[34]2079“持烛开道”的环节,让薪柴成为迎亲之工具,如胡承珙曰:“诗于昏礼每言析薪,古者昏礼或本有薪刍之馈耳。盖刍以秣马,薪以供炬。”[35]其次,束薪象征婚礼完成。“男女待礼而成,若薪刍待人事而后束也”[2]772,古人捆绑薪柴代指男女双方婚礼结束,寓意二人成婚合乎礼仪,孔颖达解释这一现象曰:“言薪在田野之中,必缠绵束之乃得成为家用,以兴女在父母之家必以礼娶之乃得成为室家。薪刍待人事而束犹室家待礼而成也。”[2]772
因此《诗经》亦常以薪喻婚。魏源《诗古微》言:“三百篇言取妻者,皆以析薪取兴。”[36]具体见于《汉广》“翘翘错薪,言刈其楚。之子于归,言秣其马”[2]592,《绸缪》“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2]772,《南山》“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2]747,《伐柯》“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2]851,《车舝》“析其柞薪,其叶湑兮。鲜我觏尔,我心写兮”[2]1035等。
三、题旨探析
至此,我们可对《野有死麕》诗旨做进一步辨析。
第一,刺淫奔,认为《野有死麕》描写男女无道淫奔之事。此说曲解“有女怀春”之意,忽视“春日相欢”之古俗。《周礼·媒氏》曰:“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8]1580中春之时不禁幽会,男女谈情亦为礼法所容,“有女怀春”正是点明这一时间,突出二者约会之正当性,如孔颖达疏:“言春,据成昏之时。吉士诱之,乃于纳彩之先,在春前矣。但以昏时为重,故先言怀春也。”[2]615李光地在《榕树语录》中给出更直白的解释:“《野有死麕》篇之言‘怀春’,非是如俗下所谓‘思春’。《周礼》仲春会男女,不是男会女、女会男,想是男女各为会。‘玄鸟至’,‘祠高禖’,即此时也。当春而出,则曰‘怀春’耳。”[37]于春日向往爱情是女子正常心思,并未带有淫欲之色彩,况女“如玉”,末句又对士急切不合礼数的行为进行劝阻,何至于淫奔?故此说恐有误。
第二,述杀礼,认为《野有死麕》遇乱世简化婚嫁礼节。但恰如前文考证,以鹿为礼,是古已有之的婚嫁传统;以白茅裹之,体现男子郑重真诚之心理;朴樕为薪,更是婚礼必不可少之道具;这些行为都是合乎礼节,遵循传统,并非遇到凶年简化婚制的偶然现象。因此,此说对婚姻古制有误读,忽视了诗中名物在婚嫁礼制上的功用与意义。
第三,赞贞女。《野有死麕》中女子的确贞洁有礼,但此说对诗中男子形象过于否定。“吉士”为古人对男子的美称,诗中以此言之,可见对其并未一味贬斥,如王质所言:“女至春而思有所归,吉士以礼通情,而思有所耦,人道之常。或以怀春为淫,诱为诡;若尔,安得为吉士?吉士所求必贞女,下所谓如玉也。”[13]20况且春日男女相会,互诉爱慕,合乎当时礼法;男子白茅裹麕,遵循婚制,态度诚恳;文末女子劝阻之言,语气温和,未有被逼迫之感,何来强暴之行?如吕祖谦言:“毛、郑以诱为道,《仪礼·射礼》亦先有诱射,皆谓以礼道之,古人固有此训诂也,欧阳氏误以诱为挑诱之诱,遂谓彼女怀春,吉士遂诱而汙以非礼,殊不知是诗方恶无礼,岂有为挑诱之汙行,而尚名之吉士者乎?”[1]56故此说刻意抬高诗中女子形象,过度贬低吉士形象,恐有误。
第四,叙民风。《野有死麕》对古代婚制有所提及,但男女二人之形象为诗歌所要传达的主体信息,对二者言行的评判才是诗歌主旨之所在,仅将“叙述民风”视为诗旨,恐是以偏概全。
第五,寄比体。此说一将女子比作有求于人者,但诗中吉士主动向女子献礼,望与之结好,何来女子相求之说?此说二将女子比作不愿为官的贤士,但诗中明言“少女怀春”,只是对吉士过于急躁之行为有所抵触,并非回避男女之情,何来避官之谈?因此,这一观点过于牵强附会,恐有误。
最贴合《野有死麕》诗旨的应为“恶无礼”。历来学者对此说存疑主要有二:
其一,认为女子“怀春”,不可视为贞女。如方玉润《诗经原始》言:“女而怀春,尚称贞女,天下有是贞女乎?”[16]113但如前文所论“怀春”不是淫乱的标志,而是少女憧憬爱情之正常心态。恋爱中的女子未被情爱所惑,仍能恪守礼法,足见王政教化的深远影响,这也正是“恶无礼”的诗旨体现。如钱澄之《田间诗学》言:“女子及笄之年,而有怀春之心,以来吉士之诱,亦倩所宜有者,而卒能守身如玉,不为所诱,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也。与江汉之思游女者同归于正,非得王者教化之深不能有此。”[38]
其二,认为末章是女子欲行淫奔之事的言谈。如陈廷敬在《午亭文编》提道:“诗言以茅包麕而诱怀春之女,又述此女之辞‘姑徐徐其来,无感我帨,无使厖吠’,有幽婉之情,无严峻之意,安见其恶无礼也?”[39]解答此点之关键在于对“舒而脱脱兮”的理解,毛《传》解“舒,徐也”“脱脱,舒迟也”[2]616。郑玄云:“贞女欲吉士以礼来,脱脱然舒也。”[2]616故“脱”非“脱衣”,而是“迟缓”之意。此句不是女子对吉士脱衣轻缓之叮嘱,而是对其无礼之行的劝阻。这也佐证女子对礼节之恪守,对失礼行为之厌弃。
要之,《野有死麕》讲述吉士与女子为相恋双方,士遵循婚制,以白茅裹麕相赠。男方欲有越礼行径,遭到女方劝阻,告诫他不可急于一时,应恪守礼节。
四、余论
《野有死麕》主旨之辨析,对我们的启示有以下三点:
首先,重视名物考证。《诗经》表达含蓄、隐晦,所用名物常具深义,赋比兴之手法又借名物呈现,如《昆山徐氏经解》言:“六经名物之多,无逾于《诗》者。自天文、地理、宫室、器用、山川、草木、鸟兽、虫鱼,靡一不具,学者非多识博闻,则无以通诗人之旨意,而得其比兴之所在。”[40]因此研究名物有助于发现诗歌细节,还原诗歌风貌,探究诗歌主旨。《野有死麕》中“麕”“白茅”“朴樕”等名物,均体现出吉士会女之合礼性,“赞贞女”“述杀礼”等说忽视其作用。
其次,重视作者编创思想。孔子编《诗经》之寄托为恢复周礼,选诗原则为“助于教化”:“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41]而二南作为“至正”之诗、雅乐代表,更维护礼乐制度。故《野有死麕》内核为“礼乐文化”,功用为“制礼作乐”,这是不可背离的选编基准。“叙民风”“寄比体”等诗旨的出现,便是忽视作者编创思想的遮蔽现象。
再者,重视作品之历史语境。文学作品是时代的产物,探究其主旨应回归创作语境,不可以今虑古、以今例古,想当然耳。“奔者不禁”的风俗,“鹿皮为聘”的礼节,“持烛束薪”的婚制,都是《野有死麕》的原生创作背景。宋儒以“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认为诗中男女逾越礼之规范,视《野有死麕》为淫奔之诗,王柏甚至要将其剔除于《诗经》:“若淫奔之诗,不待智者而能知其为恶行也,虽闾阎小夫,亦莫不丑之。”[42]这是背离文学历史语境,以现世观念揣测文学作品的差错理解。
因此,辨析文学主题,应坚持实事求是之标准,从文本出发,回归历史语境,还原古人之创作观念与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