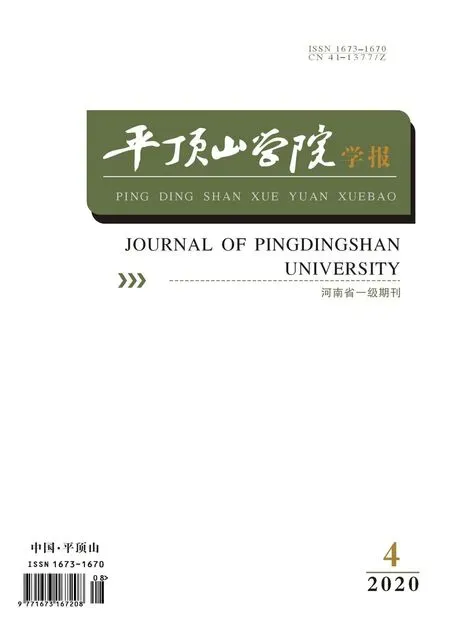《歧路灯》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
欧阳健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和《竹书纪年》于晋咸宁、太康间自汲郡战国魏墓中重见天日不同,清初李绿园所撰长篇小说《歧路灯》,200年来尚有“三五部抄本于穷乡僻壤间”[1]206,后复有洛阳清义堂1924年的石印全本和北京朴社1927年的冯友兰、冯沅君兄妹勘校的铅印前二十六回本,但终究是知者甚稀,将次晦没。现在,《歧路灯》一百零八回经栾星同志校注,由中州书画社出版了,这实在是一件应该受到称赞的大好事。
早在20世纪20年代,郭绍虞先生就盛赞《歧路灯》是“有价值的伟著”[2]788,朱自清先生也认为“《歧路灯》是中国旧来仅有的两部可以称为真正‘长篇’的小说之一”[3]553。20世纪80年代初,姚雪垠同志为《歧路灯》作序,更肯定《歧路灯》在我国古典长篇小说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而另一方面,我国小说史研究的开拓者鲁迅、胡适以及其他前辈学者似不曾注意到它,几乎所有的文学史、小说史著作,也都没有提到它。这种奇妙的状况意味着,《歧路灯》在中国小说史上究竟应该占据什么地位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一
中国的小说自来无史,留给我们的只是一部部现成的作品。要研究中国小说演进的历史,只有靠历史的、辩证的眼光,去透视这一部部作品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应该把一部小说史看成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其中,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物质生活的变化,是小说发展的客观条件,而作品内容和形式的继承与创新,则是小说史长河的实体。我们要确定一部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般应从三个方面去考察:第一,要看在这部作品之前曾经产生过什么杰出的作品,它从它的前辈那儿继承了些什么(包括思想内容、表现形式等方面),在什么方面提供了比它的前辈更多、更新的东西;第二,要看与这部作品同时,即在相同或相近的气候土壤中产生了哪些作品,它们之间的同异高下如何,从中看出它的独特的贡献表现在什么地方;第三,要看在这部作品之后,又有什么杰出的作品问世,它在哪些方面可以成为自己后来者的前导,或者为后来者提供了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教训。
从时间上看,《歧路灯》写于18世纪中叶,比《水浒传》晚400年左右,比《西游记》晚200年左右,比《金瓶梅》晚150年左右,比《醒世姻缘传》晚100年左右,和《儒林外史》几乎同时。“绿园与吴敬梓为同辈人,少敬梓六岁。《歧路灯》开笔的第二年,《儒林外史》已脱稿,当《歧路灯》约写完五分之三时,吴敬梓客死于扬州。”[4]10比《红楼梦》略早:“绿园较曹雪芹年长约九岁,《歧路灯》开笔比《红楼梦》开笔早六年,绿园约写完《歧路灯》的前八十回以‘舟车海内’辍笔时,《红楼梦》尚未具雏形。绿园老年续写《歧路灯》的结尾部分时,大约高鹗也正在续写《红楼梦》的结尾部分。”[4]8-9上述时间表,可以大致判断《歧路灯》在小说史上的坐标。当然,单凭这份时间表来安排它的历史地位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具有根本意义的东西。首先我们必须判明:《歧路灯》处在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发展进程中这样一个时间表中间,是纯粹偶然的,还是有其内在逻辑的必然性?它是这一历史长链中一个可有可无的附加物,还是一个有机地衔接在其中的环节?
李绿园有丰富的文学史素养,对于古典小说中的杰出作品都非常熟悉。他在《〈歧路灯〉自序》中说:“古有四大奇书之目,曰盲左,曰屈骚,曰漆庄,曰腐迁。迨于后世,则坊佣袭‘四大奇书’之名,而以《三国》《水浒传》《西游》《金瓶梅》冒之。呜呼,果奇也乎哉!”[5]在《歧路灯》中,关于这几部书的话头也时时出现。如书中写到戏班上演《全本西游记》《潘金莲戏叔》《武松杀嫂》等,写到衙门幕友说“《三国》上‘六出’‘七擒’,《西游》上‘九厄’‘八难’,《水浒传》李逵、武松厮打的厉害,《西厢记》红娘、张生调笑的风流”(1)李绿园:《歧路灯》,郑州:中州书画社,1980年版。本文所引《歧路灯》文本均据此书,不再一一出注。等。小说中巫翠姐称赞,“像那瓦岗寨、梁山泊,才是正经贼”,已是出语惊人;侯冠玉授徒,竟以《西厢》为教材,以《金瓶梅》为课外读物,公然赞美“这《西厢》文法,各色俱备。莺莺是题神,忽而寺内见面,忽而白马将军,忽而传书,忽而赖柬。这个反正开合、虚实浅深之法,离奇变化不测”。赞美《金瓶梅》,“那书还了得么?开口‘热结冷遇’,只是世态炎凉二字。后来‘逞豪华门前放烟火’,热就热到极处,‘春梅游旧家池馆’,冷也冷到尽头。大开大合,俱是左丘明的《左传》、司马迁的《史记》脱化下来”,更是惊世骇俗之谈。尽管作者一再斥责《金瓶梅》为“宣淫之书”,《水浒传》为“倡乱之书”,尽管小说中的侯冠玉、巫翠姐都是作者有所贬抑、否定的人物,但我们仍然不难看出,作者对于元明戏曲小说是相当熟悉的。主观上对过去作品思想倾向的排斥抵制,并不妨碍创作实践上对它们的优秀传统,尤其是创作方法和艺术技巧的容纳和继承,这在李绿园身上是奇妙地统一起来的。这一点,从《歧路灯》这部作品本身,可以得到令人信服的证明。
二
自两宋以来,由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级的兴起,促使中国文学发生了深刻变化,其标志就是“其时社会上却另有一种平民底小说,代之而兴了。这类作品,不但体裁不同,文章上也起了改革,用的是白话,所以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6]在“说话”艺术发展的基础上,我国第一部现实主义白话长篇小说《水浒传》诞生了。《水浒传》以“讲史”的形式记叙了宋江起义的传说,并借助这个大轮廓,把许多本来属于“小说”(名“银字儿”)范畴的传奇、公案、烟粉、灵怪、扑刀、杆棒、妖术、神仙类的相对独立的故事连缀成一个整体。《水浒传》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座丰碑,它实际上成为后世小说创作异常丰富的源泉和典范。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既影响到《说岳全传》这样的英雄传奇小说,也影响到《龙图公案》《三侠五义》这样的公案侠义小说,但是,真正成为开拓性的、具有创新意义的,却是它对于《金瓶梅》这样的人情小说或曰社会小说的影响。从《水浒传》题材的固有属性来看,它应该是叱咤风云的英雄传奇,然而由于《水浒传》创作过程的特殊性,使它更多地具备了“为市井细民写心”,即以市井细民的眼光来观察、思索、评价现实世界,从而写出市民尤其是中下层市民的思想、感情、愿望的特质。在《水浒传》中,出现了相当多的对于市民家庭日常生活的描写,给人以很深的现实感。如果说从描写神怪、英雄到平凡人的日常生活,是小说发展的重大转折的话,那么《水浒传》正是实现这一转折的先驱。
《金瓶梅》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典小说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从《水浒传》中武松故事的一支,派生出了以西门庆这一市井恶霸、暴发商人和封建官吏三位一体的家庭的兴衰故事;发扬了《水浒传》重视日常生活描写的特点,进一步摆脱了历史事件的羁缚,而以现实中平凡人物的家庭兴衰史为题材,并取得了成功。但是《金瓶梅》还不能不有所依傍,撇开了《水浒传》,就不可能有《金瓶梅》,更不要说它在不少地方还干脆大段移录《水浒传》的原文。同时,所谓《金瓶梅》是“我国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的论断,也大有讨论的余地。赵景深先生认为:“《金瓶梅词话》是民间的集体创作。”[7]徐朔方先生说:“兰陵笑笑生之于《金瓶梅》并不象(像)曹雪芹之于《红楼梦》那样纯然是个人创作,而更象(像)罗贯中、施耐庵之于《三国演义》《水浒传》那样的关系,是在艺人说唱——词话的基础上写定的。”[8]由此看来,说《金瓶梅》是第一部文人独立的创作,还很难成为定论。相比之下,《歧路灯》方称得上真正的文人独立创作的、以家庭为中心描摹世态的杰出长篇白话小说,它不仅继承了《金瓶梅》从内容到形式的许多长处,而且有很大的发展与提高。
暴露社会的黑暗,是《金瓶梅》进步意义之所在;《歧路灯》通过对于社会环境和人物形象的描绘,也相当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败。娄潜斋参加会试,仅因策问中有“汉武帝之崇方士,唐宪宗之饵丹药”之言,影射了当朝皇帝,就被主考官弃置不取。谭孝移不愿为官,主要是因为“阉寺得志”而“实难屈膝”,且“怕的是廷杖——这个廷杖之法,未免损士气而伤国体”。在这些方面,锋芒都是指向最高统治者的。作品还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各级官僚胥吏索贿受贿的无耻勾当。谭绍闻因平定倭寇有功,奉旨朝见,兵部书办却以“文副贡叫兵部引见,向无本例”为借口,百般勒索,直到盛希瑗偷垫了二百四十两银子,才得引见。小说辛辣地说:“银子不到书办手,如何能合朝廷的例?”谭孝移被保举为“贤良方正”,书办也借“包文移巧词渔金”,直待银钱到手,果然是“舟子不费丝毫力,顺风过了竹节滩”。这些堂堂正正的事尚且如此,到了那需要官吏徇情枉法之处,就更是“钱上取齐”了。《歧路灯》第五十二回写谭绍闻为“诱赌逼命”一案,找夏逢若、邓兰变策划,向董县主送了一份厚礼,有一段“四六”文:
结交官府,全靠着“谨具”“奉申”;出入衙门,休仗那“年家”“顿首”。倘拟以不应之律,原是陋规;若托乎致敬之情,也像典礼。长者如卷轴,方者如册页,无非上好的纱罗绸缎。走者拴蹄角,飞者缚翎毛,俱是极肥的鸡凫猪羊。光州鹅,固始鸭,还嫌物产太近。汤阴绸,临颍锦,尚觉土仪不奇。当涂莼,庐陵笋,广宁蕨,义州蘑菇,远胜似睢州藻豆、鲁山耳。安溪荔,宣城果,永嘉柑,侯官橄榄,何须说河阴石榴、郑州梨。上元鲥,松江鲈,金华熏腿,海内有名佳品。广昌葛,昆山苎,蒲田绒绢,天下无双匠工。毛深温厚,蔚州熊豹之皮;长腰细白,吴江粳稻之米。武彝茶,普洱茶,廷平茶,各种细茗。建昌酒,郫筒酒,膏枣酒,每处佳酿。色色俱备,更配上手卷款绫。多多益善,再加些酱筒醯瓮。尤要紧者,牛毛细丝称准二百两,就是师旷也睁眼;最热闹的,小楷写满十二幅,总然陈仲亦动心。
简直是一篇绝妙的声讨行贿的檄文。正如满相公所说,“天下无论院司府道,州县佐贰,书办衙役,有一千人,就有九百九十个要钱作弊的”。这种对于封建统治集团黑暗内幕的暴露,还不深刻,还不触目惊心吗?
从对经济关系的描写入手,反映出那一时代的历史内涵和本质特点,是《金瓶梅》认识价值之所在;《歧路灯》通过艺术形象的描写,也写出了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升沉变化,对于社会历史进程作了真实而生动的反映。一方面,作品写出了封建世家没落的不可阻挡的颓势。盛希侨家、谭绍闻家、张绳祖家,乃至夏逢若家,祖上都曾经做过大大小小的官,都为子孙积下了厚薄不等的家业,然而纨绔子弟不事生业,坐吃山空,即使不走“歧路”,也难以持久。走科举之路,升官发财,实在也希望甚微。难怪像盛希侨那样豪爽的人物,也要商量着“做一宗生意,图个营运”了。另一方面,作品也反映出市民阶级虽然还残留着旧日那种卑谦的心理。如王春宇所说的那样:“小弟不成才,把书本儿丢了,流落在生意行里,见不的人。”他们艳羡封建世家的门阀地位,要与之结亲拜友,但财大气粗,情况又可以说是今非昔比。宋云岫从事海上贸易,资金共长了一万三千五百二十七两九钱四分八厘,慷慨地支持谭孝移、娄潜斋:“只要中进士,拉翰林,做大官,一切花销,都是我的,回家也不叫还。”充分反映了工商业者“不干净”的金钱,已经侵蚀到“圣洁”的科举中来了。但是,金钱本是无情物,所谓“仁不统兵,义不聚财”,资本膨胀起来的工商业者,以他们所拥有的金钱的力量,尤其是高利贷的力量,咄咄逼人地向封建世家进逼过来。王中对谭绍闻说:“咱的来路抵不住利钱,将来如何结局?”正道出了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
洞达世情,写出形形色色的鬼蜮形象,是《金瓶梅》在艺术上的突出成就。在这一方面,《歧路灯》也有过之。现作一个比较。应伯爵是《金瓶梅》中最重要的反面典型之一,序中说“作者借应伯爵以描画世之小丑”。应伯爵插科打诨,趋炎附势,固然丑态百出,令人生厌,但这个小丑充其量只能算一种类型化的漫画式的平面的角色,是某种抽象意念的化身。而《歧路灯》中的夏逢若,却是一个具有多层次、多侧面的立体的形象。他是勾引谭绍闻一误再误的“调唆犯”,但作品也竭力写出他的喜怒哀乐,他的卑劣手段,无赖声口和处世哲学,最丑恶的本质与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完美的艺术形象,浑然融为一体。
如果说以上几个方面是《歧路灯》与《金瓶梅》所共有而《歧路灯》又出而上之的话,那么,《歧路灯》更具有《金瓶梅》望尘莫及的长处,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两点:
第一,《金瓶梅》是以反面人物为主角的小说,全书通是黑暗、腐朽,看不见光明、看不见理想。《歧路灯》则不然,它的主导面是宣扬正理、宣扬上进。作品所树立的正面模式固然只是“用心读书,亲近正人”,企图用此以挽救封建世家衰败的颓势。正如朱自清先生所指出的,“《歧路灯》的题材,简单地说,只是‘败子回头’。但这个败子,本来并非败子,他父亲竭尽心力,原想他成为一个克家的令子;而他自己也时时在理欲交战中。他父亲死了,他结交了‘匪类’;因为习染的关系,便让欲将理战胜了。‘东捞西扯,果然弄的家败人亡’。后来受够了‘贫苦煎熬’,阅历了人世险诈,加以族人、父执、义仆等的规劝,这才‘改志换骨’,重新让理将欲战胜了。这个理欲不断的战争和得失,便是本书的教训,或说是理想”[3]553-554。朱自清不赞同对《歧路灯》中的“理学话”采取全盘否定态度,说:“那些理学话,又都是作者阅历有得之言,说得鞭辟入里,不枝不蔓;虽是抽象的,却不是泛泛的,所以另有一种力量,不至与老生常谈相等。”[3]554这些话都说得很好。《歧路灯》还通过一批好官的正面形象,表达了作者“爱惜民命”的思想。祥符知县荆公尝对幕友说,他“一切官司也未必能听断的如法,但只要紧办速办,一者怕奸人调唆,变了初词;二者怕黠役需索,骗了愚氓;三者怕穷民守候,误了农务”。娄潜斋做济宁知府,也主张“狱贵速理”,说:“人命重情,迟此一夜,口供就有走滚,情节便有迁就。刑房仵作胥役等辈,嗜财之心如命,要钱之胆如天,惟有这疾雷不及掩耳之法,少可以杜些弊窦,且免些乡民守候死尸,安插银钱之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道台谭绍衣对“邪教”一案的态度。谭绍衣得了抚院密委,带了三百名官兵,二十名干役前去捕捉。当谭绍衣见了“邪教”奉祀的神轴,暗道:“可怜这一个奇形怪状的像,葬送了一家性命。”他搜查到一本黄皮书儿,即塞在靴筒内,临了,只逮去主犯王蓬一名。当王蓬在审讯时招供那黄皮书上记载的乃是他所封的“将军”“布政”所布施的银钱数字时,谭绍衣即怒责他“胡说”,并指示招房“这几句虚供不用写”。事后,抚台提出“还得追究党羽”,谭绍衣说:“此犯渔色贪利,惑愚迷众,这众人尚不在有罪之例。”结案回来,取出靴筒内黄本儿向烛火一燃,细声叹道:“数十家性命,赖此全矣。”作为封建国家机器组成部分的官僚,他的职能自然是镇压人民的反抗,这一点在谭绍衣也不会例外;但是他在极为复杂的情况下,却能保持头脑的清醒,不去罗织钩致,而是“曲全生灵”,这种思想意识是值得肯定的。谭绍衣式的好官形象,是以往的文学作品中所不曾有过的。总之,对于人民的一定程度的同情,是《歧路灯》中可贵的具有积极意义的元素。
第二,《金瓶梅》充斥大量露骨的色情描写,笔墨秽亵,而《歧路灯》则完全不同。《歧路灯》写谭绍闻为匪人引诱,日趋堕落,吃酒赌博,狎尼宿娼,堕入恶趣是很容易的。但作者头脑清醒,书中有诗云:“每怪稗官例,丑言曲拟之。既存惩欲意,何事导淫辞?”作者坚决不蹈“小说家窠臼”,因此通篇笔墨干净,毫无不堪入目之处。这一点不仅《金瓶梅》难以望其项背,即便《醒世姻缘传》与《红楼梦》也无法相比。由此可见,《歧路灯》是继承了《金瓶梅》的长处,避开了《金瓶梅》的短处,有所发展、有所创新的,真正由文人独立创作的现实主义长篇白话小说。
三
《歧路灯》和《儒林外史》的作者,由于生活经历、艺术情趣以及世界观的不同,使这两部作品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存在明显的差异;不过,它们所反映的却是同一个时代和那一时代固有的矛盾,反映着这种矛盾的社会思潮,却不免同样会在两部作品中打下自己的烙印。
乍一看来,《歧路灯》与《儒林外史》的思想倾向是完全相左的。后者痛诋科举制度,鄙夷热衷功名者的肮脏灵魂。前者则主张“认真读书”,津津乐道于“金榜题名”,但那仅是一个方面的现象,而且即使在这一方面,二者也有相通点。
《儒林外史》中的马二先生,曾经宣扬“‘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大道理,说“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而《歧路灯》中的侯冠玉,也公然宣称“时文有益,《五经》不紧要”,因为“学生读书,只要得功名;不利于功名,不如不读。若说求经史、摹大家,更是诬人。你想古今以文学传世者,有几个童生?不是阁部,便是词林,他如不是大发达,即是他那文章,必不能传。况且他们的文字俱是白描淡写,直与经史无干。何苦以有用之精力,用到不利于功名之地乎?”请注意,侯冠玉在《歧路灯》中,是比马二先生更受到否定和指摘的反面形象。《儒林外史》通过王冕之口,指责八股取士之法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歧路灯》也反对八股文,主张通经致用。书中写出的几个正面人物如娄潜斋、程嵩淑等,都是极少八股气的豪爽正直的人物,娄潜斋就说过“若一定把学生圈在屋里,每日讲正心诚意的话头,那资性鲁钝的,将来弄成个泥塑木雕;那资性聪明些的,将来出了书屋,丢了书本,把平日理学话放在东洋大海”的话。他还认为“士农工商,都是正务”,这些见解都比较通达。作品还写谭绍闻闲谈中,留心浙东宁波人士关于火攻破倭寇的议论,及至随谭绍衣御敌之时,果然以火箭大破倭寇,这也是“经世致用”的结果。
《歧路灯》还塑造了一群颇具“儒林外史气”的人物形象,往往亦能“烛幽索隐,物无遁形”[9]229。如谭孝移在戚翰林寓处遇见的少年得志的濮阳太史,趾高气扬,矫饰作态,要草青词,又不懂老子过函关坐什么车的典故。待谭孝移恭敬地告诉以后,他便“忽的站起身来,说道:‘本欲畅谈聆教,争乃敝衙事忙,明日建醮,该速递青词稿。幸会,幸会。’一面说,一面走”了。祥符县副学陈乔龄,更是不学无术。他自己承认“我当日做秀才时,卷皮原写习《诗经》,其实我只读过三本儿,并没读完。从的先生又说,经文只用八十篇,遭遭不走。我也有个抄本儿,及下场时,四道经题,俱抄写别人稿儿。出场时,连题也就忘了。如今做官,逢着月课,只出《四书》题,经题随秀才们自己拣着做,就没有经文也罢”。
惠养民绰号“惠圣人”,满口正心诚意,井田封建,“早把个谭绍闻讲的像一个寸虾入了大海,紧紧泅了七八年,还不曾傍着海边儿”。他在孔耘轩的席上大批《阴骘文》,说:“吾儒以辟异端为首务,那《阴骘文》上有礼佛拜斗的话头,明明是异端了。况且无所为而为之为善,有所为而为之为恶,先图获福,才做阴功,便非无所为而为之善了。”谁知在离席谢扰时,却开口道:“耘老果品极佳,恳锡三两个。有个小儿四岁了,回去不给他捎个东西,未免稚子候门,有些索然。”这种刻画,亦可称“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诚微辞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矣”[9]231。
另外,如“平素好做几句歪诗,竟看得是为其事于举世不为之日,又好在《字汇》上查几个画数儿多的字儿,用到他那诗上,自矜淹博”的谢经圻。“初在各铺子前柜边说闲话儿;渐渐的庙院看戏,指谈某旦脚年轻,某旦脚风流;后来酒铺内也有酒债,赌博场中也有赌欠;不与东家说媒,便为西家卜地”的侯冠玉。自称“方外野人,尘心久淡”“爱这丹诀,能周人济厄”,实则是大骗子的武当山道士等,都使人几乎感到是俨然游于《儒林外史》之中。
当然,《歧路灯》与《儒林外史》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各有其侧重点,并不等量齐观。就其总容量来说,《歧路灯》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似乎要更广阔一些,它所包容的思想内涵,也似乎要更丰富一些,唯此之故,《歧路灯》在结构上,也就显然具有《儒林外史》不及的成就。鲁迅曾经指出,《儒林外史》“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9]229。而《歧路灯》结构完整而严谨,朱自清先生说它“全书滴水不漏,圆如转环,无臃肿和断续的毛病”,实非过誉之词。《歧路灯》第一回“念先泽千里伸孝思,虑后裔一掌寓慈情”,写丹徒宜宾派谭绍衣下书,邀移籍祥符的鸿胪派谭孝移南去共修族谱,从“念先泽”到“虑后裔”,揭示了全书的大纲。朱自清先生说:“这第一回文字在结构上,却是极有意义的:它不但很自然的引出全书,并且为后面一个大转机的伏线……这样大开大阖而又精细的结构,可以见者作者的笔力和文心。”[3]555接着写谭孝移延师教子,极为细密慎重,师严徒聪,甚为相得;接着写颁下喜诏,谭孝移被举为“贤良方正”赴京,临别要言叮妻,此为一小转折。接着写谭孝移病故,临终病榻嘱儿“用心读书,亲近正人”,此为一大转折;父死师惰,谭绍闻年幼失教,便为“匪类”所诱。一误于盛希侨,再误于夏逢若,三误于茅拔茹,四误于张绳祖,五误于高皮匠,六误于管贻安,七误于钱可仰,八误于虎镇邦,九误于赵天洪,十误于武当道士。作者笔力遒劲,文气茂畅,大起大落,大开大阖,敢于相重相犯,决不避重就轻,诚乃弄潮之好手,雕龙之巨匠。郭绍虞先生说:“他写到谭绍闻的堕落,那就一直写下去好了,那知他偏要在此间生出许多波澜,卖弄手段,才堕落,又悔悟,才悔悟,又堕落,层波迭澜,真如置身山阴道上,应接不暇。”[2]787朱自清先生说,作者还“处处使他的情节自然地有机地发展,不屑用‘无巧不成书’的观念甚至于声明,来作他的藉口;那是旧小说家常依赖的老套子。所以单论结构,不独《儒林外史》不能和本书相比,就是《红楼梦》,也还较逊一筹;我们可以说,在结构上它是中国旧来唯一的真正长篇小说”[3]555-556。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总之,从中国长篇白话小说的演进史来看,《水浒传》—《金瓶梅》—《歧路灯》,是一条有着内在联系的轨迹,而《儒林外史》则似乎还处在这条轨迹的边上,尽管在文学史上,《儒林外史》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
四
《缺名笔记》云:“吾乡前辈李绿园先生所撰《歧路灯》一百二十回,虽纯从《红楼梦》脱胎,然描写人情,千态毕露,亦绝世奇文也。”[1]206说《歧路灯》“纯从《红楼梦》脱胎”,是弄错了作品写作年代之故,然而这一误会却并非全无道理,它表明《歧路灯》和《红楼梦》二者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的地方。对比二者的异同,不仅可以进一步摆正《歧路灯》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还可以悟出若干中国小说发展过程中的规律性的东西。
从取材看,《歧路灯》是“记载一家的盛衰”[2]780,与《红楼梦》同。《金瓶梅》虽然也写了一个家庭的历史,但西门庆只是一个市井的暴发户。《歧路灯》写的则是一个四世“书香相继,列名胶庠”的封建世家。这样一个封建世家,由于其自身的腐朽性,加上商品经济的冲击、高利贷的盘剥,已经濒于“灯消火灭,水尽鹅飞”的境地。作品介绍说,“论起来谭绍闻家私,每年也该有一千九百两余头”,他收入的主要来源是佃户缴租和出赁房银二项。但开销过大,入不敷出,“手头委实没有”,债务猬集,只能割产还债。相形之下,南乡的吴自知,是个令人生厌的“乡瓜子”,但“若是要一万两万,他也不费周章”;王春宇做药材生意发了大财,竟讲到几十万上,连家人的子孙开粮食坊子,也有了三千家当,当日主人家的后代倒要向他借贷。这种经济上的分化,更加速了封建世家走下坡路的进程。《歧路灯》第七十八、七十九回,写谭绍闻在盛希侨的支持下,硬撑着为母亲祝寿,并庆贺巫氏得子,书中评论道:“这两回书,街上送屏的花团锦簇,厅前演戏的绕梁遏云。若论士庶之家,也就算繁华之甚、快乐之极了。我再说一句冷水浇背的话:这正是灯将灭而放横焰,树已倒而发强芽。”真是充溢着封建末世的悲哀。尽管作品主张通过读书—科举—做官来挽救世家的没落和衰败,但给人的感觉是无力的,没有什么指望的。
同是写家庭的盛衰,《歧路灯》的谭家与“衣冠簪缨之族,钟鸣鼎食之家”的贾府相比,只能是小巫见大巫。唯此之故,狭小的碧草轩,就只能供几个人物一时的坐起,不像大观园那样,足以成为包容几乎一切重场戏的舞台。不过,这个先天的不足,倒促使《歧路灯》不得不把视线投向更为广阔的社会,在与社会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中,来更为真切地揭示封建世家衰败的历史原因。《歧路灯》展现了开封这个古老都市的风情世态,还通过谭绍闻的足迹,把这种社会风貌的描写扩大到外乡如亳州、济宁等地,这种活生生的社会风俗的描述,是极其成功的。正是在这样极为广阔的社会生活背景下,《歧路灯》着意描画了上百个不同阶级、不同阶层“千态毕露”的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朱自清先生评论道:
本书不但能写出各色人,并且能各如其分。《儒林外史》的描写,有时不免带有滑稽性的夸张,本书似乎没有。本书尤能在同一种人里,写出他们各别的个性,这个至少不比写出各色人容易。如他写娄潜斋、侯中肴、惠养民同在谭家做过教读先生,但心地、行止是怎样悬殊!又如谭绍闻、王隆吉、盛希侨都是好人家子弟,质地都是好的,都是浮荡少年;这样地相同,而度量、脾气又是怎样差异!作者阅世甚深,极有描写的才力,可惜并没有尽其所长。他写道学的反面,原只作为映衬之用。他并不要也不肯淋漓尽致或委曲详尽地写出来,所谓“劝百而讽一”,想他是深以为戒的。但是他写得虽简,却能处处扼要,针针见血。这种用几根有力的线条,画出鲜明的轮廓的办法,有时比那些烦琐细腻到使人迷惑的描写,反要直捷些,动人些。但以与《红楼梦》的活泼,《儒林外史》的刻画相比,却到底是不如的,因而薰染的力量也就不及它们了。本书之所以未能行远,这怕也是一个原因吧。
这是很有见地的。毋庸讳言,由于作者世界观、艺术观的限制,《歧路灯》没有达到《红楼梦》所达到的高度。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它不像《红楼梦》那样,对所谓“仕途经济”等一系列涉及封建制度的根本问题提出怀疑,相反,它主张挽回颓变的世风,主张把那些浪子从“歧路”中拯救出来。尽管作者的正面说教是真诚的,甚至是出于自己阅历有得之言,但那毕竟是与历史的潮流背道而驰的。第二,它不像《红楼梦》那样具有对于女性的推崇和尊重的态度,提出新的爱情婚姻的观点,相反,它主张三从四德,主张德言容工。它没有塑造出真善美高度统一的堪与林黛玉相匹敌的妇女形象,没有设计出令人回肠荡气、难以忘怀的缠绵悱恻的故事情节,未免使艺术感染力大为减弱。这两个方面是《歧路灯》的根本弱点,也是它不能吸引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主要原因。
朱自清先生说:“若让我估量本书的总价值,我以为只逊于《红楼梦》一筹,与《儒林外史》是可以并驾齐驱的。”[3]556恰如其分地指出了《歧路灯》在我国小说史上的地位。《歧路灯》是中国长篇白话小说写实主义传统的历史长河中的一个中间环节,它既是《水浒传》《金瓶梅》的继承和发扬光大者,又是与《红楼梦》在几乎相同的历史条件下,由具有不同世界观、艺术观的作家的不同创作实践下的产物,它们之间的对比,有助于揭示小说发展史上许多令人深思的规律性的东西。
【按】本文作于1982年7月,收录于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的《文学论丛》1983年第2辑。兹略做订正,旧文新刊,以纪念李绿园逝世230周年暨栾星校注本《歧路灯》出版4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