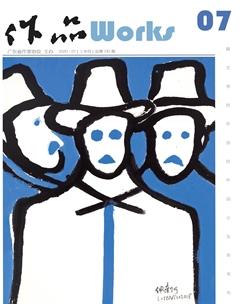谁能揪住时光背后的东西
柳冬妩
现代诗歌作为最敏感的心灵艺术,现代诗人浑身布满了一触即发的超导体,即使在不同的时空语境里,情感世界中许多普遍的东西都能产生共鸣和共振。阅读吴伟华的组诗,让我想起了希门内斯的《谁能了解时光背后的东西!》:
多少次,曙光/被高山遮蔽!//多少次,天际壮丽的彩霞/却孕育着迅雷霹雳!//那支玫瑰竟含剧毒。/ 那把利剑却是生命的武器。//我曾想在路的尽头/找到鲜花盛开的草原,/然而却陷进一潭污泥。//我梦寐以求人间的荣耀,/却在天国赢得一席之地。
现代诗歌在本质上是一种时间的艺术,个体对时间的独特体验是许多现代主义诗人表达的重要主题和思考世界的方式。作为杰出的象征主义诗人,希门内斯将人、自然、世界共存共生的时空体验,建构到一幅诗歌世界的大境界、大诗意的图景中,他对彩霞和霹雳、鲜花和污泥、生命和死亡、人间与天堂的吟咏,在时间的维度里打开了一种开放和辐射式的写作。与希门内斯相类似,吴伟华的诗歌也充满了心灵时空的场景切换,通过抒情主体在时空坐标系中位置的确立,把一些象征性的终极问题呈现了出来,形成了一个丰富的诗歌时空体,试图引导我们去了解和揪住时光背后的东西。吴伟华在《夕光》中的吟咏,是对时光的一种挽留:
看完落日,我不知该为此刻的宁静/做些什么。梅花已回到枝头/树木回到丛林/眼前的峭壁,回到了群山//身边的同伴都已离去/我曾经有过那么多担心,却没有/任何人作过交换//就在这渐渐幽深的时光里/万事万物越来越陌生/我从蓄满悲喜的尘埃身上,一点一滴/找回自己//那一块块发出微小光芒的。
希门内斯感叹“曙光被高山遮蔽”,吴伟华在诗里沉思于落日的宁静,让梅花回到枝头、树木回到丛林、峭壁回到群山,在“渐渐幽深的时光里”,“从蓄满悲喜的尘埃身上,一点一滴找回自己”。对诗歌艺术的追求,既是对生命时空的不息追问,也是对生命本体的深深索引。诗歌与诗人的时空体验紧密相关。离开了深厚的时空体验,离开了对于人,以及万事万物的洞察,就不会产生诗的语言,也就不会产生诗的意象。吴伟华的诗,与他的个体生命和情感世界紧密相连,是诗人在宁静时空中心灵的独特感光与显影,“光阴对我不再构成任何威胁”(《暮年》)。吴伟华的吟唱表达了对夹杂在昼夜轮换、人生嬗递之间的情感体验,在这种纠葛中所作的徘徊、游移,甚至心灵的挣扎。但他的诗歌始终又有一种暖色调,一种灵魂的力量,每一次阅读,我都能触摸到诗人似乎阅尽苍茫后的沉静,感受到诗人充盈的思想,仿如“一块块发出微小光芒”灯盏穿越尘世照亮心灵。
吴伟华在时间维度上的智性拓展,体现在他对季节轮回的象征性书写上。文化人类学家发现,原始人用许多生动形象描绘、解释各种自然现象,表现出充满诗意的想象力。例如四季的变化和循环、日出日落和白昼黑夜、人的生老病死等自然现象在原始人中诱发了许多关于四季、四季神、生、死、复活的神话,流传至今仍经久不衰。雪莱的著名诗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正是使用了四季循环及其象征意义。这种关于四季的象征可以称为“原型想象”。“原型想象”就是把某一物体、事件、现象看作具有普遍性的象征意义。吴伟华在他的诗里,构筑了一个四季更替、日出日落和白昼黑夜的象征性意象体系。春夏秋冬的意象,各举一例:
一个春日黄昏,独自经过李树坡。墓群静默/看不见的亲人站在明亮的夕光里(《 枯枝记》)
在这个盛夏,朴素之物,依旧被遗弃/无声之物,亦无大用/为防中暑,宜饮冰/宜失恋/宜博物馆观古物。死去又活来(《铁证》)
秋风再一次重返人世/我相信,经过新绿时,它会略有迟疑/如同亲人般的歉意(《迟疑》)
初冬也未带回奇迹/唯有怀念,抱紧黄色的叶子四处飘荡/它们哀而不伤,但同样令人不安/在有风的街道/——风一直在吹,气息迷幻,吹向你/刚刚换上的冬装、围巾/星空辽阔,文字呼啸。一行行黑色的句子/仿佛通往世界尽头的台阶(《风吹》)
毫无疑问,吴伟华的诗与神话中的四季原型主题存在着密切关系,注意到这一点,我们也许能破译其深层的象征意蕴。春夏秋冬的意象,晨昏的意象,日夜的意象,在他的诗中共同构成一个象征体,去对抗无穷无尽的死亡、黑暗、苦难、疼痛与挣扎。读吴伟华的这些诗歌,让我想起T.S.艾略特的名句“四月是最残忍的季节”。《轰鸣》中的六月,是比四月更残忍的季节。
吴伟华对叠句的运用,更好地表达时间循环的主题,造成韵律的回环往复,遥相呼应,既保持了诗歌内容和表达形式的完整性,大大加强了抒情的感染力,又产生了一种绵延不绝、萦回于耳的声韵美感。《白云》《轰鸣》《杨梅》《铁证》起句均是“这是六月”,《造句》《沉默》《一梦》《遗嘱》《虚构》《敲门》《病中》起句均是“这是七月”,《迟疑》《风吹》《拯救》《又寄》起句均是“又是十一月”。叠句也可能由一个词构成,如美国诗人爱伦·坡的诗歌《乌鸦》(1845)中的单词“永不”。吴伟华的《晚安》全诗由“晚安”这个词构成叠句诗节:
晚安,天空。晚安,繁星和明月/晚安,没有合上的书本/晚安,真理、真相/晚安,神明。晚安,苦难中的人民/晚安,想象中的大雪/晚安,黄土岭,鲜为人知的小地方/晚安,春天,我依旧相信你。
诗人借助叠句的形式,往复回旋, 一唱三叹,深切隽永地表达了往复循环的主题。春天带来万象更新。“晚安,春天,我依旧相信你”,可能在强调人性复活和走向新生的重要性。复活是人的愿望和欲望原型。春天是复活的季节,一年又一年形成完整的代序循环。春天,正是一切生命幽秘的发源地,是万物循环的发源地。对春天的相信,这是吴伟华赋予未来的意义。正如弗莱所言,“文明社会的生命常常等同于有机物的循环过程:生长,成熟,衰落,死亡,以及另一个体形式的再生。”吴伟华的一些诗,集中表达了生死轮回的主题,如《铁证》:“这是六月。流水同样微不足道/花草料事如神,其一生,便是铁证/远和近,本是虚妄之词,如镜子的正反面……/宜博物馆观古物。死去又活来;”再如《造句》:“夏天越来越轻。时代越来越重/有时,醒来后,你恨不能加快死亡的速度/假如江山仍多情/假如风雨大作。四十个春秋,深如泥潭。”死与爱一样,是人的生命伸展到无限,是把生命攫取到伟大的循环中去,把生命擲入永恒之流的一种方式。死的震颤,是活着的人的转化法门,只有“死”才能呼唤人们对自己的有限生命作必要的创造,把自己的生活造成有意义的真实的存在。吴伟华的诗歌暗示,生命将在死亡中延续;死亡也并非生命的终结,而是无限循环的生命运动中的一个环节;生、死、死而复生是宇宙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死亡就是重返生前之生,重返死前之死,重返净界,重返母腹;人所生于斯、死于斯的世界则是一个轮回再生的世界,宇宙万物都将回复其原始状态。对这个主题的揭示,里尔克的《杜依诺哀歌》比吴伟华的诗歌深刻一些:“逝者寄拯救于我们,/ 无以复加的逝者,我们愿意并应该/ 在不可见的心中将其完全转化,化入—— /哦,无限——化入我们!/无论我们最终是谁。”“无论我们最终是谁”,都逃脱不了四季的出现和消隐。
吴伟华喜欢里尔克,他们的诗歌可以进行互文性解读,他们之间应该存在着一种师徒关系。在《杜依诺哀歌》里,里尔克“卷绕并编织无休止的尘世之路”:“我们生存时,那始终被我们割裂的,/ 这才合为一体。我们的四季 /这才形成完整的代序循环”。“天使”随着季候变化若隐若现,《杜依诺哀歌》是对岁月循环的感悟与追问:“我们只不过是从万物旁经过/有如一阵空气的交替。”“哦,春天大概知晓——,此刻无处不承载/ 报道的音讯。那最初短促的试啼,/ 与幽静相衬托,揳入一个纯净的白日,/ 一个首肯的白日那无边的沉默。/ 尔后向上的梯阶,向上的音阶,/升向梦想的未来圣殿”。在吴伟华的诗歌《风吹》中也出现了“台阶”的意象:“仿佛通往世界尽头的台阶”。从里尔克到吴伟华,他们的诗歌都用春夏秋冬、日夜晨昏的意象构筑自成一界的时空体,从一个核心但又比较细微的画面开始发力,引发出一个丰富时空体的震荡和变形。对里尔克的阅读和借鉴,可以看吴伟华在试图努力构建自己的哲思、历史和生命观照体系。
诗歌代表了人类想象力所体现的永恒形式,这种永恒体现在与四季有关的原型想象中。原型批评的理论家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认为,文学作品在整体上构成了一个“自主自足的体系”,这一体系产生于人类想象力的历史积累,从而把异化的陌生的自然界原型模式结合起来,以满足人类持久的欲望和需求。在该文学体系中,与自然界四季循環运动相对应的四种基本主题(即情节形式,或称之为结构组织原则)具体化为喜剧(春天)、传奇(夏天)、悲剧(秋天)和讽刺(冬天)四种主要的文学类型。他从人与自然的同构关系出发,总结概括出这四种类型:一是黎明、春天和出生方面。英雄出生的神话,万物复苏的神话,创世纪的神话,黑暗、冬天、死亡的失败的神话。这是春季的叙事结构:喜剧。二是中午、夏天、婚姻和胜利方面。成为神仙的神话,进入天堂的神话。从属的人物是伴侣和新娘。这是喜剧、牧歌和团圆诗的原型。三是日落、秋天和死亡方面。战败的神话,天神死亡的神话,暴死和牺牲的神话,英雄孤军奋战的神话。从属的人物是奸细和海妖。这是悲剧和挽歌的原型。四是黑暗、冬天和毁灭方面。势力得胜的神话,洪水和回到混沌状态的神话,英雄打败的神话,众神毁灭的神话。从属的人物是食人妖魔和女巫。此为讽刺作品的原型。弗莱按照时辰、四季和有机生命的循环圈,为象征、神话、艺术形象和文学类型建立了基本模式。在这四种文学类型非常重要的原型主题范围之内,每一种类型的个别文学作品中的原型也会出现许多更为有限的变体——即文学作品的传统模式和类型与社会仪式以及神话、历史、法律和事实上所有的“散乱的言语结构”相联系。这是弗莱从自然界和生命的循环运动得到启发而引申出来的。弗莱关于四季的原型批评理论,完全可以运用到对吴伟华诗歌的阐释中去,在他的诗歌里能找到与自然界四季循环运动相对应的四种基本主题。他的诗歌,是对循环时间的一种重构和命名。
在吴伟华构建的诗歌时空体中,在他诗歌的有机体中,时间与空间相互依存。时间是心灵体验的形式化,而空间是时间呈现的一种形式。吴伟华诗歌里的空间,是经过身体化的空间,通过外部对内部的侵蚀,通过内部对外部侵蚀的痛感,肉身的体验混杂到无意识的话语中,表达一个个从感性出发的身体。如《暮年》写的是身体的感觉:
毕竟是冬天,气温有时冷至骨缝/如果喝酒,除了微薰,还有一醉方休/如果遇雨,除了冥想,还有望眼欲穿//毕竟往事难懂。亦难释怀/你是否知道,你追寻的意义,丢失已久/那一刻的喜悦,如鸟鸣,似流水//毕竟我已习惯各种催眠方式/愿意再一次/将自己端端正正放回肉体中间。
时间感也好,空间感也好,都要附丽于身体,“将自己端端正正放回肉体中间”,并通过个体性的身体感受、发现和命名。 一个人就是一个身体,身体是我们在世上的唯一证据。身体安置于出发点和归宿之处。“气温有时冷至骨缝”,缘自身体的感应。万事万物的起源植根于身体,生命的秘密可以在身体上找到痕迹,它在身体上刻下烙印,身体既是对“我思”“意识”的消解,又是对时空的铭写。《游魂》一诗写收恩师诗书两册。忽读到——“有时慰藉,有时释怀”,禁不住“悲从字间起/君可知,无数次,我看着自己的灵魂/蜕下身体/但我却不知它去了哪里/小寒已过。关节酸肿,疼痛如迷”。诗歌写作是灵与肉的一种危险平衡。每一个身体始终有一个统一的意志:疼痛和愉悦,但每一个身体都是与众不同的,每一个具体的时空里所产生的效果都是有差别的。《救心》《声音》等诗歌,则是关于身体与疾病的隐喻。《秃鹰》中的孩子的身体,《小小斑马》中“小小斑马还在激流中沉浮挣扎/体力即将消耗殆尽。我关掉电视/我愿意一颗心,就这么揪着”。《锯木场》表明,连植物在特定的时空里也要考虑如何处置自己的身体:“苏醒过来的只是苔藓、蕨、车前草/它们打开陈旧的身体/接纳空气中的湿润。雨水漫不经心”。诗人的悲悯之情,不仅在他的心里,而且落实到每一个句子里。他依据自己的身体、感觉、感性和梦想,进行一种身体在场的写作,他的诗歌以身体的在场而现身。
谈到特定时空里的身体书写,不能不谈到吴伟华诗歌的叙事性特征。在他的大多数文本里,诗歌的叙事和情感是相融在一起的,可触可感的叙事因素,使诗拥有了它自身的肌质和呼吸。我们的语言和经验是从身体里生长出来的,诗歌中的叙事和人的身体、情感发生着联系,诗歌中有了事,有了情,就有了身体;有了感觉,才有活的充满了生殖能力的诗歌。吴伟华写作中出现的叙事性、戏剧化、身体描写成分等恰恰对应当代诗歌中出现的某种整体特征。在他的诗歌里,更多是关于生活琐碎事件的描写和叙述,即关注日常生活中的平常事件。叙述“小事件”,吴伟华却写出了具有“大意识”的博杂的诗篇,写出了准确真实地与社会面貌及时代进程相关联,具有某种“见证”意义的诗篇,如写工人下岗的《轴承》,即是诗人用一颗揪着的心,为我们揪住了退隐在时光背后的东西。
责编:郑小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