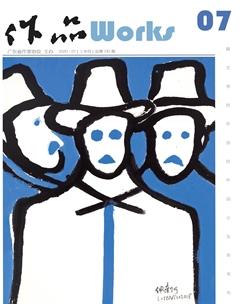闯入者
葛芳
丁果二十二岁,住在乔平城,一个城市深处简陋的公寓房。斑驳的墙面贴满了各种广告号码。她迈着飘忽不定的步子终于回来了。她没有找到任何线索,证明自己有罪。冬天太冷了,像冰窖。
脚步声,就像蜈蚣窸窸窣窣拖着尾巴,爬上楼梯,来到她门口。她打开门。不是的。是隔壁上夜班的男人,哈欠连天摸出钥匙开门。
她感觉异常孤独,春节里没有一点吉祥如意的喜气。相反,一场阴雨连绵的糟糕天气带走了她唯一可以依赖的姑母。姑母嘴瘪得好像一眼望不见底的深渊。姑母走得并不突然。眼看着殡仪馆的火苗把姑母吞噬的时候,她泪如雨下,心想,她一生的保护神走了。
连梦都要结冰的,寒冷的日子。
她抱着暖水袋,摁他的号码。他没接,直接拒绝。节假日他都陪着他妻儿,雷打不动的原则。她都习惯了,可这次不一样。她唯一的亲人去世,她觉得自己真像一片叶子,要接受风吹雨淋,不晓得日后会遭遇怎样的孤苦。她需要倾诉,需要救援,更需要他貌似怜悯的疼爱。
她知道自己貌不惊人,清汤寡水,短发,眼睛里常闪现错愕感,好像这个世界总有些不对劲。大学毕业到报社实习的第一天差点就被人嘲笑,她懵头懵脑,上厕所竟进了男卫生间,等到蹲完开出小门,发现有个男人背对着她在撒尿,弧线形的射入水槽的声音异常刺耳——
她尖叫一声,耻红着脸,尴尬奔出来。
那个男人就是她的部门领导,广告部主任唐胜,他也貌不惊人,塌鼻子厚嘴唇,一脸好人相。他“嘘”了一声,在走廊上安慰她别出声,尴尬事就自己消化不需要夸大其词。她恨不得有个地洞钻下去,自己怎么能犯这样白痴的错误?
从此,红着脸从唐胜身边走过来走过去。那抹红,成了她的条件反射,无意间在泄露内心的惶恐。他倒是忘记了,他胖乎乎的身躯在她看来就是个弥勒佛,开口常笑,大肚能容。
他的肚子確实很大,那是个巨大的盛酒器,广告部的业务基本上是靠他喝酒的本事拉到的。他仰起脖子,酒像白开水,哗哗哗流进他的嘴巴——她第一次和他出来接单的时候,结结巴巴,打开他的汽车门,怕他吐,怕他一头栽倒在地,哪想到他趴在方向盘上睡了半个小时,醒来什么事都没有,接着发动汽车,说,小苏,你住哪里,我送你回去。她连忙摆手,她觉得这样已经阿弥陀佛了,怎么好意思再让领导开车送她。
他肥厚的手掌搭过来,拍在她肩膀上,她战战兢兢。可是主任没有其他想法,他说,这么晚你一个女孩子回家,我不放心。
我不放心。
她默不作声点了点头,看上去好像在聚精会神思考着什么,实际上心潮澎湃。我不放心。长到二十二岁,只有姑母反复对她说过这样的话,再无旁人。父亲早亡,母亲改嫁,姑母可怜她这个小东西,收养并抚育她。姑母省吃俭用,供她上大学。姑母再三叮嘱她大学期间切勿恋爱。姑母爱怜地拎着她耳朵说,我不放心,你这丫头傻头傻脑,被别人卖了还帮着别人数钱。
那是个起风的夜晚,她钻出汽车的时候,主任说,我也要出来透透气,醒醒酒,不好意思,刚才让你见笑了,但现在报社需要大量的广告资金涌入,拼酒量也是必要技巧。
梧桐树的叶子有脸一样大,啪嗒落在她的肩膀上。她肩膀瘦削,胸部扁平,像是没有发育完整,在风中犹如一株淡紫色的郁金香,显得楚楚可怜。主任把梧桐叶子掸去,张开手臂,将宽厚的胸膛贴到她瘦弱的肩胛骨上。
她一愣,慌张错乱感胀满心房——但主任没有第二步,他说,我走了,你赶紧回屋,当心着凉。
她在单身公寓床上辗转不能入睡,耳畔是街边汽车的呼啸声。她想,主任不可能是那种心思,酒喝多了,他家庭和睦,也不可能看上我,他就是个长辈,想保护我。这样想着的时候她热泪盈眶,仿佛多年的孤独在回音壁上找到了相对应的洞穴,这个洞穴吸走了寒冷和孤寂,倾入世俗的温暖。
主任唐胜把这一单的业绩挂在她门下,她平生获得了第一笔奖金。当主任宣布奖励的时候,她和他眼神交会了下,那是种心领神会的默契感。她的貌不惊人获取了另一个貌不惊人的关注,她的小窃喜雾霭般,一圈圈膨胀占据了她整个胸膛,那是一种近似乡愁深沉的感动——主任是个好人。她早就听别人评价过。
她顺理成章接受了他的关心。一杯奶茶。一枚小胸针。一双鞋子。一副手套。一包零食。一盏灯。一件衣服。一支口红。一份订单……都是在私底下悄悄地送,没人知道。她心里既感动又有点惶恐。一种犯罪的味道。无功不受禄。相貌平庸但热心肠的主任送她如此多的东西,她讷讷地,嫣然笑,被人关心被人喜欢毕竟是甜蜜的,她不去管背后的原因。她和他亲昵起来,称他唐叔,谐音“堂叔”。她不晓得自己有没有嫡亲堂叔,这个从天而降的“堂叔”让她不再卑微和孤伶。
其他同事去下馆子生日聚会KTV唱歌了,这个时代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崔健和黑豹乐团也到乔平城开演唱会,《一无所有》《无地自容》重金属声音震耳欲聋,把乔平城的河水震得一波一波跃起。
微风习习,新鲜树木的气息,沁人心脾,她陪唐胜喝了一瓶红酒,晕晕然在沉醉的空气中进入了梦乡。醒来,唐胜赤裸地趴在她身上,肥厚的肚子腆着紧贴着她的乳房。她自然也是赤身。她没有尖叫,也没有惊愕,好像顺理成章的事儿。她拉上窗帘,她觉得她很幸运地要终结一个人的孤独史了,她看到自己有一种看不见的存在,真的,他的叹息,他的摩挲声,他的呻吟,都收拢在她的小掌心了。
没有人知晓他们的偷情史。
她上班,还是怯怯的,清汤寡水的脸,小雀斑在阳光下闪耀。三个实习生唯独她转岗成正式编制。她有一定的文字功夫,笔锋流畅,在报社是跑新闻条线的记者,自然能站住脚跟。他们在一个办公室,主任那间用透明玻璃隔开。她写累了站起来做扩胸运动的时候,瞅见他稀疏的头发一圈一圈盘绕在头顶时,忍不住“扑哧”一声暗笑出来。
她很识相,人前绝不露破绽,这是他们的约定。私下里纵情忘我,她的笑声在寂静中是那么清脆,那么桀骜,那么爽快,她停了下来,心醉神迷,伸长了耳朵,仿佛在聆听罕见而完美的乐器回声。
姑母终于走了,在最寒冷的日子,连梦都要结冰的日子。
她渴望睡觉。坠入黑暗,坠入梦境。梦境中,她是主人公,被分裂成两个或三个多重性格的人,她常在自己都猝不及防的狀态下享受着巅峰级别的愉悦感,然而又被孤独、耻辱践踏着,或者被某种疯狂的惊惧所驱使,醒来泪流满面。片段式的梦境,醒来后连碎片也成不了了,它成了一汪水,起初还是有形的,一摇,一晃,它全部流入了地表。
他依然我行我素,过他的逍遥日子,腆着肚子,叼着香烟,美美地享受日暮时分那缕阳光洒在脸上的感觉,然后去酒局上接洽业务,只不过不再带她了。
她没有声音,脑海里却盘算得厉害。她一路小跑,到了乔平城的市实验小学。她看见皮皮一跃跳过台阶,等待着。她小心翼翼地向前,恰好带队老师在远处张望着什么。她对皮皮挤了挤笑容,说,你还认识姐姐吗?我是你爸爸唐胜办公室的,他今天开会事情特别多,所以让我来接你。说着她拿出了唐胜办公室的一个玩具喷火小雷龙,这是平时皮皮过来最爱玩的。看见了喷火小雷龙,皮皮欣喜得眼睛直眨巴,嗯嗯,姐姐——她还带着巧克力、草莓果冻、奥特曼……她牵着他的手飞快从校门口消失,像恐龙一样在后来的世纪消失得无影无踪。
丁果看见意料中的唐胜急得焦头烂额,上蹿下跳。她缩在办公室角落里正常做她的事情。他脸色绛紫,他的老婆也出现在他办公室抓狂。那是个平庸却精干的女人,皮靴、包包都是奢侈品牌子,丁果叫不出名字,反正是大品牌。丁果带着羡慕又耻笑的眼光,隔窗望着主任老婆。办公室所有的人都站立起来议论——孩子不见了!主任家孩子不见了!赶紧去找啊!二十多个员工全部发动,各条路口,周边的小区、游乐场、公园,地毯式搜索。她也混杂其间,心不在焉装模作样地寻找。
有人建议,报警吧,二十四小时过去了——主任唐胜还是模棱两可,带着哭腔喊,再找找,再找找!再等等!再等等!
他从人群中向她扫来目光,她装作没看见。谁也没有在意那是怎样的眼神。她清汤寡水,素面朝天,一眼望得到底的小女生,有什么花头劲呢?她木木地打着瞌睡,困了,倦了,该睡觉了,主任啊,你该让所有员工下班了。
主任无力地挥了挥手,人群如鸟兽般一哄而散。
她走在回家路上,有了莫名的亢奋。到家以后,拖出床底的旅行箱,箱子很重,她下楼梯时一个趔趄,差点绊倒在地。天很黑,月亮躲在云后看不见,她拉着旅行箱。从小区直接绕到运河边。运河淤泥的味道很臭,枯涩的芦苇秆子大半腐烂在沼泽中,还有一小半挺直腰杆发出沙沙的响声。寒流又来了——防不胜防,运河边几乎没有散步的人,只有她走得热气腾腾。她好像是即将英勇就义的女英雄,为着正义去复仇去慷慨赴死。她鼻尖上全是汗。她想,即使死,她也不会一个人孤零零了,姑母在前头召唤,后面还有若干人追赶。
她记得他说过,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永恒的,要及时行乐,也要及时发泄。他还说过,这社会他妈的变化太厉害了,钱是最重要的敲门砖,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她看见办公室里的人在灯光下交头接耳,轻声交谈着。她带着一种奇怪的厌恶之情,来打量身边这个世界。一旦逃离办公室,她奔跑在大街上时,欢呼雀跃,像是得到了一个久违的麦芽糖或者一个松果。她气咻咻在运河边边转悠,昏沉的光线,高高低低的灌木丛,咕咚咕咚的流水声……她选择了一个合适的地方,把旅行箱直接往沼泽地一扔。很快,箱子下沉,浑浊的泥水冒了几个泡泡,表示箱子彻底消失。姑母的眼睛在枯枝缝隙间眨巴,她想告诉姑母,很快,春天就要来了,阵阵甜香会从树林间飘来,而小野鸭会在河边欢乐地扑腾。
回去的路上,丁果买了一串冰糖葫芦,甜而脆的味道,好吃极了,她舔了又舔,感觉像是把自己吃了。
一天以后,她没有收到主任唐胜的任何信息,却收到了公安局的审讯通知。做笔录时,她还在神思恍惚,主任家孩子失踪了,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记者。
审讯处的灯光太过强烈,射得她刺眼,她微眯着眼,在墙面上好像看到了一幅壁画,《哀悼基督》,意大利画家乔托的作品。画中圣约翰张开双臂,凝视着耶稣的尸体,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在向前的姿势中流动着。她忽然流泪了,大滴大滴的泪珠往前涌,她变成了画中的那位穿长袍的女圣徒,背对着画外,小心翼翼地托着耶稣的头,没有人知道她心里的滋味,因为谁也看不见她的表情。近处的山岗上,一棵树叶残枝枯,天空和大地被它紧紧地串在一起。而远处,灰色的山崖在寂寞中诉说着无声的绝望……
后来,她带着公安局里的人去了运河边的沼泽地。沉默在沼泽底部的箱子被打捞上来,她不想再看里面的内容——她知道,小小的皮皮成胎儿状蜷缩着,把他父亲犯下的罪行全部承担了下来。开箱那一瞬间,所有人都静穆成雕塑,世界成了一个停顿的世界。
天色渐暗,风也停了。
她回到了她的禁闭室,回想若干个画面。当皮皮屁颠屁颠跟着她来到单身公寓的时候,她给他喝牛奶、吃果冻,然后用她一条裙带勒在皮皮的脖子上。这条裙带,曾多少次被主任粗鲁地扯掉过?它现在派上了用场。皮皮的小脸从红到紫,三分钟不到就嗷呜了,她把他温热的身体放到旅行箱中,正好。她原来没有想到要把皮皮弄死的,她只是神经出现了幻觉,觉得皮皮是一只小猫,对她发脾气的小猫,嗷呜嗷呜乱叫,她忍无可忍,愤懑发展成泄愤,否则她的小宇宙要崩溃。
当主任老婆歇斯底里要扑向她的时候,她的身体纹丝不动,只有眼珠滴溜溜转过半圈,冷冷地瞥向主任。主任鼻子更塌了,嘴唇更厚了,他完全是被雷电击中的样子——她记起小时候看见过一个雨天被雷电击中的人,下身瘫痪,背部全都是伤疤。主任的模样也差不多了,他应该没有力量再扒她的内裤。
她和他的偷情故事,一下子成了乔平城百姓最热门的饭后谈资。办公室的同事们更觉得匪夷所思,不可能啊,这两个人怎么走在一起?还激起如此深的爱恨情仇?咳咳,人不可貌相,会咬人的狗不叫——千万要小心提防啊!
不过,她没有觉得不安,至少,她不用担心迷路了,她在禁闭室里,十分安全,她只需要毫不迟疑地,走下去。
她等待着审判。
她心无旁骛等待着审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监狱里,只有她文字功底最好,她协助监狱长组织文稿编排小报,做老本行得心应手的。她淡淡地微笑,两年的时光很快,即使在监狱里,空气中也能闻到栀子花的香味,潮热的气息从墙根升起来。她清晰记得两年前小野鸭在河边欢乐扑腾的场面,她没有了恨意,也没有了惆怅,因为心无挂碍无有恐怖,每天背九遍《心经》,心如止水。
由于立功表现好,她又被改判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其间,她得知,那件事以后不到三年主任又生了娃,竟然是龙凤胎,老婆才转怒为喜,于是大摆宴席,邀请报社所有同事,趁机又敛一把财。他的生活很快恢复了日常,腆着肚子,叼着香烟,美美地享受日暮时分那缕阳光洒在脸上的感觉,然后去酒局上接洽业务。看来,她也并没有夺走他的心头之爱,生活是平庸也是日常,时间能抚平一切伤痛。她再也不去品咂孤独的滋味,相反,狱中的集体生活让她心安、踏实,让她学会了与人相处,学会了与时间共度。
刑期又减了五年。当她服刑期满,走出监狱大门的时候,路边的迎春花烂漫,她四十三岁,身体圆整了些,丰腴了些,皮肤也白了些。乔平城已经进入21世纪自媒体时代,人人都在低头刷微信。街上安静空旷,只有一个看不见的人在弹奏钢琴,她路过乔平城日报社,特意打量了一番,报社大楼重新装修过了,钢化玻璃在阳光下熠熠闪光,但听说现在纸媒销量严重滑坡,甚至纸媒会走向集体死亡——嗯,她不想再提到死亡这个字眼,况且纸媒也和她无关。
一年后,她遂了愿,在县城的郊区开了一家小文印店,嫁了一个腿有疾患大她十岁的男人。
责编:鄞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