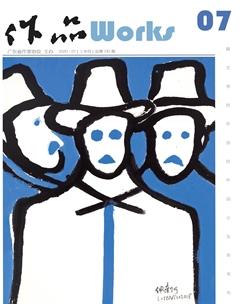我是米裳
彭杉影
1
早些年,人们称呼孙桂娥不是孙师傅,而是孙医生。那时她还在安陆那个叫赵棚的村子里,是村卫生室唯一的一名大夫。赵棚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至今也忘不了那时的孙医生,他们说起孙医生,总有说不完的故事。有人说她有两个千金,大的特别乖巧,小的特别顽皮。就有人反驳说,那个顽皮的是大的。又有人说孙医生擅长割包,说她有一把不同凡响的手术刀,那把刀有半尺长,甚至说那把刀有倒钩,当时孙医生给村里的小孩割包,总是先用刀绞几下,然后用力一拉。又有人反驳说孙医生割包不是绞几下,而是在那个包上划出一个十字架。他们最终总是争不出一个结果来,只好骂骂咧咧地不欢而散。
其实关于孙医生在赵棚给小孩们割包的事,我记得清楚,虽然我那时也是小孩。那时赵棚还没有通电,所以夏天特别热,大人可以拿把扇子摇点风,小孩子们没有那个闲心,只好闷着,脸上身上就长满痱子,然后就长包。包长大了,里面脓液饱满丰沛,就得处理。送到卫生室,孙医生让其家人用力按着小孩的手脚,她一刀划上去,脓液伴血液喷出,在空中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她然后不紧不慢地用镊子夹着黄纱条往伤口处塞。那时候村头卫生室常常有小孩在鬼哭狼嚎。村子里长了包的小孩见了孙医生就喊:快跑,孙屠夫来了。
所以说呢,那时赵棚人除了叫孙桂娥为孙医生外,还有人叫她孙屠夫的。叫她孙屠夫是因为她心狠手辣,手起刀落,眼眨都不眨一下。在赵棚人的争论中,有一点还是达成了共识的,那时候孙医生割包是从来不用麻药的,孙医生割了包之后,伤口总会非常快地痊愈。
孙医生以前是有丈夫的,但她的丈夫在他们进城不久就病逝了。他在咽气的那一刻嘱咐她要把两个女儿培养好,培养成栋梁之材,完成他未竟的愿望。孫医生含着热泪使劲地点头,如鸡啄米。他给孙医生留下了两个千金,大的叫米衣,小的叫米裳,我就是米裳。我至今都怀疑我是不是孙医生亲生的,因为米衣和我,她总是厚此薄彼。
我很小的时候,性别对我来说是个模糊的概念,我很像男孩,男孩能做的事我都会,玩水、掏鸟窝、弹珠子、爬树等,那时我是个野小子。也许就是这原因,我妈不喜欢我。米衣也不喜欢我,就像我不喜欢她一样。
那时我妈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是:怎么就没有个女孩的样,将来怎么得了。这时候,米衣也会在旁边添盐加醋:将来怎么得了啊。米衣真是讨厌,关她屁事。
2
后来我们全家响应政策号召,回到孝感城。我妈回到印刷厂当了码字工人,就没有人再叫她孙医生了,而是叫她孙师傅。其实我妈从来没学过医,在乡下她能成为医生是因为她比当地人多读过几天书,回城后理所当然是当不了医生的。
我妈很有些不适应,因为我多次听到她说,孝感有什么好啊,还不如赵棚乡下。她在怀念那些割包的日子,那些日子她风光无限。有好几次,晚上我起床上厕所,经过她的房间,看到她在房间里把玩着那把手术刀,用一块棉布仔细地擦,手术刀在幽暗的台灯下闪着寒光,她像是一名杀人的刽子手。
我后来考上了师范,因为离家不是很远,我就经常住在家里。没见到我妈再玩她的手术刀,她一定是把刀藏起来了。有一次我翻箱倒柜找拖鞋时,无意中找到了那把手术刀,她用油布纸包着藏在阁楼里了。这是一把不一般的手术刀,有倒钩,锋利无比,有一种凛然的金属光泽。我很喜欢,就收在了我的书包里,我想总会有一天会派上用场的,比如说有朝一日我去吃一只烤全羊,用上这把刀肯定能事半功倍。
3
与米衣比,我的发育是很迟缓的,米衣大我不到一岁。我刚上中师时,她胸前已是波涛汹涌,她总是很豪迈地从我身边走过,都不正眼看我一下。我的女同学们也都轰隆隆地发育起来了,胸前挺着。而我的却藏着掖着,按兵不动,弄得我很没面子,上澡堂时总是遮遮掩掩,一直到快毕业时才蓬勃起来。还有,例假大约是在十五岁的,来得很突然,早上看到床单的一片污迹,吓了一大跳,以为得了什么不治之症。阴毛,大约十四岁时,开始是一些细细的,如小荷才露尖尖角,后来便一天天茂盛起来。俗话说,女大十八变。我上中师不到一年,我的身体就完成了发育上的大飞跃。该挺起来的胸是高高地挺起来了,但是不该起来的脸部、臀部、腰部也都像是施足了肥料似的,壮大起来。米衣和我的反差太大,她和我比起来,简直是绝色美女。
不是美女又有什么关系呢?还是有人看上我的,比如那个强奸犯。
这是我这辈子中做的一件大事,我得细细说说。
那个夜晚,月色朦胧,男人的荷尔蒙应该是那时候分泌最旺盛。我那天本来不准备回家的,可是那天下午我打过羽毛球,流了汗,那么那天晚上我是一定要洗澡的,可是那天学校一直停水,男生跑到河口大桥那里去洗澡,我是女生,我不是小时候那个野小子了,我得有点淑女的范。我就等,等水,等到晚上十点多钟还没来水,就失望了。反正我家也不是很远,半个小时就能走到,我就背起包回家。出了校门,四周寂静无声,月色惨淡,远处是低矮的农户,有惨淡的灯光。我有点害怕,我提醒自己没有什么可怕的,我提醒我自己,我是米裳我怕谁。经过一片菜地时,突然被人或者是鬼扑倒了,我心惊肉跳。我在挣扎之中理清了思路,知道不是鬼,是人,还知道那人想要什么。我知道他急不可耐,那人的力气很大,很快就把我压在了身下,而且把他挺拔着的丑陋的东西掏出来了,喘着粗气,扒我的裤子。我说,大……大哥,何必这样急。那人停止了动作说,你……你什么意思?听口音,他就是这学校附近的人。我说,这好的事,要慢慢做嘛。好事要办好,是吧。他像是捡了个大便宜,喜形于色,以为我要配合他,他说,好,好。我又说,我包里有套,你用上吧。他已是乐不可支,从我身上下来了,但是没有放开我。我从包里取出来的是我妈的手术刀,我说,我给你套上。他很听话,不动了,那个丑陋的东西直挺着像是在瞄准天上那轮残月。我瞅准了时机,一手抓住那个丑陋的东西,另一只手使劲划过去,这动作很像是在乡下割稻子。一声惨烈的叫喊惊破了夜空。
后来,我被人带到了派出所,我那把带血的手术刀被搁在桌子上,所长说,你看,这是凶器,你犯了故意伤害罪。我受了惊吓,浑身发抖,根本不能和所长进行正常对话,我不记得我和他说了些什么。
但是我记得当时有位警员拿起了那把刀仔细看,然后说,所长,这真是一把好刀,我建议我们派出所的干警一人配一把这样的刀。所长使劲拍了拍桌子说,你就会出鸡巴馊主意,我们有枪,要这东西干什么,我们又不去割人家的鸡巴。他们当着我面鸡巴来鸡巴去的,根本没把我当女孩,我真是羞愧死了。
应该有人还记得,那年的春夏之交,在孝感中心医院外科楼的二楼,一个被割掉了半截生殖器的男人在那里躺了半个多月。他受伤时医院是有机会给他做缝合的,可是他们派人去那片菜地找那截东西时,已被狗吃了,几条狗东西为了这半截东西打得不可开交,差点闹出狗命来了。
据说,警察去医院找那个半截生殖器的男人了解情况,那人一直哭,不说话,根本不配合警察。后来警察给他讲了一个壁虎找尾巴的故事,那个混蛋才破涕为笑,还说,能再长出来就好,就是坐几年牢我也愿意。
我在派出所待了三天,差点崩溃死掉了的。后来我妈给干警们送来了半头猪,是她和米衣一起蹬三轮车送过去的。米衣那天流了很多汗,后来冷风一吹就感冒了。为了报答米衣的搭救之恩,我后来又很多次给她买鸡腿,绝对新鲜的那种。那次干警们吃得很开心,喝了很多酒,都把脸喝红了,所长的脸最红。他没有深究我故意伤害他人罪,定性为正当防卫,并且把刀还给我妈了,并嘱咐我妈这刀要好好保管,不可再落到我的手中。
4
这件事,老孝感人应该都还记忆犹新。那时人们津津乐道,整个孝感城都传开了,我成了那时孝感的焦点人物,我成了人们最优质的谈话资料,他们在谈论我的过程中收获颇丰,得到很多愉悦和快感。可气的是,米衣竟然在背地里说,长她那样子,还有人强奸,真是瞎了他的狗眼。好像我被人强奸这事是我讨到了很大的便宜,占了她的上风,应该强奸的是她而不是我。真是扯淡得很。
为了显示我以德报怨的宽宏气量,我当天夜里去楼下给米衣买一只炸鸡腿,是明显隔夜变质了的。这个胸部肥大,头脑简单的家伙很享受她的美味,還破例地叫了我一声妹妹。想到这只炸鸡马上在她山是山水是水的身体内旅行,我不高兴也高兴了。那天晚上,米衣一趟又一趟往厕所跑,客厅里不时响起拖鞋声,搞得我的梦分外嘈杂。
外面的传言五花八门。开始的说法比较接近事实,说那个强奸犯活该的,那个女子是英雄。后来,说法就变了一点,说怎么着也不该把人家的本钱给断了吧,不就是弄弄嘛,又不少她一块肉。再后来的说法就偏离事实太远,很不像话了,说肯定是自愿弄过了的,后来弄烦了,就截断了人家的命根。开始可能是一两个人这么说,后来说的人越来越多,我的清白和名声就受到了玷污。这风言风语不停地往我耳朵里灌,我百口难辩。但是我一定要证明我的清白,我首先想到的是到医院开一张我处女膜还健在的证明,但是我马上就否定了这个办法,一是因为我记得上中学时一次翻山时摔了一跤,下身见了红,医生说处女膜可能保不住了;二是我从医院开出了证明又能怎么样,我能把证明复印一万份贴满孝感的大街小巷吗?不能!除了开证明,我想到另一个办法,那就是自杀,以死来证明我的清白。我对米衣说我想自杀,这个家伙却笑了起来,自杀,你敢吗?真是的,米衣总是这样看不起我,大智大勇的米裳不敢自杀?
我相信老孝感人不会忘记那年精彩的一幕。那是一个夏日的傍晚,在槐荫大道那栋古建筑的三楼,一个身材稍肥胖的女子望着下面的滚滚红尘和围观的人们,一跃而出,那声“啊”的一声叫传遍了方园数千米,女子落在了很厚的棉絮上,毫发无损。她在棉絮上稍作休息,理了理头发,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回家了。
可以看出来吧,那次跳楼我是精心策划了的,时间地点都拿捏得非常准确。那天正有警察在那附近巡逻,那地方在学校和我家之间。我跳下去的时候警察已弄来了好多棉絮铺在了地上。后来,有人说,何必要跳楼啊,可以用那把刀割腕划脖子嘛。真是他妈的井蛙之见,老子又不是真的想自杀。再说,那把刀也找不到了,被我妈藏得很紧。
5
经过了被强奸和跳楼,我米裳没少一根毫毛,想开了什么事都没有,但是我妈孙师傅整天忧心忡忡,抬不起头来。她担心我的未来,我成了她的心病,她怕我嫁不出去。我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之后,孙师傅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长成这样,以后的婚事怕是要吃些苦头的。况且我又割人又跳楼的,弄出了这大的动静,谁还敢要啊。她幻想哪天一顶花轿把我抬走,她心里就踏实了,就是一台破轿也行的,她想把我嫁出去,嫁祸于人的心都有了。而她的宝贝女儿米衣,那真是一盏省油的灯,或者说她根本就不用油。我妈是胸有成竹的,她曾经亲眼见到米衣和一个高大帅气的男人手牵手走在天桥下面,她心里充盈着满满的幸福。那个男人年龄看起来是大点,但大点有什么关系,大男人才懂得体会人,孙师傅是把对米衣的满意扩大到了她未来的女婿了。
但是我敢说,在婚途上我比白白净净无脑子的米衣会更顺风顺水,虽然暂时看不出来,但这结论就像影子前面一定有不透明的障碍物一样明白无误。
6
我虽然不如米衣漂亮,但脑袋比她好使。比如,中师毕业那年,我又做了一件大事。要是米衣遇到这事,哼!结果肯定是不堪设想的。
这是我这辈子又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我得细细说说。
大致是这样:我虽然不喜欢米衣,却乐意做她的跟班。美女米衣总是能收集到很多来自四面八方的目光,跟她一起,这目光也分一小半到我身上。
在那个夏天,当米衣邀我一起去武汉玩时,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坐火车去的,到了火车站时,我和那个死丫头走散了,然后就被一个人盯上了。我神色有点不安,穿着有点像打工妹。盯上我的人是一个肥胖的中年妇女,四十岁左右。我坐在花坛那里时她走了过来。她操一口不太标准的普通话,普通话里带着很浓的湖南口音。我在赵棚时,村里有个从上面派下来的驻队的人就是湖南人,所以口音我熟。胖女人笑容慈祥,像是好人。她虽然手里拿着招工表,但不是好人,她是人贩子,她和旁边的一男一女低声说话,用的是方言,我能听懂,知道了他们是在做着见不得人的勾当。她说她们厂正在招工,工资高,活轻。我说,我还有伙伴,你那里能不能多几个人啊?她说,好啊,我们厂正缺人呢。我说,你把你们厂的地址告诉我,我回去告诉她们,然后和她们一起来找你们厂吧。胖女人说,那太慢了吧?况且你们也不容易找到那里的。要不我现在就和你一起回你那里,把她们叫上,然后一起去?我说,那当然好。我和胖女人就一起坐车,是在新华路坐的汽车。一路上,胖女人不停地夸我长得好看,真是他妈的睁着眼睛说瞎话。她又说他们的工厂有多好多好,吃海鲜住别墅。两个多小时后到了,不是到了孝感城,而是到我的老家赵棚。我把胖女人带到老光棍胡叔的家里,胡叔不在家。我让胖女人等一会,我说去把那几个伙伴找到,收拾一下就跟她走。她就留在那间破房子里,还说,你看,这差的房子,是得早点出去赚钱的。我出去,在村头找到了胡叔,我说,胡叔,给你弄了个媳妇,在你屋里呢。胡叔说,你就会和叔说笑。我说,是真的,我是专门过来给你送媳妇的。胡叔将信将疑,一脚高一脚低往家里赶。我在他身后说,叔,那是你的女人了,你想怎么弄都可以的,不要舍不得啊。
这事还是惊动了警方。第二天早上那个胖女子仓皇出逃,胡叔在后面追,派出所的小王正在那一片巡逻,就把那个女人逮住了。我也被请进了派出所,一番审问过堂,干警们非常兴奋,因为他们不费什么神就抓住了一个人贩子,而且顺藤摸瓜还能捣毁了一个贩人团伙。
胡叔从派出所出来时无比惆怅和沮丧,他叹了口气说,好日子真是太短了。我说,叔,你不要不知足,没把你当强奸犯抓进牢里就该谢天谢地了。我走的时候,胡叔一再央请我,下次再给他带一个女人回吧。
这事影响深远,在孝感人心中留下的记忆要久远多了。那年这件事传遍了大江南北,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听说孝感有女子被拐卖的。据说,人贩子学精了,孝感的女子是不能拐卖的,怕的是没拐到别人,自己却被拐卖了。
米衣又犯了老毛病,背地里说,长她那样,也有人拐卖啊,真是瞎了他的狗眼。像是我又捡到了一个大便宜似的,这次又是我占了上风,好像该拐卖的是她而不是我。真是岂有此理!
表面上,米衣是服了我,说我真是英雄,大智大勇,要是她,可能已经被卖了,她还是有点自知之明。
7
这该是好事吧,可是我妈想不开,她像是得了忧郁症,总是唠叨,这下好了,连人贩子都被你卖了,谁还敢要你啊?她真是杞人忧天。
其实我在读中师时是谈过一个朋友的,他叫杨帅。杨帅的确很帅,可是我和他的恋爱持续时间短。我后来得知他之所以要和我谈朋友,不是真正地想和我谈朋友,他是想体验,不让在读书时期少了恋爱这一课。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家里太穷,他吃不到什么好东西,跟我谈恋爱,我少不了带他吃几回麻辣烫臭豆腐。他总是以牵牵我的手、摸摸我的头发以示回报。那一阵,我妈如释重负一般高兴,如果我晚上在家里待着,她会说,出去玩啊,在家待着干吗?她就是想我和杨帅缠在一起,随便干什么都行,最好是杨帅能立即把我的肚子弄大。可是杨帅总是和我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我记得他只吻过我一次。而且是额头,像是做操,很有仪式感。我妈见过杨帅一次的,那次我和杨帅一起走出校门,正从暗影处往阳光里走,她过来了,连忙说,你就是杨帅啊,你喜欢我们家米裳啊,好啊,好啊。她热情过度了,听起来不像是好啊好啊,倒像是,谢谢啊,谢谢啊。我真是羞死了。
杨帅那家伙后来看上了米衣,真是见了个鬼!他见了一次米衣之后就迷上了她。他见到米衣时,眼神是直的,然后像蜘蛛一样在米衣身上忙碌了半天。后来,他反复说,真是想不到!我知道他的意思,一是没想到我还有一个如此貌美的姐姐,二是没有想到姐妹俩相差竟然如此大。这个没出息的东西,米衣在校门口对他浅浅一笑,他浑身的骨头都酥了。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那个杨帅帅他的去吧,给老子滚远些,老子不稀罕。他后来的目的竟然是想通过我来接触米衣,无耻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想一想就知道嘛,人家米衣那時是万人迷,哪轮得上他杨帅。再说他一个靠恋爱来混点臭豆腐的苦孩子侍候得起我们家米衣吗?他是想破他的脑壳都没有用的。他也是够痴迷的,深夜在我家院门外的树下等待徘徊观望,我知道他是在等米衣,米衣那会不在家,约会去了呢。我站在阳台对着夜空高声吼:还不滚蛋!再不滚,老子的手术刀不客气了。
8
米衣终于和那个男人分开了,人家是有妇之夫呢,人家的妇还是悍妇。米衣给他下了最后通牒,逼着他娶她。那个男人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过了一阵就差人给米衣送来了一张五万元的支票。米衣在我面前把支票弹得脆响,很看得开的样子,干吗不要,不要白不要。
这下好了,老米家的两个千金在婚途上都悬了空。我妈在接受了这残酷的现实后开始寻思出路,老大米衣不是重点,少了那个男人,还有成群的男人排队等着,还是米裳难办。我又发现,我妈又开始怀念那些在赵棚的日子。又有几次,晚上我起床上厕所,经过她的房间,看到她在房间里把玩着那把手术刀,用一块棉布仔细地擦,手术刀在幽暗的台灯下闪着寒光,她像是一名杀人的刽子手。那把刀被我妈藏在哪里了,这真是个谜。
她一定是想了好多,突然间一觉醒来后,就逼我学做菜、学烹饪,她是想给我未来的夫家一点补偿,所谓堤外损失堤内补。这可对了我的路子,因为我天生就是个吃货,很快我就能烧一手好菜,色香味俱全。米衣却说,成天就惦记着吃吃吃,到底还是苦孩子。米衣也真是的,给她吃了,吃得比谁都欢,还这样说,真不是个地道的角色,难怪那男的不要她。
如果谁以为烹饪只是手上的功夫,那就错了。烹饪和文化历史、文学艺术等都密不可分,我迷上了烹饪之后,在晚报上发了多篇关于饮食文化烹饪营养之类的文章,我的文笔生动,一点也不枯燥。报社看上了我,他们说这作者文采不错,观念前沿,就请我做了晚报的专栏作者,很多人开始叫我作家。孙师傅也是歪打正着,一个作家身份送给未来的夫家那不是一份厚礼又是什么?
我妈还逼我跑步、打球、练呼啦圈。每天傍晚时就死死地盯着我,要是我没有动静,她就像催命地叫,长这肥,还不动动的。有时我被她逼得烦不胜烦,会呛她几句,就知道一天到晚逼逼逼的。她说,到你腰是腰屁股是屁股时我就不逼你了。经过孙师傅和米裳本人的不懈努力,米裳的体重终于止于峰值,开始下滑,有点显山露水的味了。
米衣也没闲着的,走马灯似的换朋友,三天两头换。后来,米衣看上了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项峰,从来不看电视的米衣每天到了项峰那个节目点都盯着电视不放。我家里只有一台电视,我那时候正要看中央电视台的烹饪营养节目。那次,我和米衣抢遥控器,差点打起来了。她说,什么玩意,一天到晚就记得吃吃吃。我说,什么玩意,不就一不咋样的节目主持人。她说,你懂得鬼,你看人家的眉毛,多有个性,最关键的是你看人家多会说话,你知道不,他是武汉大学的高才生,在大学生辩论会上夺得团队第一,他个人还是最佳辩手呢。我说:民以食为天,他能不能不吃不喝地说说说,不死才怪的。她顺手就已经调到了孝感生活台,米衣的偶像正在妙语连珠,他旁边的女搭档被他逗得笑弯了腰,我们的米衣也喜不自禁,跟着有一搭没一搭地笑,像个白痴。
后来我才知道,米衣是认识项峰的。项峰和米衣是转了几道弯的同学。有一次米衣的闺蜜约米衣去K歌,米衣到达指定包房时那里已有二男三女,是米衣的闺蜜的同学约的场子。米衣不认识更多的人,除了闺蜜,就有一个男子她似曾相识。那人就是项峰,米衣是在电视上见过他的。K歌的气氛开始怎么都难上去,大约因为这是一个组合班子,人还不大熟。后来,米衣点了一首歌,是对唱,约项峰一起唱,他们配合得不错,有点珠联璧合的意思。再后来,项峰约米衣跳了舞,场子的气氛就活了起来。应该就是那次K歌之后,米衣就开始跟我抢电视。
我们在客厅吵起来的时候,可怜的孙师傅只好躲在她自己的房里端祥着老米的遗像暗自垂泪,她在向米老头作深刻的检讨呢。后来,我再没和米衣争电视机了,我用我的稿费买了一台,放在我的房里,我关上房门,想怎么看就怎么看。
可是不久,米衣就不看电视了,以前铁定要看项峰节目的时间,米衣要么根本就不看电视,野到外面去了,要是在看电视,就绝对调到其他台,绕过项峰的节目。而且,有一次我还听到她在客厅嘀咕,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当过辩手的嘛。我经过客厅时,很礼貌地问她,姐,谁有什么了不起啊。她把腿翘在沙发上,懒洋洋地说:就是那自以为了不起的人呗。我分析,不是项峰拒绝了她,就是项峰已经有女朋友了,反正米衣是没戏了的。
9
不久之后,有人发现,那个在晚报做专栏的作家有过传奇的经历,曾割了强奸犯的生殖器,跳过楼,还卖过人贩子。这消息在孝感城静悄悄地传开,传到电视台后,他们觉得这个懂饮食文化的生动的血肉丰沛的有纵深感的孝感女子应该在电视上露个脸,让孝感人民都见识见识。
电视台和我约了,要我上电视做个节目,那个节目叫“孝感女人”。 我妈坚决反对,还上电视啊,还不嫌乱的。我这才得知,我妈一刻也没闲着,一天到晚在给我物色对象,她说有好几个得知我割过强奸犯的生殖器,跳过楼,还卖过人贩子,面都不准备见了。后来,我和电视台说好了,上电视嘛,要上的,这多好的事呢,但是不能提及割生殖器、跳楼、人贩子的事,谈饮食,谈文化,谈写作,谈我们孝感的特产嘛,可多了呢。他们就同意了。
我上电视做节目的衣服是米衣帮我弄的,她的眼光独到,把我整成了文化精英。不在长相上下功夫,而是在气质上做文章。扬长避短的我不是灼灼其华,也还风韵绰绰,文化人的修养气质彰显无遗。
想不到的是,录节目时与我对话的人是项峰,临时换将了,彩排时是一位女的呢。项峰说,她生病了,由他临时替补。事到如今,只好上了,灯光打开,四周金碧辉煌,我马上就在全孝感人的眼皮下面,无遮无挡。按照约定,我们该谈烹饪,谈饮食文化,谈我的创作经历。项峰开口的一句话是我专栏文章里的一首诗,想不到他能背了,真让人感动,照这思路下去蛮好的,节目水到渠成。可是他偏不,不一会他就离了题,他话题一转,先是说,听说你曾經把想拐卖你的人贩子卖给了乡下的老光棍,你能不能谈谈当时的细节?我的个天,这可是在约定内容之外而且是说好要回避的。大厅的灯光是那么刺眼,我感觉我出汗了,他是把我往死路上逼啊。我只有豁出去了,于是我在他的引导下把那次经历绘声绘色地和盘托出。我的状态好极了,有了很强的表达欲望,我说了很多,我连割强奸犯生殖器的事都说了。感觉到我和项峰不是在录节目,是在茶楼喝茶谈心,项峰提醒节目时间快到时,我才如梦初醒,明白了这是在录节目,我妈看了节目不吐血才怪。
项峰最后问的问题是,你有男朋友吗?对爱情你怎么看?我说,都怪你了,把我割人命根跳楼卖人贩子的事都说了,谁还敢要我,这辈子恐怕是嫁不出去了。项峰笑了笑说,如果你愿意,嫁给我吧,我这就算正式向你求婚了,电视观众作证。我的天,这可是在录节目呢。这是他的幽默的主持风格还是在奚落我?
10
米裳终于在孙桂娥孙师傅退休的那一年嫁了出去,嫁给了孝感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项峰。孙师傅了却了一桩心事。米裳出嫁那天的情景有很多孝感人还记得。那天阳光明媚,后湖边的白杨都染上了金色。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项峰先生穿着雪白的衬衣,打着领带,独自一人骑着单车,左手握着鲜花,右手撑着车把,奋力前行。到达米裳住的小区楼下时,衬衣都已经汗湿了,汗水滴在鲜花上,花儿像是洒了水,娇嫩欲滴。他冲上六楼,把穿着婚纱的米裳背下来,搁在自行车后车架上,然后离开,经过槐荫大道、大天桥、城站路向东南方向一路奔袭。街上有很多人驻足观望,天桥上有人吹口哨惊叫,还有人放起了鞭炮。
其实那天项峰是组织了一个浩大的自行车车队去接亲的,因为他骑得太快,像飞一样,后面的没跟上,后来,后面的车队迷失了方向,就在孝感城内瞎转悠。
那年,还有个传闻,说米裳出嫁时,米衣不在孝感,她伤了心,看破了红尘,去了五台山,在那里做了一段时间的尼姑。
其实这传闻也不符合事实。那天,当项峰捧着鲜花,喘着粗气出现在孙师傅家里时,米衣也在场。当时孙师傅郑重其事地捧出了一件礼物,送给了她的女儿和女婿。那东西用帆布包着,是由米衣从孙师傅手里接过来,然后传给米裳的。当时项峰还特别清脆地叫了米衣一声姐。当时米衣戴着口罩,只露出了半边脸,据说是因为她脸上过敏,出了很多红点点。所以后来在米裳的婚礼上,她没有出现。
不过,米衣那年的确是出走了的,只是米裳结婚时,她已经回了。
那年,她先去了河南嵩山少林寺,想在那里当尼姑,因为在那当尼姑,可以天天看到舞棍弄棒的帅和尚。她去了之后,别人说少林寺没有尼姑,只有和尚,她就想当和尚,但是由于性别的原因,别人不收她。她接着就去了五台山,在那里也没有找到当尼姑的地方,别人说,尼姑庵已拆了。她有些失望,但她被那里的地貌风光吸引了,在那里拍了很多照片。她后来又去了神农架,在那里她待了一个星期,玩遍了所有景点。如果不是脸上过敏,痒得厉害,她还会玩几天的。这时候她发现自己根本就不想当尼姑,这样游山玩水多好。在米裳出嫁之前,她已经从神农架回了,而且心情非常好。
现在孝感人还在猜测,那天孙师傅送给米裳的礼物是什么。
责编:梁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