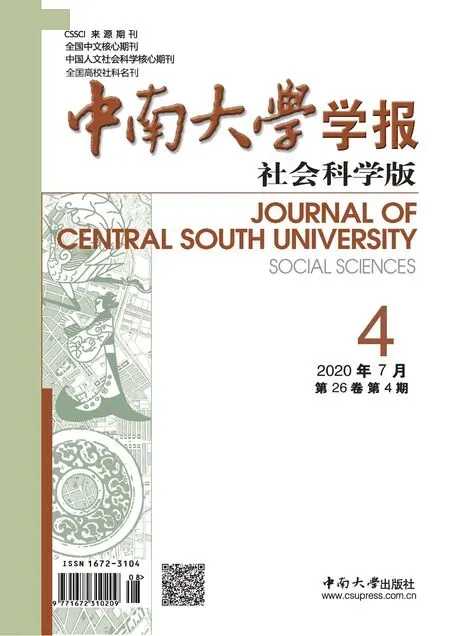中国农村“中等收入线”研究——以湖北孝昌县农村调查为例
杨华
中国农村“中等收入线”研究——以湖北孝昌县农村调查为例
杨华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农村“中等收入线”是指在时空限定条件下,农民家庭要在当地完成劳动力再生产、过上当地普遍认可的体面生活所必需的货币化收入。“中等收入线”为农民家庭提供了明确的奋斗目标,以及农村评判农民家庭及其劳动力状况的参照系和价值标准。通过实地调查发现,村庄熟人社会和共同体的特性使得大部分农民无法逃离“中等收入线”对他们的价值规约。农民需要参照当地“中等收入线”来安排家庭的劳动力和经营活动,由此形塑了具有一定规律性的农村治理及经济社会现象,包括农村治理模式、代际分工模式、农业生产状况、农民分化状况以及农民城镇化模式。围绕“中等收入线”,农村形成了中等收入群体占主导的“纺锤型”社会结构,构成了农村保持稳定与活力的社会基础。
农村;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线”;农民收入分化;劳动力;城镇化
一、农村何以形成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村出现了经济社会的分化。农民家庭的收入和经济条件在有较大提高的同时,相互之间也在比较中呈现出了差别,有的差别还较为显著[1]。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虽然各地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分化有差异,但是总体上都形成了以“中等收入群体”[2]占主导的农村社会分层结构。中等收入群体在分化的农民群体中的占比普遍在八成左右,而农村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总和则在两成上下[3],低收入群体较高收入群体占比稍高;从东部农村与中西部农村的比较来看,东部农村的低收入群体数量较中西部农村少,中等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数量比中西部农村多[4]。由此推断,东部农村和中西部农村,都形成了类似“纺锤型”的社会结构,而不是“金字塔形”[5]、“倒金字塔形”[6]或是“倒丁字形”[7]、“土字形”[8]社会结构。
所谓“纺锤型”社会结构,是指即便农村出现了经济社会分化,但是分化后同一地区内大部分农民家庭的收入差距并不大,使得农民在经济进而在社会层面上依然表现出均质化水平较高而异质化程度较低的特性。这说明农民家庭的经济收入分化不是随机性的,也不是弥散化的,更不是“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式的分布,而是有规律地集中在当地农村社会的中等收入水平上。进而表明农民家庭并不是漫无目的和盲目地获取收入,也不是过度地剥削家庭劳动力以赚取尽可能多的经济收入,更不是秉持有口饭吃就行的态度劳作,而是以达到当地中等收入水平为目标来安排家庭劳动力和生产经营活动。
调查发现,如果一个农民家庭的收入离当地中等收入水平尚有一定的距离,该家庭就会尽力调动家庭劳动力和其他资源投入到相关的经营活动中,以尽可能多地获取中等收入水平的收入;如果一个家庭的收入已经达到了当地中等收入水平,该家庭继续投入劳动力及其他资源的边际效益递减或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的话,那么就不会追加投入,而是任由家庭收入保持在当地中等收入水平上。例如一个中等收入家庭如果投入超强度的劳动,而收入却增长不显著的话,那么该家庭就不会持续投入该劳动,这样就能使家庭收入保持在中等水平,又不过度剥削家庭劳动力,使家庭过着宽裕悠闲的生活。
“中等收入水平”是一个描述收入状态和具有弹性的概念,它涵盖了中间水平、中间偏上水平和中间偏下水平的收入,其中最居中的收入线就是“中等收入线”。“中等收入线”意在明确“中等收入”的确切数额,以更具体地讨论农村“中等收入水平”和“中等收入群体”的确切内涵,以及比照研究农村“收入断裂带”[9]和农民收入的“天花板”效应。中等收入水平是农民家庭收入围绕“中等收入线”上下波动而形成的收入区间,该收入区间的上线是农民家庭收入的“天花板”,大部分依靠劳动力在市场上获得收入的农民家庭很难突破该“天花板”;而该收入区间的下线则触及缺乏劳动力的家庭的“收入断裂带”。从学界比较成熟的计算方法来看,当前对我国“中等收入线”的划分方法有两种:第一是中位数相对标准法,该方法以该年度居民收入的中位数来界定“中等收入线”,而中等收入群体则是指收入达到中位数的群体;第二是将居民收入的平均数设定为“中等收入线”,以平均数的一定区间作为划分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10]。本文对“中等收入线”的计算采用第二种,具体是一个农民家庭以两个青壮年劳动力和两个中老年劳动力为计算标准,四个劳动力所获得的平均收入就是农民家庭的“中等收入线”。在不同农村地区,青壮年劳动力和中老年劳动力所获得的收入不同,那么各地的“中等收入线”也就不同[2]。
在农村,“中等收入线”是农民家庭的收入参照系,接近或超过该收入线都意味着农民家庭的收入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有的农民家庭的收入会超过这条线,有的农民家庭的收入则会低于这条线,但都不会离这条线太远,从而使得农民家庭的收入被这条线所拉扯和牵引,并围绕这条线上下波动。不同的农民家庭都围绕这条线获取收入,进而它们就会形成一个数量占绝大多数的农村中等收入群体。
著名农学家恰亚诺夫的“劳动—消费”均衡理论指出,农民家庭的经济理性决定了他们要在劳动辛苦程度和需求满足程度之间找均衡点,这一讨论是建立在消费决定生产这一基础上的,农民家庭会根据生命周期来调整家庭消费,进而依据家庭消费决定家庭劳动力的生产行为[11]。农民参照“中等收入线”来获取收入,与“劳动—消费”均衡理论有一定的类似,都是依照家庭的总体消费来决定劳动的生产投入。但“劳动—消费”均衡理论是基于个体小农的理性,而“中等收入线”是由农民之间的分化、比较和竞争形成的,农民的消费与生产不是个体理性的产物,而是农民家庭间相互比较和竞争的结果。在比较中,消费落后的农民家庭会有压力,他们会调整家庭生产决策、调动农民劳动力参与生产,以获得更多收入以增加消费。如果农民之间的消费差距太大,落后者怎么努力其家庭收入都达不到当地认可的“中等收入线”,就可能产生“相对剥夺感”[12]。
“中等收入线”在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那么,要回答我国农村之所以会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纺锤型”社会结构,关键就是要回答农村“中等收入线”是如何塑造农民家庭的收入观念,以及由此展开的家庭劳动力安排和家庭经营活动。本文主要以笔者在湖北孝昌农村调研的经验为表述对象,并结合全国其他地区的经验,重点阐述农村“中等收入线”的内涵及其对农民家庭收入和农村社会分层结构的影响。
二、农村“中等收入线”的概念、内涵与决定因素
“中等收入线”既是农村社会的经验现象,也是在经验基础之上提炼出来的学术概念,具有一定的概括性和抽象性。
(一) “农村中等收入线”的概念与内涵
农村“中等收入线”是指在时空限定条件下,农民家庭要在当地完成劳动力再生产、过上当地普遍认可的体面生活所必需的货币化收入,围绕该收入线形成了农村收入水平的中等区间。农村“中等收入线”有以下主要内涵。
一是一地农村收入中等区间中最居中的收入数目,每一个农村地区都有一个具体但有弹性的收入数目。譬如在浙江上虞农村,“中等收入线”是15万元左右,这个数目上下浮动5万元皆属于中等收入范畴;在湖北孝昌农村,“中等收入线”在10万元上下,8~20万元也都属于当地中等收入水平;而在江汉平原农村,5~6万元是当地的“中等收入线”;中原农村普遍的“中等收入线”是4~5万元。
二是它具有时空限制,即“中等收入线”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有差异。同一时间内不同地区的农村“中等收入线”有差异,同一农村地区不同时期的“中等收入线”有差异。农村“中等收入线”既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影响,也随着整个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变化。总的来说,我国农村的“中等收入线”在不断地攀高。
三是它概括的是一地农村较为普遍的货币化收入状况。农村收入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获取的工资收入,另一部分是中老年人在家种地获取的务农收入。工资性收入纯货币化收入,务农收入则包括货币化收入和非货币化收入。务工的货币化收入远高于务农的货币化收入,二者之和是一个农民家庭的货币化总收入。在当前农村,一个家庭只要有务工和务农两笔收入,那么其家庭的货币化总收入就可以接近、达到或超过当地的“中等收入线”,也就是处在中等收入区间之内。那些没有劳动力外出务工而且家庭田亩数少、务农收入亦低的家庭收入才会跌出中等收入区间,远低于“中等收入线”;那些拥有丰富市场资源的家庭的货币化收入会突破中等收入区间,远高于“中等收入线”。由于农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劳动力,那么只要其劳动力能够参与务工和务农的市场分工,就能使其家庭收入进入中等收入区间,这样大部分农民就会成为中等收入群体;跌落或突破中等收入区间的家庭皆属于少数。所以,“中等收入线”能够概括一地农村普遍的货币化收入状况。
(二) 作为村庄参照的“中等收入线”
“中等收入线”是农民获取收入的参照坐标,并依此来安排家庭的劳动力和经营活动。一般来说,农民的家庭支出是刚性的,农民往往是“量出而入”而不是“量入而出”,他们依照支出预算来对家庭劳动力和经营活动做出安排。而农民家庭支出之所以是刚性的,是因为本地农民依照“中等收入线”这一普遍收入水平来安排不同价格的各类支出项目。如果某地的“中等收入线”较高,那么该地区的支出项目的相应消费也较高。譬如,东部农村“中等收入线”较高,那么该地在房子、车子、酒席的档次也会较高。如果一个家庭的相关消费没有达到相应的档次,就会被人看不起。也就是说,农民家庭收入处在当地“中等收入线”上下就能够获得体面的生活。那么,农民为了能够获得体面的生活,就必须朝着本地的“中等收入线”努力。因为只有农民的家庭收入接近、达到或超过当地的“中等收入线”,才够得上当地普遍认可的消费档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等收入线”是对区域内农民家庭收入的刚性规定,它使得农民家庭对劳动力和经营活动的安排会较为刚性。反过来,农民消费档次的提升也会拉高当地的“中等收入线”,进而会影响农民的劳动力和经营活动的安排。
为了在村庄里过着体面和有尊严的生活,每个农民家庭都要努力达到或者超过当地的“中等收入线”。“中等收入线”成为当地农民计算自己开支与收入的基本标准。那么,农民可不可以抛开“中等收入线”自己定义自己的收入标准?答案是否定的。
这是因为在农村会存在“中等收入线”这一参照系,与农民在村庄熟人社会里的生活有关系。与城市陌生人空间不同,村庄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村庄是熟人社会,其内部信息交流是透明的,农民的收入状况、消费行为与消费水平都是不可隐匿的。其次,村庄的价值标准具有一致性和统一性,大部分农民在生活、消费及交往的标准上都有趋同效应,他们不会标新立异创造新的价值标准。再次,在信息对称和价值趋同的基础上,农民在村庄内部展开收入比较和竞争的对象和标准都较为具体。最后,尽管村庄中有少数富裕农户能够较大地抬高其个体的生活和消费水平,但是他们的标准往往被大多数人认为是偶然现象,而不会成为大部分农民效仿的对象,只有大部分农民通过努力能够达到的标准才会成为村庄的标准。
因此,农民在村庄里进行比较和竞争的参照系是“中等收入线”,他们的预期收入目标是要接近、达到或超出这条线。接近或达到这条线,表明农民家庭收入达到了农村的普遍水平,与大多数人相比差不多,可以过上体面生活,有自我满足感,但承受的竞争压力仍较大,家庭劳动力的安排较为刚性。超出了这条线的家庭缓解竞争压力的能力较强,可调动的资源较多,他们的生活较为充裕,经济上比较自主,家庭劳动力安排较为从容机动,在村庄里会受到更多人尊重,他们引领村庄的消费标准,不断抬高当地农村的“中等收入线”。
(三) 农村“中等收入线”的决定因素
农村“中等收入线”的高低,与不同地区农民家庭基本的生活消费水平、社会交往开支和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等所需费用紧密相关。
1. 农民家庭的基本生活开支
农民家庭基本的生活消费包括“衣、食、住、行、医”等货币化开支。在广大中西部农村,农民在穿着打扮上的花销逐渐增大,务工和务农的衣着也逐渐摆脱朴实向美观大方方向发展。例如被调查的孝昌农村,地处大别山余脉,临近孝感和武汉,土地贫瘠,人口流动较大。该地的男子和妇女都讲究体面,农村青壮年男子的衣着花销较大,理发、按摩、洗脚等也属于比较正常的消费活动。女性从二三十岁到五六十岁,只要出门就必须梳妆打扮一番。许多五六十岁的妇女到年底还会要求子女买貂皮大衣,这也是一项不菲的花销。在吃的方面,受调查的几个村子农民都较为讲究,即便是生活较为困难的家庭,每天每餐都要有鱼有肉,两个人在家吃饭也至少要四五个菜,早餐一般都不在自己家里做,要到路边的早餐店去吃,有的人还专门赶到露水集上吃早餐,花销在五六元到十元不等。
目前,农村开销普遍比较大的项目是体现在“住”“行”“医”三个方面。从孝昌县农村的调查来看,现在农民一般都在县城买房子,离县城近的地方则在公路口建房子。孝昌县城的商品房已达到了3 000~4 000元一平米,一套100平米的房子买下来加装修至少要五六十万元。即便是在农村建房,三层楼房加装修的费用也要四五十万元。这对农民家庭来说是一笔较大的开支,需要其若干年甚至上十年的积蓄。在出行方面,前几年农村较多的出行工具是摩托车和面包车,现在流行轿车和SUV(sports utility vehicle)。孝昌村民的面子竞争很激烈,青壮年农民在车子方面的竞争尤甚,因为车子的显示度高。三五成群的年轻人聚会,今年有一个人开二三十万元的轿车回家,明年就一定有人开四五十万元的轿车回来,即便是按揭也要将车买下。有的年轻人借别人的宝马开回家吃酒席,还有人还没有拿到驾照就将三十多万元的车买回家。孝昌农村一到春节和清明节就会堵车。在医疗方面,孝昌农民除了购买“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简称),还有不少人购买了商业医疗保险,但该地农民对的疾病的医疗和防范还是靠存钱。
2. 农民家庭的社交开支
农民的社会交往包括仪式性社会交往和日常性社会交往,两者都需要货币支出,前者主要是指农村的人情往来。在孝昌农村,主要办酒席的项目有婚嫁、周岁、十岁、考学、建房(买房)、八十大寿、丧事等,名目虽然不多,但是农民在人情方面的负担却很重。负担重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人情礼金比较重。同村邻里的人情礼金达到了五百元每次,亲戚间的人情每次在六百元以上,至亲如兄弟姐妹、叔侄舅甥间则在一千元以上。二是孝昌农民的朋友较多。孝昌的青壮年农民多在外做生意和搞建筑,这些工作需要市场信息,所以当地人对交朋友较为重视。朋友多人情就多,重视朋友除了人情礼金要到,人也要到。所以当地人一有酒席就得从工作地赶回老家,吃酒席除了要消耗礼金之外,还有消耗路费、机会成本以及吃酒席过程中打牌的费用。孝昌农村的酒席一般是三顿,每顿饭后主家都要安排打麻将,有打大打小的,但输赢每次都在几千元,有时上万元,这是一笔较大的消费。孝昌农村一般农民家庭的人情开支一年在两万元左右,较高的则达到了三四万元。
日常性社会交往也是需要花费的,主要包括抽烟喝酒、请客吃饭、商场购物和外出游玩等方面的开支。我们调查的孝昌县香花村,这里五六十岁的妇女每个星期都要跟老姐妹们到县城K歌和聚餐,有时还要邀约到外地旅游观光;青壮年农民间的请客吃饭是一笔较大的开支,尤其是在回家吃酒席和过年返乡的时候聚会多,聚会就要喝酒吃饭、K歌洗脚或者打牌赌博等,这些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一笔巨大的消费。有的年轻农民在过年期间打麻将竟然可以将一年积蓄输掉。
3. 农民家庭的劳动力再生产开支
农村的劳动力再生产消耗主要集中在小孩的教育上。中西部农村的年轻农民对子女的教育越来越重视。孝昌县成年农民普遍的学历是初中小学毕业,而“八〇后”“九〇后”较他们父代更为重视小孩教育,很多年轻农民在县城买房子的初衷是为了小孩读书。劳动力再生产的消耗不仅包括小孩在县城上学、培训、玩耍等方面的费用开销,还包括机会成本—需要抽出一个劳动力来照看小孩。不少家庭只要有小孩在城镇书读,就会留一个壮劳动力(一般是年轻妇女)在家专门照顾小孩读书,这就使得另一劳动力赚钱的压力增大。小孩在城镇接受基础教育,是当前农民家庭货币化支出中较大的部分。
以上三个方面的家庭开销都既有零散支出,也有储蓄性的较大支出。这就需要一个家庭的收入既能够满足即时的零散消费,也需要有一定的积蓄能力。如果每月每年的收入只能满足即时性的较小开销,就无法支撑较大的家庭支出,诸如买房、买车及应对突发事件。既能够满足即时性开支,又能够支撑储蓄性开支,就需要一个家庭的收入达到当地的中等水平线。在孝昌农村,由于以上三个方面的开支都相对较大,农民预期中一年的家庭收入要达到十万元左右,才能满足上述家庭开支。如果一个家庭只有五六万元的收入,那么这样的家庭就只能应付即时性的开支,而没有储蓄性开支能力。如果达到了十万元的年收入,那么除去即时性的开支之外还能够积蓄四五万元,这个储蓄水平有了几年的工夫就可以买车或者按揭买房。那么,十万元的年收入就是孝昌县农村的“中等收入线”。
农民家庭的收入水平要达到当地的“中等收入线”,才既能满足生活的即时性消费,又能够支撑储蓄性的较大开支。而只有在即时性消费和储蓄性消费两个方面都达到了当地的标准,其家庭生活在当地才算得上是体面和有尊严。否则,缺少了任何一个层面,如生活很拮据、打不起牌、人情少、朋友少等,即便在村里面建了新楼房,村里人也会说这样的人比较抠门、不够朋友,这样的家庭在村里面也得不到他人的好评价。如果一个家庭买不起车、购不起房子,即便是经常出入麻将室,每餐有酒有肉,村里人也会说他们是“穷潇洒”。尽管这一评价比“抠门”要好一些,这类家庭有什么事情其他人也会更乐于帮忙些。总之,这两类人在村子里地位都不高,因为“没有本事”。当然如果一个家庭节衣缩食,既没有买车也没有买房,但是将子女培养成了优秀大学生,这种情况其他农民也会赞不绝口,说明他们家的“本事”和创造的资源都用在了培养小孩身上了。
三、农民参照“中等收入线”对家庭劳动力进行调动和配置
在农村,劳动力是最主要的家庭资源,农民家庭收入来源主要通过劳动力来获得。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已经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农村劳动力市场[13],农村的劳动力无论是配置在土地上,还是进入务工市场,所获得的收入都是全国平均价格。唯一不同的是,其在中西部农村市场务工的机会较少,而城市和东部地区的务工机会较多。但是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背景下,全国农村劳动力所获得的机会及劳动力的预期收入都相对均等[14]。农民根据当地“中等收入线”在务农、务工或生意经营等活动上配置其家庭劳动力。
(一) 两个典型案例的对比:农民如何参照“中等收入线”
孝昌县沙湾村是一个只有1 000余人的行政村,按规定村干部职数是3个。2015年换届选举时,村书记与会计内斗、相互告状,最后都被乡镇党委劝退,需要重新选举两个人上来。其中会计人选是一个在村的青壮年,年龄在38岁左右,他若干年前买了一辆大车一直在本地跑运输,老婆在家照顾小孩,父母都过了60岁,分家单过,在家务农,不再在建筑工地打零工。该青年一年跑运输的纯收入在10~15万元之间,如果跑得勤快年收入接近20万元。由于他年轻又长年在村,老村干部就向乡镇建议把他推选上来作为后备干部进行培养,选举前做他的工作,他没有松口答应。村里因为没有更好的人选,就将他硬选上来了,但他没有到村里工作过一天。按照他的意思,如果到村里来做干部,就会耽搁跑运输,他就赚不到那么多钱,无法养活一家老小。访谈人有疑问,认为即便村里的事情耽搁他一半的时间,他一年也有六七万元的收入,这也是一个不高不低的收入。但是受访的村干部称,这个收入在当地算较低的收入水平,还没有达到10万元的普遍水平。
沙湾这个未到任的村干部家里只有一个劳动力赚钱,却有两个小孩分别在读小学和初中;父母虽然暂时能够自食其力,但是一旦生病也要他来负担。因此,六七万元的收入虽然能够应付基本的生活,但没有结余,无法应对以后的生活风险,无法建房买房和进行高质量的社会交往。所以他一门心思搞运输。
相反,该县磨山村的齐书记却可以二者兼顾。齐书记年轻的时候在西安建筑工地做了十几年的项目经理,积累了一定的财富。2015年村干部换届选举时,镇村邀请他回来担任村支书,以带动村里的发展。他到村里之后,对村里的发展和建设很上心,白天谋村里的发展,晚上开着大车给工地运送沙子。由于白天还要工作,晚上的运输工作就不能太辛苦,并且有时晚上并不一定有运输可跑,所以他一年跑运输的总时间并不长。他说如果白天晚上都跑的话,一年可以赚二十几万元,但是只跑晚上一年满打满算也就六七万元。但齐书记能够干下去的原因是他已四十多岁,独子成婚后在外边闯荡,收入还不菲,有一个孙子,由齐书记的妻子在带。齐书记家的生活负担不重,家庭生活的主要担子已不在他们夫妇身上。因此,他可以在村干部工资低、耽搁跑运输赚钱的情况下担任村支书一职。
孝昌农村的村干部和村民都在心里算一本账,那就是他们要达到什么样的收入水平才能在当地过得体面、有尊严。经调查当地农民普遍认为,10万元是当地的“中等收入线”,一年的收入只有在这个线上下他们的家庭生活才能过得体面。齐书记跑运输的收入加上他儿子儿媳在外地闯荡的收入,年均要超过20万元,是当地“中等收入线”的两倍多,属于当地中上水平。沙湾未到任会计的父母务农,收入有限,他妻子没有务农和务工因而无收入来源,一年至少10万元的家庭收入只能靠他跑运输来赚。他就任村干部会影响他跑运输赚钱,其家庭收入就达不到当地的“中等收入线”,那么他们的家庭生活在当地就会较为拮据甚至窘困。这样,因为孝昌农村的“中等收入线”是10万元左右,那么,在当地农村担任村组干部的农民更多的是像磨山村齐书记那样的“负担不重的人”[15],而不会是像沙湾村未到任会计这样的青壮年劳动力。
(二) 农民参照“中等收入线”对劳动力和就业的选择
调查发现,孝昌农村还有一个显著的现象,那就是当地青壮年外出务工大部分是做小生意和搞建筑,而较少进工厂务工。这一定程度上也与当地“中等收入线”较高有关。未到任会计如果兼做村会计和搞运输,其家庭收入水平就要远低于“中等收入线”;青壮年农民在工厂工作的收入是固定的,即所谓赚的是“死钱”,那么其家庭收入也难以达到当地“中等收入线”,而做生意、搞建筑只要“舍得吃亏”(能吃苦卖力),赚到的是“活钱”,因为收入与努力程度成正比,所以平均收入水平要高于工厂流水线,进而容易超出当地“中等收入线”。这说明,一个地方的“中等收入线”作为普遍的标准,影响和制约当地农民家庭对劳动力和经营活动的安排。一个家庭根据家庭劳动力、资源禀赋状况,参照当地“中等收入线”对家庭的劳动力及劳动领域进行合理安排。从对农村的调查来看,农民家庭对劳动力的安排有以下四种基本情况。
一是对劳动力的动员和配置。家庭劳动力有两种分类,一种是性别分工,另一种是代际分工。当前广大中西部农村家庭分工主要以代际分工为主,性别分工越来越不明显。代际分工主要是父代在农村务农,获得务农的收入,年轻夫妇外出务工或做生意,获得工资性收入或生意利润。两笔收入之比是二比八左右,务农收入的占比明显偏少。但是这并不等于父代务农的收入不重要,事实上父代在家务农为子代节省了大量生活和消费成本,包括自我养老、看小孩、人情开支等,使得子代获得的大部分收入能够进入家庭储蓄。当然少了年轻夫妇外出的收入,该家庭的收入就很难到达“中等收入线”。磨山村齐书记家就较为典型,他担任村支书和跑运输的大部分收入作为家庭的即时性开支被消费掉,而其儿子与儿媳外出做生意的收入则被积攒了下来。在性别分工上,无论是外出务工,还是开夫妻店,夫妻分工都不明显。夫妻分工较为明显的情况是,年轻妇女留在家里陪小孩读书,而年轻男子在外务工做生意。但是,这种分工会存在较大的机会成本,使得一个家庭少了一份收入,需要另一个劳动力去弥补方能使家庭收入达到当地“中等收入线”,这样就会加大该劳动力配置的刚性,以及可能带来他对自身劳动力的过度剥削。没有壮劳动力的家庭则无法进行劳动力的有效动员和配置,家庭必然陷入贫困状态[16]。
二是对务农还是务工的安排。农民的劳动力有三种安排形式,一是务农,二是务工,三是做生意。一般来说,若一个家庭耕种一定规模的土地,收入可以达到当地中等收入水平的话,他们就会留在农村种地。在农村种地可以使家庭生活较为完整,避免了儿童的“留守”现象,还有大量农闲时间,这部分时间既可用于休闲,也可以用于打零工。比如,在江汉平原的农村,耕种四五十亩土地,再在周边打零工,每年可获得五六万元的收入,这足以达到当地“中等收入线”水平,那么当地农民就愿意通过流转土地留在农村。但是在孝昌农村,由于“中等收入线”较高,需要耕种上百亩土地方能获得10万元的收入,这对当地农民来说,耕种这么多土地的劳动强度过大,同时也很难流转到这么多土地。当地大部分的青壮年劳动力都离开了土地,较少有耕种中等规模土地的农户。所以,当地农村劳动力的市场化程度较高,耕种土地的积极性却低。随着农村“中等收入线”的抬高,在农村务农越来越难以达到这个标准,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土地外出务工、做生意。
三是对务工还是做生意的安排。务工和做生意两相比较,后者较前者更容易达到和超过农村“中等收入线”。务工的门槛较低,凡是壮劳动都能够进入务工市场,而做生意则需要资源、机会、人脉、头脑、冒险精神等。在广大中西部农村,“中等收入线”主要与一对夫妇外出务工的收入相关,所以,普通农民家庭通过青壮年夫妇外出务工,中老年人在家种地就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中老年人在家种地的同时还可照看孙辈,以解放子代的劳动力。在孝昌农村,由于“中等收入线”较高,农民夫妇的双务工收入难以达到该标准,那么当地青壮年多数选择从事建筑行业和做生意。搞建筑除了包工之外,主要是在工地上做苦力,只要能够吃苦耐劳,劳动时间长,一个男性劳动力一年有上十万元的收入;如果年轻妇女也在工地上工作,两人的年收入就可以达到15万元左右。如果仅男子一个劳动力就能够获得上十万元的收入,年轻妇女的劳动力配置就可以较为灵活机动,她们或在老家带小孩,或者做一份较为轻松但工资不高的工作。做生意除了开厂办企业之外,一般是开“夫妻店”,如租门面开服装店、小饰品店、手机店、五金店等,一年下来一对夫妇能够赚十几万到二十万元不等,门面较多则可以超过20万元。在江浙、苏南等地农村,由于当地的“中等收入线”达到或超过了15万元,而当地务工机会又相对较多,不少的中老年农民就在当地同时打几份工,以获得更多的工资性收入。
四是对留在本地就业还是到外地就业的选择。在中西部地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当地农村也有打零工、做建筑工、包工、跑运输等就业机会。但是总体来说,这些就业机会相对较少,且多为青壮年农民所优先占有,留给中老年农民的务工机会较少。在孝昌农村,如果年轻男子留在本地就业,那么其妻子也得留在本地就业,由于年轻妇女的工资较低(1 000~2 000元/月),所以赚钱的压力就集中在了年轻男子身上。他们要在本地务工市场赚到上十万元(或更高),就得更多地占据当地劳务市场,这就必然要将其他年轻人排挤到外地就业,所以留在本地的年轻人就相对较少。沙湾村未到任会计一个人要获得十几万元的就业机会才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他就必然挤占其他人的机会。相反,如果当地的“中等收入线”是六七万元,那么他开货运就不用那么拼命,这样也可以留一半的就业机会给其他人。在广大中西部农村地区,随着“中等收入线”水平的逐渐抬高,农民家庭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当地农村的赚钱资源会更加稀缺,这样就会迫使更多的青壮年农民到外地寻求就业机会。
四、“中等收入线”对农村治理与经济社会的形塑
由于区域农村的“中等收入线”具有相对稳定性,当农民参照“中等收入线”对家庭劳动力、土地等资源进行配置和调整时,在当地这些资源之间形成相对稳定的结构,也就是会形塑具有一定规律性的农村治理现象及其他经济社会现象。
(一) 形塑村庄治理模式
在农村基层治理体制给定的前提下,治理主体的差异会制造不同的治理现象和治理模式。在中西部农村,农民家庭为了达到“中等收入线”的标准,半工半耕式的代际分工必然会使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流出村庄,留下来的主要是中老年人、妇女和小孩。但是同时,广大中西部农村的“中等收入线”还可以通过耕种中等规模土地,外加在本地打零工或做小生意、搞建筑等方式来获得,虽然这些获利机会不多,但仍能吸引一少部分青壮年劳动力留在农村。在本地获得了“中等收入线”上下的收入,他们就不需要再外出务工或做生意,就可以常年在村。由于这部分农民的主要利益关系和社会关系在农村,因而他们对村庄较为熟悉,与其他村民交往频繁、关系紧密,对村庄公益事业也较为热心,支持基层党委和政府在农村的政策和工作。因此,他们不仅是农村社会生活中的主体,也是村庄治理的主体,他们往往被推选 为村组干部和村民代表,是农村中的“中坚农民”[17],由他们作为主体展开的村庄治理模式被称为“中农治村”[18]。
在孝昌农村,因为当地农村的“中等收入线”较高,青壮年劳动力必须外出务工或做生意才能使其家庭收入达到“中等收入线”,也就较少有通过耕种中等规模的土地获得中等收入水平的青壮年农民。少数留在本地做生意、搞建筑的青壮年农民又需要一门心思地赚钱,无法分出时间和精力出来做村组干部。因此,在当地做村组干部的农民不是“中坚农民”,而是一些“负担不重的人”,也就是子女都已经成家的中老年人。笔者调查了解到,当地小组长和村民代表普遍七十多岁,主要村干部也都在六十岁左右。这个年龄段的人已经完成了基本的人生任务,家庭创收的主要责任落在了子代身上,此时他们既没有物质上的压力,也没有精神上的负担,才会有闲出来担任村组干部。
(二) 形塑代际分工模式
代际分工是农民家庭劳动力的基本配置模式。农民参照当地的“中等收入线”对家庭劳动力进行调动和配置。不同农村地区的“中等收入线”不同,代际分工的状况也有差异。在广大中西部地区,“中等收入线”相对较低,农民家庭通过年轻人外出务工、中老年人在家种地的“半工半耕”式代际分工就可以达到该标准。但在孝昌农村,“中等收入线”相对较高,代际分工中的“半工”就变成了做生意和搞建筑。若青壮年只是进工厂务工,其家庭收入难以达到本地“中等收入线”的水平。
在江浙、长三角等发达地区的农村,“中等收入线”较高,农民无法通过“半工半耕”来达到该收入水平。由于务工机会较多[19],当地的年轻人都进入正规经济领域就业,留下了大量非正规的就业岗位。该地区的中老年人一般将土地流转出去,自己在非正规经济领域就业,这样就形成了“半正规半非正规”的代际分工模式。如果当地中老年人只是通过耕种承包地获得“糊口”的收入,那么该家庭中父代务农的收入加上子代务工的收入就难以达到当地“中等收入线”水平。
在珠三角农村,中等收入水平也相对较高,但是当地的耕地又多已工业化,没有工业化的土地也由村庄反租倒包给了外地农户。当地农民不再耕作农田。当地年轻人在本地企业就业,中老年人过了六十岁就不再进入劳动力市场就业,而是处于退养状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地中老年人除了有养老保险之外,还有较为丰厚的村集体分红和房屋出租等收入。地租收入加上年轻人的工资性收入足可使其家庭收入达到当地的“中等收入线”,使一个农民家庭过上当地城镇中产阶级的生活。这是一种“半工半租”的代际分工 模式。
(三) 形塑农业生产模式
“中等收入线”对农业生产的形塑源自家庭劳动力是进入土地,还是劳动力市场的安排。在广大中西部农村,代际分工模式是“半工半耕”,那么农业形态就主要是“老人农业”[20],以及耕种中等规模土地的“家庭农场”[21]。老人农业的耕种主体是农村中老年人,他们在城市工商服务领域属于兼职劳动力,但在农业领域还是劳动主力。“老人农业”的家庭耕种规模较小,一般在十亩以下,耕种的方式是精耕细作。由于机械、市场和现代农业科技的介入,农业劳动强度降低,这就拉长了中老年农民在农业领域的劳动年龄,七八十岁的老年人都还能够耕作。无论“老人农业”还是中老年人耕种土地既能够打发时间、锻炼身体,还有收获的成就感,并且能够自食其力,不向子代开口索要,既能在子代面前保持尊严,还能够自己支付人情往来的费用,保持自己的社会性身份[22]。在孝昌农村,由于“中等收入线”水平较高,中等规模家庭农场的收入无法达到这个标准,当地几乎没有青壮年劳动力经营家庭农田,所以当地的农业类型主要是“老人农业”。
在浙江农村,只有“半正规半非正规”的代际分工模式才能使一个家庭的收入达到当地“中等收入线”。若想通过耕种土地来达到当地十几万元的“中等收入线”,显然小微规模的“老人农业”和中等规模的“家庭农场”皆无法满足其要求。在较高的“中等收入线”的压力下,当地农民选择了两种农业类型,一是外出包地,使其经营的土地达到二三百亩,那么在这个规模下种植大宗农作物也可以获得较高的收入,以达到或超过当地“中等收入线”。许多浙江农民远赴江苏、安徽、上海农村包地,成为流动的“职业农民”[23]。二是在数亩到十数亩小规模的土地上精耕细作,即种植非常水果或苗木,水果如猕猴桃、蓝莓、葡萄等,将其做成地方品牌,形成典型的“精致农业”,这些农产品能够卖出高于普通同类产品的价格,从而使耕种小规模土地的农户收入亦能达到当地“中等收入线”。
(四) 形塑农民分层结构
由于大部分农民家庭都是通过劳动力的经营活动来获取家庭收入,并以当地“中等收入线”为参照来调动和配置家庭劳动力。那么家庭劳动力的数量和素质,以及是否被充分调动和合理配置就成了决定家庭收入状况的关键,并由此形塑农村的经济社会分化状况。
那些劳动力数量多(如两代人都是壮劳动力)、质量高且全部被动员参与家庭分工和市场务工的家庭,可以获得达到和超过“中等收入线”的收入水平。也有一些家庭因为壮劳动力素质高、通过做生意、包工和搞建筑等获得远超出“中等收入线”的收入,他们家庭的其他劳动力则无须参与劳动力市场竞争。这些家庭的收入水平在农村属于中上等。而那些能够进行代际分工、劳动力素质一般的家庭则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平均收入,该收入可以接近或达到当地中等收入水平。上述家庭是农村的中等收入群体,占农村的较大部分。还有一些缺少劳动力,或者有的劳动力有残缺(如懒惰、素质不高等),或者无法实现代际分工的家庭,其家庭收入要较当地的中等收入水平,属于中下等水平,但是这样的家庭仍能够完成家庭和劳动力的再生产。
最后一种情况是没有壮劳动力,或壮劳动患病或残疾,而多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这样的家庭既无法外出务工获得工资性收入,亦无法进行高强度的农业生产,只能够打些轻便零工和做些简单农活,能够获得维持生计的口粮,但是无法进行家庭和劳动力的再生产。这样的家庭属于农村的低收入户或无收入户[24]。这样的家庭在农村属于极少数,一个小组一般只有一两户到两三户的样子。这些家庭具体有这么几种情况:一是五保户;二是未到60岁的单身男子但智力或身体有残疾;三是家庭男壮劳动力常年卧床、子女小(多)、年轻妇女无固定收入;四是青壮男子去世、年轻妇女改嫁、子女由祖代抚养;五是壮劳动力残缺、无技能、收入有限、学生多。它们都属于农村中的特殊家庭,在农村中较为显眼,收入来源有限,也容易被统计出来,被评为低保户基本上没有异议。
另外,大部分农村也只有少数农户不是通过劳动力资源,而是通过市场资源如技术、知识、资本、信息、管理等获得较高的收入,这个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的收入远高于当地的“中等收入线”。这部分群体是农村中的高收入群体。在中国的中西部农村,高收入农民会搬出村庄到城镇定居,不再参与村庄的社会关系和人情往来,而在东部农村,这部分农民则仍属于村庄社会结构的一部分。
(五) 形塑村庄竞争形态
农民对家庭收入的普遍期待是处在当地“中等收入线”上下。只有达到这个收入水平,农民才能支撑家庭基本的消费支出、参与村庄人情往来和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进而才能在村庄中获得他人的认可和承认,进入村庄主流生活。否则就会被村庄边缘化,被他人瞧不起。村庄社会生活和价值生产的压力逼着农民要以“中等收入线”为参照获取家庭收入。同时,农村“中等收入线”虽然在不同地方有差异,但对于当地农民而言都不是高不可攀和可望不可及的。只要农民家庭有壮劳动力,就可以通过充分调动和合理配置家庭劳动力及其他资源达到“中等收入线”上下的家庭收入水平。各农民家庭都不会轻易“认命”和轻言放弃,都是加足马力往“中等收入线”靠拢,从而形成了相互比较和竞争的局面。
从调查来看,以“中等收入线”为参照的村庄竞争,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竞争激烈。农民家庭都不甘落后,这样就会给单个家庭带来较大的竞争压力和焦虑,使得每个家庭都有动力去调动和配置家庭资源以缓解压力和焦虑。农村家庭之间的激烈竞争推动了农村劳动力的市场化,增进了农村社会的活力,带动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二是竞争物质化严重。农民将家庭收入通过物化的形式展示出来,使村庄竞争表现为物质财富和物质消费的竞争。三是家庭资源向竞争倾斜。由于“中等收入线”上下的竞争很激烈,农民就要将家庭劳动力及其他资源都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参与竞争,这样就会挤压不属于村庄竞争“标的物”的家庭其他方面所需的资源。典型的如老年人的养老资源被压缩,使得老年人得不到应有的物质和精神照料[25]。
(六) 形塑农民城镇化模式
在中国农村,由于大部分农民家庭的收入在“中等收入线”上下,只有少部分农民家庭通过掌握市场要素可获取较高的收入。这样从家庭层面来讲,大部分农民家庭进城的模式是“渐进式”城镇化[26],也就是分阶段、分群体、分成员地进城。渐进式城镇化首先是农民家庭居住与消费的城镇化,接着是孙辈的城镇化,最后才是年轻人的城镇化。中老年人一般不在城镇化的范畴,他们主要是作为“老漂族”阶段性地进城[27]。从农民群体来讲,少部分高收入农民家庭能够较早地、全家式地城镇化,次之城镇化的是收入超出中等线的中上农民家庭,再次之的是接近中等线的家庭,远离中等线的家庭城镇化难度最大。除了高收入群体家庭是全家式城镇化外,其他农民家庭由于家庭收入皆处在“中等收入线”上下,无力支撑全家人的城镇化,因此这些农民家庭的城镇化普遍都是子代城镇化与父代留守的结合。在这个意义上,农村“中等收入线”支撑下的城镇化是典型的“半城镇化”[28]。
五、结语
农民参照农村“中等收入线”对劳动力和经营活动进行安排,并获取在“中等收入线”上下的家庭收入水平,使得大部分农民都成为农村的中等收入群体。并且,由于农民家庭的收入来源主要依靠劳动力和土地这两类资源,能够通过市场要素获取远高于“中等收入线”的收入而成为农村高收入群体的农民较少,同时因缺少劳动力而使其家庭收入远低于“中等收入线”的农民家庭也相对较少。因此,中国农村就形成了中等收入群体占主导的“纺锤型”社会结构,它是相对较为稳定和合理的社会结构。
在“纺锤型”社会结构中,农村高收入群体较少,没有规模效应,很难成为其他农民效仿和比较的对象,在中西部农村尤其如此。农村中等收入群体是现行土地制度、社会流动政策及其他惠农政策的受益者,他们的家庭收入和生活条件处在当地的中等水平,有相对较高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对现状较为满意。由于“中等收入线”是农民调动劳动力和配置资源的参照系,农民竞相使家庭收入向当地“中等收入线”靠拢,因此农村中等收入群体就会保持相对稳定并有增多的趋势。而少数因为缺少劳动力的低收入家庭则被纳入政府的低保行列,这样既能保证低收入家庭获得当地最低生活保障,亦能为这些家庭的劳动力再生产提供条件,进而推动他们进入中等收入行列。
“中等收入线”为大部分农民家庭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成为农村评判农民家庭及其劳动力状况的基本价值标准。村庄熟人社会和共同体的特性,使得大部分农民无法逃离“中等收入线”对他们的价值约束,他们需要参照当地“中等收入线”来安排自己的劳动力和经营活动。凡是家庭收入水平处在当地“中等收入线”上下的农民家庭及其主要劳动力都被认为是“达标合格”了,才能够进入村庄的主流生活,受到他人的尊重。如果一个家庭有劳动力却成为村庄低收入家庭则会被人瞧不起,而没有劳动力的低收入家庭则会被给予同情,这样的家庭“吃低保”是理所应当。
在劳动力是农民家庭最重要的资源的情况下,农民家庭的收入能否达到当地中等收入水平,与家庭劳动力状况关系最大。农民家庭劳动力状况表现在两个层面。
第一,是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高低。劳动力市场化程度与家庭收入状况成正比。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高低主要表现为劳动力是否被充分动员和合理配置起来。家庭劳动力越是被动员起来参与劳动创造,尤其是家庭青壮年劳动力被动员起来参与就业,家庭获取的工资性收入就越高。而被动员起来的劳动力如果都合理地配置在不同的经营活动上,家庭收入也就更高。在广大中西部农村,最合理的家庭分工是青壮年农民外出务工(或做生意)与中老年人在家务农。
第二,是劳动力的数量和素质,前者是指投入市场的有效劳动力的数量,数量越多获取的收入就越多。后者包括身体素质和业务素质,身体素质是指身体的健康和强壮程度,身体素质越高就越能够承受高强度、长时间的劳动,所获得的收入也就越高。业务素质包括技术、技能、管理、经验、资历、社会资本等,在这些方面越有优势,劳动力的发展空间就越大,获得的收入也会越高。总之,不同农民家庭收入会根据其家庭劳动力的市场化程度、数量和素质状况,而在“中等收入线”上下波动。一个家庭的劳动力市场化程度高、数量多、素质高,那么该家庭的收入就可能超过“中等收入线”。反之,一个家庭的劳动力市场化程度低、数量少、素质低,其家庭收入就可能低于“中等收入线”。
[1] 罗兴佐. 阶层分化、社会压力与农民上访——基于浙江D镇的调查[J]. 思想战线, 2015(4): 93−99. LUO xingzuo. Class differentiation, social pressure and peasants' petition: Pased on the survey of D town in Zhejiang Province [J]. Tinking, 2015(4): 93−99.
[2] 杨华. 中国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研究[J]. 经济学家, 2017(5): 26−35. YANG Hua. Research on middle income groups in rural China[J]. Economist, 2017 (5): 26−35.
[3] 陈柏峰. 城乡二元结构中的农村中间阶层[J]. 人文杂志, 2014(7): 105−108. CHEN Baifeng. Rural middle class in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J]. The Journal of Humanities, 2014(7): 105−108.
[4] 刘瑞翔, 范金, 戴枫. 沿海地区与内陆省份经济增长的比较测度[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0(6): 148−168. LIU Ruixiang, FAN Jin, DAI Feng. Comparativ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growth between coastal areas and inland provinces [J]. The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and Technological Economics, 2020(6): 148−168.
[5] 关晓丽. 中国社会结构正由“金字塔型”向“橄榄球型”过度[J]. 社会科学战线, 2004(6): 230−233. GUAN Xiaoli. The transition of Chinese social structure from "pyramid type" to "Rugby type"[J]. Social Science Front, 2004 (6): 230−233.
[6] 李建新. 倒金字塔理论与21世纪中国老龄社会[J]. 中国人口学, 2000(3): 35−41. LI Jianxin. Inverted pyramid theory and China's aging society in the 21st century[J]. Population Science of China, 2000 (3): 35−41.
[7] 贺雪峰. 中国是倒丁字型社会结构吗[J]. 学术界, 2017(3): 123−132, 325−326. HE Xuefeng. Is China an inverted D-shaped social structure [J]. Academics, 2017(3): 123−132, 325−326.
[8] 李强. 中国离橄榄型社会还有多远——对于中产阶层发展的社会学分析[J]. 探索与争鸣, 2016(8): 4−11, 2. LI Qiang. How far is China from olive society?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iddle class[J]. Exploration and Free Veiws, 2016(8): 4−11, 2.
[9] 贺雪峰. 论农民收入断裂带[J]. 学术论坛, 2019(1): 49−55. HE Xuefeng. On the fracture zone of farmers' income [J]. Academic Research, 2019(1): 49−55.
[10] 王宏. 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划分标准: 综述、比较与现实选择[J]. 经济研究参考, 2020(1): 58−69. WANG Hong. Criteria for the division of middle-income groups in China: Review, comparison and practical choice[J]. Review of Economic Research, 2020(1): 58−69.
[11] 袁明宝. 小农家庭的经济行为逻辑——对恰亚诺夫劳动—消费均衡理论的评析[J]. 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 2015(6): 55−58. YUAN Mingbao. Economic behavior logic of small-scale peasant families——An analysis of Chayanov's labor consumption equilibrium theory[J]. Journal of the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Hangzhou, 2015(6): 55−58.
[12] 陈锋. 中国农村阶层分化的政治社会后果[J]. 文化纵横, 2018(6): 88−95. CHEN Feng.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the stratification of rural areas in China[J]. BeiJing Culture Review, 2018 (6): 88−95.
[13] 贺雪峰. 全国劳动力市场与农村发展政策的分析与展望[J]. 求索, 2019(1): 11−17. HE Xuefeng. Analysis and prospect of national labor market and rural development policy[J]. Seeker, 2019 (1): 11−17.
[14] 杨华. 农民家庭收入地区差异的微观机制研究[J]. 河南社会科学, 2019(9): 84−96. YANG Hua. A study on the micro-mechanism of the discrepancy in farmer's household income in different regions [J]. Henan Social Sciences, 2019 (9): 84−96.
[15] 贺雪峰.“负担不重的人”是基层治理一大活力源[N].北京日报, 2016-04-25(01). HE Xuefeng. "People with less burden" is a major source of vitality for grass-roots governance[N]. Beijing Daily, April 25, 2016(01).
[16] 邢成举, 李小云, 张世勇. 转型贫困视角下的深度贫困问题研究—以少数民族深度贫困村为例[J]. 民族研究, 20189(12): 52−63, 140−141. XING Chengju, LI Xiaoyun, ZHANG Shiyong. Research on deep pover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formation poverty [J]. Ethno-National Studies, 2019(2): 52−63, 140−141.
[17] 张燮. 农民分化与农村阶层关系的东中西差异[J]. 甘肃社会科学, 20(1): 38, 45. ZHANG Xi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betwee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farmer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strata [J]. Gansu Social Sciences, 2020(1): 38, 45.
[18] 刘锐. 中农治村的发生机理[J]. 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3): 21−27. LIU Rui. The Mechanism of the village governance by the middle peasants[J]. Journal of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2(3): 21−27.
[19] 钮亮, 代丽娟. 居民收入差距的空间集聚和影响因素分析——以浙江省市县为例[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6): 88−95. NIU Liang, DAI Lijuan. Spatial agglomer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sidents' income gap: A case study of cities and counties in Zhejiang Province[J]. Journal of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8(6): 88−95.
[20] 周小洪, 贾晋, 雷俊忠. 老人农业的理论破局与对策应对[J]. 农村经济, 2014(12): 43−45. ZHOU Xiaohong, JIA Jin, LEI Junzhong. Theoretical failure and Countermeasures of agriculture for the elderly[J]. Rural economy, 2014(12): 43−45.
[21] 韩鹏云. 农业规模经营的实践逻辑及其反思[J]. 农村经济, 2020(4): 17−25. HAN Pengyun. Practical logic and reflection of agricultural scale management [J]. Rural Economy, 2020(4): 17−25.
[22] 吴海龙. 支撑老人农业运行的微观机制[J]. 老龄科学研究, 2017(2): 13. 21. WU Hailong. The micro mechanism supporting the agricultural operation of the elderly[J]. Scientific research on Aging, 2017(2): 13.21.
[23] 马流辉.“农民农”: 流动农民的异地职业化[J]. 决策, 2014(12): 52−53. MA Liuhui. "Farmer farming":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migrant farmers in different places[J]. Decision-Making, 2014(12): 52−53.
[24] 刘成良. 转型性贫困、多维贫困问题与中国的扶贫能力转型[J]. 东方学刊, 2020(1): 10−20. LIU Chengliang. Transformational poverty, multidimen- sional poverty and China's transform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bility [J]. DongFang journal, 2020(1): 10−20.
[25] 狄金华, 郑丹丹. 伦理沦丧抑或是伦理转向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农村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研究[J]. 社会, 2016(1): 186−121. DI Jinhua, ZHENG Dandan. Study 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distribution of rural family resource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decline or ethical transformation to modernization[J].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6(1): 186−121.
[26] 夏柱智, 贺雪峰. 半工半耕与中国渐进城镇化模式[J].中国社会科学, 2017(12): 117−137, 207−208. XIA Zhuzhi, HE Xuefeng. CHina’s semi-industry, semi-agricultural mode and incremenkal urbanization[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17(12): 117−137, 207−208.
[27] 陈辉. 老漂: 城市化背景下农村代际支持的新方式[J].中国青年研究, 2018(2): 24−29. CHEN Hui. Lao Piao: A new way of rural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in the context of urbanization[J]. China Youth Research, 2018(2): 24−29.
[28] 陈文琼, 刘建平. 家庭发展秩序: 非精英农民城市化的核心机制[J]. 公共管理学报, 2018(2): 69−81, 156. CHEN wenqiong, LIU Jianping. Family development order: The core mechanism of non elite farmers' urbanization[J]. Journal of Public management, 2018(2): 69−81, 156.
A study on the "middle income line" in rural China:A case study of a rural survey in Xiaochang County of Hubei
YANG Hua
(School of Sociolog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Middle income line” in the countryside refers to the monetization of incomes required for farmer families to complete labor force reproduction locally and live a generally and locally recognized decent life under limited conditions of time and space. “Middle income line” provides a definite goal for farmer families to strive for, and a benchmark and value standard to judge such families and their conditions of labor force. Through field survey, the present study finds that given the feature of acquaintance society and community in rural areas, most of farmers are unable to escape from the value rules and restrictions that “middle income line” imposes on. Farmers need to refer to local "middle income line" to arrange their family labor forces and operation activities, hence shaping rural governance and economic social phenomena with certain regularity, including rural governance mode, inter-generation division of work, situ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ransfer of farmers and urbanization mode of farmers. Revolving around “middle income line”, a “spindle” social structure dominated by middle income groups has been formed in rural areas, which constitutes the social foundation to maintain stability and vitality of rural areas.
rural areas; middle income group; middle income line; farmer differentiation; labor force; urbanization
2019−08−28;
2019−12−23
杨华,湖南郴州人,社会学博士,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与县乡村治理,联系邮箱:yanglaizhi1981@163.com
10.11817/j.issn. 1672-3104. 2020.04.016
C913
A
1672-3104(2020)04−0159−13
[编辑: 游玉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