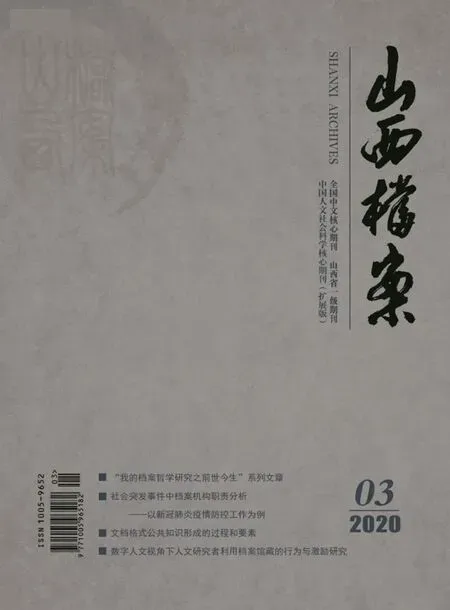本体论:档案哲学的纲领与根本原则*
(广西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南宁 530006)
1 缘起与过程
2015年8月,是我从事档案学研究30年整的日子,也是我正式动笔写《档案学本体论》[1]日子。在动笔写《档案学本体论》之前,我已经对档案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但总觉得画龙缺“睛”,我在有意识地寻找档案学中具有纲领意义的内容。在长期思考之后,我确定寻找这个内容的方向是“档案、档案工作与人类社会实践的关系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在档案学中具有根本性意义。
关于这一问题思考的第一个成果是《从实体与事物的角度论档案形成规律(上)、(下)》[2]。它从哲学的“实体”角度[3]来探讨现实世界中档案的形成来源问题。文章对“档案自然形成规律”进行了更深一步的理论阐述,为曾三先生等档案学前辈确立的“档案自然形成规律”正名,说明它与“有意识形成理论”并非对立的关系,两者处于两个不同的实践范畴。
在完成了《从实体与事物的角度论档案形成规律》一文后,我没有停止对“档案、档案工作与人类社会实践关系问题”的思考,其结果是我于2015年暑期写作完成了《档案学本体论——兼谈档案学的根本原则》一文,并发表于《档案学通讯》2015年第6期。作为我的档案学哲学思想的精华和灵魂,它在我的这个学术体系中完成的时间是比较晚的,并成为我的档案学哲学思想体系整体构建初步完成的标志。它的完成与发表,还有着一段文人相亲的故事:当时,虽然我一直酝酿着探讨“档案、档案工作与人类社会实践关系问题”的文章,但由于种种原因,在2015年暑期前一直没有动笔。而在2015年暑期“《档案学通讯》杂志社第八届通联工作会议”(2015年6月29日,哈尔滨)上,胡鸿杰总编以一个学者和学术杂志编辑者特有的学术敏感,谈到了该刊即将发表的《档案学领域本体的构建》一文的不足[4],该文采用的是一种计算机科学与信息科学领域的电子工程术语,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哲学术语。胡鸿杰教授希望有人写作一篇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的“档案学本体论”方面的文章。荣幸的是,胡鸿杰教授找到了我,敦请我尽快完成一篇关于档案学本体的文章。胡鸿杰教授的提议让我突发灵感,意识到本体论思想正是解决我苦苦追寻的“档案、档案工作与人类社会实践关系问题”问题的关键所在。原本有些慵懒的我,在胡教授的敦促下,灵感与动力齐发,在一种一气呵成的状态下迅速地完成了《档案学本体论——兼谈档案学的根本原则》一文。
在笔者的学术生涯中,许多研究成果都是在某些外部因素触发下完成的。它们有学者间的正面探讨和观点间碰撞与争论,也有杂志编辑的邀约与敦请。其中,胡鸿杰教授是常常能够给我带来思考和灵感的学界挚友之一。我是应该感谢这些朋友们的,他们推动着我的档案学研究,以至于自己想停下来也做不到。
2 档案学本体论要义
存在论被亚里斯多德定义为第一哲学,也是我们档案哲学研究中的第一问题。
在哲学上,存在这个概念是灵活的,但在我们的档案哲学中,它是具体的。我们所研究的对象,就是档案世界里的人、事、物,找出它们中的本质的、本源的、恒定的根本意义的东西来,这就是档案学本体论的研究目的。
本体是本质、本源的世界。了解这个档案世界的本体的、本质的东西,我们就实现了在档案哲学中存在与思维的同一性,本体论是认识论的前提与基础。
事物之所以成为事物,是由其本质属性决定的。档案之所以成为档案,就是因为它是人类活动的原始性符号记录。由于人类需要这种记录,它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果,也是继续进行下去的实践活动的重要经验基础,档案就是这样在人类实践活动中产生并被保存起来的。
实践本体论,是有关档案、档案工作、档案学的本体论,全称应为“档案、档案工作、档案学实践本体论”,笔者将其简称为“档案实践本体论”。
3 档案实践本体论的本质含义:从世界观到方法论
档案、档案事业、档案学,它们的本原是什么?这是本体论要回答的问题,也是档案学的终极性问题,也是我在研究档案学基础理论时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这个问题,说到底就是档案人基于档案事业的世界观。
所谓世界观,就是人们对外部世界、人本身以及人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基本观点或看法,它所关心的焦点是世界对人的意义及人在世界中的位置。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要从人和世界的关系中认识和把握人及外部世界。
所谓档案人的世界观,就是基于档案工作者的角度,对档案人、档案工作本身与其身在其中的人类世界之间的关系、意义、位置的基本观点或看法。这些看法集中体现在档案的本原问题上,并由此形成了档案人的基本思维方式,即由档案人的世界观决定的思考和解决各种现实问题的最普遍有效的模式和方法。人人都有世界观和思维方式,但并不是人人都有正确的、系统的、自觉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笔者在这里,试图提出一种档案人的系统、自觉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它是档案工作各种现象统一的基础,因此我将其说成是档案学的终极性问题。
理论与方法是分不开的,档案学的方法论一定是在档案世界观指引之下的方法论。因此,由我的档案实践本体论研究导出了“档案工作根本原则”,即“档案工作要保持与人类实践活动的一致性” 原则,它是对档案人来说具有根本意义的方法论准则。即:它是我们思维的出发点、基准点和行为的根本准则。
“档案工作根本原则”是档案实践本体论理论推演出来的必然结果。在要不要将它命名为“根本原则”的问题上,笔者最初是有所犹疑的。因为《档案法》已经规定了档案工作基本原则,“根本原则”似乎有凌驾其上之嫌。但思来想去,此原则非以“根本原则”命名不可,因为它的确具有纲领性意义,其旨趣也的确在“档案工作基本原则”之上,因此从理论上只能将其命名为“根本原则”。
4 重要意义
4.1 原始反终
在我看来,所谓的档案学原理都能从哲学那里找到它的根据或原理之原理,为此我写了档案本体论、档案时空观、档案价值论、档案定义论、档案起源过程论等等。在这些档案学理论中,本体论具有原始反终的意义!档案学对 “本体” 的寻求, 是一种追本溯源式的意向性追求。它是档案学这棵大树的根、这条河的源。原始反终,就是所有档案学研究都要追根溯源,以本体论作为理论的基本支点与出发点。所谓“原始反终”,“原”即探察事物之源;“反”即推及。原始反终,就是指通过探明的事物本源就可以推及事物发展的结果以及认识事物的种种属性。如《易·系辞上》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高亨注:“尹注‘原,察也。’反犹求也。此言‘圣人’考察万物之始,故知其所以生,究求万物之终,故知其所以死。”[5]
《档案学本体论》作为我的档案学基础理论体系建设的架梁之作,涉及了“档案学本体论”和“档案事业根本原则”两个合二为一的问题,它是在我此前种种研究的基础上,按照归纳抽象的逻辑完成的形而上的作品。它明晰了我的档案学的思想原点,成为我的档案学基础理论体系的逻辑基点。
在写作《档案学本体论》之前,我就有这样一种信念:要想真正理解档案与档案工作,首先要了解它们与社会实践的关系,搞清楚这一点,是了解档案学的关键和起点,即原始反终。著名心理学家、哲学家皮亚杰在他的著名的《发生认识论原理》一书中说道:“心理发生只有在它的机体根源被揭露以后才能为人所理解。”[6]法国哲学家孔狄亚克则说道:“要找到知识的出发点,唯一的方法就是破坏这些观念的本身而追溯到它们的本源上去,即追溯到感觉上去,从而重新取得这些观念。”[7]“笛卡尔认为,要得到一个清楚可靠的思想来作为知识的出发点,首先要清除思想中由传统教育而得来的一切成见。”[8]
档案学或档案事业的根本原则与《档案法》规定的档案工作基本原则是什么关系呢?简言之,档案工作基本原则的档案事业根本原则决定的,是在档案事业根本原则决定下的档案人的行为准则。
4.2 理论之核
我的档案学本体论和档案学、档案事业的根本原则,从本质上是唯物主义的,即存在决定思维。作为理论之本,它与档案学理论的其他部分都是相同的,对档案学理论的其他部分具有规范与指导意义。笔者自己曾感叹道:本体论完成之后,我的档案哲学体系,才有了大梁、才有了纲。常言道:纲举目张,档案学基础理论体系才有了共同的纲。
如下图所示:档案实践本体论对档案学各个部分都具有指导意义,档案学基础理论的其他各个部分都是实践本体论在某一具体方面的具体反映,并使得档案学区别于其他相关学科。我们以《中国档案分类法》为例:《中国档案分类法》是以人类实践活动的领域划分档案类别,这是档案实践本体论的具体反映,全宗理论、档案整理原则等亦是如此。而《中国图书分类法》反映的是知识本体,与《中国档案分类法》具有明显的差别。

4.3 工作之“魂”
原始返终,档案本体论源于人类活动、脯于人类活动。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说:档案实践本体论是解决档案工作实践问题的一把“金钥匙”,是档案工作的武功秘籍。存乎心,用于行。要想妙用,先要理解。如果我们的档案工作者(包括实务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能够真正理解了这个理论,就可以达到灵活运用、普遍应用的境界,这种理论在档案工作中具有无穷无尽的指向性。它本身是具有这个境界的,是否能够实现,则在于学习者、应用者是否能够知行合一。
从实践角度而言,理解理论的标志是从理论中看出实践来,找出实践来并加以应用。比如一个档案工作人员初到一个单位,首先要了解什么呢?当然首先要了解档案,但这不是最根本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要了解这个单位的实践活动。不了解这个单位的实践活动,你怎能知道它应该有什么档案?档案应该怎样分类?要做好这个单位的档案工作,首先要了解这个单位的实践活动。做到了这一点,你才能保持档案工作与实践活动的一致性,并最终做到档案工作与它所对应的人类活动的同一性。而做到到档案工作与它所对应的人类活动的同一性,是档案工作的最高境界。
5 延伸与发展
本体论的发表,是我的档案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节点窗口。它标志着我的档案哲学体系初步形成,也标志着性的深化研究的开始。距离《档案学本体论——兼谈档案学的根本原则》的发表已经有4个年头了,这4年来笔者又做了什么呢?
在这4年里,笔者的档案哲学方面的成果并不多,主要是2019年在《北京档案》发表的关于档案学研究方法3篇系列论文[9]。论文除对档案学研究方法进行了整体论述外,还从档案实践本体论出发,提出了档案学的根本研究方法为“实践皈依法”,这是档案实践本体论的延伸与运用。当然,这项工作并没有完全完成,下一步还需要对“实践皈依法”做进一步的阐述与说明。
总体而言,在《档案学本体论——兼谈档案学的根本原则》发表以后的这4年间,是一个短期的休整,主战场的短期转移(这段时间笔者以研究档案历史语言学为主);而另一方面也酝酿着新的出发。这个新出发的标志就是2020年初发表于《档案学通讯》的《论档案的根本作用是人类群体思维的重要经验基础——兼论档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一文[10],它将开启笔者的“档案经验哲学”研究之旅,它将通过“实践-经验”打通档案学与哲学的沟通与对话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