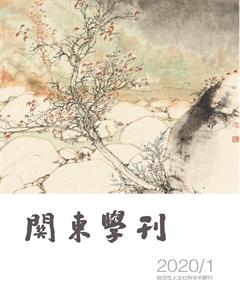文字、理性和正义:三期启蒙辨析
[摘要]第一期文字启蒙开启了文明的历史,第二期理性启蒙开启了现代的阶段,但两者都因为忽视了正义启蒙陷入了异化和自败。所以,我们今天有必要开展第三期正义启蒙,通过揭示趋善避恶、取主舍次的实然性人性逻辑,确立不可害人、尊重人权的应然性正义底线,让更多的人意识到坑人害人、侵犯权益的不义邪恶,努力减少现实生活中“正义不仅迟到而且缺席”的蒙昧现象。
[关键词]启蒙;文字启蒙;理性启蒙;正义启蒙;不可害人
[作者简介]刘清平(1956-),男,哲学博士,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上海200433),武汉传媒学院人文学院教授(武汉430205)。
也许是赶上了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事件一百周年,启蒙最近又成了学界的热门话题,反思的文章和重启的建议不时可见。在此我想从一个稍微宏观点的视角出发,讨论一下文字启蒙、理性启蒙和正义启蒙的关系,把它放在“历史性三期”的动态维度中看,以免总是停留在过去的世纪里,单靠着反思和重启炒现饭。
一、三期启蒙的历史定位
大家知道,中文里的“启蒙”一词来自《易经》的“蒙卦”:“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噬告,再三渎,渎则不告”;翻译成大白话意思就是:“不是我求不懂事的熊孩子,而是熊孩子来求我。第一次求我自然是有问必答,但要是三番两次跑来胡搅蛮缠,我就懒得搭理了。”至于“初六”里的“发蒙”二字,尤其接近现在的“启蒙”一词,显然有了“启发蒙昧”的語义。
那么,被启发的“蒙昧”又是个什么意思呢?主要是指人类的无论个体还是群体,还是小孩子的时候都免不了的愚笨状态,得经过开化才会逐渐“文明”起来。而在宏大叙事的历史分期中,“文明”有别于“蒙昧”(以及“野蛮”)的头号象征,正是“文”字的发“明”,让人们可以把平时靠亲身经验习得的知识一点点地凝聚起来,再一代代地传下去,不必周而复始地走老路,每一辈都要花很长一段时间从头习得。回想一下老祖宗们只有靠给绳子打几个结才能记下历史事件的大麻烦,我们就不难理解这发明的意义有多大了。这样看,第一期启蒙的实质其实就在于识字的人教不识字的人识字:谁识了字,谁就能尽快掌握前辈积累下来的知识,成为“文化人”(“被‘文字开‘化了的人”),不再是熊孩子般的“童蒙”或“蒙童”了。
第一期启蒙是众多的“文明”古国老死不相往来地孤立完成的,证据之一就是它们的文字系统不一样,旧约还把这档子事说成是上帝有意制造的巴别塔事件。第二期启蒙的情况就不一样了,首先发端于16-18世纪的西欧,然后又一步步蔓延到全球,这就是英文叫做“Enlightenment”的“启蒙运动”。同时,对它的“反思”也早已开始了,一直延续到今天,内容上主要围绕自由权益还是平等博爱的矛盾展开,形式上主要围绕激进革命还是渐进改良的对立展开,这里就不去细说了,只是想借此质疑一下流传很广的某种说法:尽管都打着启蒙运动的旗号,英国苏格兰的实际上是与法兰西德意志的对着干的,前者回绝了后者的“理性”,保守住了自己的“经验”,所以泾渭分明、天壤有别。或许是担心听起来不够高大上,“保守”有的时候又被说成是“守正”,强调被保守的不是随便什么玩意儿,总是正确、正当、正派、正直的东西。
如同哲学上的许多概念一样,“理性”这个词已经被西方思想家们搞乱了,所以也给今天的人们留下了不着边际的海阔天空,可以随心所欲地瞎说一气,反正谁(包括说话者自己)都弄不明白它到底有几个意思——可能或许似乎好像仿佛大概其就是指这个或那个东西吧。不过,倘若我们也能保守一下形式逻辑的同一律,让它只有“合乎逻辑的思维能力”这一种严格的核心语义,就能一举捅穿那层覆盖了两家启蒙运动的窗户纸了:要是英国的苏格兰人为了保守经验回绝了理性的话,他们其实连第一期文字启蒙也不必有的,因为人们识字的目的正在于借助理性文字的凝聚作用,把感性经验的流变知识固定成型,学起来能够容易一些。所以,宣称英国苏格兰在启蒙的时候回绝了理性,就有点类似于指认圆形之方了,等于是一脚把他们踹回到了茹毛饮血的年代。谓予不信,请看当时的休谟:他批理性的时候可激进了,一点不保守,但靠的还是自己的逻辑思维、推理论证(尽管也有不少自相矛盾),因此完全可以说是用理性反理性,不然的话怎么会留下那本洋洋几十万字的《人性论》,让现而今的保守主义者能有一些厚重的东西可以保守或守正呢。
既然文字的启蒙已经诉诸理性了,第二期启蒙为什么还叫“理性的启蒙”呢?原因很简单:在文字的启蒙那里,理性还是才露尖尖角的小荷,要等到理性启蒙的年代,才能长成一棵成熟的大树。德国的康德正是这样定义的:“启蒙运动就是人类摆脱自己加给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的状态就是别人不引导就不敢用自己的理智。……要敢于用自己的理智!”其实,这口号古罗马的贺拉斯就喊出来了,怎么要过了一千七百年,启蒙运动才想起来剽窃一下呢?就因为成熟需要时间,没法一口气吃个胖子或减肥成功。
这口号加上英国哲学家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便联手塑造了理性启蒙的“现代”阶段,后来还被德国的韦伯概括为“现代化即理性化”,与文字启蒙的“古代”阶段一起构成了“文明”的历史,以区别于原始人“蒙昧”或“野蛮”的历史。当下中外学界都有论者声称,现代化只是个“偶然”的事件,说不定压根就不会发生。这说法相当时髦,但可惜也被西方的概念绕晕了,近乎蒙童地忘记了下面的事实:假如理性化当年出现在西欧的时候,真的是瞎猫随机碰巧地撞上了一只死老鼠,后来世界上其他地方那么多的瞎猫们,就不大可能也以照着葫芦画瓢的方式,前赴后继地接连撞上同一只死老鼠了。碰巧撞上一回那叫“邂逅”,但要是一回接一回不厌其烦地总是撞上,谈过恋爱的都知道,就属于剪不断理还乱的“缘分”了,俗话或日“天注定”。
因此之故,对理性启蒙的反思,其实也就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并且催生了一大批比乌托邦还要乌托邦的“后现代”愿景,个个长得很丰满,人人见了都艳羡,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和谐圆融,世界大同。不过,我打算在此推出的第三期启蒙却是反差鲜明的绝对骨感,这就是“不可害人、尊重人权”的正义启蒙,意图也只有一个:一方面指出前两期启蒙的共通缺陷在于扭曲了正义感,让人们误以为出于这样那样的目的坑人害人、侵犯权益是正当的;另一方面说明不可害人、尊重人权为什么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终极底线,应当怎样基于趋善避恶、取主舍次的人性逻辑落到实处,尽可能减少现实生活中“正义不仅迟到而且缺席”的严重蒙昧现象。坦率地说,这里用的词是“减少”不是“杜绝”,正是要传达那份有点硌得慌的骨感体验。
二、前两期启蒙的异化自败
有人说了:我以为有多原创呢,原来是个老掉牙的常识啊。这话真没说错,因为就连人类最初的小团伙(原始人群),虽然只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木棍,也得靠这个常识撑着,不然野兽还没打死,自己先被同伴做掉了。或者换一种方式说,哪怕是被愚笨的状态蒙昧着,人们在限定的范围里也还是有不可害人的正义感的,否则就没法维系小圈子的正常生活秩序了;后来先秦的墨子将这一点概括成:“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墨子·天志上》)说白了,文明社会的伦理道德什么的,无一例外统统是从这种素朴的正义感中衍生出来的,核心的诉求就一条:不可坑害你的同伴。
既然有了前两期启蒙,并且也形成了文明的伦理,为什么今天还要推出一个第三期来呢?理由就是在保守这种最原初的正义感方面,前两期启蒙不仅是异化的,而且还自败了。
开篇的时候提到,蒙童般的熊孩子主要是因为不懂事胡闹腾的缘故,才需要“发蒙”或“教化”一下的。所以,中国古代的文化人给他们启蒙的时候,“自生自发”地选用的元典教材,就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增广贤文》这类如雷贯耳的东西。但很不幸,这些课本虽然特别强调了这事理或那规矩,却好像没怎么想起不害人的事,结果文明而又道德地花里胡哨了一大通,反倒把最基本的正义感掩盖住了(文言又叫“遮蔽”),甚至怂恿人们为了这事理、出于那规矩,不惜突破了底线去害人——或者更精确点说,怂恿人们为了关爱自己看重的同伴,不惜坑害自己不看重的同伴。最极端的例子要数“二十四孝”里面的“郭巨埋儿”了,居然不带一点掩饰地歌颂当爹的为了对母亲尽孝,不惜挖个坑想把三岁儿子给害了的未遂行为——“坑害”一词说不定就出白这个故事呢。所以叫做“异化”:只要是为了当上忠孝节义的道德模范,哪怕你干点杀人越货的恐怖勾当,也是可以允许甚至值得赞美的。
于是乎应了那句老话:不识字的时候被识字的骗,识了字又被书上的字骗——或者说不管你识字不识字,都能把你忽悠了。并且,识字后的忽悠效果似乎还要更好一些:不识字你会小心谨慎地说,“我读书少你莫骗我”;识了字有了文化,你却会气壮如牛地宣布,“我读了那么多书,难道还会被骗了不成!”结果被更有文化的人忽悠得五体投地:“您老人家真是天要是没生下来就万古长如夜的先圣前贤啊。”至于这类启蒙的“自败”一面,不妨引用鲁迅的一段话吧:“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家景正在坏下去,常听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的父亲竟学了郭巨,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么?……这大概是送给《二十四孝图》的儒者所万料不到的罢。”(《二十四孝图》)他老先生后来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干将,这类文字启蒙的自败效应想来是功不可没的。
撇开其他地方的情况不谈,西方的瞎猫撞上死老鼠的原因也大体差不离,同样是因为发现自己识了字又被书上的字骗了,不肯异化地被人挖个坑给害了,所以才大张旗鼓地发起了启蒙运动。但并非偶然的是,由于古希腊文明率先推崇理性的缘故,同时也由于另外一些相当必然的缘故,这场运动当初兴起的时候,没有浅显直白地竖起不害人的大旗,而是像康德定义的那样,藏着掖着地要求人们“用自己的脑袋瓜理性地想”,倒好像问题仅仅出在“用别人的脑袋瓜非理性地想”似的。其实,这位哲学家发这个号召的时候,原本也希望人们能用自己的脑袋瓜理性地想一想“把所有人都当人(同伴)看”的问题;然而,由于误以为逻辑思维的“纯粹理性”直接就是实践行为的“良善意志”,他始终没能看到关键的那一点:“不坑害同伴”属于“意欲”是否“正当”的态度问题,不是“理智”是否“成熟”的知识问题,结果主张:只要掌握了普遍的真理,人们就能水到渠成地维系永久和平的世界大同了。于是,这点小小的误差同样异化并且自败了理性的启蒙,甚至忽悠了后世不少学者,义无反顾地钻进了他精心构造的魅惑体系,皓首穷经地沉迷于他没想明白的晦涩概念,买椟还珠地遗忘了他绝对命令的“人是目的”,一门心思地想让自己的理智如同他老人家一般成熟,却唯独忘了这个号召的潜台词:别以为只有学到了我的理智,你才有资格大着胆子想问题。或者换一种方式说,由于真诚地叹服康德大师的启蒙号召太有威力了,这些学者真心觉得要是没了他的权威引导,自己都少了点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了……
话又说回来,启蒙运动的这种学术自败,虽然也可以说是有点愚笨的蒙昧状态,实际上没啥大不了的,无非是一小撮人自得其乐地做自己喜欢做的学问,还能顺便教学生认识几个普通人不肯花心思去认的深奥字词,因而是人畜无害。不过,启蒙运动在特别关注理智生活熟没熟透的同时,又忽略了不可害人的头号要害,异化的后果就严重多了,集中表现在:它原本以为靠着理性化的科学以及民主,就能一劳永逸地终结黑暗中世纪导致许多人丧生的宗教战争;谁承想启蒙照亮了的新时代世界大战,却凭借热兵器远超冷兵器的理性化威力,先行终结了多出了不知多少倍的可怜性命——其中不仅有法兰西德意志的,也有英国苏格兰的。再联想起几十年前还有位西方的大咖,热衷于诉诸市场经济外加民主政治连人类的历史也一并给终结了,再次向世人奉献出了圆融和谐的丰满愿景,实在是让人忍不住感叹:我们的记性怎么那么差,比金鱼的七秒钟好不到哪里。
順便提一下,一次大战的血淋淋实景(不是愿景),不仅在欧洲引发了新一轮的启蒙反思,而且还让这边某些原本激进的儒者突然转向了守正。但尽管如此,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依然是一往情深地期盼着“赛先生”和“德先生”大驾光临,虽然有点急功近利地冷落了两位绅士的“理性”母体,那种一心想要“全盘西化”的念头却是跃然纸上的,连“容忍比自由重要”的大爱标语,也被胡适以青出于蓝的方式提前挂出来了。有论者感叹说,我们学西方总是没赶上好时机。平心而论,这样说有点生意不好怨柜台的意思:你自己没眼光挑出对症的药来,凭什么把责任归咎于人家药店老板的过期特价广告啊。
相比之下,倒是鲁迅敏锐地意识到,根子不在于我们缺少了科学民主(包括现代医学)这些舶来的物品,而在于自家延续了多少年的吃人礼教,并且因此把精力放在了揭露这种害人东西的根深蒂固上。这样子的弃医从文才是足够深刻的思想启蒙,因为理性的科学并不能保证一定不害人;相反,按照它的原理制造的飞机大炮,也完全可能被用来帮助实现轴心国的邪恶目的。再往深里看,我们好像也难以振振有词地宣布:一旦得到的票数超过了51%或三分之二,结局就一定是正气浩然大义凛然的。我主要就是基于这个考虑才觉得,撇开了原创性的情况不谈,单就思想的深度看,胡适也是很难超过鲁迅的。无论如何,倘若没有确立不害人的正义感,不管你有多科学多民主,还是有可能通过高度发达的工具理性,造成坑人害人的不义后果。
二战之后,西方人好像也慢慢发现了问题不在理智成熟不成熟(难道纳粹分子的逻辑思维一定比你幼稚么),所以才重新拈出了两百年前杂有英美法德因子的人权概念,可还是没意识到“尊重权益”的实质在于“不可害人”,反倒在一系列宣言里把“尊重应得权益”混同于“满足基本需要”,结果按着胡适式的步调走,用平等博爱压倒了自由权益,甚至同样赞成为了关爱这些人不惜损害另一些人。直到今天,“全球正义”的左翼阵营仍然免不了这种大爱无疆的毛病,非要把底线划在了“让所有人过上体面生活”的维度上,却没搞明白一条简单的道理:我要是因为自己不讨人喜欢找不到对象,没过上有婚姻的体面生活,你当然可以出于无边的爱,宽大为怀地容忍我的种种缺陷(容忍比自由重要嘛),心甘情愿地娶了我或嫁给我,以满足我的基本需要;但即便这样,你还是找不到令人信服的充分理据,硬把这种自我牺牲的圣洁爱心说成是尊重我的自主婚姻权益,甚至断言它构成了全球正义的核心诉求吧。而要是你自己不肯拥有这类自律性的高尚美德,却逼着别人把它们当成他律性的义务来履行,就更是等而下之的坑人害人了,用“伪善”来形容一点不过分。
于是,启蒙启到了这种把自己都蒙住了的份上,确实该好好反思一下了,但似乎没必要搞什么再来一回的重启,因为只要错失了正义这个目的,不管怎样执着于文字和理性,还是会一如既往地在异化中自败的。原因很简单:一个人识了字有了理性,包括懂得好几国语言拿到了博士学位,不见得就能美美与共、万事大吉了,因为照样还会沦为单纯被利用的工具;只有确立了尊重权益的正义底线,他才可能拥有人格的尊严,真正成为被当作人来看的目的。所以,我们不如另起炉灶,干脆把工夫用在不害人的正义感上,以最保守的方式让更多的人明白这个最原初的事理,懂得这条最基本的规矩。毕竟,与某些受过理性化高等教育的教授专家们比,许多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的乡下农民,也许更能守住“害人之心不可有”的底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确有理由说,包括文字和理性的在内,任何不以正义为目的的启蒙都是耍流氓。
三、正义启蒙的自主性
“启蒙”(主要是启蒙运动)受到质疑甚至否定的一条主要理由,是它听起来有点居高临下的傲慢,不像“引导”那样恭顺服从的谦虚。不过,保守主义的质疑者们好像忽略了一点:撇开不启蒙、只保守容易落人单单保守了蒙昧的陷阱不谈,“引导”别人也可能充满了“要是没我指路你早掉沟里了”的优越感,甚至更有实践方面的强制性:“你要是不愿意跟我走的话,我就要不客气地领导你前进了。”可见自我反思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不然的话,你只顾挖苦别人长得白,却忘了自己刚从面缸里爬出来。
不用细说,现实中确实能找到大把的启蒙者,喜欢一览众山小地看谁都是愚笨之人,雄心勃勃地想要引导他们走上人间正道。但就其本性看,思想上的启蒙首先还是自主性的,因为与一个人不肯跟着走还能强行拖着引导他走不同,一个人要是压根没意识到自己有着明事理懂规矩方面的缺失,他是不会形成摆脱蒙昧的念想的。在这种情况下,哪怕你对他发起地毯式轰炸一般的灌输洗脑,也会如同对牛弹琴一样无效——甚至还不如,因为对牛弹琴据说是真能改善其体质、增加产奶量的。即便你拿着鞭子抽他,强迫他接受你的看法,他口中不得已也认了,心里还是会骂你一千句甚至一万句傻帽。所以,一个人如果不愿意,谁都没法给他启蒙。
说来你不信,《易经》已经察觉到了这一点,所以才说“不是我求不懂事的熊孩子,而是熊孩子来求我”。这可以表明,远古不像经过教化世风日下的现而今,算命大师们都是有骨气的:除非年纪轻轻的你觉得前途未卜心里打鼓来求我算一卦,我才不会主动上门给你参天地观六合呢。更重要的是,要是我指点了迷津你还是不信,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推倒重来,非要抽得个上上签才住手,我是不可能低三下四犯贱引导你走路的。换句话说,我尽管拥有高屋建瓴地启蒙你的优越感,但内心深处还是很清楚“你要是装睡我怎么喊得醒”的道理的,远比两千年后把这句口头禅炒得火热的人们明白得多,所以才会一开始就摆出一副“如果你不愿意我就不会开发你”的傲慢姿态。从这里看,不管去不去启蒙别人,启蒙者都很难摆脱傲慢的嫌疑。不管怎样,要是一切人际启蒙都有傲慢的毛病,我们岂不是只有割断了人与人的一切交往沟通(包括引导),才能让自己变得谦虚起来呀。
至于指责启蒙运动的理性傲慢,好像更是欲加之罪了,因为德国的康德说得很明白:“要敢于用自己的理智!”此外,为了给自己的抄袭注人新意,他还特别指出自己是为了反对那种没别人引导连脑袋瓜都不敢开动的青涩不成熟,才借鉴了一下贺拉斯的语句,仿佛已经猜到了后世有人批评他不引导、只启蒙似的。所以,以学术为志业的基本要求,就是无论做事实描述还是价值评判,也无论态度是肯定拥护还是否定反对,都要有靠谱的文本根据,不能凭空想象地信口开河,否则一不留神,神没留住却留下了把柄。
再来看第三期的正义启蒙,当然也是自主性而非他律性的。说穿了,一个人什么时候最容易进发出不可害人的“义愤”,并且基于这种发自内心的正义感,挺身反抗坑人害人、侵犯权益的行为呢?就是他自己受到了坑害、权益被侵犯的时候。所以,现实中经常可以看到下面的自我启蒙现象:某人对别人受到了坑害、权益被侵犯的事漠不关心,碰到有人来启蒙自己的正义感也是听而不闻,但一等到自己亲自受到了坑害、权益被侵犯,自己就把自己的正义感开发出来了。其实,哪怕张三是靠着李四的帮助才意识到不可害人的底线意义的,这样的启蒙对他来说依然是自主性而非他律性的,因为假如张三自己不愿接受这条底线的话,李四再开导也不会管用。
本来,倘若与文字和理性的启蒙比,正义的启蒙实在没啥好傲慢的。认识很多字,敢于用自己的理智,好歹算一种资本,足以在不识字不敢用自己理智的人们面前傲慢一下。然而,不可害人只是一个老掉了牙的常识,盘古开天地的年头就有了,现在更是无人不知,饱学之士还觉得太肤浅不值一提呢,有什么可傲慢的呀。诚然,不可害人涉及到了事情的根本,因此也可以说是深度的启蒙,需要用由浅人深、深入浅出的方式展开,但这也没法赋予正义启蒙高人一等的特权地位,因为它的核心诉求恰恰是:既不允许任何人坑害自己,也不允许自己坑害任何人。也只有这种既限制了别人、又限制了自己的特定平等,才是我们唯一应当强制性地坚持到底的人人平等。因此,尽管正义的启蒙并非没有异化和自败的可能(尤其在权益之间出现冲突的两难情况下),我们也有必要时刻警惕这样的风险,但与前两期启蒙比,它在自身中业已潜含了克服异化和自败的契机了:不管你识不识字(现在这种可能性很小了)、理不理性,都既不可坑害别人,也不可让别人坑害你,而应当在复杂的冲突中,将既尊重自己权益、也尊重他人权益的正义底线贯彻到底。
再说了,对于那些明明知道这常识,可还是顽固不化地坑人害人的野蛮之人,谈得上傲慢不傲慢吗?难道不是应该把所有的谦虚甚至怜悯甩在一边,义愤填膺无情鄙视才对吗?你摆出一副容忍高于一切的样子同情作恶者,把受害者置于何处呢?而對于那些明明知道这常识,但自己受到了坑害、权益被侵犯却还是不抗争,反倒对加害者感恩戴德的蒙昧之人,又哪里有必要谦虚谨慎向他们学习啊?这样的斯德哥尔摩症患者连自己的尊严都不要了,你要是真的虚心学了他们,不会把自己也变成了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的奴才么?
前面说第三期启蒙属于绝对骨感的硌得慌,并非风情万种的乌托邦,部分的原因也在这里:不管正义的启蒙取得了怎样的成就,任何时候任何社会都还是会有人无视不可害人的老掉牙常识,或者为了一己私利,或者为了家人亲情,或者为了忠君大义,或者为了虔诚信仰,或者为了建功立业,或者为了世界和平,总之是一些要么卑鄙要么高尚的理由,不惜坑人害人,侵犯人的应得权益,甚至打着这样那样冠冕堂皇的旗号躲开正义的惩罚,在自己做下的恶中骄奢淫逸纵享荣华。正义的启蒙根本不会沉溺在那些美妙而又空虚的幻想里,试图以后现代的梦幻方式完全避免所有的不义;相反,它仅仅寄希望于让更多的人明白什么叫人的应得权益,这些权益为啥是不可侵犯的,从而意识到不管有着怎样圣洁的借口,坑人害人都是邪恶的,并且敢于用自己的努力(不只是自己的理智)积极反抗不义,最终建立起恪守底线的正义法治,尽可能地惩罚一切坑人害人的侵权罪行。
事实上,即便建立了这样的法治,正义的启蒙也不会渲染“正义虽然迟到不会缺席”的理想愿景,因为人毕竟是有限的,并非洞察秋毫的全知万能,所以不管正义的启蒙取得了怎样的成就,任何时候任何社会都还是会有害人者借助于这样那样的方式逃避正义的惩罚,导致正义的不在场或缺席。换句话说,由于人的绝对有限性和冲突的不可避免性,人生在世永远不可能达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和谐圆融、世界大同的美妙乌托邦。但事情的另一面是,这类蒙昧的现象非但没有取消、相反还恰恰凸显了正义启蒙、建立法治的底线意义,能够让我们通过硌得慌的骨感体验,更迫切地察觉到正义启蒙的绝对必要和至关紧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