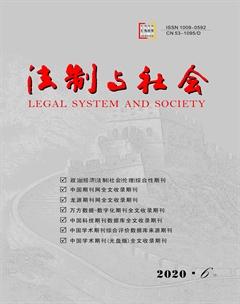新型网络组织卖淫案件实务研究
唐敏芳 徐思诗
关键词 互联网 组织卖淫 零口供
作者简介:唐敏芳,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徐思诗,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
中图分类号:D920.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06.139
一、新型网络组织卖淫案件的特点
(一)网络的传播速度为招嫖信息的散播带来便捷
新型网络招嫖犯罪突破了传统淫业中地域及场所的局限性,借助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社交软件的普及,向社会各阶层、各领域、各年龄段的人群扩散。在组织卖淫案件中,利用互联网发布的招嫖信息也不再受限于宾馆内散发小卡片的形式,而是通过微信群、朋友圈、QQ空间,甚至建立专业的网站等平台整合发布卖淫女的相关信息,不受纸张篇幅等限制,不仅有卖淫女的照片可供参考,更是将价格、服务内容等信息一应公开,使得嫖娼卖淫犹如进行网购一般便利。
(二)犯罪者的年龄层次趋于年轻化
2019年11月19日,最高法发布了《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之网络犯罪特点和趋势》,显示网络犯罪案件在全部刑事案件中的案件量及占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其中被告人的年龄主要分布在20周岁至40周岁之间,28岁的占比最多,未成年人亦占比0.82%。笔者办理的吴某组织卖淫案中,组织者吴某是一名95年的小伙,而其雇佣的协助其组织卖淫的其他涉案人员多为90后的青年,年龄最小的不满18周岁,仍系未成年人。此类案件中组织者善于利用网络,通过前期的雇佣客服、现场接待、司机等人员,足不出户的在幕后就能完成对整个卖淫活动的操控。个别年纪尚小、初入社会的打工者,心智尚未发育成熟,身处组织卖淫团伙之中,甚至无法分辨其工作内容是在协助犯罪,对日后的其成长及发展都将产生巨大的危害。
(三)层出不穷的招嫖方式
近期,有几种新型的招嫖方式出现,并引发了一定关注,出现在某主打二手物品交易的APP平台,商品描述为“新茶”,封面配有美女照片,实则是带有“性暗示”话语的招嫖广告。在笔者办理的吴某组织卖淫案中,客服人员亦向客户发送过暗语“新茶到”,经调查,“新茶”“喝茶”已成为了行业内卖淫、嫖娼的暗语。某主打分享体验的社交平台被爆涉黄,一些在该平台分享酒店体验的帖子,实则亦为招嫖广告,如有人在评论中询问酒店价格,得到的回复实际上是对方提供卖淫服务的要价。
(四)“真凶”隐匿于虚拟的网络世界中
为躲避侦查,犯罪者通常会通过使用他人注册的微信号实施犯罪,由于社交软件的匿名性和虚拟性,使得犯罪者可以很好地“隐形”,隐藏于一个个虚拟的账号下对查证工作带来巨大的难题。除此以外,犯罪者还会通过收购他人身份信息注冊的银行卡在第三方支付平台完成嫖资的收付,此种线上支付的方式将资金去向隐匿,对侦破工作带来阻碍。
二、办理新型网络组织卖淫案件的难点
(一)确认犯罪者与虚拟账号之间的关联性存在难题
在笔者办理的吴某组织卖淫案中,吴某先后使用过多个微信号与团伙成员进行交流并收取嫖资。为逃避侦查,一般犯罪者使用的微信号绑定的手机号都不是其实名注册过的号码,在当事人不承认的情况之下,这些用于实施犯罪的微信号是否就是犯罪者本人持有使用,在这一关系的确认上存在难点。此外,微信昵称可随意改变,通常在查找到案件相关证人或当事人作笔录时,也只能记得犯罪者使用的微信昵称比如”小X”“老Y”,并不能体现犯罪者的真实身份。
(二)团伙成员之间各自分工,互不相识
排除了地域的局限后,网络组织卖淫案件中通常没有一处固定的“办公场所”,组织者、客服人员、接待人员、司机等团伙成员通过网络聊天工具进行联络,各环节人员按步配合,远程操控卖淫嫖娼活动的进行,团伙成员相互之间可能只知QQ、微信的昵称,有的通过组织者组建工作群,群聊名称通常伪装成一些养生SPA工作群、姐妹交流群等,给案件侦办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团伙成员甚者只与组织者单线联络,更不可能与团伙成员见面,自然不知道互相之间的真实身份。
(三)电子证据的灭失导致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通常组织者均具有一定的反侦察意识,会经常更换使用不同的微信账号,也势必会将相关的聊天记录清除,防止留下犯罪痕迹。如前所述,团伙成员之间可能在真实社会中互不相识,在缺少聊天记录、通话记录,又缺少当事人指证的情况下,仅靠供述无法准确认定完整的犯罪事实。
(四)卖淫女及嫖客无法有效指证组织者
尽管网络招嫖犯罪多是存在一段时间后才被侦破,能够查获的卖淫嫖娼行为占少数,即便当场抓获了卖淫女,也不一定是组织者直接招募,在笔者办理的吴某组织卖淫案中,在各处抓获的20余名卖淫女中,几乎无人指证系由吴某直接招募。此外,因卖淫女行业流动性较大,案发后再去查找以往为该团伙服务过的卖淫女难度较大,因此对于卖淫人次上的认定无法做到全面。
三、建议及对策
(一)做好前期预防犯罪工作
首先,从源头上加强互联网监管,切断淫秽信息散播途径,做到打小打早,防止卖淫团伙在监管的黑洞下成长为庞大的犯罪团伙。
其次,加大网络卖淫监管的人员和技术投入。目前,网络警察的人数占比仍属少数,同时,现有的网络警察中并不都专业出身,建议公安机关招纳适当比例的有网络专业背景的人才。
最后,充分发挥居委会、村委会及社区民警的作用。对辖区内场所或租用房内经常性出现不明人员出入的异常情况多加注意,必要时开展治安检查,防止组织卖淫者以居住为幌子,以此作为提供卖淫服务的窝点实施违法犯罪活动。
(二)提高证据收集能力
首先,卖淫女及嫖娼人员的笔录尤为关键,卖淫女的供述中能够体现卖淫团伙的组织性,由何人招募而来、如何进行管理、服务内容及收费标准、如何招揽嫖客、分成的约定及嫖资给付等细节问题均需作详细询问。嫖客的笔录中一般只能证实卖淫场所的显性问题,隐藏幕后的想要他们来证明,一般会超出证明能力,但有以下作案细节可以通过询问嫖客予以印证,如从何处获知招嫖信息、由谁具体负责接待及介绍、嫖资如何进行结算等。对于利用微信、支付宝等账号支付嫖资、获取分成的情况下,对收款人、转账人的账号需进一步深挖,以此为线索查找幕后关联人。
其次,组织者到案后往往会否认查获的电子账号系本人操控,法证之父艾德蒙·罗卡的定律告诉我们“凡走过必留痕迹”,即使狡猾的犯罪者隐藏于虚拟网络之中,仍会流出蛛丝马迹带来侦破的线索。在吴某组织卖淫案中,吴某对于查获的微信号均否认持有,通过后期引导侦查,一方面,从涉案微信号绑定的手机号追踪到实名注册人,另一方面通过房东确认卖淫场所的承租人及对方缴纳房租使用的账号,最终确认了吴某与这些微信号之间的关联性。
四、定性的把握
网络招嫖行为虽脱胎于传统卖淫,但其组织行为的方式、内容、性质等已经远比传统淫业中的组织行为丰富得多,在判断网络招嫖犯罪中的组织行为时应当更多地结合网络犯罪的新特点,考虑行为人对被卖淫人员的管理、控制的方式及程度等情况,对组织行为加以正确把握。
(一)对卖淫人员的管理、控制
在网络招嫖案件中不难看出,组织者对卖淫者的人身和精神上的强制性管束开始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类似公司对员工的管理模式和调度方式。如果暂且忽略卖淫嫖娼活动的违法性,单纯将其作为劳动的一种,那么卖淫组织的头目就是用工者,而卖淫者则是提供劳动的工人。从组织者角度来说,组织者“招募”卖淫者,使其在自己的安排下开展卖淫活动,并从卖淫活动中牟取暴利是最大的犯罪目的。从卖淫者角度来说,在竞争日趋激烈、管控日益严苛的市场环境下,为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和风险成本的最小化,自愿接受组织者的调度与安排,开展卖淫活动,最大限度的赚取利益。组织者和卖淫者在共同的经济利益刺激下,形成了“雇佣者”与“被雇佣者”的“双赢”,自然不需要像传统卖淫产业中通过对卖淫人员进行人身自由或施加精神压力来实现管理、控制的目的。
(二)对卖淫活动的管理、控制
对卖淫活动的控制主要体现在:事前,由组织者整合卖淫人员信息资源后,统一发布至群组、空间、网站等平台,招嫖信息中卖淫活动内容为标准化的服务流程及统一的收费标准;事中,统一由“客服人员”与嫖客洽谈交易细节,确认服务时间、引导嫖客至指定场所、安排卖淫人员上钟等具体事宜;事后,统一由“客服人员”向嫖客收取费用,再按照约定的比例分配给卖淫人员。
其中,场所要件已经逐渐从网络组织卖淫案件中淡化,成为认定组织卖淫行为的非必备条件,传统淫业中,组织者往往会以宾馆、洗浴中心、会所、发廊等为固定场所,或者以经营宾馆、会所等场所为名,行组织卖淫之实。但在网络招嫖案中,往往采取动态管理的模式,一般不需要建立固定的卖淫窝点,而是利用互联网通信远程操控他人从事卖淫活动,但其本质始终没有改变,都是以一定手段和方式对卖淫者进行管理和约束,控制卖淫嫖娼活动的进行。这种动态管理模式,将分散的卖淫人员组织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资源的共享,组织者手中掌握的卖淫人员不再限于场所内能够容纳的几人、十几人,而是通过互联网将资源整合,这些临時储备于“云端”的卖淫人员一旦接受了组织者指派的“卖淫任务”,又必须按照组织者制定的规则进行卖淫活动,这样做不仅扩大了卖淫活动面对的人群范围,提高了组织者对卖淫活动控制的灵活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设置卖淫场所的基础成本,又有利于逃避公安机关的追查,呈现出一种多赢的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