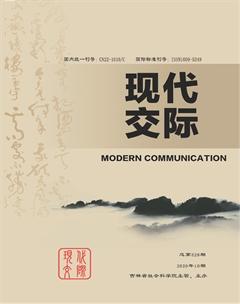浅谈两性围城中新式妻子形象
朱诗诗
摘要:以凌叔华《酒后》中采苕形象为例,探讨新女性进入婚姻后两性关系中的女性形象。首先,在“弑父”中与传统的割裂后,新式妻子是作为“女性”书写的,弥补了新文学对女性本身叙事的空缺;其次,“第三者”的符号化构思反证女性主体意识的匮乏;再者,在两性关系中主动行动者的形象凸显对“性别自我”的追求和作为“人”的主体意识的探寻;最后,自我形象的矛盾揭露了当时历史语境下女性婚姻角色与女性角色难以选择的危机困境。
关键词:新式妻子 女性意识 主体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20)10-0112-02
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批具有现代意义的新式女性形象诞生于五四时代,是推翻父系文化权威后初次进入话语领域的群体,主要以三种形象出现:作为“父亲的女儿”、作为“儿女的母亲”、作为“丈夫的妻子”。而婚姻关系中,男人/女人,是五四新时代中新女性的命题,象征着男权的社会结构/女性生存方式。在“弑父”般的叛逃、决裂的历史语境下,追求人生幸福、个体自由的新观念孕育了一批爱情的胜利者——“新式妻子”。
从这个层面说,新式婚姻关系是建立在爱情自主之上的,那么爱情能走多远?新式妻子的女性意识觉醒使两性沟通能达到什么程度?这类新式妻子所代表的妻性对于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形象有何颠覆或超越?新式妻子凸显的“人”的独立意识与个体意识怎样在作为特定性别话语——“女性”中实现更好的平衡?凌叔华笔下对新式妻子的想象,如《酒后》中的采苕,便直面此类问题。
一、作为“女性”的书写——对新文学盲区的弥补
对于生活在封建妻妾婚姻制度下的中国女性而言,现实生活就如同高耸威严的密封城墙,囚禁且泯灭妻子作为“人”的个体自由,将“女性”性别经验扭曲化,从而依附于父系社会为中心的宗族权力体系。五四期间的新女性,注定要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中披荆斩棘。《伤逝》中子君的宣言指涉的便是父权制家庭和封建意识形态对女性人身权利的压迫,实际上仍未摆脱作为“反叛女儿”的话语阴影,未能触及作为“女性”本身的生命体验——女性与异性的角色关系问题。
不难发现,所谓新女性与旧女性没有根本的区别,每个女人婚后都要面对角色的重负,都要承担作为妻子、母亲的义务。作为“新闺派”代表作家,凌叔华以女性的性灵体验和细致的艺术感觉直面这个问题,去掉新女性称号的光环,从婚后两性关系中透视新式妻子形象。这既是对新文学世界里新女性形象的补充,又开辟了婚姻围城中两性关系里对“女性”角色的符号审视,进一步走进作为“女性”本身的话语世界。
二、“第三者”符号化的艺术构思——女性主体价值自我审视契机
《花之寺》《春》《酒后》《女人》描写的新式夫妻间存在某一真实或拟想的外来因素——“第三者”。如《酒后》采苕酒后争得丈夫同意去吻一个醉倒的朋友子仪;宵音在春天惦念一位病中的倾慕者,这样的非常态第三者的介入,提供了一个女性试探主体价值的契机,透视出妻子这一角色在规训的角色内涵里被压抑的女性主题价值的匮乏。
小说的最后,采苕决定不要kiss子仪可以理解为采苕的目的不是在于得到对方,而是在这个象征性的关系里,对符号化的对象实现主体角色的尝试,甚至可以认为是在两性关系的规训中,尝试得到丈夫对自己的“过界”行为的批准。显然,第三者提供的非常态契机显示出美满夫妻关系中事实上的不平等、妻子的被动和被创造的地位。凌叔华写出了男人——丈夫们所不能洞悉的妻子的内心秘密,并通过这一点揭示两性之间、恋人间、夫妻间那种不可互通之处。
因此,凌叔华笔下的“第三者”形象首先为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自我审视提供一个契机,将女性从妻子的角色中剥离分化,展现女性作为“人”,作为“女人”的情感体验与主体意识的必要性;其次,第三者介入暗示两性关系中的不可互通性,揭示婚姻美满幸福背后仍然存在的性别话语经验差异;再者,第三者是一种女性心理补偿的存在。“这一他者功能并非在于破坏改变夫妻关系,而是十分微妙的女性心理补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指涉丈夫已不能给与妻子的东西——男女之间某种关系方式。”这种从女性角度探寻的心理活动,彰显了新时期女性性别意识的主动觉醒。
三、“性别自我”的探寻——两性关系中主动的行动者
凌叔华《酒后》中的采苕在作为觉醒的新式女性,其形象在与子仪的象征关系以及与丈夫的夫妻关系中形成一种微妙的相对张力。在对子仪的想象中,采苕的身份不再是“丈夫的妻子”“父亲的女儿”或“儿女母亲”,她对子仪的崇拜、爱慕、欣赏之情溢于言表,作为妻子的她去吻一个非丈夫的男子的行为,是出于少女般的憧憬,是戀爱的感觉,行动本身冲破作为“他人妻子”的规训内涵,以一个“性别自我”的姿态追求爱情和自由。
这种“性别自我”凸显着新式妻子作为“女性”的意识的觉醒,她以一个主动的、行动者的姿态出现,是对传统两性关系中女性作为被动者、被创造者、被代言者的形象的颠覆。凌叔华对子仪的描写并没有从子仪的角度赋予其心理活动或语言活动,一方面是因为他作为“第三者”的形象本身只是一个符号化的指称,作为一个被爱的对象,一个爱的承受者的存在;另一方面,体现了子仪作为男性在该状态下处于两性关系的被动位置,强化采苕作为女性的主动意识和创造者的形象。而在永璋对采苕外貌的描写中,妻子的存在更多地是一个被审美的对象,一个值得称赞的他物,是被给予的、被爱的、被倾慕的对象,消解妻子作为“人”的主体性。
因此,两性关系中主动行动的采苕体现的是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即从丈夫的意愿中区别自己,使自己作为行动意愿的主动发起者,内在生命体验的主动探寻者,进一步表现出作为“人”和“女人”的主体意识。
四、新文化体系中新式妻子的危机处境——矛盾割裂的自我形象
新女性在文学史上的出路要么进入家庭,要么拒绝家庭。前者埋没于琐碎日常生活,从而磨灭其“我是自己的”自由追求;后者拒绝承当社会性别角色,保持自主性。这两条出路从正反两面说明新思想女性在自主与寄生、“是自己的”与“是他的”之间的两难选择。而作为“新式妻子”的两难选择在于:要么实现已经完全社会化的婚姻妻子的角色期待,要么做一个感情的给予者、主动者,成为一个尚未被社会化的角色。前者将摒弃作为女性主体意识、自我意识,并且承担新文化价值体系下的诟病;后者则面对尚未完全成熟定型新文化体系的价值怀疑以及传统规训的指责。《酒后》中的采苕即是在以上两种选择中矛盾割裂的女性形象。
“酒后”的语境呈现出剥离于被理性伦理压抑束缚的日常规训状态,实现的是一种暂时的自觉的失控,一方面为女性内心原始生命体验的原动力的迸发另辟蹊径,在一种未开化的、原始的生命状态中弥补情感主动以及表达自我的空白;但另一方面,“酒后”产生的游离、虚幻感暗示这一切冲动的无力和苍白。即便是冲出现实两性关系的围城,女性作为妻子在婚姻关系中实现“人”的本能冲动也是有限的,只存在于短暂的“酒后”,是思维混沌、逻辑矛盾的“酒后”而已。
由此,在新文化体系中,新式妻子的形象是矛盾割裂的自我形象。这种矛盾割裂既源于旧有生活方式规训的性别角色要求——作为丈夫的“妻子”,又源于新的主体价值观念——“我是一个人”的呼喊。
五、结语
“女权主义进入中国从来不是针对男人,而是针对封建社会——男人借女权主义反对封建主义——这是它在中国的第一个特点。”因此,女性主体意识觉醒伴随“弑父”历史零点的发生,甚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与民族、国家的进程紧密相关。凌叔华笔下对新式妻子形象的想象,充斥著的女性关怀,实际上是一种人道主义在家庭生活领域的体现,她希望借此解决作为“社会中人”的女性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和婚姻问题,但现实生活中这种对女性的关怀力量是有限的,只能化为乌托邦般的理想与憧憬。
因此,对于新式妻子形象的分析有利于揭示社会角色对女性生存样态和心态的规定作用和强制效果,展现其作为女性在社会性符号惯例的规训和无从符号化之间难以抉择的符号性困境,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五四”对于女性解放的神话,为进一步反思女性主体价值意识在近代中国充满政治化民族色彩的历史进程实相撕开一道口子。
参考文献:
[1]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2]李小江,朱虹.性别与中国·序言[M].北京:三联书店,1996.
[3]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4]黄人影.当代中国女作家论: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M].上海:上海光华书局,1985.
[5]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藩篱:文学中的男权意识的批判[M].北京:三联生活出版社,1995.
[6]乔以钢.多彩的旋律[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孙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