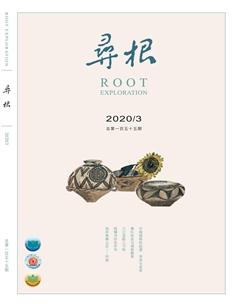明代士人疟病浅话
王涛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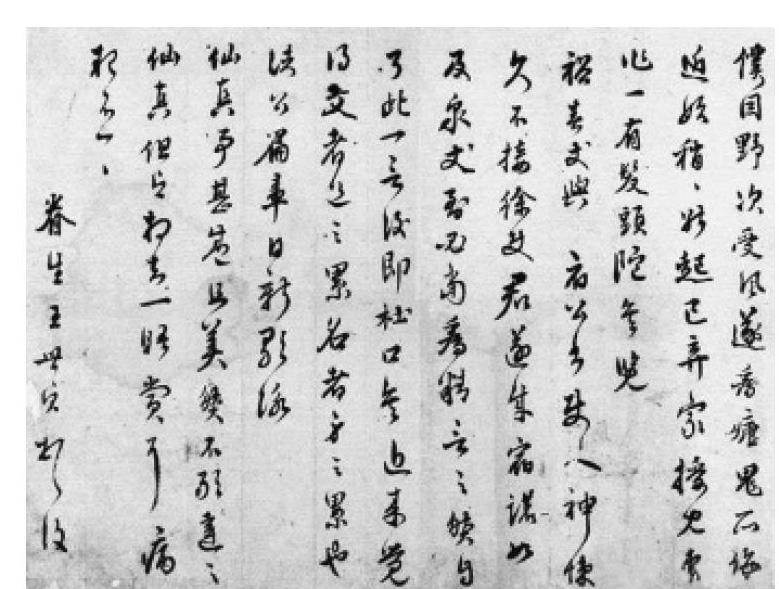
“疟”是中国的一种古老疾病,据记载,周武王姬发“克商之二年,即病疟”(张萱:《疑耀》卷二),虽不能确定属实,但先秦文献如《左传》对此病有所记录,出土简帛如上博简也有《景公疟》等篇,皆是旁证。可以说,“疟”贯穿数千年的华夏文明,人们对它曾十分熟悉。不过,随着现代医学的昌明发展,“疟”在日常生活中逐渐销声匿迹,而古病名“疟”也几乎被西医“疟疾”(malaria)完全替代。这一医疗化进程,促使今人对“疟”的历史变得相当疏离。庆幸的是,近年来人文学者从文学、史学等角度对其再次审视,从而唤醒这份独特的生命记忆。鉴于学界对“疟”与明代士人阶层的关系重视不足,本文将以此展开探讨。
诗人多病瘧
检索明代文献,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士人文集中有大量“疟”病内容,包含诗歌、书信、奏牍等多种文体,并涉及私人生活、仕宦、社交等广泛领域。初步推究,这一风潮形成于唐宋时期,杜甫、韩愈、王安石、秦观、陆游、杨万里等文豪皆有文章传世,其中韩愈诗作《谴疟鬼》可谓典范,明人的疟病书写就深受其影响。不少诗人更对韩诗多有效仿,如明初李昱的《遣疟鬼》,在开篇部分写道“汝本颛顼子,变化逃其形。胡不肖厥祖,骑龙升帝青”(《草阁诗集》卷一),而韩愈原作是“屑屑水帝魂,谢谢无余辉。如何不肖子,尚奋疟鬼威”(《韩愈全集校注》,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两相比较,从题目、结构到内容叙写都高度相似,不难窥其全豹。需要说明的是,韩愈型遣疟诗,很可能有着固定的格式,以应用于特定治疗仪式,因而后人虽难以突破,却无须创新。
对于“疟”病书写的蔚然兴起,元人早有深刻论述,如舒岳祥《山甫病中归峡,作此问之》有“诗人多病疟,强饭更何忧”(《阆风集》卷五)的诗句,而方回则认为“疾病呻吟,人之所必有也”,“足以见士君子之操焉”(《瀛奎律髓》卷四十四)。这种文体衍生的理论,被明代著名文人王世贞戏称为“文章九命”之后的第十命。他首先肯定古人“诗能穷人,究其质情,诚有合者”的观点,列出促进文学创作的“一贫困,二嫌忌,三玷缺,四偃蹇,五流窜,六刑辱,七夭折,八无终,九无后”等情形,并举例证明。然后,王氏将疟病归入第十命“恶疾”,他说:“吾于丙寅岁,以疮疡在床褥者逾半岁,几殆。殷都秀才过而戏曰:当加十命矣。盖谓恶疾也。因援笔志其人:伯牛病癞,长卿消渴,赵岐卧蓐七年,朱超道岁晚沉疴,玄晏善病至老,照邻恶疾不愈至投水死,李华以风痹终楚,杜台卿聋废,祖胡旦瞽废,少陵三年疟疾,一鬼不消。”(《艺苑卮言》卷八)
不得不说,这种文体自觉,促进了明代“疟”病书写的日益成熟。诗人既可凭疟书愤,如宋濂《次刘经历韵》:“空堂悲坐发孤咏,风刺欲斗《离骚》家。岂惟草堂诗止疟,如句亦可苏痿”(《萝山集》卷三),又能由疟而交际,如明宗室朱多《病中得余灵承书》“疟来君子病,书展故人心”,“山中如见月,疑策素车临”(《列朝诗集》闰集卷五),甚至借疟申明自身的理学立场,如邹元标致友人信中说:“弟自先秋感疟至今春,大剧,几与天游,幸稍愈。杜门谢事,始知了死生一路,此路一提,不知事者硬以为佛氏之学,不知《易》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吾夫子先道之矣。”(《愿学集》卷二)概言之,正是士人对疟病书写的热衷,文人病疟的印象才得以建构起来。
苦为疟所侵
明代丰富的“疟”病史料,是今人感受古人疟病体验,进而了解当时疾病、医疗的理想渠道。然而,必须明确的是,疟是一个复杂的疾病类型,人们关于它的认知也一直在演化。具体来说,明人长期奉行元末医家朱震亨的学说,通常认为疟有以下种类,即“风、暑、食、痰、老疟、疟母”,同时指出“疟又名疾者,其证不一。《素问》又有五脏疟、六腑疟”(《丹溪心法》卷二)。明中期以后,对疟病的认知趋于细微,分类竟有十多种,“疟有风疟、寒疟、热疟、湿疟、痰疟、食疟、劳疟、鬼疟、疫疟、瘴疟、疟、老疟”(《东医宝鉴》卷七)。至于临床症状,则有“一日一发者,受病一月;间日一发者,受病半年;三日一发者,受病一年;二日连发住一日者,气血俱病”等情状(《丹溪心法》卷二)。不难发现,疟病的上述特征,不仅范围超出现代医学意义上的疟疾,而且在辨证施治上颇具难度,因而病者时常备受煎熬,如方孝孺的《遣病》诗就有生动描绘,“冬疟春仍壮,身羸气觉虚。吻干食粥,眼眩废观书。行步儿童笑,形容老病如”。(《逊志斋集》卷二十四)
提倡诗文师法唐宋的归有光也曾患疟,在与友人沈敬甫的通信中,他直言医、巫治疗全无效果,“病良苦,一日忽自起,可知世间医、巫,妄也”。并于信中附诗两首,其一《题病疟,巫言鬼求食》揭露巫术疟鬼说的虚妄,“疟疠经旬太绎骚,凝冰焦火共煎熬。奴星方事驱穷鬼,那得余羹及尔曹”;其二《题病疟,医言似疟非疟》则批评庸医的无能,“似疟非疟语何迂,医理错误鬼啸呼。我能胜之当自瘥,禹乎卢乎终始乎”。(《震川先生集》别集卷七)而同为“唐宋派”的唐顺之,染疟时却只谈病后的无聊寂寞,他向友人田柜山倾诉说:“仆自送约之至姑苏,触暑积劳遂尔发疟,迄今伏枕未及能强起也。病归以来,生平交游一时雨散,空山独坐,每每念之。”(《荆川集》卷四)
面对疾病带来的狼狈衰困,也有人能够不断反省,从中探寻健康之道。晚明文坛巨擘王世贞作有《病疟作》诗,他先是直书疟病之凶险,“今年气候恶,疟鬼何太横。三家两家泣,十人九人病”,显然这是发生了具有传染性的疫疟。接着又写到救治资源的匮乏,“延医医伏枕,呼觋觋不竞”,看来当时难以寻觅到医、巫等治疗人员。在一番思索之后,王氏借疟鬼之口说,“公但时自爱,鬼当奉公命”,进而做出结论:“洒然梦初觉,摄念入清净。从此尼连河,尽作四禅境”(《弇州四部稿》续稿卷六),也就是他认为清心寡欲是养护身体的根本。
值得补充的是,疟所引起的恶症,虽一般难致人死命,却缠绵不休、不易根除。士人宦游,因此往往难以任事,遂以此休致归乡。如成化朝状元罗伦多次上书要求归养,他说:“自去年力疾赴命,日服医药暂得苟安。及秋之任,抵冒热邪,辄发痰疟,到任以后诸症侵加,头目昏晕,四肢痹软,形貌虽人,精华已竭,实難任事”。(《一峰文集》卷一)
文字可愈疾
疟,病因多端,不易痊治。明初御医戴思恭有论,“《内经》诸病,惟疟最详。语邪则风、寒、暑、湿四气,皆得留着而病疟”,又说“疟作之际禁勿治刺,恐伤胃气与其真也”(《推求师意》卷上)。这样,加上宗教及民间巫术的多重影响,明代社会存在着多样的疟病治疗方法和风俗。
对士大夫阶层而言,医治固然必要,但其效用却受到怀疑,方孝孺在给医生邵真斋的赠序中写道:“今年春余患疟,逾百日不止,肌体瘠惫,形容累然,兄弟宾客忧而谋诸人。忽之者以为不足治,行且自愈。危之者以为疟久为蛊,久且不可治。”(《逊志斋集》卷十四)这种“有病不治,常得中医”的做法并不鲜见,王世贞寄周公瑕的信中说:“仆自昨秋冬时感霜露小恙耳,而为乡里应酬所困,病羸削,至春三月而始知就医。六月病疟,三日良已。”(《弇州四部稿》续稿卷二百六)可以看到王氏虽患疾却数月不求医,此后病疟与此不无关联。另一方面,非医学疗法仍有较大的吸引力,如对于道符治疟,王世贞作有诗《吴生得神符,治余少子士骏疟,应手即愈,走笔赠之》:“眼见儿曹病骨苏,将言无鬼未全无。少陵总有花卿句,不及吴郎一字符。”(《弇州四部稿》)续稿卷二十四)该诗既因“字符”之力而认可疟鬼存在的可能性,进而又与另一种治疟法——“少陵总有花卿句”做比较,认为神符更胜一筹。
所谓“少陵总有花卿句”是指诗人杜甫所写的《戏作花卿歌》,之所以称其能够治疟,原因在于宋代笔记文献中广泛流传着一则轶事“杜诗愈疾”:传说杜甫告诉病疟者,诵读他的诗可以疗疟,特别是诗句“手提髑髅血模糊”(《宋诗话辑佚》卷上《古今诗话》)。据考“手提髑髅血模糊”的原文,即是《戏作花卿歌》中的“子章髑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一联,本是讲述安史之乱将军花敬定作战勇猛,斩杀唐朝叛将段子璋一事。随着杜诗在宋以后的经典化,杜诗治疟遂成为士人美谈,并转化为文化典故。如明人谢迁《再叠前韵酬雪湖》诗有句“少陵有诗驱疟鬼,公诗亦合传万人。病眸真与缄并启,笑口不知杯几巡”(《归田稿》卷六),更是借杜诗治疟之典夸赞友人。该诗附有小注云“来札有文字愈疾之语”,反映出有明士人沉醉于文字为表征的雅文化。他们相信,既然杜诗可以驱疟,文学乃至艺术创作活动未尝不可治病。明代藏书家邵宝曾称赞友人:“古闻诗句曾驱疟,石老今夸笔有神。莫道幽明非一理,若能惊鬼定惊人”(《容春堂集》续集卷五),好的诗文不仅能驱除疟鬼,还能影响人间。
这一文字愈疾的传统,确实在不断发展。如嘉靖朝工部尚书刘麟读邸报而疗疾,他在给吴行可信中说:“病榻阅邸报,荷观英主、名将命德讨罪一段新奇号令,宛然截疟良方也。”(《清惠集》卷十)而诗人皇甫则有诗题记“季弟示我以沙门之偈,伯兄广我以大道之篇”(《皇甫司勋集》卷六),以用于逐疟。此外,宋代有秦少游观《辋川图》而愈疟之说,明人何乔远在《高道记》也记载嘉靖时高作画数幅治好友人疟病之事,时人甚至称赞说“少陵有佳名,不若霞仙笔”(《名山藏》卷九十六),看来书画与文字相系,自然也能愈疾。
简言之,诗文、符、书画以及阅读等文化活动,在明代士人们看来皆能治疟愈疾。在此过程中,疟病由恶疾似乎变得风雅,而文学艺术的欣赏与创作更带有了治疗功能。这无疑是士人阶层对疾病的一种文化建构,也值得今人深入思考和专门探索。
作者单位:河南師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