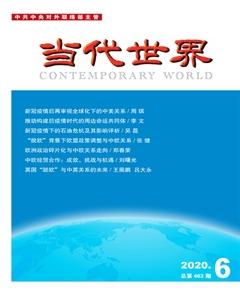欧洲政治碎片化与中欧关系走向
【关键词】欧洲政治;碎片化;中欧关系;民粹主义
【DOI】10.19422/j.cnki.ddsj.2020.06.005
过去10多年来,欧盟经历了一系列危机。即使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10年,欧盟依然危机不断,先是英国于2020年1月31日正式“脱欧”,其后是新冠肺炎疫情在欧洲扩散蔓延。在多重危机持续冲击下,欧洲政治生态发生深刻变化,传统主流政党式微,民粹政党尤其是右翼民粹政党纷纷崛起,欧洲政治碎片化日益明显。欧洲政党政治生态的变化造成欧盟成员国政局不稳、欧盟内部共识与团结缺失,继而在中国和欧洲需要加强合作的大背景下,给中欧关系带来诸多不确定性。
欧洲政治碎片化成为一种“新常态”
随着民粹政党尤其是右翼民粹政党的普遍崛起,碎片化已成为欧洲政治的一种“新常态”。这种碎片化反映在多个方面,一是欧盟各国议会内政党数量增加;二是主流政党与非主流政党力量对比发生逆转;三是政党力量从主流政党集中化转向主流政党和非主流政党扩散化;[1]四是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组合的流动性加速。
2019年5月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结果呈现的最大特征就是政治碎片化。这种碎片化既发生在“拥欧”阵营,也体现在“疑欧”集团。在“拥欧”阵营,欧洲人民党党团(EPP)和社会民主进步联盟党团(S&D)历史上首次失去了该组合在欧洲议会中的多数地位,而在此前欧洲自由民主者联盟党团(ALDE)基础之上新成立的复兴欧洲党团(RE)以及绿党/欧洲自由联盟党团(G-EFA)获得的选票增长可观,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前述两大传统中左、中右党团的选票损失,因而由这四个党团构成的欧洲议会“政治中间力量”得以维持,只是这个“政治中间力量”较以往更加碎片化。在“疑欧”集团,右翼“疑欧”政党的得票率和席位均有所增加,尤其是新成立的身份与民主党团(ID),这个右翼民粹党团取代了之前的民族和自由的欧洲党团(ENF),席位数从此前的36个增至73个,其成员包括意大利联盟党(Lega)、法国国民联盟(RN)和德国选择党(AfD)。因此,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产生的不只是一个“疑欧”势力进一步上升的议会,而且是政治力量也更为碎片化的议会。[2]

即使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10年,欧盟依然危机不断,先是英国于 2020年1月31日正式“脱欧”,其后是新冠肺炎疫情在欧洲扩散蔓延。图为5月18日,在德国柏林,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屏幕中)的联合视频记者会上发言,共同倡议欧盟设立总额高达5000亿欧元的恢复基金,以帮助经济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中恢复。
尽管长期以来欧盟议题日益“政治化”,但欧洲议会选举依然未摆脱“次级选举”的特征,因此欧盟层面政治碎片化只是成员国层面同一趋势的连锁反应。2017年欧洲大选年中荷兰、法国、德国三国的大选结果及其政党格局后续发展清晰地反映了这一点。
荷兰政党政治具有明显的碎片化特征。碎片化甚至被贴上“荷兰化”(Dutchification)的标签,这是因为荷兰高度比例化的政治体制为新政党和特定利益集团赢得议会代表权创造了有利条件。在2017年3月15日的荷兰大选中,首相吕特领导的自由民主党保住了作为建制派的领先优势。然而,由海尔特·维尔德斯领导的右翼民粹政党自由党所获议席数上升并成为最大反对党,而其他主流政党得票分散,因此自由民主党必须至少组成四党联盟,才能“凑够”组阁所需多数席位。这场议会选举后,荷兰国内政治力量更加分化,共有17个政党进入议会,近一半政党在议会里只有1—2个席位。不过,自由党未能延续崛起势头,在2019年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一度由于得票率过低而被排斥在新一届欧洲议会之外。英国“脱欧”后,欧洲议会议席需重新分配。73个英国议员席位中,46个将为未来的欧盟新成员保留,其余27个分配给14个欧盟国家“以反映人口变化”。荷兰自由党借此“捡回”了1个席位。需要指出的是,自由党的沉沦并不意味着荷兰政党政治碎片化的减弱,从该党的衰败中获利的是另一位反移民、反欧盟的民粹主义新星蒂埃里·鲍德特,他领导的民主论坛党(FvD)在此次欧洲议会选举中斩获了3个席位。在2019年3月举行的荷兰地方选举中,民主论坛党已经战胜自由民主党,成为参议院第一大党。
在2017年的法国总统选举中,人们一度担心飞出黑天鹅,所幸的是,最后“非左非右”的“前进” 运动(后更名为“共和国前进党”)领导人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总统第二轮选举中战胜了右翼民粹的“国民阵线”领导人玛丽娜·勒庞。不过,此次选举将法国政治碎片化的现象暴露无遗:首先,除传统共和党和社会党两个主流政党外,参加此次大选的还有10多个非主流政党;其次,首次打破中左、中右两大主流政党轮流坐庄的格局,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國建立59年来首次由两位非主流政党候选人占据总统对决的舞台;再次,第一轮大选出现“四强争霸”局面,前三名政党候选人的得票率相差仅为2%—3%,得票率在三个政党候选人之间分布相对较为平均。勒庞虽然在与马克龙对决中败北,但35%的支持率远好于其父亲在2002年时的表现(支持率18%)。[3]在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勒庞领导的“国民联盟”(2018年6月从国民阵线更名而来),虽然较2014年得票率有所下降,但仍然再次成为法国第一大党(得票率23.3%),领先马克龙领导的共和国前进党(得票率22.1%)。尽管目前距离法国下次总统大选还有两年时间,但民调数据显示,勒庞与马克龙在2022年的大选中几乎势均力敌。[4]
德国这个曾被认为由于历史原因而对右翼民粹主义具有免疫力的欧盟中心大国,也在2017年迎来了“民粹主义时刻”。在当年9月24日的联邦议会大选中,德国选择党取得了12.6%的得票率并首次进入联邦议会,从而使得联邦议会中的政党数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再次达到6个。德国两大全民党联盟党(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与社会民主党(社民党)的合计得票率从历史最高峰时的90%以上,缩水到本次选举中的53.4%。与此同时,2017年德国大选也是参选率上社会分化(Social Divide)显著缩小的一次,这主要得益于“德国选择党效应”。德国选择党动员了通常参选率最低的社会问题区域如德国东部地区选民的投票。在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德国选择党相较于2014年实现了得票率的稳步上升,增幅近4%,而两大党联盟党与社民党遭遇了滑铁卢,得票率分别下降了6.5%和11.4%。[5]

英国“脱欧”后欧洲议会议席需重新分配,73个英国议员席位中,46个为未来的欧盟新成员保留,其余27个分配给14个欧盟国家“以反映人口变化”。图为2020年1月31日晚,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大楼前的英国国旗降下。
政治碎片化并非西欧仅有的现象,在中东欧也同样可以观察到。比如在2017年10月的捷克议会众议院选举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史无前例的结果。安德烈·巴比什领导的“ANO2011”成为大赢家,打破了自1993年捷克独立以来中左翼的捷克社会民主党和中右翼的公民民主党轮流坐庄的政党格局;历史上首次有9个政党进入捷克议会,而且反体制政党在众议院占有多数席位,与传统主流政党分歧严重。[6]
欧洲政治碎片化的影响
右翼民粹政党壮大导致欧洲政治碎片化,继而对欧盟各成员国的国内政治以及欧盟的行动力产生深远影响。[7]其中,有三个影响尤为值得关注。
第一,欧洲政治更为右倾。主流政党的右倾导致右翼民粹主张主流化。经过2019年选举,欧洲议会中的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又有所增长,在英国“脱欧”、欧洲议会再平衡后,由于主流政党阵营席位的净损失更大,这种右倾更为明显。[8]而且,右翼民粹政党一旦在成员国层面执政,如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PiS)和匈牙利的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Fidesz),它们在其他欧盟机构,如欧洲理事会、部长理事会以及欧盟委员会中的话语权也势必会增强。
同时,欧盟各国主流政党纷纷效仿右翼民粹政党的言论与政策主张,尤其是2015年的难民危机导致了整个欧洲大陆民族主义以及民粹主义言论和政策主张的主流化与正常化。主流政党越来越不加掩饰地将移民定义为对国家身份和安全的威胁,并对移民采取限制性措施。特别是中东欧国家,对移民、难民的排斥表现得最为强烈,采取的措施也更为强硬。对此,有学者提出欧洲存在“欧尔班化”的危险,担心匈牙利总理维克多·欧尔班在其国内推行的“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政策会向其他欧盟国家“外溢”,原因是欧尔班凭此政策在匈牙利实现了连选连任:在2018年4月8日的匈牙利新一届国会选举中,匈牙利执政联盟(青民盟和基民党)获得压倒性胜利,这是欧尔班自2010年以来的第三次连任。
右翼民粹主张被主流政党容忍或吸收,奥地利表现得更为明显。2017年10月的国民议会选举后,中右翼的人民党主席塞巴斯蒂安·库尔茨12月接受右翼民粹的奥地利自由党为联合执政伙伴。就任总理后,库尔茨将人民党改造成了一个介于中右政党和右翼民粹运动之间的政治力量,这是右翼民粹主义正常化的一个范例。[9]2019年5月,时任奥地利副总理、自由党主席海因茨-克里斯蒂安·施特拉赫因丑闻辞职,库尔茨也因此被国民议会罢免,奥地利不得不于2019年9月提前举行国民议会选举。选后经过为期数周的谈判,人民党和绿党于2020年1月7日达成了一份主题为“保护气候与边界”的联合执政协议。在观察家看来,这份联合执政协议包含了许多自由党核心人物、前内政部长赫尔伯特·基克尔提出的主张,这也意味着,一向倡导人权和自由价值观的绿党接受了他们先前强烈反对的政策主张。除了强调他们在联合执政谈判中坚持了应对气候危机的主张并得到贯彻外,绿党为自己参政使用的合法化论据还包括“别无选择论”(There is no alternative, TINA),意思是要取代此前的人民党与自由党联盟,绿党只能参与执政并作出妥协。[10]
第二,欧盟内各个层级政府的组阁更为困难,组成的政府也更加脆弱。在国家层面,德国、荷兰、瑞典等国均经历了组阁僵局。2017年9月24日大选后,德国经历了历史上最长的171天的组阁过程,联盟党和社民党才最终于2018年3月14日组成了新政府。此前,由于社民党不愿意再次委身于大联合政府,联盟党不得不寻求与自民党和绿党组成黑黄绿联合政府(又称“牙买加联盟”),但是这一跨政党阵营的试探性会谈最终夭折。2017年3月15日荷兰大选后,吕特经历了近7个月(创纪录的208天)的尝试才在10月中下旬组成了在议会仅拥有一席多数的四党联合政府。在瑞典2018年9月9日的国会大选中,原少数派联合执政的中左翼两党社民党和绿党的得票率分别只有28.26%和4.41%,兩党经过4个多月的组阁拉锯战后才得以继续执政。
在地方层面,多个欧洲国家时而出现组阁困境,不得不组成少数派政府,其中以德国图林根州的组阁僵局最为显著。德国最大党基民盟的联邦理事会基于“不可调和性决议”颁布合作禁令,不仅拒绝与右翼民粹的德国选择党合作,还反对与带有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烙印的左翼党合作。这一决议在联邦层面的施行并无问题,但是到了德国东部,这一“划界策略”就将基民盟的地方支部推入两难境地。由于在德国东部的部分州议会中,左翼党和德国选择党的得票率相加超过50%,因此,如果基民盟两者都不支持,就无法在那里组成多数政府,这导致东部地区的基民盟地方支部出现了不同的分离力量,有些主张与左翼党合作,有些则倾向于与德国选择党合流。例如,在经历州政府组阁“闹剧”后,图林根州陷入严重的执政危机。最终,基民盟不得不以“容忍”的方式,接受左翼党领导下的少数派过渡政府(左翼党、社民党和绿党),并扮演“建设性反对派”角色。各方都同意在2021年4月重新举行州议会选举。这四个党达成上述妥协方案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不至于使议会的决策依赖于德国选择党的表决票。图林根州的执政危机虽然由此告一段落,但是基民盟内部有关定向问题的争论才刚刚开始。曾经一度被视为默克尔接班人的基民盟主席安妮格雷特·克兰普-卡伦鲍尔由于对此次事件处理不当,丧失党内权威,黯然宣布不会出任联盟党的总理候选人并辞去基民盟党主席职务,这无疑给德国政局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
第三,欧盟的集体行动力受到制约,欧盟及其成员国将采取更具保护主义色彩的政策。为应对来自右翼民粹政党的挑战,欧盟各国主流政党及其政府不得不投入很多精力和资源,而且由于在与右翼民粹政党打交道的策略上存在分歧,主流政党及其政府内部往往陷入公开争吵中,这不仅削弱了它们的行动力以及在民众中的信任度,而且使得它们没有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入到欧盟事务中。由于欧洲民粹主义与疑欧主义紧密相伴,哪怕右翼民粹政党还未强大到足以掌握政权,它们也能影响各国国内的政治力量对比和民众对欧盟的态度。因此,在高度政治化的议题(如应对难民危机)上,欧盟层面达成妥协的余地变小了。
不过,也必须看到,如今右翼民粹政党不再打“反欧牌”,不再要求本国“脱欧”,而是要求推行“另一种欧洲”,这既是英国冗长而又反复的“脱欧”程序以及英国在“脱欧”谈判中并未捞到多少好处所起的震慑作用使然,更是右翼民粹政党调整其对欧策略的结果。它们意图缓和极端立场,以扩大选民基础。由此,欧盟内的分歧将围绕“更多欧洲”还是“更少欧洲”(more or less Europe)展开,欧盟想要在有争议的议题领域推进一体化会变得更加困难,其要求成员国进一步让渡主权的做法更会遭到主张“民族国家的欧洲”力量的坚决抵制。[11]不仅如此,欧盟还需要应对来自匈牙利和波兰对其法治与人权等基本原则的挑战。欧盟虽然可以用剥夺理事会表决权或削减欧盟资金援助等惩罚手段威胁匈牙利和波兰,但真正落实的可能性并不大,因此双方的拉锯战还很漫长,这将在中长期削弱欧盟内部的凝聚力。
无论是右翼民粹政党掌权,还是主流政党的右倾,都将导致右翼民粹主张的主流化与正常化,这也意味着欧盟及其成员国会采取更具民粹主义特征的内外政策。由此,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会在欧盟内更有市场,这种思潮和力量会渗透到贸易、投资、工业政策、公共采购和货币政策等各个领域。欧盟及其成员国近年来先后引入或收紧外商投资审查框架以及加强保护型工业战略等,都是这种保护主义政策主张抬头的表现。民粹主义的另一个特点是倾向于将所有现存问题的责任归咎于他人,这使得欧盟及其成员国内部很难就必要的改革展开诚实而又具建设性的讨论。[12]
总之,由于欧盟及其成员国政党政治的碎片化,使其在内部寻求共识和达成妥协进一步复杂化,欧盟更难采取一致和连贯的对外行动。同时,欧盟及其成员国会极力渲染国内政治,越发使外交服务于内政,即沉溺于“非外交”的外交。这对欧盟对外行动能力的直接与间接影响不可小觑。[13]
中欧合作不确定性上升
在国际格局深度调整、大国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下,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的核心关切是如何确定和调整自身定位,并由此提出要提高欧盟的战略自主性,打造“主权欧洲”,实现“经济自主”“产业自主”“数字自主”等一系列愿景。欧洲政治碎片化进一步扩大了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对自身实力和行动力下降的担忧,也进一步增强了其“强身健体”需求的迫切性,这也反映在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想要打造一届“地缘政治委员会”的雄心上。目前,新一届欧盟领导层已经成立,但其对华政策尚待观察。无论如何,考虑到欧洲政治的碎片化及其影响,未来的中欧关系总体上将呈现出双边合作需求与竞争同步增强的态势。
一方面,中欧的相互需要在增加。在中美发生贸易争端背景下,欧洲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性上升,与此同时,面对美国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政策,欧洲对中国的借重与合作需求也在上升。特别是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形势,中欧双方在维护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等方面有着一致立場和共同诉求,在维护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落实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等全球治理问题上,欧盟也需要与中国合作。
另一方面,由于自身实力下降,欧盟对新兴力量尤其是中国崛起的恐惧和防范心理显著增强。这尤其体现在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于2019年3月发布的《欧中关系战略展望》报告中。虽然该报告称中国在诸多政策领域是与欧盟有着共同目标的天然合作伙伴,是欧盟进行利益平衡的谈判伙伴,但同时指出,在追求技术领导地位上中国是欧盟的经济竞争对手。此外,对欧盟而言,中国是推动替代型治理模式的“体制对手”。“体制对手”是此前从未有过的提法,它重点强调的是欧盟“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与欧盟认知的、由国家主导的中国经济模式之间的对立。基于上述认知,欧盟在保护主义趋势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对所谓战略性价值链的保护,收紧了海外投资并购政策,并对所谓中国“不公平的贸易实践”提出批评。
欧洲政治碎片化将使中欧双边关系复杂性、不确定性增加。对此,可以着力从以下几个方面引导未来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一是必须把扩大和深化合作作为根本途径。随着中欧双方合作进一步深入,矛盾与摩擦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要避免采取保护主义措施。迄今,《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的实施以及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的打造,有力推动了中欧关系的发展。当前,中欧双方应进一步构建新时期合作的战略规划,以增强战略互信、夯实利益融合为目标,以双方共同关切的数字化、绿色化等领域合作为重点,通过双方战略对接、优势互补,为全球树立合作共赢的典范。
二是必须坚持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系。欧盟需与中国相向而行,而不是一面要求中方打开大门,一面受内部右翼民粹主义和政治碎片化影响,收紧甚至关闭自己的大门,以国家安全为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向世界释放错误信号。为此,双方应积极推进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在这一过程中,欧方不应漫天要价,也不应通过公开指责破坏谈判进程,而应以合作共赢的心态努力使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为未来早日启动中欧自由贸易谈判奠定基础。
三是必须推动中欧合作向更高层次发展。高科技领域(包括医药技术领域)的合作不仅可以促进中欧之间的经济融合,而且也能增强中欧之间的政治互信。目前,全球价值链、供应链相互交融,“经济脱钩”“技术脱钩”的观点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不现实的。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应对进一步表明人类是一个患难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只有携手同行,才能有效应对病毒这类非传统安全的威胁。
四是必須在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中行稳致远。双方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加强友好合作,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来应对当今世界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和大挑战。欧洲国家不应将自身发展中的问题,包括内部不团结的问题(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各自为政)归咎到他国身上,而是应首先做好自身功课;不应在对华政策上犹豫、焦虑甚至追随美国炒作体制竞争,沉迷于搞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竞争,而是应彰显自身相对于美国的独立性自主性,从互利合作出发,保持对华政策的独立性、稳定性和积极性,使中欧双边关系在不确定性增加的大背景下更具韧性。
(作者系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欧盟研究所
所长,教授)
(责任编辑:甘冲)
[1] 吴正龙:《法国大选凸显欧洲政党碎片化》,https://opinion.huanqiu.com/article/9CaKrnK2NZT。
[2] Cas Mudde, “The 2019 EU Elections: Moving the Center,”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30, No.4, October 2019, pp.20-34.
[3] 同[1]。
[4] “France—2022 presidential election voting intention,” https://www.politico.eu/europe-poll-of-polls/france/.
[5] “Europawahl am 26. Mai 2019,” http://www.wahlrecht.de/news/2019/europawahl-2019.html.
[6] 姜琍:《从议会大选和总统选举看捷克内政外交走向》,载《当代世界》,2018年第3期,第74-78页。
[7] 郑春荣:《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影响》,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99-108页。
[8] Ma?a de La Baume and Francesco Piccinelli, “Brexit means rightward shift for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european-parliament-reshuffle-details-after-brexit/.
[9] Karin Liebhart, “The Normalization of Right-Wing Populist Discourses and Politics in Austria,” in Stefanie W?hl, Elisabeth Springler, Martin Pachel and Bernhard Zeilinger, eds., The State of the European Union. Fault Lines in European Integration, Wiesbaden: Springer VS, 2019, pp. 79-101.
[10] Ruth Wodak, “The Normalization of Far-Right Populism in Europe,” https://rantt.com/the-normalization-of-far-right-populism-in-europe.
[11] 伍慧萍:《2019 年欧洲议会选举以来西欧民粹政党的新变化及其影响》,载《当代世界》,2020年第2期,第40-47页。
[12] Marcel Fratzscher, “Populism, Protectionism and Paralysis,” Intereconomics, Vol.55, No.1, 2020, pp.1-2.
[13] David Cadier, “How Populism Spills Over into Foreign Policy,” https://carnegieeurope.eu/strategiceurope/78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