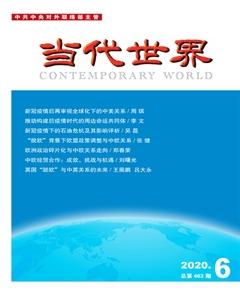新冠疫情后再审视全球化下的中美关系
周琪

【关键词】全球化;逆全球化;美国对华战略;中美关系;新冠肺炎疫情
【DOI】10.19422/j.cnki.ddsj.2020.06.001
一个普遍的预测是,在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基本结束之后,世界将变得与之前大不相同。这看来将是确定无疑的。实际上,在此次疫情之前,世界已经在发生一些显著的变化,有迹象表明,那些引起变化的因素在疫情之后将会进一步放大,从而使一个自特朗普总统上任后国际上一直在关注的问题——全球化将走向何处,成为一个突出的关注点。今后全球化将会有怎样的命运?曾极大受益于全球化的中国将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国际发展环境?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中美关系将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些将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全球化过程中获益最大的是发展中国家
在过去的约30年,人们公认全球化是一个世界发展的主线和趋势。全球化被认为是一个客观过程,表现为在全球层面上信息、金融、经济、贸易与交换,以及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融合与统一的过程。[1]全球化会给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人们带来怎样的影响?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对全球化所做的最初评估中,把重点放在全球化对全球经济造成的破坏上。他曾认为世界上最不富裕的国家是全球化的主要受害者,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85%,但他們的收入却仅占世界总收入的39%。受害最大的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其人均收入仅为美国的2.5%。这些国家在全球化面前别无选择,要么参与其中,成为全球化体系的一部分,要么被排除在外,成为全球化体系的弃儿。[2]
自冷战结束以来,全球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89年不仅是东欧剧变的一年,也是日本遭受其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金融危机和苏联经济严重衰退的一年。美国心目中的两个经济强国在经济上都不再能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而美国作为全球最富有超级大国的地位似乎变得不可动摇。到1992年,美国的GDP占世界的26%,并控制着大约一半的有效专利,它完全不必担心其他国家的竞争,因而它以推进全球化的姿态来处理国际经济问题。根据一位著名的俄罗斯经济学家的看法,美国在1994年帮助墨西哥走出债务危机,避免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对亚洲廉价进口商品实行任何限制,2000年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欢迎中国加入WTO,并允许中国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其中。[3]
事实上,全球化以一个与斯蒂格利茨最初的关注点完全不同的特点在发展,即它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1991年至2015年,全球有超过10亿人口摆脱了贫困,其中亚洲人口占了75%。[4]2009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出口国;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位于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经济体,并成为最大的工业生产国;2014年,中国按购买力平价(PPP)衡量的人均 GDP(以2011 年不变价国际元计算)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从这些数据来看,可以说,亚洲,特别是中国,是全球化及体现全球化的国际经济体系的最大受益者。美国没有忽略亚洲经济的快速增长,在自2001年开始的10年反恐战争的后期,美国已经意识到全球的政治、经济中心正在向亚太地区转移,亚太地区是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因而从2010年起,美国开始把其全球战略的重心转到亚太地区,其经济方面的意图就是参与亚太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5]
然而,也正是在这一全球化的过程中,美国的相对实力开始下降。到2018年,按购买力平价衡量,美国在全球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下降到15.1%,其贸易逆差从1991年的310亿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6220亿美元。亚洲国家总体来说成为最大的外汇储备持有方[中国内地(大陆)与港台地区、韩国、马来西亚以及泰国合计拥有超过4.6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6]
时至今日,斯蒂格利茨承认,他大大低估了全球化对发达国家带来的打击。不仅美国中西部铁锈地带的工厂工人,而且在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国家中,大批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的工薪阶层也成为全球化的受损者。这些人在过去的30年中,生活状况的改善一直停滞不前。当其他地区的死亡率在下降时,由于遭受到社会衰落和经济不平等,美国中年男性白人因酗酒、自杀和吸毒死亡率在上升。那些原本可以依靠自己买房、送子女上大学,最后安稳退休的美国人,现在做不到了。他们为此而感到愤怒。[7]
美国对全球化态度的转变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主导了消除贸易壁垒和建立全球性和区域性贸易体系的进程,在塑造全球贸易体系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推动达成了许多构成全球化框架的多边和双边协定。多年来,美国一直认为,这些贸易协定将为美国带来更强劲的经济增长,并为美国工人和企业带来更大的机遇,但是,美国对此失望了。在特朗普总统上任之后,美国开始进行反省。2017年3月,即特朗普上任后仅2个月,美国政府就发布了《2017年总统贸易政策日程》。这份文件认为,自2000年,即中国加入WTO前一年以来,美国的各项经济指标都在持续恶化:GDP增速放缓、就业增长缓慢、制造业就业人口大幅度减少、贸易逆差加大。具体来说,2000年1月,美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为1728.4万,这一数字与上世纪80年代初的大致持平,但是到2017年1月6日,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仅为1234.1万,失业人数接近500万;2000年,美国实际家庭收入中位数(按2015年美元计算)为57790美元,而到2015年下降到了56516美元,低于16年之前。在中国加入WTO之前的16年期间,即1984年到2000年,美国工业生产增长了近71%,而在2000年至2016年期间,美国工业生产增长不到9%。[8]更不用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成倍增长了。该文件由此得出一个结论:目前的全球贸易体系对中国是有利的,但是从2000年起,它并没有给美国带来同样的好处。这些分析使特朗普政府更加相信,美国在全球市场上因不公平贸易而处于劣势,全球化让美国受损。
特朗普是全球化坚定的反对者。他曾引用美国智库经济政策研究所的研究报告,宣称“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订后,美国几乎损失了近三分之一的制造业工作岗位,而自中国加入WTO之后,美国损失了5万家工厂”。 [9]此外,按照该智库的说法,自2001年至2013年,对华贸易逆差使美国损失了320万个工作岗位,其中240万个来自于制造业。[10]
在此背景下,美国的国内舆论也开始发生变化。以往一般来说,在美国持不同政治观点的经济学家都认为,贸易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工具,而经济发展可以促进社会富裕和政治自由。贸易对美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也得到普遍的承认。但是2017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对自由贸易越来越持怀疑态度,71%的美国人认为促进“有利的”(而不是自由的)贸易政策“非常重要”,而且共和党选民对自由贸易协定的看法比民主党选民更为消极。[11]2015年和2017年印第安纳州立大学的两名研究者发现,2000—2010年,制造业失业率的大约13.4%是由贸易造成的,但他们的研究也得出另一个结论:最近几年制造业将近88%的工作岗位的丧失是由于生产力增长所致。[12]然而這后一个结论——生产力的增长是美国就业岗位减少的关键因素,却很少受到人们的关注。
全球化确实带来这样一个现象,即发达国家的总收入提高了,但是工作岗位却流失到了外国。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是,全球资本、资源和劳动力的全球配置。受资本趋利性的驱使,发达国家的公司趋向于在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投资建厂,这为投资对象国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但同时为美国创造的就业岗位却十分有限。以苹果公司为例,根据该公司2012年的几份研究报告,这家在全球市值排名第一的美国公司,在美国直接雇用了4.7万人,“创造或支持了”51.4万个美国工作岗位,包括它在加州总部参与软件设计和在零售网络工作的将近50万人、用来运送其产品的联邦快递公司(FedEx)和联合包裹速递服务公司(United Parcel Service Inc.,即UPS公司)的雇员,以及康宁公司为iPad和iPhone生产玻璃面板的雇员。[13]但同时,商业内幕网(Business Insider)、彭博新闻社(Bloomberg)等公司的其他分析报告又揭示出,在苹果产品的竞争下,其他在美国的相关公司被“摧毁了”总数约490570个就业岗位。这些报告还发现,相比之下,苹果公司通过发展iPhone、iPad和其他产品的供应商网络在海外创造了大约70万个工作岗位。[14]这样的发展趋势对哪类国家更为有利,显而易见。
一些案例表明,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和铁锈地带经济的衰落,有时达到令人瞠目的程度。曾经是美国三大汽车公司所在地和美国制造业强大经济实力标志的底特律市,于2013年7月向美国联邦破产法院提出破产保护申请,成为美国制造业空心化后果的一个典型事例。这座城市随着美国汽车制造业的衰落而衰落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又给了底特律致命打击,三大汽车公司裁员14万人,城市人口从1950年繁盛时期的180万减少到2013年的70万,仅在2000—2010年10年间就减少了25万。由于纳税基础缩小,政府财政收入减少,2008年以来市政府不得不靠借债来填补财政赤字,其债务总额达到180亿—200亿美元;城市公共服务几乎陷于瘫痪,失业率高达18.2%,相当于当时全美平均水平的2倍多;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市区治安恶化,抢劫、盗窃、劫车、枪击事件频繁发生。底特律市政府除了削减开支、发行城市建设债券外,还需要用出售机场和公园来抵债。[15]直到2018年,还未能看到底特律经济全面复苏的迹象。这一年底特律的人均实际收入在美国53个最大都市区的核心城市中排名倒数第一,仅为14523美元,约为旧金山55366美元的四分之一。[16]
技术创新所推动的全球市场确实没有使发达国家的某些人口受益。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两位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彭斯(Michael Spence)和桑戴尔·赫施瓦约(Sandile Hlatshwayo)于2011年3月初发表了一份题为《美国经济结构的演变与就业挑战》的研究报告。他们的结论是,美国的就业问题是特别有效的全球市场造成的。许多美国人不是从全球市场中获益,尤其是那些拥有中等技能工作的人,他们成为海外低工资成本的受害者。较不发达的国家开始生产比美国价格更低、质量更高的产品,虽然这会带来消费品更加便宜的正面效果,但也同时会带来分配方面的负面效果。在国家内部,不平等可能会加剧;在国家之间,新兴经济体的成功可能使富裕的经济体付出代价。[17]
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戴维·奥托(David Autor)指出了类似的问题。他认为,总体来说,贸易和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显然大于坏处,但也带来很大的损失,这些损失会落到一部分劳动者身上。工作向海外流失使美国劳动市场发生了两极化,即较高级的工作(需要受过高水平教育的专业、技术和管理职业)和较低级的工作(不需要高水平教育的饮食和服务行业中的工作)机会都在增加,但中等工作的机会却在减少,包括中等技术人员、白领职员、管理人员,销售职业,以及中等技能、蓝领工人、手艺和技工职业。[18]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及两年后的欧债危机,更加剧了这一长期存在的问题。[19]
自由贸易、资本自由流动、人口迁徙固然能提升世界各国的总体福利,但福利增长是不均匀分布的,它们同时会损害一些国家和一国国内部分群体的利益。由此不难理解,为何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但30年后它们之中的一些却成为全球化的强烈反对者,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则成为全球化的积极拥护者。
反全球化的根源来自发达国家内部
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可以提高全球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经济和收入的增长,这一点可以通过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贸易量和经济总量同时快速增长得到印证。但是,自由贸易对于美国经济发展来说存在两个最重要的缺陷。第一,自由贸易可能导致某些群体失业和收入下降。当资源在全球配置、分工在全球展开时,市场竞争压力会比仅在本国内大得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企业纷纷外迁或外包,这样发达国家的劳动者就必须与待遇比他们低得多的发展中国家劳动者进行竞争。来自其他国家的市场竞争加速了美国产业的空心化,尤其是白人蓝领集中的制造业出现了严重的衰退。更重要的是,由于受冲击的劳动者大多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而且转换行业或迁居的成本往往很高,结果很可能导致受冲击地区失业率升高和居民收入减少,而且教育程度更低、收入更少的工人受到的冲击更大。[20]
第二,贸易具有重要的收入分配效应,这一点往往被其经济效应所掩盖。自由贸易在理论上能提高全球总产出和总体福利,但并不能保证所有的人都能从中受益或同等程度地受益,而是会导致一部分人获益,另一部分人受损。由于流动资本重新部署了世界经济中的职业和生产,贸易强化了国际竞争压力,全球金融体系又限制了国家的福利和再分配能力,全球化加剧了国家间和国家内部的经济不平等。[21]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特朗普胜选后强调了这一问题,他指出,近年来,推动全球增长的、基于规则的国际贸易和投资体系所带来的好处,“并没有层层惠及所有人口。随着企业为应对竞争残酷的全球市场而进行外包,并尽可能提高效率,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失去了工作”。[22]
此外,随着贸易越来越自由,其经济效益会日益减弱,而分配效应会日趋增强。研究表明,在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全球化过程中,最大的受益者是发展中国家的中上阶层和发达国家的高收入群体,而最大的受损者却是发达国家的中低收入群体。至于发展中国家的低收入群体,他们依然无法摆脱极端贫困。[23]全球化加剧了美国国内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由于经济全球化,美国跨国公司高管、技术精英可以不受国界的限制,在全球范围内竞争工作岗位,但是那些中、低阶层劳动者只能在地方上进行竞争,而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已经使地方丧失了大量就业机会。结果导致白人蓝领生活水平下降,更难以进入中产阶级。这进一步带来了美国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平等。美国白人蓝领阶层和中产阶级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相对受损者。对金融市场过度放宽管制引发的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更是严重打击了美国的中产阶级。美国劳工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4月,受疫情影响,美国非农就业岗位减少了2050万个,失业率飙升至14.7%,为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的最高值。[24]其中处境最艰难的仍是这些中低收入人群。
特朗普旗帜鲜明地反对全球化,激烈地攻击自由贸易和外来移民。他声称:美国的“政客们一直在不遗余力地追求全球化……全球化让金融界的精英们赚得金银满盆,但是它带给数千万美国工人的却只是贫穷和心痛”。[25]特朗普的当选对于那些自认为深受自由贸易之害的中下层白人来说是一场胜利,他们认为自己是被高科技发展造就的后工业经济和以金融业为基础的经济所抛弃的人,因而他们成为自由贸易最激烈的反对者和特朗普逆全球化政策及“美國优先”政策最坚定的支持者。
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曾带给很多人乐观情绪,就像欧盟的发展曾经带来的乐观情绪一样,他们以为国家主权和民族情绪都会逐渐弱化,身份认同将从民族国家转移到超国家或全球层面上来。但现实情况却远非如此,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原则、英国“脱欧”、欧洲各国极右势力的兴起,都证明深度的全球化反而会激发民粹主义情绪。
许多研究者都意识到,解决全球化带给发达国家的负面效应,需要政府采取积极的国内社会经济政策,例如带有倾斜性的税收政策、健全的社会保障、对失业者的职业再培训等等。但这些都是现在的美国政府所不关心的,它一心想在国际上以打压竞争对手的方式来为美国争得利益。实现美国经济状况的好转,确实可以使美国人整体受益,但并不能解决美国国内现有的收入分配不均和社会不平等的问题,包括中低收入群体所遭遇的困境。在这方面,美国一贯看不起西欧国家以效率来换取福利国家和收入平等的做法,因而做得远不及后者。而且,正如思想史家、历史学家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所指出的,福利国家要求非常高的税率来维持公共服务,而“美国的政客不能说服选民承担福利国家的费用”。[26]

疫情期间,美国股市5次触发熔断机制。美国许多政客担心,中国可能通过有效抗击疫情显示出比西方更强的国家治理能力。图为2020年4月20日拍摄的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外景和华尔街路牌。
因此,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国际上出现的逆全球化潮流主要不是源于全球治理体系的自身效率问题,全球治理的优化解决不了各国国内出现的问题。以美国而论,一方面有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发展促成的国家经济持续增长,另一方面存在贫富差别拉大、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生活状况持续恶化、教育成本提高、国家认同危机等问题。只要这种社会状况得不到改善,美国国内就会存在反全球化的力量,[27]普通民众在一些政客的煽动下也就会把积怨撒在中国身上。这种情绪自然会反映到美国的选举结果及当选总统的对外政策上。
中美之间可能出现的经济和科技脱钩
同共和党人相比,美国的民主党人对全球化持有较积极的态度。基于这种态度,他们更愿意在全球性问题上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合作,特别是在应对气候变化、核不扩散、流行性传染病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上;由于他们更赞同自由贸易,在国际贸易问题上也不像特朗普政府那样剑拔弩张。[28]然而,虽然民主党人反感特朗普总统的国内外政策,但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受意识形态的驱使,他们中的很多人持有同特朗普政府相近的立场,即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战略挑战,这突出地体现在人权问题、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上。因此,无论在今年即将到来的大选中结果如何,中美关系都不会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在疫情中,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抗击疫情的努力和成绩不断进行抹黑,除了特朗普为了达到其竞选目的、掩盖自己处理疫情危机不力的事实之外,还由于这些国家的许多政客担心,中国可能通过有效抗击疫情显示出比西方更强的国家治理能力,从而凸显中国政治体制的优越性。西方的记者不断就此问题追问福山,而福山的回答大概代表了西方学者中较温和的观点:他承认中国模式在此次疫情中有突出表现,而且“中国模式是非西方模式中最成功的一个,它是国家干预和准资本主义的混合体”。但是在他看来,国家制度与抗击疫情的成果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决定各国表现的是国家能力和卫生制度。中国这样的政权更有能力应对紧急情况,但这并不能证明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因为:一来,西方民主制下的国家也有抗疫成功的,例如德国和韩国;二来,“中国有权力集中的悠久历史,这一传统在日、韩等一些邻国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但是,这种模式无法被亚洲以外的国家所复制,例如拉美国家。[29]
由于疫情在一个时期延误了产业链的供应,对于一些发达国家来说,从中国撤资或将生产转移到中国之外的必要性更具有了说服力。一些国家已经公开这样做了,例如美国政府以优惠政策要求本国企业迁回国内,日本政府建议企业考虑从中国迁走部分工厂,以降低供应链过于单一的风险。许多国内外经济学家都已对此类举动做出评论,指出重建美国的传统工业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美国劳动力成本过高;在机械化和自动化的条件下,即使恢复传统工业也创造不了多少就业岗位;把产业链移出中国,会增添在其他国家重建的成本,可能还会面临较差的投资环境;最重要的是可能会丧失广大的中国市场。由于这些原因,全面经济脱钩很难实现。
在这个问题上,福山认为,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之前,全球化已经达到了其最大限度。这次疫情促使许多西方国家考虑抑制全球化。不过在许多公司打算调整散布在世界各地的供应链以便优化资源时,如果认为可以通过在整个经济领域将产业调回本国来实现自给自足,无疑是荒谬的。尽管逆全球化极有可能出现,但可能改变的只是全球化的程度。[30]换言之,全球化仍然是一个大趋势,尽管全球化的程度可能因一些发达国家逆全球化的举动而有所降低。也有人提出,有可能出现所谓的“多元全球化”。
讲到“多元全球化”,就涉及了经济脱钩的问题。尽管全面的经济脱钩目前看来不大可能,但科技脱钩的问题却日益凸显出来。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现在不仅担心企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且更担心能否确保国家安全。也就是说,在经济模型中加入了“安全”这一变量,这会使其计算结果发生偏差。如今,科技领域里的竞争已被视为战略竞争,对于美国来说还是一场争夺世界领导权的竞争。中国促进军民融合技术发展的理念令美国感到不安,认为这会降低自身的竞争优势;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更令美国担心,认为这是一项大规模的全球计划,将会给予中国制定全球技术标准的机会。美国对中国高科技的发展做出的回应是竭尽全力压制中国的发展速度,所采取的措施包括:对中国对美国核心技术的投资进行更严格的限制,严密审查中美之间的学术交流,实施有针对性的关税以降低中国在关键部门的竞争力,加大对美国认定的参与经济间谍活动的中国公民的起诉,并在反情报行动中投入更多的资源,[31]以及最近禁止美国公司对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出口关键产品,以对中国进行科技封锁。从现有的美国和欧洲的政策趋向来看,疫情之后,这些措施很可能会加大。
国际上更多的人担心中美之间日益激烈的技术竞争可能导致技术领域的分离,最后导致欧洲、北美、南美和澳大利亚主要采用美国的技术和标准,亚洲、非洲和中东则采用中国的技术和标准。许多人在议论,中美之间在5G标准方面的全球竞争可能是这种脱钩的早期迹象。中美在诸如5G方面的创新竞争将冒分离技术领域的风险,它们将通过引入5G网络来影响下一代移动标准、频谱分配以及在关键市场和地区的部署。如果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美国竭力限制中国的市场,将可能导致形成两个不可兼容的5G生态系统:一个系统可能由美国领导,并由硅谷开发的技术支持;而另一个系统可能由中国领导,并由其强大的数字平台公司提供支持。[32]在这种场景下,中国的市场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国家的技术建设资源有限;美国公司将主要在竞争激烈的发达国家市场开展业务。[33]从现有的迹象来看,这种情况在未来并非是不可想象的。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必须为疫情之后中美关系将进入一個更困难的阶段而做好思想和政策准备。由于美国国内现存的社会、经济问题,除非美国真正尝到苦果,否则美国政府在逆全球化的道路上不会退却,把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国家安全战略还会继续下去。为此,中国应采取相应措施,妥善应对中美之间可能出现的一定程度的经济脱钩和最大限度的科技脱钩。
(作者系同济大学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院长)
(责任编辑:孟洪宇)
[1] Sadykova Raikhana, Myrzabekov Moldakhmetb, Myrzabekova Ryskeldyc, Moldakhmetkyzy Aluad, “The Interaction of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 in the Modern World,”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74017385_The_Interaction_of_Globalization_and_Culture_in_the_Modern_World.
[2] Paul Hockenos,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Revisited,” Feb. 5, 2018, https://www.ips-journal.eu/book-reviews/article/show/globalization-and-its-discontents-revisited-2708/; Joseph E.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02).
[3] Vladislav Inozemtsev, “Fukuyama's Post-Historical Model Got Politics Wrong and Economics Right,” June 21, 2019,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fukuyamas-post-historical-model-got-politics-wrong-and-economics-right-63617.
[4] 全球化是增加还是减少贫困人口?这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且没有定论的问题。2003年马丁·拉瓦雷(Martin Ravallion)在其被广泛引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由于缺乏数据和模糊不清等问题,在全球化对贫穷和不平等造成的影响上存在争议。[参见Martin Ravallion, “The Debate on Globalization, Poverty, and Inequality: Why Measurement Matter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9, No. 4 (July 2003), pp.739-753.]认为存在争议的代表作是2015年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弗朗索瓦·布吉尼翁(Fran?ois Bourguignon)的著作《不平等的全球化》(Fran?ois Bourguignon, The Globalization of Inequality, translated by Thomas Scott-Railt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作者认为在全球化的世界中,要把导致国内或国际不平等的因素区分开来变得更加困难,他借助各种资料来源审视了每一种趋势,并研究了这些不平等是如何相互平衡或相互加强的。但最近的相关文章和研究都采用了科学化的量化测量方法,例如一个研究团队从世界治理指标中提取治理指标,运用因子分析法构建总体指标,建立了9个数学模型,并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估算,结果证实所有治理指标都对减贫有利,全球化、竞争力和发展支出也有助于减贫。可见M.S. Hassan, S. Bukhari & N. Arshed, “Competitiveness, Governance and Globalization: What Matter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 2019, pp.1-28, https://doi.org/10.1007/s10668-019-00355-y。
[16] Pete Saunders, “Detroit, Five Years After Bankruptcy,” July 19, 2018, https://www.forbes.com/sites/petesaunders1/2018/07/19/detroit-five-years-after-bankruptcy/#5866cb00cfeb.
[17] Michael Spence and Sandile Hlatshwayo, “The Evolving Structure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and the Employment Challenge,” March 2011, http://www.google.com.hk/url?sa=t&rct=j&q=The+Evolving+Structure+of+the+American+Economy+and+the+Employment+Challenge&source=web&cd=2&ved=0CDEQFjAB&url=http%3A%2F%2Fwww.cfr.org%2Fcontent%2Fpublications%2Fattachments%2FCGS_WorkingPaper13_USEconomy.pdf&ei=bwVAUIbuC-ueiAfog4HgCA&usg=AFQjCNEA21h_rd6T0YgrWcT3K-Ku7SAw0g&cad=rjt.
[18] Thomas B. Edsall, “Is This the End of Market Democracy?”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9, 2012. http://campaignstops.blogs.nytimes.com/.
[19] Francis Fukuyama, “US against the World? Trumps America and the New Global Order,” The Financial Times, November 11, 2016, https://www.ft.com/content/6a43cf54-a75d-11e6-8b69-02899e8bd9d1.
[20] David H. Autor, David Dorn, and Gordon H. Hanson, “The China Syndrome: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MIT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No. 12-12, May 3, 2012, https://ssrn.com/abstract=2050144.
[21] 【英】戴維·赫尔德和安东尼·麦克格鲁著,陈志刚译:《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2页。
[22] 同[19]。
[23] Christoph Lakner and Branko Milanovic, “Global Income Distribution: From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to the Great Recession,”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015, p.14, https://www.gc.cuny.edu/CUNY_GC/media/LISCenter/brankoData/wber_final.pdf.
[24] 吴乐珺:《美国失业率创新高》,载《人民日报》,2020年5月13日。
[25] “Full Transcript: Donald Trump's Jobs Plan Speech,” Politico, June 28, 2016, http://www.politico.com/story/2016/06/full-transcript-trump-job-plan-speech-224891.
[26] 《福山曾预言历史的终结,然而全球化并未一统天下》,2020年1月2日, http://culture.ifeng.com/c/7stsHSntqXs。
[27] 这种力量早在1992年世贸组织西雅图会议期间发生的震惊世界的美国反全球化示威时就显示了出来。
[28]不无巧合的是,倾向于赞同全球化的民主党人在一系列与中国有关的问题上,立场都不像共和党人那样强硬。自2020年3月以来,美国哈里斯民调中心(Harris Poll)在全美展开的“新冠追踪”(COVID-19 Tracker)系列调查显示,在一系列有关中国问题的表态上,民主党人都更加温和。其中,在因冠状病毒扩散“问责中国”的问题上,72%的共和党人表示支持,而民主党人中仅有42%的人表示支持;在特朗普政府是否应对华采取更强硬的政策上,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中的支持者分别为66%和38%;在对华贸易政策上,90%的共和党人支持与中国进行贸易对抗,而民主党中的支持者约为53%;在“中国病毒”问题上,有80%的共和党人在不同程度上支持“中国病毒”之说,而民主党人中的支持者仅占30%。总的来看,在大多数与中国有关的问题上,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之间对中国的敌意程度都有30%左右、最高达到50%的差距。哈里斯民调中心的原始民调数据可参见:https://theharrispoll.com/the-harris-poll-covid19-tracker/。
[29] 《福山再发声: 我承认新自由主义已死, 但中国模式难以复制》,2020年4月9日,https://zhuanlan.zhihu.com/p/135271012.
[30] 同[29]。
[31] Ryan Hass and Zach Balin,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January 10, 2019, pp.3-4,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us-china-relations-in-the-age-of-artificial-intelligence/.
[32] Paul Triolo, Kevin Allison, and Clarise Brown, “Eurasia Group White Paper: The Geopolitics of 5G,” Eurasia Group, November 15, 2018, p.4, https://www.eurasiagroup.net/siteFiles/Media/files/1811-14%205G%20special%20report%20public(1).pdf.
[33] Ryan Hass and Zach Balin,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January 10, 2019, p.5,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us-china-relations-in-the-age-of-artificial-intellig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