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最能说明作家其人
卞毓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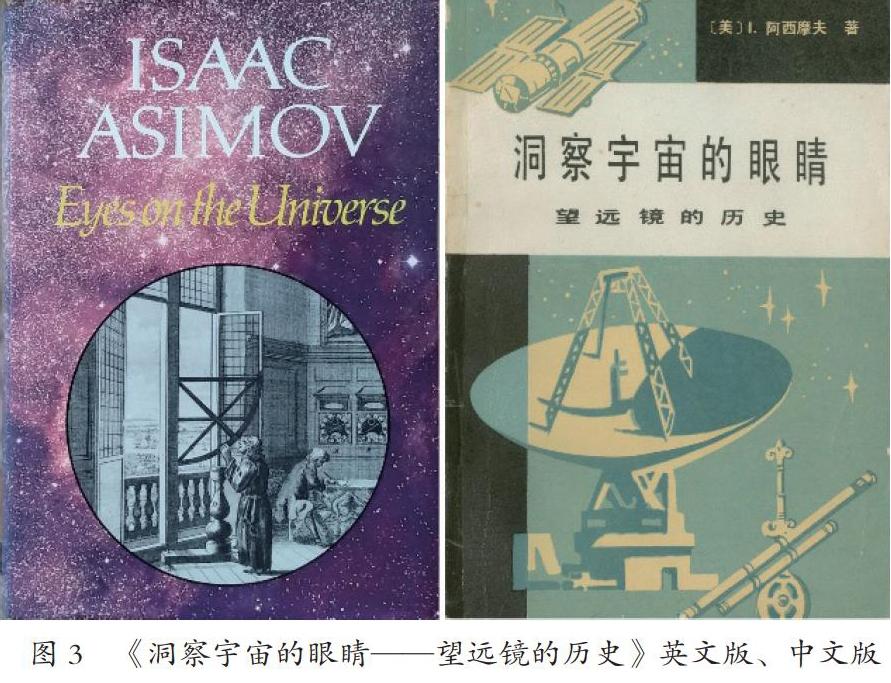
2020年,适值美国科普泰斗兼科幻巨擘艾萨克·阿西莫夫百年诞辰。40多年来,我发表的关于阿西莫夫的文章已不下40篇,它们或视角不同,或主题各异,或深浅有别,或详略不一。今又逢读书日,正好借书缅怀已辞世28载的阿西莫夫。
“比他们想知道的还要多”
大约半个世纪以前,阿西莫夫就说过:“作家自己写的作品最能说明其人。倘若有人坚持要我谈谈我自己的情况,那么他们可以读一下我的几本书:《作品第100号》《早年的阿西莫夫》以及《黄金时代以前》,在那些书里,我告诉他们的东西比他们想知道的还要多得多。”
《作品第100号》是阿西莫夫的第100本书,1969年出版。该书节选他此前99本书中的代表性片段,精心编排,酌加说明而成。书末按时间先后列出这100本书的序号、书名、出版者和出版年份。那么,这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作品呢?
所有的图书可归为非虚构的和虚构的两个大类,在这两个方面阿西莫夫都是一流的高手。他的头100本书中,非虚构类的有72种,包括科学读物57种(科学总论6种,数学5种,天文学12种,地球科学1种,化学和生物化学13种,物理学6种,生物学6种,科学随笔8集),人文类读物14种(历史9种,文学1种,谈《圣经》的4种),再加上《作品第100号》本身;虚构类的有28种,包括长篇科幻小说16部,探案1部,科幻小小说与短篇科幻故事8集,以及由他主编的科幻故事3集。
这100种书中,包括首创“机器人学三定律”的《我,机器人》,著名的《基地》科幻系列小说之前三部,日后数次增订的传世之作《聪明人的科学指南》《阿西莫夫氏科技传记百科全书》等。1967年春,阿西莫夫曾对美国《新闻周刊》的记者哈维·安罗森说:“从1939年到1949年,我认为自己是个科幻小说作家;从1949年到1958年,我仍然自认为是个生物化学家;从1958年到1965年,我认为自己是个科普作家。现在我不知道该把自己看成什么,我的兴趣是历史。”
阿西莫夫的头100种书,出版时间跨度是整20年:第一个5年出版13种,第二个5年19种,第三个5年19种,第四个5年出了29种。更有甚者,这样的速度在日后竟被不断超越。1985年2月,我收到了阿西莫夫签名寄赠的《作品第300号》(1984),他在此书“序言”中写道: “我的第一个100本书,花费了我237个月;我的第二个100本书,花费了我113个月;我的第三个100本书花费了我69个月……”
1988年8月,我到他家做客时,他告诉我,刚收到其新出版的第394本书。
阿西莫夫一生著述多达470种,其中非虚构类作品有科学类读物205种,人文类读物47种,自传3卷,以及其他14种;虚构类作品有长篇科幻38部,科幻小小说与短篇科幻故事33集,主编科幻故事118集,以及探案故事等作品12部。有一位热心的图书管理员说,阿西莫夫写的书几乎涵盖了杜威十进分类法的每一个类别。诚然,没有一个作家比他在更广阔的领域写下更多的书。
阿西莫夫的工作量大得惊人。但是他说:“其实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我的工作量是一点一点增加的。这种情况就好像古希腊传说中的克罗托那的米洛,那位成功的举重运动员。据说他先举起一头刚出生的小牛犊,然后在小牛长大的过程中,他每天举它,直到他能够举起一头完全长大的公牛。”
如今,最有助于了解阿西莫夫其人的,我认为是《作品第100号》《作品第200号》《作品第300号》,以及他的3卷自传《记忆犹新》《欢乐依旧》和《人生舞台——阿西莫夫自传》,后文对此还会详谈。至于阿西莫夫何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那还得从他的童年谈起。
阅读是写作的上游
阿西莫夫1920年1月2日出生于俄罗斯,双亲是犹太人。1923年他随父母移居美国,定居纽约的布鲁克林区。他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化学,1939年19岁时毕业,两年后取得硕士学位。此后,他在美国军队服役4年,1948年又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49年起阿西莫夫在波士顿大学医学院任教,升至副教授。1958年离校成为职业作家,1979年波士顿大学医学院授予他教授头衔,1992年4月6日在纽约病逝。
阿西莫夫的父亲是个小店主,他无暇亦无能引导子女优选发展方向。环境使阿西莫夫从小练就了一种独特的本领:保持适度的压力使自己迅速地汲取知识,但又不觉得压力的存在。他在上学之前,就请年龄稍大的孩子教他读、写英语字母,自己学会了识字。上小学后,他常常会因其他孩子识字有困难而感到惊讶。
上学后,阿西莫夫一个星期就看完了学校发的课本。父亲给他办了一张图书馆借书卡,因为无人引导,所以他什么书都读。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竟然一字一句地记住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全部。“你任意背诵一节,我都能告诉你可以在哪里找到。”他晚年在自传中如是说。
有一次阿西莫夫病了,让母亲替他到图书馆借书。他答应母亲,她借什么他就看什么。结果母亲带回一本关于托马斯·爱迪生的书,这几乎就成了阿西莫夫走进科技世界的入门阶梯。
长大一些之后,小说把阿西莫夫引向了非虚构类读物。读了大仲马的《三剑客》,自然会对法国历史感兴趣。阿西莫夫读了房龙谈论历史的书,觉得还不满足,于是又将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迪吕伊写的世界史读了好几遍。年龄再大一些,他发现了狄更斯,竟然将《匹克威克外传》看了26遍!
阿西莫夫认为,自己早年真正的教育是从公共图书馆获得的。图书馆是一座敞开着通往奇迹和成就的大门,他为自己聪明地敲开那扇门,充分地利用它而深感自豪。晚年的阿西莫夫不斷从报纸上看到图书馆基金被一再削减,不由得哀叹:“我只能认为这扇大门正在关闭,美国社会又找到了一条毁灭自己的途径。”
阿西莫夫自认是典型的“书虫”。他猜想,有些人必定会好奇:究竟是什么缘故居然会使一个年轻人如此可悲地不断读书,而毫不在乎生命的光辉在不经意地流逝?阿西莫夫则认为:人生快乐,生命便是辉煌的,思考和想象的相互影响远胜过肌肉和神经之间的作用。他觉得,“阅读一本好书,迷失在它趣味盎然的语言和引人入胜的思想之中,实在是一种难以形容的极大乐趣。” 令人难以置信的大量综合性阅读,将阿西莫夫的兴趣引向了20个不同的方向,并且所有这些兴趣都终生保留下来了。阅读是写作的上游,海量的阅读为他日后著书论述科学、历史、文学、神话……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阿西莫夫成名后,介绍其作品的文章汗牛充栋,而涉及其阅读的却甚罕见。偶尔也会见到一些实例,如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开始酝酿研制大型空间望远镜(后以“哈勃”冠名),遂有出版社邀请阿西莫夫撰写一部关于天文望远镜史的科普读物。阿西莫夫说自己对此并不熟悉,编辑就给他送来一大堆有关望远镜的资料。此后他写成的《洞察宇宙的眼睛——望远镜的历史》非常出色。我有幸(与黄群合作)执译此书,天文界同人对此颇多褒扬。
阿西莫夫读书的方式,不可能成为一种范式,但这对他的成功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他的阅读史无可复制,但是富于启迪,值得研究。
年近不惑的双重转折
1989年春天,在波士顿大学建校150周年庆祝活动中,69岁的阿西莫夫给一大批学生做报告。在互动环节有学生问:“阿西莫夫博士,我们听到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报告。既然你是波士顿大学的教师,为什么不定期给我们授课?”
阿西莫夫答道:“40年前,我是这个学院的教授,讲了9年课,总共大约有100门次,它们是学生们听到的最好的课,但是,”他停顿了两秒钟,以便确认学生们都在听——“我被解聘了。”
听众席上传来一片叹息声。可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当年阿西莫夫取得博士学位后,在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系得到一个教职,1951年晋升为生物化学助理教授。几年以后,他被公认为学院里最出色的授课者,1955年被提升为副教授。
那时,阿西莫夫已因他的机器人故事、《基地》系列以及杰出的短篇科幻《日暮》(一译《黄昏》)等作品而出了名。非虚构类作品方面,他在20世纪50年代也开启了一道新的泄洪闸,接连出了8本青少年科普读物:《生命的化合物》(生物化学)、《种族与人民》(遗传学)、《原子内幕》(核物理学)、《宇宙之砖》(化学)、《区区一亿万》(科学随笔)、《碳的世界》和《氮的世界》(均为有机化学),以及《我们赖以生存的时钟》(天文学)。
在医学院期间,晚上、周末和节假日,阿西莫夫都在写科幻小说,但他从不在上班时间写,他觉得那样做不道德。然而,这还是引起了校方的不满。到了1958年,他的年薪在整个大学的教授层中是最低的。
1956年,阿西莫夫接受了一小笔政府拨给的经费,要他写一本关于血液的书。当时的医学院院长基弗拒绝把钱给他。阿西莫夫指出:“这一笔是指定给我的,如果不让我拿到,我要告到华盛顿去。”基弗把钱给阿西莫夫了,暗中却在准备解雇他。
1957年12月18日,基弗把阿西莫夫召到办公室摊牌:“我们这所学院供养不起一位科学作家。你的任职到1958年6月30日结束。”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基弗助推阿西莫夫走上了职业作家之路。几乎与此同时,阿西莫夫写作的方向也发生了一个重大转折。
早期的科普作品,使阿西莫夫发现自己其实很擅长此道,而不只是将其用作科幻小说情节的陪衬;加之1957年下半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又使他深感美国公众的一般科学素养已落后于卫星上天所标志的当代科技水平,自己有责任努力使这种差距尽快地缩小。于是,他毅然收缩早已得心应手的科幻创作,而全神贯注于撰写科普读物了。直到15年后,1972年才重新出现他的大部头科幻新著,那就是有名的《诸神》。
写作经验和教学生涯使阿西莫夫认清,自己决不会成为第一流的科学家,但有可能成为第一流的作家。“作出选择当然很容易:我决定做自己能够干得最好的事情。”1958年他在离开波士顿大学时对上司说,自己已经是世界上最好的科学作家之一,但他的打算是成为最好的,而不仅是“之一”。他不太在乎自己能不能成为正教授,而富有戏剧性的是,鉴于他的巨大贡献和声望——
“1979年,波士顿大学医学院——我本人完全没有任何暗示——主动将我提升到正教授的行列。经历了24年,我的头衔中终于不必再带上那个令人生厌的‘副字了。”“现在,我是生物化学教授。”这是他第二卷自传《欢乐依旧》的结尾。
说说那些“大部头”
阿西莫夫著作中有不少篇幅不大的儿童读物,但也有好些体量非凡的“大部头”。这里介绍一些非虚构类作品,暂且不谈科幻小说。
阿西莫夫的科学读物,部头最大的有3种:《阿西莫夫氏最新科学指南》《阿西莫夫氏科技传记百科全书》和《阿西莫夫氏科学和发现年表》,皆为近百万言的巨著。
《阿西莫夫氏最新科学指南》的原型,是1960年出版的《聪明人的科学指南》,1965年修订为《聪明人的科学新指南》,1972年再修订为《阿西莫夫氏科学指南》,1984年再度修订而成《阿西莫夫氏最新科学指南》。我国科学出版社曾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分成 4个分册出版中译本。1991年科学普及出版社推出名为《最新科学指南》的中本版,1999年江苏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同一译本,书名《阿西莫夫最新科學指南》。全书从“科学是什么”谈起,对现代自然科学做了流畅细腻的全景式描绘,并在这幅瑰玮的科学导游图中,融入许多精妙的见解。例如,作者鼓励人们不必对科学望而生畏:“要能满意地欣赏一门科学的进展,并不需要对科学有完满的了解。没有人认为,要欣赏莎士比亚的戏剧自己就必须能写一部伟大的作品:要欣赏贝多芬的交响曲,自己就必须能作一部同等的乐曲。同样地,要欣赏或享受科学的成果,也不一定非得具备科学创造的能力。”关键则在于科学家与非科学家之间要多多沟通。
此书的成功出乎始料,于是编辑又纵容阿西莫夫再写一本“大部头的书”。这最终导致了两大卷的《阿西莫夫氏圣经指南》:第一卷谈“旧约”,1968年出版;第二卷谈“新约”,1969年出版。接着,1970年又出版了两大卷的《阿西莫夫莎士比亚指南》,第一卷为“希腊、罗马和意大利戏剧”,第二卷是“英国戏剧”。
《阿西莫夫氏科技传记百科全书》的中文版书名为《古今科技名人辞典》。它1965年问世时,是阿西莫夫已出版的部头最大的一本书。经1972年、1982年先后两次增订,最终包含了1510位古今科学家的传略。阿西莫夫在“序言”中写道:许多人似乎“想当然地把这本书当作集体努力的结果,即由我带领了一队数目可观的人马进行研究和编写而成”,事实上却是“我一个人做了所有必须进行的研究和写作,而没有任何外来的帮助,就连打字工作都是我自己做的”,“我写这本书是出于一种无与伦比的爱好。所以,我非常珍爱它”。书中的传记主要以出生时间先后为序排列并编号,在每一篇传记中插入一些供相互参见的其他传记序号。这样就可诱导读者在查阅某一科学家时去查阅与之有关的其他人,然后又进一步引导他去追踪更多的其他人。“如果这样认真地一一查阅,他们会发现无论从哪里开始,都可以把本书通读一遍。” 这样做有着深刻的内涵,因为所有的科学知识实质上全部是复杂地缠结在一起的。这部百科全书之妙则在于“不管从哪里抽出一个线头,整个线团就会随之抽出”。
这部巨著也很成功。阿西莫夫有意仿其体例,适时再写一部《阿西莫夫氏战争与战役传记百科全书》,可惜终未如愿。
《阿西莫夫氏科学和发现年表》约700页,于1989年出版。两年后,体例与之相同而体量略小的《阿西莫夫氏世界年表》问世。但它们尚无中译本。
阿西莫夫一些文学类的“大部头”:《阿西莫夫注唐璜》(1972)、《阿西莫夫注失乐园》(1974)、《阿西莫夫注格列佛游记》(1980)、《阿西莫夫注吉尔伯特和沙利文》(1988)等,篇幅亦皆可观,此处不再赘述。
一首小诗和三卷自传
阿西莫夫晚年健康状况迅速下降。1988年夏我们晤面时,他体格和精力都还不错。1990年1月11日,他即感觉体虚而入院检查,发现心血管状况很糟糕,而且影响到肺和肾。阿西莫夫面对病重并不惊慌,但极不希望自己像一只足球那样,由一位医生传给另一位医生,接着又传给下一位医生;而所有这些医生则不断地给他做各种复杂的检查,以期延续他的生命。他希望宁静地死去。
死神尚未来临。1990年1月26日,从医院回家的那天,其夫人珍妮特·阿西莫夫建议他再写一部更富有思想性的自传,而不是像前两部那样按时间先后罗列各种事件。阿西莫夫很赞同,随即干了起来。不久,他再次入院,写作时断时续,他说这仿佛是在和死亡赛跑。最后,他在1990年5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
“现在可以交稿了。从开始动笔至今一共125天。在这点时间里写下235 000个(英文)单词,并不是许多人都能做到的,况且此间我还得干别的事情。”
阿西莫夫很希望这部自传不久就能问世,可惜未能如愿。他去世后,珍妮特承担起手稿的编辑工作。1994年年初,此书正式出版,全书560余页,前有阿西莫夫本人的“序言”,末有珍妮特写的“后记”,还有作者亲自编定的“阿西莫夫书目”。
《人生舞台》比前两卷自传更富有思想、感情、哲理。它突破时间先后的限制,把作者认为有意义的话题和思考,作为一个个专题来写。全书共有166个专题,将作者本人的家庭、童年、学校、成长、恋爱、婚姻、疾病、挫折、成就、至爱亲朋、竞争对手,乃至他对写作、信仰、道德、友谊、战争、生死等种种问题的见解娓娓道来。每一个专题不过几千字,短的只有两三千字,行文非常流畅,可读性极强。你读完一篇,往往会情不自禁地心想:嗯,有意思,值得回味。
早先,阿西莫夫的第一卷自传于1979年出版,第二卷则于翌年问世。出版社曾同他一起商定书名,阿西莫夫拟用《我的回忆》,出版社则希望书名能听起来更富有诗意。一位编辑甚至提议找一首意境朦胧的小诗,引用诗句作为书名。阿西莫夫遂提供了这样一首诗——
In memory yet green, in joy still felt,
The scenes of life rise sharply into view.
We triumph, Times disasters are undealt,
And while all else is old, the world is new.
他用首句“In memory yet green”作为第一卷自传的书名,中译《记忆犹新》;第二句“In joy still felt”则成了第二卷的书名,中译《欢乐依旧》。晚年述及往事,阿西莫夫还提到他曾考虑接着用“The scenes of life”作为第三卷自传的书名,中译或可作《人生幕幕》。不过,实际上其最后一卷自传的书名是《I. Asimov》。
出版社的编辑找不到这首诗的出处,他们还想知道这位诗人的名字。结果阿西莫夫道出了真情:“这是我自己写的。”前两卷自传都印上了这首小诗,且故弄玄虚,伪托作者“佚名”。我对此一直蒙在鼓里,直至读到《I. Asimov》中的有关章节才恍然大悟。
1994年4月,北京师范大学的吴岩老师在美国为我买到还散发着油墨香的这部新书。书名《I. Asimov》很朴实,就是《艾萨克·阿西莫夫》。但有趣的是,在书末附录“阿西莫夫书目”中,列出的书名却成了《I,Asimov》:下圆点成了逗号。依我看来,这倒也是一个不错的书名,它可以译成《我,阿西莫夫》,恰与那部享誉全球的《我,機器人》相映成趣。
2002年夏天,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这卷自传的中译本《人生舞台——阿西莫夫自传》,译者是20年前与我共同翻译《洞察宇宙的眼睛》的老友黄群。这一次,我虽然不再是译者,却成了中文版的责任编辑,依然十分愉快。
热爱写作胜过一切
阿西莫夫热爱写作胜过一切。他曾说:“我不是写作的时候才写作。在吃饭、睡觉、洗漱的时间里,我的脑子一直在工作。有时候,我会听见脑子里闪过的对话片段,或整段文章。通常,它们都与我正在写的或者将要写的东西有关。我知道自己的大脑正在无意识地进行工作。这就是我为什么随时都可以动笔写东西的原因。”
阿西莫夫回想,一个家庭里作为丈夫和父亲的人,除了坐在房间里写东西别的什么也不想干,是很让人烦心的。他第一次婚姻失败,部分原因正在于此。他说:“有一次,我正在写第100本书,我的第一任妻子格特鲁德抱怨说:‘你这样究竟有什么好处?等到你快要死的时候,你就会明白自己在生活中错过了什么。你错过了所有原本可以用你挣的钱享受到的美好事物,那些由于你头脑疯狂,只知道写越来越多的书而被你忽略的美好的东西。到那时,100本书对你又有什么用?我说:‘我死的时候,你俯下身来聆听我的临终遗言。你会听到我说,太糟糕了!只写了100本书!”
有一次,电视台记者巴巴拉·沃尔特斯采访阿西莫夫,问他是否有时候也会想做点别的什么,阿西莫夫回答:“不。”她又问:“如果医生说你只能活6个月了,你会做什么呢?”回答是:“我会加快打字速度。”
最惟妙惟肖地体现阿西莫夫酷爱写作的话语,我认为是他答法国《解放》杂志之问“您为什么写作”:“我写作的原因,如同呼吸一样;因为如果不这样做,我就会死去。”
还有他行将告别人生之际在《奇幻和科幻杂志》上发表的那篇“告别词”:“我这一生为《奇幻和科幻杂志》写了399篇文章……但我发现自己写不了第400篇了,这不禁令我毛骨悚然。”“我一直梦想着自己能在工作中死去,脸埋在键盘上,鼻子夹在打字键中,但事实却不能如人所愿。”
難怪有人说,阿西莫夫“一生中只想做一件事,并且极为出色地学会了它:他教会自己写作,并用自己的写作使全世界的读者深受教益、共享欢乐”。诚哉斯言!
中文版的新纪录
我有一些文章受读者青睐多年,如第一篇论述阿西莫夫科幻创作历程的长文《阿西莫夫和他的科学幻想小说》(纳入黄伊主编《论科学幻想小说》,1981年)、近万字的《在阿西莫夫家做客》(《科普创作》1990年第5期)、约2万字的《科普巨匠艾萨克·阿西莫夫》(《科普研究》2001年第5期)、档案式的长文《阿西莫夫著作在中国》(《科普研究》2012年第2期)等。
40多年来,我始终乐而不疲地注视着每一种新推出的中文版阿西莫夫著作,迄今这在中国大陆已达115种之多。须知,这并非百篇文章,而是百余本书;亦非一书多译,而是百余种不同的书!全世界无论已故还是健在的所有外国作家,其著作被译成中文的品种最多者,既非莎士比亚、巴尔扎克这样的经典作家,亦非儒勒·凡尔纳、阿加莎·克里斯蒂这样的类型小说家,而是艾萨克·阿西莫夫。
第一个中文版的阿西莫夫著作,是1973年面世的《碳的世界——有机化学漫谈》,译者郁新是笔名,实为林自新和甘子玉两位学长。首功难忘,它至今仍有许多值得重提的地方。首先,此系“文革”期间所为,译者冒着被扣上“崇洋媚外”“洋奴哲学”之类大帽子的风险。其次,这本仅8万多字的小书以非常浅显的语言讲述颇有深度的有机化学,秩序井然地介绍了五花八门的有机化合物(汽油、酒、醋、维生素、糖类、香料、肥皂、油漆、塑料……)与人类的关系,使中国读者看到了科普居然可以如此精彩。再次,它的一些经典段落,依然可作为科普写作的范本。最后,《碳的世界》也使许许多多中国人记住了阿西莫夫这个名字。
在前已提及的《阿西莫夫著作在中国》一文中,我逐一简述了当时已有的106种中文版阿西莫夫作品的概况。此文有如一幅阿西莫夫氏“大观园”导游图,游人尽可按图索骥。此后,又有9种中文版新品首发,它们是(方括号中以时间先后为序给出中文版编号): [107]《永恒的终结》和[108]《神们自己》(即《诸神》)皆系长篇科幻小说,2014年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推出;[109]《诺比的微型反重力装置》、[110]《诺比的超空间逃亡》、[111]《诺比与外星动物园》、[112] 《诺比与扭曲时空的项链》、[113] 《诺比与平行宇宙的钥匙》、[114]《诺比、龙和意识星云》和[115]《诺比与错乱的时间线》,皆系儿童科幻小说,2018年由接力出版社推出。“诺比”系列是阿西莫夫伉俪合著的系列作品,珍妮特署名在前,自1983年始陆续问世。1988年我到他们家做客时,“诺比”已出版6种,承蒙主人签名惠赠。中文版书名与英文原名相去甚远,国情不一,只要对方认同,倒也未尝不可。
尾声
阿西莫夫走了。遵从他的意愿,遗体火化,未举行葬礼。他留下的是关注社会公众的精神,传播科学的热情,脚踏实地的处世作风,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还有他那470本书。
2003年12月14日,我再次访问珍妮特,当时她77岁,身体康健,还在写书,待人依然热情。我送给她一批这些年回望、纪念阿西莫夫的文章,她赠我一册亲笔签名的《美好的一生》(It's Been a Good Life)。此书概述艾萨克的一生,由珍妮特基于大量第一手材料编纂而成。“It's been a good life”乃是艾萨克对自己一生的评语,正好借用做书名。我很希望日后有机会再次见到珍妮特,这位年长我17岁的优秀作家。然而,这已经永远不可能了。2019年2月,珍妮特·阿西莫夫与世长辞,享年93岁。
10年前,《文汇报》邀我撰文纪念阿西莫夫90诞辰。我在文末写道:“阿西莫夫用他那真诚的心和神奇的笔写了一辈子,使五湖四海的读者深深获益。愿中华大地上也能涌现出一批像阿西莫夫那样优秀的科学作家——他们也有一颗同样真诚的心,还有一支也许更为神奇的笔!”如今我仍做如是思。
作者系天文学家、科普作家、科技出版专家、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原副理事长、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终身荣誉理事长、上海市天文学会原副理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