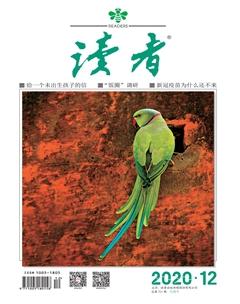柏林爱乐的孤独夜晚
李斐然

没有观众的柏林爱乐演出现场
音乐还在
柏林的每个夜晚,音乐都在。它有时候出现在教堂,有时候出现在街头,但最好的音乐从晚上8点开始,它出现在柏林爱乐音乐厅。这是每天晚上音乐会的开场时间,也是一天当中最热闹的时段。整个大厅回荡着提示广播,工作人员急匆匆地帮迟来的观众找座位,走在楼梯上都会有人提醒:“快点,音乐会就要开始了!”
一切从2020年3月12日开始变得不太一样。这是柏林爱乐暂停公开演出的第一天,那天晚上的主角是英国指挥家西蒙·拉特,他是柏林爱乐前任首席指挥,与乐团有16年的合作经验。他也是最受欢迎的世界级指挥大师之一,举办由他指挥的音乐会的晚上,音乐厅外面总是堵车。
但那一天,音乐厅外面的路上空荡荡的。上午排练到一半,乐团经理来通知,今晚没有观众来了。怎么办?
在柏林爱乐138年的历史上,有过不止一次这样的特别夜晚。这个世界顶级交响乐团用音乐陪伴人们度过了一天又一天,它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冷战时期柏林墙的修建与倒下、经济危机。不管发生什么,柏林爱乐的音乐会是不会停办的。纳粹统治期间,乐团的首席指挥是富特文格勒,老音乐厅在一场空袭中被炸毁,指挥家就带着乐团去柏林歌剧院演出;不久后,歌剧院也被炸为废墟,他们就继续换地方演出。有时候音乐会会被空袭警报打断,观众甚至习惯了按序疏散,等到警报结束再回到大厅,听乐团把剩下的曲子演奏完。战争结束后,柏林爱乐在废墟中举办了战后的第一场音乐会。
“二战”结束之后,一个记者在德国街头采访,他拉着来往的人问:“每天经历轰炸和死亡,你是如何熬过战争,熬到明天的?”其中有一个人想了想,回答他:“因为明天还有富特文格勒的音乐会。”
柏林爱乐必须演出,音乐必须在,这一点无须讨论。观众来不了,他们就想办法把音乐送过去。于是,在取消公众聚集现场音乐会的通知发出后,他们很快发了另一条通知:“柏林爱乐大厅将关闭至4月19日。但是,西蒙·拉特爵士及柏林爱乐的音乐家们决定,在没有观众的情况下,也要继续完成本场音乐会原定曲目卢奇亚诺·贝利奥《交响曲》和贝拉·巴托克《乐队协奏曲》的演奏,并免费向全世界直播。”
面对空无一人的观众席,晚上8点,音乐会开始,西蒙·拉特站上了指挥台,他和乐团成员们互相看了看,笑了起来。在这个夜晚,西蒙·拉特和柏林爱乐想要向世界传递一个信号——音乐还在。
音乐的答案
今晚的音乐主角是两个活在困境里的人,和他们对命运的回答。他们所讲述的是音乐的一个经典命题——在残酷的命运里,在熬不下去的时候,人为什么活下来?
第一部作品是意大利作曲家贝利奥的《交响曲》,这是一部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的作品——那是一个充满变化的时代,也潜藏着变数,“当你顺着音乐走到终点,会发现,自己回到了最初出发的地方,但已经在不知不觉间,变成了另一个人”。
另一部作品是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创作于1943年的《乐队协奏曲》,它是一个孤独的病人对命运的解读。“二战”中,巴托克公开反对法西斯:“我看到你们如何对待犹太作曲家,从今天开始,我要求你们也这样对待我,虽然我并不是犹太人。”为此他不得不离开家乡,移居纽约,但是他几乎不会说英语,也和纽约的都市生活格格不入。在纽约,他不算一个客人,但那里不是他的家,他也没有能够回去的地方。每天被困在自己的房间里,疾病、孤独和异乡感一起袭向他,他总是发烧,几乎无法作曲,沮丧地判定自己的职业生涯走到了尽头。他被生活困住了。
1943年春天,巴托克的一位小提琴家朋友写信给当时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指挥谢尔盖·库赛维茨基,请求他的帮助——巴托克需要药,但他更需要音乐,“音乐也是一种治疗”。
库赛维茨基为这位作曲家到美國军队求情,希望能给他使用青霉素。那时候青霉素在美国只有军队有权支配,是仅次于核计划的顶级项目。一个月后,指挥家来到巴托克的病床前,给他带去了青霉素,还有一份交响乐约稿,他希望巴托克创作《乐队协奏曲》。这给了巴托克极大的希望,音乐成为他的动力,虽然身体依然虚弱,但他在精神上得到了极大舒缓。这一年的夏天,他用了55天时间,一气呵成地写完了全部5个乐章。巴托克是全世界第一个使用青霉素的平民,他因此熬过了那个垂死的1943年,有机会看了自己代表作的首演,听到现场观众的喝彩,也获得了额外的时间,为妻子的生日偷偷写了一首曲子,藏在曲谱的后面。显然,这是一次有效的治疗,治愈他的有时候是青霉素,有时候是《乐队协奏曲》。
这位被困在命运难题里的作曲家,把他所有的情感都写在《乐队协奏曲》中,这成为他最知名的代表作——它包含着令人窒息的黑暗,时而又跳跃着幽默,在最后的章节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乐观和明亮。

西蒙·拉特
对西蒙·拉特来说,演奏巴托克的作品像是一场从黑暗驶向光明的旅行,但他常常觉得乐谱最后十几个小节实在是太明亮了,在经历了之前的种种黑暗、挫折、迷茫、困顿后,迎接我们的出口是什么?光明的终点之后,那是什么?
在柏林最孤独的夜晚,这个答案逐渐清晰起来。这个晚上,在场所有的音乐家似乎感同身受地理解了这份隔绝中的孤独、未知中的希望,他们在交响乐中又一次实现了灵魂的共鸣。西蒙·拉特说,在音乐最后的十几个小节,他看到巴托克在音乐中复活,就坐在他们面前,讲述他自己的故事。事实上,青霉素并没有拯救巴托克,他在两年后的秋天去世了。最后一次住院治疗前,他恳求医生再多给他一天时间,让他把另一部钢琴协奏曲写完。可惜他的时间只够勉强写完草稿,在最后一个音符后面,他歪歪扭扭地写下了“The End(曲终)”。不久后,他的生命也走到了终点。然而,正是藏在乐谱里的这些音符,开启了属于巴托克的新音乐时代。终点之后,是另一个起点。
音乐结束之后
最后一个音符不可避免地到来了。音乐的世界有一条真理:任何音乐会都有结束的那一刻。走出音乐厅,带走的可能是伤感、感动、希望、失落,或是无法平息的激动。即便是在柏林爱乐的数字音乐厅,曲终也是不可避免的告别:“音乐会结束了,谢谢你的观看。保重!你的柏林爱乐。”
然而,还有另一条音乐真理:等到明天醒来,无论世界将变成什么样子,柏林爱乐一定还会演出。它可能以不一样的方式出现,演奏不一样的曲目,但它一定会出现,在历史的任何一个夜晚,音乐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