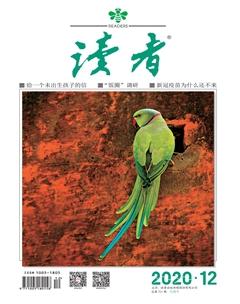我在等你啊
〔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逢珍译
这间工作室是我从一个摄影师手里继承来的。一幅淡紫色的油画立在墙边,背景是一片看不大清楚的花园。我坐在一张藤椅上,就像坐在画面深处花园入口的门槛上。我坐着想你,一直想到天明。
一
天亮时分非常冷。一些泥塑人像从黑暗中现身,其中的一个——模样像你——被包在湿布里。我从这间幽暗的房间里横穿过去。玻璃窗上挂着黑色窗帘,宛如破碎的战旗,我用一根竿子将它们相继挑开。
我把清晨引进屋来,一个睡眼惺忪的可怜清晨。我不由得笑起来,不知为何发笑,也许原因很简单,就是我整整一夜都坐在一张藤椅上想你,周围全是垃圾和石膏碎片。
每当有人提起你的名字,我总会想起这样的画面:你双臂向上抬起,扶正头发上的纱网——黑光一闪,有力的动作带着香气。那时我已经爱上你很久,至于为什么,我至今不知道。你狡猾刁蛮,害得我和你一样无所事事、虚度时光。
秋天的清晨在风中闪着微光。窗外视野开阔,能看到柏林城里平铺的屋顶。前一天和你通过电话,是我主动打给你的,我们约好今天在勃兰登堡门下见面。电话的杂音像蜜蜂嗡嗡叫,而你的声音越滑越远,最后消失了。我紧闭双眼跟你说话,难过得直想哭。
吃过早饭,我出门去见你。黄色的阳光如滚滚洪流,我开始眩晕。
我边走边想,你可能不会来。即便来了,我们还是会再吵一次。我只会塑像,只会爱。这对你而言是不够的。
多雄伟的城门。高大的公交车从城门洞里挤过去,沿着林荫大道驶向远方。我在城门压抑的拱顶下等你,两边是两根冰冷的柱子,不远处是门卫室的格子窗,到处是人。我倚着手杖,在两根柱子清冷的影子里等着。我想你不会来了。
二
门卫室窗户附近的一根柱子旁有一个小货摊,摆着呈扇形摊开的明信片、交通图、彩色照片。货摊旁有一张小凳,上面坐着一个小老太太,短腿、胖身材,被晒黑的圆脸上长着雀斑,她也在等。
我心想,我和这老太太等的人哪一个会先到——她的顾客,还是你。
行人不停地从两根大柱子之间走过,有的人走过去时会朝明信片瞅上一眼。遇到这种情况,老太太总是绷紧每一根神经,两只亮闪闪的眼睛盯着往来的人,仿佛在传递她的想法:买吧,买吧……可是对方瞥一眼便走了过去。老太太好像并不在乎,垂下眼帘,重新看起手中的那本红皮书来。
我认为你不会来了,但我还在等你。我竭力想象你正走过来,趁我没注意就走到我跟前了。我只要再往拐弯处看一眼,就会看见你的海豹皮外衣。但我故意不往那边看,舍不得刚才自欺欺人的想象。
一阵冷风袭来。老太太站起身来,使劲按住明信片,让它们各安其位。她上身穿的是黄色丝绒夹克,下身是褐色裙子,前面裙裾短、后面裙摆长,这样她走起路来就像挺着个大肚子。这会儿她正忙着整理她的货摊。

我觉得寒气在同我作对,一浪接一浪地直扑我的胸口。到现在一直没人买她的东西,老太太又坐到她的凳子上。
已经过去一个钟头了,也许不止一个钟头。不知不觉间天空乌云密布,一场暴风雨即将到来。行人弓起背,扶着帽子,快速离去。现在你要是来了,那可真成奇迹了。
老太太小心翼翼地往书里夹了张书签,停下来陷入沉思。我猜,她是在幻想从阿德隆饭店走出一个富有的外国人,买下了她摊子上的所有小物品。她穿着那么一件丝绒夹克,想来也不是很暖和。
你可是说好了要来的呀!我记得你在电话里说的话。我多么想见你!狠心的风又刮了起来。我拉起了衣领。
突然,门卫室的窗子打开了,一名绿衣卫兵叫老太太过去。她赶快站起来,挺著肚子急忙朝窗口跑去。那名卫兵递给她一个热气腾腾的杯子,然后关上窗户。
老太太小心翼翼地端着杯子,回到她的凳子上。从杯口黏附着的一圈奶皮来看,那是一杯牛奶咖啡。她喝了起来。我第一次见有人喝咖啡喝得如此全神贯注,津津有味。她忘了小摊,忘了明信片,忘了寒风,忘了顾客,只是一门心思地细细品尝,完全沉浸在她的咖啡中了——这情形倒像我一样,忘了自己的等待,只管看她那双幸福得迷迷瞪瞪的眼。她喝了好长时间,把杯口的一圈奶皮虔诚地舔掉,双手握住杯子取暖。一股看不见的甜蜜暖流注入我的心田。我的灵魂也在喝咖啡,也在取暖,和老太太品味着牛奶咖啡一样。
她喝完了,一动不动地坐了片刻,然后站起来,走到窗子边去还杯子。但走到一半,她停住了,双唇一收,露出淡淡的微笑。她快步折回货摊,抽出两张彩色明信片,又快步走到门卫室窗前,用她戴着羊毛手套的小拳头轻叩玻璃。窗子打开了,一只绿袖子伸了出来。她把杯子连同明信片递进窗户,急匆匆地连连点头致谢。卫兵翻看着明信片,转身离开窗口,反手缓缓关上窗扇,走到屋子里面去了。
三
这时我突然明白,世界原来充满关爱,我周围的一切都深怀仁慈之心。在我和天地万物之间,有着幸福的纽带。我明白了,我想从你身上找到的欢乐并不只隐藏在你身上,还在我周围:在街上喧闹的声音中,在意外翻起的裙裾上,在冷雨欲滴的秋云里。这世间并不只有争斗,也不仅是一系列弱肉强食的偶然事件,还有光明亮堂的快乐、仁慈之心的颤动,它是一件赠予我们、尚未被打开欣赏的礼物。
就在这一刻,你终于来了——其实来的不是你,而是一对夫妇。男的穿着雨衣,女的高个儿、苗条,穿一件海豹皮外衣。他们俩走到货摊前,男的开始挑选摊子上的小东西。小老太太满脸通红,喘着气,一会儿望望那男人的眼睛,一会儿又看看摊子上的明信片,激动得眉毛突突跳,看神情就像一个正使足全身力气赶马前行的马车夫。可男人还没来得及挑出什么东西,他妻子就一耸肩膀,拉着他的袖子要走。这时我注意到她很像你,不是相貌相似,而是挑剔、不依不饶的神色相似,不屑一顾的一瞥相似。
他们走了,什么都没买。老太太只是笑笑,又一次埋头读她的书了。我没必要再等下去了。我沿着逐渐暗下来的街道离开,遇上过往的行人,便往他们脸上悄悄观瞧,捕捉笑容和意想不到的小动作。
天黑了,雨也大起来。这时一辆有轨电车叮当驶来,我跳上车。车厢里的乘客个个沉着脸,打着瞌睡,摇来晃去。黑沉沉的车窗上是小雨滴打过后留下的无数斑点,就像繁星点点的夜空。电车沿街道前行,街两旁是哗哗作响的栗子树。
电车停下时,可以听见被风吹落的栗子砸在车顶上的响声。电铃一响,车又开动了。
我怀着一种苦中作乐的心情,又开始等待那些从车顶传来的轻响声。一个急刹车,又落下一颗栗子。过了一阵,又砸下来一颗。砰,砰,栗子顺着车顶滚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