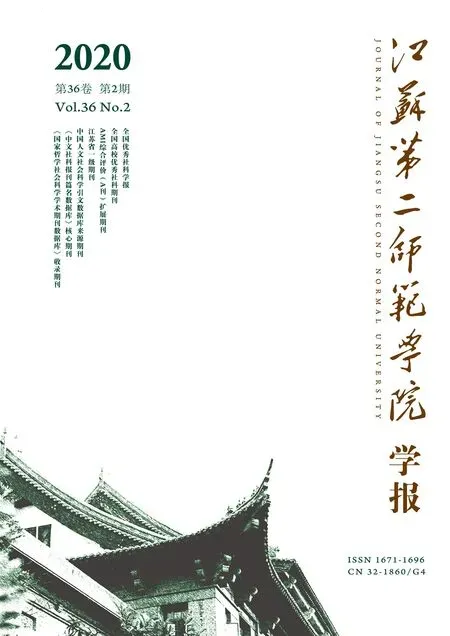石臼湖流域汉语方言形成初探*
侯 超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1200)
引言
石臼湖位于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高淳区和安徽省马鞍山市博望区、当涂县的交界地带,是江苏、安徽两省的界湖。石臼湖西部有长江支流青弋江、水阳江、姑溪河汇入,北部经天生桥河(旧名胭脂河)与秦淮河相通,南部经石固河、芦溪河与固城湖相连。石臼湖因形状酷似“石臼”而得名,湖面200多平方公里。石臼湖、固城湖和原丹阳湖同源于古丹阳湖,因泥沙淤积,逐渐分化出固城、石臼、丹阳三湖。丹阳湖成湖之初面积很大,湖面4000余平方公里[1]283。唐代诗人李白《姑熟十咏·丹阳湖》诗云:
湖与元气连,风波浩难止。
天外贾客归,云间片帆起。
龟游莲叶上,鸟宿芦花里。
少女棹归舟,歌声逐流水。
此诗前两句描写了丹阳湖波澜壮阔的景象,可见直至唐代该湖依然是烟波浩渺的大泽。因历代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围垦,丹阳湖湖面不断缩小,目前只剩石臼、固城二湖。
石臼湖流域处于吴语和江淮官话交界的前沿,原属吴语区,周边有当涂、博望、溧水、高淳一县三区,其中当涂西部、北部,溧水北部的方言以江淮官话为主,当涂东部、溧水南部和高淳区以吴语为主。此外,本区还有移民方言岛分布,尤以溧水地区为最。据新版《中国语言地图集》[2],整个宣州吴语地区的吴语和官话方言成交错状分布,不像其他方言片区那样界限分明。
目前石臼湖流域的土著吴语受到江淮官话的冲击,正在逐步丧失原有的领地。20世纪80年代,叶祥苓(1984)曾经调查过苏浙皖三省交界处的方言,对这一地区的方言分布状况和主要特点作了初步分析,其中涉及高淳、溧水和当涂三地的吴语。[3]近年来,石臼湖流域的方言正在逐步受到学界关注,但有关该区方言形成原因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从方言分布及方言特点出发,结合行政区划、历史移民、方言接触三方面尝试探讨石臼湖流域汉语方言的形成过程。
一、历史行政区划与方言分区
从方言分区来看,石臼湖流域江淮官话和吴语的分界线自东向西大体上在溧水城区—石湫镇北部—丹阳镇—薛镇—护河镇—太白镇一线。石臼湖流域的吴语分属宣州吴语铜泾小片、太高小片和太湖吴语毗陵小片:博望区、当涂东部、溧水西南部、高淳西南部的吴语属于宣州吴语铜泾小片;高淳桠溪镇以西(砖墙镇除外)及当涂湖阳镇西部属于宣州吴语太高小片;溧水东南部(白马等镇)、高淳东部桠溪镇属于太湖吴语毗陵小片。石臼湖流域的土著方言为吴语,主要特征是古塞音声母今读仍保持三分格局,多数方言点有六至七个声调,且入声分阴阳。词汇方面和邻接的太湖吴语有一些共同特征,如“下雨”说“落雨”,“淋雨”说“沰雨”“去年”说“旧年”,“时候”说“辰光”,“迟”说“晏”,“割稻”说“斫稻”等。语法方面,石臼湖流域吴语表被动可用介词“把”(如高淳:他把狗咬则)、表处置可用介词“拿”(如高淳:拿门关起来)。石臼湖流域吴语特征的保留显然与其历史上长期处于吴语的地域范围内有关。
石臼湖流域的文明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1997年高淳薛城遗址的发现,表明距今5500—6000年,这一地区已有人类活动[4]。除高淳外,当涂、溧水也都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从历史行政区划沿革来看,石臼湖流域长期处在同一政区。(1)历代行政区划的沿革主要参考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当涂县志编纂委员会《当涂县志》(中华书局,1996)、高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高淳县志1986-2005》(方志出版社,2010)、溧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溧水县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西周时期,石臼湖流域属吴国,东周时期先后为越、楚所辖。秦朝实行郡县制,设有丹阳县、溧阳县,时石臼流域大部分属丹阳县,小部分属溧阳县,两县先后为鄣郡、会稽郡所辖。两汉至西晋时期隶属丹阳郡。西晋时,于丹阳县南部分置于湖县。东晋及宋、齐、梁、陈的都城都在今南京市,此时石臼湖流域属丹阳郡及侨置南豫州、淮南郡等。时另有侨置当涂县,初无实地,今当涂县之名始于此。隋开皇十一年(591年),析溧阳西北及丹阳(江宁和博望交界处)故地东部置溧水县(今溧水、高淳属之),为溧水建县之始。隋朝当涂、溧水之地属丹阳郡,高淳之地属宣城郡。唐朝石臼湖流域大部属宣州,隶江南西道,此时石臼湖地区与南京地区(属润州,隶江南东道)已有分隔。明弘治四年(1491年),析溧水西南境置高淳县,是为高淳建县之始。自北宋始,溧水、高淳和当涂已有明确分野,此后,石臼湖流域的行政区划基本没有大的变化,高淳、溧水始终和南京一起先后为江宁府(北宋)—建康府(南宋)—集庆路(元)—应天府(明)—江宁府(清)所辖,当涂始终和芜湖、繁昌一起先后为太平州(两宋)—太平路(元)—太平府(明清)所辖。
周振鹤、游汝杰(2015)指出,中国古代的行政区划对方言的发展演化有很大的影响,一府(或与府相当的州、郡)或一省(或与省相当的路、州)之内的语言有一体化的趋势。特别是唐宋的州和明清的府所辖的地域,对一体化来说非常适中。[5]62石臼湖流域自古属于吴地,其方言早期显然属于吴语范畴。自东晋以来,北人南迁,石臼湖流域自北向南逐步受到北方方言的影响。唐代,高淳以及当涂、溧水南部均属宣州(辖今石臼湖流域和芜湖、宣城、安庆地区),而当涂、溧水北部的一小部分区域属于润州(辖今南京、镇江地区),时宣州和润州的分界线大体跟今天石臼湖流域北部的吴语和江淮官话的分界线一致,只是后期随着时间的推移,方言分界线略有南移,可见唐代的行政区划对石臼湖流域的吴语和江淮官话的分区有着重要影响。
北宋时,当涂属太平州(辖当涂、芜湖、繁昌三县),溧水、高淳属江宁府,此后,太平、江宁名称虽有沿革,但辖地基本不变,当时太平州和江宁府东部在地理上基本上以石臼湖的中线为界,这条分割线也成为今安徽、江苏两省的分界线。在地理上,石臼湖的阻隔,使得宣州吴语内部产生分歧:西部(不包括当涂湖阳镇)属宣州吴语铜泾小片,而石臼湖南岸(包括当涂湖阳镇)则是宣州吴语太高小片。这种宣州吴语内部的分区也大体上跟宋代以来太平州和江宁府的行政分界相一致。可见,地理上的分割对石臼湖流域宣州吴语的内部分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历史移民与方言演变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移民是西晋永嘉丧乱之后的北人南迁。永嘉丧乱之前,苏南、皖南地区都说吴语,用吴语传唱的南朝乐府民歌中的“吴声歌曲”就产生于建业一带。[6]西晋永嘉年间北方少数民族乘机攻入长安,俘晋愍帝,西晋亡。317年,琅琊王司马睿于建康(今南京)即位,史称东晋。永嘉丧乱后,中原士族臣民大批南迁,史称“衣冠南渡”。永嘉移民的特点是时间长、数量大,自永嘉元年至泰始二年的一百五十年间,南迁流民达九十万人之多,占南朝刘宋人口的六分之一。[7]410由于移居建康的北方人多是统治阶层和名门望族,社会地位很高,他们所说的语言自然也具有很高的威望,因此南方士族纷纷效仿北方口音。“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辨,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8]529-530前贤一般认为,六朝时期,南京方言属于吴语[6]9,但当地居民实际操北方话和吴语两种方言,北方人和南方士人操北方话,庶人则操吴语。因为北方移民在人口、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占有优势,北方方言在南京地区逐渐取代了吴语。[5]17
语言的传播路径大体上有两种,一是人群之间的传播,这种传播在中国古代通常是自上而下的,即从上层阶级向普通百姓传播,六朝时期金陵吴语被北方话取代的过程正是由士族向庶民方向发展的。二是地域之间的传播,又有跳跃式和渐进式两种,前者往往形成方言飞地或方言岛,后者则形成地理上相连的方言片或方言区。北方话在南京、芜湖等沿江城市取得优势地位之后,在地理上进一步向离江较远的地区推进,但是由于古代交通不便,城乡经济、文化水平差异明显,这种推进是非常缓慢的。石臼湖地区距离南京城区80公里左右,古代多是经济上不发达的农村,加上湖水阻隔,所以尽管北方话在濒临长江的南京等城市逐步取代了吴语,但是进一步的南推显然受到了阻碍,至今仍然没有越过石臼湖,直到20世纪80年代,石臼湖以北溧水城区仍然能够调查到属于吴语的“老在城话”[10]2,可见,石臼湖北部地区的吴语被江淮官话取代还是比较晚近的事情。朱蕾(2016)认为皖南的强势江淮官话的形成主要是在明清以后[11],从时间上来看,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古代北方方言不断南扩,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占据优势且人口数量超过土著的北方方言要在它所迁入的中心城市取代当地方言相对比较容易,但要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农村地区取得优势并非易事。宋室南迁,建都临安(今杭州),北方移民所带来的官话在杭州城区具有优势地位,致使杭州城成为吴语包围中的官话方言岛,但优势的官话方言遭到周围吴语的抵抗,从而形成了具有官话色彩的吴语杭州话。[12]古代石臼湖流域交通不便,且经济、文化上跟长江沿岸的大城市相比要落后很多,这种状况使得这一地区的吴语得以保存。相对而言,长江沿岸多为人口聚集的中心城市,北方移民南迁以后往往定居于此,士族大户也不愿意进一步往南迁移到农村去,所以当时的移民并没有大规模扩散到石臼湖流域。永嘉丧乱之后,大批的北方移民都是沿着长江分布的,除南京外,今芜湖、马鞍山等地也被北方移民填充,《晋书》卷十四《地理志》载“成帝乃侨立豫州于江淮之间,居芜湖。时淮南入北,乃分丹杨侨立淮南郡,居于湖。又以旧当涂县流人渡江,侨立为县,并淮南、庐江、安丰并属豫州。宁康元年,移镇姑熟”[13]272。“芜湖”当指今芜湖市,侨立豫州于此,“丹杨”即丹阳县(今小丹阳),“于湖”由丹阳县析出,“姑熟”即今当涂县城。可见,今长江沿岸的芜湖市、马鞍山市在永嘉丧乱之后,都被北方侨民占据,只是跟南京地区的移民来源地略有不同,今芜湖市、马鞍山市(包括当涂县城)的方言均属江淮官话,这跟永嘉丧乱之后的北方移民不无关系,只是因为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低于南京,这里的吴方言被北方方言覆盖的时间略晚于南京地区。如上所述,北方移民到达江南后集中分布于长江沿岸,并未扩散到离江较远的石臼湖地区,至今,吴语仍散存于芜湖和当涂两县的东部和南部。
第二次移民大潮始于唐安史之乱后,持续至五代,历时近两百年。这一时期的移民不像第一次大移民主要集中在长江沿岸,而是遍布南方各地,“其中,江南、江西、淮南和蜀中吸收了最大量的移民,是移民的主要迁入区域,福建则是唐末移民的重要迁入区”[7]269。“江南”指今江苏、安徽两省的长江以南部分和上海市与浙江省。与第一次迁入江南地区的移民不同,第二次迁入江南地区的移民分布范围很广,今苏州、南京、杭州、绍兴、宣州、歙县、贵池都是移民聚居的重要地区。从移民分布来看,第二次大移民主要迁入江南地区的一些重要城市,迁入石臼湖流域尤其是农村地区的移民相对较少。安史之乱后的北方移民方言加速了沿江城市吴语向北方话发展的过程,使得北方方言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但没有对石臼湖流域的吴语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第三次大移民是靖康元年至建炎四年(1126-1130)的北方人口南迁。据葛剑雄(1997),此次移民大约有三个浪潮:金军攻入河北、河东以后,移民进入河南和淮南;攻入淮南后,移民进入江南;攻入江南以后,一些移民进入岭南、福建以及其他山区。[7]279北方移民在江南地区分布很广,临安府作为南宋都城,成为北方移民分布的中心地区。平江(今苏州)、建康、镇江三府是江南仅次于临安的移民较多的府州。建康及其周边地区(太平州、池州等)也是北方人民迁入避难的重要据点。据《高淳县志》(1998-2010),高淳境内万人以上大姓多为南宋期间徙入的后裔,[14]9这说明即使是离江较远的城市也有移民前来定居。从总体上来看,当时北方移民仍以移居中心城市为主,县城虽有移民,数量有限,农村更少。南宋以来,石臼湖流域的方言仍以吴语为主,但自北向南已逐步受到北方方言的冲击。
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大移民均对苏皖长江南岸地区方言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一次大移民奠定了北方方言的基础,第二次和第三次大移民进一步巩固了北方方言的地位,同时使得北方方言的区域不断南移。在第三次大移民时期,南京、马鞍山、芜湖等集中了数量相对较大的北方移民,“此时应已成为北方方言的次方言区”。[15]与第一次大移民主要定居长江沿岸城市略有不同,第二次、第三次大移民的范围扩大,普通的县城亦有移民迁入,这些北方移民的方言显然对石臼湖流域的吴语产生了一些影响,使得这一地区的吴语逐渐脱离太湖吴语的轨道而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发展。
除了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大移民,还有一次局部移民活动也对石臼湖流域的汉语方言分布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就是太平天国战争及战后的大移民。1851年至1864年的太平天国战争波及十六省,造成生灵涂炭,人民流离失所,其中苏浙皖交界地区因为是太平天国战争的主战场,人口损失尤其严重。据葛庆华(2002)统计,战争期间苏浙皖交界地区人口损失约1048万,损失率达90.1%,战后这一地区有大量移民迁入,持续半个世纪之久,至宣统三年移民达二百余万,占全区人口的58%。[16]1战后石臼湖流域移民大部分来自河南、湖北、皖中和苏北地区,显然移民的来源地主要是北方方言区。大量移民移居石臼湖流域,对这一地区的方言地理分布格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形成了为数不少的方言岛(当地人一般称之为“客民话”),其中溧水地区最为明显,如白马、共和、东屏等镇的河南话方言岛[17][18]。从总体上来看,客籍移民方言只是使得石臼湖流域吴语的生存空间进一步受到挤压,但其方言特征并未明显渗入本地吴语。
三、方言接触与方言演变
永嘉丧乱和唐末五代的北方移民奠定了沿江城市南京、马鞍山和芜湖等地北方方言的基础,至南宋靖康之变发生历史上第三次大移民之后,这几个沿江城市应该已经成为北方方言区了。至于这些城市的方言进一步演变为江淮官话的时期,目前尚无确切的材料能够证明。刘丹青(1997)认为,比较稳固而定型的江淮官话区的形成较晚,是在原先南方方言(主要是吴语)和不断南下的历代北方人的方言长期融合之下逐步形成的。[19]44-45这种观点很有见地,历代移民所带来的北方方言不断地和不同时期的本地方言接触融合,形成了今天长江南岸江淮官话的基础。在方言的交界地区,两种方言之间的接触是必然的,就石臼湖流域而言,这种接触发生的时间相当早,而且是在持续不断地进行之中。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在古代,本地方言对外来方言的抵抗力量也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由于离江较远,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加之水系复杂、交通不便,石臼流域的土著吴语能够保存至今。近代以来,由于经济、交通条件的改善,方言之间的接触变得更加频繁和深入,从方言发展的大势来看,沿江的北方方言持续不断地向南推移,五六十年代溧水县城还有吴语存在,现在基本上已经找不到说吴语的人了。
当涂东部、溧水南部目前仍属吴语地区,具有一些跟江淮官话不同的特征,如:声母有清浊对立,泥来母不混,侯韵读[ei][ø][]等,但因为直接面临江淮官话,这里的吴语带有一些江淮官话的特征,如:古浊音声母出现更多的清化现象;微母更多地读零声母;蟹止摄开口三四等字舌尖化;宕江摄主元音读低元音;通摄主元音央化;声调数量五至六个;次浊上归阴上。有些语音特征跟邻接的江淮官话并不完全一致,那很可能是早期方言接触过程中语音折合或后期发展的结果。词语方面跟江淮官话也有一致性特征,如“今天”说“根朝”,“彩虹”说“虹kɑ谁”说“哪个”,“西红柿”说“洋柿子”等。
需要指出的是,高淳地处石臼湖南岸,距离沿江城市较远,交通相对不便,所以历史上到达这里的移民相对较少,即使是太平天国战争以后,高淳地区的土著也显著多于移民(2)据葛庆华(2002),宣统三年,高淳县人口约20.1万,移民及其后裔约6.2万,数量明显少于石臼湖流域其他地区。,这一点跟当涂、溧水的情况有所不同。应该说高淳吴语受到官话方言的影响相对要小得多,至今仍然保留一些跟太湖吴语一致的特征,如语音方面,有七个声调、阳入为低升调、覃韵有读[]的现象等;词汇方面,雄性动物前加“雄”(如“雄鸭”)、雌性动物后加“婆”(如“鸡婆”)等。有些太湖吴语难觅的说法甚至还能在高淳方言中找到遗迹,例如“茄子”高淳方言说“落苏”,太湖吴语基本上已被“茄子”取代,只在上海方言中还保存着。
前文指出,自北宋以来,高淳一直和南京在同一行政区内,而与镇江、常州不同区,行政区划的阻隔也使得高淳地区的吴语跟太湖吴语有明显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不少都是晚期自发形成的,例如奉微母读重唇音[b][20]、咸山摄开口一二等字读[ie](如“三ie1”)[21]、次浊上归阴平[22]、边音自成音节、“去”白读[kh7]、“关”读[ye1]等。当涂、溧水地区的吴语也有一些既不同于江淮官话也不同于高淳吴语的特征,例如古浊音声母今读强气流辅音、山摄开口一二字有鼻韵尾丢失的现象(如“山”读[s1])、果摄元音高化或裂化等。还有个别的吴语方言点发展出一些独特的语音特征,如博望方言第一人称代词说[nie7]、第二人称代词说[nie8],两者只有声调差异。石臼湖流域复杂的语音面貌表明,在语言接触的前沿地带,土著方言在跟外来强势方言接触的过程中,会在剧烈的抵抗中缓慢地接受外源方言的影响,同时在演变的过程中也可能产生一些新的独有特征,方言接触加上方言自身的演变可能导致本土方言变得跟周边的方言都不一样,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高淳吴语。多种方言之间的接触还可能导致一字多音现象。溧水石湫镇西部横山村覃韵个别字有三种不同口音,例如“胆”读[tã3][tia3][t3],三种形式之中,[tia3]和[t3]是吴语层次,[tã3]是江淮官话的层次。不同的读音形式之间相互竞争,最终只有一种胜出。
四、结语
石臼湖地区是江淮官话和吴语交界的前沿,结合语言的外部环境来看,江淮官话是本区强势方言。历史上,官话方言和吴语的总体发展趋势是北进南退,目前这种趋势仍在石臼湖流域上演。石臼湖流域马鞍山、当涂地区属于皖南,而目前整个皖南地区的强势方言是江淮官话。关于皖南地区强势江淮官话的形成,郑张尚芳(1986)和孟庆惠(2000)秉持“移民说”,前者认为江淮官话主要是江北移民带来的,后者认为历史上的永嘉移民、晚清移民和抗战移民都是皖南江淮官话形成的重要原因。[23][24]2338-2339朱蕾(2016)不同意二人的观点,认为皖南强势江淮官话主要是明清以后标准语通过文教力量在皖南持续推行的结果。[9]我们认为,皖南强势方言江淮官话的形成不能一概而论,有些在很大程度跟历史移民有关,如沿江的马鞍山、芜湖等,这些城市永嘉丧乱之后就成为北方移民聚居之地,唐末五代和宋室南迁时期也都是北方移民南迁的重要据点,这些城市的江淮官话是在本地方言和不断南下的历代北方人的方言长期接触融合之下逐步形成的。朱蕾(2016)也承认芜湖、当涂等沿江城市江淮官话的形成及发展可能和南京、扬州等方言基本同步或略后。[11]可见南京、马鞍山、当涂县城等沿江城市的江淮官话形成较早,且形成之后基本上处于一种比较稳定的状态。这些沿江城市的江淮官话不断向东南方向推进,蚕食石臼湖流域吴语的地盘,则是比较晚近的事情,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溧水城区还有吴语存在,目前部分靠近江淮官话的镇村多种方言形式并存的现象,也直接证明了江淮官话和吴语之间的竞争关系。石臼湖流域的吴语跟主流吴语有很多不同,特别是石臼湖南岸的高淳方言,早期曾被认为是“古韵方言活化石”,其实它的很多特点大都是后期音变的结果,当然也有一些特点跟方言接触密切相关,如麻韵主元音读[a]等。总之,我们认为石臼湖流域方言的形成是行政区划、历史移民、方言接触和自发演变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发挥了程度不等的作用。
——以浙江地区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