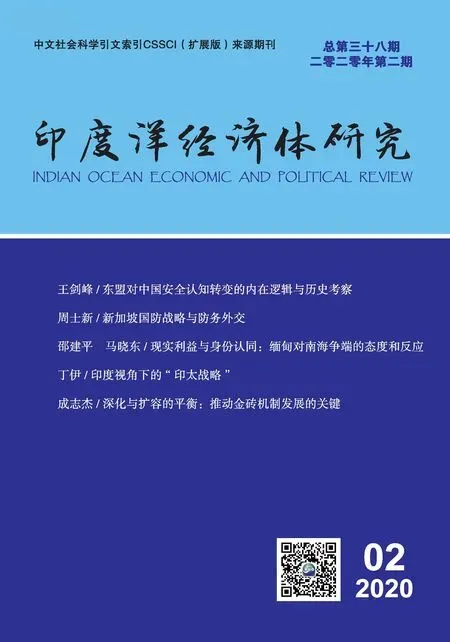东盟对中国安全认知转变的内在逻辑与历史考察
——国际政治心理学的视角
王剑峰
【内容提要】安全认知是行为体在外部环境刺激下,对安全领域中的事件、政策、行为、趋势及其发展规律等方面形成的预期、评估、信念和推理过程。行为体安全认知的转变并非自发导致的,而是在外部环境刺激和安全意象投射这两大核心自变量的互动作用下共同完成的。外部环境对行为体的刺激本质上是一个信号发射与接收的过程,行为体在接收外部环境刺激而输入的新信息后会在心理环境中有个调适过程;而经由心理环境反应的最终结果就是行为体对特定认知对象逐渐投射出内涵各异的安全意象,从一个安全意象向另一个安全意象的过渡即是行为体安全认知的转变。此外,这一“刺激—投射”模式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还会受到行为体的实力差距、历史记忆及地缘因素等干预变量的影响。本文即是从这两大核心自变量和三个干预变量着手,系统梳理出东盟对中国安全认知转变的内在逻辑演进机理,并以此为分析框架考察1967年以来东盟对中国安全认知转变的历史进程,其根本要义在于找到确保东盟对中国安全认知始终维系在正面化和积极化方向的历史经验和战略教益。
一、问题的缘起
安全认知是安全研究领域中的核心议题之一。行为体在不同安全认知主导下构建什么样的安全关系直接影响到各自的对外战略政策与其内部的战略动员模式。在更深的意义上,性质各异的安全认知还意味着行为体动员和消耗既有战略资源的多少。例如,朋友式的安全认知所营造出的政治互信与合作氛围使得行为体可以将本国的战略资源更多地投入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上去;而敌对性安全认知所产生的恐惧心理及对冲突与战争不可避免的预期,则致使国家将大量的战略资源用于军备竞赛。由此可见,不同类型安全认知主导下的不同性质的安全行为模式,对一个国家的内外战略影响甚远。在此背景下,本文所关注的重点是东盟对中国安全认知的转变问题。东盟对中国安全认知反映的是东盟内部群体意识中的中国安全构想,它既是东盟在与中国交往中对中国的安全行为和政策长期理解的一种心理积淀结果,亦是东盟预判未来中国安全战略的一项重要心理因素考量。为什么要关注东盟对中国的安全认知转变呢?
一方面,东盟与中国在各自的安全战略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就东盟来说,自1967年成立至今,中国始终在东盟的安全认知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对东盟而言,中国是,并且从一开始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安全关系”(1)[菲律宾]鲁道夫·C.塞韦里诺:《东南亚共同体建设探源:来自东盟前任秘书长的洞见》,王玉主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44页。。维持对中国或敌人或竞争者或朋友的安全认知对东盟的政治一体化进程及社会经济发展存在着不可估量的影响。而就中国来说,东南亚地区目前在中国的外交战略布局中已经牢牢占据重中之重的位置,这一地区已经成为未来中国崛起为区域性或全球性强国的重要战略缓冲区。尤为重要的是,东盟及其主导构建的安全规范和安全制度在中国与其它大国在亚太/印太地区的争端与摩擦中扮演着“润滑剂”的角色,“与东盟建立密切的双边关系对于中国来说就是宝贵的战略资产”,“中国的战略规划者们应把东盟视为其最重要的战略资产之一”。(2)[新加坡]马凯硕、孙合记:《东盟奇迹》,翟崑、王丽娜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02、103页。作为中国崛起进程中的重要安全疆域,东盟已经成为中国对外安全战略的优先方向,考察东盟对中国持有何种安全认知是中国制定对东盟和周边安全政策的重要前提条件。
另一方面,也是最关键的,东盟对中国的安全认知及其影响下构建的安全关系并非总是积极的与正面的,其对华安全认知转变过程不断遭到负面因素的干扰和迟滞。中国在东盟安全认知中被建构为何种身份不仅是东盟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根源,它在更深的层次上还影响着中国着力打造的周边安全环境布局,同时更是关乎东南亚乃至亚太/印太地区安全的核心变量。对这一安全认知变迁的探究不仅需要从理论上梳理出东盟对华安全认知转变的逻辑演进机理,更重要的是,通过考察东盟对华安全认知转变的发展历程及其背后的促进和阻碍因素,从中透析出促使当今东盟对华安全认知维系在正面化、积极化方向大有裨益的历史规律,是中国构建和谐、稳定的周边环境不可或缺的经验借鉴。
因此,理论上与现实中的双重意义使得梳理出东盟对华安全认知转变的逻辑机理并考察其安全认知转变的历史发展经验,成为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二、文献回顾与既有解释的不足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东盟对华安全认知转变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成果。然而,具体到这一安全认知转变背后的动因分析则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通过对既有文献的回顾可以发现,当前学界对东盟对华安全认知转变的分析主要集中为以下几种观点:
其一,中国政策或行为变化说,认为中国对东盟外交政策或行为的变化促使后者改变了对中国的安全认知。奥斯卡·马蒂(Oscar Martí Lluch)认为,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渐调整并改善与东盟国家的外交关系,并在安全问题上奉行负责任的态度和多边外交政策,从而“促进了中国在东盟成员国中的积极形象”,中国实现了“从地区安全的威胁者到保障者”的转变。(3)[西班牙]奥斯卡·马蒂:《发展中的东盟“中国观”:从威胁到机会?》,《南洋问题研究》2008年第4期,第11-13页。罗伯特·萨特(Robert Sutter)指出,东盟的中国形象历经了从20世纪60年代的“共产主义威胁”到如今的“利益合作者和协调者”的转变。他认为是中国通过灵活的、适度的和援助的外交方式表明“中国已经学会利用细致入微的和关切的政策获取东南亚地区的支持”,进而改变了东盟对中国的形象认知。(4)Robert Sutter,“China’s rise, Southeast A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in Evelyn Goh,Sheldon W.Simon(eds.),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east Asia(New York:Routledge,2008),p.96.
然而,这类观点无法解释在和平的外交政策之外,为什么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领海争端甚或战争行为依然得以令东盟对华安全认知维系在总体良性运转的层次上。例如,1979年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却得到了东盟内部的支持,原先逐渐松动的安全困境状态并没有因为中国的战争行为而退化。此外,1995年中菲在南海美济礁的武装对峙以及2012年中菲“黄岩岛事件”等领海争端也并未阻断东盟与中国构建安全共同体的愿景。因此,仅考虑中国对东盟外交政策的变化,难以合理地解释东盟为何在中国的冲突与战争行为出现时,没有发生退回彻底的安全困境式的认知逆转。
其二,域外大国影响说,认为某些域外大国尤其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刺激东盟扭转对中国的敌对性安全认知。这类观点强调冷战时期东南亚地区的安全结构是在美国的操控下建立起来的,东盟的安全防务有赖于美国的保障。因此,美国与中国的互动关系势必影响东盟对华安全认知。伊恩·斯托雷(Ian Storey)认为,1967年东盟的成立是对中国威胁认知的直接回应,并且东盟还积极支持美国主导的针对中国的遏制战略。然而,“1972年中美友好关系的恢复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东盟对中国的威胁感知”。(5)Ian Storey,“Singapore and the Rise of China: Perceptions and Policy”,in Herbert Yee and Ian Storey(eds.),The China Threat: Perceptions, Myths and Reality(London:RoutledgeCurzon,2002),p.209.屠年松、屠琪珺则认为20世纪50—70年代,东盟视中国为该地区“主要的不稳定因素以及对它们的威胁”,因而选择加入美国组织的反华阵营;而东盟与中国结束敌对状态并实现安全关系正常化的很大动因,在于70年代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及中美关系的改善。(6)屠年松、屠琪珺:《中国与东盟国家和谐关系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18年,第61页。
不过,这类观点无法说明为何美日等域外国家与中国关系交恶之后,东盟依然与中国保持着良性运转的安全关系。又如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所指出,1989年中国国内出现政治风波后,面对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的制裁与排斥,东盟国家选择通过外交活动接触而非孤立中国,“当世界其它国家尽力孤立中国时,东盟选择向北京伸出援手”。(7)David Shambaugh,“China Engages Asia: 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9,No.3,2004/05,p.68.也就是说,东盟对华正面安全认知并未因域外大国对华关系的恶化而扭转。这就说明将域外国家影响作为东盟转向对华安全认知转变的关键动因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其三,体系结构压力说。一种观点认为作为整体的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动直接促成东盟对中国的安全认知转变。唐翀、李志斐等学者强调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与东盟对中国的理解密切相关,他们认为冷战结束后尽管原先美苏两大力量或消失或回缩,但由于中国崛起造成的结构性压力和地缘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导致东盟依然缺乏安全感,中国在地区安全角色中的不确定性是东盟在安全上对华威胁认知的重要根源。(8)唐翀、李志斐、张楠:《不确定下的担忧:冷战后东盟国家对中国在地区安全角色的认知》,《南洋问题研究》2012年第3期,第47-58页。但亦有学者对这种单一性的威胁式认知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例如,喻常森认为中国崛起为地区大国对21世纪的国际体系格局影响最大,东盟面对这一冲击对中国形成了威胁、机会和伙伴三种交织的认知。(9)喻常森:《东盟国家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政策反应》,《当代亚太》2013年第3期,第111-128页。换言之,体系结构的变动导致东盟对中国形成了不同的安全认知,没有任何一种安全角色占据主导。
另一种观点则着眼于区域性的体系结构变动,强调东南亚地区体系结构中的大国及其数量和相互间的战略博弈对东盟对华安全认知转变的影响最甚。颜欣系统考察了1967年以来的体系压力对东盟安全认知及地区安全治理机制的影响,这其中,中美在该地区的竞争以及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始终被东盟视为不变的和恒定的外部体系压力,故而中国在东盟的安全认知中始终被视为重要威胁源。(10)颜欣:《体系压力、安全认知与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变迁》,《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9年第2期,第76-105页事实上,中国在东盟安全认知过程中并非一直被视为恒定的威胁,这种看法忽视了东盟对华安全认知转变过程中的朋友意象和安全共同体要素。故此,无论是全球层面还是区域层面上的体系结构变动说作为单一的动因,亦不足以解释东盟对中国的安全认知转变的现实。
其四,制度规范约束说,认为东盟构建的一系列以东盟为核心的地区安全机制和安全规范等制度性安全要素有力地规约了中国在该地区的安全行为和安全战略,使得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安全行动更具稳定性和预测性,从而促使东盟主动抛弃原先的安全困境认知,转而主动与中国共建地区安全共同体。吴翠玲(Evelyn Goh)认为东南亚国家在20世纪50-60年代对中国的安全认知集中于共产主义威胁,70-80年代处于对中国作为地区大国的疑惧和对中国巨大经济潜力的预期存在矛盾认知,以及90年代冷战结束初期阶段对中国弥补东南亚地区“权力真空”倍感担忧。但是,东盟通过一系列多边制度安排最终成功将中国“社会化”到东盟主导的安全规范中去,从而大大降低了东盟对中国安全认知中的威胁程度。(11)Evelyn Goh“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a Challenge”,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Vol.30,No.4-5,2007,pp.809-810,815-818.丹尼·罗伊(Denny Roy)指出,东南亚国家鼓励中国参与多边组织和国际对话与协定,并通过东盟地区论坛、“东盟+3”、“清迈倡议”等制度框架积极与中国接触,而中国被“社会化”到“东盟方式”之中以及对东盟主导的安全制度的认同,促使东盟转变了对中国这一地区大国的威胁认知。(12)Denny Roy,“Southeast Asia and China: Balancing or Bandwagoning?”,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27,No.2,2005,pp.310-312.
诚然,中国积极融入东盟主导的安全制度和规范有力促成了后者对中国的安全认知转变。但东盟与中国之间的安全机制和安全规范的构建时期开启的较晚,正如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所指出,20世纪90年代起,东盟开始有目的地通过“东盟方式”及其行为准则等将中国“社会化”到区域性规范秩序的规则中去。(13)Alastair Iain Johnston,Social States: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1980—2000(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preface),p.xvi.而自东盟1967年成立至20世纪90年代前这段时期内,东盟—中国之间的安全制度建设尚未起步,但彼时东盟对华安全认知已经出现从安全困境中逐渐走出的趋向,东盟与中国的安全关系得到明显缓和,中国在东盟的安全意象中并不完全是敌人身份。因此,制度规范约束说难以解释20世纪90年代之前东盟对华安全认知的转变。也就是说,以制度规范约束说作为动因考察自1967年至今全时期的东盟对华安全认知的转变历程是存在先天不足的。
总之,对既有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上述观点为我们理解东盟对中国安全认知转变提供了或多或少的借鉴与启发。但是,它们中的任何一种单一的观点均难以合理地解释东盟对华安全认知转变的现实,并且这些既有观点还缺乏对这一安全认知转变背后逻辑机理的系统梳理。此外,安全认知本质上是心理学范畴的内容,而既有研究却鲜有借用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去深入、系统地探讨东盟对中国的安全认知转变问题,这是既有研究的一项空白。据此,本文在反思和借鉴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试图从国际政治心理学的视角出发构建一个综合性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更好地解释东盟对华安全认知的转变问题。还需要说明的是,“认知变量既是自变量又是因变量”(14)尹继武:《社会认知与联盟信任形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页。,前者是指行为体的认知是影响其决策和行为的重要决定性因素;后者是指行为体内在的情绪、动机、经历以及外在环境因素等都会影响其认知过程。本文所重点考察的是作为因变量的认知,具体而言,从外部环境刺激和安全意象投射两大核心自变量及若干干预变量着手,来探究东盟对中国安全认知转变的内在逻辑。
三、安全认知转变的内在逻辑
(一)安全认知的内涵
认知(cognition)是心理学范畴的核心概念之一,本杰明·莱希(Benjamin B.Lahey)认为“认知可以被界定为通过智识过程(如知觉、记忆、思维和语言)获取、转换、存储、提取和使用信息”,这一概念强调信息是认知的基础,且信息在认知过程中是积极变化的。(15)Benjamin B.Lahey,Psychology: An Introduction(11th edition)(New York:McGraw-Hill,2012),p.265.由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存在解释和预测现实的缺陷,加之国际关系研究向微观层次的“回落”趋向,(社会)认知心理学的概念、方法及相关理论被一些学者引入到国际关系领域之中,并促成了国际政治心理学这一新兴分支学科的兴起。冷战的终结为一直处于偏弱地位的认知心理学派提供了崛起的契机,(16)王建伟:《认知和形象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载王建伟主编:《国际关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10页。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国际现象和国际事件也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迈克尔·扬(Michael D.Young)和马克·舍费尔(Mark Schafer)强调认知“构成了所有政治行为的基础,亦是理解权力和利益的基础”。(17)Michael D.Young and Mark Schafer,“Is There Method in Our Madness? Ways of Assessing Cogni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42,No.1,1998,p.64.行为体对任何现象、事件、趋势等都会形成特有的信念体系和认知结构,当这样的信念体系和认知结构建立在行为体之间的安全议题和安全关系的基础之上时就形成了安全认知。
在综合考察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安全认知界定为行为体在外部环境和信息的刺激下,对安全领域中的事件、政策、行为、趋势及其发展规律等方面形成的预期、评估、信念和推理过程。这个定义主要强调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外部环境所释放出的各类信息及其所构成的情势是刺激行为体对特定对象形成不同安全认知的重要动力源。第二,心理预期等内在认知的重要性。哈罗德·斯普劳特(Harold Sprout)和玛格丽特·斯普劳特(Margaret Sprout)夫妇认为“真正重要的是决策者所想象的环境是怎样的,而不是环境实际上是怎样的”。(18)Harold Sprout and Margaret Sprout,“Environment Factors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 James N.Rosenau(ed.),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a Reader in Research and Theory(New York:Free Press,1969),p.49.迈克尔·布雷彻(Michael Brecher)则指出,行动环境对决策的影响“要通过决策者的认知才能实现”。(19)Michael Brecher,The Foreign Policy System of Israel:Setting,Image,Proces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2),p.4.可见,一个完整的安全认知的最终转变通常是内外因素互动作用的结果。
(二)安全认知转变的核心自变量
1.外部环境刺激:安全认知转变的诱发
斯普劳特夫妇指出,环境政治研究中的一个长期趋向就是“认为‘环境’是不包含人类属性的术语”,人们倾向于认为环境就是指“土地、空气、水、非人类的有机体及诸如高楼大厦、道路等人造结构”,这种环境概念实际上排除了社会性条件和无形因素。在批评这种狭义式的环境概念后,两位学者基于生态学视角强调环境概念应该是包含人类属性与非人类属性、社会性与非社会性因素的综合性定义。(20)Harold Sprout and Margaret Sprout,Toward a Politics of the Planet Earth(New York:Van Nostrand Reinhold Company,1971),pp.23-24.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D.Lasswell)亦区分了环境(environment)的物质属性和社会环境(milieu)的建构属性。(21)[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世界政治与个体不安全感》,王菲易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第141页。据此,本文用以考察安全认知转变的其中一个自变量——外部环境是指与行为体发生联系的客观世界,它包括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具体到影响行为体安全认知转变的社会环境主要包括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动、国际/区域安全机制和安全规范的完善与否、认知对象的安全战略/行为/政策等要素;物理环境则主要是指地理位置和距离等要素。
外部环境对认知主体的刺激本质上是一个信号发射与信号接收的过程,它一般可以分为正面信号刺激和负面信号刺激。就正面刺激而言,它的信号源既可以是客观环境本身所“无意”释放出的。例如,国际体系结构从高烈度的两极对峙向多极化趋势演变所带来的全球/区域安全环境的缓和;全球性/区域性安全机制和规范对地区安全局势的规约功能所营造的和平氛围等。同时,正面刺激亦可以是特定社会环境下认知对象有意而为之。正如尹继武所指出,信号表达是“行为体通过有意的信息传达,试图让接受者领会、理解并接受特定的含义”(22)尹继武:《诚意信号表达与中国外交的战略匹配》,《外交评论》2015年第3期,第3页。,它带有很强烈的动机性、目的性和针对性。这种信号表达既可以是裁军、缔约、经济援助、外交互访等具体行动,亦可以是发表和平宣言或白皮书等话语表达。行为体有意释放出能让认知主体明确而清晰地观察或感知到的信号,“主要是为了影响信号接收者对发出者的印象”(23)[美]罗伯特·杰维斯:《信号与欺骗:国际关系中的形象逻辑》,徐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第13页。。一般来说,正面信号刺激有助于推动行为体对他者的安全认知朝向积极化、正向化的趋势转变。
而就负面刺激来说,它的信号源同样既可以是外部环境“无意”释放的。例如,国际体系结构剧烈变动的震荡、新旧国际秩序交替时期的混乱、世界性或区域性战争等造成的不安全感。此外,它亦可以是认知对象传达出的。例如,行动层次上,如增加军费开支、大规模军事工事修筑和军备竞赛、断交或外交降格、废约等;语义层次上,如对他国形象的蓄意抹黑、话语权打压和剥夺、外交恫吓等。无疑,负面信号刺激往往导致行为体对他者的安全认知转向消极层面。总而言之,外部环境的正面刺激亦或负面刺激是导致行为体安全认知转变的重要“催化剂”。
2.安全意象投射:安全认知转变的基础
社会认知理论认为,行为体在面对认知资源或认知客体时并非只是被动地接受和应对,而是会根据认知主体自身的社会知觉(感知、理解和思维等)赋予认知客体以抽象意义;然后会将抽象形成的特定社会印象与其所处的认知环境进行对比判断,进而形成对外部刺激的态度和评价。(24)孙国辉等:《社会认知理论视角下区域刻板印象的形成机制研究》,《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第120页。石之瑜亦指出,认知主体的信息接收过程即便是被动的,“也并不代表人们对所有环境中的刺激都一样对待;事实上,大多数环境中所发生的刺激都受忽视”。(25)石之瑜:《政治心理学》,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第105页。这些论断都表明行为体面对外界环境和信息的刺激,往往不会直接而迅速地转变安全认知并立即作出安全决策或行为;反之,认知主体在接收外部环境刺激而输入的新信息后,会在自身的心理环境中有个调适过程。
心理环境在行为体处理接收到的外部刺激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类似于一种“中转站”机制,外部环境刺激经由心理环境反应的最终结果,就是认知主体对特定认知客体逐渐投射出内涵各异的意象,它的一个必要认知功能就是有助于行为体“理解政治环境及其中的关系”(26)David O.Sears,Leonie Huddy,Robert Jervis(eds.),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294.,而行为体的安全决策和行为正是建立在心理环境投射出的不同安全意象的基础上,行为体在外部刺激下的战略选择和战略行为模式取决于何种安全意象在决策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由于外在安全环境和内在心理预期始终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之中,在此影响下的行为体对特定对象的安全认知并非始终定格在某一种固定意象之上。反之,动态演进中的安全认知才是常态,而从一个安全意象向另一个安全意象的过渡,也就是行为体安全认知的转变过程。从一个不那么宽泛的意义上讲,安全认知是行为体在外部安全环境的刺激下从心理上将他者构建为敌人、竞争者或朋友等安全意象,这三种不同安全认知投射出的安全角色在互动中最终往往会形成安全困境,介于安全困境与安全共同体之间的摇摆状态及安全共同体三大安全互动模式。至此,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行为体安全决策的心理认知过程,即一个三阶段的假设模式:外部刺激→心理反应→安全意象→安全决策/行为。
(三)影响行为体安全认知的干预变量
外部环境刺激和安全意象投射是一般意义上影响行为体安全认知的两大核心自变量,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往往还会受到行为体的实力差距、历史记忆及地缘因素等干预变量的影响。
其一,实力差距。认知主体与认知客体在实力对比上的差距会显著影响前者对后者的安全认知。当认知主体与认知客体之间的实力差距水平较小或维系在认知主体可接受的范围内,它对客体的安全认知将定位在正面化与积极化的方向上。此时,认知主体对自身实力不断增长的知觉过程实际上就是它的“自我意象”构建逐渐迈向成熟、自信与强大的演变过程,它是促进主体对客体安全认知的正向干预变量。而当认知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实力差距过于悬殊或超出认知主体的预期水平,那么它对认知客体的安全认知便趋于负面化、消极化。此时,体系结构中权力的不对称分布是造成认知主体对客体安全认知出现偏差及恐惧心理的主要现实因素,它是导致主体对客体安全认知的反向干预变量。简言之,实力差距水平与安全认知定位之间存在一定正相关关系。
其二,历史记忆。行为体往往会通过历史类比将从过去事件中汲取的知识经验投射到当前的认知中。一方面,如果过往阶段认知主体与认知客体之间的交往与联系充满和平、和谐、稳定和愉快等积极记忆,并且认知主体从这些历史互动中汲取到积极记忆始终在其认知结构中占据主导,那么这类正面历史记忆就是影响行为体安全认知的重要正向干预变量。另一方面,当认知主体以历史上的弱者和受害者进行自我身份建构,以及对认知客体作为强者和威胁源进行他者形象塑造时,行为体对客体的安全认知中便始终存在安全困境因素,此时这类负面历史记忆便成为影响行为体对客体安全认知的反向干预变量。可以说,历史记忆扮演何种类型的干预变量取决于历史记忆自身的属性。不过,在多数时候行为体往往有选择地从历史记忆中提取会对其认知和决策产生较大程度负面影响的经验类比(27)[美]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41页。,它既可能是过往时期屈辱、惨痛的灾难性记忆持续刺激行为体的结果,亦可能是行为体对历史事件错误知觉而产生的“遮蔽”效应。故此,一般来说,作为干预变量的历史记忆其反向效应通常要大于正向效应。
其三,地缘因素。地缘环境是影响国家对外认知的最基本、最直接和最重要的因素,(28)钱洪良主编:《中国和平崛起与周边国家的认知和反应》,军事谊文出版社,2010年,第181页。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认为“国家投送实力的能力随着距离的远近而变化。临近的国家比距离远的国家构成的威胁更严重”。(29)[美]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周丕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1页。由于距离、位置等地缘因素的不可磨灭性和恒定性特征,认知主体与认知客体在地理上紧密相邻这一现实情境本身就会加大前者对后者威胁认知的敏感度,而一旦认知主体在实力差距上与客体相比过于悬殊,那么这种实力对比上的脆弱性会显著加剧地缘因素带给认知主体的畏惧感。当然,如果认知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地缘距离过于遥远,那么前者对后者的威胁认知将大大降低甚或不存在,而无需考量双边实力对比如何。不过,需要辨别的是,地缘上的非临近性一般不会影响行为体的安全认知,因为这种地缘上的远距离难以构成一种外部刺激,意味着行为体的心理环境也就接收不到此类威胁信号,进而不会投射出安全意象。因此,地缘因素在影响行为体安全认知时主要是作为反向干预变量运行的。
如图1所示,认知主体对认知客体的安全认知转变是在外部环境刺激和安全意象投射两大自变量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它们之间互动形成的“刺激—投射”模式是行为体认知转变的重要动因。同时,这一认知转变过程还受到实力差距、历史记忆与地缘因素等干预变量的影响。其中,实力差距是正向与反向效应同等的干预变量,历史记忆是反向效应大于正向效应的干预变量,而地缘因素则是一种纯粹的反向干预变量。如此,以这两个核心自变量主导,加之三个干预变量的共同作用一并构成了行为体安全认知转变的内在演进机理。

图1 安全认知转变的内在逻辑
注:干预变量中的实线箭头表示正向效应,虚线箭头表示反向效应,实线与虚线的长短比例代表该干预变量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何种效应的作用更大。
四、东盟对中国安全认知转变的历史考察
本部分将根据前文构建的安全认知转变的理论分析框架,系统考察东盟对中国安全认知转变的历史演进。可以发现,1967年以来,东盟对中国的安全认知转变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与反复性特征。所谓阶段性是指东盟对华安全认知转变大致沿着从敌人意象(高烈度的安全困境)、竞争者意象逐渐到朋友意象(安全共同体的初现)的发展方向演进,其安全认知图谱实现了从安全的威胁源、敌对势力到安全的维系者、安全战略伙伴的观念转变。而反复性则是指东盟对中国总体上的正面安全认知演进过程中,会因为一些反向干扰因素的作用不时出现破坏安全氛围的倒退现象,其对华安全认知转变往往处于安全困境与安全共同体的矛盾状态之中。
(一)完全的敌人意象(1967—1971)
1967年东盟在冷战的背景下正式成立,该时期东盟对华安全认知形成过程中接收到的几乎全是负面刺激信号。首先,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美苏将冷战争斗的范围拓展至第三世界。在亚洲地区,美国极力鼓动东盟实行反共反华、敌视和拒绝承认新中国及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政策,并积极拉拢东盟参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禁运、封锁与围堵。此外,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为营造冷战氛围而推销的“共产主义威胁”和“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下,成立之初的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就处在与中国对峙的对立面”。(30)陈乔之等:《冷战后东盟国家对华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9页。国际体系结构的紧张对峙,以及帝国主义阵营的挑唆促使东盟对华的安全预期处于极为消极的层面。其次,成立之初的东盟在彼时中国的外交话语中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它被中国视为“侵略性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孪生兄弟,是美帝国主义反华包围圈的一个组成部分”。(31)《美帝走狗拼凑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出笼 美国主子急忙为其反华反共反人民的反动联盟喝彩叫好》,《人民日报》1967年8月12日。加之东盟成立适逢中国“文革”时期,当时中国外交受到“左”的错误思想影响,对外开始推行“革命外交”,并对东南亚共产党领导的反政府武装斗争予以各种支持。这些负面信息大大刺激东盟在安全评估上对中国的敌意和不信任,以及对共产主义“红色政权”持有的深深的恐惧和怀疑。
外部刺激导致东盟最终认定中国为区域安全的重大威胁,由此,1967—1971年期间东盟对中国安全认知的结果就是敌人意象在认知图谱中牢牢占据了主导地位。当行为体在安全认知中将他者构建成敌人意象时,他者就会被视为威胁源,其动机被认为是邪恶的和无节制的。(32)Richard K.Herrmann and Michael P.Fischerkeller,“Beyond the Enemy Image and Spiral Model: Cognitive-Strategic Research after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9,No.3,1995,pp.426,428.这种敌人意象映射到行动环境中,中国在东盟的安全决策中自然就成了安全威胁源和战略防范对象,安全认知中的疑惧与不信任因素导致双边互动最终形成了安全困境的情势。正如有学者所指出,这一时期内东盟完全是以“安全困境”中的“最糟糕的打算”来为应对中国可能的威胁,这也是中国在20世纪“第一次成为东南亚直接而严重的威胁,并且这种威胁被东南亚所剧烈地感知到”。(33)Chang Pao-Min,“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The Problem of a Perceptional Gap”,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9,No.3,1987,p.185.概而言之,在东盟成立最初的四年时间里,源自国际体系结构层面和中国的负面信号刺激,致使消极性安全预期笼罩着东盟对中国的安全认知。
(二)敌人意象的退化与竞争者意象的初现(1972—1990)
1972—1990年期间是东盟对华安全认知转变的第一个阶段,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从完全的敌人意象转向不断退化中的敌人意象;二是从敌人意象转向初始的竞争者意象。与前一阶段东盟接收到的完全的负面刺激信号不同,本时期东盟逐渐开始接收到一系列正面刺激信号。首先,西方阵营的刺激。冷战阴影下成立的东盟在对华安全认知上唯美国马首是瞻,而中国与西方阵营关系的改善必然会影响东盟对中国的安全评估。1972年中国与美国、日本的关系均实现正常化,这极大刺激了东盟对中国的安全认知,原先高烈度的安全困境和敌人意象逐渐打开了缺口。其次,第三方威胁的刺激。1978年,越南公然开启在中南半岛的谋霸行径,此举严重威胁到了东盟的安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后期,为了对付越南的安全威胁,“东盟与中国结成了战略上的同盟关系”(34)曹云华、唐翀:《新中国—东盟关系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16页。。源自西方阵营和反越南的正面信号刺激东盟重新审视对中国的安全预期和评估,原先的地区安全潜在侵入者转向共同反对地区霸权的盟友,继而前期高烈度的敌人意象逐渐开始衰退,东盟对华安全认知首次出现转变。
除此之外,这一时期中国主动传达的正面刺激信号亦不容忽视,它不仅进一步削弱了东盟对华安全认知中的敌人意象因素,还促成了东盟对中国投射出竞争者意象。首先,与东盟成员国先后建(复)交。1974年中马建交;1975年中菲、中泰建交;1990年中新、中印尼分别建(复)交。其次,1975年,中国正式承认了东盟的合法性地位。1978年中国领导人首次访问新加坡、马来西亚与泰国,并明确表示支持东盟国家维护主权与独立,支持东盟建立东南亚和平、自由和中立区的主张,赞成东盟加强东盟自身团结的立场。再次,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的经济改革中所获得的巨大成就,使得东盟与中国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在南海争端中强调“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些务实的外交思维促进了东盟改变对中国的安全角色定性。事实上,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得益于中国经济改革催生的贸易与投资联系,加之东盟认同中国在制衡越南中的作用,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出现缓和。(35)Richard Sokolsky,Angel Rabasa,C.Richard Neu,The Role of Southeast Asia in U.S.Strategy Toward China(CA:Rand,2001),pp.30-31.
尽管这一阶段东盟与中国互动形成的安全困境的烈度有所降低,但东盟对中国的安全认知仍然呈现出一种矛盾的心理状态。一方面,东盟自身实力的持续增进刺激了东盟对华安全认知转向良性势头。朱利叶斯·凯撒·帕雷纳斯(Julius Caesar Parrenas)指出,“20世纪70年代及80年代大部分时期,东盟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提升了其战略地位”,这促使东盟着手武装现代化建设,从而提高了东盟的军事和外部防御能力。这是影响东盟认知中国的一项重要的环境因素。(36)Julius Caesar Parrenas,“China and Japan in ASEAN’s Strategic Perceptions”,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12,No.3,1990,p.210.另一方面,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仍然是东盟在安全认知上疑惧和防范的对象。冷战早期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共产党组织的亲密关系,并对该地区共产党领导的反政府运动予以外交声援和武力支持,这一历史记忆始终干扰着东盟对华安全认知。(37)Allen S.Whiting,“ASEAN Eyes China: The Security Dimension”,Asian Survey,Vol.37,No.4,1997,p.302.事实上,1976年东盟发布《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际实力对比有利于共产主义国家”,中国在意识形态上仍然推行革命输出战略是“带来东南亚国家安全恐惧的重要因素”。(38)江帆:《东盟安全共同体变迁规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03页。简言之,1972—1990年间东盟对中国的安全认知,是在留有敌人意象(程度有所下降)的基础上逐渐向竞争者意象转变。
(三)竞争者意象与朋友意象的交织(1991—2002)
这一时期东盟接收到的正面刺激信号从烈度和广度上较之前一阶段都显得更加深刻。这其中,外部环境施予的最大刺激就是1991年苏联解体导致两极体系结构彻底坍塌,原先严密的两极体系结构下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分敌友的做法失去现实意义,全球安全环境总体上趋于缓和,意识形态在东盟对华安全认知转变过程中的干扰作用大大降低。冷战结束后,东盟开始建立新的地区安全机制,并通过谋求将中国纳入到更大范围内的集体安全机制中来构建东盟与中国的安全共同体,从而使中国以参与者的身份共同维护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对此,中国亦释放出了更加积极的正面刺激信号,即主动加入东盟主导下的各类安全制度,并认可东盟在其中的领导地位。1991年东盟—中国“10+1”机制正式创立,“该机制内的首脑、部长及其他高官会议,提升了东盟与中国在政治—安全上的对话与合作”(39)“Overview of ASEAN-China Dialogue Relations”,https://asean.org/wp-content/uploads/2012/05/Overview-of-ASEAN-China-Relations-August-2018_For-Website.pdf,p.1.。1994年东盟倡导成立东盟地区论坛(ARF),20世纪90年代东盟与中国双边安全关系一个显著的转变,在于中国倡导在东盟地区论坛的规则下召开会议以增进亚洲军事交流,而在这之前中国拒绝与东盟商讨安全与军事问题。(40)Evan S.Medeiros and M.Taylor Fravel,“China’s New Diplomacy”,Foreign Affairs,Vol.82,No.6,2003,pp.25,26-27.1997年东盟—中日韩“10+3”机制诞生,进一步拓展了东盟与中国的安全对话范围。中国主动内嵌进东盟倡导构建的这一系列区域安全机制,意味着中国的安全行为和安全决策将更加具有可预见性和可控性,这也刺激东盟对中国的安全评估更趋积极化和正面化。
与此相呼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与东盟双边安全关系的战略性深化,是中国持续释放正面刺激信号的另一面。1991年中国正式成为东盟的对话伙伴。1992年东盟外长会议上通过了《东盟关于南中国海宣言》,这就“在自我克制、不使用武力及和平解决争端的基础上制定了一个非正式的行动准则”。(41)Ralf Emmers,“Maritime Dispu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Strategic and Diplomatic Status Quo”,https://www.rsis.edu.sg/wp-content/uploads/rsis-pubs/WP87.pdf,p.9.1996年,中国成为东盟的全面对话伙伴国。1997年,中国与东盟正式确立了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的目标和指导双方关系的原则。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对增进中国与东盟在南海地区的安全互信有重要的积极意义。通过这一系列新型安全协议和安全关系的构建,加之中国主动融入到东盟主导的安全机制中,使得中国被成功社会化到作为整体的地区安全合作架构之中。而中国融入并内化架构中的安全规范和规则,是双方安全角色结构发生转变的重要动因。区域和双边安全制度和规范的构建与完善,致使东盟开始将中国视为东南亚地区安全秩序的构建者与维系者,更是东盟超越安全困境并与中国构建安全共同体的关键性推动力量。
除了安全领域直接的正面刺激,中国在经贸合作领域亦传达出了重要的诚意信号。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负责任行为“大大改善了东盟对中国的认知和信任”;而东盟对华安全认知中的“中国威胁论”亦逐渐转向“中国机遇论”和“中国责任论”。(42)尹继武:《文化与国际信任—基于东亚信任形成的比较分析》,《外交评论》2011年第4期,第29页2001年,中国提出并与东盟就建立“中国—东盟自贸区”达成共识,“中国—东盟自贸区协定的实现意味着东盟成员国与中国之间的历史积怨与政治冲突,已经不再是影响双边关系的重要因素了”。(43)Rommel C.Banlaoi,“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s on the Rise of China:Regional Security after 9/11”,Parameters,Summer 2003,p.99.总之,上述四个方向上的正面信号刺激,特别是中国直接释放出的三大诚意信号大大改变了东盟对中国的安全心理预期,东盟对华安全认知开始出现转向朋友意象的趋势。然而,尽管本时段东盟已经开启了与中国构建安全共同体的进程,但由于中国在南海争端中坚持双边谈判、1995年美济礁事件及1996年台海危机等消极信号刺激,致使“东盟对中国在东南亚的意图存在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安全上的疑虑尚未完全消除。(44)N.Ganesan,“ASEAN’s Relations with Major External Powers”,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22,No.2,2000,pp.269-270;Allen S.Whiting,“ASEAN Eyes China: The Security Dimension”,Asian Survey,Vol.37,No.4,1997,p.299.有学者指出,鉴于与北方强邻中国的地缘临近性、长时期历史互动及领土争端,来自中国的威胁因素在所有东南亚国家的地缘考量中占据着重要地位,(45)Herbert Yee and Ian Storey(eds.),The China Threat: Perceptions, Myths and Reality(London:Routledge Curzon,2002,introduction),p.14.地缘因素作为反向干预变量的迟滞效应由此可见一斑。可以说,本时期东盟对华安全认知逐渐转向朋友意象的进程中,仍然存在竞争者意象的干扰。
(四)不稳定的朋友意象(2003年以来)
在前一时段中国从不同维度释放的正面信号刺激的基础上,加之本时期中国持续传达出的诚意信号的影响,2003年以来东盟对中国的安全预期继续向朋友意象转变。不过,在这一认知正面化转变过程中诸多不稳定因素的干扰作用有所回升。2003年,双方缔结《中国与东盟国家领导人联合宣言》,宣布共建“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随之,中国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这标志着中国东盟安全关系进入了一个以法律为基础和保障的新阶段”,“有利于中国东盟在安全领域互信关系的构建”。(46)王光厚:《冷战后中国东盟战略关系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5、177页。2006年,双方签署《致力于加强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国承诺完全支持东盟实现安全共同体。2012年和2016年,双方先后分阶段制定了两份《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未来行动计划,以更明确的纲领将双方间的安全互信与合作落到实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构建以及一系列后续保障协定的支撑,意味着东盟对中国的正面化安全认知有了法律化和制度化的保障。
除了制度层面的信号外,本时期中国刺激东盟安全认知转变的一个重大创举就是从观念层面释放刺激信号。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要与东盟携手共建命运共同体,呼吁双方“摒弃冷战思维,积极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新理念”(47)《习近平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人民网,2013年10月3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003/c1024-23101573.html.,周边命运共同体本质上体现的是中国对同东盟构建安全共同体的期望。肯·布思(Ken Booth)等指出,世界政治中难以解决的不确定性使得行为体无法彻底逃脱安全困境,但人们可以通过安全共同体这一有效模式超越安全困境。(48)Ken Booth,Nicholas J.Wheeler,The Security Dilemma:Fear,Cooperation and Trust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8),p.296.因此,中国主动提出与东盟共建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大大有利于增进东盟对华安全认知中的和平因素。2014年,习主席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新安全观,倡导亚洲走共建、共享、共赢的安全之路。这些观念层面上的正面信号刺激,有助于东盟和中国在互动过程中建构起一致的安全身份和安全认同,它将夯实东盟对中国安全认知继续转向正面化和积极化的观念与认同基础。
源于制度和观念层面的双重信号,刺激东盟在安全评估中将中国界定为安全战略伙伴,东盟对华安全认知中的朋友意象进一步加深。然而,值得警惕的是,2003年以来,东盟对华安全认知转变过程中的负面刺激信号较之前一时期有所强化。“大致从2010年下半年起,东盟对华战略疑虑不断上升”,双方在地区安全观上的认知分歧显著加剧,由此造成东盟与中国“陷入一定程度的安全困境”。(49)张哲馨:《新安全观与中国和东盟的安全困境》,《国际展望》2014年第3期,第40页。一方面,以美国2011年“重返亚太”为契机,日印澳英等域外大国纷纷介入南海争端,并通过在东盟国家间挑拨离间来压制中国的安全战略空间,由此在东盟与中国之间造成紧张的安全态势。另一方面,有如时殷弘所指出,大致自2012年开始,中国在亚洲和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军事”和“硬权势”增进大为显著,从而“扩展了与东南亚海洋国家的紧张”,并刺激后者与美国“着手构建相互间的安全合作网络”。(50)时殷弘:《关于中国的亚洲西太平洋战略和南海问题》,《东南亚研究》2016年第5期,第34-35页。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东盟对华安全认知中的竞争者意象和安全困境因素。负面信号刺激的回升,意味着东盟对中国安全认知的正面化转变过程中仍然面临着潜在退化风险。本时期东盟对华安全认知形成的朋友意象实际上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的侵蚀,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地缘因素的反向干预造成的。
五、结 论
东南亚地区是中国稳定周边的重要战略疆域,亦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因此,东盟对中国持有何种安全认知、构建何种安全意象、进而采取何种安全政策、推行何种安全行为,对正处于战略变革期和战略机遇期的当代中国来说至关重要。未来,东盟对中国安全认知转变过程中的正面刺激信号与负面刺激信号将持续并存。对中国来说,确保和维持东盟对中国安全认知转向正面化和积极化,将是相当长时期内的重要战略考量。
最为关键的是中国应该持续不断地释放正面刺激信号,以此保证东盟对中国的安全心理预期和评估始终保持在和平与安全的维系者、安全共同体构建者及朋友意象(至少也应该是竞争者意象)的层面上,极力避免东盟对华安全认知出现安全困境和敌人意象式的逆转。考察东盟对中国安全认知转变的历史可以发现,这一转变历程基本上沿着正向、积极的路线演进。但是,每一转变时期内始终存在若干负面刺激信号的干扰,尽管正面信号的刺激效应要远大于负面刺激。事实上,由于地缘、历史记忆、领土争端、域外大国挑唆等消极因素的阶段性刺激,东盟对华安全认知的负面刺激信号是难以根除的。故此,这种情境就格外要求中国尽可能多地释放正面刺激信号,以此消弭负面刺激信号在东盟对华安全认知转向正面化和积极化过程中的不利影响和阻滞效应。
在这一正面刺激过程中,特别要重视安全规范和安全机制等制度性要素的建设,因为“机制,以及比机制更具权威性、结构更庞大的制度,可以促进认知的演化”(51)[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第174页。。冷战结束以来,东盟对华安全认知出现过不同程度的负面信号刺激。在此背景下,东盟对中国的安全预期之所以未回到敌人意象,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中国认同东南亚地区安全制度规范对自身的约束。制度规范是影响东盟对华安全认知转变的重要正面刺激信号,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制度规范越是完善,中国被“社会化”到这些区域安全规范的程度越深,那么中国的朋友意象和安全共同体形象在东盟的安全认知中就愈加强烈。即便未来东盟与中国的安全共同体建设出现停滞、甚或倒退,但内蕴于安全共同体之中的安全规范和机制依然会发挥其惯性作用,规约和影响双边的安全行为和安全战略,从而不至于刺激东盟对中国的安全认知退化到敌人意象和安全困境的消极局面。
与此同时,还要注意作为干预变量的历史记忆会对行为体的安全认知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就要求中国最大化地消弭这类反向干预变量的消极影响。除上述安全制度和安全规范的构建之外,观念和认同方面的路径亦是值得思考的。回顾古代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历史,其中内蕴着和平友好的互动模式和深厚的和谐特质,而东盟对中国安全认知的历史记忆通常会忽视这些积极面。故此,对作为刺激源的中国(施动者)来说,要善于从古代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交往中挖掘出正面的“历史遗产”,塑造以和平、和谐、文明和包容等为主题的中国形象,进而以文化软实力和“二轨外交”为手段刺激东盟(受动者)对中国的安全认知朝正面化和积极化的方向持续推进,以扭转东盟对华安全心理预期中的负面效应。此外,由于另一项干预变量地缘因素(地理位置和距离)的不可消除性更加强烈,通过挖掘双方互动中的正面历史教益,亦有助于适当缓解地缘临近性给东盟对华安全认知造成的畏惧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