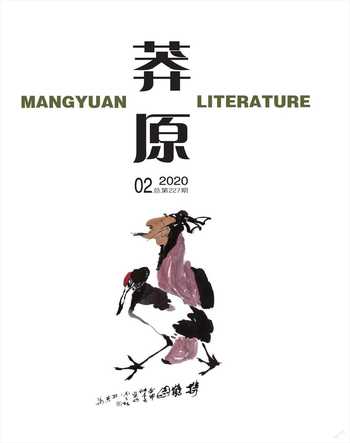渔人今世
陈七一
1
一开始,他们就是一叶浮萍。从江上、从湖中、从青通河里,随波逐流,汇聚到这里,虽是落了脚,有了属于自己的三间茅舍,可骨子里仍然无根。
夹江对面是一处绿洲。传说当年地藏王菩萨过江上九华时,踩断藕山一茎,顺流至此,生出此洲,是为荷叶洲。那时的荷叶之上,已然生出三街十三巷,热闹繁华得无以复加。
枕河拥江的他们一直期待着,期待有朝一日,能够像江对过的绿洲一样,在这里扎下根,化浮萍为莲藕,生出碧绿的荷叶,开出或素洁或嫣红的莲花来。
“君看一叶舟,出入风波里”。衣食无忧的岸上人,读这样的句子,读出的是诗意,而于他们则是宿命的全部写照。渔舟唱晚,在旁人看来,是多么温暖柔美的一幅画卷,而画卷里的他们,那些惯看秋月春风的他们,则是欲诉无人能懂的莫可奈何。
与河南嘴隔青通河而望的是一条老街。老街曾是沿江四大米市之一,也是清末民初官盐的集散地。而在米市、盐市之前,则是一处鱼市。杨万里的诗句“渔罾最碍船……鱼蟹不论钱”,道出了鱼市的成因,佐证了鱼市的繁华,最为人们津津乐道。
2
青通河由南而下,在河南嘴东北弧形入江。青通河曾是徽商水道,也曾是下江香客上九华山礼佛之水道,当然还是各类鱼儿进入白荡湖、缸窑湖、十八索等水域的通道。每年的桃花汛,从海里溯江而上的鲥鱼、刀鱼、鞋底板子鱼,从江里洄游来的鳜鱼、鲤鱼、柳叶鳊、船钉、鮰鱼、华鱼、鲟鱼,在这条河里不期而遇,尔后各自觅一处安乐窝,繁衍生息。
桃花汛,亦是鱼汛,但河南嘴人这时却收起扳罾渔网,钓而不纲,就连摆渡的动作都比往常舒缓得多。家里来了客人,偶尔钓得一两尾江鱼,就地取江水煮了,不用任何佐料,就能让客人感觉鲜美无比,多喝两盅酒,多吃一碗饭。江水煮江鱼,成就的是清欢滋味,蕴藏的却是简而不繁之大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条江水滋养一种美味,人与水土,鱼与江水,在自然形成的圈子里已经铁定为一个硬币的两面,变换一种场景,就没有那个味道了。
“扳罾,起罾。扳个鲤鱼十八斤。大鱼送隔壁,小鱼自家吃。”姥姥在教孙女唱儿歌,孙女长大后,有了女儿,教的仍是这首儿歌。
3
老翁这时正在给孙子们讲故事。
扬子大江,流到大通,遇群龙饮江,折转向北。河南嘴的嘴,便是其中一条叫作蟠龙的龙嘴,因其位于鹊江之南,后人便称之为河南嘴。
嘴上本为荒滩,芦荻成荡,为渔民系缆避风之所。一天半夜三更,有渔民听到芦荡深处有雄鸡啼鸣,以为恍惚,定心细听,真切分明,后数夜如此。待平明,上岸进入芦荡遍寻,不见半点人烟,哪里有什么雄鸡,连一只野鸡的影子也没有。此人将这一异端说与从兄,从兄始不信。于是,邀从兄,至夜阑,复闻雄鸡高唱。从兄惊喜万分,此人问其故。从兄凑近了低声说道:“此地荒无人烟,却又雄鸡夜唱,乃金鸡落巢之兆。说明这是块宝地啊!”说完,二人拊掌大笑。河南嘴上,自这俩兄弟起,便有了第一缕人烟。
金鸡报晓的故事,显然借用的是司马迁的 《高祖本纪》 笔法。众所周知,高祖刘邦在世时,从来不文饰自己的出身,言行质朴,每每提到何以成了真龙天子时,口口声声称老子提三尺剑取天下,这皇帝位子,是骑在马上打下来的。可是,历史总是需要不断地被重新解释和附会。金鸡报晓的故事,只是河南嘴人讲给自己的后人听的,要义只在于宣示他们落脚于此,是皇天后土的眷顾与天无绝人之路的艰辛。后来,街上的人或者更远的人都听说了这个故事,而且复述得比河南嘴人原生态的故事更倾向于神话,更加绘声绘色。有时候,他们想想这些个事,觉得挺好笑的。
4
长相思,摧心肝。
拉开落地窗帘,幽远的高天上是一轮可望而不可及的明月。
很久没有听过纺织娘的振翅声了,尤其是在这样的月夜。最后一次,还是四十多年前的一个夏末秋初的夜晚,江流婉转,月辉似银。他送走所有来道贺的亲朋好友,从江堤到河堤来回蹀躞,路边的草丛中,纺织娘为他“轧织、轧织”地唱着歌儿,似在欢送,亦像是在挽留。和许多同伴一样,打小时候,他们就想着外面的世界,想着有朝一日挣脱母亲的怀抱和父亲的视线,再也不要重复父辈们打鱼为生、靠天活命的生存方式。想着有一条属于自己的船,不打鱼只是载着自己的梦想,远离这方寸之地。而当这一天终于来到时,当他收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当他梦想成真时,他在月光下、在纺织娘的欢歌声里,一边规划着更遥远的未来,一边脚踏在这块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心里升腾起无以名状的情愫来。
也曾春风得意,也曾落寞惆怅。有时居庙堂之高,有时处江湖之远,唯一不变的是对亲人的思念,对故土的怀想。庙堂高峻,江湖险恶,会让他常常想起家乡的老树、旧屋、炊烟、鸡犬,想起青通河边的乌篷船和出入风波里的一叶扁舟。
在河南嘴,他是一位志满意得的偶像,然而,事实上,他真的是身衰志未遂。
早已过了知天命之年,再也不论什么衣锦还乡或是行囊空空了,他终于决定再回来看看。可当他来到渡口边,只向对岸张望了一眼,瞬间改变了主意,抽身回到老街上。
他还是怯怕了,怯怕那对面七十八亩土地,再也无法容得下他的脚印,更怯怕见到故人不知从何说起。他清晰地记得,他曾跟他们讲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而他们则说他是书读多了,人都读出毛病了。他还清晰地记得,他已经往生的父亲曾经告诉他,人不是鱼,能换钱,能当菜,有什么价钱。人要活得明白,平淡就好。
5
天色已晚,唐僧勒馬道:“徒弟,今宵何处安身?”行者道:“师父,出家人莫说那在家人的话。”唐僧道:“在家人怎么样?出家人怎么样?”行者道:“在家人,这时候温床暖被,怀中抱子,脚后蹬妻,自自在在睡觉;我等出家人,便是要戴月披星,餐风宿水,有路且行,无路方住。”
孙猴子的牢骚很有正能量,唐三藏不食人间烟火般的厚朴倒也很可爱。
叶家父子,目不识丁,当然不知道 《西游记》上这一段对白。他们生在船上,长在船上。一条船,一条江,就是他们的安身之所,几乎也就是他们的全部生活轨迹。上至汉口,下至江阴,他们长年累月看着岸上的水村山郭、烟树楼台,猜测、向往着那个世界里的生活。几乎在同样的年龄上,他们都曾问过自己的父辈同样的问题,什么时候能够像岸上人家一样,不再风餐露宿,月亮点灯。而他们的父辈总是说,人各有命。命中注定,我们就是水上漂的,犟不过命啊。
小叶不信命,决然上岸,投奔了一位汽修厂的师傅,拜师学艺。没有文化的小叶,敦厚、勤快、好学,很快赢得师傅的欢心。师傅逢人便夸,别看小叶像个哑巴,心里敞亮着呢。不几年,小叶成了小叶师傅,有了自己的一爿路边茅店。再过几年,在开发区有了自己的修理厂,在小城里有了自己的住宅楼,楼内有温床暖被,有娇妻爱子。
长江里的鱼越来越少了,老叶也漂不动了。小叶将老叶接到城里。行走江湖惯了,泊在另一个世界里,老叶似乎有点依依不舍。
一日,小叶陪老叶在客厅看电视,播放的正是唐僧勒马师徒问答这一出。父子二人对视,什么也没说,都会心地笑了。
6
他,大器晚成。说大器,是相对于他的家族而言,祖宗八代逐鱼群而漂流,家里没有一个识字的,更遑论当一名老师了。说晚成,是自进学堂,他就比同班同学大四五岁,人家中师毕业不到二十,他已经是二十四岁零几个月了。
他清楚地记得,十二岁那年春上,父母狠了心让他上岸进学堂读书,他掂量着饔飧不继的家境,死活不同意。住在岸上的舅舅,应承了他的学费和一日三餐,他才勉强答应。母亲带着他,过河,穿过老街,来到学校,找到校长。校长见到只比他矮一头的半大小伙子,还以为是转学来上初中的。当他的母亲嗫嚅着,说是来破蒙上一年级的,校长的第一反应是这孩子一定有问题,以年龄偏大为由婉拒了。
他跟着母亲回到渡口,站在母亲身后。母亲呆呆地立在寒风里,任凭江风吹散了头发。他看见,母亲撩起衣襟拭泪。
掌灯时分,他随父亲再次过河,直接去校长家里。校长一家刚刚吃过晚饭,碗碟还在桌上。
校长站起身,望望父子俩,也没有招呼个座儿。父亲就僵立在那里,双手不知所措地垂着,脸上堆着笑,比哭还难看,额头上冒出了汗。
“你家里早上不是来过学校吗?”校长凝视着他,先开了口。
“是的……不是。”父亲点点头,又摇摇头,有点语无伦次。“这不,我白天在湖里搞了几条鳑鲏,晚上给校长送过来尝尝鲜。”
“这怎么使得?”校长将眼光转向父亲,不无诚心地拒绝道。
父亲听校长这话,心里更慌了。他向校长赔着笑说道:“我们打鱼的都说,鱼上半
斤,各有其主。这鳑鲏上半斤的可不多见,我寻思着,只有校长你能消受得起。”说完,从孩子的手里拿过装有鳑鲏的网兜,放在地上,拉着孩子就要离去。孩子知道,舅舅只教了父亲这几句话,再待下去,父亲真的就是磨子也压不出一个屁来了。
校长见状,拦住父子二人:“等等。”进到房间,出来对他父亲道:“这是五毛钱,你收下,给孩子买点文具,你若不收,就把鳑鲏带走,明天孩子也不要来学校了。”
父子俩默默地走在黢黑的老街上,风比白天更大也更冷了,两人心里却暖洋洋的。
中师毕业时,他以品学兼优、厚道持重被学校看中,拟请他留校任教。他却谢绝了母校的诚意,执意来到鸡公山小学。鸡公山,在青通河畔,距河南嘴不到五华里。渔业公社与天斗、与地斗,沿河围水成湖,是为白荡湖。于是,他的父老和部分水上漂的乡亲,上岸定居于此,白天下湖从事渔业生产,晚上脚后蹬妻从事人口生产。于是便有了这座小学。这所学校是他家园的一部分。
开学的第一顿晚餐,他发现餐桌上多了兩道菜,一道是红烧仔鸡,一道是清蒸江鲜——两条足有半斤以上的鳑鲏。父亲仍然是沉默寡言,提来一壶温好的老酒,脸上如沐浴过春风,漾出笑的涟漪。他一直以为父亲不会笑,可这会子,父亲的微笑,分明发自内心。
如今,鸡公山还在,白荡湖还在,青通河也还在。他曾经的家园和学校已经成为遗迹留在鸡公山,那段平凡美好的岁月已成为记忆留在他的脑海里。偶尔,他会披荆斩棘,于荒芜丛生中寻觅过往的蛛丝马迹。他靠在冰冷庞大的高铁墩墙上,头顶,高铁呼啸而过。远处,水桥湖高速枢纽上,南来北往的车辆川流不息,蓝天上,白云悠悠。他不禁喟然,这个世界变化太快,许多曾经的家园,在不经意间,就变得城春草木深了。
7
拼命吃河豚,是江南流行的一句俗语。究其来历,纷纭不一,多则附会到苏大学士头上,大约是因了东坡先生擅美食,又有“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之诗句的缘故吧。河豚有毒,烹饪不当会有性命之虞。但是,其鲜美的味道,实在让人难以拒绝,为此而丢了性命的,常见于报端。
不过,在河南嘴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他们这些渔民,视河豚如牛溲马勃,偶尔捕到几条河豚,随手放归江河。不是他们不喜欢吃,也不是他们不会吃,而是河豚烧起来要耗费许多工夫,会耽误他们赶鱼汛。只有在鱼汛过了,闲暇时,他们才可能烹一回河豚。别看他们这些渔民剖杀、清洗、烹饪河豚的手艺只是口口相传的江湖知识,它的安全性绝对是穿钉鞋戳拐棍般牢靠。
他,矮矮胖胖的,一双圆溜溜的眼睛,有几分呆萌,像极了河豚的双眼。平时,有事无事总爱弄一条河豚在手里玩,同伴们便送了他一个“河豚”的雅号。“河豚”有一玩伴,长相正与他相左,单薄苗条,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被同伴唤作“刨花鱼”。二人一向交好,“刨花鱼”经常用一串五香蚕豆,跟“河豚”交换河豚。得手之后,“刨花鱼”便将河豚左拍右拍,让其白白的腹部鼓成一个小小的皮球,然后,用一截麦秸插入其魄门,再将它放入水中。刚入水的河豚,紧闭双眼,一动不动装死,浮在水上,像个大鱼鳔。少顷,缓缓张开那双萌眼,确认安然了,迅速翻身,潜入水中,在身后留下一串长长的气泡。气泡渐渐没了,五香蚕豆也没了,这种交易显然是公平的,二人对视,发出咯咯咯的笑声。
“河豚”,不痴不呆,却天生不是读书的料,只长身体不长课业,与“刨花鱼”同一天入学,人家上初中了,他还留在三年级。好不容易度日如年般地熬完六年级,家人让他上初中,他将脖子一伸,说让家人把他勒死算了。辍学后,像尾放生的河豚,悠然潜入水中,整天出没于江河湖泊,与青草鲢鳙、虾豚蟹鳖周旋,自称是“敢下五洋捉鳖”——这大约是他在课堂上学会的唯一的一句文辞。
凭着一个敢字,他开始倒腾一些小鱼小虾,进而倒腾江鲜水产,名声渐起,有些酒楼就跟他签订长年的供货生意。酒楼跑多了,他觉着开酒楼是个赚钱的行当,便在小城里赁下一爿门脸,挂出江鲜酒楼的杏帘,自己当起了老板。他本就对江鲜了如指掌,加上他潜心收集揣摩河南嘴上烹制江鲜的土法子,悉心请教河豚烹饪的关门过节要领,两年不到的工夫,他的酒楼就做得风生水起,门庭若市。
那日,那位总角之交、人称“刨花鱼”的少时玩伴来到他落成不久的六层楼的河豚大酒店,享用他亲自下厨烹制的河豚炖莴笋后,手拊他的肩背,不无感慨地说:“我早就知道你这尾‘河豚不是牛溲马勃,败鼓之皮,这不,终于发达了,再也不是那个吴下阿蒙了”。
8
火车到南宁站已是日落时分,他和他的“末代渔民”同胞们在这趟绿皮车上差不多度过了整整一天一夜。
顾不得一路劳顿,他们各人驮起行李和行头,木木地随人流出站。站前,事先赁好的大巴正在等候他们,他们要再花两个多小时,连夜赶到武鸣。他们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舞龙团队,会聚到此,共襄群龙争霸之盛事,角逐山花大奖。
河南嘴有一年一度的“鱼龙盛会”,旨在祈福渔业丰收,祈求生意兴隆。鱼龙灯采用明灯彩绘,由众多壮汉擎舞,或穿街,或踏浪,精彩非凡,扣人心弦。鱼龙会上的龙灯有别于民间常见的龙灯,龙的造型一律是“闭眼龙”,忌睁眼睛。来武鸣参赛的队伍,就是从河南嘴这些老把式中遴选出来的。
初春的武鸣,已然是草长莺飞,山花烂漫,只是景色这会儿被浓密的夜幕笼罩着,宛如新娘子顶着盖头。
夜幕遮不住他们的欣喜。这种欣喜,不完全因为此行不同于過往的江上漂泊,有着非常明确的目的性,而更多的则是源自他们作为一个群体被看重。尽管他们腿上的水锈尚未完全褪去,可毕竟已经弃舟登岸,行走在大地上,望见了与水天一色、渔舟唱晚完全不一样的风景。
其实,他们一行,除了文联带队的那位小老头子,没有一个人晓得这山花奖是个什么东西,自然不会为之倾心或者烦心。一路上,他们不谈山花奖,甚至连舞龙也绝少提到。到武鸣落脚后,立马找了家快要打烊的小酒馆,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大声吆喝着。文联那位小老头,颓然其间,心头那点关于山花奖的焦虑,早就被这吆喝声赶到爪哇国去了,醉意渐渐爬上脸颊。众人酒酣时,小老头停箸,拿微醺的双眼瞧着坐在对面的一位壮汉——他没喝酒,也没吆喝,一直埋着头吃饭。当他吃完第九碗,抬头正撞见小老头的眼光,讷讷地笑了,随即,把目光转向面前的饭碗,那意思似在解释:这碗实在太小了。他们吃饱喝足,踏着碎月,回到房间,倒在床上,呼呼大睡。
古人云:介子推不言禄,禄亦弗及。大赛放榜,他们紧随孙山之后。
回程的列车上,他们仍旧谈笑风生,那情形一点也不逊于那些得了奖项的。只有文联的小老头颇有不甘。他们便围拢过来,给他递烟点火,为他提壶续水。
“惜乎惜哉!要是我们的着装能够整齐一点,再有点特色,还有鱼龙眼睛不是闭的,也许我们就中了。”他们听了,不以为然,憨憨地笑笑,看不出半点的遗憾。
列车行进在西南的崇山峻岭中,山谷间回荡着列车的呼啸声,还有这帮汉子粗犷的说笑声。
9
村里的人家年前都搬走了,搬到一个叫民福家园的大社区去了,那里有好几幢楼,安置的都是从河南嘴上岸的渔民。
他和他的儿女们各自在民福家园分到一套住宅,儿女们随村里人早就搬过去了,他却守在河南嘴,像一株盘根错节的老柳树,岿然不动。
青通河上通往河南嘴的渡口早就停渡了。社区的两位干部从上游青通河大桥绕过来,已近正午,阳光洒在灰白的芦花上,有点耀眼。一缕炊烟从芦花荡那边的树林中袅袅升腾,快到炊烟升起的地方,三五架扁豆花繁叶茂,架下四周是一丛丛半人高的辣蓼,花穗正红。
一曲二黄散板行云流水般地从扁豆花架后飘过来,二人驻足细听,正是京剧 《锁麟囊》,唱腔幽怨婉转、低回曲折:
想当年我也曾绮装衣锦,到今朝只落得破衣旧裙。在此间,遇水患痛苦受尽,我只得,收余恨,免娇嗔,且自新,改性情,休恋逝水,振作精神,早悟兰因……
二人本不谙京剧,只是每次过来动员这棵老柳树搬迁时,总能听到这本 《锁麟囊》。而且,每回来时,老柳树不听完一段戏,谁的话也听不进去。
二人循声进到老柳树的厨房里,他正在那里一边听戏,一边给灶下添柴。见到二人,他递过一眼,算是招呼了,继续听他的戏,烧他的锅,把二人晾在一边。
一折戏终了。他往锅里加了点水,到灶下添了把柴,转身关掉录音机。开口道:“你们又来啦,我可没有为你们备饭哪。”
“我们是来看你的,没有打算揩你的油。”二人自己往自己带来的茶杯里续了水,掏出香烟递给他一根:“儿子女儿送节的好烟吃完了吧?吃我一根差烟。”
“我可是吃了人家嘴不软的,”老柳树接过烟,自己点上,“甭想用一根烟就叫我答应你们。”
二人知道他说的是玩笑话,也是真话。
三十多年前,他的内人,撇下一双儿女,在一个薄雾蒙蒙的清晨,像一条鮰鱼,从青通河游走,就再没有了讯息。有人说在芜湖看到过一个人像她,也有人说在南京,还有人说在武汉。其实,老柳树心里清楚,她肯定是去了上海。她曾对他提到过一个人,那人曾拜她父亲为师学习京戏,与她是师兄妹。后来,她父亲进了班房、戏班子散了,那人就辗转到上海,凭借一手娴熟的京胡,在那里立身。他从她讲述时的眼神里,分明瞧得出她埋在心里的依恋与无奈。
三十年来,他最怕听到的就是京戏,尤其是 《锁麟囊》。那曾是她得到父亲嫡传、最为拿手的一出戏。她素面下船,坐在如豆灯下,清唱一段,凄婉哀怨,每每直抵心尖,让他黯然销魂,长吁短叹。
直到几年前,听到渔民上岸、河南嘴要整体迁移的消息后,他一反常态地让儿子弄来录音机,买回十几本京剧磁带,还特别叮嘱,要程砚秋的 《锁麟囊》。他足足用了三十年的光阴消解了对她的怨恨,甚至理解了她的苦衷——昔日班主的女儿嫁给他,毕竟也是迫不得已。
不过,他信守着一日夫妻百日恩的老话,笃定她会回到河南嘴,这里曾经是她的家。假若有朝一日,她洄游到青通河,他不想因为村庄的搬迁、他的离去,而让她找不到回家的路。
责任编辑 晓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