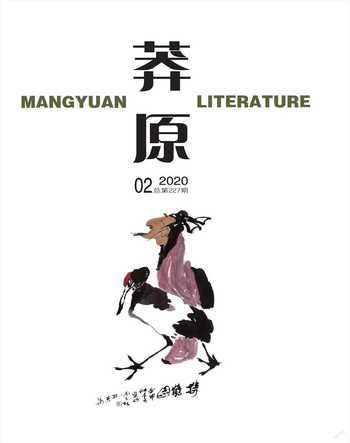将军族
陈映真
在十二月里,这真是个好天气。特别在出殡的日子,太阳那么绚灿地普照着,使丧家的人们也蒙上了一层隐秘的喜气了。有一支中音的萨士风在轻轻地吹奏着很东洋风的《荒城之月》。它听来感伤,但也和这天气一样地,有一种浪漫的悦乐之感。他为高个子修好了伸缩管,瘪起嘴将喇叭朝地下试吹了三个音,于是抬起来对着大街很富于温情地和着《荒城之月》。然后他忽然地停住了,他只吹了三个音。他睁大了本来细眯着的眼,他便这样地在伸缩的方向看见了伊。
高个子伸着手,将伸缩管喇叭接了去。高个子说:“行了,行了。谢谢,谢谢。”
这样地说着,高个子若有所思地将喇叭夹在腋下,一手掏出一支皱得像蚯蚓一般的烟伸到他的眼前,差一点碰到了他的鼻子。他后退了一步,猛力地摇着头,瘪着嘴做出一个笑容。不过这样的笑容,和他要预备吹奏时的表情,是颇难于区别的。高个子便咬那烟,用手扶直了它,划了一支洋火烧红了一端,哔叽哔叽地抽了起来。他坐在一条长木凳上,心在很异样地悸动着。没有看见伊,已经有了五年了吧。但他却能一眼认出伊来。伊站在阳光里,将身子的重量放在左腿上,让臀部向左边画着十分优美的曼陀铃琴的弧。还是那样的站法呵。然而如今伊变得很婷婷了。很多年前,伊也曾这样地站在他的面前。那时他们都在康乐队里,几乎每天都在大卡车的颠簸中到处表演。
“三角脸,唱个歌好吗!”伊说。声音沙哑,仿佛鸭子。
他猛然地回過头来,看见伊便是那样地站着,抱着一只吉他琴。伊那时又瘦又小,在月光中,尤其显得好笑。
“深夜了,唱什么歌!”
然而伊只顾站着,那样地站着。他拍了拍沙滩,伊便很和顺地坐在他的旁边。月亮在海水上碎成许多闪闪的鱼鳞。
“那么说故事吧。”
“啰唆!”
“说一个就好。”伊说着,脱掉拖鞋,裸着的脚丫子便像蟋蟀似的钉进沙里去。
“十五、六岁了,听什么故事!”
“说一个你们家里的故事。你们大陆上的故事。”
伊仰着头,月光很柔和地敷在伊的干枯的小脸上,使伊的发育得很不好的身体,看来又笨又拙。他摸了摸他的已经开始有些儿脱发的头。他编扯过许多马贼、内战、死刑的故事。不过那并不是用来迷住像伊这样的女子的呵。他看着那些梳着长长的头发的女队员们张着小嘴,听得入神,真是赏心乐事。然而,除了听故事,伊们总是跟年轻的乐师泡着。这使他寂寞得很。乐师们常常这样地说:
“我们的三角脸,才真是柳下惠哩!”
而他便总是笑笑,红着那张确乎有些三角形的脸。
他接过吉他琴,撩拨了一组和弦。琴声在夜空中铮着。
渔火在极远的地方又明又灭。他正苦于怀乡,说什么“家里的”故事呢?
“讲一个故事。讲一个猴子的故事。”他说,太息着。
他于是想起了一个故事。那是写在一本日本的小画册上的故事。在沦陷给日本的东北,他的姊姊曾说给他听过。他只看着五彩的小插画,一个猴子被卖给马戏团,备尝辛酸,历经苦楚,有一个月圆的夜,猴子想起了森林里的老家,想起了爸爸、妈妈、哥哥、姊姊……
伊坐在那里,抱着曲着的腿,很安静地哭着。他慌了起来,嗫嚅地说:
“开玩笑,怎么的了?”
伊站了起来。瘦楞楞的,仿佛一具着衣的骷髅。伊站了一会儿,逐渐地把重心放在左腿上,就是那样。
就是那样的。然而,于今伊却穿着一套稍嫌小了一些的制服。深蓝的底子,到处镶滚着金黄的花纹。十二月的阳光浴着伊,使那怵目得很的蓝色,看来柔和了些。伊的太阳眼镜的脸,比起往时要丰腴了许多。伊正专心地注视着天空中画着椭圆的鸽子们。一支红旗在向它们招摇。他原也可走进阳光里,叫伊:
“小瘦丫头儿!”
而伊也会用伊的有些沙哑的嗓门叫起来的吧。但他只是坐在那儿,望着伊。伊再也不是个“小瘦丫头儿”了。他觉得自己果然已在苍老着,像旧了的鼓,缀缀补补了的铜号那样,又丑陋、又凄凉。在康乐队里的那么些年,他才逐渐接近四十。然而一年一年地过着,倒也尚不识老去的滋味的。不知道那些女孩儿们和乐师们,都早已把他当作叔伯之辈了。然而他还只是笑笑。不是不服老,却是因着心身两面,一直都是放浪如素的缘故。他真正开始觉得老,还正是那个晚上呢。
记得很清楚:那时对着那样地站着的、并且那样轻轻地淌泪的伊,始而惶惑,继而怜惜,终而油然产生了一种老迈的心情。想起来,他是从未有过这样的感觉的。从那个霎时起,他的心才改变成为一个有了年纪的人的心了。这样的心情,便立刻使他稳重自在。他接着说:
“开玩笑,这是怎么的了,小瘦丫头儿!”
伊没有回答。伊努力地抑压着,也终于没有了哭声。月亮真是美丽,那样静悄悄地照着长长的沙滩、碉堡和几栋营房,叫人实在弄不明白:何以造物主要将这么美好的时刻,秘密地在阒无一人的夜更里展露呢?他捡起吉他琴,任意地拨了几个和弦。他小心地、讨好地、轻轻地唱着:
王老七,养小鸡,叽咯叽咯叽……
伊便不由地笑了起来。伊转过身来,用一只无肉的腿,向他轻轻地踢起一片细沙。伊忽然地又一个转身,擤了很多的鼻涕。他的心因着伊的活泼,像午后的花朵儿那样绽然地盛开起来。他唱着:
王老七……
伊揩好了鼻涕,盘腿坐在他的面前。伊说:
“有烟么?”
他赶忙搜了搜口袋,递过一支雪白的纸烟,为伊点上火。
打火机发着殷红的火光,照着伊的鼻端。头一次他发现伊有一只很好的鼻子,瘦削、结实且因留着一些鼻水,仿佛有些凉意。伊深深地吸了一口,低下头,用夹住烟的右手支着额,左手在沙地上歪歪斜斜地画着许多小圆圈。伊说:
“三角脸,我讲个事情你听。”
说着,白白的烟从伊的低着的头,袅袅地飘了上来。他说:
“好呀,好呀。”
“哭一哭,好多了。”
“我讲的是猴子,又不是你。”
“差不多——”
“哦,你是猴子啦,小瘦丫头儿!”
“差不多。月亮也差不多。”
“嗯。”
“唉,唉!这月亮。我一吃饱饭就不对。原来月亮大了,我又想家了。”
“像我吧,连家都没有呢。”
“有家。有家是有家啦,有什么用呢?”
伊說着,以臀部为轴,转了一个半圆。伊对着那黄得发红的大月亮慢慢地抽着纸烟。烟烧得“丝丝”作响。伊掠了掠伊的头发,忽然说:
“三角脸。”
“呵。”他说,“夜深了,少胡思乱想。我何尝不想家吗?”
他于是站了起来。他用衣袖擦了擦吉他琴上的夜露,一根根放松了琴弦。伊依旧坐着,很小心地抽着一截烟屁股,然后一弹,一条火红的细弧在沙地上碎成万点星火。
“我想家,也恨家里。”伊说,“你会这样吗?——你不会。”
“小瘦丫头儿,”他说,将琴的胴体抬在肩上,仿佛扛着一支枪。他说:“小瘦丫头儿,过去的事,想它做什么?我要像你:想,想!那我一天也不要活了!”
伊霍然地站立起来,拍着身上的沙粒。伊张着嘴巴打起哈欠来。眨了眨眼,伊看着他,低声地说:
“三角脸,你事情见得多。”伊停了一下,说:“可是你是断断不知道:一个人卖出去,是什么滋味。”
“我知道。”他猛然地说,睁大了眼睛。伊看着他的微秃的,果然有些儿三角形的脸,不禁笑了起来。
“就好像我们乡下的猪、牛那样地被卖掉了。两万五,卖给他两年。”伊说。
伊将手插进口袋里,耸起板板的小肩膀,背向着他,又逐渐地把重心移到左腿上。伊的右腿便在那里轻轻地踢着沙子,仿佛一只小马儿。
“带走的那一天,我一滴眼泪也没有。我娘躲在房里哭,哭得好响,故意让我听到。我就是一滴眼泪也没有。哼!”
“小瘦丫头儿!”他低声说。
伊转身望着他,看见他的脸很忧戚地歪扭着,伊便笑了起来:
“三角脸,你知道!你知道个屁呢!”
说着,伊又弓着身子,擤了一把鼻涕。伊说:
“夜深了。睡觉了。”
他们于是向招待所走去。月光照着很滑稽的人影,也照着两行孤独的脚印。伊将手伸进他的臂弯里,瞌睡地张大嘴打着哈欠。他的臂弯感觉到伊的很瘦小的胸。但他的心却充满另外一种温暖。临分手的时候,他说:
“要是那时我走了之后,老婆有了女儿,大约也就是你这个年纪吧。”
伊扮了一个鬼脸,蹒跚地走向女队员的房间去。月在东方斜着,分外地圆了。
锣鼓队开始作业了。密密的脆皮鼓伴着撼人的铜锣,逐渐使这静谧的午后扰骚了起来。他拉低了帽子,站立起来。他看见伊的左手一晃,在右腋里夹住一根银光闪烁的指挥棒。指挥棒的小铜球也随着那样一晃,有如马嘶一般地轻响起来。伊还是个指挥的呢!
许多也是穿着蓝制服的少女乐手们都集合拢了。伊们开始吹奏着把节拍拉慢了一倍的 《马撒永眠黄泉下》 的曲子。曲子在震耳欲聋的锣鼓声的夹缝里,悠然地飞扬着,混合着时歇时起的孝子贤孙们的哭声,和这么绚灿的阳光交织起来,便构成了人生、人死的喜剧了。他们的乐队也合拢了,于是像凑热闹似的,也随而吹奏起来了。高个子神气地伸缩着他的管乐器,很富于情感地吹着 《游子吟》。也是将节拍拉长了一倍,仿佛什么曲子都能当安魂曲似的——只要拉慢节拍子,全行的。他把小喇叭凑在嘴上,然而他并不在真吹。他只是做着样子罢了。他看着伊颇为神气地指挥着,金黄的流苏随着棒子风舞着。不一会儿他便发觉了伊的指挥和乐声相差约有半拍。他这才记得伊是个轻度的音盲。
是的,伊是个音盲。所以伊在康乐队里,并不曾是个歌手。可是伊能跳很好的舞,而且也是个很好的女小丑,用一个红漆的破乒乓球,盖住伊唯一美丽的地方——鼻子,瘦板板地站在台上,于是台下卷起一片笑声。伊于是又眨了眨木然的眼,台下便又是一阵笑谑。伊在台上固然不唱歌,在台下也难得开口唱的。然而一旦不幸伊一下高兴起来,伊要咿咿呀呀地唱上好几个小时,把一支好好的歌,唱得支离破碎,喑哑不成曲调。
有一个早晨,伊突然轻轻地唱起一支歌来。继而一支接着一支,唱得十分起劲。他在隔壁的房间修着乐器,无可奈何地听着那么折磨人的歌声。伊唱着:
这绿岛像一只船,
在月夜里漂呀漂……
唱过一遍,停了一会儿,便又从头唱起。一次比一次温柔,充满情感。忽然间,伊说:
“三角脸!”
他没有回答。伊轻轻地敲了敲三夹板的墙壁,说:
“喂,三角脸!”
“哎!”
“我家离绿岛很近。”
“神经病。”
“我家在台东。”
“……”
“他妈的,好几年没回去了!”
“什么?”
“我好几年没回去了!”
“你还说一句什么?”
伊停了一会儿,忽然吃吃地笑了起来。伊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
“三角脸。”
“啰唆!”
“有没有香烟?”
他站起来,从夹克口袋摸了一根纸烟,抛过三夹板给伊。
他听见划火柴的声音。一缕青烟从伊的房间飘越过来,从他的小窗子飞逸而去。
“买了我的人把我带到花莲。”伊说,吐着嘴唇上的烟丝。
伊接着说:“我说:我卖笑不卖身。他说不行,我便逃了。”
他停住手里的工作,躺在床上。天花板因漏雨而有些发霉了。他轻声说:
“原来你还是个逃犯哩!”
“怎么样?”伊大叫着说,“怎么样?报警去吗?呵?”
他笑了起来。
“早些时候收到家里的信,”伊说,“说为了我的逃走,家里要卖掉那么几小块田赔偿。”
“啊,啊啊。”
“活该,”伊说,“活该,活该!”
他们于是都沉默起来。他坐起身子来,搓着手上的铜锈。
刚修好的小喇叭躺在桌子上,在窗口的光线里静悄悄地闪耀着白色的光。不知道怎样的,他觉得沉重起来。隔了一会儿,伊低声说:
“三角脸。”
他咽了一口气,忙说:
“哎。”
“三角脸,过两天我回家去。”
他细眯着眼望着窗外。忽然睁开眼睛,站立起来,嗫嗫地说:
“小瘦丫头儿!”
他听见伊有些自暴自弃地呻吟了一声,似乎在伸懒腰的样子。伊说:
“田不卖,已经活不好了,田卖了,更活不好了。卖不到我,妹妹就完了。”
他走到桌旁,拿起小喇叭,用衣角擦拭着它。铜管子逐渐发亮了,生着红的、紫的圈圈。他想了想,木然地说:
“小瘦丫头儿。”
“嗯。”
“小瘦丫头儿,听我说:如果有人借钱给你还债,行吗?”
伊沉吟了一会,忽然笑了起来。
“谁借钱给我?”伊说,“两万五咧!谁借给我?你吗?”
他等待伊笑完了,说:
“行吗?”
“行,行。”伊说,敲着三夹板的壁,“行呀!你借给我,我就做你的老婆。”
他的脸红了起来,仿佛伊就在他的面前那样。伊笑得喘不过气来,捺着肚子,扶着床板。伊说:
“别不好意思,三角脸。我知道你在壁板上挖了个小洞,看我睡觉。”
伊于是又爆笑起来。他在隔房里低下头,耳朵胀着猪肝那样的赭色。他无声地说:
“小瘦丫头儿……你不懂得我。”
那一晚,他始终不能成眠。第二天的深夜,他潜入伊的房间,在伊的枕头边留下三万元的存折,悄悄地离队出走了。
一路上,他明明知道绝不是心疼着那些退伍金的,却不知道为什么止不住地流着眼泪。
几支曲子吹过去了。现在伊又站到阳光里。伊轻轻地脱下制帽,从袖卷中拉出手绢揩着脸,然后扶了扶太阳镜,有些许傲然地环视着几个围观的人。高个子挨近他,用痒痒的声音说:
“看看那指挥的,很挺的一个女的呀!”
说着,便歪着嘴,挖着鼻子。他没有作声,而终于很轻地笑了笑。但即便是这样轻的笑脸,都皱起满脸的皱纹来。伊留着一头乌油油的头发,高高地梳着一个小髻。脸上多长了肉,把伊的本来便很好的鼻子,衬托得尤其精神了。他想着:一个生长,一个枯萎,才不过是五年先后的事!空气逐渐有些温热起来。鸽子们停在相对峙的三个屋顶上,凭那个养鸽的怎么样摇着红旗,都不起飞了。它们只是斜着头,愣愣地看着旗子,又拍了拍翅膀,而依旧只是依偎着停在那里。
纸钱的灰在离地不高的地方打着卷、飞扬着。他站在那儿,忽然看见伊面向着他。从那张戴着太阳镜的脸,他很难于确定伊是否看见了他。他有些张皇起来,手也有些哆嗦了。他看着伊也木然地站在那里,张着嘴。然后他看见伊向这边走来。
他低下头,紧紧地抱着喇叭。
他感觉到一个蓝色的影子挨近他,迟疑了一会儿,便同他并立着靠在墙上。他的眼睛有些发热了,然而他只是低弯着头。
“请问——”伊说。
“……”
“是你吗?”伊说,“是你吗?三角脸,是……”伊哽咽起来:“是你,是你。”
他听着伊哽咽的声音,便忽然沉着起来,就像海滩上的那夜一般。他低声说:
“小瘦丫頭儿,你这傻小瘦丫头儿!”
他抬起头来,看见伊用绢子捂着鼻子、嘴。他看见伊那样地抑住自己,便知道伊果然地成长了。伊望着他,笑着。他没有看见这样的笑,怕也有数十年了。那年打完仗回到家,他的母亲便曾类似这样地笑过。忽然一阵振翼之声响起,鸽子们又飞翔起来了,斜斜地划着圈子。他们都望着那些鸽子,沉默起来,过了一会儿,他说:
“一直在看着你当指挥,神气得很呢!”
伊笑了笑。他看着伊的脸,太阳镜下面沾着一小滴泪珠儿,很精细地闪耀着。他笑着说:
“还是那样好哭吗?”
“好多了。”伊说着,低下了头。
他们又沉默了一会儿,都望着越划越远的鸽子们的圆圈儿。
他夹着喇叭,说:
“我们走,谈谈话。”
他们并着肩走过愕然着的高个子。他说:
“我去了马上来。”
“呵呵。”高个子说。
伊走得很婷婷然,然而他却有些伛偻了。他们走完一栋走廊,走过一家小戏院,一排宿舍,又过了一座小石桥。一片田野迎着他们,很多的麻雀聚栖在高压线上。离开了充满香火和纸灰的气味,他们觉得空气是格外的清新舒爽了。不同的作物将田野涂成不同深浅的绿色的小方块。他们站住了好一会儿,都沉默着。一种从不曾有过的幸福的感觉涨满了他的胸膈。伊忽然地把手伸到他的臂弯里,他们便慢慢地走上一条小坡堤。伊低声地说:
“三角脸。”
“嗯。”
“你老了。”
他摸了摸秃了大半的、尖尖的头,抓着,便笑了起来。他说:
“老了,老了。”
“才不过四、五年。”
“才不过四、五年。可是一个日出,一个日落呀!”
“三角脸——”
“在康乐队里的时候,日子还蛮好呢,”他紧紧地夹着伊的手,另一只手一晃一晃地玩着小喇叭。他接着说:“走了以后,在外头儿混,我才真正懂得一个卖给人的人的滋味。”
他们忽然噤着。他为自己的失言恼怒地瘪着松弛的脸。然而伊依然抱着他的手。伊低下头,看着两只踱着的脚。过了一会儿,伊说:
“三角脸——”
他垂头丧气,沉默不语。
“三角脸,给我一根烟。”伊说。
他为伊点上烟,双双坐了下来。伊吸了一阵,说:
“我终于真找到了你。”
他坐在那儿,搓着双手,想着些什么。他抬起头来,看看伊,轻轻地说:
“找我?找我做什么!”他激动起来了,“还我钱是不是?……我可曾说错了话吗?”
伊从太阳镜里望着他的苦恼的脸,便忽而将自己的制帽盖在他的秃头上。伊端详了一番,便自得其乐地笑了起来。
“不要弄成那样的脸吧!否则你这样子倒真像个将军呢!”
伊说着,扶了扶眼镜。
“我不该说那句话。我老了,我该死。”
“瞎说。我找你,要来赔罪的。”伊又说。
“那天我看到你的银行存折,哭了一整天。他们说我吃了你的亏,你跑掉了。”伊笑了起来,他也笑了。
“我真没料到你是真好的人。”伊说,“那时你老了,找不上别人。我又小又丑,好欺负。三角脸。你不要生气,我当时老防着你呢!”
他的脸很吃力地红了起来。他不是对伊没有过欲情的。他和别的队员一样,一向是个狂嫖滥赌的独身汉。对于这样的人,欲情与美貌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系的。伊接着说:
“我拿了你的钱回家,不料并不能息事。他们又带我到花莲。他们带我去见一个大胖子,大胖子用很尖很细的嗓子问我话。我一听他的口音同你一样,就很高兴。我对他说:‘我卖笑,不卖身。大胖子吃吃地笑了。不久他们弄瞎了我的左眼。”
他抢去伊的太阳镜,看见伊的左眼睑收缩地闭着。伊伸手要回眼镜,四平八稳地又戴了上去。伊说:
“然而我一点也没有怨恨。我早已决定这一生不论怎样也要活下来再见你一面。还钱是其次,我要告诉你我终于领会了。”
“我挣够给他们的数目,又积了三万元。两个月前才加入乐社里,不料就在这儿找到你了。”
“小瘦丫头儿!”他说。
“我说过我要做你老婆,”伊说,笑了一阵:“可惜我的身子已经不干净,不行了。”
“下一辈子吧!”他说,“我这副皮囊比你的还要恶臭不堪的。”
远远地响起了一片喧天的乐声。他看了看表,正是丧家出殡的时候。伊说:
“正对,下一辈子吧。那时我们都像婴儿那么干净。”
他们于是站了起来,沿着坡堤向深处走去。不一会儿,他吹起 《王者进行曲》,吹得兴起,便在堤上踏着正步,左右摇晃。伊大声地笑着,取回制帽戴上,挥舞着银色的指挥棒,走在他的前面,也走着正步。年轻的农夫和村童们在田野向他们招手,向他们欢呼着,两只三只的狗,也在四处吠了起来。
太陽斜了的时候,他们的欢乐影子在长长的坡堤的那边消失了。
第二天早晨,人们在蔗田里发现一对尸首。男女都穿着乐队的制服,双手都交握于胸前。指挥棒和小喇叭很整齐地放置在脚前,闪闪发光,他们看来安详、滑稽,都另有一种滑稽中的威严。一个骑着单车的高大的农夫,于围睹的人群里看过了死尸后,在路上对另一个挑着水肥的矮小的农夫说:
“两个人躺得直挺挺地,规规矩矩,就像两位大将军呢!”
于是高大的和矮小的农夫都笑起来了。
责任编辑 杨雪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