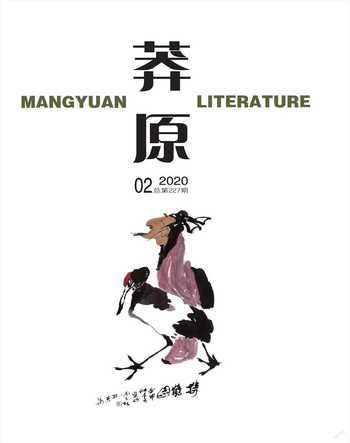吴元成诗选
吴元成
蝉蜕记
在地下待了两年还是三年
我已经记不清了
今晚,决意要挖个洞,钻出去
我听见兄弟姐妹们在喊
“死呀死呀”
不就是一死嘛
死也要在死之前喊一声
死呀
为了出去透口气
为了在高枝上发声
我拱开最后一粒细沙
洞开了一个从未见过的世界
一道道的白光在我眼前晃动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只听见
为死亡伴奏的风声
流水声,还有垂涎三尺的人声
我看见无数的树干
无数比树干还粗壮的腿
人的腿,从我头顶上跨过
踩塌了我刚刚爬出来的洞口
我确认我找到了树
在地下,我啃咬过它的根
吸吮过它的汁液
我熟悉它的气味
它是垂直的,粗砺的
每一条褶皱
都是通向高处的康庄大道啊
我只有一个心思
向上,向上
不是在和生命赛跑
我是在加速爬向死亡
兄弟姐妹们
正在放声高歌:“死呀死呀”
难道我们生来就是歌唱死亡的吗
绕过一道树疤
又是一道断茬
翻过断茬,又是一个枝杈
通向死亡的道路
也这么崎岖
我有点儿后悔了
可后悔有什么用呢
我听见人们追捕的呐喊
“这儿有一只!”
“这里也有!”
我可不能让人逮住
我得赶紧往上爬
一片树叶挡住了去路
树叶边缘悬挂着我的兄弟
我左爬右爬
就是绕不过它
我说,伙计,让道啊
它动了一下
土黄色的脊背裂开一道缝
慢慢蜕去了的外壳
背部伸出了两片透亮的翅膀
我会不会也像它一样撕裂
那该是怎样的疼痛啊
刹那间,它的
翅膀忽闪了几下,竟然
嗡的一声向上飞去
留下一个干硬的外壳
在风中摇曳
一道白光射来
两只手指捏住了我的脖颈
“咕咚”一声
我跌进了水桶里
我知道
我的死亡之路
已走到尽头
鹌鹑的眼泪
不知道是先有鹌鹑
还是先有鹌鹑蛋
我只看到铁锅里
鹅卵石泛着油光
还有厚厚的雪一样的盐
布满麻点儿的鹌鹑蛋
堆积在一起
胖女人一遍遍吆喝叫卖
我相信鹌鹑会飞
会下蛋,从来不曾想过
是先有鹌鹑
还是先有鹌鹑蛋
鹌鹑在交配时
交颈而拥,翻身而上
快活地叫一声
带着一丝自豪
它们想不到自己的蛋
来不及孵化
就被从窝里掏走
被放在盐焗的铁锅里
几番蒸烤,几番煎熬
胖女人还在吆喝
纯天然,滋肾壮阳
我没有见过鹌鹑流泪
如果它们哭泣
那浑浊的泪滴
也应该是像鹌鹑蛋一样饱满
且微咸
邻 居
夹竹桃睁开眼睛,看
不开花的石楠,龟背竹和
开花的凌霄,紫薇
刺楸拿锥子刺午后的阴云
它们的邻居是一小片翠竹
我紧挨着它们
像一棵流氓樹
不开花,不结果
只做,只爱
做错误或正确的事情
做一个正经的人
暴雨之后
雨还在下,虽然已经小了
窨井盖喝饱了往外吐
小区门口,小孩撑伞
趟过小腿肚高的泥浪
退回去五十年,我也如此
在嘉庆年间的路碑下
踢掉脚趾甲盖
雨水顺着老屋的皱褶下流
终于风停雨住
人行道上的楸树
被洗得更像是一棵树了
手机在枕旁响
提包放在门前高坡上
到洼地里小解
邻村的几个娃子放学归来
在地头搬弄柴捆
父亲带人在砌墙
猛听见一阵马达轰鸣
邻村娃子从坡顶垂下吊车的挂钩
试图钓走我的提包
我认得领头的,大叫一声
老表,弄啥哩?
他跑上来,脸上红红的
不知道是你的啊
好像我做了错事,连忙解释
里边就几页打印稿,没啥东西
我知道手机也在里边
但只有几页打印稿,字迹模糊
打开茅台的N种方式
首先,你要抽出一条红丝带
拧开红日普照的瓶盖
然后,晃一晃,摇一摇
听见珠子滚动
酒在里边唱
喝我,和我一起醉
看颜色微黄
酒液微黏,挂壁而下
你就可以说,开喝
第一杯,不能快
要在唇齿间品味三到五秒
这是最短的时间了
酒神与你的舌尖和喉咙
喁喁细语
第二杯要快
否则,你喝不到第三杯
谁愿意看着别人把美酒饮尽
三杯下肚,可谈诗,可作赋
可乡情,可亲情
可禅,可道,可儒
只是别忘了
为什么追寻酒神的脚步
它疗过肉体之伤
慰藉心灵之痛
你哭,你歌
就等着它说
醉吧,醉吧
从赤水到黄河
都在酒杯里
三山五岳
都身姿摇曳,口吐莲花
你话已稠,脸已红
说人生不易
不知身在何处
唯酒知己
酒瓶亦已空
你作揖抱拳
且别去
待来日共醉
责任编辑 伊 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