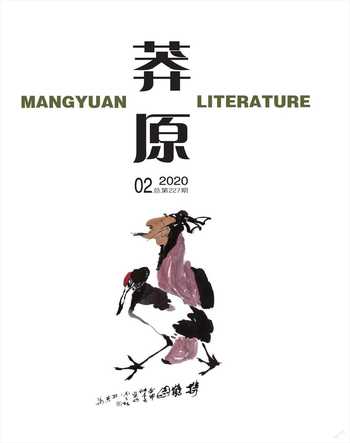宝儿
张洁方
白光的肚子扣了个瓷碗
毒日头逼着宝儿脱衣裳,宝儿就抬手解扣子,从上至下,解了一个,又解了一个,挨住第三个,扣子不出扣眼。宝儿抠掐半天,也解不开,急了,用手揪,仍然揪不开,就脖儿一缩,两手抓住衣领,蝉蜕般从衣裳里钻出来。两只奶子弹跳了两下,挂在前怀不动了。白光的肚子凸出来,像扣了个瓷碗。
宝儿娘弯腰割麦,抬头见了,狼掐住喉咙般嚎:丢人鬼吔,亮膘哩?快把衣裳穿上!
宝儿揪揪奶头,嘿嘿地笑。
听见没有?声音更尖了。
宝儿摸摸肚子,还是嘿嘿地笑。
宝儿娘的喝斥带着响哨,传到正在捆麦的宝儿爹耳朵里。宝儿爹看见了,像被日头剜了眼,急急扭回头,吼声甩过来:给我打!
宝儿娘就扬起了巴掌。宝儿不笑了,撑起衬衫,头钻进去,衬衫拥到脖子上,半天扯不下来。宝儿娘扔了镰,绕过几个麦铺子,走到宝儿跟前,前一拽,后一拽,弹跳的奶子和瓷白的肚子不见了。
十丈开外的宝儿爹,一屁股坐到麦铺上,长长地叹了一声气,粗重,沉闷。
屁股下的麦铺子,辨出宝儿爹叹出的两股味道:一股是叹他咋要了个憨憨傻傻的闺女;一股是闺女咋干下这憨憨傻傻的事。
才十七呀!
他发现宝儿肚子鼓起来时,仰天发一声吼,弯腰脱了鞋,紧紧攥着鞋底子,喝问:说,跟谁?
宝儿不说跟谁,只嘿嘿地笑。
一鞋底抡到宝儿屁股上。宝儿不笑了,哇哇地哭。
娘心疼闺女,急忙护着,说,她知道跟谁,就不是憨憨了……
宝儿爹把鞋撂到地下,鞋底朝上。他踢一脚,鞋面翻过来,将黑脏的脚向鞋窝里一擩,来不及勾起后跟,趿拉着,燎燎燥燥上了自家房顶,吼起来:哪个杂种羔子,干下这伤天害理的事啊!
吼声近似驴叫,却没有驴叫的抑扬顿挫,像是砸夯一样,一个字摞着一个字砸向人们的耳朵。村子不大,前后左右也就十几户人家,还有三四家锁了门,门前的荒草有半人深。荒草不理會他的吼叫,自顾疯疯地长。家里有人的,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纷纷走出来,探头向他家房顶上张望。
哪个杂种羔子,干下这伤天害理的事?有种站出来,别当缩头乌龟!
人们没有从他的吼骂中听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只见他气急败坏的样子,眉眼鼻子都歪了,都不言语,呆呆地站着,仿佛一根根木桩。
宝儿娘跌跌撞撞爬上房顶,扯一下他的胳膊,小声说:家丑不可外扬,你吆喝啥嘛!
宝儿娘的话,不但没有阻止他,反而像泼了一瓢油,把他的火浇得更旺了。他甩一下胳膊,声嘶力竭地吼:
这算啥家丑?是我宝儿偷情养汉了?这分明是哪个杂种欺负宝儿是憨憨嘛!狗日的,干下这伤天害理的事,也不怕上山摔死,过河淹死!
人们听出点眉目,便纷纷往宝儿家的院子涌。宝儿见来了这么多人,便嘻嘻嘿嘿地笑,把衣襟一撩一撩。人们这才注意到,宝儿的肚子有点鼓。
人们都愤怒了,跟着宝儿爹一起骂。骂了一阵,把问题的焦点集中到“哪个杂种干的”上。女人的目光在男人脸上逡巡,男人的目光在另一个男的脸上逡巡。可是,有什么好逡巡的呢?村里五十岁以下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去了,五六十岁、七八十岁的,不是给宝儿应叔,就是给宝儿应爷,断不会干出这畜生一样的事。再说,也没有干那事的本事了。即便干了,也不会把宝儿的肚子干起来啊。只有铁拐李三十多岁,光棍一条,在家种香菇;还有个豁子李,快四十了,也是光棍一条,在家放羊。人们就在人群里寻这两个人,却一个也不在。
告他鳖孙!有人这样说。
告谁?有人问。
能跑了他!有人说。
跑不了他!又有人说。
告鸭子不下鸡蛋?你看见啦?还是按住人家沟子啦?有人这样说。
人们叹声气,摇摇头,慢慢退出宝儿家的院子。临走,都没忘记往宝儿的肚皮瞄上一眼。
告鸭子不下鸡蛋——这话,活脱脱就是把锥子,扎到宝儿爹的心上,把一肚子的怒气全放了,瘫坐到房顶,不知该把这事怎样收到篮子里。
宝儿娘坐在门槛上,望望宝儿的肚子,一边呜呜嘤嘤地哭,一边诉说命苦。不知是叹宝儿命苦,还是叹她自己命苦,抑或是叹一家人命苦。
宝儿命苦,是先天的;宝儿娘命苦,是后天的;她把她一家命苦,归到了穷字上。她不是罗圈洼人,住在罗圈洼十里开外的三道壕。她男人姓徐,叫徐旺才。两口子结婚第二年,就有了个男娃。他们给娃起名叫徐有福。那时,虽然计划生育,但允许间隔四年生二胎。有福八岁了,那个小小的环,还在她那里边套着。不是她不想取,是不敢取。她怕取了,再生个男娃咋办?熊耳山穷啊,山是穷山,水是穷水,没啥出产,地里打把粮食,能轱辘圆肚子算不错了。要再生个男娃,从生草落地就开始熬煎媳妇的事,脚抠肚攒,攒到娃大了,也攒不来一个媳妇。熊耳山里有三多:树木多,石头多,光棍多。随便哪个村,没有十个八个光棍?
有福长到十三岁,旺才说,娃学习成绩不赖,奖状贴了一屋,将来是上大学的料,咱得抓紧多挣俩钱,供娃上大学。说了这话,他上秦岭背矿石,不料一脚踩空跌下山崖,摔死了。三十四岁的她,哭着埋了丈夫,守了两年寡,经人说合,嫁给罗圈洼四十岁的半老光棍,就是现在的宝儿爹。
光棍好不容易讨个老婆,解馋固然重要,传宗接代更重要。虽说宝儿娘带了个油锤,但这娃倔,就是不改徐姓。宝儿娘面性软,不能叫人家只养活自己的娃吧?一咬牙,就生了宝儿。
宝儿生下来时,粉鼻子粉脸,粉胳膊粉腿,长得桃花骨朵一般。两口子喜欢得嘴咧成了盆,给宝贝闺女起名叫宝儿。可咧着咧着,盆变成了碗,碗拉成线,彻底不咧了——他们发现,宝儿是个憨憨,是个吃饭不知饥饱、睡觉不知颠倒的憨憨。
憨憨就憨憨吧,有啥法呢?谁知火候咋没烧到,总不能掐脖子捏死吧?再说,宝儿爹四十得女,好赖也是自个骨血,仍当宝贝疙瘩养着。
宝儿除了脑子憨,别的地方可不憨。长到十四五岁,身上该凸的凸,该凹的凹,脸油红脂白,如果不是眼珠子痴滞不动,如果不是见人嘻嘻嘿嘿傻笑,没人知道她是憨憨。
方圆左近的年轻人,因拿不出到城里买房的钱,眼看着姑娘们一个挨一个被城市吸走了,不得已,有人就打宝儿主意。他们觉得宝儿憨,不会到城里要房子,这是其一。其二是宝儿的哥哥有福在村里说不来媳妇,招赘进了镇上,成了上门女婿,老两口肯定要给宝儿招个女婿,留在身边养老。如果说十七八的年轻人还有点自尊,临到二十七八、三十七八,憋得嘴脸乌青,浑身起疙瘩,什么自尊都没有了,自然就不会嫌弃宝儿是憨憨了。这些动了心思的人,就央了人,掂了烟酒,上门提亲了。宝儿爹打了四十年光棍,深知光棍的苦,对上门提亲的人,从不甩冷脸,只说一句话:到城里买下房子再来!
妈的,鸡也想和凤凰比!
他们忘了物稀为贵这句话,在别人眼里,宝儿是鸡,在宝儿爹眼里,宝儿就是凤凰。宝儿从小到大,宝儿爹可没有亏欠过她,别的女孩子有的,宝儿也有;别的女孩子穿红戴绿,宝儿也穿红戴绿。尽管宝儿的头常常是娘给梳的,脸是娘给洗的。别的女孩子寻家,张嘴就是城里买房,宝儿寻家,也得到城里要房子。如果不是出了这事,那是没得商量。
碗扣到宝儿肚子上,搅了宝儿爹的梦。他瘫坐到自家房顶上,叹了一阵气,开始抽烟。抽一根,再抽一根,烟雾绕着头,把他的头绕成一盆糨子,直到麦熟,直到“瓷碗”马上就要变成“瓷盆”,脑子里依然是一盆糨子。
他大,咱放口吧。宝儿娘将衣裳给宝儿从脖上扯下来,苫住肚皮,叹着气,来到宝儿爹面前。
宝儿爹掐灭了烟头,长长叹口气,说,放口!
说罢,竟驴一般嚎了一声,滚下两颗浑浊的老泪……
左手扳困换右手
宝儿寻家,不再要求城里的房子了。
最早得到消息的是铁拐李。铁拐李和宝儿家隔道土院墙,他的香菇棚紧挨土墙扎着,有事没事,总一瘸一拐往墙根去,好像那地方永远有摘不完的香菇。
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铁拐李把隔墙听来的话,对他大李根朝说了。李根朝掂着烟酒进了村主任的门,村主任掂着烟酒进了宝儿家的门。
宝儿爹听说是给铁拐李提媒,立马肚子里就生了气。气向下行,变成屁,熏人;气向上行,从嘴里出来,也不好闻。
哼,那个野种!
宝儿爹骂铁拐李野种,实在有点不地道。凭什么说铁拐李是野种呢?只不过不是李根朝的种罢了。
李根朝比宝儿爹大几岁,也是马儿放尽说不来个媳妇的主,三十大几了,仍是光棍一条。别人说不来媳妇,是因为穷。他呢,不光穷,还窝囊,窝囊到大小娃娃踢他一脚,他都不敢还人一拳;有人拧着胳膊,让他跪下喊爷,他不敢喊大。同伴嫌他窝囊,村人嫌他窝囊,他娘他大也嫌他窝囊,常常说:你长手干啥?别人打你,你咋不还手?可任凭怎样开导,他就是不敢还手。像这样没血性的人,哪个女的肯嫁给他?
李根朝三十三岁那年春天的一个早晨,天才灰灰明,他起来放牛,大门一开,一脚踢着个包裹,婴儿的啼哭,把他吓得像狼叼住了腿,大喊大叫。他大他妈从屋里出来,抱起那个包裹,拨开褥子角儿,看清是一个胖乎乎的婴儿,看清婴儿腿间的鸡鸡如蚕蛹般招人喜爱,只是一条腿粗,一条腿细。李家老两口也不管那么多了,跪地上如鸡叨米般给送子观音磕头。李根朝四下望望,并不见送子观音,不过,这丝毫不影响他成了这娃的大。
他给娃起名叫李大侠,只因那几天村上说书,说的是《三侠五义》。这个名字,恐怕寄托了他太多的期望。可是,自李大侠会走后,细腿总是攒不上劲,走路一瘸一拐,除了老师,没人喊他李大侠,都喊他铁拐李。久而久之,他也认为他就叫铁拐李。
李根朝这个老子应的,说称职也称职,说不称职也不称职。称职的是,娃从小上学,五里山路,他天天背进背出。直到娃大了,不再让他接送;直到小学撤到镇上,大侠不再上学。不称职的是,大侠十八九了,仍和他窝在一间屋里,挤在一盘炕上。一夜,大侠和他掏心窝子,说他都十八九了,该娶媳妇了……他也掏心窝子,说,老子银钱不凑手啊……大侠有点上气,说,黑夜睡覺扳橛睡……他开导说,左手扳困换右手……你说,这老子应的!
老子窝囊,并不代表娃子窝囊。可关键是,宝儿爹就是看不惯铁拐李。那年在场里打麦,宝儿爹和李根朝开玩笑,开得有点过火,一柄木杈叉住了他的脊背。他疼得龇牙大骂,回头看竟是铁拐李紧握木杈,眼瞪得像个铜铃。就在那一刻,宝儿爹心里颤了一下,对这个七八岁的娃娃产生了畏惧。他不让有福和铁拐李一块玩,可铁拐李偏偏跟有福好得像亲兄弟。有福招赘离家以后,铁拐李依然到他家院子来,眼里亮着贼光。宝儿爹知道这光为谁放的,就敲鸡骂狗来对付。后来,铁拐李不到他家去了,可宝儿爹总觉得那贼光能隔着墙头照进来。
村主任掂着烟酒来找宝儿爹,宝儿爹马上就明白了村主任意思,他不等村主任开口,就说他怀疑宝儿的肚子和两个人有关:一个是铁拐李,一个是豁子李。村主任说,怀疑归怀疑,你没有按住人家屁股,法院也不能定人家的罪。又说,眼见闺女的肚子藏不住,倒不如趁早嫁人算了……宝儿爹知道村主任说的是谁,脖子一拧:我就是把宝儿垫茅坑,也不嫁他个杂种!
村主任掂起桌上烟酒,气夯夯出门走了。临走,不忘甩一句话给宝儿爹:你狗日以后别求着我!
被老骚狐牴个仰八叉
宰相肚里能撑船,村主任不是宰相,可肚子几句难听话也盛得下。日头一落下,他就忘记了和宝儿爹曾经发生的不愉快,傍晚时分,又进了宝儿家的门。
宝儿爹看到村主任手里提的已不是中午那份烟酒了,他的脸色也就和善了许多。也不全是烟酒的缘故,村主任中午走时撂的那句话,让他心慌了一下午——“你狗日以后别求着我!”能不求着村主任吗?低保,补助,扶贫款,哪一项不得村主任点头?
他叔,啥风把您又吹来啦?宝儿娘脸上堆满了笑。
啥风?西(喜)风!你家宝儿成了香饽饽,我不来中吗?
这话有点打脸。宝儿爹的眉毛拧了一下,把脸上的褶子全拉直了。
村主任并不瞅他的脸,把烟酒往堂桌上一放,说,瞧瞧这礼,李老大就是比李根朝那鳖孙大方!
宝儿爹浑身的肌肉开始抽动,脖子上的青筋疙疙瘩瘩的,像暴出来的老树根。
他的脑袋扑轰一下,又扑轰一下,抬腿就往堂桌那儿走。宝儿娘见了,急伸手拉住他的衣襟,猛一扽,宝儿爹犹如木桩般站住不动了。
李老大是豁子李的大。豁子李嘴唇上的豁子胎里带,就像大坝被水冲了道口子,让门牙和牙床都无遮无拦裸露在外边。由于先天缺陷,媳妇肯定是娶不上的,可李家就这一根独苗,李老大不想断后,就动了换亲的念头。待豁子李长到二十岁时,他妹子也十八岁了。有人来提亲,李老大就放出了换亲的风。山里人都听过《李豁子离婚》,“脸又麻,头又秃,脖子还长个肉嘟噜……”尽管,豁子李没有恁多毛病,但光那张豁嘴,谁见了都会恶心!豁子李亲没换成,他妹子也跟着一个耍猴的外路人跑了。李老大一分彩礼没有见上,连块糖都没吃上,气得天天跳脚大骂。
换亲梦破灭了,豁子李成了实实在在的光棍。同龄人都跑出去打工,他那副尊容怕出门引发恐慌,只能在熊耳山里窝着。晃荡了几年,豁子李已经三十多了,觉得应该干点啥事,正好,上边来了扶贫队,给他弄了几只羊,并在村外帮他盖了羊圈。但他那几只母羊总也怀不上羔,每到夜深人静,村人总能听见羊在圈里撕心裂肺地嚎,声音很恐怖。第二天,有细心的人发现,一只油光白亮的母羊尿器红红的。豁子李赶羊上坡,冷不防,被老骚狐牴个仰八叉,半天爬不起来……
宝儿爹怀疑宝儿肚子扣的这个瓷碗,跟豁子李有关,也不是没有道理:有一次,豁子李放羊下坡,偷偷塞给宝儿几个野洋桃。这是被宝儿爹撞见的,没见的,还不知道偷塞过啥歪瓜裂枣哩。当时,他就把野洋桃从宝儿手里夺过来,砸到了豁子李的身上。
宝儿爹觉得受了污辱。一个连畜生都不放过的货,有啥资格来说宝儿!他想把那烟酒砸了,再把村主任骂个狗血喷头。可宝儿娘扽他的衣襟,把他扽灵醒了,就想起低保、扶贫款的事,瞬时换了笑脸,说,养女百家提嘛。不过,我宝儿不到城里要房子,但十万块的彩礼,少一分可不中!
村主任知道,这是宝儿爹刁难他的。豁子李的家底谁都清楚,几只羊卖了,加上那三间房子,也凑不齐五万块,别说十万了。然而,村主任毕竟是村主任,他得维护村里的规矩,就说,别人彩礼都是五万,你咋要十万?
宝儿爹一本正经地说,宝儿可是两个人呢!
趁塄堰刨疙瘩
宝儿爹的话,等于向山村投了一把火,山村立时烧了起来。尽管十万块不是个小数目,但和城里一套房子比起来,一个像天上的星星,一个就像树梢的柿子,树梢再高,毕竟还有够着的希望。
最先看到希望的是旭升爹。旭升爹收完麦子,拿着镰刀往回走,走到宝儿家墙外,正好听见宝儿爹那句话,接着看见村主任从宝儿家甩门出来。
旭升爹拿着镰刀,没有回家,跟着村主任的屁股,来到村主任家院外。
村主任觉察身后有个影子在晃,一回头,见是旭升爹,没好气说:你跟我后边吃屁哩?
旭升爹挥了一下镰刀,问:十万,咋回事?
十万,宝儿。
当真?
她爹说的。
十万等于宝儿,宝儿等于媳妇,值!
觉得值,就给你家旭升。
我正是这个意思。
三十年前秋天的一个早晨,日头爷刚跳进王家院子,一声婴儿的啼哭就从王家的窗棂飞出来,伸手拽住了日头爷的胡须——这个婴儿就是旭升。
名叫旭升,人却没像旭日一样升起来。都吃粗茶淡饭,别人家的娃都粗枝大叶地疯长,可旭升却像一根铁钉,长到一米多点,就锈死不长了。加上家里穷,旭升从小到大没穿过一件囫囵衣裳,上到初中就辍学了,跟着村里的大人跑到外地去打工。
旭升爹进了院子,把镰刀挂到院墙上,直接奔了屋里,伸手抓起搁在堂桌上的电话。电话是闺女出门打工时装的,说装个电话,人不论走多远,家都近。旭升爹拿起电话半天,想不起儿子的手机号,无奈放了电话,哐哐当当在抽屉里乱翻,翻出一个泛黄的纸皮本子,却还是找不到旭升的号码。就问旭升娘:咱升子的手机号记在哪坨?
旭升娘问:不年不节的,给升子打电话干啥?
旭升爹瞪着眼说:干啥?眼看娃就要打光棍了,你咋啥心不操!
旭升娘不服气,说:能怨我吗?只怨你没本事!人家要到城里买房子,你把头扎到裤裆里,咋一声不吭哩?
忽然灵醒过来,急忙问:有茬了?
旭升说:宝儿。
旭升娘嘴张开了,说,就那个憨宝儿?
旭升爹说:别嫌馍黑,有馍总比没馍强!
旭升娘不再说啥,拿起电话机下一张纸片,照着纸上的号码拨电话。
电话通了,一声,两声,三声……响了八九声,也没人接。又打,一遍,二遍……打了四五遍,依然没人接。旭升娘说,兴许娃还上着班哩。
月亮已经从东山头探出脑袋了。往常这个时候,旭升爹会坐在门墩上吸一袋烟,然后上炕睡觉。可今天他遇上了急事,就像一群人进山,突然发现了一棵灵芝,紫红紫紅的,很耀眼,你出手慢了,别人就会一把抢了去。穷人的娃,说媳妇难呐!他感叹着,不停在院子转圈圈,转一阵,回去打一次电话,打不通,出来再转。直到把月亮转到西山,电话却自己响起来。旭升爹跟斗踉跄往电话机前跑,进门时被门槛绊了一下,差点跌倒。
野哪去了,不接电话?
啥事?电话里,儿子声音夯夯的。
那个啥……宝儿怀孕了。
宝儿怀孕,跟我有啥关系!
宝儿爹说不到城里要房子了。
不要房子也不要!
别人都在抢……
谁爱抢抢去!
旭升娘听到他们的对话,知道父子二人从来敲锣敲不到一个点上,就把听筒从老汉手里夺过来,说,升娃。
妈——声音柔下来。
升呀,妈知道你心性高,可咱命穷啊!我和你大挣不下大钱,挣俩小钱,都叫妈买药吃了。你在外打工,挣挣花花,猴年马月才能在城里买房子?你不能打一辈子光棍啊,王家可不能断后啊……
说着说着,旭升娘的泪就滚出来了。
娘,宝儿是个憨憨啊。
咱吃不上白馍,黑馍也得吃呀,总不能叫饿死吧?过去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
可宝儿肚里怀了别人的娃呢……
怀别人娃咋了?生到咱炕跟,就是咱的娃!这叫趁塄堰刨疙瘩,不趁塄堰,疙瘩不好刨呀……
电话那头,长时间没了声音。旭升娘连着“喂喂”半天,才听到一句少气无力的话:妈,叫我想想……
话没落音,电话已挂了。
老两口一个坐在高凳上,一个坐在矮凳上,谁也不说话,任由夜气在屋里流动,直到老鼠困得趴了窝,旭升爹才按着大腿站起来,说:睡!
旭升娘跟了声:睡!
盛开成一丛血花
旭升爹掂着烟酒进到村主任屋里时,屋里已经围有七八个人,有本村的,也有外村的。堂桌上高高低低杵着七八撂烟酒,跟一座座山头似的。
村主任坐在高凳子上吸烟,鼻窟窿里喷出一股股烟雾。他眯着眼,问:
都给娃们通过电话了?
通过了。
都愿意?
愿意。
都愿意出十万?
比去城里买房轻点。
村主任扔了烟头,站起来,用脚拧了拧,说,狗日的,就一朵花儿,招来八九个采花人,叫我咋办?
先来后到!
我来得早!
我来得早!
……
一屋子的人,就属旭升爹来得晚。他不能睁眼说瞎话,可也不甘心,就可着喉咙喊了一嗓子:抓鬮!
忽然一阵凄厉的哭嚎,像鬼吹哨,尖利地刺进人的耳膜。人们愣过神来,意识到出什么事了。
确实出了大事。一只锦鸡拖着红红的尾巴,在宝儿房后的石崖上悠闲踱步,被在崖下玩耍的宝儿瞄见了。宝儿从崖侧攀上去,蹑手蹑脚向锦鸡靠近。马上就够着锦鸡尾巴了,锦鸡发现了宝儿的企图,翅膀一展,飞到石崖下边。宝儿的身子已经扑了出去,两条胳膊一奓,从石崖上摔了下来,盛开成一丛血花……
宝儿死了。
埋过宝儿的那天夜里,宝儿坟上传来一个男人撕心裂肺的哭嚎。哭嚎变成红色的鞭子,蹿到天上,把沉沉夜空抽裂出一道道口子。
瞬时,暴雨倾盆而下……
责任编辑 申广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