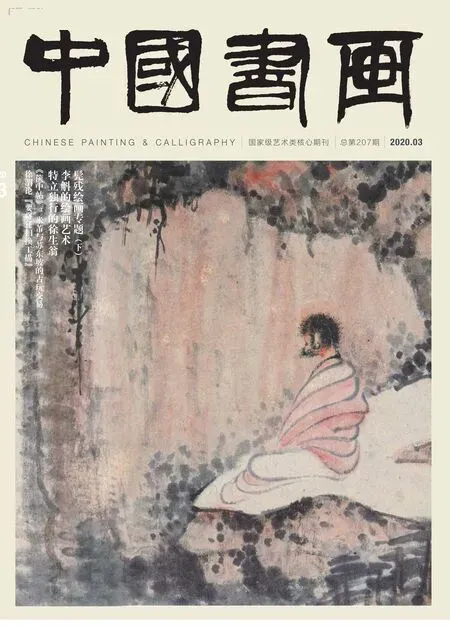笪重光出佛入道问题研究
◇ 周心瑶
明清时期,京口(今镇江)及周边地区人才辈出,艺文昌盛,“家诗文而户笔墨”。张九徵、查士标、笪重光、恽寿平等等,一大批文人、艺术家、收藏家出现。其中笪重光(1623—1692)较引人注目,他既是书画理论家,又是收藏家、文学家。
笪重光晚年隐居茅山,以道士的身份为人们所熟知,过着深山杖黎、鹤唳凫飞的生活,潜心修道。“道教龙门派的一代宗师王常月,曾于顺治十三年被封为国师,在北京白云观开坛说戒期间,就连当时还是太子的康熙也皈依在他的门下。王常月于康熙二年(1663)来到南京隐仙庵,传戒于江浙一带,至康熙十五年(1676)的13年中,前往受戒的弟子达1000人之多,笪重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1〕在此后的十余年间,他细心考证,在元代刘大彬的基础上,编修完成了《茅山志》,补添了明清诗词及道秩考等,为茅山道教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在修道期间,笪重光艺术创作不间断,创作内容多与道教息息相关。如1686年《行书戏拟白乐天放歌行》(图1),结字章法与东坡相似,略参米南宫意,整篇潇洒苍劲,毫无做作态,文末“本无壁落任游行,漫说仙班分果位。只待虚空粉碎时,与尔虚空同一气”文书俱佳,书中隐隐然有一股神仙气,正如恽寿平评其“江上翁抗情绝俗,有云林之风”。
笪氏一生乐于写诗,其甥零星掇拾,集得《江上诗集》,后得丹徒藏书家李丙荣搜辑增补,部分是漫兴寄怀之作,多雅趣,不事雕饰。笪重光晚年信奉道教是众所周知的,但浏览笪重光《江上诗集》早年创作的诗歌及其早期的书画作品,却几乎没有道教的影子,而是完全沉浸在禅佛的世界。宗教信仰对一个人的艺术观念的形成和表现是有一定影响的。笪重光对佛道的态度,值得我们探讨。
一、笪重光的佛学修养
明亡前,笪重光曾读书于焦山僧舍,以句容籍补博士弟子。他的一生曾多次游历“镇江三山”,焦山、金山、北固山皆是佛门圣地。焦山有定慧寺,原名普济禅寺,康熙曾题写寺名匾额。笪重光在焦山的时间最多,因此以焦山为背景题材的诗占多数,有十余首,皆是静心修禅,如《宿焦山》:“谁云高士宅,只许老僧居。余欲分禅榻,焚香读梵书。世事流水淡,生计暮云虚。落日下远渚,凭栏恒宴如。”〔2〕从诗中可见笪重光虽是尘中客,却在 “三山”间以佛理心,得静处与山僧同修,可谓“高枕听禅偈,狂歌托友生”。时有禅友相会,焚香畅谈,以至于每每来三山间,总是忘记乘船回去。他在《金山》中云:“戎马关城冷,鱼龙宫殿闲。惟宜禅定客,钟梵隔人寰。”〔3〕可见笪重光在登金山时,对待佛禅的态度。边塞将士尸骨流外,寒风如刀,金龙盘柱的宫殿让人生闲,唯做一个禅定客与这人间作隔,才是个好的选择。
笪重光23岁时跋《宋黄文节公书梵志诗卷》:“按行南康,游庐山开先寺,见涪翁所书七佛偈于石壁,苔藓剥蚀不可读,因令工人洗涤,并构亭其上,名曰‘获偈亭’拓得数本而归,获《莲经》《晋门品》《富阳刘生读书》《绿阴》《藏镪》诸帖。”在游开先寺时见黄山谷书梵志诗欣然拓之,并获其他佛教典籍名作,可以看出笪重光游走寺庙与禅友相会,是他的一大乐事。
抄写经书是明清人治学的一种重要方法,早年间笪重光曾抄录过《参寮子(释道潜)诗集》(图2),手抄本共三册,在第三册末尾有“江上外史手录”之款,并钤有“笪在辛”方印〔4〕。诗集的字迹与董其昌小楷相似,推断为笪氏早期作品,可见他年轻时对佛教类的诗集十分用功。明末清初以董其昌为主的云间书派席卷各地,加之帝王推崇,崇董书风盛行。董书简淡清雅,禅眼作书,笪氏也深受其影响,书风清淡简约,颇有禅意,后又习“宋四家”书,而空灵清秀之意犹存。笪氏书作早年流传甚少,比较珍贵的是1665年《行书跋廖大受画雪庵画像轴》(图3),此书风明显是学董其昌,疏简淡雅,弥漫着风规自远的从容,极富禅意。

图1 [清]笪重光 行书戏拟白乐天放歌行94.5cm×42.7cm 纸本 故宫博物院藏
此外,在《江上诗集》中,有部分诗句明显表现出笪重光对于佛教净土宗的倾向,如《携秋岳曹司农,思龄王纳言将至同西溪访友宿天竺僧舍》:“欲随处士寻松径,先向山僧借竹楼。日落精蓝苍翠绕,夜虚上界白云留。浮生自信空王法,清兴能宽浩劫愁。说向远公时贮酒,不妨莲社再同游。”〔5〕在诗中他明确地指出自己“浮生自信空王法”〔6〕,并且从“携秋岳曹司农,思龄王纳言至西溪访友宿天竺僧舍”这个线索可推断出此诗的创作时间。曹溶顺治十八年(1661)49岁,在西湖断桥赏月。康熙元年(1662)50岁,夏日,在杭州与曹尔堪、余怀和朱彝尊等人游〔7〕。而笪重光罢官后,也在苏杭一代游历,大可断此诗作于1662年到1663年之间,此时笪重光还是个不折不扣的佛教信仰者。其后两句“说向远公时贮酒,不妨莲社再同游”,“远公”指的是晋代高僧慧远,被人们追为净土宗之始祖。名仕谢灵运,钦服慧远,在东林寺为其开两池遍种白莲,遂称“白莲社”,诗中的“莲社”也是对慧远结社念佛的向往。除此之外,笪重光在多首诗词当中都有提到慧远法师,《游晋寺》有云“自契无生理,何劳问远公”〔8〕,无生理亦是佛教用语,谓无声无灭的真谛,意为自己最契合无生无灭的真谛,何苦去劳烦问慧远大师呢?又有《赠拨云庵定上人》中“偶然寻慧远,松下且盘桓。馔出伊蒲供,居通灌莽寒”〔9〕。从佛学的宗派来看,笪氏所信仰的是净土宗。
净土法门不依赖师承,不论根器,一切无碍,所以比较简单,因此也成了笪重光做官时的精神依托。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就有轮回报应的思想,人生来不只有一生,而是不断重复生死转环,循环于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间、天上六道之中。净土宗慧远对于轮回报应也有云:“经说:业有三报。一曰现报,二曰生报,三曰后报。现报者,善恶始于此身,即此身受。生报者,来生便受。后报者,或经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后乃受。”〔10〕笪重光也深受其影响,《江上诗集》中就有“生死如转环,千载以为期”之句。
综上种种迹象,都表明了笪重光前半生流连佛教,只是并未作出实际的行动,也没有像佛教徒那样生活,但他却时刻流露着对佛教的虔诚和笃信。后半生他却选择了入道,其中又有何契机呢?
二、笪重光出佛入道的问题
笪重光在40岁左右还徘徊在佛道之间,辗转四五年,经历了人生百态。康熙六年(1667)时44岁,笪重光始入道,改名蟾光,自号郁冈居士、郁冈扫叶道人,居松子阁修身养性。在茅山编写《茅山志》的同时,也喜与众友人吟诗作画。康熙八年(1669)秋作《墨山水》自题:“渔舟过去,山水生风,轻快飘逸,胸中块垒一扫无余。”可见其已心胸洞达,再无世事扰心,并坦言“华阳有真趣,不慕五云飞”。对于笪重光晚年入道,众说法不一,下面尝试辨析其入道的动因。
清初全真教的兴盛。道教在明末清初处于特别发展时期,全真道王常月的推动使道教一度辉煌,清初道教经过短暂的沉寂又慢慢发展起来。全真教强调的是道士们的心性修养,注重个体的修行,其做法是根绝世俗的欲望,修炼心性。在社会动荡的朝代更迭之际,许多遗民纷纷加入,以求精神寄托。全真教的代表人物王常月于1663年南下传教,其思想正与笪重光的内心相契合,于是他全身心投入道教,并在王常月江浙设坛传戒期间担任启派师。

图2 早年间笪重光曾抄录过《参寮子(释道潜)诗集》。国家图书馆特藏组善本书室(台北)
笪重光个人的身体状况与服食丹药。随着年事愈高,笪重光身体状况的下降也是不可避免的。笪氏亦有炼丹养生之举,在诗词、题跋和友人的互相唱和中,不乏关于服食丹药、养生决等信息。在《归山中》自娱 :“服食可延年,虚名岂为宝。感此不能寐,引领思蓬岛。”〔11〕又在《寄摄山王野云炼师自号治炉子》诗中,提到了摄山王野云炼师教他体悟自然、炼丹养生的诀窍:“授我养生诀,蹉跎不及持。体道和自然,柱下诚吾师。”
笪重光的现实生计问题。当然,笪重光入道还牵扯到一些现实原因。顺治十四年(1657)后解官放归,随之要面临的就是生计的问题。他在退隐之初,困于贫窘,在《赠杨圣调》诗中道:“嗟哉罢官后,旧业各荒芜。酒债俸钱少,丹方药竈虚。君贫非病也,我空其庶乎。”〔12〕笪氏虽鬻画为生,然不是长久之计,从后期他的生活状态来说还是比较轻松惬意的,并先后购买了大量的藏品,道教的活动或成为他谋生的主要途径。
诵读老庄,广结道友。笪重光少览群书,只不过那时读庄老,若在梦中一般,玄幻至极,不得其中一二,但蹉跎四十年后,在不惑之年突然顿悟了庄老的真谛。其有诗《山中杂咏》:“少闻达生论,泛然若梦寐。蹉跎四十年,始悟庄老义。”〔13〕随着笪氏的学识与人生经历的变化,不惑之年突然了悟,思想上的巨变,让他真正领悟了道教。另外在《江上诗集》中有《口占示张炼师》一诗:“白发羞看镜,丹砂未驻颜。西泠桥下水,流向客中闲。春草南屏路,晴云北固山。与君同作伴,何日始知还。”描绘了他与道士张炼师游山玩水,莫逆于心的事。游玩西泠、北固山,是罢官后的旅途中所作,此时还未入道,可以看出笪氏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道友的影响。
“己亥通海大案”的影响。除了以上因素之外,笪氏罢官后还经历了一件大事。郑成功、张煌言于顺治十六年(1659)攻占镇江,据李光地《河南提学道佥事公选张公传》记载,张湘晓在郑军围城时谓御史笪重光曰:“吾辈虽非守土官,无城社责,然受国恩一也。朝廷土地且我桑梓,忍见其涂炭乎?”光曰:“奈吾侪书生何。”征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备,吾筹之熟也。”后笪重光赴常州、杭州求援,并参与谈论迎降问题。由于郑与张在作战时战略问题,郑放弃了瓜洲、镇江等地,而清军重新占领镇江。清廷严厉镇压迎奉郑军的地方人士,制造了“己亥通海大案”,据说镇江就有“八十三家,后皆伏法”〔14〕。此事牵扯到了家乡几百余人的生死,事事动荡,生灵涂炭,这使他更想归隐于山林,不再纠于世事纷争。
由此可看,笪重光入道正是种种原因作用之下的结果。社会环境的推动与心境的变化等,都是一个人思想发生改变的重要因由,而非是一蹴而就的。
三、笪重光晚年对佛道的态度:“道傍禅关”
明清鼎革过程中,佛、道异常的兴盛,实则夹杂着文人士大夫们的精神隐痛,于是他们参禅角诗、拄杖炼丹。“道禅”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剂良药,让他们能寻到一处自我安放的静地。笪重光作为清初的官员,虽不算作遗民,没有经历过这种亡国的隐痛,但却受社会大背景下的佛道观的影响,对佛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潮流,有研究者表明:清初大批士人剃发为僧,托迹佛门的逃禅风潮,在规模、影响方面堪称史无前例〔15〕。反观笪重光信奉的全真教,在创立时就以三教合一为开端,明清之际王常月又将三教合一推向高峰,这使得儒释道三者的关系紧密,三者之间也没有明显的界线。正如笪重光晚年入道后,他对佛教并没有排斥,而是积极参加佛教活动。
九华山作为佛教圣地,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笪重光的一生曾多次攀爬,1655年秋月宿九华山僧舍,他说自己“喜复来”,这时他还在佛教的世界游走,而1680年又复登九华山时,他已入道十余年,留下了《庚申秋日从越中归宿虎丘三仙阁》这首诗。末尾两句“何当谢尘纲,常得傍禅关”〔16〕,道明了他那时的心境。怎么才能逃离这尘世间的繁纲呢?除了学道还得时常依靠禅关来使自己更明了。庚申年孟冬,题宋黄文节书《梵志书》:“此卷颇长,所录乃古德语,知老生之精于禅,悦发为笔,墨如散僧入圣。”可见他晚年也喜收藏佛教作品。这一切说明,笪氏在入道后,并未真正意义上逃离佛教,而是有佛道不分家的思想,这种思想的由来,一定程度也受到友人佛道观的影响。
笪重光的密友张风(?—1662),善画,其画向称逸品,张风是知佛修道之人,常寄居佛寺道观,自号“升州道士”,又署名“真香佛空”,从其字号便可窥见一二。张风《石室仙机图》中有跋,记载了与笪重光的来往,笪重光退官后,为排遣苦闷,张风陪同其游走“三山”,又南下苏杭,游走三月之久〔17〕,不料他天首未全,三年后便逝,笪重光在《江上诗集》中有多首挽悼大风的诗,多数是以佛禅之境追怀,“贫来曾贷监河粟,老至同参雪窦禅”,猜测两人有过一起修禅的经历,而张风其兄张瑶星,是归隐的道士,张风自然也受其影响。关于张风的信仰问题,周亮工在《印人传》“二〈书张大风印章前〉”云:“大风学道学佛,三十年不茹荤血,客有烹松江鲈鱼者,因大噱曰:此吾家季鹰所思,安得不噉,遂欣然以饱,从此肉食矣。”〔18〕笪重光的另一好友查士标(1615—1698),自1657年从新安来到扬州,其后半生都是在扬州度过的,与笪重光交往甚密。查氏的《种书堂遗稿》序中载“二瞻查先生,静者也,少时曾学吐纳之法,渊穆冲恬,不求闻达,一室之外,山水而已。”查氏无直接入佛道的行为,但遗存下的诗稿中有不少关于道教的物象,如野鹤、方壶、丹决等,同时查氏又喜与许多禅友僧侣来往,如师昂、济若等。这一时间段的江南文人个体,他们礼佛又服丹,消弭隐痛,并将宗教融入他们的艺术世界,笔下书写着对人生的百般领悟。

图3 [清]笪重光 行书跋廖大受画雪庵画像轴(廖大受 雪庵像轴 115cm×26cm纸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
笪重光的这种“道傍禅关”的宗教观,对他晚年所撰的两部理论著作《画筌》《书筏》具有很大的影响。道教追求阴阳化生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笪氏将阴和阳的关系在《画筌》中化以“动静”“虚实”“聚散”等矛盾组合展现出来,如“山本静,水流则动,石本顽,树活则灵”〔19〕,又“山实虚之以烟霭,山虚实之以亭台”〔20〕等。笪重光晚年精研庄老,同时把庄子的思想融入自己的书画理论。庄子曰“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21〕,意喻“我”与“彼”之间是互相牵制、依存的,是以对方作为自我存在的前提条件。《画筌》中笪氏巧妙地把庄子的辩证法代入,将“空”与“实”、“真”与“神”的微妙关系表达得淋漓尽致。“空本难图,实景清而空景现;神无可绘,真境逼而神境生。”〔22〕意为虚灵空旷之物,难以具体的表现,但实景表现好了,虚白处也自然在观者心中呈现出景象来了,同理,“真境”与“神境”也是如此。又见《书筏》中“黑之量度为分,白之虚净为布”〔23〕,正是因为“白”的存在,才能凸显出“黑”的价值,计白当黑,注重字外的布白,以不用为用,可谓大道。可见笪重光是站在至大的境界去俯瞰,当然这也基于他对于道学、易学的深刻理解。
同时《画筌》《书筏》这两部书画理论中也潜藏着他的佛教观念。笪重光在未入道前诗中屡次提到“慧远”大师,慧远在《沙门论》中提出了“形尽神不灭”论,将“形”和“神”上升到了形而上的高度。笪氏也将“形”与“神”引入自己的《画筌》中,常以“神境”作为绘画至高的境界,亦有“人不厌拙,只贵神清。景不嫌奇,必求境实”之句〔24〕,主张绘画不流于形质,必得其神。另外笪重光信仰的净土宗,其“净土”二字就是心的表现,心是一切的根源,因此他在《画筌》中对绘画创作者的心境与品性做出了更高的要求,所谓“人非其人,画难为画”〔25〕。受宗教的影响,笪氏的书画观流露出了超脱世俗的远见,如书法创作的布白、山水画创作的形神兼备、书画融通观等等,同时他的艺术创作也散发着虚寂宁静、冷落清幽的气质,影响着后世的书画者。
朱良志先生说:“道禅哲学的色空思想、无住观念,视世界如幻象的思想,对中国艺术的影响极为深远,这绝不仅仅是一个虚实问题。它是一种人生态度,一种看世界的方法。”〔26〕笪重光以及江南的文人们,将这种“道禅哲学”深入到了自己的艺术中,无论是绘画、书法、诗词,都表达着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他们的艺术也因此绽放出了无比绚烂的生机,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