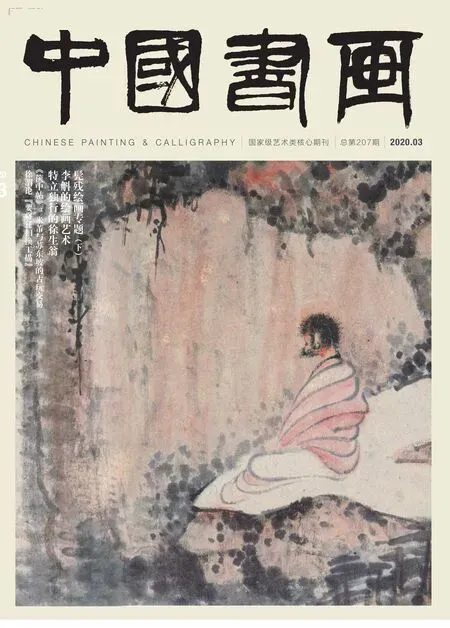风流题客—吴伟青楼题材画与周边人
◇ 林霄
吴伟(1459—1508),字士英,更字次翁,又一字鲁夫,号小仙。以山水人物绘画闻名于当时,一生中曾三度被宪宗、孝宗招致宫中,授锦衣卫镇抚、待招,被孝宗赐“画状元”印。关于吴伟的绘画,台湾学者刘英贝硕士论文《吴伟人物画风格研究》(2008年)对此有深入的研究,然而对吴伟画上题跋者的发掘还不够到位,因而此文也是在刘英贝文章的基础上发复。
吴伟生性不耐约束:“性豪放,轻利重义,在富贵室如受束缚,得脱则狂走长呼!”〔1〕每致宫中,总不能久留,每从宫中放归,便回到长居之地南京,秦淮河畔才是他的中意之地。吴伟辖宫廷画家之盛名,在南京更受权贵们的欢迎:“伟好剧饮,或经旬不饭,其在南都,诸豪客日招伟酣饮。故伟又好妓,饮无妓则罔欢,而豪客竟集妓饵之!”〔2〕
若想邀请吴伟作画,宴会上必少不了酒和妓,酒色刺激了吴伟的创作,也造成了吴伟的短命,50岁便死于被第三位皇帝(武宗)征召入宫的途中。
吴伟存世画作中,除了山水神仙题材外,另有《铁笛图》《歌舞图》《武陵春图》及《琵琶美人图》四幅场景皆与携妓宴饮有关。这类题材皆以白描细笔的形式绘成,其上必有文人题跋增加热闹。有人记载:
中山武陵王玄孙徐某,一日与吴小仙、孙院使宴饮,命吴画女乐诸子及孙、吴陪饮之图。画毕,徐喜曰:“欠风流题客”。〔3〕
携妓图已美,若无风流题客诗赋其上,总有缺憾。
吴伟38岁时为南京锦衣卫世袭指挥使黄琳作《仿李公麟洗兵图》,现藏广东省博物馆,题款:“弘治丙辰(1496)秋七月,湖湘小仙吴伟为献蕴真黄公。”钤有黄琳收藏章。
黄琳,字美之,号休伯、蕴真,明代项元汴之前最负盛名的书画鉴藏家,萌荫获授南京锦衣卫指挥同知。他的叔父黄赐,是成化朝的司礼监太监,成化帝朱见深从小便得黄赐伺候,深得信任。

图1 [明]彭时《东轩清玩序》。上海博物馆藏
成化年间,黄赐就以收藏闻名,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成化年间吏部尚书彭时为黄赐的收藏作《东轩清玩序》(图1)〔4〕,彭时是正统十三年(1448)状元,这件《东轩清玩序》书于成化六年(1470),用楷书恭恭敬敬地抄写,其上亦有黄琳藏印。以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尚书的身份对这位司礼监太监如此恭敬,令人吃惊。可见黄赐在成化宫中的地位,亦说明当时的黄赐庋藏已相当丰富。
黄赐死后,其所藏书画皆归黄琳。至今存世的古代名迹中,经他们叔侄收藏的有:王维《伏生授经图》、董源《夏山图卷》、苏轼《枯木竹石文同墨竹合卷》、苏轼《与梦得秘校尺牍》、宋徽宗《草书千文》、米芾《论书帖》,李山《风雪杉松图》、赵孟頫《趵突泉诗》、赵孟頫《赵氏一门法书册》、邹复雷《春消息》等。其余钤有黄琳鉴藏印者,散见各处的宋人信札、圆光不胜其计。董其昌跋黄琳所藏米友仁《五洲图》时如此评价:“此画本黄美之所藏,收藏鉴赏为一时之最。”〔5〕
文士都穆自负善于鉴赏,1512年某日与顾璘曾一同到黄琳家看其收藏,都穆记下一则:
右唐王维画《济南伏生像》,宋秘府物,今藏金陵王休伯家。予官金陵,闻休伯所藏书画甚富,一日,与顾吏部华玉过之,休伯张燕,余戏谓之曰:“必出书画乃饮,宋元姑置,亦有唐人笔乎?”休伯笑而不答,遂出此及维著色山水一卷,余不觉惊伏,以为平生之未见也。〔6〕
黄琳丰富的收藏,定让吴伟开阔了眼界,或许黄琳收藏有李公麟的《洗兵图卷》,是吴伟为黄琳临摹的缘由。
黄琳的出手阔绰闻名当时,“黄琳美之元宵宴集富文堂,大呼角伎集乐人赏之,徐子仁(1462—1538)、陈大声(陈铎)二公称上客。美之曰:‘今日佳会,旧词非所用也。请二公联句。即命工度诸弦索。何如。’于是,子仁与大声挥翰联句,甫毕一调,即令工肄习。既成,合而奏之。至今传为胜事。子仁七十时(1531),于快园丽藻堂开宴,妓女百人,称觞上寿,缠头皆美之者”〔7〕。
徐霖七十寿宴,黄琳竟然大方地包揽了百名艺妓的小费(缠头)。
徐霖新筑快园后,宾客好友不绝,大方的黄琳再次显示了他的豪举:
徐子仁快园落成,美之携酒饮于园中,一友人曰:“此园正与长干浮图相对,惜为城隔,若起一楼对之,夜观塔灯最是佳境。”美之曰:“是,不难。”诘旦,送银两百两与子仁造楼……〔8〕
上面提到的这位徐霖,是另一位风流客,字子仁,一字子元,号髯仙、髯伯,别号九峰道人、快园叟。徐霖的祖先原是苏州人,后举家徙居南京,家境优渥。徐霖于尤其以词曲与书法闻名。“自号九峰道人,或称快园叟,或羡其美须髯,又称呼髯仙。”〔9〕想见是一位美髯公。徐霖在南京城东筑了名为“快园”的宅邸,就在秦淮河畔,徐霖“性好游观声伎之乐。筑快园于城东,善制小令,得周美成、秦少游之诀,又能自度曲,棋酒之次,命伶童侍女传其新声,盖无日不畅如也”〔10〕。
徐霖善制作小曲,填词,留都人竞传而歌之,武帝(正德皇帝)南巡时,竟提出要召见徐霖,让他当场填词作曲,结果令皇帝大喜。贪玩的正德皇帝滞留南京,多次到徐霖的快园游玩,竟有一次半夜乘月驾临,令徐霖手忙脚乱,正德皇帝却非常尽兴。一回皇帝在快园垂钓,得一金鱼,宦官们争买之,竟使皇帝失足落水,徐霖遂将池塘命名为“浴龙池”。正德皇帝竟在南京逗留九个月之久,不得已才还京,赐徐霖飞鱼服,扈从还京,每夜宿御榻前,与皇帝同卧起。皇帝要赐官让徐霖留京,而徐霖坚辞归里,活到77岁〔11〕。
吴伟当是黄琳、徐霖们家宴文会中的常客,在吴伟存世画作中,徐霖曾在吴伟的《武陵春图》《子路问津图》《词林雅集》《龙江别意》四幅作品上留下题跋或引首。
在这样的名流宴集的文酒之会中,戏班妓女夹杂期间,文人女色相互刺激,诗词戏曲交相辉映。有条件的文人家中甚至蓄有女妓,如北方的李开先(1502—1568)家有“戏子几二三十人,女妓二人,女僮歌者数人”〔12〕。
才子祝允明也是他们交友圈中的一员,祝允明(1461—1527),字希哲,号枝山,“吴门四杰”之一。他在存世吴伟画作的《铁笛图》《李奴奴歌舞图》上留有题跋。祝允明虽是苏州人,南京却是他常来之地。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称其:“好酒色六博,善度新声,少年习歌之间,傅粉墨登场,梨园子弟相顾弗如也。海内索其文及书,贽币踵门,辄辞弗见,伺其狎游,使女妓掩之,皆捆载以去。”〔13〕

图2 [明]祝允明《梦游莺花洞天记》。近墨堂书法研究基金会藏
有人向祝允明索文,未必能给,若为妓女写字皆心甘情愿。
祝允明的性情与吴伟颇有相似之处。祝允明一生“五应乡举,七试礼部”,每次乡举都得来南京。南京,是六朝古都,更是明朝的“留都”,自是祝氏的常来之地。对于文人才子而言,金陵还有一个更吸引他们的去处,便是与贡院一河对望的旧院。秦淮河畔青楼的兴起,起源于朱元璋时代,盛于明代中期,据《板桥杂记》的描述,可以想象科举场所贡院连着青楼的风景:“旧院与贡院遥对,仅隔一河,原为才子佳人而设。逢秋风桂子之年,四方应试者毕集,结驷连骑,选色征歌,转车子之喉,按阳阿之舞,院本之笙歌合奏,回舟之一水皆香。或邀旬日之欢,或订百年之约。蒲桃架下,戏掷金钱;芍药栏边,闲拋玉马。此平康之盛事,乃文战之外篇。”〔14〕因此,“旧院”是举子们纾解压力与排解寂寞的最好去处,青楼文化的龙脉之地。

图3 [明]吴伟 铁笛图卷 32.1cm×155.4cm 纸本墨笔 上海博物馆藏

图4 [明]祝允明题吴伟《铁笛图》诗
祝允明中举后,文名、书名已闻于江南,亦频繁来往于南京,并与黄琳、徐霖、顾璘、吴伟等人交善。
祝允明性格任性自便,不守礼法,不善理财,好作声色饮,曾作有“闺体诗”十卷〔15〕,大多未能流传。另沈德符记录祝允明《风流遁赋》中有句子:“‘画堂内,传杯递斝,参辏着玉帐牙旗。绣帘前,品竹弹丝,掩映出高牙大纛’又云‘四边厢眼里火,假捏妖言。一会子耳边风,虚张声势。’又云‘急邓邓,通红粉脸,不过是诈败佯输。颤巍巍,咬定银牙,无非是里应外合。’又云‘寸心千里,坐守老营,一日三秋,肯离信地。’又云‘欢娱嫌夜短,惟求却日挥戈。寂寞恨更长,那讨闻鸡起舞。’其他皆不及记。词虽淫媟,亦自有致。盖二公(指祝允明与唐寅)皆老公车不得志,寄迹平康,以销壮心,即见嗤于礼法士,非所计也。”〔16〕
沈德符将祝允明、唐寅好作淫词艳曲,比为“老公车不得志,寄迹平康”,将秦淮河畔的“旧院”比作唐代的“平康坊”,对祝、唐的不守礼法报以理解之同情。
1503年之前的祝允明与黄琳更是交往频繁。1502年秋,祝允明宿于黄琳府邸,为黄琳作《一江赋》以及《梦游莺花洞天记》(图2),这两件皆存世。《一江赋》〔17〕,将黄琳比为“一江之在天地间,大而有本”,极尽歌颂之能事。而《梦游莺花洞天记》不见其文集,近年现世,现藏于近墨堂书法研究基金会。何良俊(1506—1573)记载祝允明为黄琳作《烟花洞天赋》,曾名动一时,很有可能就是这件《梦游莺花洞天游记》。
“莺花”是春时的景物,亦可代称妓女。依《梦游莺花洞天记》所记,祝允明夜宿黄府,梦中受“长乐君”邀请赴宴之经历,其奢华程度仅有西王母蟠桃之会可比。入夜,两青衣小童来请畅哉生祝允明赴宴,引导至一朱门,主人号称“蓬莱谪仙莺花洞天主人长乐君”。主君出门迎客,只见主人面貌,当是黄琳形象:
面若满月,气如景风,广颡修髯,玉树亭立,唐帽葛裘。其容飘飘,真拔俗之仙卿也。
既而入门,则见:
乐吏数百,夹拥阶下,奏小调以导行。既而,画屋交启,珠帘徐卷,室内银屏绣幄,代筵肆设,繁彩闹竹,乐具充牣,仙姝女童,二八列侍。
所谓“梦境”,实为黄琳家宴情景。
入座后有两位号称“莺花洞天仙部之首”的仙娥陪侍祝允明左右。这两位仙娥居然口占《天净沙》与祝允明以诗词相答。客人陶醉在温柔之乡直至天明酒醒。可见在黄府家宴中已有会作诗词的诗妓陪客。
吴伟26岁(1484)的绘画《铁笛图》(图3),现藏上海博物馆,内容是铁笛道人杨维桢(1296—1370)携妓弄笛场景,身旁站一女侍手捧铁笛,另一侧有两女坐在圆凳上,一人拈花插鬓,一人以扇掩面。后有祝允明题诗:“雌龙响歇小女持,铁精坐调双花枝;大枝拈枝对郎插,小枝掩扇诲妖痴。”(图4)
虽无年款,但从字迹上判断,此跋与1490年书写的《祖允晖庆诞记》(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结字相似(图5),应是其三十岁左右甚至更早的行书,说明题跋时间当在吴伟画后不久。祝允明题诗描绘铁笛道人调戏双妓之状,颇有情调。
明人都穆(1458—1525)记载:“杨廉夫,倪元镇,一日会饮于友人家,时席有歌妓,廉夫兴发,脱妓鞋,置酒杯其中,使坐客传饮,名曰鞋杯。元镇素有洁病,见之大怒,翻案而起,廉夫亦变色,饮席遂散,后二公竟不复面。”〔18〕
倪瓒翻案而起,应该出自都穆杜撰,而杨维桢举金莲作杯确有来源,据与杨维桢同时代的陶宗仪(1329—约1412)所记:“杨铁崖耽好声色,每于筵间见歌儿舞女有缠足纤小者,则脱其鞋载盏以行酒,谓之金莲杯。予窃怪其可厌。”〔19〕
陶宗仪见到杨维桢此举应该也不止一次,不然不会说“每见歌儿舞女”,然而怪其可厌的是陶宗仪自己,而不是倪瓒,作为晚辈的陶宗仪虽觉得此举可厌,也断不敢翻案而起。
而杨维桢此荒诞之举,因陶宗仪的记载,却影响了后世。何良俊竟效仿之:
余尝至阊门,偶遇王凤州(王世贞)在河下,是日携盘榼至友人家夜集,强余入坐,余袖中适带王赛玉鞋一只,醉中出以行酒。盖王脚甚小,礼部诸公亦常以金莲为戏谈。凤州乐甚。〔20〕
此举亦被《金瓶梅》的作者写入了小说:“少顷,西门庆又脱下她一只绣花鞋儿,擎在手中,放一小杯酒在内,吃鞋杯耍子……”〔21〕
吴伟的另一画作《武陵春图》,描绘的是诗妓齐慧真独坐书斋郁郁思君的一个场景,卷尾有徐霖书写的长篇《武陵春传》,现藏故宫博物院。
在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中,有一段齐慧真的记载,她又名齐景云:“诗妓齐景云,亦善琴,对人雅谈,终日不卷。与士人傅春定情,不见一客。春坐事系狱,景云为脱簪珥,至卖卧褥以供橐饘。春谪远戍,景云欲随行,不可。蓬首垢面,闭户阅佛书。未几病殁。”〔22〕
徐霖在《武陵春传》评曰:“武陵春一娼家女流,狎客其分内事也。工文翰已为奇绝,而必择所合者委之,此殆有所见欤。既得其人,遂以死相守,其用情亦当矣,假使其初不失身焉,安知其不可以踵李哥哥之迹乎?”(图6)
文人化的妓女,历代来受到文人们的青睐,到了晚明,更是有“秦淮八艳”与文人的故事被人频频传颂。诗妓齐慧真对坚爱情坚贞不渝的故事,令画作者吴伟与《武陵春传》作者徐霖投射了深深的同情。徐霖仅存的戏曲《绣襦记》,也是描写妓女的爱情故事,或许齐慧真的死正是他的灵感来源。

图5 [明]祝允明《祖允晖庆诞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下面重点解读吴伟另一轴《李奴奴歌舞图》,此图现藏故宫博物院。之前的学者对此图有所研究,却未能解读其中人物。
图上方有唐寅、祝允明、金庭居士、九华居士、七一居士、髯九翁等人题跋(图7),皆是吴伟朋友圈中的人物。此图描绘的是主人公招名妓李奴奴歌舞欢宴的场景。
现试破解画中人物,十岁的李奴奴画成了孩童的娇小尺寸,她在客官们的欣赏之下跳着舞。画面的男性主人坐在春凳上,在身边艺妓的牙板伴奏下,微微张口歌唱,身边另一艺妓似在低吟和声。画面另三个男客作欣赏状。画中三个男客中,至少有两位已知:才子唐寅与画家吴伟。
唐寅(1470—1524)第一个题跋其上:
歌板当场号绝奇,舞衫才试发沿眉。缠头三万从谁索,秦国夫人是阿姨。梨园故事久无凭,闲杀东京寇老绫,今日薛谭重玩世,龙眠不惜墨三升。吴门唐寅题李奴奴歌舞图,时弘治癸亥(1503)三月下旬,李奴奴十岁。
唐寅明显是亲历者,此诗跋描绘了当日歌宴的状况以及男主的特征。第一句描写的是主人绝奇的歌板和李奴奴的舞姿。第二句将此风流歌宴比作唐明皇梨园轶事〔23〕。末句点题:“今日薛谭重玩世,龙眠不惜墨三升。”将今日歌板的男主比为“薛谭学讴”中的秦青,并将画作者吴伟比为宋代李公麟。
“薛谭学讴”典,见于《列子·汤问篇·薛谭学讴》:“薛谭学讴于秦青,未穷秦青之技,自谓尽之,遂辞归。秦青弗止,饯于郊衢,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薛谭乃谢求反,终生不敢言归。”
所以这位男主角一定是位擅长歌板之人。
可以看到,题跋中有一位“七一居士”。这位“七一居士”就是前面所说的黄琳宴会上,与徐霖一道现场作词谱曲的陈铎,而他是位善歌者吗?
陈铎,字大声,号秋碧、七一居士,约生于正统七年(1442)至十三年(1448)间,卒于正德二年(1507)〔24〕,邳州睢宁人。世袭南京济川卫指挥使,生性倜傥豪爽。虽是一位世袭武官,却工诗画,精通音律,擅长制曲,以散曲名世,有《陈大声乐府全集》存世,在明代中期戏曲史上地位不凡。
顾起元《客座赘语》有则轶事:“大声为武弁,尝以运事至都门,客召宴,命教坊子弟度曲侑之,大声随处雌黄,其人距不服,盖初未知大声之精于音律也。大声乃手揽其琵琶,从座上快弹唱一曲,诸子弟不觉骇伏,跪地叩头曰:‘吾侪未尝闻且见也。’称之曰‘乐王’。自后教坊子弟,无人不愿请见者,归来问餽不绝于岁时。”〔25〕

图6 [明]吴伟《武陵春图》卷(27.5cm×93.9cm 纸本墨笔 故宫博物院藏)及徐霖跋文《武陵春传》

图7 [明]吴伟 李奴奴歌舞图118.9cm×64.9cm 纸本墨笔 故宫博物院藏
陈铎不仅能作词曲能弹而且能唱,足令教坊子弟们拜服。
周晖《金陵琐事》另有一则关于陈铎“牙板随身”的轶事:“指挥陈铎以词曲驰名,偶因卫事谒魏国公徐俌于本府。徐公问:可是能词曲之陈铎乎?陈应之曰:是。又问:能唱乎?铎遂袖中取出牙板,高歌一曲。徐挥之去,乃曰:陈铎是金带指挥,不与朝廷作事,牙板随身,何其卑也!”〔26〕
这两则轶事都说明陈铎不仅善于填词作曲还擅长自弹自唱,甚至公务在身也带着牙板,随时准备开唱,以至于被魏国公认为不务正业。所以笔者认为,吴伟画中的男主角非陈铎莫属。
未能赶上这次三月宴集的祝允明,迟数月才到南京,遂被男主邀题其上:“春雾浓香浥海棠,楼心初月媚垂杨;未消姑舍峰头雪,一剪东风一点霜。后伯虎数月漫为续响,恐不免污佛头耳。枝山。”
有证据显示,从这年九月到十月祝允明住在黄琳府邸〔27〕,所以祝允明说“后伯虎数月漫为续响”。
接下来是“金庭居士”与“九华遗士”的题诗(略)。
而男主“七一居士”陈铎,亦题诗其上:“倾城一笑抵千金,况复司空是赏音。舞锦乱翻歌未彻,行云楼外月楼心。七一居士。”
六年之后,南京人“髯九翁”谢承举〔28〕题:“唇喷玉树凤喉香,步镞金莲蝶翅扬。若使君王轻瞥见,不移新宠在平阳。虔州髯九翁醉题时。正德戊辰再后伯虎者六岁,而奴奴破瓜久矣。”
最后一个题跋的谢承举,感叹李奴奴破瓜已久。
在娼业中,“初破瓜者,谓之梳栊”〔29〕,意思是打鬟的丫头已成为大人,可以梳头成髻了。在各妓院中,“梳栊”是一件大事,要大摆宴席,点大红蜡烛,放爆竹。妓院上下都需开销,嫖客更需为清倌人置备若干衣服、金饰等等,布置新房,宛如新婚一般〔30〕。
所以画面上的四个男人分别是主人陈铎与客人唐寅、吴伟,还有一位尚不知何人,必是“金庭居士、九华遗士”中的一位。
有人误解此画是主人为李奴奴“梳栊”〔31〕,理由是画中李奴奴的头饰已经梳成了“髻”,意味着李奴奴已经破瓜。然而依据《大明律集解·犯奸》,“强奸者,绞。奸幼女十二岁以下者,虽和同强论”。这可是死罪。即使律法已经执行不严,陈铎也不敢冒此罪并声张此事,甚至让朋友画下为证。谢承举是在六年后感叹李奴奴“破瓜已久”,并非指的是此次宴集之时。
其实这仅是一次召妓歌舞的文人宴集。猜测主人陈铎请吴伟画下当日艳景,吴伟此画或许受南唐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影响,事后陈铎再请风流客们题诗其上,作为“行乐图”以志其乐。倒是如此“写实”的“行乐图”在明代也是仅见。
题诗其上的九华遗士,流露出对青楼雏妓的同情,这是一种复杂的感情:
十岁青楼女,盈盈傍画屏。共怜歌舞处,疑是彩云凝。杨叶岸楼头,莺声晚更幽。当筵试歌舞,似欲妒春柔。垂手云光乱,翻词白苧鲜。可怜今夜乐,不是五年前。
或许五年前,正是李奴奴被卖于娼家的日子。
结语
吴伟青楼题材画,其周边牵带出一干以南京为活动中心的诗人、戏曲家、画家、收藏家群体。他们与秦淮河畔的歌妓、舞妓、诗妓们共同构成了独特的“青楼文化”。可以说,“青楼文化”是歌姬舞妓们与诗人、戏曲家、画家、收藏家们共同造就,彼此离不开对方的相互塑造。
杨海明有篇《论歌妓对唐宋词的作用》文章用了个标题“妙在得于妇人”,引用宋人王铚论晏几道词:“叔原(晏几道字)妙在得于妇人。”黄琳、徐霖、祝允明、吴伟、陈铎、唐寅等人与青楼文化的关系,都在证明同样的道理:青楼女是这些文人艺术家们创作的灵感来源之一。同样可以说,他们的诗词、绘画、戏曲“妙在得于妇人”。
同时我们也不能够用今天人们对娼妓的认识来理解明代时期的青楼女。青楼女们不仅是文人画家们的灵感来源,同时他们也在努力地被培养或者自我实现地拔高自己的品位修养,以迎合对岸贡院文人才子们的喜好,不仅琴、棋、书、画,甚至其中有诗人画家,如马守真、董小宛。其中也不乏坚贞不渝的爱情,如齐景真、李香君〔32〕。其中亦有在鼎革之际显出不屈精神的节义之士,如劝钱谦益自尽的柳如是、兵败被缚抗节而死的葛嫩〔33〕。这些都是明代青楼女们的正面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