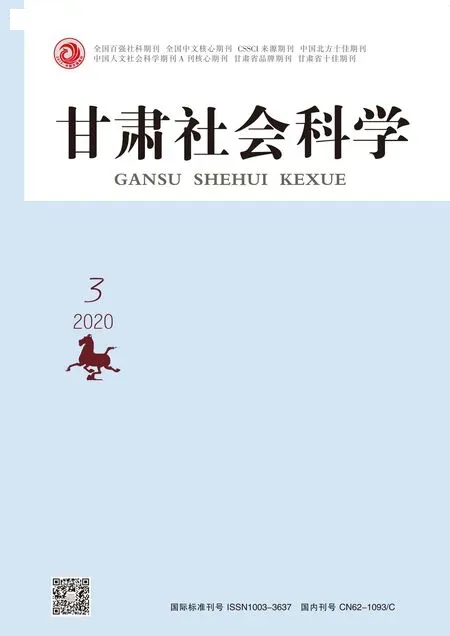城乡统筹发展视角的新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王永军 张东辉
(山东大学 经济学院,济南 250100)
提 要: 从城乡统筹发展的视角系统分析了新型城镇化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新型城镇化对于城乡统筹发展具有倒U型的影响,即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其对于城乡统筹发展的影响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城乡统筹发展水平的提高并不利于经济增长速度的提升,但是由于新型城镇化的互补作用,使得这种不利作用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与此同时,城乡统筹发展对于新型城镇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有门限效应,当城乡统筹发展水平低于某一水平,即泰尔指数高于某一水平时,新型城镇化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而当城乡统筹发展水平超过门限值,即泰尔指数低于门限值时,新型城镇化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相对下降,这也意味着新型城镇化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存在极限的。
一、引 言
长期以来,学者们围绕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展开了激烈的争论。Chenery[1]、Lucas[2]和Krey et al.[3]均发现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Henderson[4]、Bloom and Canning[5]和Shabu[6]则发现城镇化和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有表现出系统的关联性。还有学者发现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是简单地线性关系,而是表现出S型[7]或者倒U 型[8]等非线性特征。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争论,究其根源,则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测度不够准确,二是缺乏对于城镇化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分析。事实上,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简单地以人口城镇化率(城镇人口/总人口)来衡量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已经难以反映现代城镇化的本质特征。这一点对于中国来说尤其如此。中国从2003 年就开始反思传统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并走上了以内涵培育和质量提升为特征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因此,本文将在对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科学测度的基础上系统分析新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进一步来说,新型城镇化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通过多种机制来实现的,不同的机制会对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产生不同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时空条件不同,发挥主要作用的机制也自然不同。因此如果不对各种机制进行区分,那么就无法精确地辨识出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这也是为什么不同的学者使用不同的样本会得出不同结论的根源所在。为了解决该问题,本文将主要聚焦于新型城镇化影响经济增长的城乡统筹发展机制。城乡统筹发展主要表现为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缩小[9]。根据Lewis[10]、Daniels[11]和Keeble & Nachum[12],在二元经济社会中,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流动可以显著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尽管Robbinson[13]、王小鲁和樊纲[14]以及莫亚琳和张志超[15]都认为城镇化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倒U 型关系,但是他们实际上也没有否认随着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最终会走上不断缩小的变动趋势。那么,“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是否也会带来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呢?
二、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测度
新型城镇化以科学发展作为基本理念,以人口发展作为核心任务,以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作为最终落脚点。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其主要包括经济基础、人口发展、社会功能和环境质量等四个子系统。因此结合《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2014—2021)》和相关的研究成果[16-19],我们构建了如表1 所示的用于衡量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在对指标体系内各指标进行加总整合的过程中,我们主要是采用客观赋权法中的熵值法。“熵”是对不确定性的一种度量。一般来说,数据所提供的信息量越大,则不确定性越小,熵也就越小。假设有n 个研究对象,m 个评价指标,xij表示第i 个对象的第j 项指标。则“熵值法”的测度步骤如下:
(1)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以消除量纲、量级以及反向指标的影响。
对于正向指标而言,其标准化的公式为:

对于反向指标而言,其标准化的公式为:


(2)计算第i 个指标值在第j 项指标下所占的比重。
其公式为:

(3)计算第j 项指标的熵值:

(4)计算第j 项指标的差异性系数:

(5)计算第j 项指标的权重:

(6)计算各评价对象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

其中,(7)式中wj为熵值法确定的指标权重,sij为各指标的标准化数值。

表1 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测度指标体系
2002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提出要“走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十六届五中全会更是将城镇化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2007 年10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将城镇化列入“新五化”的范畴。2014 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 -2020》和《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因此,本文将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测度样本确定为2003 -2017 年30 个省级行政区(不包括西藏自治区)。
基于2003—2017 年全国30 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我们首先通过熵值法计算了指标层的权重,所使用的原始数据来自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以及《新中国六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为确保数据的可比性,我们以2003 年为基期对相关的名义数据进行平减。

图1 2003—2017 年各省(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平均发展水平和发展趋势①
图1a 和图1b 分别给出了2003—2017 年各省新型城镇化的平均发展水平和分地区各年新型城镇化的平均发展水平。首先,根据图1a,我们可以发现,上海、北京和广东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最高,而河北、广西和贵州等省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最低。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河北省虽然毗邻北京市,但是其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依然较低。这说明相对于特大城市对周边资源的“虹吸效应”,北京市发展的外溢效应尚未充分发挥。其次,根据图1b,我们可以发现东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要明显高于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并且还高于全国平均的城镇化水平。与此同时,虽然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相似,都低于全国平均的新型城镇化水平,但是中部地区正在超越西部地区,并且差距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最后,根据图1a 和图1b,虽然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都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但是相对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各省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更加均衡,而东部地区各省级行政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水平存在较大异质性。

图2 各省(地区)泰尔指数的平均值及其变动趋势
三、新型城镇化对城乡统筹发展水平的影响
(一)城乡统筹发展水平的测度
虽然城乡收入差距是衡量城乡统筹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但是该指标并未考虑城乡居民人口分布的差异,尤其是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使得城乡人口基数的变动较大,因此本文将采用泰尔指数来对城乡统筹发展的水平进行测度,该指标综合考虑城乡居民的收入分布和人口分布,因此对于城乡统筹发展水平的测度更为精准。设Tt代表某省时期t 的泰尔指数,其计算公式为:

上式中,i=1,2 分别代表城市和农村,It,Pt 分别代表该省的总收入和总人口,增加下标i 则代表该省城市或农村的总收入和总人口,其中总收入使用人均收入和人口的乘积获得。我们得到了28 个省级行政区2003—2017 年共15 年的泰尔指数,在此基础上,我们计算了28 个省级行政区15 年期间泰尔指数的平均值,图2a 给出了各省均值的柱状图,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上海市的泰尔指数最小,因此城乡统筹水平最高,其次是北京和天津,相反,贵州的泰尔指数最大,因此其城乡统筹发展水平最低,此外,云南、甘肃和陕西的泰尔指数也仅次于贵州,城乡之间的差距较大。除三大直辖市以外,黑龙江、江苏、辽宁、吉林和广东的城乡统筹发展水平也较高。
我们进一步将全国28 个省级行政区按照前文的标准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区②,并计算了全国和各地区每一年泰尔指数的均值,图2b 给出了这些均值的变动趋势,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全国还是东、中、西三大地区,其泰尔指数均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尤其是在2009 年之后,下降的速度明显加快。此外,从图2b 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城乡统筹发展水平要高于全国和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则是最低的,东部地区则优于中部地区,成为城乡统筹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
(二)新型城镇化对城乡统筹发展水平的影响
本部分将基于城乡统筹发展水平GAP 的测度分析新型城镇化URB 对其变动的影响,为了对其进行更加精确的分析,我们将引入(1)产业结构升级指数STR,其具体的测算公式为:

(9)式中,μi为不可观测的个体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我们使用2003 -2017 年28 个省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根据F 检验和Hausman 检验,我们最终使用固定效应对样本进行估计,其估计结果见表2。

表2 新型城镇化对泰尔指数变动的影响
从表2 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新型城镇化对于泰尔指数的抑制作用最明显,因此最能够促进城乡统筹水平的提高。与此同时,国际直接投资、人力资本和结构升级指数也都有利于城乡统筹水平的提高。为了更精确地分析新型城镇化对于城乡统筹发展水平的影响,我们进一步使用面板数据分位数模型,分析新型城镇化对于处在不同分位点的泰尔指数的影响,并进一步讨论这种影响的区域异质性。结果发现:首先,无论是全国的整体样本还是分地区的子样本,无论是对于处在10%、25%、50% 还是75%和90%分位数上的因变量而言,新型城镇化对于泰尔指数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因此能够显著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水平的提高;其次,无论是全国的整体样本,还是分地区的局部样本,随着泰尔指数所处分位数的提高,新型城镇化对于泰尔指数的影响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单调性,但是其单调性的方向存在差异,对于整体样本、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子样本而言,随着因变量所处分位数的提高,新型城镇化对于泰尔指数的抑制作用是逐步递减的,而对于东部地区而言,随着泰尔指数所处分位数的提高,新型城镇化对其的抑制作用却是逐步增强的。与此同时,与全国和东部地区相比,在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对于泰尔指数的抑制作用更为强大,结合图2b,西部地区泰尔指数的均值明显高于全国和东部地区,由此,我们大胆推测,新型城镇化对于泰尔指数和城乡统筹发展水平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因此,下面我们将在式(9)中引入新型城镇化的平方项对这种非线性关系进行验证;最后,对于全国的整体样本而言,各控制变量对于泰尔指数都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是对于分地区的子样本而言,各控制变量的显著性甚至是影响方向开始出现明显差异,比如东部地区,三个控制变量的系数在所有分位数的估计中都是不显著的,而中西部地区控制变量系数的显著性虽然得到提高,但是仍然存在部分系数的不显著性,而且与新型城镇化不同,各系数在不同分位数的回归中不存在明显的单调性。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中部地区的面板分位数模型估计中,人力资本对于泰尔指数的影响显著为正,这可能与其人力资本的大量流失有关,对此,我们将在后续研究中进行深入探讨。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将新型城镇化的平方项引入(9)式中,同时对泰尔指数取倒数以更好地对城乡统筹发展水平进行正向描述,为简洁起见,使用其自然对数进行估计,由此得到:

上式中,URB^2 为新型城镇化的平方项,δi为不可观测的个体固定效应,vit为随机扰动项,我们使用2003 -2017 年28 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对其进行估计,经过F 检验和Hausman 检验,个体固定效应是最佳的,其估计结果见表3。

表3 新型城镇化对于城乡统筹发展水平的非线性影响
从表3 的估计结果我们可以发现,新型城镇化的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因此,其对于城乡统筹发展具有显著的倒“U”型影响,即随着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其对于城乡统筹发展水平的影响先上升然后下降。与此同时,产业结构升级也显著有利于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水平的提高,但是人力资本和FDI 的影响则是消极的,尽管对于FDI 来说,这种影响是不显著的。
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统筹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城乡收入差距对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适度的城乡差距有利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工业化的顺利推进,但是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农村和农业的落后将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瓶颈,此时推动城乡统筹发展也将成为新型城镇化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和渠道。
(一)城乡统筹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城乡统筹发展对于经济增长有何影响,这是本节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我们将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衡量城乡统筹发展水平的泰尔指数来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根据前文的分析,我们引入如下控制变量:资本存量③、劳动力数量、创新(以专利数量来测度)、出口额、人力资本(以每万人的在校高中生数量来测度)和新型城镇化。在此基础上,我们将主要考察城乡统筹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部分主要是考察如下三种模型:(1)模型1为简单的线性关系,只引入各变量的一次项;(2)模型2 验证非线性关系,引入城乡统筹发展水平的平方项;(3)模型3 验证交互关系,引入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发展的交叉项。三种模型均使用2003—2017 年全国28 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经过F检验和Hausman 检验,三个模型均使用固定效应方法进行估计,其估计结果见表4。从中我们可以发现:首先,无论是使用张军等[20]方法计算得出的固定资本存量,还是使用单豪杰[21]方法计算得出的固定资本存量,模型2 中城乡统筹发展的平方项均不显著,因此,城乡统筹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是U 型关系。其次,无论是模型1 中的直接线性关系,还是模型3 中城乡统筹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交互项,两者均是显著为正的,这表明,一方面,泰尔指数的增加即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因此使得泰尔指数降低的城乡统筹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但是模型3 交互项的估计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将有利于降低城乡统筹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而且根据上文的研究,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其对于城乡统筹发展的影响系数将下降,因此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城乡统筹发展的速度会降低,因此其对于经济增长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将会逐渐消失甚至会由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转而促进经济增长。最后,资本存量、创新和出口都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劳动力的影响并不显著,甚至符号为负,这说明中国的劳动力供需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劳动力的成本开始上升,导致其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

表4 城乡统筹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
综上,城乡统筹发展并不利于经济增长,但是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不利影响,与此同时,由于新型城镇化对于城乡统筹发展具有倒U 型影响,因此随着新型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城乡统筹发展的速度会降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其对于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并可能由于新型城镇化的互补作用而逆转经济增长持续下行的趋势。
(二)新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上文分析了新型城镇化会影响城乡统筹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那么,城乡统筹发展是否会影响新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呢?本部分就将对此进行分析。在这一节中,我们主要是验证在不同的城乡统筹发展水平下,新型城镇化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因此下面将引入面板门限模型对其2003 -2017 年间28 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其中,门限变量为城乡统筹发展水平。表5 给出了面板门限个数的估计结果,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该面板数据拥有一个门限值,表6 进一步给出了门限值的具体数据和置信区间。

表6 门限变量的估计结果和置信区间

表7 面板门限模型估计结果
表7 进一步给出了该面板门限模型的估计结果,从中我们可以发现:首先,随着城乡统筹发展水平的提高,即泰尔指数的降低,尤其是当其降到0.0312 以下时,新型城镇化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所下降,这也说明新型城镇化虽然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但是这一手段作用的发挥可能也是有极限的;其次,无论是使用张军等[20]的方法还是使用单豪杰[21]的方法计算得到的固定资本存量,其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都显著为正,与此同时,创新和出口对经济增长也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最后,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影响并不稳健,这一方面与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趋势有关,另一方面则与我国人力资本的不合理配置有关。

表5 门限个数检验结果
五、小结与展望
本文系统探讨了新型城镇化影响经济增长的城乡统筹发展机制。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的确对城乡统筹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对处于不同分位数的城乡统筹发展水平而言,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存在重要区别,对于全国、中部和西部地区而言,随着城乡统筹发展水平的提高,新型城镇化对其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强,但是对于东部地区来说,随着城乡统筹发展水平的提高,新型城镇化对其的促进作用却是递减的。而且相对于东部地区和全国的影响程度而言,中西部地区的影响更为明显。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对于城乡统筹发展具有倒U 型的影响,即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其对于城乡统筹发展的影响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分析了新型城镇化、城乡统筹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城乡统筹发展水平的提高并不利于经济增长速度的提升,但是由于新型城镇化的互补作用,使得这种不利作用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进一步来说,城乡统筹发展对于新型城镇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有门限效应,当城乡统筹发展水平低于某一水平,即泰尔指数高于某一水平时,新型城镇化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而当城乡统筹发展水平超过门限值,即泰尔指数低于门限值时,新型城镇化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相对下降,这也意味着新型城镇化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存在极限的。需要注意的是,城乡统筹发展仅仅是新型城镇化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中一种机制,在以后的研究中,我们还将进一步研究新型城镇化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机制。事实上,与传统城镇化模式相比,新型城镇化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经济增长速度上,更体现在经济增长质量上。而所谓经济增长质量,既包括本文所分析的城乡统筹发展,也包括产业结构升级和公共服务供给。因此,从产业结构升级和公共服务供给等角度对新型城镇化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进行分析将成为我们下一步研究的重点。这些机制也将与城乡统筹发展机制一起共同构成新型城镇化区别于传统城镇化的最显著标志,并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全新动能。
注 释:
①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和重庆;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
②与上文相比,东部地区不再包括海南,中部地区不再包括重庆,共包括28 个省级行政区。
③为稳健起见,分别采用张军等(2003)和单豪杰(2008)的方法进行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