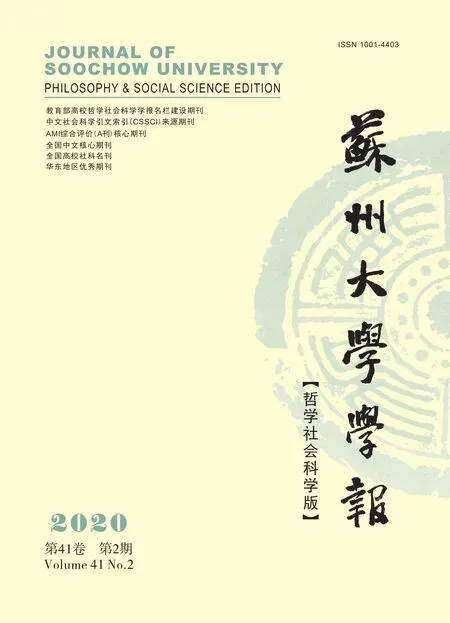葛瑞汉《庄子》英译中的“道”及相关概念的遮蔽
刘 杰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5)
英国汉学家葛瑞汉(Graham,1919—1991)的《庄子·内七篇及其他》是迄今为止众多《庄子》英译版本中较为严谨的学术译作。目前国内的《庄子》英译研究中,葛瑞汉的《庄子·内七篇及其他》多次被提及和论述,研究者大多浮于对其结构形式、语体特点、章前导读做整体性介绍或转述,鲜有人立足于译文自身,对译文概念词句的翻译、思想内容的传达做深入辨析,并探究其背后的文化成因。姜莉在她的《经典的诠释:解构还是重构》中提到:“葛瑞汉对《庄子》文献做了重构式的研究,并且把自己的研究思路贯彻到英译本中去。”[1]147笔者深表认同,正如陈刚指出,如果能在比较研究中对一个概念在另一种文化中的理解程度进行分析,就有机会借此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特质。[2]144故本文立足于葛氏的《庄子》译文,选取核心概念做透视点,在西方二分法的映照中,对比原文本的经典释意,辅以副文本材料,探索“道”“气”“天”等哲学概念在传达中发生的遮蔽,探究葛瑞汉对《庄子》核心概念的遮蔽成因,并揭示出遮蔽背后的文化立场和理论预设。
一、“道(the way)”
“道”作为道家学说的核心观念,不仅给出了世界存在的理据,也揭示了宇宙生成的历程。道家典籍以“道”为中心建立起来的“气”“天”“性”“德”“命”等范畴与“道”一起构成了庞大的哲学体系,反应了先秦时代中国人如何看待个人与社会、宇宙的关系。在《庄子》“道”的英译史上,主要有三种方式,巴尔福将“道”主要译为“nature”,沃森主要译为“the way”,翟理斯和理雅各主要译为“Tao”。从西方文化本身来看,“nature”指整个宇宙万物、生息演变的物质现象及不受人类文明影响的生物。这一定义与“道”有重合之处,但并不能包含庄子“道”的本体论及境界论方面的内涵,为后来的译家所摒弃。《庄子》的第三位译者理雅各基于“道”的丰富内涵在英文世界中很难找到对等词的认识,主张将“道”音译为“Tao”,以避免不必要的误译。这种译法得到了国内译者冯友兰、汪培榕、任秀桦的延续,有一定的可取性,但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不容易带来误解,但没有意义的引导也容易造成无效的翻译。沃森主张用“The way”来译“道”,因为“道”的本意即“道路”“通道”的意思,英文中的“The way”也是在“道路”的本意上引申出13种丰富内涵,这恰好契合了中国“道”的丰富性和包容性,得到了韦利、林语堂、葛瑞汉、梅维恒等人的沿用。但是把“道”译为“way”,同样存在因为中西方概念图式的不完全重合而带来的译入语附加意义的牵连与原语丰富内涵的损耗等问题。葛瑞汉虽然表现出对《庄子》极大的敬意和忠诚,但在编译的过程中,采用“the way”来译“道”,依然反映了在西方二元论的映照下对“道”的遮蔽。
(一)“道”的心灵境界论变神秘论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3]213
庄子的这段话传达了“道”的几个特点:(1)“道”的现实存有身份。(2)“道”的自本自根的自存性。(3)“道”的宇宙终极根源性,即“道”化生天地万物。(4)“道”与物逞游的心灵境界论。葛瑞汉对“道”的中间两个方面的意义传达基本上没有问题,但在“道”的实存性和心灵境界论方面存在问题。
首先,庄子的“有情有信”,意在说明“道是真实而能被信验的”,与《齐物论》中所说的“可行已信,而不见其形,有情而无形”是同一个意思。葛瑞汉曾明确提出,在汉代以前,“情”字的意义是“真实”或“实情”,作为“情感”和“真情”的意义是后来演化来的。[4]59-66然而在葛氏的译文(1)参见:A.C.Graham.Chuang-tzu: The Seven Inner Chapters and other writings[M].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 1981,p.86.葛氏译文:“As for the Way, it is something with identity, something to trust in, but does nothing, has no shape..……it is elder to the most ancient but is not reckoned old.”中,葛瑞汉把“情”译为“something with identity”,即是“有身份的”,意含“真实性”却不直接肯定它的真实存有,把“信”译为“something to trust in”,而不是“可证实的”,在整体意义上虽然没有偏离对“道”的“真实存有”的肯定,但又有一些迟疑。因为“identity(身份)”有真也有伪,假的“identity”是对“道”实存性的一种消解。同时将客观的能被信验的“道”,译成人可以相信的道,强调了人的主体性,描述的中心由道转向人,虽然意义上没有产生重大的变化,但还是对“道”的实存性造成削弱。
其次,“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明人释德清和近人陈鼓应解释为:“‘道’可以心传而不可以口授,可以心得而不可以目见。”[3]213但按葛瑞汉的译文这句话被解释为:道可以传递但不可据为己有,可以领会但不可以看见。两者的显性的差别在于葛瑞汉的英译中作为主体性的“心”和“言”的缺失,隐性的差别在于中西文化背后的某些思想模式的差异,即西方长期受二元相分思想影响,讲究身与心、物质与精神、理性与情感、主体与客体的二元相分,“心”只是身体官能的一种,并没有思考的能力。但古代中国人思想中没有二元相分,尤其是“道”的思想,它拒绝身与心、主体与客体、意识与行动的分离,“心”在中国文化中不仅具有“脑”的思考能力,还包含情感和意识的内涵。正如赫大维、安乐哲所言:“心是一种能够起改造作用的能量之源。像镜子那样去‘认知’,不是要重复这个世界,而是要将其投射于某种光亮中。”[5]50因而葛瑞汉翻译中对“心”的遗漏,给西方读者对“道”的理解造成了一定的障碍,使“道”流于神秘化。尽管葛瑞汉深受赖尔《心的概念》的启发和影响,意识到了中西方“心”的概念图式的不同,但在翻译实践中,还是难以逃脱西方二元文化的强大磁场。另外,原文中“可传而不可受”,本意为“道可以心传但不可以口授”,强调了“道”与“心”“言”的关系。“道可以心传”中的“心”决非西方意义上的官能的心,而是虚空澄明的境界之“心”,是已经达到与物逞游、物我两忘的心境。“道不可言授”是庄子经常论及的话题,葛瑞汉把它译为“It can be handed down but not taken as one’s own(可传递但不可以占为己有)”,虽然没有造成重大错漏,却丢失了与物逞游的心境之“心”和“道不可言”的特点,导致“道”的丰富内涵的消解,给西方读者眼中的“道”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除此之外,《庄子》中还有几处提到“心”,均与“道”的心灵境界有关系。如《齐物论》:“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其厌也如缄,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复阳也。喜怒哀乐,虑叹变执,姚佚启态;乐出虚,蒸成菌。”[3]52这句话是在说那些沉浸在是非利害之中的人们心灵闭塞如受强索束缚,越老越执迷;直向死亡的心灵,再也没有办法使他们恢复活泼的生气了。他们的喜怒哀乐等七情六欲莫不是出自被填满是非利害的心。这里一共出现了四个“心”“日以心斗”的“心”指官能的“心”;“其厌也如缄”中的“其”与“近死之心,莫使复阳也”的“心”统指“心灵”;后文“其形化,其心与之然,不可谓大哀邪”[3]58中的“心”指“精神”。但葛瑞汉统一将这四个“心”译为官能的“heart”,并在两处后文的注释中指出:庄子认为“心”只是用来思考的身体官能,但庄子思想的主题就是反对官能的“心”,认为它仅仅是身体的一部分,它的功能由整个身体和“道”来决定的,它不应当成为支配人的整个生命的主角。[6]50-51葛瑞汉在翻译中统一用“heart”来译心,虽然体现了庄子反对官能的心的特点,却丢失了《庄子》原文中“心”的工夫论的倾向,即养心以至虚空澄明、回应大道的状态,这是“道”由本体论走向认识论的关键。究其原因,还是中西方对于“身与心”“主体与客体”“理性与情感”的认识不同。如果不了解中国文化中的这种主客、身心不分的思想倾向以及认识、伦理、审美一体的文化特质,很容易让西方的读者认为庄子是一位喜欢故弄玄虚的神秘人物。
(二)“道”由整一性转向价值中立
葛瑞汉在对“道”的“整一性”的翻译中也透露出与原文不一样的地方。“道”第一次出现在《齐物论》的以下段落:
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道隐于不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是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3]62-67
这里庄子提出因“成心(completed heart)”(2)葛瑞汉把“成心”翻译译为“completed heart”有些欠妥贴。明代的释德清解“成心”乃是“现成本有之真心”;近人蒋锡昌解“成心”乃是“天然自成之心或真君所成之心;陈鼓应认为都不对,他赞成成玄英、王闿运等人的观点,认为“成心”即“成见之心”,意指片面的、不完整的一己之点。葛瑞汉把它译成“本心”大概是受蒋锡昌的影响,其意义与原文的文旨发生了变化,势必会造成西方读者对“道”的理解前后矛盾。如果用“completed heart”来译“成心”就会让西方读者误以为,“成心”乃是一种原自本性未染之心,是完善之心,是体“道”的一种必备条件,与前后文失去衔接。因为前文论及“成心”与 “言”和“彀音”的区别,是对后文“道”由于“成心”的遮避而生是非判断标准、最终提出“莫若以明”的铺垫。因此这里的“成心”更偏重于意识层面的“成见”,“completed heart”的译法有些悖离原意。而生“是非(that’sit/that’snot)”判断的标准,论说“道”具有普遍、全面的意义,但事物真相往往被“小成(formation of the lesser)”之心遮蔽,人只有去除“成心”,打开封闭的心灵,消除彼此、是非的差别才能用心如镜,关照事物的本然情形。葛氏在译文中(3)参见:A.C.Graham.Chuang-tzu:The Seven Inner Chapters and other writings[M].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81,pp.52-53.葛氏译文:But if you go by the completed heart and take it as your authority, who is without such an authority?……Therefore I say: ‘The best means is Illumination.’”,把“是”译为“that’s it/is”,“非”译为“that’s not/other”,“彼”译成“other”,“此”译为“it/that’s it”,“因是”译为“that’s it which goes by circumstance”。这里葛瑞汉似乎混淆了“是/非”的两种用法:第一种是指代词“这”(is this)或“不是这个”(is not)。第二种是判断一个行为“正确”(is-this)或“不正确”(is not)。葛瑞汉指出:“作为相近的指示词它们表明,我们根据当时距离于我们近或远来赞同或反对。”[7]177“近”(this)则“是”(is-this),“远”(that)则“非”(is-not)。翻译中,葛瑞汉通过对“是非”与“此彼”的对应关系的操纵,来解释因个人的主观性导致是非争论的无意义,认为不如放弃区分,放弃“成心”,取消万物之间的差别,这样才能把握住“道枢”(the axis of the Way),达到对道的真正领悟。在另一段话中,庄子提出了“为是”说: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为是而有畛也,请言其畛:有左,有右,有伦,有义,有分,有辩,有竞,有争,此之谓八德。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3]91
原文意思是“道”是没有界线和分别的,与其争论是非,不如放弃是非选择。这里的“为是”在原文中有两解:释德清认为“为是”当作“只因执了一个‘是’字,故有是非分别之辩”;蒋锡昌认为“儒墨之间,只缘为了争一个‘是’字,故有彼此人我之界,以致辩论不休也”[3]92。葛氏在这一段译文(4)同上,p.56.参见原文:“The Way has never had borders, saying has never had norms.……but he does not argue over alternatives.”中采用释德清解,将“为是”理解为“由于坚持一个‘是’的标准”。庄子在这里提出了“为是(that’s it which deems)”与上文的“因是(that’s it which goes by circumstance)”相对,“因是”即“顺应自然情势”。葛瑞汉认为这是庄子的新造词,意在说明顺应“道”即“因是”的做法是可取的,而为了暂时方便以命名的方式来划分万物是“为是”的做法,最终会导致偏离“道”。葛瑞汉基于对西方哲学中“真理与价值”判断标准的关注,发现庄子很早就注意到了儒墨辩论中判断的主观成分,大家都不关心事实和真理是什么,而是从自己的立场来确定判断标准并对事物进行命名,做出价值选择。葛瑞汉将这种行为总结为“名实不符”。庄子的“方死方生,方生方死”“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说明了标准本身的变动性必然会导致价值判断的无穷相对性,这种真理与价值的割裂的背后隐藏着对“道”的偏离。庄子认为事物是变动不居的,矛盾双方在同一时刻共存或是相互转化都有可能,用各自的立场和标准去命名、区分事物变得毫无意义,因此大道“不名”“不言”,不做选择,自然而无为,即是顺应大道。在葛瑞汉看来,“道”的这种“不论”“不议”“不辩”是一种价值中立,是一条与西方伦理价值体系迥异的伦理途径。葛瑞汉因此把庄子看成一个相对主义者,认为他弃绝区分、命名和二者择其一的价值选择,而最终符合于“道”。他译笔下的“道”不仅传达着庄子注重平等的思想,让许多西方的生态环保主义者找到了共鸣,同时流露出价值中立的伦理意向,这是一种过度解读,对原典中的“道”产生了遮蔽。
二、“气”(breath,energy)
“气”是《庄子》哲学中的重要概念,据黄柏青统计:“‘气’在《庄子》中一共出现了43次,其中单独出现了17次,作为复合次出现有26次,另外还有以‘阴阳’表‘气’的出现有20次,以‘一’表‘气’的出现有13次。”[8]72“气”本意指云气,春秋时期除了天气、地气之外,《国语·周语上》出现了阴阳二气;《左传·昭公元年》中出现了“阴、阳、风、雨、晦、明”六气的概念;至《老子》,“气”开始被提升为哲学化范畴;《管子》“内业”篇提出了“精气”说;《庄子》继承了管子的精气理论,把它转化为一种蕴含世界本源范畴的无限性、普遍性、变化性的“气”论,沟通“道”与万物的关系。具体来说,《庄子》的气有以下几个含义:(1)指充盈于天地间无所不在的自然之气。(2)指阴阳二气,有时用“一”来指称。(3)指人的精神、活力之气。(4)是生化万物的本原之“气”。葛瑞汉对《庄子》“气”的体认是建立在他对《列子》之“气”的翻译基础上的。
(一)一意两译造成“气”意义的含混
1960年葛瑞汉译《列子》时将“气”译成了“breath”“air”“energy”和“vitality”四种形式。在翻译《庄子》前,葛瑞汉发现历史上的不同译家对《庄子》的“气”进行了多样化的翻译:翟理斯将“气”译为“breath”“vital fluid”“soul”和“substance”;理雅各译为“breath”和“spirit”;沃森译为“spirit”和“energy”;冯友兰译为“vital breath”“spirit”和“nature”。[9]57-59葛瑞汉综合前人的做法,在1981年翻译的《庄子》时统一将“气”译成了“breath”和“energy”两种形式。葛瑞汉在《庄子·内七篇及其他》的副文本部分指出:
“气”是根植于古代中国的宇宙论哲学中一个与我们有根本差别的概念。在古代中国,宇宙不是由惰性物质构成,而是一池有能量的液体,即气,事物从其中浓缩而来,又消融于其中,如此永不停息地循环。它其中最纯、最透明、活动的是促进人生存的呼吸之气和最具激情活力的精,即生理学上所称的精液。在宇宙整体中,有一部分轻盈之气上升成为我们呼吸之气,更厚重的、惰性的“气”沉积下来成为地,在人身上则凝结为身体。在这个宇宙哲学中,世界万物被非实体的、自由运动的天空上的气所激活,思想家有时将“气”人格化,而人格化到什么程度则要看他们把天和人的类比推得多远。[6]76
这说明葛瑞汉对“气”的理解有一定的理论自觉,经历了一个不断修正和重建的过程。葛瑞汉删繁就简保留了“breath”或“energy”的译法,表明他对庄子之“气”进行了体认,并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自然物质始基之“气”(breath),一类是生命能量之“气”(energy)。他在译文中将“breath”的用法分为两方面:(1)“道”生化出的具有化育万物能力的“气”,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与“道”并提。(2)世间万物的生理气息,即人体或动物的生命存在,靠呼吸空气来促进血液循环,血气运行。“energy”也分为两个方面:(1)指人的精神、活力之气。(2)指阴阳之气。葛瑞汉对自然物质始基之“气”的翻译很好地传达了“气”论的思想,但在对第二类生命能量之“气”的翻译中出现了一意两译的混乱现象。
如《庄子·知北游》:“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之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故曰,通天下一气耳’。圣人故贵一。”[3]646
庄子认为“气”通过聚散化生万物,生命的存在是宇宙大化流行的产物,物与物间的相互转化均是“气”的作用。在葛氏译文(5)参见:A.C.Graham.Chuang-tzu:The Seven Inner Chapters and other writings[M].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81,p.160.葛氏译文:“Man’s life is the gathering of energy;when it gathers he’s deemed alive…… Hence it is said:‘Pervading the world there is only the one energy’ That is why the sage values the One.”中,葛氏选用“energy”来译第一个“气”,没有问题,这里的气指影响人的生死、趋动人的生命活力之气。但后文当中的“通天下一气耳”中的“一气”被译为“energy”,而它本来指具有本根作用的生化万物的物质始基之“气”,是万物齐一思想的延续,在其他地方通常被译为“breath”,但这里葛瑞汉却将它译为“energy”,即出现了将作为物质始基的“气”一意两译的现象,反映出葛氏对《庄子》之“气”理解上的混乱,或是对“气”化思想的无意识。
(二)知识论背景对“气”的钳制
“心”在《庄子》中重复出现达186次之多,除此之外还有大量未用心表达却指心的词,可见“心”的概念在庄子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心在《庄子》中有三重含义:一指官能的心;二指心理活动;三指人精神活动的主宰,是认识主体、道德主体与修养主体的统一。由于葛瑞汉的翻译中,“心”往往被统一译为“heart”,其官能之心的意义被保留,而其他含义常被遮蔽消失,影响了与“心”相关的“气”概念的建构。如《庄子·人间世》:
“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3]139
此句意在说明:心志专一,不用耳听而用心去体会,不用心去体会而用气去感应。耳的作用止于聆听外物,心的作用止于感应现象;“气”是空明而能容纳外物,只有达到空明的心境,道理才会自然显现。在此处的葛氏译文(6)参见:A.C.Graham.Chuang-tzu:The Seven Inner Chapters and other writings[M].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81,p.68.葛氏译文:“Rather than listen with the heart listen with the energies.……The attenuating is the fasting of the heart.”中,直接省去了“若一志”,因此“若一志”中隐藏的“心”被直接忽略掉了。其次,“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葛瑞汉用“energy”来译此处的“气”,把“气”看成一种纯能,但以往的译者理雅各、冯友兰、沃森选均用“spirit”来译“气”,都有一定道理又有其局限。因为整句话论述了“心”“气”“虚”“道”四者的关系,即内心排除外物干扰,呈现虚气空明的心理状态,就能用心如镜,顺应大道。此处的“气”可以视为一种抽象的虚的精神状态,因此理雅各、冯友兰、沃森选均用“spirit”来译“气”是合理的,但是显然“spirit”只能显示“气”的内涵而无法呈现“气”的外在物质形态,存在一定缺陷。葛瑞汉选用的“energy”,源自希腊文“υργεια”,意为“在工作中”“在活动中”,后作为物理学术语,本意指能量、精力、活力。在现代物理学知识背景中,“气”的确是一种“能量”,因而葛氏的译法很容易被西方读者理解,但这种站在西方知识背景下,用现代科学体系下的概念图式来阐释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的做法,势必会在翻译、阐释的同时消解掉《庄子》“气”的其他意义。而且文中的“心”“气”“虚”“道”四者是一个紧密相联的生发机制,但在葛瑞汉的译文中,四者之间的联系因为“心”与“气”意义传达的折损而变得松散和随意,影响了对《庄子》气论和道论的传达。
葛瑞汉对第二类“气”译为“energy”,指具有驱动生命活力的阴阳之气。《人间世》曰:“事若不成,则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3]145葛瑞汉译为:“If the enterprise fails, we are sure to suffer the penalties of the Way of Man, and if it succeeds we are sure to suffer the maladies of the Yin and Yang.”[6]70这里的“阴阳之患”指“因阴阳之气激荡而致失调患病”,葛瑞汉直接将“阴阳”译为“the Yin and Yang”,并未加“energy”。但在前言部分,葛瑞汉已经表达了对“阴阳即气”的认识:“气是一种流动的纯能,为我们提供生命活力。人体内的气分阴、阳两种,人的出生和生长是阳气的作用,人的疾病和衰老是阴阳两气不平衡所致。中国的宇宙学中阴阳不仅存在于人的体内,也存在于整个宇宙,它可以引申为明与晦等其他对立模式。庄子沿袭了古代的‘六气’说框架,‘六气’即指阴、阳、风、雨、光明和晦暗。庄子从传统的生理学角度思考,他建议我们培养自发的能力,而不是使用心去思考、命名、归类和设置目的和行动规则。”[6]7葛瑞汉明确了“阴阳”为六气中的两种相对的气体,天清、地浊是阴阳二气调和的结果,而“培养自发的能力”即是前文所说的对“虚而待物”能力的培养,即“心斋”。庄子由气化理论提出物化(庄周梦蝶),最终提出心斋,“气”论的生成机制得以完美生成;但葛瑞汉似乎无意于对庄子“气”论体系的完美复制,而是凭经验从西方的知识背景中寻找“气”的对应概念,赋予它“纯能”的译名,并用现代科学思维为它正名。
客观说来,葛瑞汉基本准确地传达了庄子“气”的不同内涵,但在不同的语境中,由于受到西方二元相分等知识背景的影响和对庄子“心”的概念的忽视,造成了对“气”论的生成机制的钳制,进而影响了对《庄子》“道”论的准确传达。
三、“天(heaven/sky)”
“天”在先秦哲学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将“天”总结为“物质之天”“人格之天”“命运之天”“自然之天”“义理之天”。[10]44《庄子》全书“天”一共出现650多次,除了承袭“自然”之天外,“天”与“道”融通,是“道”的境界的另一种表述方式,如“天府”“天倪”“天钧”“天机”“天理”“天游”等。除此之外,庄子还第一次将“天”与“人”进行对举关照,同时又主张 “天人合一”。葛瑞汉对“天”的翻译基本上可以做到忠实,但在副文本部分对“天”的总结中,却表现了与原文不同的文化景观。
(一)副文本中对“天人关系”中“天”的倾斜
1960年葛瑞汉在翻译《列子》时,用“Heaven”来译具有道家哲学色彩的“天”,用“sky”来译作为“自然天空”的物质的“天”。葛瑞汉翻译庄子时延续了这一做法,但表现出对《庄子》中“天人关系”的格外关注。他在《庄子·内七篇及其他》的序言中提到:“天人相分在公元前350年左右就引发了一些难题,如果我们承认人有本性,而本性独立于人的意志,因此本性由‘天’规定,那么不是应该理解为:人由于服从自己的本性,因而服从于‘天’,那天性似乎不就与道德是冲突的了吗?”[6]14
在这里葛瑞汉发现庄子 “天人相分”理论无法为他的伦理道德体系进行奠基的问题,因而着力强调“天人合一”的思想。从某种程度上说,中西方文化的分岐可以浓缩为对“天人关系”认识的分途。西方自古希腊开始,在毕达哥拉斯的“数”,巴门尼德的“一”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思想形塑下的西方文化主张灵肉对立,身心相分的“二元论”主张[11]156-162,即崇尚理性,强调因果逻辑,与道家主张的“万物一气”“天人合一”的思想形成鲜明对照。葛氏认为庄子的“天人合一”“道枢”精神,既不遵从理性意志,也不受情感左右,而是顺从天性指引,离形去智,自然无为,很好地弥合了西方伦理哲学中“理性”与“情感”“动机”和“行为”之间的裂痕。因此葛瑞汉在对庄子“天”的翻译中如实地翻译了自然之“天”和作为“道”之“天”的部分,但当涉及“天”与“人”的关系时,尽管他意识到了庄子思想中“天人相分”的一面,但他还是直接删去了《秋水篇》中“何谓天?何谓人?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4]496这一段关于“天人相分”的内容,把焦点集中于“天人合一”中的“天”。
(二)“二分法”映照下对“天”的扭曲
所谓“二分法”,即西方从苏格拉底时代开始,长期在因果的逻辑思维主导下形成的理性与情感、天与人、主与客截然相分的知识体系。西方在“二分法”的基础上形成了以理性为主导的伦理价值体系,与中国在“天人合一”的基础上形成的关系式伦理价值体系呈现出较大不同。葛瑞汉在进入中国先秦道家文化之时,以西方的“二分法”作为参照,发现中国先秦道家文化的殊性特征,并不自觉地渗透到了他的译文及注释中。
如“虽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后当,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讵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所谓人之非天乎?……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3]200这段文字,在原典中它表达的是具有怀疑精神的庄子对“知”提出的怀疑。因为知识必须有固定的依凭对象才能判断它是否正确,但依凭的对象却是变化无定的,那么我又如何知道我所谓属于天然的不是属于人为的,属于人为的不是属于天然的呢?这里的“天”仍然是自然之“天”,葛瑞汉如实地翻译了原句内容,但在后文注释中,他点评道:“在这一段内容中,庄子试图对第二章他曾引用的或构想的问题提出疑问,即人们把二分法当成理所当然,对人的思想或行动过程中源于天的自发性悬置不议,如人的身体是由天所生的‘气’所支撑,只要人照顾好身体就能活到自然阳寿。但是我们能在自然的行为和人为的行为之间做出选择吗?庄子最后重新批判了二分法,认为圣人本质上仍然是受天所支配,无论他是否认同天人合一的思想。”[6]86
这里葛瑞汉提到了两个关键问题,一个是“二分法”,一个是“自发性”。“二分法”的本质是真理和价值的问题。葛瑞汉发现中西文化最大的不同在于,西方是以理性为基础的分析思维,注重主与客、身与心、理性与情感、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而中国是以“道”为基础的关联思维,拒绝天与人、身与心、理性与情感的简单二分。葛氏认为中西在二分法方面的分歧最终导致了中西方的伦理哲学的分途。西方以理性为最高法则为道德行动寻找理据,而中国则以圣人自发的道德行动作为楷模引领人们走上正轨。由于理性主义自身的缺陷,近现代西方伦理哲学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理性主义危机,20世纪初的许多被奉之为经典的科学理论被推翻,整个科学的根基几乎被动摇,人们陷入普遍恐慌。葛瑞汉基于对这场危机的关注,在孔子的“礼”,道家的“道”中发现了“自发性”。

葛瑞汉认为:“庄子继承了我们称之为从孔子而来的预设传统,行动发自自然而被智慧所指引。”[13]224即上文翻译中的“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基于《天地》篇有云:“物得以生,谓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命;留动而生物,物成生理,谓之形;形体保神,各有义则,谓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是谓玄德,同乎大顺。”[3]363葛瑞汉发现“自发性(自然)”与道、气、德、天、性之间的紧密联系:万物得到道而被生化是德;没有形体却有阴阳之分,称之为命;元气中浊气停滞而生成物,各具形态称之为形;有形之物保有精神,各有规则,叫作性;经修养返于德,德同于太初,太初即虚,包容天地,同于自然。而葛瑞汉认为,自然的倾向就是“德”,德源于潜藏于内心的性,性生发于“天”,因而古代中国人身上的德不仅包含了圣人的全部潜力,也潜藏于普通人的人性深处,而培养德的唯一途径就是养气。《大宗师》的这一段译文中的“天”均是“自然”之“天”,人则是受“天”支配、有回应天的能力的人。当人能够依照自然行事,无为而活,就具有了对客体自然的回应能力,与天合而为一。葛瑞汉用“heaven”对庄子哲学化的“天”进行统一化的翻译,本身可能不存在对“天”的错译,但在前言、注释及章前导读等副文本部分,葛瑞汉对人源自“天”的“自发性”的解读及理论预设呈现出与传统庄子哲学不同的理解面向。
四、小结
葛瑞汉在西方汉学界素来以严谨著称,他对于《庄子》的翻译和研究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西方对“道”理解的庸俗化倾向,其功绩毋庸置疑,但在翻译中难免因中西方概念图式差异而碰触暗礁。然而正是通过研究这些暗礁所激起的思想涟漪,我们才能够按图索骥,找到中西方文化差异背后的理论预设。
葛瑞汉从自身固有的文化背景出发,带着西方现代伦理哲学疑惑来解读《庄子》中的“道”“天”“气”等重要概念,把庄子定义为怀疑论者、神秘主义者,显然是基于自己的文化诉求,在理解和翻译过程中增加或减损了庄子的“道”及相关概念的内涵。张隆溪先生在《道与逻各斯》中曾经把中西方两种思维模式概述为“道”和“逻各斯”,葛瑞汉在进入《庄子》之前有着类似的文化立场。他认为中国先秦古典文化与西方的古典文化的思维构成因子类同,只是主流思想朝着不同的构成因子而去。西方在巴门尼德的“being”,柏拉图的“idea”,普罗提诺的“the one”,圣奥古斯丁的“God”,康德的“thing in itself”等理论建构中走向了“逻各斯”中心主义,而中国先秦古典文化在儒道合流的趋势中走向了对“道”或“自发性”的体认。他认为曾经创造了无数辉煌文明和领先科技直到近代才开始没落的中国文化蕴藏着医治西方理性主义危机的良方。
葛瑞汉对“道”及相关概念的翻译启发我们关注中西方对“心”及“价值”问题的理解差异,这些差异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文化塑形期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不同的思维方式产生了不同的文化框架,决定了人类未来的文化走向。具体来说,西方长期在二元相分基础上形成了一套以理性为标尺的数理逻辑和伦理哲学体系,与中国在“道”或“关联思维”的模式下形成的以感应、类推为基础的美学的、诗性的、关联的体系大相径庭。葛瑞汉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些差异,在肯定“道”的同时,努力尝试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立场。遗憾的是,作为历史文化生活中鲜活在场的个人,他也很难逃脱被哺育过他的西方文化束缚的夙命。但无论如何,我们该为他的执着称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