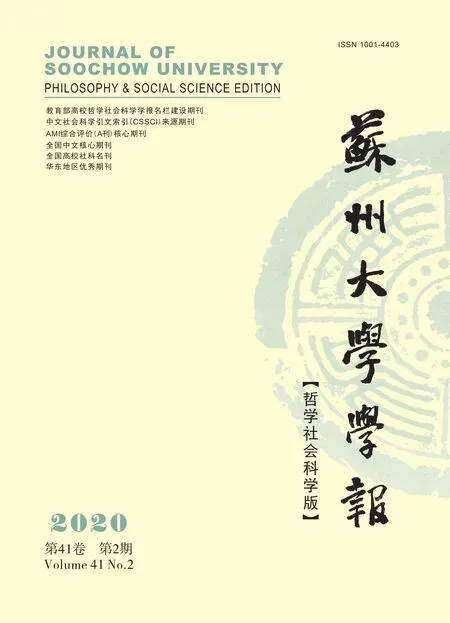跨越真实与想象的边界:阿尔比戏剧《海景》中的空间解读
王瑞瑒 周 丹
(1.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6;2.南京审计大学 科研部,江苏 南京 211815)
爱德华·阿尔比(Edward Albee, 1928—2016)是美国现当代最为杰出的戏剧家之一,曾三次获普利策戏剧奖,被誉为“美国戏剧史上最全面地捕捉和展现社会情状的戏剧家”[1]47。《海景》(Seascape, 1975)是阿尔比第二次斩获普利策戏剧奖的作品,著名评论家克莱夫·巴恩斯(Clive Barnes)评价其为“一个伟大的事件”“含义相当丰富,不论是情感上还是智力上的”。(1)参见Clive Barnes,New York Times,January 27,1975.该部作品的诞生正逢二战后的数十年,“水门事件和越战失败”导致民众一直以来的乐观主义受到“激烈震撼”[2]211。“富足和高经济预期造就了所谓的‘城市危机’”,在许多城市,“工作没有了、人也走了、人们对于未来的乐观心态也不复存在了”。[3]231作为一名密切关注社会动向的戏剧家,阿尔比将这些“美国独特的社会问题”[4]258融入《海景》的创作之中,他以自然布景隐喻生活空间,让“剧中主要角色都来到了海洋——这一位于地理边缘的自然空间”[5]309,并用幻想空间展现真实生活,将所有情节都“放置在位于陆地和海洋、过去和未来、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复杂的、充满变化和挑战的空间边界之上”[6]8,以后现代主义笔触完美呈现了美国20世纪中期影响较为深远的危机图景。
《海景》的主要情节在南希和查理——这一对中产阶级夫妻身上展开,出于对喧嚣城市生活的逃避,他们来到了沙滩之上,而正当他们在沙滩上享受生活时,两个人形蜥蜴——莱斯利和莎拉出现了。与南希和查理逃离城市生活的状态一致,这对蜥蜴夫妇也厌倦了海洋深处的生活,渴望探索新的外部空间。从表面来看,大片沙丘和海滩是舞台空间对于自然环境的重构,但这种舞台空间早已演化成了社会空间的一个模拟体,变成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笔下“巨大对抗的场所”[7]10,成为“体现权力斗争关系的运动与变化、张力与冲突、政治与意识形态、激情与欲望等的复合物”[8]174,让人类夫妇感受到了对未知环境的恐惧、对个体疏远的疑虑以及对自我生存状态的担忧。阿尔比以多重模拟自然的空间展现了城市危机,通过对称的舞台结构实现了“镜像”人物角色的塑造,并给出了跨越真实和想象空间的合理路径。
一、自然空间的多重建构
在《海景》一剧中,阿尔比并未延续《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Who’sAfraidofVirginiaWoolf?,1962)或是《微妙的平衡》(ADelicateBalance,1966)中位于“房屋内部”的中产阶级夫妻的相处模式,而是把情节的展现地点建构到了城市之外,借由创新的自然空间来演示另一视角下的城市生活。《海景》的舞台布景所涉及的“道具、服装更是全部使用环保材料”[9]5,在亲近自然的舞台环境中,观众完成了与真实自然的零接触。根据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的观点,“可以根据物质想象”,将物质分为“‘火’、‘空气’、‘水’和‘土的依附’(2)加斯东·巴什拉提出的物质分类可细化为:“土”为大地、沙漠等,“水”与溪流、大海联系,“火”则可以同“指导着信仰、激情、理想和人生哲学的某类遐想”联系起来,在《海景》中信仰的化身便是蜥蜴夫妇,而“气”则是自由的向往与生命的奥秘,是灵性的象征,在文中便隐喻了自然本身。参见高方、樊艳梅:《勒克莱齐奥作品中自然空间的构建》,《外国文学研究》2013年第4期,第124、126、128页。”[10]6。《海景》中大海,沙滩恰好对应了“水”和“土”,蜥蜴对应了“火”,而自然本身则对应了“气”,它们共同组合成了三层自然空间:即以大海、沙滩为主体的静态元素空间、以人形蜥蜴为主体的动态元素空间以及自然与城市交汇的景观元素空间,这也使得自然空间成为展现城市形象的另一面“镜子”,与20世纪60年代自然与城市间矛盾日益扩大的社会情状相吻合。
生态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指出,“世界的启示在‘荒野’”(3)在A Sand County Almanac and Sketches Here and There(《沙箱年鉴》)一书中,奥尔多·利奥波德引用了梭罗的名言“世界的启示在‘荒野’”来印证自己的观点,他指出,荒野中的动物、群山、河流背后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奥秘,回归荒野可以帮助人类进行客观的思考。参见Aldo Leopold.A Sand County Almanac and Sketches Here and There.Oxford UP,1949:133.[11]133,他认为在回归“荒野”(Wilderness),回归“未经开垦的原生态自然”[12]89的过程中,人类可以更好地找寻自我的本质。《海景》的创作即践行了这一构想,所有人类活动的情节均被安排在了海边天然的沙滩上,最初版本的第二幕甚至完全被安排在海水下(4)《海景》一剧最初有三幕,后阿尔比将第二幕——蜥蜴夫妇将人类夫妇带回水底的家中的情节删去了,一是因为在试演过程中,演员被章鱼攻击了;二是因为阿尔比觉得“无法驾驭”这种形式。参见Mel Gussow.Edward Albee:A Singular Journey.Applause Theatre Books, 2001:291-292.,它们共同组成了静态元素空间。大海通常被认为是“位于表层经验下无法触碰到的深层经验的一种隐喻”[13]152,男主人公查理在年少时便体验过这种“深层经验”,他常常“沉在游泳池底部,直到自己需要氧气再浮起,在底部静静思考”[14]378,他会“游泳,在水面拍打,看看天空,休整,然后沉下水底……在这一过程中,甚至还有鱼同他说话……”[14]379对于成年后的查理而言,大海所代表的自然空间还多了一层“深层经验”——那便是成为他梦寐以求的“避难所”。查理在《海景》的开头和南希提到,他们来到海边是为了“逃离喧嚣的城市生活”,是为了近距离触及美丽的自然风光,同行的南希也曾抱怨道:
为什么我们不能像老人一样,为什么不能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卖掉,然后背着一个小包就去加尼福利亚,或者去那些有农场的沙漠中……为什么我们不能和寡妇和鳏夫一起玩乐透、凯钠斯特,吃谷物?[14]375
南希的话语中饱含着对自然空间的向往,却也从侧面反映出人类具有消费主义性质的扩张带给自然空间的巨大冲击。随着经济生活的日益繁荣,人们对于度假地点的选择也由偏远的城市转到距离更远的乡村、直至变为“草木葱茏、蔓延扩展出的郊区”[15]8,甚至是无人踏足的“荒野”,自然空间也逐步被降级为人类城市生活可有可无的附属品、人类逃避城市空间的“避难所”,一点点治愈人类因为“物质文明所带来的各种精神疾病和行动上的延宕”[16]34。
如果说静态景观元素是阿尔比对于舞台空间的第一次创新,那么人形蜥蜴的展现实则是阿尔比对于舞台设计发起的第二轮挑战,他在关于《海景》的特别采访中提到,“在海洋的底部存在着史前的鱼类,他们可能会进化,而进化的模式也促成了成千上万的改革模式。”[17]289主人公查理曾多次表达他从年少以来便怀有的一个梦想,他希望在海底看到一种鱼,“有手、有腿、住在珊瑚之中……而且足够大到可以不被吃掉”[14]377,这样的愿望很快在第一幕的结尾以一种“近乎疯狂”的方式得到了实现:在沙滩和海洋的连接处,穿着蜥蜴服装的演员模仿着蜥蜴匍匐前行的动作,肚子贴着地面,从海洋慢慢爬到了沙滩上。蜥蜴夫妇实则是“变形”(5)汪义群在《西方现代戏剧流派作品选》(五)一书中指出,塑造“抽去个性的人物”是荒诞派戏剧常用的表现手法,具体可分为三种模式:第一种是制造一些“来历不明的人”,没有国籍、职业、出身、教养的区别;第二类方法是“使人物失去个性”,人物的身份可以相互转换;第三种则是“变形”,如三只鼻子的女儿等。《海景》中的莱斯利夫妇有着蜥蜴的身体、姿态和生活习性,同时拥有人类的面庞,并且会说英语,这些都符合第三种“变形”人物的特点。参见汪义群:《西方现代戏剧流派作品选》(五),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的查理和南希,他们和人类的相处过程其实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模式。虽然动物元素在阿尔比的作品中早已屡见不鲜,譬如《动物园的故事》(TheZooStory, 1959)中被主人公杰瑞残忍杀死的狗,或是《山羊,或谁是西尔维娅?》(TheGoat,orWhoisSylvia?, 2000)中悲惨死去的山羊,但《海景》中的蜥蜴夫妇却大有不同,他们“不仅仅作为叙事元素存在”[6]6,而是真正参与并推动了剧情的发展。蜥蜴夫妇有着自己的名字——莱斯利和莎拉,他们和人类夫妇的对话模式也像“镜子”一般,折射出人类从自然个体向社会群体的动态转变。
随着戏剧情节的发展,由第一、第二层自然空间所维系的视觉平衡很快被充满矛盾冲突的“第三层空间”打破。在戏剧的开头,“在静谧的沙滩上,喷气式飞机的轰鸣声从舞台右侧一直蔓延到了左侧,慢慢变大,然后变得震耳欲聋,接着消失得无影无踪”[14]371;而后在南希和查理畅想美好未来的时候,“喷气式飞机的声音再次出现,从舞台的右边传向左边,不断变大,变得更加震耳欲聋,然后消失”[14]376;最后在查理夫妇和蜥蜴夫妇交谈的过程中,“喷气式飞机的声音从舞台的左侧到了右侧,逐渐增长,变得震耳欲聋,然后消失”[14]433。喷气式飞机若干次不合时宜地出现打破了舞台上宁静和谐的氛围,也将自然环境与现代工业社会的矛盾以直观的方式呈现于舞台之上:20世纪中期,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环境受到了巨大的破坏,“开发商的推土机推平了山地,填平了湿地和溪流,并清除了存在已久的植被”[18]262,而一直以“居高临下的嬉戏态度”[19]499面对自然的人类也从未想到由于“大量排放二氧化碳,以及广泛使用农药和塑料制品,将付出的难以预计的代价”[20]214。出于对自然状况日益恶化的担忧,阿尔比借助飞机和大海的交汇、机械和海鸥的碰撞等来呈现自然与城市的冲突,以此来提醒观众:人类与自然是密不可分的整体,人类对环境的破坏,对自然的入侵最终会报应到人们自身。通过自然元素的建构,蜥蜴角色的塑造,自然空间和城市空间的冲突,阿尔比成功实现了将原始与现代、真实与想象、自然与社会放置在一起的创作意图,由浅入深地书写了工业文明社会下,城市与自然之间不可忽视的矛盾,也向观众展示了人必须“回归、尊重动物,构建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和谐”[16]32才能真正实现与自然和谐、平等相处的美好愿景。
二、人类-蜥蜴对话的“镜像空间”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剧作家兼导演,阿尔比擅长用舞台空间呈现主要角色之间的力量对比和心理转变。在《海景》中,阿尔比又有突破,通过舞台结构空间建构了“前对话-后对话”、呈对称模式的人类、蜥蜴交流空间,借以刻画两者之间真实的交流状态。胡妙胜教授在《充满符号的戏剧空间——舞台设计论集》一书中提出,根据“舞台设计与戏剧的物质与信息联系”[21]3,舞台设计主要有三个功能特性,分别是S:组织动作空间,E:再现动作环境,A:表现动作的情绪与意义。S组织动作空间即“从事件和动作出发,为整个戏剧动作的进程确定合适的舞台空间结构”[21]32,E再现动作环境,包括“说明剧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交代事件,促进戏剧情节和冲突的展开,揭示人物的境遇、性格和心理状态”[21]10等,A表现情绪与意义,“是剧中人物的精神世界在空间上的投影”[21]12,它提供了一种“编码了的感情,传达了戏剧动作的情绪与意义”[21]13,16。根据“功能的不平衡性”,“顺序、主次、强弱”的不同,可以将这些功能以不同的方式组织在一起,主要有三个基本模式(如图1):S-E-A,E-S-A,A-E-S,处于三角形顶端的表示“出发点或是优先地位的因素”[21]31,三角形的另外两个顶点则是呈现强—弱(左强右弱)的关系,舞台功能出现的先后顺序也代表了剧作家对于空间组织不同形式的侧重。

图1
在蜥蜴夫妇和人类夫妇的“前、后”两个对话环节中,阿尔比实则尝试构造了S-A-E/E-A-S两种“镜像对称”(6)严格从三角形的布局形状来看,S-A-E和E-A-S在图形上并不呈现镜像对称,本文提到的“镜像对称”是按照其意义来阐释的。我们可以将舞台结构空间转化为简写模式,《海景》的两幕分别依托S→A→E和E→A→S这两种空间组织形式来建构舞台空间,无论从字母排列或是内涵意义都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出两幕剧中的舞台结构空间呈现对称关系。的舞台结构空间模式。在第一幕的结尾,男性蜥蜴莱斯利首先上场,“他从沙丘后出现了,身体有一半闪现在舞台上……他看到查理和南希之后,迅速缩回了身体”,随后未被南希夫妇发现的莱斯利回去找到莎拉,他们再次出现在沙丘之上,“慢慢向上爬”“蹲在自己的尾巴上”[14]392。在此,阿尔比先行从组织动作S出发,通过“出现”“闪现”“缩回”“爬”“蹲”等动作来展现戏剧环境,确定对话空间结构,营造了蜥蜴缓慢“入侵”人类空间之感,也突出了蜥蜴胆小怯懦的“性格”与警戒、防备未知事物的“内心世界”。[21]7随后不久南希和查理发现了蜥蜴,查理提高音调喊道:“我的上帝!”南希激动地问:“他们是什么?”查理让她赶快“回到这里”[14]393。在简短的对话之后,“南希一步步退向查理,并共同退到了舞台右边,莱斯利和莎拉则躲向了舞台的左边”[14]393,人类夫妇使用一系列语言和动作来表达恐惧,传递了“A戏剧动作的情绪与意义”[21]13,16。人类和蜥蜴的对峙之势展现了舞台上两部分力量间的对比和冲突,揭示了蜥蜴和人类第一次碰面、相互防备的心理状态,这也与20世纪中叶的社会情状相吻合:抛开那些“表面上的友好”,人与人接触的实质就是“距离和冷漠”,以及“许多微妙的不信任”[22]113。很快查理就让南希找来了一根大棍子,试图与蜥蜴决斗,就在两方都剑拔弩张之时,飞机出现了:在舞台的边缘,“喷气式飞机的声音响起,这一次更为低沉,声音也更响”[14]396。“莱斯利和莎拉用爪子贴着沙子,肚子贴着地面,慢慢返回了水里”[14]396,查理和南希这才缓过神来,开始讨论起刚刚看见的生物。随着飞机的出现,蜥蜴夫妇的逃离,舞台中心被人类夫妇所主导的社会空间占据,舞台结构也实现了“E再现舞台环境”的空间转向。相比于另外三次长时间、大噪音的飞机登场,此次短暂的“飞机”回归实现了用城市景物与自然景物的碰撞来建构人类和蜥蜴夫妇对话空间的意图,也为蜥蜴和人类夫妇的第二次碰面埋下了伏笔。
随即剧情延伸到了第二幕的开头,在一望无垠的沙滩上,“天气晴好”,人类夫妇和蜥蜴夫妇分别位于舞台的两侧。南希“用自己的脚对着莱斯利和莎拉”“慢慢翻过身”“她的手托着脸部,手指弯曲,像爪子一般”[14]399,她维持这样的动作并让查理也模仿她的动作,还称之为投降的状态,蜥蜴夫妇随后“缓慢挪向了人类夫妇”,莱斯利“用爪子戳了戳查理”。[14]401相对于第一幕中较为激烈的组织动作空间展示,阿尔比在此处首先完成了“E-再现空间环境”的转向,他以人类夫妇和蜥蜴夫妇势均力敌的空间对抗状态为第二幕两方的深入交流奠定了宁静、和谐的空间基础。海洋空间的二次呈现看似将观众从先前由查理夫妇主导的城市空间中释放出来,但实质上,人类居住的城市“就像草原犬鼠的居住地和牡蛎居住的海底一样,是自然的过程”[19]498,海洋空间实则是阿尔比精心塑造的、为了展现人类真实交流状态的“镜像”空间。在感知到蜥蜴夫妇对人类语言的兴趣后,南希开始对蜥蜴夫妇进行语言教学,她用大量的动作、话语来解释“乳房”“手”“脚”“衬衫”“鸟”等词汇。不难看出,人类夫妇之所以愿意同蜥蜴交流,是因为发现蜥蜴会说英语,可以教学、驯化,甚至被利用来发掘“商机”,这种“利己主义原则”[22]114促使人类夫妇走向了蜥蜴。查理甚至还将自己的悲观情绪用语言传递给蜥蜴,他对蜥蜴说:“如果死亡真实来临,我会将我的叉子放在盘子里,把它和刀具放在一起,喝完最后一滴酒,或是水,折好纸巾,把椅子放回去。”[14]433查理口中的“叉子”“盘子” “酒”“纸巾”这类经常出现于家庭空间的物品其实是他自己的“精神世界在空间上的投影”[21]12,“喝完、折好、放回”这一系列完全连贯的动作还原了他在城市生活的麻木状态。在这期间,人类夫妇通过语言和动作实现了自己的目的,成功传达了内心的情绪,完成了舞台结构空间的功能转向,起到了“A—展现动作背后情绪与意义”的效果。随后,在一片近乎死寂的氛围中,“喷气式飞机的声音再一次从舞台的左边响至舞台的右边,震耳欲聋,最终消失”[14]433,查理和南希盯着飞机的轨迹,而莱斯利和莎拉则吓坏了,他们一下子躲到土堆后面,只露出了半边身子。伴随着飞机出场的“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人类夫妻的“盯”以及蜥蜴夫妇的 “吓”“躲”“露”这一系列动作为二者在下一阶段的争执和分离确定了合理的舞台结构空间,第二幕在此成功实现了S组织动作空间的功能转向。
在蜥蜴夫妇从海底进入沙滩到在沙滩遇见人类的过程中,S-A-E和E-A-S的“镜像”舞台结构空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外部作用,根据情节发展的不同阶段,蜥蜴与人类或是以动作、神情、声音传递信息,或是以物品、语言、行为抒发情感,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因为舞台空间的变化而呈现出“疏远—紧密—疏远”的趋势。事实上,除了呈“镜像”对称的舞台结构空间外,阿尔比还模仿了意大利戏剧家皮兰德娄(Luigi Pirandello)“塑造‘镜像角色’,以达到将脱下面具的过程戏剧化”[23]47的创作手法。通过展现镜子外的正常角色和镜子中的扭曲角色——“一对角色和我们的日常生活保持一致,另外一对则与我们的传统相悖”[23]47的方式,阿尔比完成“镜像”角色的建构,为情节发展奠定了合理的内部因素。蜥蜴夫妇就是“变形”的查理夫妇,这种“扭曲”的形象却更能让观众直面真实的生活状态,激发观众对于个体本真状态的思考:“查理呆滞迟钝,南希活泼敏捷;查理遇事逃避,南希寻求融入”[24]132;莎拉是女版的查理,但性格软弱极其害怕变化,接受不了和莱斯利的片刻分离,稍遇挫折便有轻生念头;莱斯利则是男版的南希,对一切的事物都有猎奇心,却遇事冲动,甚至因为小事几次扬言杀死查理。阿尔比不吝以各种手段暗示观众,蜥蜴夫妇的存在就是为了打破“由人类自己创设的幻想模式”[25]16-17,让人类能更为直观地看清自己自私、虚伪的本质。舞台结构空间的“对称”建构与戏剧角色的“镜像”塑造背后,是阿尔比以“病态”相处模式和“扭曲”动物性格指涉人类真实生活状态的意图,他在成功将观众的注意力由自然与社会空间的冲突转移到了缺陷的个体性格、功利的人际关系上的同时,也唤起了观众对于正常生活模式的理性思考。
三、跨越真实与想象的空间
受到麦卡锡主义、冷战、越战、民权运动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城市“处于其最低点”并迎来了影响深远的“都市危机”[18]276,持续的“暴力统治”和“骚乱”让民众失去了对于“邻舍”“同事”“信息”或是“体制和领袖”[26]1的信任,他们开始对于世事“漠不关心,不思进取”[20]148,只追求“效率、理性与自我利益”(7)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认为,追求“效率、理性与自我利益”实则淡化了人际交往的亲密性,将所有人格和品质都化约成一个简单的问题:“这值多少钱?”这里的“理性”实则是“理智性”的简称,指都市居民用理智而非感情来处理日常或工作事物,人很少显露感情或直接向他人表露思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淡漠疏远。参见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7]3,加缪(Albert Camus)曾在《西绪福斯神话》(TheMythofSisyphus)中具体描述道:
起床、电车,四小时办公室或工厂里的工作、吃饭、电车,四小时的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二、三、四、五、六,总是一个节奏,大部分时间里都轻易地循着这条路走下去。[27]19
与“经济领域繁荣与富裕”[20]185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众在精神世界上的贫瘠和对于自我价值的否定。查理时常向南希发问:“我们来这里是为了什么?”[14]375“你都要做些什么?”[14]376他们身上清晰地展现了60年代社会青年处于“寻找出路”和“没有出路”[20]174困境中的矛盾心理。对因过分追求物质享受以致失去生活热情的查理和南希而言,蜥蜴夫妇其实是阿尔比所建构的幻想世界对于真实空间的一次入侵,他们是“人类本真状态的最佳还原”,他们“帮人类找寻日常生活下的真实”[28]24。在莎拉和莱斯利身上,观众感悟到了存在的意义,那就是“对人类弱点的合理认识,对于自我意识的回归,以及对于生活本质意义的探索”[23]51。纵观全剧,蜥蜴夫妇代表的幻想空间与查理夫妇代表的真实空间在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后,才从互斥走向融合。初次遇见蜥蜴,查理高度怀疑自己看到的“想象”空间并全盘否定了他们的存在,他对南希说道:“一定是阳光的温度太高,导致肝泥坏了并且把我们毒死了”“把你的三明治嚼完,咽下去,躺回去,让毒药慢慢渗透 ”[14]398,这种感觉和“牛奶进入眼睛”和来自“其他房间”的声音[14]398都不一样。在这里,现实生活的经验再一次成为查理抵御外来空间的屏障,帮助他获取了逃避的机会,然而就在他以现实空间来抵抗幻想空间的企图即将得逞之时,南希提醒他蜥蜴夫妇再次到来了,他们需要“在地上滚几圈,把腿抬起来,手放在脸上,手指弯曲”[14]399来摆出投降的姿态。随后,查理在发现蜥蜴夫妇没有恶意,并且会说简单的英语后,慢慢接受了他们的存在,他开始试图凭借“规训技术”——即“通过对空间、时间、他者等进行社会控制”[29]161的手段来达到征服蜥蜴的目的,这也表明他进入了“跨越真实和想象空间”的第二阶段:通过对蜥蜴夫妇进行“强制教学”来占领蜥蜴的领地。他们以人类的事实经验——“人有两只手,两条腿,不是四只手”“我身上穿的是衬衫”“那些动物是鲸鱼”来教授蜥蜴夫妇,并从各个方面炫耀自己所代表的先进科学技术文明。在几轮博弈中,蜥蜴从岩石前被挤到岩石后,他们瑟瑟发抖、渴望逃离。而后随着轰鸣的“飞机声”一次又一次响彻舞台,莱斯利和莎拉完全吓坏了,“他们退到了舞台旁边,伸出爪子警惕地看着它(飞机)”[14]434。人类夫妇也彻底掌控了对话的主导权,查理更是试图建构“二元对立”,即非此即彼的讯问模式,来促成和蜥蜴之间“或明或暗的压制关系”[30]52,“你们很喜欢自己的尾巴,不是吗?”[14]440“你们准备告诉我什么?是抨击的话,还是无意义的话?”[14]441“你们在了解关于情感的事情,难道不是吗?”[14]443在发现蜥蜴夫妇无力回击后,尝到甜头的查理仍不放过他们,甚至变本加厉,对莎拉进行了“一对一”的逼问,来确保自我的权力“自动地发挥作用”[31]226。
查理:莎拉,你会做什么呢?如果莱斯利 “走了”……很长时间……你会做什么呢?
莎拉:如果他不告诉我他将会去哪里?
莎拉:我会去找他。
莱斯利:你顺着什么去找?
查理:你会去找他,很好,但是如果你知道他永远都不会回来了呢?你又会怎么样?[14]443-444
原本处在和平、安定的想象空间中的莎拉被推向了舞台的中心,暴露在了公共空间之中,在一种“有意识的和持续的可见状态”[31]226下,她的情绪接近了崩溃:
我会哭……我会……把我的眼珠子哭出来……哦!莱斯利!
我想要回家,我不想呆在这里了,我想要回家。[14]444-445
在一阵撕心裂肺的哭泣后,两只蜥蜴“挪向舞台后方的沙丘”[14]447,准备回归海底,而通过“训诫”手段获得了沙滩“占有权”的人类却没有享受到胜利的喜悦,他们突然意识到,无休止的占有带来的后果只有仇恨和分裂,没有蜥蜴的沙滩也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这也意味着人类进入了“跨越真实和想象空间”的第三阶段:走向共生。人类夫妇“希望抓住蜥蜴的手”,“为蜥蜴的进化提供帮助”[14]448,“请求”[14]447蜥蜴夫妇留下,随着莱斯利的“好吧,开始。”[14]448的回应,以沙滩开始的故事也终结于沙滩之上。莱斯利、莎拉因为人类的劝说,决定遵循进化过程而留在沙滩,查理、南希则因为希望提供帮助而留在沙滩,这也使得沙滩,这一连接着海洋与陆地、自然与城市、过去与将来的地理媒介成为同时“存在于”真实空间与幻想空间,并且“建构完好的‘异托邦’”[32]24,真实与想象在此走向了统一。因为人类和蜥蜴的加入,“沙滩”这一自然场景被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充满着“希望”和“生命原动力”[33]65的“第三空间”,并化身为“真实-和-想象旅程”(8)爱德华·索亚(Edward W.Soja)指出,“第三空间”是“真实的又是想象的而且又是亦此亦彼的空间,对于这一空间的探索可被描述和写进通向‘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海景》中的沙滩即是对于这一层“亦此亦彼”空间的呼应,沙滩这一景观既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幻想虚拟的,因为沙滩上出现了真实的人类,也出现了不真实的蜥蜴,蜥蜴夫妇通过沙滩从幻想的海洋空间走向了真实的进化空间,人类通过沙滩从自我设置的幻想空间走向了充满意义的真实空间,人类、蜥蜴分别代表的真实与想象空间也在此完美融合。参见Edward W.Soja.Thirdspace: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Blackwell Publishers Inc.,1996:6.[29]6的终点。
剧评家M.C.罗达尼(Matthew C.Roudane)指出,在与社会环境的相处中,人类需要直面艰难的困境和成长的痛苦,“唯有回归真正的自我”[24]148,才能直面真实的人生,这也指明了查理顿悟并挽留蜥蜴夫妇的真实原因。在《海景》中,查理经历了死的恐惧和生的希望,见证了蜥蜴的喜怒哀乐,认清了自我的生存状态,并且实现了跨越种族的交流。在查理身上,观众似乎可以看到不少“托拜厄斯”[34]163的影子,在社会公共空间中,他极力扮演一个“好丈夫”的角色,照顾妻子,抚育儿女,然而当他和南希单独相处时,他的许多弱点都暴露无遗,在内心深处,他害怕变化,只愿意将自己束缚在狭小的空间里,冷漠对待周围的一切,蜥蜴夫妇的出场实际为查理突破自我禁锢的幻想空间提供了机会。在查理企图控制蜥蜴,并迫使他们接受人类复杂的现代文明过程中,他突然明白,暴力、自私的行为终会让蜥蜴变成和他一样的人,或是“走向变化的极端”,或是“变得异常冷漠麻木”[35]80。因此,不让人类的“焦虑、失落和沮丧感”[36]1088侵占蜥蜴的精神世界,以真诚、平等、尊重的方式对待蜥蜴,让他们遵循进化的自然过程才是最佳选择。查理试图以争夺话语主导地位来占领空间的企图最终破灭,而他以真诚和爱来消解真实与想象的界限,并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相处危机的方式也在引导观众,唯有当“个体从冷漠逃避的生活中”重拾热情,“才能打开一条通向人的尊严和生存意义的救赎道路”[37]80,而从这种冷漠状态脱离的最好方式,便是将自私、虚伪的个人主义转向“对于同胞的同情和宽容之心”[1]52,也只有对周围的一切始终保持着尊重、怜悯、敬畏,人类才能走出自我禁锢的幻想空间,走向充满意义的真实世界。
四、结语
与《山羊》一剧中被主人公马丁当作性侵对象并被马丁的妻子残忍杀死、尊严全无的山羊西尔维娅形成鲜明的对比,《海景》中的蜥蜴夫妇完成了和人类“跨越种族”的交流,这样的一种经历“给蜥蜴和人都提供了顿悟的机会”[5]314,蜥蜴夫妇接受了来自人类社会的先进文明,他们自始至终的真诚、热情也让人类看到了自己身上的虚伪与冷漠。在真实与想象的边界,阿尔比与观众玩了若干次游戏,他在剧中塑造了在真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会说话的蜥蜴,又让舞台响起了一次又一次的“飞机”轰鸣,这些都在提醒观众,他们真实地进入了这一层戏剧空间吗?还是仅仅作为舞台表演的旁观者?令观众感到惊奇的是,“飞机”的巨大噪音逐渐成为他们的期待,因为这是他们唯一没有迷失自我的依据,在这一点上,观众又何尝不是另一对南希和查理夫妇呢?
在《海景》中,阿尔比进一步拓宽了文学创作的维度,他依托戏剧舞台呈现了自然空间与城市空间的另类碰撞,打破了一直以来自然空间主观性被忽视的状态,它没有以静止的“容器”或“平台”[7]8形式呈现,更“没有被作为‘攻克’和‘掠取’的对象”[38]9;相反,它以一种生动灵活的方式出现在了舞台之上,并完成了从附属到主宰的华丽转变。除此之外,阿尔比还以“镜像”的舞台结构空间、“镜像”的角色塑造模拟了真实的人类生活场景,以此来唤起人类对于自我生活状态的正视;他借真实空间与想象空间的冲突,展现了人类所面临的“焦虑和绝望”,让观众体会到了“对于各种解决办法、幻想和目的性的丧失所产生的一种若有所失之感”[39]18。正如阿尔比戏剧研究专家保卢奇教授(Anne Paolucci)所言:“除非人类意识到,只有不断调整自己的生活状态,才能找回真正的真实,否则对他们来说,真实就如同‘镜中’的幻影,毫无意义。”[23]52-53在不适、异样甚至是痛苦的观剧体验下,观众完全脱离了自我设置的个人空间,他们如同查理一样,以更为清晰、明朗的态度重新投入充满着意义与希望的真实空间。阿尔比在倒逼观众审视自我存在状态、激发他们对于生存的意义进行积极思考的同时,也对美国社会进行了深刻反思,并为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指出了合理的解救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