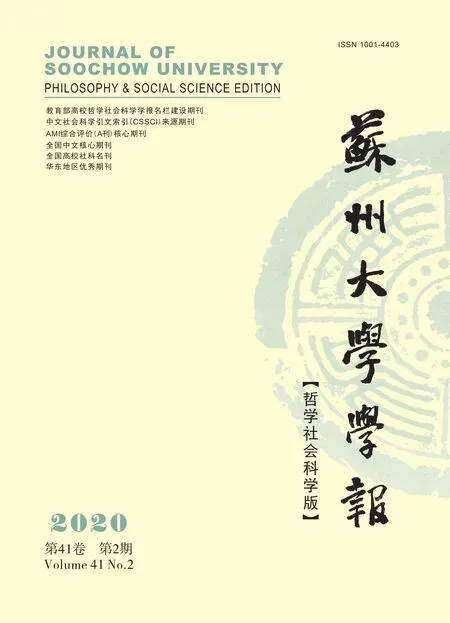清初世运与文人心态对“词史”观念建构的影响
黄晓丹
(江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词史”观念源于“诗史”,取杜甫“诗史”之“存史”“补史”之意,意在将词与经史并论,扩充词的表现领域。这一文体观行于甲申易代之时,由陈维崧明确提出[1]614-620[2]101-107、144,在清末遗民中掀起一轮高潮,学界对此已有所研究。笔者认为,对“词史”观念的讨论,不应局限于词体发展的内生性维度,须在政治、历史、文学三者的关系中加以理解。而且由于在文学内部,诗与词本身具有不同的功能划分,所以“词史”观念之构建,不仅意味着文学对史学功能的侵入,还意味着词对诗之功能的吸纳,故应进一步追问:自《云谣》《花间》以来,词体发展700余年,于宋可谓极盛、于明素称中衰,何以“词史”观念确立于顺、康之世?“由史至诗”“由诗至词”的功能转移,这一现象表达了怎样的文化生态?
一、关于“词史”观念的再讨论
观念的形成有一个长期的过程,人们在“词”的发展中逐步感知、认识其特征、作用,某种意识于焉渐生;而由一个概念来明确表达意识,则表明观念之成熟与确立。清初“词史”观的成熟与确立,是长期以来关于“词”意识的积累与转变,具有对诗词文体界限的颠覆意义。
康熙十年(1671),陈维崧与阳羡词人吴本嵩、吴逢原、潘眉合作编撰《今词苑》,陈维崧作《今词苑序》,其中有“选词所以存词,其即所以存经存史也”的话。此处“词史”并未表述为一个专有概念,但论者一般都认为“词史”观念实际上于此已经确立。原因有二:第一,《今词苑序》的主旨即是在说各种文章都有表现、记载历史的功能,词也不例外;第二,陈维崧本时期的创作也与《今词苑序》中提出的观念相符,秉承了“以词存史,以词补史”的精神。
在谈及“词史”观念对陈维崧创作的影响时,以下文献史料常常被提到:
王阮亭先生官扬州,倡倚声之学。……先生内联同郡邹程村、董文友,始朝夕为填词。然刻于《倚声》者,过辄弃去。间有人诵其逸句,至哕呕不欲听。因厉志为《乌丝词》。(蒋景祁《陈检讨词钞序》)[3]94
《今词苑序》的一段话可以作为“间有人诵其逸句,至哕呕不欲听”的注解:

于今客观来看,《倚声初集》中的作品虽然未脱明人冶荡词风,但并无琐语淫词,何至于“哕呕不欲听”?这也许是因为在《今词苑序》中,陈维崧采取了一种与前人不同的考量词体的逻辑。
魏泰《东轩笔录》里有一记载,说“王荆公初为参知政事,闲日因阅读晏元献公小词而笑曰:‘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而为尔,顾其事业岂止如是耶!’”[5]10这条文献说明在唐宋文人那里,诗词是有其文体、伦理、美学上的分工和互补的,所以我们不能用诗的严肃性来否定词的游戏性,也不能用诗的公共性来否定词的私人性,“词媚”“诗庄”各是其文体的本色。
陈维崧《今词苑序》的论述逻辑,表现出他对“词”体的“应然”态度和标准。以其与诗同高的标准而言,这当然算是“推尊”了词体,但这种近似“无差别”的标准,也可以说是“取消”了词体。总之,陈维崧颠覆了诗词之间的界限。从正面影响来说,词当然因此可以书写更宽广的世界;从负面影响来说,词也失掉了自己的文体特征。
陈氏“选词所以存词,其即所以存经存史”说道出“词史”意识的基本内涵,但清人的“词史”观具有复义性,至少应提及以下数端。
(一)“词史”观之本意
“词史”概念极为丰富,如考虑到“词史”概念与“诗史”的词源关系,则“词史”本意主要立足于其纪实意义。现代学者中,叶嘉莹《论清代词史观念的形成》中认为“词史”的严格定义指亲历者有意识地记叙特定历史事件,表达泛泛的家国之感的还算不上“词史”;[6]122-129周明初《南明词人方惟馨〈菩萨蛮〉的“词史”价值》中认为“所谓 ‘词史’,是作者以亲身经历所写的具有实录性质的、能够充分反映出历史大变动时期社会状况的、具有史料价值的词作”[7]115-128,都取“词史”的这一“本意”,以“亲历”“纪事”为“词史”的必要条件,而且还暗含了所纪之事,应为与历史变革、家国盛衰相关的大事之意。
(二)“词史”内涵与题材相关
“词史”概念的形成过程是具有时间错位性的。鼎革历史下,真正亲历纪实者,往往没有意识到或来不及提出任何文论概念。而在平安时世中,有明确理论追求,提出“词史”概念的人,却并不具备亲历与纪实的外在条件。因此,“词史”概念如果要对写作有所影响的话,就必须在题材上加以拓展。
张宏生在对陈维崧的“词史”的研究中,认为在明清鼎革的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下,追忆、感叹、反思,甚至广义的宇宙人生、历史文化,狭义的政教事件,入词都可称为“词史”。[2]101就陈维崧写作《词选序》的时代而言,明清鼎革已成为过去,亲历、纪实式的书写必然让位于闻见和追忆,因此陈氏所言“穴幽出险以厉其思;海涵地负以博其气;穷神知化以观其变;竭才渺虑以会其通,为经为史,曰诗曰词,闭门造车,谅无异辙也”[4]54,正是贯彻了“词史”的存史、补史、观史之宗旨,而予其题材有了更大的拓展。
至于提出“诗有史,词亦有史”的周济,其生活时段是在嘉道年间,并于鸦片战争前一年去世,比陈维崧更不具备亲历家国盛衰、历史变革的条件。细读其拈出“词史”的著名论述:“感慨所寄,不过盛衰;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己溺己饥,或独清独醒,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8]1630可知大至国家盛衰、小至己溺己饥都已被列入“词史”书写之题材范围。这是继陈维崧之后,对“词史”题材的进一步拓展。
(三)“词史”表现与手法相关
“纪实”是一切历史书写的题中应有之意,但词体区别于其他文学体式的本质恰恰在于它并不那么纪实,即王国维语“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9]。因此,“词史”之作的表现手法在实践中,也不可能限定于纪实,而必然向隐喻、象征、寄托等间接性的表现手法扩展。这种扩展是普遍的,但其动机分为两种,一种来自外在的政治压力,一种来自词内在的尊体要求。
在清初文字狱的背景下,对明清鼎革的历史予以“纪实”是不被允许的。吴梅村《满江红·白门感旧》不得已以“要眇宜修”之词体,假托永嘉南渡之事书之。同样经历了明清鼎革的曹贞吉评论此词,说“陇水呜咽,作凄风苦雨之声。少陵称诗史,如祭酒可谓词史矣”[10]564。这就是外在政治压力下,“词史”之作手法拓展的一例。
上文所述嘉道年间周济以“感慨所寄,不过盛衰: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论证“词史”,言“感慨”“绸缪”“太息”而不言“直书”“纪事”,乃是常州词派尊体的要求下,从词之美感出发,而令“词史”之作手法拓展的一例。
正因为“词史”概念的复杂性,所以不可能脱离历史背景,完全在文学内部得到清晰界定。陈水云的《清代的“词史”意识》涉及词作、词选、词话对于史已有载的历史事件的化用、史不能载的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述、史不及载的各种琐事的保存;与之相对应的是词作为文学、历史、文献的三种功能。这样在“词史”问题上使用意群式分析,更能展现词之文体和时代本身的复杂性,也更切近词人将历史关切融进文学书写各个方面的努力。
实际上,清人的“词史”与“诗史”是有所区别的。首先它隐含着比“诗史”更强的历史记忆流失的焦虑。杜甫主观上或许并没有明确的存史意识,他关注现实,其眼之所见、耳之所闻、笔之所书无非麦秀黍离、民困民饥,被后人当作了历史素材。而清初“词史”之作诞生时的历史背景,是庄廷鑨《明史》案宣告史书不再能承担记录鼎革历史的责任、黄培诗案显示以诗体承担存史功能也充满风险。故知清人将“词史”作为一种文体意识,其初带有更多保留历史记忆的责任。其次,杜甫的“诗史”“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11]18,而“词史”则“事难毕陈,语多隐晦”。以被曹贞吉誉为“词史”的《满江红·白门感旧》为例,吴梅村借永嘉南渡喻甲申士夫奔赴南明、借新亭对泣喻遥祭崇祯、借火烧赤壁喻多铎破金陵事。借古多于言今、喻托多于直陈。与“诗史”相比,吞吐、隐晦反倒成了清初“词史”的特点。
综上所述,“词史”观念是在明清鼎革的时代萌发,在顺、康词坛对历史记忆流失的焦虑中催生。与其说“词史”观念改变了词的演进,不如说“词史”观念本身就是改变的结果。既然“诗史”都面临着历史性与文学性之间的两难,那么词史又如何平衡更为幽隐的词体本质与历史真实性之间的矛盾呢?这种矛盾对于词体是否能发生有益的刺激?
二、世运书写与“词史”观念之构建
龙榆生在《近三百年名家词选》的后记中说:“元、明词学中衰……明、清易代之际,江山文藻,不无故国之思,虽音节间有未谐,而意境特胜。”[12]225又说:“然则词学中兴之业,实肇端于明季陈子龙、王夫之、屈大均诸氏,而极其致于晚清诸老……论近三百年词者,固当以意格为主……而三百年来词坛盛衰之故,与世运为倚伏,盖庶几于此帙觇之矣。”[12]226这段话表达了三层意思:一,就词的演进来看,从明末到清末,是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首尾相续的整体;二、与之前时代相比,这三百年来词与世运的联系空前紧密;三、由世运剧变带来的身世之感提升了词的“意格”,赋予了词体新的审美内涵。
将世运作为解释词风、意格变化的首要因素,对于清代之前的词学并不适用,但对于清词却极具阐释力。近世以来,大部分研究者在对具体清代词作的阐释中都延续了这一传统。与世运关系之远近,甚至成为论定词作是否堪为经典的重要标准。根据这一思路,研究“词史”等重要观念的构建,也应考虑到世运的影响。
清代“词史”是创作、文论、接受三者互动的产物,而世运及其文人心态正是促使这三者冲撞交融的动力。下文将以明末、顺治朝、康熙朝三个最重要的词人陈子龙、吴梅村、陈维崧为中心,探讨他们在词的创作、编辑、品评中,如何通过有意识地建构或无意识地被误读,而使“词史”观念得以诞育、丰富。
1.陈子龙:鼎革记忆中的历史影像
在叙述世运对清词发展的影响时,学界一般把陈子龙当做思考的起点,这正如《近三百年名家词选》所说:“词学衰于明代,至子龙出,宗风大振,遂开三百年来词学中兴之盛,故特取冠斯编。”[12]4但这样的论述逻辑面临着一个可能的质疑——虽然陈子龙是明末清初最重要的词人,也是鼎革时期最富盛名的抗清义士之一,这就说明他的词学成就与世运相关吗?
由于陈子龙在明末文坛的地位、诗文词各方面的成就、与柳如是的浪漫关系,以及坚持抗清、最后效彭咸投水而死的事实,在鼎革时代的记忆中,陈子龙承载着人们的崇敬和想象,也承载着对于历史的追忆和反思。清人对陈子龙词的理解、接受与出版也随之产生着微妙的变化。
陈子龙的词主要收在他与李雯、宋征舆唱和的《幽兰草》(55首)及与宋征璧、宋征舆、宋存标、宋思玉、钱榖唱和的《倡和诗余》中,即《湘真阁存稿》(29首),另有弟子王沄所辑《焚余草》已佚,但据王英志所说:“词皆录入《全集》诗余,共有《如梦令》、《长相思 》等50题,78首。”[13]98-106另有散入诸合集的,共计80余首,唯甲申年的诗词稿全部佚失。陈子龙的词学观点可见于《幽兰草·题辞》《王介人诗余序 》《三子诗余序 》《宋子九秋词稿序》等,大致有标举南唐北宋、严分诗词之别、追求婉约自然等[14]106-111,但总的来说与后世所谓“词史”差别甚大,也从未提到词与世运的关系。以下两则材料可以看出陈子龙对于“小词”一以贯之的态度。
大樽(陈子龙)每与舒章(李雯)作词最盛,客有啁之者,谓得毋伤绮语戒耶?大樽答云:“吾等方少年,绮罗香泽之态,绸缪婉娈之情,当不能免。若芳心花梦,不于斗词游戏时发露而倾泄之,则短长诸调与近体相混,才人之致不得尽展,必至滥觞于格律之间。西昆之渐流于靡荡,势使然也。(彭宾《二宋倡和春词序》)[15]345
丁亥暮春,同大樽、舒章二子,集子建(宋存标)荒圃。是日春雪乍霁,庭兰放花。大樽示予《上元》篇。已而眺崇岗,俯清流,感叹瑗公(夏允彝)。既相与极论诗文,予因即席赋《念奴娇》长调,故有“阳春郢雪”之语。明旦接读和章,至“空赠金跳脱”,未尝不愧春意也。乃未几而大樽亦效彭咸,则“湘水波澜”,“重临幽涧”,竟若为谶云。(宋征璧《念奴娇·悬崖欹石序》)[16]歇浦倡和香词16
第一条材料对应陈子龙早年词作,即收于《幽兰草》中的作品,可知陈子龙对于“诗词分界”的恪守是有意的选择。他认为诗的世界足可以言志,因此词只需写作“绮罗香泽之态,绸缪婉娈之情”便可。第二条材料是指《湘真阁存稿》中的《念奴娇·和尚木春雪咏兰》一首。此时离陈子龙投水而死不过数月,且此词在《湘真阁存稿》中也算得上较为声情激越,与其一贯的婉丽词风有别,故此词为后人带来很多联想,至有专文论述其为祭奠黄道周所作。但《倡和诗余》中实有宋征璧原词及后补之序。以此序来看,此词写作的实际背景还是一次切磋诗文的集会。虽然序中说到“感叹瑗公”,但只是在此时代中不可回避的话题和无法开解的情感基调,而非唱和的主题,且陈子龙必然未曾更改词以言情的观点,未曾试图将词作为志意的表达和历史的记录,不然宋征璧何以不能读出其词中的弃世之意,而要于陈子龙殉难之后再发“何以竟若为谶”之问。
陈子龙经历了极其精彩壮烈的人生,并在诗文中得以充分淋漓地表达,这与他克制、委婉的词作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似乎随着时间的推进,人们越来越不相信陈子龙词中的伤春只是伤春、闺情只是闺情。从接受史上来说,离陈子龙殉国的时代越远,人们越认为其词中具有政治寄托。
朱惠国在《陈子龙词略述》中说:“(对陈子龙词的接受)从清初到清末,大体上表现出由重风格研究到重社会功用研究的基本走向。”[17]21-36王兆鹏、姚蓉《作品意义的展现与作家意图的遮蔽 —— 以陈子龙〈点绛唇·春日风雨有感〉为例》比照两首“显豁地表达了词人在江山易代之际的悲愤心情、忧患心绪”的词在《陈忠裕公全集》与《湘真阁存稿》中的异文[18]1-6,证明原词只是书写闺情,并无感慨世运之意。其实不仅陈子龙词在清初常被加以过度阐释,宋征舆早年《蝶恋花·秋闺》“新样罗衣浑弃却,犹寻旧日春衫著”诸语也被附会为仕清后的追悔之语。
《陈忠裕公全集》由王昶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至嘉庆八年(1803)间编定,但清人将江山易代之痛、恢复故国之意加入到对陈子龙词的理解中,应在康熙年间就已开始。顺序应是《湘真阁存稿》中的词首先被赋予世运化的解读,然后这种解读方法蔓延到《幽兰草》及云间诸子的词作中。随着原刻的被禁和解读心理的变化,异文开始出现。与原刻相比,异文虽看似无关紧要,但总体上口吻更为激烈,更足阐发亡国之愤。这一趋势自康熙年间开始,经《兰皋明词汇选》《今词初集》《瑶华集》等,至《陈忠裕公全集》而在文本上固定下来,之后在文学阐释中继续发展,流响至今。
顺治十七年(1660)出版的《倚声初集》与康熙元年(1662)出版的《兰皋明词汇选》皆带有评语,如果比照二者对陈子龙词的看法,则可窥见这一转变的痕迹。总的来说,《倚声初集》论陈子龙词,重在技法才调;《兰皋明词汇选》论陈子龙词,重在世运、人格及忠愤之情。陈子龙标举南唐北宋本只是就词之格调、做法而言,并非以身世自比后主,但《兰皋明词汇选》中,强调《湘真词》为甲申、乙酉两劫后作,及比之为李后主感旧诸作及屈子香草之怀,则是以陈子龙词当一部亡国痛史来读。
从陈子龙弃世的顺治四年(1647)到《兰皋明词汇选》刊刻的康熙元年(1662),仅仅十五年间,人们对于鼎革历史的记忆和对故国的恋念之情就深深渗入到对陈子龙词的阅读心理之中。350年后的今天,我们甚至很难将陈子龙词从这种阅读背景中剥离出来重新审视。曾经的过度阐释事实上已被清代文学史所共认,并以文化潜意识的方式传递下来。至清末民初、抗战爆发,每到时代转折的关口,总有学者重提陈子龙词,以获得历史的共鸣和人格的激励。词作为历史的见证,与史不可辨分,似即从陈子龙始。
2.吴伟业:文网恐惧下的“史外传心”
鼎革后,吴伟业 “每东南有一狱,长虑收者在门,及诗祸史祸,惴惴莫保”(《与子暻疏》)[10]1131。顺治四年,陈子龙、夏完淳、李雯同年去世。顺治七年(1650),吴伟业应宋征舆、宋征璧兄弟之请,为陈子龙、宋征璧、宋征舆、宋存标、宋思玉、钱榖六人词合集《倡和诗余》作序。此时吴伟业避居太仓,决意终老林园。据《梅村家藏稿》,顺治七年(1650)元日吴伟业梦见在旧朝禁苑中见杏花一株,醒来忆及去登第之岁已二十年,赋《庚寅元旦试笔》,化用陈与义于南宋时追怀北宋的《临江仙·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本年记录中,更有多次因忆及旧人而“大哭”“大恸”。此年秋,又于常熟钱谦益宅中约见卞赛不得,作《琴河感旧》四首。当宋氏兄弟求序之时,吴伟业借他人酒杯,浇内心块垒:
若乃紫台云锁,回首难堪;碧海波沉,拊心何限。旅葵蔓井,宁无何逊之悲;蕖槿临扉,遂有萧郎之叹。……惨角悲笳,非春院咒花之客,啼香怨粉,尽秋江酬月之人尔。……余影结梅村,兴颓药圃。鹤城仙去,时逢怆笛山阳;鸥渚舟横,久绝献环洛浦。[16]倡和诗余1
吴序通篇充斥着“回首难堪”“拊心何限”“何逊之悲”“萧郎之叹”“怆笛山阳”“故人枯骨”等语,故国黍离之悲、怀念殉节诸友之意清晰可辨,恍如一篇词序版的《恨赋》,且“紫台”“碧海”诸语更直指李自成入京及鲁王奔逃海上事。与吴梅村相比,作为词集作者的宋征舆所作二序则并无政治隐喻:第一篇完全是对宋七家词的看法,《再序》则提出“词之旨本于‘私自怜’,而‘私自怜’近于闺房婉娈”[16]倡和诗余2的观点,依然秉承诗词有别的观点。
宋征舆、宋征璧兄弟在明亡后很快仕清,其政治选择当然影响了文学表达,但吴、宋两序的差别可以让我们再次看出,在顺、康之际,词之作者与读者的理解心理已发生分歧。而另一个倾向是,吴伟业此时“惨角悲笳,非春院咒花之客,啼香怨粉,尽秋江酬月之人尔”的说法,已经近于张惠言在《词选序》里所说的“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19],只不过张惠言是抽空了历史背景,从词的文学本质上来说的,而吴伟业是就极其具体但又不可言说的鼎革历史而言的。
在这篇序中,吴伟业虽然没有提及“词史”“诗史”“史外传心”任何一个概念,但其以史说词,以心说词之意已呼之欲出。而其如此,与当时的言论条件下,秉笔写史与以诗记史都变得危险有关。
吴梅村一向有以史入诗的兴趣。但梅村明亡之前的作品,比较重视历史事件的真实、具体及议论的准确得当;明亡之后的作品,则如严迪昌所说“锋芒锐钝,议论胆缩”“情多于事,在伤感的氛围中‘史’多泯灭于事中。”[20]391显然这不尽然是个胆量的问题。顺、康雍乾四朝文网密集。虽然顺治朝文字狱较后三朝为少,但顺治四年之函可《变记》案,顺治五年之毛重倬等仿刻制艺案、黄毓祺反诗案、冯舒《怀旧集》案皆足以震慑士林。而一种恐惧初肇之时,民众所感之苦痛尤其深切。经历顺、康两朝的唐孙华有诗为证:“时事何容口舌争,畏途休作不平鸣。藏身复壁疑无地,密语登楼怕有声。”[21]413而吴伟业的同榜状元陈于泰即是在顺治七年“无地可匿迹,在荒庄卧复壁中,食饮缘墙而下”死去的,其墓志铭正是出于吴伟业之手。云间陈子龙战而死、海虞冯舒吟而死、宜兴陈于泰藏而死,都在短短三年间发生,对此,吴伟业如何能继续他“记事真”“论事切”的诗史理想?
史不能言则流之于诗,诗不能言则流之于词,有以词言史之心则于故人春院咒花之语中听闻惨角悲笳,于美人香草中窥见紫台碧海。“春院咒花之语”即是“惨角悲笳之辞”,这不符合客观真实性,但符合心灵真实性。基于保存、书写心灵真实的需求,吴伟业提出了“史外传心之史”的概念。
人谓是映薇湎情结绮、缠绵燕婉时,余谓是映薇絮语连昌、唏吁慷慨时也……映薇之诗,可以史矣,可以谓之史外传心之史矣。[10]1206
映薇指遗民徐懋曙,宜兴人,明亡后广蓄歌姬,尽日打谱唱曲以为韬晦。考《且朴斋诗稿》中实有吴伟业早年“诗史”所标举的叙事详尽、议论惊警之作,如《甲申乙酉间事》其十三记录了江阴屠城,其十七记录了苏州四乡被屠戮一空,但吴伟业在作序之时偏偏着眼于“湎情结绮、缠绵燕婉”之作,认为“余谓是映薇絮语连昌、唏吁慷慨时也”。这句话的逻辑结构与《倡和诗余序》中“惨角悲笳,非春院咒花之客,啼香怨粉,尽秋江酬月之人尔”一以贯之。这样写当然与徐懋曙在明亡后的形象有关,却更与吴伟业自身与其时代的文学思想转变相关。
这一转变从外在来说,就是“叙事详尽”的“诗史”不但危险,而且不利于传播。徐懋曙为清初以来各种《遗民录》所缺收,事迹在四库系列大型丛书中阙略,《且朴斋诗稿》亦未被清廷禁毁,可见其“揭露史事过于大胆,袒露遗民心志过于直率,在根本上限制了其传播”[22]72-75。
这一转变从内在来说,就是追求诗风的含蓄委婉、要渺幽微。冯舒《怀旧集》案后,其弟冯班的诗风从早期的“美刺有体,比兴不坠”变为“兴在象外,言尽而意不尽”“出入于义山、牧之、庭筠之间。其情深,其调苦,乐而哀,怨而思”[23]939的“隐秀之词”[24]73。朱庭珍《筱园诗话》也说“吴梅村……迨国变后诸作,缠绵悱恻,凄丽苍凉,可泣可歌,哀感顽艳”[25]2355。经过这样转变后的“史外传心”之作,就意味着社会写实的减少和心灵复杂性的增加。
这一转变的结果是诗词界限的模糊和写作动机流向词体。“湎情结绮、缠绵燕婉”“缠绵悱恻,哀感顽艳”“兴在象外,言尽而意不尽”接近传统上对词的美学风格的定义。既然这个时代对诗的要求是“其文小”“其质轻”“其径狭”“其境隐”(缪钺论词语)[26]5660,并以个人化、情感化的表达置换公共性的、思考性的表达,那么必然有一部分作者直接去写词了。
就吴伟业本人而言,在顺、康年间,诗体与词体在功能和美学上都显现出一定程度的互相渗透。在诗在领域,“诗史风范和哀艳情韵相结合”[27]397,出现了《圆圆曲》《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赠寇白门六首》《题冒辟疆名姬董白小像八首》诸佳作,以词所擅长之闺房儿女之情来旁述鼎革心史。而在词的领域,却出现了如《风流子·掖门感旧》《满江红·金陵怀古》《木兰花慢·话旧》等“词史”之作,但仍保留词体蕴藉、托寓的特点,并重视主体感受远超于史实书写。
吴伟业表彰徐懋曙“史外传心”、曹贞吉表彰吴伟业“词史”,从中既可以看出清初士人一步步撤离公共表达,遁入心灵书写的无奈,又可以看出其保存历史记忆的不懈努力。正是因为史书、诗文中的表达空间受到极大压缩,才使词不得不承担原先不属于自己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词史”对于文学史和社会史的意义才能得到更深理解。
但梅村“词史”也有其局限性,如果以《满江红·白门感旧》作为“词史”标准来进行创作,就会遇到两个问题:一方面,不存在完全割裂于社会生活的私人心灵,心理世界的书写也无法回避对具体历史事件的体验和记忆,如果把历史事件写得过于缥缈隐晦,事之史与心之史便都不可传;另一方面,当历史记忆鲜明、激愤郁积之时,借助词体要眇宜修的特征,进行暗示性的书写,或许能深得比兴之妙,但随着记忆的消散和激愤的淡化,就不免落入空疏琐屑。这一轨迹也可窥见于阳羡、浙西二派的升降之中。
3.陈维崧:身份焦虑下的“弃诗作词”
陈维崧有着世运与家变下的双重身份焦虑。康熙十年,编写《今词苑》时,陈维崧47岁。从“三不朽”的角度来说,陈维崧自惟一事无成。甲申之变时,陈维崧20岁。清军南下后,由于兵灾与游民劫掠,陈家事实已经破产,以至于顺治五年(1648)陈维崧父陈贞慧被太湖游匪绑架时,竟因为陈家无力相赎而只能放回。顺治六年(1649),曾在陈维崧家坐馆的诗人昝质因南北反诗案系狱。顺治七年(1650),陈贞慧的族叔,那个藏在夹壁中日夜哀鸣的陈于泰去世。顺治十年(1653),陈贞慧及二子陈维嵋因受周鍭反清案牵连被逮捕,数月后方得释。顺治十三年(1656),陈贞慧死后,由于地方官的威胁、与其他姓氏的矛盾及族人侵产夺宅,陈维崧兄弟已无法在宜兴立足,不得不外出流浪二十年,依靠同为“明末四公子”的父执冒襄、侯方域生活。顺治十七年至康熙十七(1678)年,陈维崧七试省闱不遇,而《今词苑》之编写,正是在第四次落第后寄居商丘之时。
从外在的境遇来说,康熙十年(1671)与前后数年并无太大不同,但从生命周期和心理阶段的角度来说,这年却并不平凡。首先,陈维崧无嗣,十二年前冒襄就建议他娶妾延嗣,并令二子割产相助,但直到此年,陈维崧才终于纳妾;其次,此年陈维崧致书龚鼎孳,急切而直接地恳求推荐,希望能“一观太学之碑,便脱诸生之籍”[4]562。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说,生育和成就欲的忽然加强,尤其是在中年之时,往往意味着死亡焦虑的影响。在案主近于其父母去世的年龄时(陈贞慧死于52岁),死亡焦虑的作用会更明显。本年陈维崧作《念奴娇·用前韵酬柘城王叔平》,有“壮不如人今已老,臣是江东亭伯。万事都非,一年将尽,才命交相敌”正可以看出死亡焦虑的阴影笼罩。相比于明亡时36岁的吴伟业和11岁的王士禛,陈维崧关于“我是谁”的冲突更强烈。而且因为家道中落,寄居如皋、商丘近二十年,这种故乡与他乡、贵家子与穷书生的矛盾更加强了个人与时代的冲突。陈维崧在诗文中常常强调自己“生在甲族”,与其说是某种虚荣或者自卑,不如说是宜兴亳里陈氏之后、明末四公子陈贞慧之子的身份认同是他的自我同一性中最牢固的部分,这部分认同与他后来能在困境中坚持不懈并获得成就极其相关。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部分认同的消极面越来越明显。首先,对于自己作为儿子的身份的过度认同妨碍真正从心理上进入成年。陈维崧中年诗词中常见的与年龄不符的意气风发正可视为青年时期冲突的未解决。其次,这种对于过往家世的想象还会加重他在谋求现世功名时的冲突。也就是说,如果陈维崧停留在陈贞慧、冒襄、侯方域的历史叙事中,他就会成为过去历史的陪葬者和当下历史的局外人。从潜意识理论来看,陈维崧中年无嗣、七试不中,与此不能说无关。是做一个合格的遗少,还是成为一个具有原创性的作者,这取决于陈维崧能不能摆脱父辈的阴影,建立属于自己的完整认同。从这个角度来说,陈维崧在康熙三年(1664)违背冒襄的意志,执意北上(1)冒襄《和其年留别原韵,兼寄阮亭先生》序云:“其年读书水绘庵七载,昨岁下第,决计游燕,坚留不得。”[28]550陈维崧《将发如皋留别冒巢民先生》:“我闻长安街,连云矗扶荔。金张许史家,敝裾尚堪曳。逝将舍此去,愿言一谒帝。阳春二三月,渌水正溶漪。扁舟过先生,话别去燕翼。”[4]98(后为王士禛劝回),以及最终于康熙十年(1671)纳妾延嗣、直白地向龚鼎孳寻求推荐,都可以视为挣脱阴影、心理成年的过程。而成熟带来的是风格的稳定、创造力的爆发、词人身份的确定,同时,其社会性成就的其他方面,如子嗣的诞育、科考的成功也渐渐到来。
就词学而言,向来研究者都会注意到他后期“弃诗弗作”“专力作词”一事:
《乌丝词》刻而先生志未已也。向者诗与词并行,迨倦游广陵归,遂弃诗弗作……磊砢抑塞之意,一发之于词。诸生平所诵习经史百家古文奇字,一一于词见之。如是者近十年,自名曰《迦陵词》。(蒋景祁《陈检讨词钞序》)[3]94
《湖海楼诗集》中康熙十二至十四年没有诗歌收录。至于弃诗原因,严迪昌认为“正当其诗‘益苍辣奔放’之时,毅然弃去,显然有政治上的原因”[20]191。政治压力当然是存在的,但陈维崧在“弃诗不作”之前的几年内,其诗作也并无什么违碍之语。考虑到陈维崧中年以后强烈的仕进欲求和屡见于集中的干谒权门之诗,可知明清鼎革之事并不是他中年写作兴趣的所在。因此,“弃诗作词”在政治压力之外,应还有其他原因。
如果我们将康熙十二年(1673)“弃诗”一事与康熙十年所发生的人生转折合参,也许可以说,其“弃诗作词”也是个人同一性完成、心理成年与心理独立的结果。因为此时“天下填词家尚少”(陈维崧《任植斋词序》)[4]195,且其父执辈亦未有词学上的成就或陈规,这足以使陈维崧在词的世界里获得更大的创作自由,首次使自立门户成为可能。他于康熙十二年写给王士禛的信中有“数年以来,大有作词之癖。《乌丝》而外,尚计有二千余首”(陈维崧《与王阮亭先生书》)[4]53,说明了在康熙十年左右,他已经进入了创造力爆发的阶段。
对于终于获得独立的陈维崧来说,找到自己在历史时间中的位置,形成自己的历史叙事至关重要。对于大部分时代的人来说,历史时间是先天给定并且唯一的,但经历了易代的人们,同时属于两个或数个历史时间,必须对此进行主动的选择。这种选择的实质是身份认同。比如顺治十八年《明史案》中的主要罪状之一,就是不用清帝纪年而用亡明纪年。但文学作品中的时间感比纪年更隐晦而更可靠,遗老张岱在《西湖梦寻》中“历史终结了”式的叙事,或新贵王士禛在《冶春绝句》中“时间开始了”式的叙事,都可以看作对于自身归属的诚实表达。而陈维崧的表达,就是“词史”。
“词史”概念首见于《今词苑序》中,前已述及。陈维崧、吴本嵩、吴逢原、潘眉合编的《今词苑》,收词461首,109家。之前清词选本皆为明清合选,但此书是“第一本严格的清人选清词”[29]12,对于横跨两朝者,不奉清朝正朔者不予选入,如云间派中宋征璧与李雯皆入选,而未收陈子龙词。则此书与故明交割,在文化上依从清廷之意甚为明显。与此相应,陈维崧之序论述了以庄骚开端的宏观文学史,吴本嵩序则专叙本朝词坛盛事,二序于明清文学的递承关系皆未提及。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选词所以存词,其即所以存经存史也夫”并非虚语,而可看作历史书写的清晰意识与明确立场。
不仅如此,陈维崧还真正把“词史”带向了纪实。他打破了入清以来“词史”文学“幽微深隐”的惯例。这种惯例的特点是:重视政治史超过社会史,更愿意书写对故国的抽象怀念而不是民众的实际生活;重视主观感受超过客观事实,即“史外传心”式的书写;重视追忆过去超过实录当下;以及普遍使用隐喻的书写和阐释方法。陈维崧在《曹实庵咏物词序》中说:“苟非目击,即属亲闻……谁能郁郁,长束缚于七言四韵之间;对此茫茫,姑放浪于减字偷声之下”[4]365,这意味着陈维崧将“词史”写作带向一个由内至外、由隐至显、着眼当下的新阶段。
因此,在陈维崧的“词史”写作中,我们可以看到继承和创新的双重痕迹。《杏花天·咏滇茶》《水龙吟·咏杜鹃花》这些书写鼎革历史的作品,依然秉承幽微深隐的风格,只是这种“隐”不再是欲说还休、如字谜般的文词隐晦,而是由历史距离感带来的空灵,是将宇宙、人生、历史、文化涵括在内的复杂感慨。而在幽微深隐的反面,《贺新郎·纤夫词》《金浮图·夜宿翁村,时方刈稻,苦雨不绝,词记田家语》《念奴娇·送朱近修还海昌 ,并怀丁飞涛之白下,宋既庭返吴门,仍用顾庵韵》等词即所谓关注当下的“目击”“亲闻”之作,真实记录了历史事件、时代氛围和个人经历。至于“补史”功能也不再是文学上的夸大或幻想,而真正得以实现。
正是在“目击”“亲闻”之作丰富的主题、真切的关怀、直率的表达中,陈维崧“横霸精悍”的个人风格才成为可能、开宗立派的词坛地位才得以奠定。“词史”也终于在鼎革历史淡化的背景下,真正走向纪实。但由于纪实之目的与词体之特性终究有所抵牾,后世词人对阳羡词派遂多“直白”“粗率”“叫嚣”之讥。一百年后,常州词派振起,张惠言以“意内言外谓之词”重申诗词界限,再次将词带向寄托幽隐。而同处常州词派的周济,也在这一基础上再次改写了“词史”概念。
三、“词史”:在政治、文学与个人生命之间
王汎森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文献中的自我压抑现象》中揭示了乾隆时期,在文字狱造成的恐慌之中,因为“违碍”的标准并不明确,导致整个文化社会陷入一种扩大化的自我审查、自我猜忌和自我阉割之中。[30]权力因此通过生活化、日常化的方式,越过官僚制度的能力边界,渗透到帝国的每个角落。王汎森的论文揭示了这一统治策略绝对有效的一面,但在文学的领域内,特别是在词这一种富有弹性的文体上,应承与悖违、压力与转机中展现的动力关系,却显得格外复杂。本文从康熙年间出现的“词史”概念入手,梳理了“词史”背后的政治史、接受史和个人生命史问题,展示了在政治压力下,文学如何通过隐喻、误读、自我否定等多种方式,拓展表达的世界,成为记忆的保留者。
笔者的基本认识是,陈子龙词的被误读为“亡国之痛”与吴伟业以“史外传心”之愿入词既源于同一种时代心理,又有着文学思想上的继承关系。它们的共同点是既使用词承载原先不属于词的主题,但又恪守词的美学特征,同时带有强烈的追忆色彩。而其造成的格外幽微迷离、深远悲凉的效果,本身就是对词之境界的开拓,外在世界言论空间的压缩,又使得心理书写在词这一“缘情”的文体中结出硕果。但这种深幽、曲折、隐蔽、私人的书写只应作为对特定时代的呼应与对特定主题的表达策略。这种风格一旦形成,人们会渐渐将之泛化为一种普适的美学追求和评价准则,而忘记它背后最初的政治无奈,最后导致写作的狭窄与虚空,哪怕对于那些并不敏感的主题也无法予以直接、细致、富有批判性地写作。文学发展要重新获得动力,就要突破这一风气的笼罩。而呼应这一历史要求的正是陈维崧。“词史”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孕育成熟,成为既可以寄托历史感怀,又可以直陈现实人生的新的写作传统。这其中展现的,既有政治与文学间的动力关系,也有三十年间士人心态的急剧变化,以及词体本身的良好弹性。
“诗庄词媚曲谐”。当文学不受到外在侵扰之时,文体之间的功能划分及美学风格趋于稳定,作者大可以将自己不同层面的需求放在不同的文体中表达,而不会感到冲突。有些文体被置于较为严肃、公共并易于监管的位置,有些文体则更为自由。但当政治压力或文学传统本身的压力过于巨大时,创作动机将会流向那些压力更小的文体中去,并在那里开花结果。这些文体互相之间的消长、渗透、对话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显现着这个时代公共空间的开放程度与私人生活的丰富程度。而对于写作者,这曲折而艰难的历程只不过如《浮士德》所昭示:“成形,变形,永恒的心灵的永恒创造。”[3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