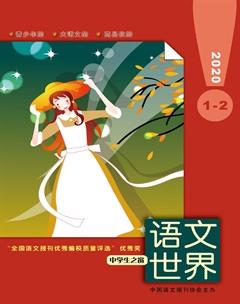高考古诗鉴赏中需弄清的几组概念
何永顺
在古诗鉴赏的教学实践中,笔者发现学生常常混淆“工笔、白描”“借代、借喻”“借景抒情、寓情于景、触景生情”等几组概念,导致阅读理解题失误不断,影响了学习的质量和信心。为了廓清认识,帮助学生分辨这些易错的概念,本文尝试从概念梳理及案例剖析两方面切入,深入浅出地析缕阐述,并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重心把握准,工笔白描易分清
工笔与白描是描写这种表达方式之中正面描写的两种方法。古诗鉴赏之中常出现这两个概念,需要進一步厘清它们的含义,才能正确判断两者的区别。
工笔,是细节描写的另一说法,指用细腻的笔触作精细地刻画和重点描绘,以突出它的特点,使读者有清晰、深刻的印象。古代诗人常用工笔着意于动作、外貌和心理的描绘,突出细节的重点,进一步强化情感。如张籍《秋思》中的“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作者因见秋风初至,忽发思乡之情,欲作书一封,但就在家书将要发出那一刻,他又觉得信中言语未能写尽心中之意,叫转送信之人“又开封”。一个丰满的细节将人物思乡浓情写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再如《孔雀东南飞》写刘兰芝被休回家,临别之时的装束:“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对穿戴的服饰及外貌写得十分具体详细,既突出了刘兰芝的漂亮也表现出她的自尊,形象鲜明饱满。
白描,本是国画的一种技法,纯用线条勾勒,不加渲染烘托。后被文学艺术借用,指用简明准确的语言,勾勒事物形象,表达作者感受。白描常与列锦结合。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温庭筠《商山早行》),“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马致远《秋思》)。列出几种景物,用蒙太奇手法建构成完整意境,不加修饰,突出情感,均属于白描。另外,白描很少拘泥于具体的动作、外貌和心理的描绘,而重在突出“神韵”,营造含蓄的“意境”。如:“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李白《赠孟浩然》)寥寥几笔,勾勒出一个高卧林泉、风流自赏的高洁形象,神韵顿出。再如“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用简洁的语言营造了明净悠闲的意境,富有感染力。
二、本质理解透,借代借喻很明了
借代与借喻都属于修辞手法。两者虽都带“借”字,但本质上却有着明显的区别。
借代,侧重于“代”,即代替。或以特征代整体,如“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用“雕栏玉砌”代故国宫殿;或以部分代整体,如“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用“樯橹”来代战船;或以颜色代本体,如“落红不是无情物”,用“红”代替花;或以工具代本体,如“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用“尺素”(写信用的绢)代替书信;还有用专有名词代替本体,如“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用“杜康”这个人的名字代酒;再如“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用“吴钩”代刀剑。不论何种形式,借代的本体和客体之间都有一定的关联,即相关性。
借喻侧重于“喻”,即比喻。借喻是一种特殊的比喻,它仅出现喻体而掩藏了主体。借喻可以还原成明喻。如“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苏轼《西江月·顷在黄州》)中“琼瑶”本是美玉,这里用来比喻皎洁的月色。再如“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李贺《梦天》)中“九点烟”喻“九州”。
借喻与借代的根本区别在于:借喻属比喻,本体与喻体不同类不同质,只是外形相似;而借代的本体与客体间紧密相关,而非相似。
三、细微见真章,情景关系渐分明
借景抒情、寓情于景和触景生情都属于间接抒情的手法。这几者之间的区别需要仔细分辨,才能把握。笔者曾就这一问题认真查阅过一些资料,发现在不同的高考复习资料中表述有差异,甚至相悖。笔者也曾就这一问题向一些资深的语文教师甚至专家求教,或语焉不详,或泛泛而谈,或避重就轻,均未切中要害。经过一番思考、对比和研究,笔者发现三者之间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若能区分,对于准确界定情与景之间的关系,提升古诗词鉴赏能力定有所裨益。
借景抒情,情与景兼顾,重在于情,景只是抒情的媒介,诗人在景中饱含强烈的情感。这就是王国维先生曾说的“情景相生,以情着物”。例如唐代韦庄的《含山店梦觉作》:“曾为流离惯别家,等闲挥袂客天涯。灯前一觉江南梦,惆怅起来山月斜。”最后两句借景抒情,思念家乡、思念亲人的惆怅和盘托出,情感强烈。再如李商隐的《端居》:“远书归梦两悠悠,只有空床敌素秋。阶下青苔与红树,雨中寥落月中愁。”最后两句借景抒情,赋予“青苔”“红树”以浓郁的情感,寄托思亲孤寂之情。
寓情于景,重在于景,情隐藏在景中,需要结合语境细细斟酌方能悟出。如“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景中寓情,含蓄蕴藉。再如韦应物的《滁州西涧》:“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寓情于景,读者要知人论世,方能披文得情,悟出其间不得其用的无奈伤感之情。
借景抒情和寓情于景其实密不可分,只是侧重不同。如张说的《送梁六自洞庭山作》:“巴陵一望洞庭秋,日见孤峰水上浮。闻道神仙不可接,心随湖水共悠悠。”前两句寓情于景,景下隐藏着送人时的孤独之情;后两句借景抒情,借湖水悠悠抒发遭贬谪的失落、送别的伤感,言有尽而意无穷!
触景生情,重在于触,即诗人见到景物后所触发的联想和情感,其间有一个由此及彼的跳跃或转换。如王昌龄的《闺怨》:“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属于典型的触景生情,少妇看到杨柳春色,突然想到自己戍守边疆的丈夫,触发了思念之情和后悔之意。
顺便提及,一些参考书上经常将移情于景(移情于物)与寓情于景相提甚至相混,其实两者还是有区别。移情于景(或移情于物)即将主观的感情移植到事物上,反过来又用被感染了的事物衬托主观情绪,使物人一体,能够更好地表达人的强烈感情,发挥修辞效果。如白居易《长恨歌》:“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断肠声。”月亮和铃本身并没有情感,作者将“伤心”之情、“断肠”之声移于月色和铃之上,赋予这两种物浓郁的情感。再如苏轼的《海棠》:“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花不会睡,但作者却将深深爱护之情投射于其上,以“睡”字点出,别具一番韵味。
当然,这些都是笔者的一家之言,仅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以便让学生厘清这些概念及关系,在实际的教学中发挥出更大的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