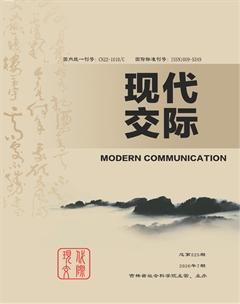豪斯翻译质量评估模式下人物语言英译比较
张欧荻 高梦瑶
摘要:现代中国文学中先锋文学的力量不容小视,其中余华的作品充满暴力、死亡、苦难等主题,语言简洁、生动、冷漠,对人物的刻画入木从三分,讽刺荒诞的人物语言集中体现着余华小说特色。从网络书籍销售和书评来看,余华小说在海外很受欢迎,译者在余华中篇作品的海外译介中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基于多篇中篇小说,基于豪斯翻译质量评估模式中语域理论对比分析特色的人物语言,通过案例分析研究译作品的英译质量。
关键词:翻译质量评估模式 语域 人物语言 翻译质量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20)07-0083-02
话语分析及语域分析领域自上世纪90年代逐渐成为一些翻译学家关注的焦点。朱莉安·豪斯作为代表人物,立足于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语篇分析等理论,出版了《翻译质量评估模式》和其修订本,促进一套逐渐系统化的翻译评价模式得到完善和发展。屠国元和王飞虹(2003)认为该研究使翻译行为得到规范,翻译质量更加精进,实现了语际转换机制多途径得以实现的目的。人物话语是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申丹,1998)。她提出人物的言词和思想是很多小说家塑造和丰盈人物的工具,有利于推动情节的发展。此外,在文学作品当中,人物身份、角色要和人物习惯个性相符合,与所处的场合相符合(郭粉绒,2000)。在翻译中对人物语言的准确把握能够更加形象丰满地表现人物形象,进而提高故事本身的真实感和可信度。因此,笔者从余华的两篇中篇小说的语域层面看英译人物语言。
一、翻译质量评估模式概述
功能语言学是该模式的来源和出发点,语域分析是该模式立足的方法,主张翻译质量评估中的“对等”问题中语义、语用及语篇之间的对等性。豪斯首先考虑到情景角度的重要性,用地域、阶层、介入程度、社会职能、态度等八个维度,并将这八个维度作为标准来对比原文本和目标语文本在不同层面上的异同,分析得出二者之间所有不匹配的地方。因此,译本的质量高低就取决于两个文本的相符程度。同时豪斯还提出功能对等是译者必须考虑的因素。显性错误包含文本中指称意义的错误和译语语言系统的断裂。而凡是在语域三要素各个维度上的不匹配均为隐性错误。从这个运行模式基本可以看出,翻译质量评估模式通过统计隐性错误(词汇与情景语境角度)和对应的错误描述系统,全面地对英译文本质量作出评价。豪斯翻译质量评估模式的修订版针对之前理论架构的缺陷,创造性地提出从文本、语域和体裁等层面对译本质量和译本功能进行深入研究。在这一理论架构中,语域同样还是来自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当中的三要素之一。本质上,这个模式首先关注文本的语域,其中包括语场、语旨和语式,通过分别客观比较进而分析译文在处理过程中的概念功能与人际功能是否与原文贴合,对明显错误和不匹配现象要说明和描述,目的是归类文本的翻译类型为先行翻译还是隐性翻译并作出陈述和总结。
二、案例分析
1.小说题材和内容对比
《一个地主的死》是小说集《战栗》中余华风格的代表,像是《活着》的另一种写照。小说的时代背景为抗日战争时期,描述的是战火纷飞年代里,地主家少爷以一己之力与敌军斡旋并斗争走向不归途的故事。而《我为什么要结婚》选自中篇小说集《黄昏里的男孩》,讲述生活中婚姻给主人公带来的困扰,以及他自身作为旁观者对于朋友婚姻的思考。两篇文章社会背景和故事情境既有主题背景差别,又有人物性格的鲜明差别,但从整体上都不乏大量人物语言烘托背景,促进情节发展。笔者试图从语场这个角度出发,通过这两个故事当中人物语言的英译,对豪斯翻译质量评估模式做进一步研究。
2.语场层面比较
语场一般指正在发生的社会活动的本质,像活动主旨,文本内容和话题,以及活动场所等(芒迪,2014)。《我为什么要结婚》语言简单,风格荒诞,从形式看故事三个语场被明显分隔开:家中的主人公及其父母;回忆中朋友萍萍和林孟的相识相知场景;萍萍林梦家中。故事荒诞地讲述了“我”的出现导致一对夫妻的关系彻底破裂,还稀里糊涂地“被结婚”。而《一个地主的死》的故事场景则更复杂多变,涉及的人物和情节也更加繁多,而且从时间发展来看,故事场景交替出现,情节的横向和纵向变化双重发展。那么相对应来说,两个故事的译本也应当考虑到语场特点,恰当选择合适表达。
句法当中往往通过译者使用的人称词和所用动词的及物性推断人物之间的关系,判断人物心理状态甚至是所处境遇。《我为什么要结婚》在第一部分中反反复复出现“我”重复的“你们拿一把菜刀把我劈成两半吧”,而每当这句话出现,主人公的心态都是听到父母无休止呼唤自己时的无奈和崩溃,译者将它翻译为“Better get a cleaver and chop me into two.”这样的处理采用了祈使句,省略了主语,“把”结构处理成了两个英文中的及物动词,祈使句表明“我”的不耐烦和抵触。“我”是整个故事发展的核心,而作为我好友的夫妻萍萍和林孟婚后关系不比从前,尤其在第三部分“我”的出现使得二者关系彻底破裂。通篇中人物语言主要由“我”从第一视角诉说,比如:“萍萍,你和他离婚是对的,和这种人在一起生活简直是灾难。”被译为:“Pingping,its good that you and he are getting divorced.”译者保留原文“我”给好友叫“他”,同一时空下用第三人称显然是表达“我”对林梦的愤怒,是疏远双方关系的表现,这个尴尬情境下译文被直译为人称代词“he”。另外,译者还把评价词“對的”翻译为“good”,比起“right”更加强调说话人的坚定语气。
同样从称呼的翻译来看,《一个地主的死》从总体来说选词有几处在程度和文化信息上不太匹配。比如:“老太婆”被翻译成“old lady”,但是原文本当中“老太婆”这个称呼是说话者由于关系亲近而使用的非常平常的称呼,从语气程度上来说是非常不正式甚至粗鄙的言语,但是译文用“old lady”当中的核心词汇“lady”,相比之下在正式程度上不同,反映的社会等级关系也不同;“乌龟王八蛋”则是这种民间粗话的另一个实例,译者通过直译的方法翻译对应的“turtles egg”,具有特殊的情绪特征,但文化差异性可能会给读者带来一定的阅读障碍,可能“bastard”用在这里比较合适;文中提到的“人上人”被处理为形容词“immortal”,原文中重在表达人物的权财实力和社会地位,可是“immortal”是一种歌颂精神层面的高度褒扬形容词,对比之下可见这样的翻译还是不太合适。但是在句法方面明显通过拆分法调整目标语形式,在这个过程增加了大量新的信息。长句分成短句,例如:“干什么都要有手艺,种庄稼要手艺,剃头要手艺,手艺就是饭碗。”译为:“Whatever you do,you have to do it with skill.If youre planting crops,do it with skill.If you cut hair,do it with skill.Having a skill is like having a full rice bowl.”译文还增添了新的信息,例如“脱掉,赶紧脱掉”,译为: “Take it off! Dont just stand there! Take off your clothes!”这里直接增添了一个新的句子,承载新的信息,是译者考虑到原文语境,创造性地丰富译文内容的体现。此外,文章开始“都等着你吃饭呢”被处理成“were waiting for you to start dinner”,增加了新的主语。
三、结语
以人物语言翻译中词汇和句法比较为前提,笔者选取的译例对两篇小说中人物语言英译本的翻译质量进行分析和研究,立足原文与译文在语场信息上的忠实情况,发现从该评估模式的框架来看,相比较《一个地主的死》的译本,白亚仁翻译的《我为什么要结婚》在语场层面保持了更高的一致性,尽管用词和句法上有细微差别,但不影响整个语篇的语场信息贴合程度,这个可能与故事本身情节设置和背景信息的清晰程度有关。从整体来看,本文涉及的两个译本都能充分考虑小说翻译中语场的重要性,并且利用一些翻译技巧去平衡中英文语言和文化不可避免的差异。豪斯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能够恰当指导人物语言英译质量比较,为文本之间的对比分析提供了可以参考的框架,在整个文本分析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接下来,笔者会从余华更多作品中总结更多类型和体裁的翻译案例,从人物语言的翻译中洞悉译文质量,从而作出更加全面和客观的分析。
参考文献:
[1]House,J.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A Model Revisited [M].Tubingen:Gunter Narr,1997.
[2]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Barr,Allan H.Boyinthe Twilight[M].New York:Pantheon Books,2014.
[4]黄粉保.论小说人物语言个性的翻译[J].中国翻译,2000(2):44-46.
[5]屠国元,王飞虹.跨文化交际与翻译评估:J.House《翻译质量评估(修正)模式》述介[J].中国翻译,2003(1):60-62.
[6]余华.黄昏里的男孩[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7]余华.战栗[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8]杰里米·芒迪.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应用[M].李德凤,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刘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