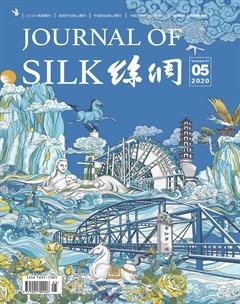内蒙古察哈尔蒙古族传统服饰的简繁艺术特征解读
李洁



摘要: 察哈尔传统服饰是蒙古族28个部落传统服饰中的一支,具有突出的形制之简、色彩之素、头饰之繁、佩饰之多的艺术特征,在众多的蒙古族服饰中独树一帜。文章通过对察哈尔蒙古族现主要居住地锡林郭勒和乌兰察布地区的田野调查和历史文献调研,运用艺术学和民俗学的视角,概括其独特的简繁艺术特点,探讨该族群如何通过适简与从繁的服饰礼仪功能来构建民俗生活。研究表明,察哈尔蒙古族传统服饰的简与繁不仅是一种艺术特征,也是族群历史记忆的载体和身份建构的工具,其形成原因受到历史中军事职能、宫廷文化和游牧生活三者的共同塑造,并影响至今。
关键词: 察哈尔蒙古族;传统服饰;简繁;艺术特征;民俗
中图分类号: TS941.12;K892.23 文献标志码: B 文章编号: 1001
Abstract: Chahar traditional costume is one of the traditional costumes of 28 Mongolian tribes. It has prominent artistic features such as simplicity of form, plain colors, complexity of headwear and many accessories. It is unique among many Mongolian costumes. Based on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historical literature investigation in Xilingol and Ulanchabu areas where the ancient Chahar Mongol nationality now mainly liv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ir unique simple and complex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t and folklore, and explores how the ethnic group constructs folk life through the function of simplicity and complicated costume etiquette.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simplicity and complexity of the traditional costume of Chahar Mongol nationality is not only an artistic characteristic, but also a carrier of the historical memory of the ethnic group and a tool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 The reason for its formation is the common result of military functions, palace culture and nomadic life in history, and generates influence still in the present day.
Key words: Chahar Mongol nationality; traditional costume; simplicity and complexity;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folk customs
蒙古族服饰是北方游牧民族服饰的典型代表,因其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而备受瞩目。蒙古族部落众多,传统服饰按照地域与部族可划分为28个部落单元[1]2。在这些异彩纷呈的部落服饰中,察哈尔传统服饰具有突出的形制之简、色彩之素、头饰之繁、佩饰之多的简繁特征,更多地保留了蒙古族宫廷、军事、游牧生活的历史印记,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近代以来,半农半牧的察哈尔地区受汉文化的影响,日常生活中的传统服饰逐渐消失和变异,在牧区也只有年长的人依然穿戴。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的深入开展,察哈尔传统服饰又逐渐回归到人们的视野中,尤其以节日仪式活动中的使用最为活跃频繁。通过文献调研资料发现,学者对于蒙古族服饰的研究多数聚焦在游牧生活保留较多的巴尔虎、布里亚特、鄂尔多斯、乌珠穆沁、土尔扈特等部落服饰上。对察哈尔传统服饰的研究则较少,并且主要以记录描述为主,相关资料记载于《察哈尔史》[2]、《察哈尔民俗文化》[3]等地方性资料中。学术性的研究关注点多数集中在繁缛华丽的察哈尔头饰上,代表性研究有《察哈尔蒙古部女性头饰艺术研究》[4]、《蒙古族女性头饰民俗学研究》[5]等。因此,本文在对察哈尔传统服饰整体把握的基础上,提取出袍服和饰物中最具特色的简繁特征为切入点,力求呈现其最本质的艺术特征和民俗生活。简繁虽然是中国民族服饰共有的艺术特色之一,但每个族群对于简繁的选择却大相径庭,体现了一个族群特有的审美情趣、历史记忆、文化认同和精神追求。
本文考察的对象为“察哈尔传统服饰”,考察的地区为察哈尔传统服饰保存最集中、最完整的内蒙古锡林郭勒和乌兰察布地区,考察时间覆盖四季,地域涉及该地区的城镇和牧区,访谈对象有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普通手工艺人、牧区牧民等,并对那达慕、美食节等集中穿着民族服饰的传统性和非传统性仪式活动进行重点考察,希冀透过该部落极具特色的简繁特征来展示察哈尔蒙古族传统服饰的样貌和民俗文化,并从历史记忆的角度解释其形成原因。
1 察哈尔蒙古族传统服饰的简繁艺术特征
“服饰”包括衣服和饰物,蒙古族服饰也不例外,按照从上到下的穿戴顺序依次为头饰、帽子、袍服、腰带、佩饰和靴子。察哈尔蒙古族传统服饰最具特色的是女性头饰、男女袍服和相关佩饰。具体来說,察哈尔蒙古袍崇尚形制简洁、色彩简素,男女略有差异;而女性头饰却极其繁丽;男女都喜欢佩戴饰品,男子的佩饰尤其精美复杂。总体上,简与繁构成了察哈尔传统服饰的两大特色,这也是区别与其他部落服饰最重要的部分。本文对形制之简、色彩之素、头饰之繁、佩饰之多这四个特征进行展开。
1.1 形制之简:高度凝炼的袍服款式
蒙古袍是蒙古族服装的主体部分,蒙古语叫“德格乐”。察哈尔蒙古袍具有明显的季节特征,有夹袍、棉袍、无面皮袍、吊面皮袍等。其整体形制简洁,特点都是立领,大襟右衽,宽袍窄袖,袍长及靴,是蒙古各部较为典型的款式服饰[6]。内部造型一般无明显分割线,主要特征是沿脖领、襟甬、腋窝和腰部镶1~3条0.5 cm左右的细边。已婚女子长袍,称作“特日丽格”,较其他部落更加紧身收腰,这不能仅从外观上突出了女性身材的优美线条,也使察哈尔蒙古部落的女性看起来更干练利落[7],如图1[1]309-321所示。
据当地服饰传承人乌云其木格(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介绍:现在的察哈尔女袍更加紧身收腰,突出曲线美。腰带也从3~4 m长,变成了仅60~80 cm长的装饰物。男女袍服的变化主要还体现在边饰的数量上。最早穿一条边儿的,后来穿两条边儿的,20世纪80年代左右开始多穿三条边儿的。扣襻儿的数量与镶边的数量通常相匹配,有几条边就装饰几道扣襻儿,使用的材料、色彩也与边饰大都相同。除此之外,几乎再无其他装饰。察哈尔蒙古袍简洁的边饰与其他部落形成鲜明的对比,如表1所示。察哈尔蒙古袍造型简洁,但是对制作工艺要求特别严格,沿边儿是否宽度均匀、扣襻儿是否笔直精致、牵缝是否均匀一致是决定一件袍服工艺优劣的关键所在。
1.2 色彩之素:端庄典雅的单一色彩
察哈尔蒙古袍的色彩崇尚单一和简素,有两层意思:一是单件服饰的色彩主色面积大、配色少,袍服简洁的边饰为大面积的单色拓展了足够的色彩空间,如图2所示。
二是对某些色彩的重复使用率高。根据地方志资料记载:“察哈尔男子通常穿靛蓝色、蓝色、绛紫色长袍,女子则多穿绿色、暗绿色、蓝色、天蓝色和粉色长袍。夏天穿单夹袍,一般颜色较淡,如淡绿、粉红、浅蓝、乳白等颜色;冬季多穿老羊皮、羔皮做的袍子,颜色多为青、灰、深蓝等。”[8]可见,察哈尔地区的服饰色彩主调集中在蓝色、白色、绿色和红色上,并且色彩作为一种民俗象征符号,具有区分群体、性别、季节等信息的功能。笔者田野调查的资料也显示出该地区对这几种色彩的偏好。为了尽可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察哈尔蒙古袍的色彩情况,本文分别选取了夏季与冬季不同季节的两次大型聚会(2018年7月9日乌兰察布察右后旗第二届“中俄蒙”商品博览会暨国际美食节和2018年12月29日锡林郭勒正蓝旗第十六届“浑善达克”冬季那达慕)服饰作为信息采集的来源,共随机采集80套袍服色彩信息进行数据分析,发现现在察哈尔地区的服饰面料比从前丰富了许多,但牧民常用的袍服颜色较以前并没有太大差别,尤其以蓝色居多,其次是白色、绿色和红色,如图3所示。察哈尔蒙古族对蓝色情有独钟,除受自然环境的审美习俗影响外,主要与“五色四藩”中青色蒙古居中的宗教思想有关[9]。
随后笔者对袍服的季节、性别再做区分,方法是将这80件袍服中面料相同,几乎没有色差的色彩去除,提取出来的色彩可归纳为36种,如图4所示。根据以上分析显示,在夏季集会上男女袍服色彩鲜艳且性别差异明显,男子多穿白色、蓝色,女子多穿红色、绿色,面料也极为丰富,有棉、丝、毛、化纤等织物。而冬季那达慕参加者以男性居多,并不能反映男女袍服之间的色彩区别,整体提取出的色彩纯度较低,面料以深色缎面、乳白色吊面皮袍及人造皮毛为主。总体来说,察哈尔地区的服饰色彩并未发生太多的变化,仍然延续了传统的简素色彩和区分季节、性别等信息的功能,同时也反映出该部落民众长期不变的内在审美心理和族群意识。
1.3 头饰之繁:堆金成冠的华贵头饰
头饰也叫头戴,蒙语称“陶勒盖伊甲斯勒”,是女性的专属物件。蒙古族各部落女性头饰造型差异很大,款式种类繁多。按照造型样式大体可分为连垂式、犄角式、辫套式和盘发式四大类,如表2所示。
察哈尔蒙古族女性头饰属于连垂式,是头饰中结构最为复杂,金银珠宝用量最多,工艺最为精湛的类型。复杂并不意味着随意堆砌,察哈尔头饰在“繁复中见规整,丰富中见条理,变化中见秩序”[10]。在制作工艺上各旗县略有不同,但基本结构都是由头箍额饰、鬓角垂饰、耳后坠饰、胸饰和脑后饰组成。材质使用金银作为框架,上面镶嵌大小不一的珍珠、玛瑙、绿松石、红珊瑚、琥珀、蜜蜡、翡翠、青金石等贵重珠宝。色彩讲究五色俱全,各色珠宝相间串联,在乌发的映衬下显得富丽堂皇、璀璨夺目。头饰作为服饰中最重要的点睛部分,其意义不仅是审美装饰品,也是整个家庭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象征,个体头饰的材料和质量的选择取决于家庭条件,蒙古谚语说“男人有钱用在马上,女人有錢戴在头上”。传统的察哈尔蒙古族头饰多则重达5 kg以上,少则1~2 kg,一些富裕人家往往愿意花费几十头牲畜的价格来为置办一件体面的头饰。现在,头饰已经退出了民众的日常生活,只在婚礼和节日展演场合才能看到,且材质、做工都大不如以前,那些聚宝成塔的古老头饰成了博物馆里的遗留物。
1.4 佩饰之多:琳琅满目的精美佩饰
蒙古族着装具有“少穿戴,多佩饰”的特点,这与其游牧生产方式有关。“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必要的生活用品需要能够随身携带。蒙古人非常珍惜这些物品,制作上也相当精美,既有生活功能,又有装饰功能,如图5所示。
与其他部落相比,察哈尔地区的佩饰无论从数量上,还是精美程度都更甚,男子佩饰尤其丰富,典型的佩饰有银鞘刀、筷子、托海、火镰和褡裢等,如图6所示。
银鞘刀是察哈尔男子必备的佩饰六宝之首,可用于挽缰结绊、修鞍换辔、削柳绑杆、宰杀牲畜、防兽护身等多种功能。男子的托海可挂火镰和刀,褡裢装鼻烟壶、哈达、银钱等。富裕人家在烟口袋上配银夹子连着扣烟盅、银坠子、银烟签等物件。这种垂挂佩饰的方式可追溯到契丹时期的“蹀躞带”,是牧民生活智慧的结晶。佩饰品质高低差别很大,一个好烟嘴的价格甚至超过一批骏马。妇女佩饰主要是一对半月形的荷包,一个是鼻烟壶荷包,装鼻烟壶、牙签儿、镊子、耳勺等;另一个是针线包,装别针的针页。随着游牧生计方式的衰退,这些精美佩饰的实际功能已经退化,演化成具有审美价值的生活装饰品。
2 察哈尔蒙古族传统服饰适简与从繁的民俗功能
察哈尔蒙古族传统服饰的简繁特征体现在静态的服饰视觉表层,且动态的实践形式表现在丰富多彩的民俗生活中。为了深入揭示服饰的简繁背后所反映的文化内涵和行为意义,本文从人类学、民俗学所关注的人生礼仪和社会礼仪两个方面对民俗服饰的简繁应用进行剖析。
2.1 人生礼仪中服饰的简与繁
察哈尔蒙古族的人生礼仪突出体现在女性的“换装”仪式上,遵循“两头简单,中间复杂”的原则,即服饰的简繁随着年龄的增减而变化,装饰从出生的无,到中年的繁,再到老年的简。
察哈尔小姑娘头发梳成牛角辫或一条独辫儿,几乎没什么装饰,长袍的镶边也很简单,通常只有一道边。逐渐长成大姑娘以后,饰品渐次增加,开始佩戴简单的头饰,但不能戴大耳环和辫套,衣服大襟扣上戴银牙签、绣花荷包及针线包等。
结婚成家是蒙古族特别重视的人生礼仪,标志着个体“从一社会地位到另一社会地位的最重要过渡”[13],婚礼仪式中所有的装饰都极尽繁复,达到人生礼仪的顶峰。新娘出嫁前吟诵的“感念母恩”祝颂词中所描述:“今天女儿要出嫁,离您远去要成家,最好的衣服给她穿,金银首饰也不少……”[14]在过去,婚礼头饰是女方的重要嫁妆,很多人家在女儿很小的时候就从草原货郎手中购买宝石,攒到女儿成年了,再配上母亲、祖母头饰上的宝石,给她做一顶全套的婚礼头戴,称为“宝德斯”。这顶头戴寄托了亲人的思念和祝福,也反映了草原民族独特的财产分配制度。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发展与定牧生活的变迁,现在大部分婚礼头饰已趋于简化,也不再固定由女方家做,男女双方通过商榷来决定,材料都也是在店里直接选购订制。婚礼仪式上新娘、新郎都要穿艳丽的蒙古袍。新娘去掉腰带,称作“布斯贵洪”,意为无腰带之人,外面还加套一件齐肩长褂的对襟敖吉。从过渡礼仪的角度来看,不系腰带和对襟敖吉都体现出分离仪式的特点,象征女性从未婚到已婚的身份转变。
已婚妇女的服饰在儿女长大后递繁从简,这代表着社会角色和家庭地位的再次转换。尤其到了老年以后,饰品、色彩也越来越趋于简素,在人生抛物线上逐渐回落到原始水平。服饰的简繁在整个人生礼仪中伴随着人生角色的调整,有序变化,折射出草原儿女顺应天时的生活智慧和祈福求祥的家族愿望。
2.2 社会礼仪中服饰的简与繁
察哈尔蒙古族传统服饰的简繁饱含着蒙古族民众的经验和智慧,不仅具有实用性,还展现出社会礼仪的光辉。一般来说,日常服饰简单,待客时复杂,节日着盛装。
以察哈尔白旗女性头饰为例,头饰由四个部分(小发箍、发筒、大耳环、大发箍)组成,佩戴的简繁由场合和客人的层次决定。场合不同,组合佩戴的方式也不同。单独戴小发箍的是未婚少女,已婚妇女见客人的最低标准是小发箍加发筒,中等层次的客人要再加上大耳环,最高规格是四部分全部带齐[15]。这种叠加佩戴的方式在察哈尔其他地区也一样。客人的层次高低不完全取决于社会地位,还与亲属关系、年龄大小、熟悉程度甚至地理位置的远近有关。接待熟悉的邻居可以小发箍加发筒的最低标准,宴请尊贵的客人或盛大的节日上则需穿戴最高规格的头饰。在察哈尔蒙古族心中接待尊贵的客人就等同与盛大的节日,这也体现出蒙古人的热情好客。
如前所述,现代察哈尔地区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很少佩戴头饰,但是一年几次的“耐亦日”聚会上依然可见。“耐亦日”意为联欢、喜庆、盛会,反复强调一个主题词就是“聚会”[16]。草原上地广人稀,聚会是人们物质交流与精神交流的双重需求。这种特定的“公共关系”下的聚会仪式区别于日常生活,穿戴也自然不同于平常。已婚婦女还要在袍服外面套一件装饰精美的大坎肩,男性也必须衣帽靴穿戴整齐,佩戴成套的饰品,呈现出反结构的仪式特点。日常之简与节日之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简繁在社交礼仪中的灵活应用,也正是蒙古族知礼守节、尊重长辈、惜物节约的优秀文化传统的集中展现。
3 察哈尔蒙古族传统服饰简繁特征的形成原因
察哈尔蒙古族传统服饰的形成与当地的历史文化、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有着密切的关联。历史上,军事属性、宫廷属性和游牧属性三者共同塑造着察哈尔文化,也成为察哈尔蒙古族传统服饰简繁艺术特征、民俗活动形成的主要成因,并作为核心文化因子至今保留在现代察哈尔传统服饰中。
3.1 军事职能属性
关于察哈尔蒙古袍边饰简洁的原因,在田野调查中呈现出几种不同的猜测:以乌云为代表的当地牧民认为和以前物质溃泛有关;以朝孟鲁为代表的当地牧民则认为与当地民俗有关,即镶边的数量与年龄成正比,小孩儿镶得少,大人镶得多;服装店的萨仁则从制作工艺角度考虑,认为衣服面料薄的镶一条边,衣服面料厚的镶得多。当地著名学者夏·东希格老先生的说法更具解释力,他认为边饰简洁体现了军事功能的需求,并且一条边的袍子配一道扣子,是为了打仗时可以快速系好衣服的缘故。自成吉思汗起,察哈尔的前身“怯薛”曾担任大汗的贴身侍卫和宫廷护卫亲军,以英勇善战著称,被誉为“利剑之锋刃,盔甲之侧面”。蒙古民间谚语中有“没有衣领就不称其为袍子,没有察哈尔就不起兵出征”的说法。察哈尔的军事职能一直延续到近代的抗日战争,如察哈尔正蓝旗的“袍子队”就是当时有名的抗日团体。如今,察哈尔的军事功能已经消失,但在服饰上仍然保留了典型的军戎服饰的特点,边饰简洁不能超过三条边,并且窄而朴素,无刺绣、镂花、拼贴等复杂的装饰手法。
3.2 宫廷文化属性
察哈尔部从承担历代大汗的“怯薛”侍卫开始就一直生活在汗帐周围,服饰受到蒙古族宫廷文化的熏染,形成了典雅、高贵、庄重的宫廷特点。马可·波罗曾记录了大汗赏赐怯薛服饰的情形:“缘其颁赐此一万二千男爵袍服各十三次,每次袍色各异,此一万二千袭同一颜色,彼一万二千袭又为别一颜色,由是共为十三色。此种袍服上缀宝石珍珠及其他贵重物品,每年并以金带与袍服共赐此一万二千男爵。金带甚丽,价值亦巨,每年亦赐十三次,并附以名日不里阿耳之驼皮靴一双。靴上绣以银丝,颇为工巧。”[17]从史料可见,这些服饰价值昂贵、做工精美、色彩统一,具有典型的宫廷风格。在现代的察哈尔蒙古族传统服饰中,依然保留着宫廷生活的历史记忆,如袍服色彩简素,头饰富丽华贵,佩饰做工精美,正式场合全套穿戴等。尤其是现在女性穿的贴身、窄袖、无腰带的袍子“特日丽格”,就是汗帐中管理宫廷内务的侍女们(察哈尔部的属民)在职业要求精干、利落、美观、简便的服装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10]张杰, 靳向斌. 艺术设计中的“简”与“繁”[J]. 艺术与设计(理论), 2008(1): 27-29.
ZHANG Jie, JIN Xiangbin. The "simple" and "complex" in art design[J]. Art and Design (Theory), 2008(1): 27-29.
[11]杜娟. 蒙古族金银器发展与现状研究[D]. 北京: 北京服装学院, 2013.
DU Juan.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and Status of Mongolian Gold and Silver Ware[D]. Beijing: Beijing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 2013.
[12]徐子淇, 苏日娜. 荷包文化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作用及保护路径[J].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17(4): 97-105.
XU Ziqi, SU Rina. The role of Chinese pouch cultur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ountryside and corresponding protection path[J]. Heilongjiang National Series, 2017(4): 97-105.
[13]阿诺尔德·范热内普. 过渡礼仪[M]. 张举文,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87.
ARNOLD Van Genep. Transitional Etiquette[M]. Translated by ZHANG Juwen.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2010: 87.
[14]樊永贞, 潘小平. 察哈尔风俗[M]. 呼和浩特: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10: 7.
FAN Yongzhen, PAN Xiaoping. Chahar Custom[M]. Hohhot: Inner Mongolia Education Press, 2010: 7.
[15]齐木德道尔吉. 天之骄子蒙古族: 上[M]. 上海: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7: 134.
CHIMEDDORF. Gods Favored One Mongolian: Upper Part[M]. Shanghai: Shanghai Jinxiu Wenzhang Publishing House, Shanghai Cul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7: 134.
[16]邢莉. 内蒙古区域文化的变迁[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538.
XING Li. Changes in Inner Mongolia Regional Culture[M].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2013: 538.
[17]马可波罗行纪[M]. 沙海昂, 注, 冯承钧, 译.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360.
Travel of Marco Polo[M]. Noted by SHA Haiang, Translated by FENG Chengju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3: 360.
[18]恩斯特·卡尔西. 人论[M]. 甘阳,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83.
ERNST Cassirer. On Man[M]. Translated by GAN Yang.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85: 83.
[19]苑秀明. 淺析蒙古袍结构的“烟囱效应”[J]. 天津纺织科技, 2012(2): 37-38.
YUAN Xiuming. Analysis of the "chimney effect" of Mongolian robe structure[J]. Tianjin Textile Science&Technology, 2012(2): 37-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