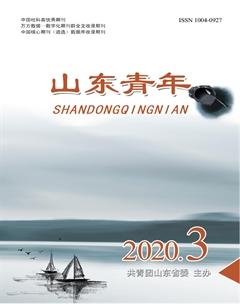历史视角下解构权威兼论权力与权威的关系
邓浩然
摘 要:权威作为贯穿人类历史的一种普遍社会现象,存在于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对于我们的制度和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本文在对前人有关权威的理论分析总结的基础上,试图根据语义环境分析“权威”,从权威的萌孽到制度化的完成,再到社会惯性之下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入手,定义权威。旨在从历史的视角下揭示权威的本质、探索权威的源流并探讨权力与权威的关系问题。
关键词:权威;权力;解构
“解构”概念源于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deconstruction”一词,由钱钟书先生翻译,原意为消解、揭示等,德里达在这个基础上补充了“消除”、“反积淀”的意思。在本文中,采用‘解构一词,旨在表达分解、重构的含义,并试图摆脱固有语义环境中关于权威定义的惯性,从权威的萌孽到制度化的完成,再到社会惯性之下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入手定义权威,揭示权威的本质、探索权威的源流并探讨权力与权威的关系问题。
当我们开始定义周边的一切时,我们也正在被周遭的一切所定义,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相对哲学,这是意识对客观世界一切已发生事项的复杂反馈。意识或者思维体系建立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人脑,所以在这种制度化之下建立起的权威,逐渐在我们的思维体系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反应程序”。单从这一方面讲,权威可以说是人脑中的一种主观反映形式。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点认为,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权威体系的建立在本质上也符合这种原则,分工的固化与约定俗成的传统形成了思维惯性,人们对旧有传统的习惯性依赖,成为了权威得以层构的土壤。
笔者尝试对权威进行了定义,即权威作为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现象,代表着一种以权力为执行路径的服从关系,表现为人们在意志方面对具有某种威望和支配作用意识的主观认可,是社会惯性之下层累地造成的认知传统与现有的公共信奉在人脑中的主观反映形式。
一、传统语义习惯下关于权威的认知惯性
(一)概念意义的传统
基于汉字的表述方式,我们在理解或者解释权力与权威时通常会从“权”字入手,权力在字面上的表达侧重于一种有组织性的“强制力”,即一种有实施途径的执行方式;而权威在字面上则通常被解释为“权力与威势”[1],我们更倾向于将他理解为一种“基于惯性的影响力”。某种程度上来说,权威不具备实施途径,是一种更为内在的作用形式,但这种潜在的影响力却是潜移默化、深远持久的。
利奇(G.Leech)的《语义学》认为语义有七种类型[2]。其中最核心的一种即为概念意义(也译为“理性意义”),又称外延意义(denotative meaning)或认知意义 (cognitive meaning)。它是指一个词或短语与现实世界或虚构世界的现象所联系的那部分意义。 概念意义是一个词项的中心意义,是语言交际的核心因素。我们必须清楚一点,固有名词出现在固有现象之后,一切类似于“权力”与“权威”的这类概念型名词都具有认知意义。概念意义是词的基本意义,是一种抽象的意义,它不与客观世界中的事物和现象发生直接的联系,也不会对其产生直接的影响,但它又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因此概念意义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社会的发展、事物的变化而逐渐成为一种非线性的叠加态。
“权威”一词最开始在《吕氏春秋·审分》中提及时说道:“万邪并起,权威分移。”而《北史·周纪上论》同样记载:“昔者水运将终,群凶放命,或权威震主,或衅逆滔天。”权威在这里注解为“权力与威势”,后世沿用。于是权力与权威在我们的语义习惯里成为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每提及权威必定伴随权力。我们在解释权威时,习惯上以“权”字具化出的组织体系和服从关系为出发点,把权威作为权力作用效果的外在显化。
(二)概念意义的语义饱和[3]
我们使用逻辑化的语言去表述一个概念性的名词,当该名词位于特定的语义环境和语言体系中时,词义在这种特定环境里会进行适应性的表述,并根据语义传统和主流文化被界定适用范围。于是,对应了固有现象的词汇就可能无法完整的代表它所承载的属性。这类由于词汇的功能化,以文化堆积层的不断叠压覆盖为线索造成的语义扭曲或缺失,在某种程度上会干预我们对于事物本质的认知,甚至陷入一种概念上的“语义饱和”。
我们尝试解释并定义权威的时候,下意识从“权”字入手,以至于将权威视为权力的派生,更有甚者还会将权威和权力不加区分的使用,这都是囿于固有语义习惯而陷入了一种“概念上的语义饱和”怪圈。每当一个名词被赋予概念性的解释,并根据文化序列的不断层叠累加和规律的反复修正而逐渐形成一系列高效、严密的逻辑体系时,这种“制度化”的语义环境越具有时代性,那么后来沿用的概念性名词“语义饱和”的特征也就会愈发明显。我们必须承认,人类的认知具有时代性,知识架构、文化土壤、制度設计、现有的公共信奉和某些死者加诸于生者的固有传统,都会影响我们对于概念的整体性认知。而对于权威的概念性“语义饱和”,归根来说是只将注意力停留在后现代具象化权威的某一点上,从而忽略了对权威本源性及整体性的认知,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局限本身就是一种“权威惯性”。
国内认为权威就是权力的观点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概念饱和的特征。这一观点细分起来大概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认为权力与权威在本质上是一种东西,权威就是权力[4];而另一种是孙钱章、吴江、马抗美认为的权威就是广义的权力。
以上都旨在说明,过度专注于固有的语义习惯及叠加态下的字符意义(对权威的认识本身就存在惯性,而字符的概念意义也具有这种“权威”特征),会影响我们对于“权威”这种现象本质的认知,即使这种局限的思考方式是下意识的。
二、权威的制度化
(一)权威是权力的精神实质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权威的本质在于其合法性,于是他将这种合法性分为了三种类型:魅力型权威,传统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马克思韦伯关于权威的合法性理论,其实在本质上就已经揭示了权威在诞生之初的运作和制度化的演进过程。
魅力型权威[5]又称为克里斯马型权威。首先,我们认为其基本可以涵盖历史时期之前权力组织还未形成但已经在氏族社会内部产生“服从性”现象的这一阶段。“旧石器时代中期就已经开始的埋葬死者的习俗,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普遍出现于世界各地,中国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遗址的下室就是山顶洞人的葬地,这一时期的墓葬中常放有生产工具,装饰品等随葬品,并在死者身上或墓地撒上赤铁矿粉末一类的红色颜料,这些情况说明原始宗教观念到这时已有了进一步发展”[6]。在这一时期,氏族社会出现原始宗教崇拜,祭祀阶层的神圣性开始具备工具特征,而大家长则通过血缘纽带获得道德拥戴或进行更为直接的武力统治。对祭祀阶级超凡神圣性的服从、对部落首领或大家长道德感召力的认可,即是魅力型权威的早期表现形式。
权威在本质上体现的是一种服从关系,但值得强调的是,权威本身所具有的组织性也同时满足了我们内在的精神需求。相比于私欲,服从更像是一种生物与生俱来的动物天性,人类在精神上需要一柄凌驾于世俗的达摩克利斯剑,我们在根源上希望为许多直觉而来的臆想和心理需求寻找一个归宿性的解释,于是我们用权威架构起带有工具性的意识皈依,用以量化复杂的执行程序、消弭思索带来的痛苦,基于这种需求,“以权威为根源,以权力为外延”的服从关系才得以贯穿我们的社会和历史。
(二)权力是权威的路径保证
权威最原始的服从状态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武力的征服、氏族血缘纽带的感召、自然敬畏带来的原始崇拜,高效的分工与组织合作造成的阶级固化。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组织的不断架构使克里斯马型权威得以走向制度化,而魅力型权威的制度化过程就是向法理型权威过渡的过程,即形成法理型权威[7]。直到此时,被统治者信奉的不再是统治者个人,而是由统治者通过人定的程序上升到制度层面的规章和法律。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权威带来的服从关系并不具备实施途径,或许在建立之初由于武力或者道德保障的存在使其具有一定强制性,但这种强制具有时效性。于是就迫切需要一种具有持久影响力的干预手段来消弭一切摧毁权威的不确定因素,制度化带来的强制规章和法律手段使权力满足了这种条件,这时,无论“权力”一词是否已经出现,但以法律和规章为强制手段的权力已经寻求到了保障权威的基本路径。
(三)权威的潜在强制性
目前看来,权力提供的强制手段是保障权威最有效的一种基本途径,但这也并不是唯一途径。起码在一切具化出权力的组织形式和规章制度没有架构起之前,权威就已经具备了更为直接但原始的手段用以维持这种服从关系,如武力的压迫、氏族血缘关系和原始宗教超凡神圣性的约束,这也说明了权威是具有潜在强制性的,只是这种强制性相对于权力带来的更为明确的从属关系来说不那么明显罢了。中国古代社会延续数千年、源于原始社会后期父权家长制的“宗法制度”,就是权威用以维持这种原始服从关系的缩影。宗法制度在本质上就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种群作为划分依据的原始组织团体,它以淡化个人色彩、压制个人意识来树立一个公共信奉,从而上升集体利益。建国之初,新中国法律体系尚未完善的时候,某些地区依旧存在的宗法大于国法现象就足以证明这种“原始权威惯性”深远而潜在的影响。
美国学者丹尼斯·朗在马克斯·韦伯合法性权威的基础上,从服从者的角度探究了权威的来源,进而根据权威的作用形式对其进行了更为细化的分类,除了强调强制性权威他还提出了一种诱导性的权威。丹尼斯·朗认为,权威除了权力保障的强制性服从关系,还带有一种依据社会需求的诱导式特性,即凭借公共价值取向和物质资料进行诱导式的“软强制”。这和薛广洲教授所说的“他律性”权威具有相似的效果,薛广洲先生认为,“它律性权威是指人们对某一权威的服从与其自身的利害相关 ,尽管不是被迫地去服从,但也是不得不服从的一种权威实现形式。”[8]相较于传统观点中的“自律性权威”,虽然他们都代表了这种现象并且表明了权威的实现都通过了权威客体一定程度上的自我约束,但笔者认为薛广洲先生他律性的说法更加符合这种受制于一定的资源与权力的软性强制手段。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雇佣劳动关系时明确指出:“雇佣工人的协作只是资本同时使用他们的结果。他们的个别职能之间的联系和他们作为生产总体所形成的统一, 存在于他们之外,存在于把他们集合和联结在一起的资本中。因此,对他们来说, 他们的劳动的联系在观念上表现为资本家的计划 ,而他们的结合体的统一在实践中表现为资本家的权威,一种使他们的活动服从资本家的目的的他人的意志的力量。”[9]这种权威客体一定程度的自我要求建立在資本家向权威受众提供的生存资料是其必需的基础上,换句话说,资本家的权威是凭借生存资料作为诱导的强制性服从关系。
无论是丹尼斯·朗所说的诱导式权威还是薛广洲先生认为的他律性权威,这种带有渗透性的软性强制都从不同侧面印证了权威的潜在强制性。
服从是一种天性,我们树立的一切权威都旨在量化复杂的执行程序、消弭思索带来的痛苦。所以在那之后漫长的历史时期,以相信统治者章程所规定的制度和指令权利的合法性为前提,传统型权威[10]建立在了传统与约定俗成的习惯神圣不可侵犯的基础之上。分工的固化与约定俗成的传统形成了思维惯性,人们对旧有传统的习惯性依赖,成为了权威得以层构的土壤。而权威统治者的合法性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就可以简单地认为是一种社会惯性,一种基于习惯得以沿袭的共识或是死者加诸于生者的某种生活方式。
到此为止,人类社会的服从关系体系得以架构完善。权威成为一种“文化”或者说“习俗”,并由“服从”这一根源不断发散,具化为各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而这即是权威的萌孽到制度化的完成,再到社会惯性之下成为普遍社会现象的演化过程。
三、权力与权威
如果从政治学的观点来看,权力的强制服从性集中表现在政治权力上。因此我们通常认为权力带来的服从关系是具有强制性的,而基于马克思韦伯的权威合法性理论,权威的服从过程则具有“自觉性”。很长一段时间国内存在权力与权威不加以区分使用的情况,有一种持权威就是广义的权力的观点, 如孙钱章、吴江、马抗美认为 , 权威就是广义的权力[11]。在这里权力被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 狭义的权力是指职务权力, 而广义的权力除了职务权力以外 ,还包括个人权力。权威又被认为是一种“自觉服从的权力”,当下不少学者就认为权威就是对权力的一种自愿的服从和支持。
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指出,“这里所说的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
[12]恩格斯对权威的定义中也体现了权威的“服从性”特征,区别是这种服从是带有强制性的。
不难看出,马克斯韦伯的“权威”侧重于“社会权威”,而恩格斯强调的权威则更倾向于“政治权威”。在政治学中,社会权力和国家权力是一对历史概念,社会权力先于国家权力产生。相似的,社会性权威和政治性权威(王沪宁提出)也应该作为一对分开的概念来讲。而从共性上来讲,无论权力与权威的服从形式是如何的,他们都体现着一种服从关系。
笔者在前文论述过,武力的征服、氏族血缘纽带的感召、自然敬畏带来的原始崇拜,高效的分工与组织合作造成的阶级固化等一系列因素,都决定了权威在本质上是具有潜在强制性的,而权力提供的强制途径则是使这种潜在的强制性具化为了一种实在的“强制力”,于是权威潜在强制性的表现途径迁移到权力实在的强制力之上,这也就造成了“权威貌似不具备强制性,是一种自觉性服从认可”的假象。
权威是权力的精神实质,而权力是权威的路径保障。任何一种权威意识建立的最初都旨在量化复杂的执行程序、消弭思索带来的痛苦,而一切权力的建立都必定具有权威带来的意识温床。我们可以看到,以权威为根源不断发散能够带来权力,但有了权力却不一定能够带来权威,如果有了权力就会带来权威,那么也就不会出现被人民推翻的政权了。
权力与权威在本质上都体现着一种服从关系,而权力的建立就是希冀着寻找一种稳定的途径来保障这种服从关系的长久,用一种具有持久影响力的干预手段来消弭一切摧毁权威的不确定因素。所以归根来说,权力是为权威提供了路径保障,而不是权力派生出了权威。后现代一系列崭新社会权威意识的建立同样逃不开“基于传统和惯性”的特征,这是权力体系构建后权威寻求到路径保障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辩证的看,这又是得以层构的社会权力以及政治权力反过来作用于权威,进而具化为各种普遍社会现象。权力与权威之间的先后关系应该是“权威—权力—权威”,而我们显然是把这种必然和反作用当作了权威之于权力的从属关系,认为就是权力派生出了权威或者权威就是权力。对二者先后性及派生关系的误读,根本上讲是对权力與权威的本源进行的生硬割裂,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
四、结语
以上从话语体系说明了囿于语义传统会影响我们对于权威本质的认知,过度专注于后现代具象化权威的某一点,而忽视从起源和整体的架构认识权威,则会使我们陷入一种概念上的语义饱和。这就要求我们需要从权威的萌孽到制度化的完成,再到社会惯性之下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入手,认清权力与权威的先后性及关系问题。目前看来,关于权威的研究通常以学科作为划分的依据,就一种现象可能带来多重视角,但从事物的本质上来讲就不可避免的会对事物的性质产生割裂。权威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无论政治学还是社会学都对这一概念有着独立的研究方向,大多数区分度不大的情况下,不同的研究视角可以丰富学术体系,但过于明确的界限区分会对重合的部分进行过于冗杂的重复解释,甚至同一问题为了区分学科专门采用不同的说法,这在某种程度上会使问题复杂化,为此就非常需要进行一种跨学科的有机整合。
[参考文献]
[1]《辞海:1999年缩印本(音序)3》,第1735页.
[2][美]利奇:《语义学》(Semantic)李瑞华等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7年8月,第13—23页.
[3]语义饱和(也称完形崩溃)是一种心理现象,这个现象在西方被叫做Jamais vu.针对它的研究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开展.一些学者用“语义饱和”(Semantic satiation)来解释这个现象.他们认为:神经系统有一个固有特点:如果短时间发生多次重复的刺激.就会引起神经活动的抑制.脑内类似面部神经元的汉字神经元产生疲劳.便会影响感官机能,这时熟悉的字,人也会对其形态产生怀疑而觉得不像甚至变得不认识了.这就是语义饱和.
[4]王沪宁.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247页.
[5]魅力型统治建立在某个英雄人物、某位如有神授天赋的人物的个人魅力基础之上,被统治者之所以服从是因为他们确信他们的统治者有着超凡的能力,从而成为其追随者和信徒,而统治者也必须通过不断地证明其超凡能力的存在而维持其合法统治,典型的魅力型统治在先知、圣徒和宗教领袖所建立的组织中可以看到.
[6]张之恒主编;《中国考古通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9页.
[7]法理权威是指法理型统治是建立在以下基础上的,即任何一项法律都是以目的合理性或价值合理性(或两者兼而有之)为目标制定出来的,并努力加以贯彻,包括强迫使之得以实施.
[8]薛广洲;权威类型的哲学论证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1年第 1 期.
[9]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10]在这里,统治者或主人是由传统的世袭制度决定的,统治者具有终身的权力,并将这种权力不断传给自己的后代.这种统治具有很强的个人性质,统治者作为统治者,并不表示他是“上司”,而是人格意义上的“主人”.
[11]孙钱章、吴江、马抗美:新领导力全书[ 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8.第1359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4—227页.
(作者单位:潍坊学院,山东 潍坊 261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