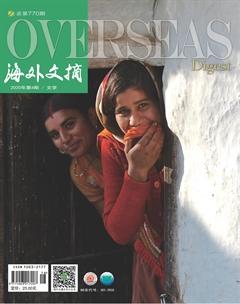面对藏经洞
张映勤
面对莫高窟的藏经洞,我有一种莫名的悲哀。洞不大,只有丈余见方,像是老式窑洞的里外间,里面黑洞洞的,空无一物,那些举世震惊的敦煌遗书早已被挪运一空。可悲的是,藏经洞里最早保存的五万多卷经卷只有很少一部分保存在我们自己的博物馆里,绝大部分被洗劫到国外,诸如英、法、俄、日等十几个国家的图书馆、博物馆都藏有。
我一直就对这个神秘的藏经洞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应该说,作为“世界八大奇观”的敦煌莫高窟,它的闻名于世并非是因为那些精美的佛像和壁画,更主要的是这个20世纪初被发现的藏经洞。历史上的战乱和当政者的好恶,使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文字历史受到了空前的破坏,图书资料残缺不全,面目全非,幸好有这样一处藏经洞得以保存一大批稀世瑰宝,然而却又不幸散落到了国外。
敦煌莫高窟本来是佛教圣地,却在20世纪初无端地被一名破落道士所糟蹋。道士名叫王圆篆,祖籍湖北省麻城县,大约在1851年前后出生在陕西,由于家乡连年受灾,年轻的王圆篆无以为生,只能像逃难一样入伍从军到了甘肃。一百多年前的甘肃,想必是极尽荒凉贫困,历来为内地犯人充军发配之所。王圆篆能从地肥水美的家乡流落到穷山恶水的边陲,显然也是出于生活所迫,身不由己。在军队混了几年,他退伍了,生活仍然没有着落。就生存而言,王圆篆的能力很低,在偏远的甘肃,他没有任何亲戚朋友的帮衬,个头不高,体力有限,又缺乏起码的技能和文化,文不能食,武不能衣,为了糊口,他只能出家当了道士,最初的动机也许只是为了能混上碗粥喝喝。
王圆篆的出家纯粹是为生活所迫。可以肯定地说,他对宗教缺乏最起码的了解,更不是出于信仰的需要。当道士也好,当和尚也好,不过是混碗饭吃罢了。作为一名游化四方的道士,到处化缘乞食,成了他维持生活的一种手段。王圆篆这种对宗教的无知,可以从他以后的行为中得到证实。
1892年前后,贫困潦倒的王圆篆流落到了当时已同样贫困破败的敦煌莫高窟。
敦煌原为古丝绸之路的要塞,位于著名的河西走廊一侧,从东汉一直到明朝,敦煌一带始终作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商贾云集,物流繁茂,各路使者客商穿梭往返,不绝于缕。古时的贸易,海路不通,只有靠陸路进行,敦煌作为重要的陆路口岸,是古代沟通欧亚经济贸易的丝绸之路的重要地段,其作用不亚于如今的沿海口岸。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带来了敦煌莫高窟佛教的兴盛,自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朝代,僧人及工匠在敦煌鸣沙山东麓的崖壁上开凿了一个个洞窟,用于供佛修行,至唐代武则天时有洞窟千余个。元代以后敦煌停止开窟,逐渐冷落荒废。
明代的海路运输逐渐取代了陆路,河西走廊古道中衰,数百年间,气候条件变化,这里繁华的城镇为风沙所患,渐至荒凉败落,尤其是明嘉靖七年(1528年)朝廷封闭嘉峪关,敦煌成为关外边塞游牧之地。从此,河西走廊绿洲的面积逐渐缩小,人口日益减少,莫高窟也被淹没在积年沙漠之中,人们忘却了那里的一座座佛窟。从敦煌莫高窟的衰落中,我们看到了历史的无情。
在敦煌莫高窟销声匿迹数百年之后,直到王圆篆的到来才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机。不过,这种转机从一开始就带有一种悲剧色彩。
1892年,落魄的王圆篆来到同样落寞的莫高窟。从现在的情景我们仍不难看出它当年的荒凉败落。莫高窟东有鸣沙山,由于环境恶化,每日风沙扑面而来,四处戈壁荒滩,了无人烟,而且常年干旱少雨,气候异常炎热,人迹罕至,舟车不通。莫高窟洞穴中的佛教艺术品在特殊的气候地理环境条件下得以较为完整地保存。那些曾经辉煌一时的佛寺对世人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吸引力,荒置多年的洞窟像一片无人管理的烂尾楼,残破毁损,惨不忍睹。大部分洞窟被风沙掩埋,有的倒塌,有的空置,只有为数不多的僧人住在里面勉强度日。当时的敦煌县只有3万多人口,莫高窟附近方圆几百里之内只有25个小村庄,地广人稀,交通不便,香客来得少,哪来的香火钱?王圆篆来到莫高窟时,这里只有上、中、下三座寺院,其中“上寺”和“中寺”的僧人主要是属于藏传佛教的喇嘛,他独身一人寄居在破败不堪的下寺,也算是穷途末路,无可奈何。
王圆篆虽然无知愚昧,但对他所依附的宗教有一种惊人的迷恋和执着。遗憾的是,作为一名最底层的道士,他甚至连佛教和道教的区别都分不清楚,于是,决定寄身佛窟,化缘谋生,为佛教道教的功德做些益事。他雇人将佛窟的积沙清理干净,改为供奉道教神灵的老君堂,找来一些工匠,把洞窟优美的壁画刷白,拆毁佛像文物,换上道教的神像。王道士由于文化水平太低,力单体弱,便请了一位当地姓杨的贫穷书生帮助他抄写经卷。他将现在编号为16号窟的一处洞穴的积沙进行清理,供杨某居住和抄写经卷之用。
历史充满了偶然,16号窟的背后就是后来举世闻名、震惊世界的藏经洞,它的发现充满了偶然。
荒无人烟、破落衰败的洞窟里只有两个穷困潦倒的道士和书生打发时光。有一天,杨某闲来无事,将一根点烟用的芨芨草插进了身后墙壁的裂缝中,一个旷世珍贵的文物宝藏由此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
杨某将草棵插进墙壁上的裂缝,挺长的芨芨草插到里面不见尽头,洞窟是开凿在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深不见底的裂缝让杨某心生好奇。他用手敲了敲墙壁周边,墙上发出的声音竟然像是空的。杨某毕竟是读过书的,想得多一点儿,就把这件事告诉了雇主王圆篆。山崖上开凿的洞窟会有这种声响,两个人为了一探究竟,连夜拆开了这道裂缝,他们惊奇地发现,墙后原来是一扇用泥封住的小门。拆开小门,由此进去,两个人立时惊呆了,只见里面密密麻麻堆满了数不清的历代经卷、纸画、绢画、刺绣等文物。后经测量,藏经洞长宽各2.6米,高3米,如同老式的方形窑洞,如今空无一物的洞内当年保存的遗书经卷等文物多达5万多卷。
这一天是1900年6月22日。
对密室里这些经卷的价值,王圆篆可以说一无所知,应该说,他是一个老实人、本分人,既没有把经卷一把火烧了,也没有当作废品随便卖了,而是按照惯例,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那时候的行政部门简单,既没有宗教局,也没有道教协会之类的机构,管理全县政务的只有县衙门。王圆篆知道这是些古物,但它们的价值究竟如何却并不清楚,于是便带着几卷经卷跑了50里路找到了敦煌县令严择。严大人拿经卷随便看了几眼,并不感兴趣,礼节性地留下两卷便把他打发走了。王圆篆既没得到表扬,也没得到奖励,碰了一鼻子灰,怏怏而去。
时间不长,湖北老乡汪宗翰于1902年调补敦煌县知县。汪知县是位进士,对金石学、书法、诗词也很有研究。王道士把希望寄托在这位有学问的知县身上,企盼着他能解决好藏经洞的保护问题。王道士风尘仆仆再赴县衙,向汪知县报告藏经洞的情况。汪知县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自去莫高窟查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汪宗翰取走其中几件画像、经卷,其他的文物命令王道士暂作封存。汪宗翰自己研究数日后,感觉这些文物古迹的珍贵,便将这几件画像和经卷托人带给了很懂金石学的甘肃学政叶昌炽,希望上司认真研究其价值,以保护和处理藏经洞里的大量文物。叶昌炽毕竟是饱学之士,经仔细研究后,知道这批文物价值的重要,于是便建议甘肃藩台将这批文物运往省府兰州妥善保存。然而,敦煌离兰州路途遥远,叶昌炽估算这些东西光运费就要五六千两银子,官府一时经费无处落实,于是就命令敦煌县令汪宗翰就地“检点经卷画像”,再次封存,并责令王道士妥加保管,不许外流。
1906年,汪宗翰调往兰州,遗书之事不了了之。王圆篆不死心,决定接着往上反映,于是就雇了毛驴,驮着两箱字迹比较漂亮的经卷,送到驻扎在肃州(酒泉)安肃道的道台兼兵备使廷栋大人处。王道士从前就是在这里当兵的,知道廷栋大人爱好书法,所以特意远道来“投其所好”。可是这位道台大人虽然是科举出身,爱好书法,却认为这些经卷的书法还不如自己写得好,因此兴趣不大,赏了王道士一杯茶,留下几卷经卷作为样品,答应把它们转呈远在兰州的甘肃藩台,就让王道士回去了。谢稚柳在《敦煌艺术叙录》中记录他们的调查结果如下:“王道士于是延城中士绅来观,士绅辈不知其可贵,谓此佛经流落于外,诚大造孽,辄嘱仍还置窟内。王道士颇机诈,思借之以贸利,私载经卷一箱至酒泉,献于安肃道道台满人廷栋。廷栋不省,以为此经卷其书法乃出己下,无足重。王道士颇丧沮,弃之而去。”
王圆篆在发现藏经洞的几年里,可以说是守土有责,不遗余力地看护保管,经卷在他手里基本上完好无损,但是屡屡上报,得不到肯定认可,尤其是没有得到起码的重视,上司的无视、冷落,不觉让他心灰意懒,有一种热脸蹭到冷屁股的失落和沮丧。直到7年之后,一位洋人的出现才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
洋人名叫斯坦因,出生在匈牙利一个犹太人家庭,英国籍,著名的探险家、考古学家。1907年,斯坦因第一次来到莫高窟之时,王道士对藏经洞看管得很紧,散失的卷子很少。
斯坦因为了看到日夜盼望的藏经洞,想了很多办法接近王道士,但王道士避而不见,斯坦因束手无策。后来他了解到道士王圆禄对唐代高僧玄奘非常崇拜,便把自己装扮成唐玄奘的信奉者,并欺骗王圆篆,说他是沿着唐玄奘西天取经的路来的。这一招很灵,是宗教信仰把他们的思想沟通了。斯坦因最终只用了200两银子,便换取了24箱写本和5箱其他艺术品。1914年,他再次来到莫高窟,又以500两银子向王圆篆购得部分敦煌文献。两次合计,共掠走藏品2万余件,现存于大英博物馆和印度的一些博物馆。
1908年,精通汉学的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在得知莫高窟发现古代写本后,风尘仆仆地赶到敦煌。他在洞中拣选了三个星期,最终以600两银子为代价,获取了一万多件堪称精华的敦煌文书,这些文书后来大都人藏法国国立图书馆。其后,日本的探险家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俄国考古学家奥尔登堡、美国考古学家华尔纳等人闻风而至,对藏经洞文物进行大量盗运。
对发现藏经洞的道士王圆篆,多数论者指责他罪不容赦,好端端的一个文物宝库,竟毁在他的手里,洞里一多半的文物精品被他盗卖一空。但是,王圆篆身为一个无知愚昧又贫穷的道士,实在又承担不起如此大的罪责。在西人斯坦因、伯希和盗运经卷之前,王圆篆曾经屡次将此事报告给当时的敦煌知县汪宗瀚和安肃道台廷栋,结果碰了钉子。知县大人只挑了一部分画像和写经留作私物玩赏或送人,而知府大人看了经卷,竟觉得还不如自己的字好,轻蔑地说了句:“无足重!”让这些贵重的文物继续尘封洞内。如果说一个偏僻州县的地方官学识浅薄的话,那么号称金石学家的甘肃学台叶昌炽应该长着一双慧眼,他把从敦煌得来的几件献品写进了自己的著作,并且也提议过将这些文物运往兰州保存,但是因为官府拿不起几千两白银的运费,此事同样不了了之。
中国古代历来就是以权术而不是以学识取士的,当官的兴趣只在于贪财享受,为了发财是不惜砸了佛像当废铜卖,拆了祖宗牌位当劈柴烧的,国家的财富如果不搬到自己家里从来就不知道珍惜。一大批稀世瑰宝因为无人识货,只好交由王道士处理,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1907年,在藏经洞被发现7年之后,一个个外国探险家闻风而至,他们辗转来到荒凉偏僻的敦煌,从王圆篆手里连哄带骗,像买废纸一样将宝贵的文物盗运出国。洋人对遗书的重视最终引起了国人的注意,1909年,法国探险家伯希和,将他窃得的遗书在北京六国饭店公开展览,这才将藏经洞的发现公之于众。長期无人问津的经卷外国人一说好,立刻惊动了朝廷。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敢情偏远的敦煌还有如此珍贵的文物。于是一纸电令发到敦煌,对洞里剩余的东西进行封锁,严禁外运,适时运往北京。殊不知,此时洞里的文物已去之大半,而接下来长途运输带来的损失较之洋人的盗窃更为严重,遗书在途中几近处于无人看守,任其丢失的状态,大小官吏和看守层层窃取,运到北京时只剩下八千六百多残卷了。
敦煌遗书在藏经洞里经历了上千年,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而一旦到了世间立刻遭到浩劫,变得散缺不全。这种窃取文物的黑锅岂能让王圆篆一个人来背?那些满朝官吏在干什么?那些学人精英在干什么?王圆篆只不过是一个愚昧无知的道士,对无知者的行为我们不能过于苛责,就像我们对待一个孩子犯下的错误。他的罪过只是在不适当的时候发现,以不适当的手段处理了这些珍贵的遗书,他做过努力而没有得到回应,连那些有识之士都认识不到遗书的价值,对国宝的流失不置一词,一个无知的道士又能何为?
陈寅恪先生曾痛呼:“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反省这段历史,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悲哀,单单责怪王圆篆,拿一个愚昧的道士祭刀,实在是我们的耻辱!
不管怎么说,这些“见者惊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的经卷绝大部分还是保存下来了。散落到国外不知是它的幸与不幸。从国家的角度看的确是损失了,好端端的祖上宝物被人家白白拿走,竟连点儿外汇都没换到。但是从保留人类文化遗产的角度讲,我们又似乎稍稍能得到点儿安慰,不管经卷是存在大不列颠,还是法兰西、俄罗斯的图书馆里,它总算没有毁掉,只是暂时不能物归原主罢了。人们对王圆篆的责难,也许是出于这样一种观念,宝物宁可毁于家奴,不能让于外藩。但是对文物来说,保存的价值无疑永远要胜过毁灭!我们在痛心疾首的同时,是否会为它的留存于世而感到一丝庆幸呢?据说陕西咸阳的秦始皇陵早已勘定,只是政府采取必要的措施,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暂不开掘。我想,这才是保护文化遗产的明智之举!
选自《红豆》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