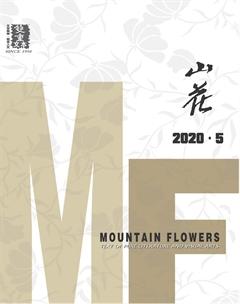盲女古银霞的奇遇
黎紫书来自马来西亚怡保,是华语文学世界的重要作家,在中国大陆也享有一定知名度。上个世纪末她以《把她写进小说里》(1994)获得马来西亚花踪文学奖小说首奖,自此崭露头角,之后创作不辍。《流俗地》是她继《告别的年代》(2010)后第二部长篇小说。十年磨一剑,黎紫书的变与不变,在《流俗地》中是否有所呈现?
《流俗地》的主角古银霞天生双目失明。她的父亲是出租车司机,因为这层关系,银霞得以进入租车公司担任接线生。她声音甜美,记忆力过人,在电话叫车的年代大受欢迎,视障成就了她传奇的一部分。黎紫书透过银霞描绘周遭的人物,他们多半出身中下阶层,为生活拼搏,悲欢离合,各有天命。
银霞和其他人物安身立命的所在——锡都,何尝不是黎紫书所要极力致意的“人物”。锡都显然就是黎紫书的家乡怡保。这座马来西亚北部山城以锡矿驰名,十九世纪中期以来曾吸引成千上万的中国移民来此采矿垦殖,因此形成了丰饶的华人文化。时移事往,怡保虽然不复当年繁华,但依然是马来西亚华裔重镇。
然而怡保又不仅只有华人文化,马来人,印度人和华人相互来往,加上晚近来此打工的印尼人和孟加拉人,形成了一个多元族群社会。是在这样的布局里,黎紫书笔下的盲女银霞遇见不同场合、人物,展开她的一页传奇。也必须是在这样众声喧哗的语境里,她观察、思考华人的处境,以及今昔地位的异同。
《流俗地》人物众多,情节支脉交错,黎紫书以古银霞作为叙事底线,穿插嫁接,既有现代主义参差对照的风格,也有旧小说草蛇灰线的趣味,不是有经验的作者,不足以调动这些资源。银霞担任租车公司接线员是巧妙的安排。在她日夜“呼叫”下,所有大小街道的名称、熟悉不熟悉的地址不断跃动在字里行间,形成奇妙的锡都方位指南。比起《告别的年代》刻意操作后设小说技巧,《流俗地》回归写实主义,显示作者更多的自信。黎紫书娓娓述说一个盲女和一座城市的故事,思索马来西亚社会华人的命运,也流露此前少见的包容与悲悯。
流俗与不俗
《流俗地》的“流俗”顾名思义,意指地方风土、市井人生。这个词也略带贬义,暗示伧俗不文,下里巴人的的品味或环境。黎紫书将锡都比为流俗之地,一方面意在记录此地的浮世百态,一方面聚焦一群难登大雅之堂的小人物。这些人的先辈从唐山下南洋,孑然一身,只能胼手胝足谋生。上焉者得以安居致富,但绝大多数随波逐流,一生一世,唯有穿衣吃饭而已。黎紫书更关心的是女性的命运,这一向是她创作的重心。要为这些人物造像,写出她们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
古银霞天生视障,但她自己和周遭家人亲友似乎不以为意。生活本身如此局促,老老实实过日子都嫌捉襟见肘,谁有余力刻意照顾她怜悯她?但也因此,银霞和组屋周围邻居打成一片。她没有什么学识,但自有敏锐的生活常识;她没有社交生活,却也自然而然的有了相濡以沫的同伴和朋友。一次出游,一场谈话,一碟小吃,一只小动物的出没都足以带来令人回味的喜悦与悲傷。银霞的成长没有大风大浪,唯一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却带来此生最大的惊骇与创伤。即使如此,她还是熬了过来,最后迎向生命奇妙的转折。
黎紫书塑造人物的方法,俨然回到十九世纪欧洲正宗写实主义的路数,经典之作包括像福楼拜(Gustav Flaubert)的《简单的心》(A Simple Heart)。这类写作看似素朴的白描,其实自有一套叙事方法和世界观。所谓“人物”不再享有独特位置,而是人与物——事物与环境——的相互依赖影响关系。作者从小处着手,累积生活中有用无用的人事、感官资料,日久天长,形成绵密的“写实效应”。只要回看《告别的年代》,即可看出黎紫书的“变”。《告别的年代》里的主人翁杜丽安也是来自底层的女性,她出身不佳,力争上游,嫁了黑道大哥后,摇身变为另类社会名流。即使如此,她并不安分,因此有了更多的曲折冒险。《流俗地》里的古银霞没有杜丽安的姿色和本事,她甚至看不见世界。她必须和生命妥协,退至人世的暗处,她必须认命。然而,黎紫书却从这里发现潜德之幽光,最终赋予这个角色救赎意义。
而银霞不是单一的例子。《流俗地》以集锦方式呈现锡都女子众生相。沿门签赌的马票嫂早年遇人不淑,独立营生,竟然遇见黑道大哥,有了第二春。这个角色似乎脱胎于《告别的年代》的杜丽安,只是更接地气。马票嫂没有大志,因婚姻所迫走出自己的道路,但就算苦尽甘来,最后也得向岁月低头。她曾经穿门入户,好不风光,晚年却逐渐失智,一切归零。银霞童年玩伴细辉一家是《流俗地》的另一重点。这家的男性或早逝、或无赖、或庸懦,反而是从母亲何门方氏、媳妇蕙兰、婵娟、小姑莲珠,还有第三代春分、夏至等女性,各自活出命运的际会。母亲的顽固、蕙兰的空虚、婵娟的刻薄、莲珠的风流,无不跃然纸上。
这些人的生活苦多乐少,浮沉有如泡沫,认命到了自苦的地步。但她们不需要同情。就像银霞一样,这些人兀自存在,以自己的方式“作人”与“格物”。当何门方氏佝偻跪倒猝逝,当蕙兰坐看自己臃肿如象的身躯,当婵娟因寡情而自陷忧郁困境,或当莲珠发现机关算尽,还是不能锁住良人时,她们以肉身经历的无明与不堪,演绎生命的启示——或是没有启示。然而生命再庸庸碌碌,也偶有灵光闪烁。这里没有天意使然,甚至无关什么人性光辉,却足以让我们理解现实的无情与有情,人之为人的随俗与不俗,自有一份庄严意义。
黎紫书有意将这样的观点镶嵌在更大的历史脉络里。锡都五方杂处,曾经有过繁华岁月,如今风华褪尽。华人生存的环境充满压抑,却仍然得一五一十地过日子。银霞坚守出租车站,以南腔北调的方言沟通来往过客,名噪一时。新街场旧街场,酒楼食肆,甚至夜半花街柳巷的迎送都需要她的调度串联。黎紫书藉着银霞的声音召唤自己的乡愁。但在私家车日益普遍,手机网络和各种替代性租车行业兴起后,传统租车业江河日下。银霞可能是最后一代接线员。她已不再年轻,将何去何从?
与此同时,马来西亚华人的生态悄悄发生改变。黎紫书以往的作品也曾触及种族政治议题,如《山瘟》《七日拾遗》等,但这类题材不是她的强项。《告别的年代》虽以一九六九年“五一三”华巫暴动为背景,仅仅点到为止。《流俗地》也处理这段历史,但方式不同。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三日,马来西亚反对势力在全国选举中险胜,第一次超越联盟政府,选后双方冲突,华人成为主要受害者。事件不仅牵涉双方种族政治,更与长期经济地位差异有关。“五一三”后,华人地位备受打压,华校教育成为马来官方和华人社团对峙的主要战线,延续至今。
《流俗地》的时间开始于“五一三”之后,暴乱的喧嚣已经化为苦闷的象征。几个主要人物在这样的情境里长大成人。华人社会一向逆来顺受,市井小民尤其难有政治行动。但小说一路发展,最后陡然一变。就在古银霞为自己的未来作出最重要的决定时,马来西亚社会也经历大变动。二〇一八年五月九日,马来西亚举行大选,超过2300位候选人争取727个国会议席,结果带来联邦政府六十一年来的首次政党轮替。尽管政治变天对华人日后的影响有待观察,至少为华人的长期压抑出了口气。
古银霞虽然不关心政治,也为那一晚锡都华人圈的焦虑期待以及狂欢所震惊:
真有那么一瞬,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时辰了,比美丽园中唱《苦酒满杯》的声音……有更大的震撼力。甚至比城中所有回教堂同时播放的唤拜词更加澎湃,以致那一排共享的一长条屋顶轻微晃动一下,像某种巨大的史前爬虫类忽然苏醒过来,耸动一下它发僵的脊椎……电视中的讲述用喊的也不行,他的旁白被背景里汹涌的人声和国歌的旋律淹没了去。
就这样,古银霞生命的转折居然也和一页历史产生了若无似有的关联。流俗之地也有不俗的时刻。但明天过后,锡都或整个马来西亚的华人生活又会面临怎样的光景?惘惘的威胁挥之不去。
视觉的废墟
黎紫书叙事基调一向是阴郁的。从早期的《州府纪略》到一系列具国族寓言色彩的《蛆魇》《山瘟》等,她徘徊在写实和荒谬风格间,百无聊赖的日常生活和奇诡的想象间,愤怒和伤痛间,找寻平衡点。她曾自白:“我本身是一个对人性、世界、社会不信任,对感情持怀疑态度的人。我做记者的时候,接触的都是社会底层的阴暗面,看到很多悲剧,无奈的现实以及人性的黑暗,这些很多成为了小说的素材。我没有办法写出阳光的东西,我整个人生观已经定型。我不是为了黑暗而黑暗,为了暴力而暴力,是因为人生观就是这样。”
《流俗地》也书写黑暗与暴力,与黎紫书此前作品不同的是,这部小说并不汲汲夸张暴力奇观(如马共革命、种族冲突、家庭乱伦等),转而注意日常生活隐而不见的慢性暴力(slow violence)。华人遭受不公待遇,女性在两性关系中屈居劣势,底层社会日积月累的生活压力,无不一点一滴渗透、腐蚀小说人物的生活。而“黑暗”也不再局限社会的暗无天日或人性的恶劣败坏。《流俗地》甚至没有什么巨奸大恶的反派人物。我认为黎紫书有意探触另一种生命的黑暗面:无从捉摸的善恶“俱分进化”,难以把握的人性陷溺,还有理性逻辑界限外的偶然。从这里看来,她创造盲女古银霞就特别耐人寻味。
“视障”不是文学的陌生题材。当代中文小说里,史铁生的《命若琴弦》写一对老少瞎子琴师找寻重见光明的偏方,毕生在路上行走的寓言,毕飞宇的《推拿》以盲人按摩院为背景,写一群推拿师之间的欲望和挫折。这些都是精心之作,但不脱以盲人与明眼人世界的对比,暗示众生无明的障蔽。古银霞的故事当然可以作如是观。她虽然目不能见,但是“眼盲心不盲”;她有绝佳的音感和触觉,她的记忆力甚至超过常人。银霞的存在彷彿为“残而不废”这类老话现身说法。
真是这样么?黎紫书仿佛幽幽问道。银霞从来没有看见过现实世界,她所经历或想象的“视界”又怎能被想当然尔地界定。她的“黑暗”果然如一般所谓的一片漆黑么?换句话说,黑暗与光明的对比只是明眼人太轻易的想象。盲人既未必能轻易安于黑暗,或总是渴望光明;同理,明眼人不论如何眼观八方,也未必能够尽览一切。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摄影,首先批评现代人对视觉表征的懵懂无知。在摄影和电影(以当代的虚拟)技术发达之后,我们同时罹患恐视症(scophobia)和窥视癖(scophilia)。[1]前者因信息资源过剩,让我们害怕观看,甚至视而不见,后者则驱使我们无穷的观看欲望,放大缩小,无所不用其极。另一方面,这不只是一个奇观的社会,也是一个被监视的社会。[2]然而无论动机为何,现代视觉文化有其盲点。德里达(Jaques Derrida)提醒我们,现代性的思想兴起源于对视觉谱系的确认,殊不知这一切建立在“视觉的废墟”上。[3]“欲”穷千里目,我们看能看或想看的,那看不见的都被笼统归类为黑暗。
德里达提议以“视障”作为方法,提醒我们都在视觉的废墟摸索,揣摩真理真相而不可得。明眼人对一般所见事物已然有限,何况视力所不能及的,以及视觉透过技术所带来的千变万化。但盲人不代表任何更清明的洞见或透视;盲人无非启动了“自在暗中,看一切暗”(鲁迅《夜颂》)的视觉辩证。相对黑暗、光明的二元逻辑,黑暗广袤深邃,其中有无限“光谱”有待探勘,何况存在宇宙中的“暗物质”[4]还是知识论的未知数。
黎紫书当然不必理会这些论述。可以肯定的是,她有心从一个盲人的故事里考掘黑暗的伦理向度。马华社会平庸而混乱,很多事眼不见为净;更多的时候,盲女银霞必须独自咀嚼辛酸,包括知识的障碍和情爱的挫折。银霞成长期间有两个同龄男性邻居玩伴,细辉和拉祖。细辉父亲早逝,拉祖则是个印度裔理发师的儿子。拉祖聪明而有语言天分,引领银霞进入另一个文化环境。三个同伴终将长大,银霞注定独自迎向未知的坎坷。这就引向小说的核心——或黑洞。
银霞担任出租车公司接线员前,曾进入盲人学校學习谋生技能,尤其点字技术。银霞对学校这新环境充满期待,也遇见一位赏识她的马来裔点字老师。老师循循教导,学生努力学习,殊不知情愫已经在两人间萌芽。但老师已婚,且妻子待产。银霞以点字信笺表达她的感受,欲言又止;老师也发乎情,止乎礼。然后,发生了突如其来的暴力和伤害。银霞匆匆退学。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银霞是当事人,但她无从看见真相。甚至事件本身日后也被极少数知情者埋藏、淡忘了。多年之后,银霞遇见了另一位老师,在另一个黑暗的空间里,银霞终于说出她的遭遇……
黎紫书处理银霞盲校求学的段落充满抒情氛围,是《流俗地》最动人的部分。在叙事结构上,所谓真相的呈现其实发生在小说尾声。换句话说,时过境迁,我们所得仅是后见之明。这类伏笔安排固然是小说常见,然而就黎紫书的创作观以及上述有关视觉的讨论而言,却别有意义。《流俗地》代表黎紫书回归写实主义的尝试,而写实主义的传统信条无他,就是以透视、全知的姿态观看、铭刻人生百态。不论采取什么视角,叙事者或作者理论上掌握讯息,调动文字,呈现声情并茂的世界。《流俗地》对锡都人事栩栩如生的描写,的确证明作者的写实能量。
张、黄两人近作都触碰马华历史的非常时期,以书写作为干预政治、伦理的策略。黎紫书另辟蹊径,将焦点导向日常生活。张贵兴和黄锦树书写(或质问)马华历史的大叙事,黎紫书则不在文字表面经营历史或国族寓言或反寓言。她将题材下放到“流俗”,以及个人化的潜意识闳域。生命中有太多的爆发点,无论我们称之为巧合,称之为意外,都拒绝起承转合的叙事编织,成为意义以外的、无从归属的裂痕——乃至伤痕。黎紫书不畏惧临近创伤深渊,甚至一再尝试探触深渊底部的风险。她这样的尝试并不孤单。香港的黄碧云,台湾的陈雪,还有大陆的残雪,都以不同的方式写出她们的温柔与暴烈。
黎紫书更是以一个女性马华作者的立场来处理她的故事。马华小说多年来以男作家挂帅,从潘雨桐、李永平、张贵兴、黄锦树、梁放、小黑、李天葆到年轻一辈的陈志鸿都是好手。女性作者中商晚筠早逝,李忆君尚缺后劲,黎紫书因此独树一帜。但黎不是普通定义的女性主义者。如《流俗地》所示,虽然她对父系权威的挞伐,对两性不平等关系的讽刺,对女性成长经验的同情用力极深,但她对男性世界同样充满好奇,甚至同情。毕竟在那个世界里,她的父兄辈所经历的虚荣与羞辱,奋斗与溃败早已成为华族共通的创伤记忆。
而《流俗地》不同于黎紫书以往作品之处在于,铭刻族群或个人创伤之余,她愿意想象救赎的可能。与以往相比,她变得柔和了,也因此与张贵兴、黄锦树的路线有了区隔。张贵兴善于出奇制胜,黄锦树“怨毒著书”,黎紫书则以新作探触悲悯的可能。这三种方向投射了三种马华人与地的论述,有待我们继续观察。《流俗地》中时光流逝,古银霞不再年轻,她偶遇当年的顾老师。上了年纪的老师体面依然,但竟也有段情何以堪的往事。老师对银霞的关爱有如父兄,让她获得前所未有的温暖。写作多年,黎紫书终于发现,世界如此黑暗,鬼影幢幢,但依然可以有爱,有光——老师的名字就叫顾有光。
黎紫书让她的银霞不遇见野猪,而遇见光。这是当代马华小说浪漫的一刻,可也是“脱离现实的”一刻?识者或谓之一厢情愿,黎紫书可能要说知其不可为而为,原就是小说家的天赋。而世界不止有光,更有神。
黎紫书将这一神性留给了来自印度的信仰。与其说她淡化了马华文化的中国性,不如说是对多元现实的认同。童年银霞曾从印度玩伴拉祖——一个“光明的人”——那里习得智慧之神迦尼萨的典故。迦尼萨象头人身,有四条手臂,却断了一根右牙,象征为人类作的牺牲。拉祖的母亲曾说银霞是迦尼萨所眷顾的孩子。
拉祖成年后成为申张正义的律师,前程似锦。却在最偶然的情况下遇劫丧生。银霞念念不忘拉祖,也不忘迦尼萨。她从这个印度朋友处明白了缺憾始自天地,众生与众神皆不能免。生命的值得与不值得,端在一念之间。她从而在视觉的废墟上,建立自己的小小神龛,等待光的一闪而过。
以此,黎紫书为当代马华文学注入几分少见的温情。她让我们开了眼界,也为自己多年与黑暗周旋的创作之路,写下一则柳暗花明的寓言。
注释:
[1]Walter Benjamin, On Photography , trans. Esther Leslie (New York:Reaktion Books, 2015)
[2]Michel Foucault 在Discipline and Punish的看法。
[3]acques Derrida, Memoirs of the Blind: The Self-Portrait and Other Ruins, trans. Pascale-Anne Nrault and Michael Naa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51–52.
[4James Peebles, “Dark Matter” PNAS (Proceedings of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October 6, 2015 112 (40) 12246-12248; first published May 2, 2014 https://doi.org/10.1073/pnas.1308786111
作者簡介:
王德威,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比较文学博士。曾任教于台湾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现任哈佛大学东亚系与比较文学系Edward C. Henderson讲座教授。著有《想象中国的方法》《当代小说二十家》《茅盾,老舍,沈从文:写实主义与现代中国小说》《抒情传统与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等多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