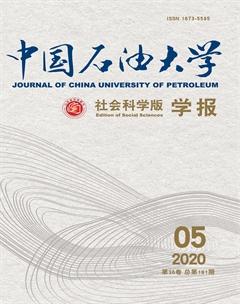认罪认罚案件中如何考量公共利益
杨航
摘要:当前认罪认罚案件中对公共利益的考量,主要集中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后在社会利益层面产生的影响,而并未关注在确定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前对公共利益的衡量。2017年美国地方法院承办的“美国诉沃克案”中,法官基于对公共利益的评估而拒绝辩诉交易做法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一时引发热议。此案将公共利益作为决定是否适用辩诉交易的判断标准,并提出对公共利益评估的四步程序,对我国将公共利益引入认罪认罚案件具有借鉴意义。在办理认罪认罚案件中,法官可以通过社会背景、审判利益、民意宣泄、适用动机四个步骤对公共利益进行考量评估,由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公正适用作出界定。
关键词:公共利益;辩诉交易;认罪认罚
中图分类号:D9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20)05-0083-08
一、引言
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美国辩诉交易在制度设计理念上具有共通性,应对“诉讼爆炸”、缓解案件压力以提高诉讼效率是促使二者产生的共同原因并成为其制度旨归。我国在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过程中可以借鉴辩诉交易的合理成分。
通过辩诉交易处理案件,如何保障公共利益?相关讨论在论述辩诉交易正当性时不绝于耳① [1-2],直至1975年《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明确把公共利益吸收到法典之中②,并作为法官接受辩诉协议的重要考量标准,这种讨论才有所收敛。之后,公共利益成为法官判断辩诉协议正当性的重要标准,相关判例也不断出现。但其中的缺陷是:公共利益的内涵是模糊的,缺乏对其判断的具体步骤与方法。这限制了公共利益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广度与深度。2017年“美国诉沃克案”(United States v. Walker)中,Goodwin法官率先提出了判断的步骤与方法并引起热议。
公共利益的具体适用价值在于,它不仅是辩诉协议正当性的重要判断标准,还可以有效地圈定辩诉交易适用范围,不至于使辩诉交易借助实用主义的力量吞没艰辛建立的正当诉讼程序。这对我国极具借鉴意义。
201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明确了认罪认罚从宽原则并付诸于具体的制度,与美国的辩诉交易在制度设计理念上具有共通性。同样,司法模式也相似,皆为检察官主导进行,通过控辩双方签署协议,形成初步定罪量刑方案,由法官进行审查来最终结案的模式。面临的问题也具有共通性,到底哪些案件不能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目前立法只是从主体、案件影响、当事者意愿等方面要求某些案件不得适用速裁程序③。而且,其中有些判断要素是模糊的,比如“案件有重大社会影响的”等。至于普通程序中,则无任何限制性要求。这带来实践中的困惑与模糊。
本文通过分析“美国诉沃克案”中有关公共利益的讨论,明确公共利益的内涵,同时整理各种不同的观点,评析法官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而拒绝辩诉交易的做法,由此引发对我国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有关公共利益问题的思考:到底哪些案件不能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我国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已经较多地涉及对公共利益的考量,刑事诉讼过程中也应当将公共利益准确定位,并使之成为认罪认罚案件适用的正当性与适用范围的判断标准。
二、“美国诉沃克案”的基本案情
从2016年4月开始,大都会禁毒网络小组(Metropolitan Drug Enforcement Network Team)利用秘密线人“进行7次控制下交易”,从Charles York Walker手中购买海洛因和芬太尼。[3]2073大都会禁毒网络小组在同年9月逮捕了Walker,他因违反《美国法典》第21编第841(a)(1)条④而受到3项分销海洛因和两项分销芬太尼的指控,以及违反第18编第922(g)(1)条⑤而受到1项持有枪支的重罪指控。Walker针对1项海洛因分销指控的罪名进行了认罪答辩,以换取检察官撤销大陪审团的指控。2017年1月26日,Walker向美国西弗吉尼亚州南部地区的地方法院作出了认罪答辩,联邦地区法官Joseph R. Goodwin接受了被告的认罪,但推迟了对辩诉交易协议的接受,要求等到对审前调查报告审查后再做决定。
Goodwin法官在审阅了调查报告后,于2017年6月26日驳回了答辩协议。法官在解释拒绝的理由时,考虑了被告人进一步的事实情况。
首先,Walker非常熟悉刑事司法系统。13岁时,Walker闖入一间公寓偷盗,尽管被指控犯有严重盗窃罪,但最终以入室盗窃罪判处12个月的缓刑。从14岁到17岁,Walker被判犯6项与盗窃有关的罪行。成年之后,Walker因另外的犯罪被判18项徒刑,定罪包括:持有管制物质、携带未经许可的隐藏武器、肆意危害、持有意图分销的可卡因、持有快克可卡因、持有枪支的重罪犯等,还有8项未决指控。此外,Walker13岁以来的47项其他指控或被驳回,或被撤销,或处置不明。尽管有很长的犯罪历史,但法院和检察官一再给予他宽大处理。其成年之后将近8年的时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
其次,Walker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与非法药物有关。他在12岁时开始使用大麻,13岁时使用可卡因,20岁时使用酒精,26岁时使用PCP⑥、苏布特克斯、罗西酮和沙奈克斯等药片,30岁时使用海洛因。他承认,在被捕期间,也持续使用大麻、可卡因、海洛因等。
另外,除了Walker丰富的犯罪历史,本案还有一些具体事实。从2016年4月12日开始,大都会禁毒网络小组合作的秘密线人在几个月的时间内与Walker进行了7次控制下交易,购买海洛因、芬太尼或这两种药物的混合物。在一次控制下交易时,Walker告诉秘密线人,他的一些其他购买者最近服用过量,并警告线人小心使用,由此Walker被认为“似乎在从事一个持续的毒品交易业务”[3]2074。基于控制下交易,大都会禁毒小组获得了Walker的逮捕令和搜查令。2016年7月14日,大都会禁毒小组执行了授权命令。
三、相关判例及法律背景
美国刑事司法中有关公共利益的讨论大多体现在判例之中,但是具体到是否将公共利益作为决定适用辩诉交易与否的问题上,在“Walker案”之前并没有相类似的案例。在《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中,针对辩诉交易中的公共利益问题已经作出了相关规定。
(一) 刑事司法中的公共利益
United States v. Hamm案⑦、United States v. Salinas案⑧以及United States v. Smith案⑨中,主要是围绕《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48条的有关规定展开讨论,法官对检察官撤回起诉的动议进行审查,判断其是否违反了公共利益。
United States v. Hamm案中,根据检察官撤回起诉的动议和被告撤回其有罪答辩的动议提起诉讼。美国德克萨斯州东部地区地方法院首席法官驳回了检察官撤回上诉的动议,并拒绝被告撤回其有罪的上诉。上诉法院的巡回法官在重新审理案件时认为,检察官提出撤诉的动议并非出于明显违背公共利益的考虑,因为检察官考虑到被告过去的合作,并为了确保他们继续合作,为其他可能决定与政府合作的潜在被告树立积极的榜样,认为撤回起诉最符合公众利益,即使在检察官提出驳回起诉时,被告已被判有罪,因此拒绝检察官撤回起诉是错误的,撤销对被告的定罪,发回地区法院重审。
United States v. Salinas案中,被告Salinas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南部地区地方法院被判串谋罪和实质性占有与意图交付海洛因罪,提出上诉。上诉法院巡回法官认为,检察官陈述中撤销原起诉的原因是政府对陪审团的不满,即陪审团中有一些人认识被告,提出撤诉的动议是不诚实的。因撤诉的动议并非真诚作出而违反公众利益,则该项动议即被推翻。
United States v. Smith案中,被告承认共谋占有并意图分销超过5公斤可卡因,在4名共同被告被无罪释放后,政府撤销了起诉。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中部地区地方法院法官认为撤回起诉不符合公共利益,驳回了撤回起诉的动议。上诉法院高级巡回法官认为,审判法院滥用自由裁量权拒绝其驳回的动议,因此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以上案件关于公共利益的讨论集中于法官对检察官撤回起诉动议的审查,将检察官视为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将法官视为对维护公共利益事项的审查者。虽然上述案件中也不乏有辩诉交易的出现,然而实质上并未提及公共利益在辩诉交易过程中的影响,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意识到了公共利益因素在刑事司法领域的重要影响。
(二) 辩诉交易中的公共利益
辩诉交易在刑事司法领域逐渐合法化的过程中,其本身对公共利益的影响也成为当时讨论的热点。从司法经济角度看,辩诉交易符合重要的公共利益,因为辩诉协议倾向于确保公众对起诉犯罪的兴趣得到满足,并确认检察官的指控实际上没有检察资源的支出,节省司法资源;从实体正义方面看,辩诉交易的存在本身就是违背公共利益的,为了达成交易,案件的真相被掩盖,有罪与无罪的界限变得模糊,只有经过陪审团审判的案件才更能符合公共利益的要求。但随着辩诉交易的广泛运用,公共利益因素以一种新的方式再次进入到了我们的视野中——作为辩诉交易适用与否的评价标准。
除了本文探讨的United States v. Walker案之外, United States v. Wilmore案⑩的主审法官也是Goodwin。在该案中,被告Wilmore被指控多项与海洛因相关的罪名,但被告只承认1项海洛因分销罪名的认罪协议。法官认为,被告涉嫌利用该地区猖獗的毒瘾来赚取利润,涉嫌出售海洛因和芬太尼的混合物,辩诉协议掩盖了争议中的犯罪行为,这不符合公众利益,因而拒绝该协议。同样地,法官基于对公共利益的保护而拒绝了检察官与被告的辩诉交易。
通过对大量外文文献分析发现,辩诉交易中对公共利益的考量观点不一。有些学者认为,检察官是代表公共利益对犯罪行为提出指控的,其在指控交易中行使自由裁量权应当符合公共利益、忠诚于公共利益。[4]加拿大的传统观点认为:公共利益是普遍存在的,如果公众利益的重要性超过了辩诉交易,那么围绕辩诉讨论的特权将被取缔[5];其中,检察官必须始终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其对公共利益的评估不是一项选择而是一种责任[6]。理论上,检察官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但是在辩诉交易过程中,有关的协商是发生在检察官与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之间的,透明度低,公众缺乏关于检察官表现的公共信息,所以无法对检察官是否考量公共利益进行监督。[7]《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11条提出,法官要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行使监督辩诉协议的职责。一些美国学者认为,在辩诉交易的背景下,法官的角色就是要保护公共利益,法官通过审查辩诉协议的方式来考虑有关公共利益的问题,从而决定是否接受辩诉交易。[8]但同时有人提出,法官是极其不愿用其对公共利益的观点来替代检察官的观点的,因为法官要保证被撤销的交易必须是恶意的或者是明显违背公共利益的。[9]
在大量文献中,关于辩诉交易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并不清晰。理论层面,为了达成辩诉交易,一些案件的真相会被用以换取轻刑,使得罪与非罪的界限难以区分,在程序中寻求真相的价值便不复存在,从这个角度讲,交易本身也损害了公众利益;[10]立法层面,法律要求辩诉交易的内容不得损害公共利益,法官要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行使监督辩诉协议的职责,并且拥有自由裁量权决定接受或者拒绝辩诉交易;实践层面,法官基于对诉讼效率等方面的考虑很少会拒绝辩诉交易,个案通过交易实现的狭隘的利益并不能够解决公众广泛关注的问题。
(三) 相关法律规定
在撤回起诉方面,《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48条规定,根据驳回起诉的规则,初审法院在考虑政府的撤訴动议时几乎没有自由裁量权,必须在没有发现恶意或损害公共利益的情况下批准动议;撤诉中公益因素的初裁权属于检察官,无论是初审法院还是上诉法院都不能用其判决代替检察官的判断,也不能对检察官的评价进行二次猜测;法官不得重新评估检察官对公共利益的评价,以决定是否在审判开始后提出撤销公诉的动议;只要检察官不是出于明显违背公共利益的考虑,就必须许可动议;法院对撤回起诉给予许可需要考虑两个因素:法院首先审查检察官寻求撤回的动机,然后对检察官提出的撤回理由是否符合公共利益作出客观判断。
如上,《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对检察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对公共因素的考量作出了很多规定,但具体到辩诉交易中的公共利益问题仅有第11条作出了规定:区域法官在选择接受或拒绝认罪协议时享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并且没有义务接受双方达成的任何建议或交易;法官要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行使监督辩诉协议的职责。这说明法律将在辩诉交易中对公共利益的审查交给了法官,法官需要将公共利益因素考虑在内,这也是Goodwin法官在本案中的观点。
四、联邦法官在“美国诉沃克案”案中的观点及不同意见
联邦地区Goodwin法官在本案的判决中提出了对公共利益进行评估的四步,从四个方面的考量来判断辩诉交易是否违背了公共利益。但同时,对于Goodwin法官的观点也有人持不同的意见。
(一) Goodwin法官的分析思路
首先Goodwin法官讨论了Walker“丰富”的犯罪经历,记录了被告人非法使用药物的历史。同时,利用统计数据,分析得出海洛因和鸦片类药物的流行是当前重大公共健康问题之一。西弗吉尼亚州的致命药物过量率是全国最高的,而且该州在药物接触下出生婴儿的发病率居全国领先地位,依赖鸦片类药物的婴儿出生率最高。Goodwin法官指出,“西弗吉尼亚州这场危机的严重性使我相信,我应该仔细审查那些交易撤销多数大陪审团起诉的认罪协议。”
其次,联邦法官Goodwin认为,虽然《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11条赋予被告和检察官签订认罪协议的权利,并对法院在其裁判中应该或可能考虑的内容未做明确规定,但法官也有义务接受或拒绝这些协议。所以Goodwin法官以被告人所涉的辩诉交易违背了公众利益为由,拒绝了该案的辩诉交易。他从制度层面解释说,《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11条赋予地区法官对辩诉交易的广泛的、非指导性的自由裁量权,并且美国宪法明确指出,美国是一个参与式民主国家,是一个民有、民治的政府,政府部门依赖并要求公民积极参与权力的行使。而辩诉交易消除了陪审团的审判,混淆了法官和检察官的角色,建立了刑事司法的行政制度。这种通过辩诉交易解决刑事指控的方式取代了经过陪审团审判的解决方案,但陪审团的审判能够以一种辩诉交易的有罪辩诉无法做到的方式来揭示毒品分配和滥用的黑暗细节。在审判过程中听取证据的陪审团成员,获得了有关海洛因和鸦片类药物危机的信息。陪审团成员在履行公民义务的过程中接受教育,很可能将他们在法庭上的经历传达给家人和朋友,并且陪审团的审判向社会传达了什么样的行为是非法的。这种公开定罪和监禁的羞耻感特别能够防止被判刑的罪犯再次犯罪,从而使法律得到维护和执行。经过陪审团的公开审判和民众的参与,不仅能够查清案件事实,而且能够保证案件处理的透明度和最大限度地考虑公共利益,而不是依赖辩诉交易获得案件解决的权宜之计。
此外,Goodwin法官根据美国有关部门的年度统计报告指出,尽管刑事审判有所减少,但自1970年以来,联邦检察官的人数稳步增加。司法机关的刑事审判工作量逐渐减少,地方法院法官也不会因为审判而负担过重。辩诉交易中最常见的解决案件繁多的正当理由不再具有实质性的影响力,公众在监督和参与过程中普遍利益的平衡需要在每种情况下都仔细考虑辩诉交易,法官有更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来判断认罪答辩是否符合当前的社会公共利益,若辩诉交易违背公共利益则是不公平的。因此,法院应在认定认罪协议不符合公共利益时驳回答辩协议。
基于对以上分析的总结,Goodwin法官提出了评估公共利益的四步程序。第一步,考虑与犯罪行为有关的特定地区的社会背景,本案中特定地区的社会背景是一个深受海洛因和鸦片类药物折磨成瘾的地区;第二步,权衡公众参与对指控犯罪审判的利益,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公众对特定类型犯罪的审判产生兴趣,从而通过公开的审判以达到对普通公众的教育和威慑作用;第三步,考虑在没有公开陪审团审判的情况下是否会发生“社区宣泄”,刑事案件中的陪审团审判允许和平表达对任意政府或恶性犯罪行为的不满;第四步,应审查辩诉协议背后的动机,并根据审前调查报告,确定表面动机是为了促进司法公正,还是为了方便避免审判。本案中该协议交易了一项大陪审团的起诉,指控三项海洛因分配罪名、两项芬太尼分配罪名及一项持有枪支分销海洛因的重罪,其主要动机似乎是将辩诉交易视为权宜之计。基于以上四点,Goodwin法官认为辩诉交易不符合公共利益。
综上,Goodwin法官基于对犯罪人的犯罪历史、社会现状、制度基础等因素的综合考虑,认为本案中的辩诉交易违背公共利益,因此拒绝了被告人的认罪协议。
(二) 对Goodwin法官意见的评析
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两个方面:一是应否因考虑公共利益而拒绝辩诉交易
从而牺牲被告人利益,二是若需考虑公共利益应该如何进行评估。《哈佛法律评论》的一篇文章对Goodwin法官以违背公众利益为由,拒绝本案辩诉交易的做法进行了批判,其中所指出的问题归纳为两个方面。[3]
第一,Goodwin法官拒绝辩诉交易的决定有损被告人的利益。忽视被告人通过辩诉交易谈判获得较低判决的利益,导致对像Walker这样的被告人的选择任意拒绝,这对被告人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并且几乎没有任何公共利益来证明这种权衡是正当的。事实上,此类交易被拒绝的通常情况,是鉴于特定被告犯下的特定罪行,法官担心这种特定的交易过于宽松。而在本案当中,被告人Walker发现,他选择达成有利的认罪协议被拒绝了,不是因为他有特殊的背景或犯罪的特殊方面,而是他碰巧遇到一位决定以这种方式来解决鸦片类药物危机的法官。这虽然在刑事司法系统中存在一定程度的任意性,个别法官被赋予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但在决定是否拒绝被告人的交易时,这并不能成为忽视被告利益的借口。
第二,通过一次审判和单个法官的力量试图解决一个系统性问题是难以实现的。Goodwin法官忽略了一点,他作为一名法官,只对他监督的认罪交易有权力,在处理他提出的公共利益问题上处境不利。Goodwin法官所关心的不是某一特定交易的具体内容或其寬大处理的结果,而是几乎所有案件都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解决的总体效果。后者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单一法官的行为无法令人信服。Goodwin法官侧重于关注审判对公众的价值,认为公开的审判比秘密交易更能揭示案件的细节,他将审判作为一个平台,向民众通报鸦片类药物危机的实际运作状况。如果通过公开审判来处理许多或所有这类罪行,那么由于陪审团参与和媒体的曝光,公众作为一个整体可以受到教育并体验到对犯罪行为不满的宣泄。但法官个体不能单独达到这一效果,它更需要全州(或至少全社区)的政策来反对在鸦片类相关案件中的辩诉交易。
对于一个充满民主法治的社会来说,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二者同等重要,但若二者发生冲突时,需要依照具体情况进行判定。在本案中,面对当前的社会危机,法官本着对公共利益负责的态度而选择拒绝辩诉交易,同时,被告人渴望通过辩诉交易获得较轻量刑的利益受到损害。然而法官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通过牺牲个案中特定被告人的利益是难以真正缓解整个社会所面临的危机的。
在辩诉交易盛行的社会背景下,Goodwin法官提出以公共利益作为法官接受或者拒绝辩诉协议的衡量因素,这一点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但如前所述,Goodwin法官对于公共利益评估的标准并没有妥善地解决他所提出的问题。在特定危机时期,公众对陪审团审判的兴趣当然值得考虑,但教育、民主参与治理和社区宣泄的目标最好是通过重大和统一的政策变化来解决。只要辩诉交易是法官在规范的制度下运作,他们就必须仔细而全面地考虑在行使拒绝辩诉交易的权力时,所考虑的是谁的利益。虽然公共利益可能是衡量的一个有用因素,但法官应在裁判中关注被告人的利益,并现实地看待通过拒绝个别交易能取得多大的成就。
五、中国法语境下的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一词频繁出现在政治、法律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为公共利益的存在使得一个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更具备正当性。上文对辩诉交易中关于公共利益的讨论,引发了对我国法律有关公共利益问题的思考。
(一) 公共利益的内涵
公共利益在学理上被解释为一定区域或一定社会条件下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此种界定较为模糊,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好把握。通常司法机关处理案件时,将多种影响因素统称为“公共利益”。我国法律中还将公共利益表述为“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群体利益”等,虽表达各异,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或者说公共利益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以及群体利益的上位概念。
与公共利益相对的概念是个人利益。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往往能更多地考虑到公共利益因素,而司法实践中的裁判者更关注的是特定案件中的个人利益。这其中的原因也很简单:对于立法者来说,面对的对象是不特定的,立法初衷也是为了从宏观层面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裁判者不同,他们面对的是特定案件中一个个鲜活的主体,需要与当事人直接接触,因此相对于立法者而言,裁判者从微观上更加注重维护个案的利益。然而,强调明确公共利益不是为了牺牲个人利益,而是为了在司法程序中达到保障人权与维护公共利益的统一。
结合前文论述,我国法律中公共利益包括司法利益、裁判的社会效果等内容,因此对公共利益内涵的思考应当包括以下要素。
第一,特定行为发生的社会状况。社会背景决定了违法犯罪行为对当时当地社会的危害性,以及对公共利益的损害程度。如,Walker案发生在毒品滥用的社会背景下,因此毒品案件对公共健康利益的损害更加严重。再如,在我国食品安全受到威胁的社会背景下,制造有毒有害食品类犯罪对公共利益的损害也更严重,所以对此类案件中被告人的处理应当从严把握。
第二,公序良俗与道德规范。民事法律中考虑公共利益要求尊重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公序良俗是不特定多数人所共同追求的,因此也是属于公共利益判断应当考虑的因素。在处理刑事案件时,首先必须要严格依照法律进行诉訟,同时也可以在法律的框架内考虑道德规范的约束,符合道德规范的处理方式也更能切合公共利益。
第三,社会舆情与公众关切。在诉讼中考虑民众对案件的关注程度,并不是说案件的处理要被社会舆论所“绑架”,而是通过分析社会公众对司法案件发表的意见,来判断案件所涉及的公共利益,以便在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对公共利益进行考量。同时也能通过此种方式教育、引导公民遵守法律,参与法治进程,在司法案件中感受公正的力量。
第四,权衡立法的价值追求。在对前三点进行思考过后,应坚守法律框架的底线。对公共利益评判的前提就是在法律基础之上进行的,而在这一过程中为了防止公共利益决定法律裁判的状况出现,必须要再次强调立法的价值追求。
(二) 刑事诉讼中的公共利益
刑事诉讼法是调整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的公法。在刑事诉讼过程当中,人民检察院代表的是国家,所维护的是国家利益;诉讼当事人是代表自己或其亲属进行诉讼,所维护的是个人利益。虽说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个人利益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实际上公共利益与国家和个人利益在某些方面也会发生冲突。
虽然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较多地涉及到对公共利益的考量,但《刑事诉讼法》中并未明确规定何为“公共利益”。刑事诉讼中的公共利益散见于其他法律之中,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第15条规定,“涉及群体利益、公共利益的”“人民群众广泛关注或者其他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应当由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2019年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条规定,有关陪审员的参审情况要“向社会公告”等。
然而刑事诉讼过程中所涉及的任一司法机关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公共利益。公安机关要及时向社会公开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案件的有关信息;检察院在对犯罪行为进行审查起诉时,应当将公共利益考虑在内,以作出正确的决定;法院在作出裁决时同样需要考虑特定案件的处理结果对社会不特定多数人利益的影响等。如赵宇案中,检察机关“为弘扬社会正气,鼓励见义勇为,综合全案事实,对赵某作出不起诉处理”B11;于欢案中,法院基于对社会公共秩序的维护,考虑到辱母情节的存在,给予被告人从轻处罚的判决B12;再如长春长生公司疫苗案轰动全国,引起社会公众的强烈关切。所以,司法机关在裁判案件中必然要考虑公共利益因素。
由此可见,在我国的刑事诉讼过程中,对于法益和公共利益的考量是必须的,所以在认罪认罚案件中也要将公共利益考虑在内。
(三)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公共利益
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有关公共利益的考量很少有讨论。根据有无被害人,将认罪认罚案件分为无被害人的犯罪案件与有被害人的犯罪案件。无被害人的犯罪案件包括贿赂犯罪案件、毒品犯罪案件等;有被害人的案件包括金融诈骗类犯罪、套路贷案件、涉黑案件等。对于上述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尤其是涉众类经济金融案件,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国家或被害人达成谅解,及时挽救损失,修复社会矛盾,同时达到教化犯罪人的目的。
2018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法官在作出判决时,一般应当采纳检察院提出的对被告人从宽处理的量刑建议,在例外情况中未提及“公共利益”,那么如果被告人的认罪认罚有损公共利益,检察院与法院应当如何衡量?此种情况下便需要在公共利益、诉讼效益以及被告人利益之间进行权衡。即使被告人已经承认自己所犯的罪行,并与人民检察院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人民法院在审查时也应当考虑案件的特殊情况对公共利益的影响,权衡过后再对案件作出公正处理。
六、“ 美国诉沃克案”对我国认罪认罚案件中公共利益考量的借鉴
Walker案判决不仅在美国引发热议,也对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有关公共利益问题的思考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公共利益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现状
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对公共利益的考量基本集中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后对公共利益有利的方面,比如,对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制度能够较大程度地恢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而未关注到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前公共利益的影响程度。如前所述,法律中并未明确对公共利益的衡量,司法实践中,也并没有发现法官基于对公共利益的考虑而拒绝适用认罪认罚制度案件的发生。法官在个案中可能更多地顾及被告人或被害人的利益。
公共利益在实践当中似乎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因素,然而这却是在我国进行法治建设过程中必须要考虑的关键。因此,刑事诉讼中不可避免地要将公共利益准确定位,以便在认罪认罚案件的诉讼程序中得以合理运用。
(二)公共利益引入认罪认罚案件中的必要性
第一,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引入公共利益,有助于明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范围,保障制度的合理运行。我国2018年的《刑事诉讼法》明确了认罪认罚从宽原则并付诸具体的制度。目前立法只是规定了不适用速裁程序和简易程序的案件范围,并没有对认罪认罚程序的适用范围进行明确。因此,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引入公共利益的判断要素,有助于明晰认罪认罚程序的适用范围、规范程序有效合理运行。
第二,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引入公共利益,有助于保证审判的独立性。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建立,带来检法关系的重塑,在此过程中法院保证审判的独立性就必然要考虑公共利益,而同时也必须要维护控方和辩方的预期利益。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案件中,审查起诉阶段由检察院提出对被追诉人从宽的量刑建议,根据法律规定,在审判阶段法院一般应当采纳检察院的意见。由此可以看出,在认罪认罚案件的处理过程中,检察院的意见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从另一个角度看检察机关似乎分割了法院的裁判权。因此,为了贯彻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就必须要保证审判的独立性,而将公共利益因素引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将其作为决定适用该制度与否的因素,由法院独立作出判断,这样便能很好地解决其中的矛盾。
第三,在認罪认罚案件中引入公共利益,有助于体现裁判的正当性。特定案件的裁判结果不仅能够影响当事人的生活,而且带来的社会影响也不容小觑。在当前这个信息快速传播的时代,司法案件的处理过程更加清晰地呈现在社会公众面前,公众对于案件的裁判结果也更加关注。这就要求审判机关处理案件的时候,不仅要维护控辩双方的利益,还要顾及公共利益和裁判的社会效果,向广大群众彰显司法的公平正义,体现出裁判的正当性。
第四,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引入公共利益,有助于最大程度缓解社会矛盾。法官在决定是否对被告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时加入对公共利益的考量,通过刑事司法系统使社会公众提高对某一社会问题的认识程度,并起到警示、教育甚至是威慑作用,以缓解社会面临的问题,最大程度上解决矛盾。
(三)公共利益引入认罪认罚案件中的路径
在认罪认罚案件中,也可以参考Walker案中Goodwin法官的做法——将是否违反公共利益作为判断是否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衡量标准。然而,我国无论是在刑事诉讼还是民事与行政诉讼当中,对于公共利益的评估标准都不明确,甚至可能只是一种模糊的认知,因此需要对公共利益的判定进一步明晰。Goodwin法官对公共利益评估的四步程序对我国将公共利益引入认罪认罚案件有很大启发,完全可以套用四步程序对我国案件中的公共利益进行判定。以长春长生公司疫苗案为例,可以进行以下分析。
第一步,考虑与犯罪行为有关的特定地区社会背景。长春长生公司的问题疫苗主要投放在山东这个人口大省,严重威胁了当地人民的生命安全,造成社会恐慌。第二步,权衡公众对所指控的犯罪进行完整审判的利益。在食品药品安全危机的社会背景下,公众对有关药品安全问题的特定类型犯罪的审判产生兴趣,审判的结果也会影响到公众的利益。第三步,考虑在从简的程序中进行审判,是否会造成群众的不满。疫苗案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很大,若在简化的程序中完成审判,未能提供表达宣泄的平台,则必定会造成群众的不满。第四步,审查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动机。若对本案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则必须要考虑背后适用的动机,以确定其明显的动机是为了促进司法公正、提高效率,还是为了避免完整审判而获得从宽结果。综合以上四步的分析,得出若对长春长生公司疫苗案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符合公共利益,则检察官提出适用认罪认罚时法官应当拒绝。
公共利益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可以参照以上四步进行判定。另一方面,加强被害人的有效参与也将有助于将公共利益引入到认罪认罚案件中。如前文所述,对于裁判者来说,较多地关注的是控辩双方的预期利益,很有可能忽视公共利益甚至被害人的利益,而被害人的利益往往也代表着社会公众的利益。因此,加强被害人的有效参与,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增强对公共利益的关注。
七、结语
认罪认罚从宽作为一项新的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还需要从各个方面进行不断的完善。对“美国诉沃克案”处理方式的分析,为我国办理认罪认罚案件考量公共利益带来了启示。在公共利益的判定上进行明确,以更好地应用于认罪认罚案件,甚至可以推广到其他案件的办理程序当中去。但需要在考虑公共利益的同时尊重被告人的利益,企图通过牺牲某一特定案件被告人获得较轻刑罚的利益来解决某一类社会问题是不现实的,也不能因过于依赖公共利益而漠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设立的初衷。
注释:
① The Unconstitutionality of Plea Bargaining一文中提出:对被告人的正式、公开的谴责或辩护通过提高刑事司法系统的合法性而有益于社会,而辩诉交易通过诱导被告人对宪法审判权的放弃,对此造成了破坏;在认罪时,审判的价值丧失。Stephanos Bibas在 Incompetent Plea Bargaining and Extrajudicial Reforms 中总结道:辩诉交易使公共司法半私有化……它将正义商品化,使其隐避化,排除了中央和支持者,并繞过了陪审团审判中的道德宣泄。
② 《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11条(b):被告人只有在法庭允许下才能作不愿辩护也不承认有罪的答辩。法庭只有在正当考虑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和有效司法中的公共利益后,才能接受这样的答辩。
③ 《刑事诉讼法》第223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适用速裁程序:(一)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二)被告人是未成年人的;(三)案件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四)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被告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量刑建议或者适用速裁程序有异议的;(五)被告人与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没有就附带民事诉讼赔偿等事项达成调解或者和解协议的;(六)其他不宜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
④ 《美国法典》第21编第841(a)(1)条:除本分章授权的情况外,任何人明知或故意制造、分销或配发受管制物质,或意图制造、分销或配发受管制物质而持有受管制物质,均为非法行为。
⑤ 《美国法典》第18编第922(g)(1)条:任何人在任何法庭被判有罪,可判处一年以上有期徒刑;在州际或对外贸易中装运或运输,或在商业中占有或影响商业的任何火器或弹药;或接收在我国境内装运或运输的任何火器或弹药,都是违法的。
⑥ PCP (pentachlorophenol),五氯苯酚,一种迷幻药。
⑦ U.S. v. Hamm, 659 F.2d 624 (1981)。
⑧ U.S. v. Salinas, 693 F.2d 348 (1982)。
⑨ U.S. v. Smith, 55 F.3d 157 (1995)。
⑩ United States v. Wilmore, S.D.W.Va.2017, 282 F.Supp.3d 937。
B11 见中国长安网,福州公安案情函报,http://www.chinapeace.qov.cn/chinapeace/c54222/2019-02/21/content_12212715.shtml。
B12 山东省最高级人民法院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2017)鲁刑终151号。
参考文献:
[1]The Unconstitutionality of Plea Bargaining[J]. Harvard Law Review, 1970,83(6):1390.
[2]Bibas S. Incompetent Plea Bargaining and Extrajudicial Reforms[J]. Harvard Law Review, 2012,126(1):150-175.
[3]Criminal Law[J]. Harvard Law Review, 2018,131(7).
[4]Witten L. Proportionality as a Moral Process: Reconceiving Judicial Discretion and Mandatory Minimum Penalties[J]. Ottawa Law Review, 2016,48(1):115.
[5]Zina L B S. An Inconvenient Bargain: The Ethical Implications of Plea Bargaining in Canada[J]. Saskatchewan Law Review, 2018,81(1):53-86.
[6]Mark P. The Public Interest Criterion in Prosecutorial Discretion: A Lingering Source of Flexibility in the Canadian Criminal Process[J]. Windsor Review of Legal and Social Issues, 2015,36:57.
[7]Gold R M. "Clientless" Prosecutors[J]. Washington Law Review, 2017,92(1):87-143.
[8]Peter Reilly. Corporate Deferred Prosecution as Discretionary Injustice[J]. Utah Law Review, 2017(5):873.
[9]Garrett B L. The Public Interest in Corporate Settlements[J]. Boston College Law Review, 2017,58(5):1495.
[10]Abebe A A. Appraisal of Plea-Bargaining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Policy of Ethiopia[J]. Bahir Dar University Journal of Law, 2015,5(2):286.
責任编辑:曲 红、康雷闪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consideration of public interests in the cases of admission of guilt and punishment mainly focuses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leniency of admission of guilt and punishment on the social interests afte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eniency of admission of guilt and punishment, rather than on the measurement of public interests befor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eniency of admission of guilt and punishment. In the U.S. V. Walker case, held by the U.S. District Court in 2017, the legitimacy and rationality of the judges refusal of plea bargaining based on the assessment of the public interest caused a heated debate. This case takes the public interest as the criterion to decide whether to apply plea bargaining, and puts forward the four-step procedure to evaluate the public interest, which has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introducing the public interest into the case of guilty plea and punishment in China. In dealing with cases of admission of guilt and punishment, judges can evaluate the public interest through four steps: social background, trial interests, public opinion venting and application motivation, thus defining the fair application of leniency system of admission of guilt and punishment.
Key words: public interest; plea bargaining; guilty pl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