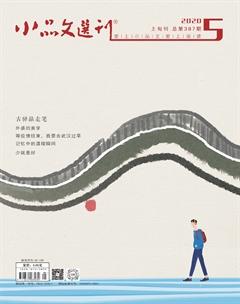鸟鸣啼春
任随平
鸟声是能够润泽春色的,尤其是在春晨。
天色微明,当清晨的第一缕曙光顺着窗棂的罅隙挤进来时,就有啁啾的鸟声跟着进来了,落在被单上,落在眼眸上,落进耳根,落进心灵深处,清清凉凉的,明明亮亮的,似珠露,若温玉,就那么一声,却又长长久久地萦绕在心间,于是,春晨就醒了。而西边的天幕上,还有星星亮着,未来得及隐去那淡淡的光芒。
之后,就有鸟雀三三两两地醒过来,至于那起初的一声,是什么鸟,我每每听过,但始终未能清晰地辨别出来,但这鸟声却是真真实实地叫醒我,叫醒我的村庄,叫醒高树上栖息的鸟雀。三三两两的鸟雀醒来,就开始窸窸窣窣地动,振翅,弯了头清理羽毛,腾挪翻越,从一根枝条到另一根枝条,突然间又猛然停住,静静地聆听,似是听到了谁的召唤,或是蓦然间想起了什么似的,安安静静立了好几分钟,让树下的我为之捏了一把汗———它还会不会啁啁啾啾地醒过来?就在我凝眸静立的瞬间,它将头猛甩了两下,蹬枝而去,紧接着就听到了木门吱呀的声响。哦,这鸟雀,总是比人敏锐得多了。这时候,太阳翻过了远山,煦暖的光线斜斜地照过来,众鸟儿一齐醒来了。
醒来的众鸟,屋脊是它们的最爱。青青瓦舍,屋脊高高,从高树到屋脊,它们总是喜欢俯冲而下,一只,三两只,呼啦啦一群,落在屋脊上。这时就有炊烟升起,袅袅娜娜,丝丝缕缕,盘旋着,萦绕着,而这鸟雀最喜欢钻进萦绕的炊烟里,跳跃着,钻出钻进,顽皮地,向着烟雾浓密处狠狠地啄去,谁料那尖喙却啄在空虚里,于是扑棱着翅膀左右望了望,又向别处跳去。场院,檐下的台阶,也是它们的去处。其实,在村庄,鸟雀是不怕人的,不论是成群结队的麻雀,还是喜欢将巢穴安在紧邻屋舍高树上的鹁鸪,还是后院崖面上的灰鸽,它们都把村庄当成家,把青青瓦舍当成练兵场。在这里,它们腾挪飞跃,将春天戏成一幅画,一幅春鸟啼春图。
春鸟啼春,啼醒烟柳婀娜。
在村巷行走,我一直認为这鹅黄嫩绿的柳芽是鸟儿叫醒的。立于巷口,搭眼望去,近旁的柳枝上泛着鹅黄的光晕,渐行渐远,这光晕就由鹅黄淡淡地滑向嫩绿,闪闪烁烁。而鸟雀,就躲在高枝上,水灵灵地叫,每一声,都是一滴晶莹的水滴,顺着枝柯滑落下来,落在晕黄的芽苞上。那芽苞被层层的绒毛包裹着,鲜鲜亮亮,轻轻地凑近鼻息,散逸着淡淡的柳香,轻轻盈盈地入了肺腑,丝滑绵长,就若这鲜亮的鸟声一般,弥散在心胸间。
烟柳馨香的时候,若是恰逢一场蒙蒙细雨,春天就是洇染在大地上的巨幅册页了。
烟柳朦胧,鸟影归斜,望春的人立在郊外的木桥上,远山,村巷,一切浸染在雾霭般的烟雨里,湿了翅羽,湿了发丝,湿了眼眸,而望春的无限爱恋,早已化为胸中无限的诗情。就这样,不疾不徐,不念不想,等待归鸟的翅羽,将一抹淡烟春色驮回暮晚的钟声里。
及至村野苍茫,就卷起这巨幅册页,裹进村巷,裹进胸间,裹进这春的夜梦……
选自《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