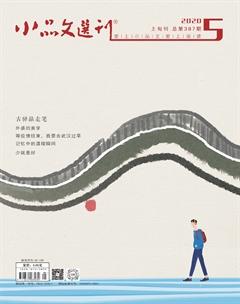在时光的水中
夏海涛
泰山南麓的大汶河,是一条人们并不陌生的河流,闻名天下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就坐落在这条河的中游。在距今7000~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就活动在这河畔,那些出土的石斧、石锛、石凿和磨制的骨器上,留下了祖先劳作的痕迹和汗迹,因了这些人的痕迹而成为极具“价值”的文物。
就在大汶河两岸,还盛产一种俗称“燕子石”的奇石,石头上有无数的春燕穿柳,姿态万千,故名“燕子石”。其实它是距今5亿~3亿年前,盘踞地球达3亿年之久的三叶虫的遗体形成的化石。
令人惊奇的是,在时间的河流中,这些死去数亿年的三叶虫居然复活了,在人们发现它们的那一刻!它们以飞翔的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或者压根儿就没有死,它们只不过潜伏在时光深处,默默等待着苏醒的这一天。
所有的生命都是不可替代的,都会在时光中留下痕迹,渺小如这微不足道的三叶虫,概莫能外。只不过时光的尘埃遮蔽了太多的生命,我们无法确认,在时间向度上,是怎样的力量让存在的东西消失,又让这些消失的东西依然存在。
据科学研究,目前泰山上最“年轻”的岩石距今也已有16.2亿年;而在泰山极顶的玉皇顶,岩石距今已经有30亿年。这些古老的岩石,是成就古老泰山的物质基础。然而人们也许想不到,泰山依然年轻着,依然以每百年10厘米的速度在增长着。
在长与短、古老与年轻之间,我们找不到临界点。我们只是站在河中,被裹挟着身不由己地被动前行。
距离泰山90公里的曲阜市,是孔子成长的地方,他的儒家思想,2500年来成为中华文明的一座独尊的精神泰山。虽然时间已经湮灭了尊孔与反孔、反孔与尊孔的是是非非,但是他留下的精神,却仿佛水流一样柔软绵长,从未间断。
一种非物质的意志存在,最后以物质的形态进入了中国人的基因。
在《时间简史》中,史蒂芬·霍金曾用了这样一种表达:“空间和时间是一个整体,有空间的地方就有时间,有时间的地方就有空间。那么宇宙在膨脹,时间就在延续,宇宙一旦停止膨胀,时间也就停止。那就是世界末日。时间和空间只能是一个整体,它们之间的夹角只能是零。
“因为它们在大爆炸之前交于奇点,所以它们不可能平行。时间和空间是一个整体意味着它们不可能单独存在。这样,接着我必然得说,空间和时间是连续的,那么它们有速度吗?因为空间膨胀有速度,所以时间也必然有速度,即空间膨胀的速度等于时间的速度。”
这是伟大科学家关于时间的想象和解释,而时间在诗人的眼中同样具有神性。
诗人所有的工作,都在切割生活,打造一个时间剖面,如同老式收录机一样留住时光。诗人像怀孕的少妇、蛰伏的三叶虫和石斧、石锛上留存的汗水,他们留下文字,期待着未来……
诗人表达了他在时间流程中的感悟,因此他笔下的文字就有了强烈的感染力。他小心翼翼地将选择过的生活带入诗歌,那些以大自然为主题,那些充满着爱的文字,关注着人类心灵的成长和成熟,关注着生命的终极。这样的文字也因此具有了超越自我的神性。
水是这个世界上最单纯、最复杂的物质之一。你看得到,在成千上万年的岁月中,一滴一滴的水,从高处滴下,然后在低处慢慢隆起一个奇迹。这个过程是如此漫长,你不知道,我不知道,水也不知道,这种隆起是偶然加上必然的,不知不觉中,时间缓慢地伸出锋利,切割了焦躁,留下了恒久。这种缓慢是一种运动,朝着时光的正向,不间断地动着,把感觉中每分每秒拉长,再拉长,在舒缓的进程中,完成。或者压根儿就没有结果,这个过程却从不停歇……
还有一种水,在巨大的压力下,会产生无比的锋利。它天马行空,桀骜不驯,以无比的速度和力量,在一切有形的物体上剥开痕纹……这是水的另一面。
突然就想起了旧时光。小时候学过很多无用的技艺:下象棋、吹笛子、打乒乓球、练羽毛球……在我17岁踏入社会的那一天,我学会的第一门技艺就是摄影。我攒了6个月的工资,买回了一台海鸥牌120型照相机,开始了摄影。这完全是一种无用的技艺,当我操着这台笨重的相机去面对花花绿绿的世界时,内心感觉到了一种无比的富足……
写诗是一门无用的技艺,好像是屠龙之技。因为写诗,总是爱把目光投向天空,看星空、看夕阳、看风车一样转动的春夏秋冬。日子久了,就养成了习惯,对世间的一切挚爱着。这也无所谓好坏。
时光之水流着,刀锋一样划过,呈现在面前的是一个生存的断面。这上面或有想象中的永恒,或者压根儿就是一片看不到边的虚幻。
一切交给时间。
选自《红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