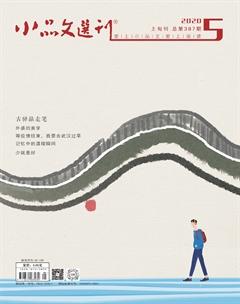瓦豪河谷那座村庄
宁白

多瑙河流經奥地利后,最美的就是瓦豪河谷。
从船上看去,连绵的山坡,遍栽着葡萄树,山顶上有中世纪的古堡,河岸边矗立着宏大的教堂,童话般彩色的木屋,星星点点,在浓郁的绿色中,只露出尖顶。
走在村里葡萄园的小路上,身边一米多高的葡萄树,齐齐地排到远处的山脚下,每排葡萄树前,栽了一棵小巧的玫瑰树。同行中有善酒者说,景色虽美,但这里是奥地利最重要的白葡萄酒产区,应该品一品这里的酒啊。甘愿醉在这葡萄树的绿荫下!话音一落,应和者众。
当地人领我们去了酒窖。其实就是一个山洞,狭窄深长,昏蒙暗黑。凹凸的洞壁,凿有密密的小洞,插入了瓶装葡萄酒,恍若是密麻排列的手榴弹。迷乱的灯光下, 20来个人坐在长条桌的两侧,每个人面前放了一个茶杯、一个高脚葡萄酒杯。一袭黑裙、面色苍白的奥地利老妇给我们斟酒,一红二白,第三杯,清冽醇厚,每个人在暗黑中拿起高脚杯仰头的那一瞬,都陶然。这样的酒,犹如葡萄果子的琼浆玉液,该握着酒杯,在阳光下的葡萄园畅饮。我看着洞口的光亮,想开去的是,酒的作坊在哪里?那一片山坳,都被葡萄树覆盖,田园的静寂,不允有作坊屋宇和劳工吆喝的闯入?那位善酒者,正躲在洞底边的暗处,置身于酒的包围中,眼睛闪亮,一派舒适。
村庄,离酒窖不远。屋前院落,葡萄架下,老人闲坐,神情安详,桌上的一杯白葡萄酒静默,像一个道具,走进这样的安宁里,得微语轻步;屋角边,一位身材颀长、衣着陈旧、额宽鼻挺的中年男人,洒脱地站在并不鼓肚的橡木酒桶旁,一手插入裤袋,一手握着酒杯,面目严谨,双眉紧锁,像一个尚未走出困境的哲学家,在隐隐传来的教堂钟声中思考着什么。
在村子里用餐,排场依然考究,高脚杯、白餐巾、整套的刀叉,你得正襟危坐,装作斯文。可是,菜上桌后,却让你端庄的架势散了。一碗汤,西红柿加土豆,漂着几片菜叶,叶已烂熟,汤汁不浓不淡;一片大于手掌的牛肉,有半寸之厚,肉质老而无味……一桌人吃着最后上的冰激凌,调侃起了小村菜点的粗简:这里是奥地利的“农家乐”!再吃一餐就乐不起来了!七嘴八舌,东答西应。
这时,有手风琴的乐声传来,引出了一段苍老的歌声。循声回头,在狭长的餐厅中央,一位满头白发的长者,拉着陈旧的手风琴,仰着头,半眯着眼,沉迷地演唱。餐厅瞬间安静。他的歌声,沉缓又有点感伤,像从山边掠过葡萄园飘逸而来,有着一个村民辛劳的沧桑和生活的感怀。
是朴素的劳动者的心声,源出于这个淳朴的小村,也源出于这个广袤的、无际的葡萄园。我倏然浮想,餐桌上厚实的牛肉、粗圆的饺子、烂熟的素汤,正保持着农家的本真,与这歌声一起,融合在河谷小村日常生活的场景和气氛里了。这位老人,朴实得像一位农夫。他的演唱自有一番生命的深沉,这沉郁的旋律,让我将行走中所见到的图景瞬间组合起来,铺展成一幅乡村世俗画卷,小村的生活里流动起了寂静和古旧的气息。
歌声停息的时候,餐桌上无人言语。对菜品的调侃,显示出的是调侃者一厢情愿的评判,这是单一的、就菜论菜的物质思考,完全没有弄明白,瓦豪河谷中的小村想呈现给你的整体感受是什么。
斜阳的余晖铺洒在蜿蜒无边的葡萄树上,散落于葡萄园的屋顶被抹上了一层柔暖的亮色。这时,村庄慵懒了。村口,却有一位中年男人,圆脸、凸肚,满脸灿烂,吹着黑管,身体随节拍大幅度地摇摆,高帽上插着的那支长长的羽毛,轻飘抖动。在这恬静安然的农庄里,他如入伊甸园般的舒展和快活。
船继续在瓦豪河谷行游,目光投向两岸的风光时,眼中不仅仅是草木起伏、冈陵绿影和藏于其间的古老建筑了,我长久地注视着山谷中偶尔出现的一个个村庄,直至它慢慢离开船尾,远去。这时,心有漫想,便靠着船栏,与人议论:瓦豪河谷被纳入世界文化遗产,不仅是因为犹如诗画的美景,更因为在河谷村庄的世俗生活里,有着古朴、淳厚的乡土气息与遥远的教堂钟声。
我的脑海里,久久不忘的是,暗黑的酒窖、古远的歌声和沉思中的男人的目光。这样的画面,不忍飘散,是想告诉我,在历史进程的漫长路途中,这是一座没有走失的村庄……
选自《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