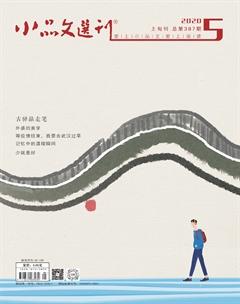等疫情结束,我要去武汉过早
梅姗姗
2017年的夏天,因被池莉笔下的武汉美味所吸引,我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武汉吃饭之旅。出发前,我给林子发了个微信,“我要来武汉三天,准备接驾吧”。“好,不让你撑死在武汉街头,我就不姓林。”她回我一个轻蔑的笑脸,我带着饥肠辘辘的胃,坐上了去往武汉的高铁。
一
出了高铁,扑面而来的热浪打得没跌个踉跄,我才知道武汉的夏天可真不是人受的,随便38度的气温,能杀死任何活物的求生意志。
林子就在出站口,我俩跟人形包子一样,走进了笼屉的世界。“先去吉庆街好么?”我带着对池莉笔下武汉的膜拜,试探性的问了一下。林子说吉庆街早就不是书里那样了,你听我的,不会亏待你。
我被林子带过繁华的江汉路,穿过老社区,来到一条长长的街道。沿边的黑暗与几百米外灯火通明的大洋百货形成鲜明的对比。林子说,“外头人只知道武汉的过早,只有武汉人自己知道,卤菜才是探一家之绝学的真地方。”
黑黢黢的巷子,一个白炽灯泡就那么远远的摇晃着。这家名叫吴长子的卤菜馆,一口直径一米二的大铁锅支在门口。大锅里面铺满了豆干猪儿海带五花肉香肠莲藕,每个都润上了深深的褐色。白色的雾气氤氲在铁锅上方,飘散出的是让人忍不住分泌唾液的香气。

林子说,这家店已经20多年了,是武汉市卤菜第一第二的存在。“没有服务哈,你自己拿要用的碗筷,然后找位子去。我先去点餐。”
老板娘利索地抓着各种卤味就是一顿猛切,我要了海带,莲藕,猪耳,肥肠,林子去隔壁买了一瓶啤酒。就这样,我俩自给自足地蹲坐在夏夜武汉居民小巷的路边,听着周围人各种聊天。
二
过早,武汉的标志。这个被蔡澜称作“早餐之都”的城市,有着吃不完的早餐。
按武汉作家舒怀的说法,过早的产生,跟它作为交通运输中转站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江汉平原自古富庶,再加上“九省通衢”,每个人带来一点点,生成的就是武汉丰富的早饭文化。
曾记豆皮是林子几年前发现的。她说人人都说严老幺好,但那家永远在排队。可曾记口味也没差,都是老武汉的滋味。她点了一份三鲜豆皮,一碗糊米酒,我则跑出去看老板做。
豆皮的制作是视觉和味觉的双重艺术。一口大铸铁锅烧得滚烫,一勺豆皮汁下锅,晃荡几下就占了满锅,抹上一层蛋液,翻一面,撒上糯米,哨子,哨子汁,最后大型翻锅———这是最精彩的一幕,最后撒葱切开。
刚出炉的豆皮带着一种酥脆的口感,糯米软却不失韧劲,混上了哨子汁后更多了一层湿润,里面大粒的肉丁,笋丁和香菇丁让人欲罢不能。我一口一口不停歇,干了就来一口糊米酒。
干的配稀的,咸的配甜的,是武汉过早的基本原则。别看名字好像很神奇,其实糊米酒跟江南的酒酿元宵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更粘稠些。
林子趁我吃得欢,跟我科普豆皮。她说如果你吃的里面有豆腐干,就不合规矩。要知道,武汉夏天是很热的,在以前没冰箱的时候,豆干放一天就馊了,所以正统的豆皮都不会有豆干的!
之后去吃熱干面的路上,我无意发现了武汉的另一个特产:“碳水炸弹”油饼包烧麦。这是一个看起来就有年份的小门脸,老板拿着长筷子在油锅里摆弄,老板娘默契地在旁边桌上一手小铲一手筷子,撑开油饼,拣起刚蒸好的猪肉糯米小烧卖。我没忍住要了一个,趁着刚出炉的劲儿咬一口,油饼酥、香、薄、脆,搭配着猪肉香菇的鲜美,烧卖皮还能吸掉油饼多余的油腻,太完美了!
三
热干面在武汉的任何马路上都随处可见,但按林子的话说,每个都差一点。“好的热干面不能用黑芝麻酱,白芝麻酱不能用水得用芝麻油澥,面要先煮半熟吹凉拌油后再用,吃的时候烫一烫就好,而且一定要有辣萝卜头......但今天,每家都有那么点偷工减料。”
我可没那么讲究。热干面于我最美好的地方,就是性价比极高,且满足感极强。你想想,微带韧性的碱面沾满了咸香的芝麻酱,为了不腻,神来之笔般地加了勺醋,嚼着嚼着,还有脆辣的萝卜干和辛辣的香葱冒头,给你一丝丝口感上的惊喜。吃完一大碗才4、5块钱,请问在哪里还能找到这种廉价的幸福!
当然还有著名的武汉牛肉粉,腰花粉和汤包……在每天高强度的碳水轰炸下,我连挪步都有种肚皮随时会炸的感觉。林子嘲笑我,“又不是不再来了,吃成这样至于么!”但的确没再回去,直到现在。
2020年伊始,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把林子隔离在了围城里面。我翻着手机里,那年夏天我和她在武汉街头各种吃照,把其中一张她吃得巨认真的照片发给她,说“等解封了,我们再去吃豆皮吧!”她回复:“等疫情结束,我要把曾记豆皮,吴长子卤菜,老魏氏牛肉粉,民生甜食一家家都吃一遍!我要亲眼看到他们每个人都健康,都好好的。我要亲眼看到!”我哭了。
选自《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