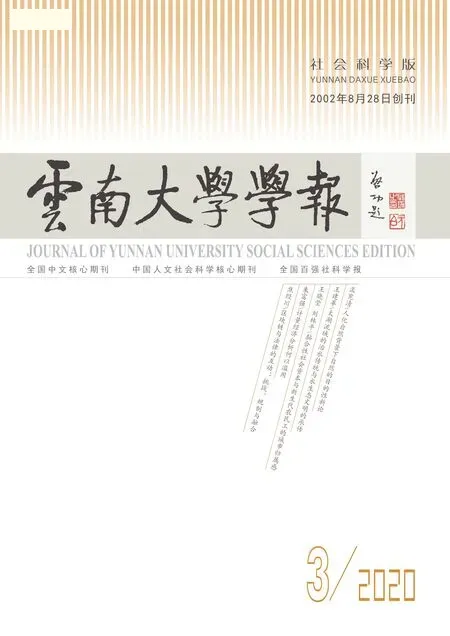从《文心雕龙》“由内及外”的思维方式看其礼学蕴涵
程景牧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刘勰《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虑周”(1)〔清〕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五(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59页。的文论著作,体大虑周固然彰显在体系结构、思想主旨及理论阐释等方方面面,但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即其“由内及外”的思维方式。《文心雕龙·体性》开篇云:“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刘勰在此即指出了文章创作是一个“因内而符外”的过程,“因内而符外”即是“由内及外”。正是“由内及外”的思维方式的导向作用,促成了《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的建构、思想框架的定型、审美旨归的确立。然而,当前学界对于《文心雕龙》的思维方式并不甚关注,有限的研究著作或是探讨玄学与佛学对其之影响,或仅仅采用内部视角就《文心雕龙》的文本自身进行探讨,而关于《文心雕龙》的思维方式与礼学的关系,则更是鲜有问津。本文有鉴于此,即以 “由内及外”的思维方式为切入点,探赜《文心雕龙》与礼学的内在联系,以起到抛砖引玉之功效。
一、刘勰《文心雕龙》由内及外的思维方式
刘勰《文心雕龙》彰显出鲜明的由内而外、由里及表的思维方式与论述模式。约略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从体系结构的设置来看,《文心雕龙》的整体与部分均彰显出由内而外的思维方式。《文心雕龙》章节篇目之间,各自独立而又紧密联系,一脉相承,首尾呼应,既面面俱到,又点面结合,呈现立体化的理论体系模式,体大思精,以极其缜密的由内及外的思维特质建构全书。此书共10卷50篇。分为上下篇,各25篇。上篇,从《原道》至《辨骚》5篇为总论,即总纲,从《明诗》到《书记》20篇是文体论。下篇,从《神思》到《物色》20篇是创作论。《时序》《才略》《知音》《程器》四篇,则为文学史论、作家论、鉴赏论等批评论。最后一篇《序志》为一篇自序性质的总结文字。这样的体系结构集中地从整体上反映了由内而外的思维方式。前五篇为总纲,即文之枢纽,是本体论或称为文原论,是对文学内在属性与本质的界定与探赜,内在属性确立下来,自然要涉及文学的外在表现形式——文体,所以要讨论各种文体的来龙去脉,接下来20篇则对各种文体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概述,而且,刘勰在文体论中先论述诗、乐府、赋等具有纯文学性质的有韵文体,然后论述史传、诸子、论说等与纯文学有一定距离的无韵之文体,也在一定程度上彰显出这种思维方式之特征。在对各类文体进行考察梳理之后,自然要转入对创作过程与方法的探讨,因而紧接着便是创作论,创作论是以文体论为依据的,如果文体不明,创作则无从谈起,所以创作论处于相对外在的技巧方法的层面,而创作论中首先是《神思》这篇营构论,其次是《体性》《风骨》《通变》《定势》等风格论与方法论等具体理论,这样的排列组合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即先有内在心理的构思,才能有外在的风格、方法的体现,由内及外的思维方式昭然若揭。要之,《文心雕龙》全书的理论体系贯穿着由内及外的思维方式,而正是这种思维方式,也造就了《文心雕龙》的体大虑周。
其次,从具体篇目来看,无论是文体论,还是创作论,在具体论述时皆先阐释概念、追本溯源,然后举例论述这种文体、风格、创作方法的发展过程,最后阐明写作原理。例如对于文体论,刘勰以本原探究为出发点,对各种文体皆要探其源流。刘勰说:“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文心雕龙·序志》),可见,刘勰十分注重各种文体的来源与流变,这当然是由内及外的思维方式所致,正如台湾学者尤雅姿所说:“以论文叙笔的23篇34种文体来说,‘按辔文雅之场,环络藻绘之府’的刘勰,其所以能‘乘一总万,举要治繁’,靠的就是他卓越的逻辑思辨能力。从文体论四条例来看,‘释名以章义’是对概念的内涵界定;‘选文以定篇’是对概念外延的画定;前者是共相,是抽象普遍的定义;后者是殊相,是具象且独特的作品。”(2)尤雅姿:《文心雕龙文艺哲学新论》第一章,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10年,第30页。尤雅姿点明了文体论先内涵后外延的论述方法,而她所说的这种逻辑思辨能力即包含着由内及外的思维方式。刘勰的文体论主要分为四个步骤,即首先说明各类文体的名称概念,其次论述这种文体的源与流,再次具体举例论证各种题材的代表作品,最后阐述各种问题的创作原理与风格特征。很明显,这种论述模式大体上是按照由内及外、由里及表的逻辑顺序进行的。如《诠赋》篇开头即对赋下了定义(《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然后点明赋出于《诗经》与《楚辞》(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接下来论述赋在汉代的繁荣发展,并依次列举了两汉魏晋赋家的代表作品,最后阐述了赋的写作道理,并提出了对赋的写作要求:“风归丽则”。由是观之,刘勰按照解释概念、叙述源流、评述作品、阐述原理的次序对赋进行了逐步拓展式的阐释,即是对由内及外的思维方式的践行。不仅从文体论中可以看出这样的构思方式,创作论亦是如此,如《章句》篇先是对章句的概念作了阐释:“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接下来论述了“章句”的意义以及分章造句的原理,举出《诗经》《楚辞》中具体的例子进行论证,最后结合两汉魏晋文人的创作经验与主张阐述自己对章句要义的看法,很显然是按照由里及表、由近及远的模式进行论述的。
复次,从总纲五篇的排列顺序来看,由内及外的思维特质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文心雕龙·序志》云:“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刘勰将《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这五篇定为“文之枢纽”。概而言之,这五篇主要由本体论(文原论)、流变论两部分组成,而又是以《宗经》为核心向上下两个维度辐射拓展,也就是说《宗经》为总论之核心,《原道》《征圣》与《正纬》《辨骚》为《宗经》的外延。詹福瑞先生认为:“《宗经》在《文心雕龙》理论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即在总论中,亦可称为‘枢纽’,是总论的理论核心。”(3)詹福瑞:《汉魏六朝文学论集》,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0页。他进一步指出作为形而上的道经过圣文转化为形而下的经,经再流变为纬与骚,(4)詹福瑞:《汉魏六朝文学论集》,第145页。所以《原道》《征圣》两篇为《宗经》造势、做理论铺垫,《正纬》《辨骚》则为《宗经》的理论流衍,《宗经》囊括了《文心雕龙》文体论与创作论的基本理论内容,确立了为文之准则,在总论及全书中居于核心地位,詹先生的看法是颇具慧眼的,点明了《宗经》篇的重要地位与实际价值。无独有偶,台湾学者王更生先生也具有同样的看法,他在《文心雕龙管窥》中说:“《宗经》是刘勰文学思想的骨干,非但《原道》《征圣》以此为理论结穴,就是《正纬》《辨骚》亦以此为发议的基点。”(5)王更生:《文心雕龙管窥》(四),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7年,第84页。他在《文心雕龙·新论》中说:“详观这五篇,其中又有主从。大抵以宗经为主,前乎此者,有《原道》《征圣》;后乎此者,为《正纬》《辨骚》。因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故《原道》《征圣》乃正面的宗经,是以曰:‘原’曰‘征’;纬书‘乖道谬典’,楚辞‘语多夸诞’,故《正纬》《辨骚》为反面的宗经,因而曰‘正’曰‘辨’。但不管它们是正面或反面,两方都是贴着经典出发。所以我们可以大胆的说,刘勰的文学思想就是‘宗经’。宗经既是刘勰文论的最高指导原则,则读者势必先要了解他这个重要的关键,才能对《文心雕龙》的内涵,有根本的理解。”(6)王更生:《文心雕龙新论》(一),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第3页。王更生先生认为《文心雕龙》的总论这五篇以《宗经》为中心朝着正反两个向度扩展,这一观点与刘永济先生在《文心雕龙校释》中以正负为标准将总论五篇分为两类的看法大同小异。可以说英雄所见略同,总论五篇即是以宗经为旨归内核,向上溯源至“道”这个形而上的概念,向下衍生出正纬、辨骚的文学理念,这就是总论部分的逻辑结构也是由内及外的思维方式所促成的。值得注意的是,《宗经》虽然居于核心地位,但《原道》的地位亦不可忽视,《原道》从本体论的高度、形而上的层面,点明了文学的之本原,即是对文学发生、生成因缘的探讨,同样也是对文学本质内核的讨论,因而《原道》《征圣》《宗经》三篇共同构成了总论部分的内核,是文之枢纽的枢纽,对《正纬》《辨骚》二篇具有极高的指导意义。
最后,从《文心雕龙》的命名来看,刘勰十分重视内心情志,以“‘用心’为‘为文’的第一要义”,(7)王更生:《从〈文心雕龙·序志〉篇文看刘勰的智慧》,《2007年〈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8年,第769页 。体现出以内在心灵为本的文章观念。《文心雕龙·序志》云:“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可见“文心”即是指作文之用心、运用心思,刘勰极为重视心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与作用及其与物的关系。如《物色》篇开头即云:“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即是说人的内心情感随着自然景物的变化而变化,可见刘勰十分重视内心情感,所以他认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即强调在写景状物之时,既要随景物而曲折回旋,又要重视自己内心情感的抒发。刘勰认为心为文章之本源,他在《原道》篇中说:“性灵所锺,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可见,性灵之心催生了语言进而形成了文章,他在创作论中首标“神思”,而对神思的定义则是“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可见神思即是心思、心的想象与灵感。由是观之,刘勰以心为作文之本源,即是从文章的内在本质入手,来探寻文学的要义。这同样体现出由内及外的思维方式。
总之,《文心雕龙》的论述具有鲜明的等差性与层次性,大抵从问题的中心点向外辐射发散,进行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思维活动,彰显出由内及外、由里及表、由近及远的思维方式与论述模式。这种从事物的本质出发,首先把握其内在属性,在此基础之上探究事物的外在属性、发展规律,因而显得极具条理性、逻辑性与系统性,是以《文心雕龙》的具体论述能够“乘一总万,举要治繁”。我们不禁要问,这种思维方式是刘勰的独创,还是源于佛玄思想的浸润,抑或是受到儒学的影响?如果是儒学,那么又是儒学中的哪一类思想体系?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只有明了这种思维方式的渊源,才能更进一步加深对《文心雕龙》思想体系与学理意义的体认。
二、由内及外的思维方式在南朝礼学中之表现
如果仔细梳理寻绎《文心雕龙》这种由内及外的学理导向式思维方式的学术文化之因素与背景,我们不难发现,其实这种思维方式是南朝礼学与《文心雕龙》的共性之一,换句话说《文心雕龙》在很大程度上汲取了南朝礼学的这种思维模式加以融化改进,进而形成了这种由内及外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与礼学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在南朝礼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南朝礼学的思想特质。
南朝礼学是在儒、玄、佛三类思想的融合会通中、在门阀士族社会中发展成熟的,彰显出以内在血缘关系、血缘逻辑为出发点,逐步延及外在社会人际关系、国家制度的学理特征。在古代社会,礼的制定即是以亲疏关系来规范人伦等级秩序的,即“亲亲尊尊”。这样的等级制度在汉代主要是以建构外在的国家等级秩序,维护大一统的封建皇权为着眼点的,“尊尊”高于“亲亲”,但到了六朝,由于皇权的衰落、门阀士族的崛起,礼的规范作用则以士人家族为着眼点,“亲亲”胜过“尊尊”,是以即形成了由内及外的思维模式。萧梁徐勉《上修五礼表》云:“臣闻‘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故称‘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夫礼所以安上治民,弘风训俗,经国家,利后嗣者也。”(8)〔唐〕姚思廉:《梁书》卷二十五,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59-260页。在表文中,徐勉先是对礼的本质属性做了一番形而上的理论阐述,然后指出礼的经国治民的社会功能,这一段的话语与《文心雕龙·原道》的开篇极为相似。南朝礼学注重由启发人们心灵的体悟以作用于外在的社会伦理秩序,建构了一个由内及外的学理过程。如陈代沈不害《上书请立国学》云:
臣闻立人建国,莫尚于尊儒,成俗化民,必崇于教学。故东胶西序,事隆乎三代,环林璧水,业盛于两京。自淳源既远,浇波已扇,物之感人无穷,人之逐欲无节,是以设训垂范,启导心灵,譬彼染蓝,类诸琢玉,然后人伦以睦,卑高有序,忠孝之理既明,君臣之道攸固。执礼自基,鲁公所以难侮,歌乐已细,郑伯于是前亡,干戚舞而有苗至,泮宫成而淮夷服,长想洙、泗之风,载怀淹、稷之盛,有国有家,莫不尚已。(9)〔唐〕姚思廉:《陈书》卷三十三,第310页。
沈不害请立之国学即是以礼学为主的儒学。他在上书中指出礼学通过感化人心,启导心灵,然后规范人伦秩序,实现社会功用,此即揭示出礼学由内及外地施展教化之功用的学理过程,由起初的对人们内在心灵的启导以达到立人建国、成俗化民之终极目标。《南齐书·武帝本纪》记载武帝临崩诏书云:“祭敬之典,本在因心,东邻杀牛,不如西家禴祭。”(10)〔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三,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1页。按《周易·既济卦》第五爻之爻辞云:“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郊之禴祭,实受其福。”齐武帝引用此爻辞的意思是祭祀之礼根本在于心灵,与其用杀牛宰羊来举行盛大祭礼,不如虔诚恭敬地用心举行薄祀,如此才能实享福分。可见他不注重外在的祭祀形式,而强调内心的恭敬。由上述几例可见,南朝礼学首重内在心灵,次及外在形式及社会功能,运用的是一种由内及外的思维方式。总的说来,南朝礼学的这种思维方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从南朝礼学体系来看,以三礼为经、五礼为纬的礼学体系从整体上彰显出由内及外的思维模式。《礼记》《仪礼》《周礼》合称三礼,南朝礼学,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均以三礼学为核心内容,南朝礼学专家大多被称为好三礼,明三礼,善三礼,长三礼,足见三礼在礼学中之重要性。(11)梁满仓:《魏晋南北朝五礼学述论》,《文史》2005年第3辑。南朝礼学家大抵以郑玄三礼注为基础,旁采他家之说,建构了新的礼学体系,为五礼制度的实行奠定了理论基础。如果说三礼是礼学高屋建瓴的至高理论,统摄礼学之研究,那么五礼就是南朝士人在礼的具体实践中遇到的五大类礼制问题,五礼即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五礼在维系社会秩序,规范人伦道德,确立正朔问题等具体问题方面极为实用,是以五礼制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能够不断地发展。南朝萧齐是五礼制度由发展到成熟的过渡期。萧齐政府于永明年间诏令礼学大师王俭等人重新撰制五礼。萧梁是五礼制度发展的成熟期。萧梁天监初年,“何佟之、贺蒨、严植之、明山宾等覆述制旨,并撰吉凶军宾嘉五礼,凡一千余卷,高祖称制断疑。于是穆穆恂恂,家知礼节。”(12)〔唐〕姚思廉:《梁书》卷三,第64页。五礼围绕三礼即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学术理论体系。《宋书》《南齐书》之《礼志》皆以五礼为主要内容次第展开。五礼制度的建设需要三礼之学的指导,而三礼之学的发展又依赖于五礼制度的实践与发展,是以三礼之学与五礼制度有着密切的关联。礼学家要用三礼知识解决具体的五礼制度建设中所遇到的各类疑难问题,这就促使着三礼之学的不断发展与更新。三礼之学作为形而上的指导思想,五礼制度作为形而下的具体实践,三礼之学的实用性与意义即通过五礼制度体现出来。是以,三礼为经,是内在的思想理论依据;五礼为纬,是外在的具体的礼仪制度。礼学家在谙熟三礼经典之后,即根据具体需要建构五礼制度,呈现出一个由内而外的学理过程。

宗法与丧服制度就是因应组织家族的需要而产生的,宗法是建立家族 的广大轮廓,而丧服制度则是亲属关系的精密区分,凭借这两项制度的普遍推广实行之后,真正属于中国传统的家族观念才能正式形成,才能成为影响后世历史社会,根深柢固的中古文化的特色。家族观念的理论基础,就是深浅厚薄的相对等差观念,由于强调等差的结果,从“血浓于水”的内外分类,终于形成“五伦”的概念,我们所谓的五伦是:
君臣 父子 夫妇 兄弟 朋友
这种层次的排列并不仅是从上到下,表示尊卑上下的等级;而且是表示由内而外的发展形态。因为这也说明五伦是以夫妇作为中心,逐渐由此向外扩展的层次,……由此可知人伦关系真正的核心是家族,君臣、朋友的关系都是由此外衍的末梢。(15)周何:《礼学概论》(四),台北:三民书局,1998年,第23-24页。
周何分析得十分精辟,把握了礼学由内及外的发展形态与思维方式,点明了正是由于血缘关系的内外之分,逐渐形成以家族夫妇为核心的由内而外的层级等差次序。
最能体现南朝礼学由内及外的学理导向的则是对心丧礼的探讨与实行。南朝礼学以丧服礼最为精审,心丧之礼又是丧服礼中最具特色的制度之一。心丧礼在丧期、丧服、仪式等方面均有特定的内容,要求居丧期间与五服丧礼不同,不穿正式丧服,以心丧代替服丧,但要表现出心忧,不重外在形式,而重视内心的虔诚。心丧礼在先秦两汉偶有实行,直至晋代,方成为定制,在南朝得到大力发展,成为朝廷热议的话题之一。如刘宋“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崩。皇太子心丧三年。礼心丧者,有禫无禫,礼无成文,世或两行。皇太子心丧毕,诏使博议。”(16)〔南朝梁〕沈约:《宋书》卷十五,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65页。孝武孝建三年三月,有司就皇后之服心丧,临丧及服终除之日当着何服的问题奏请礼官处正。大明二年正月,有司奏议皇后心丧服期的问题。领仪曹郎朱膺之奏议:“今皇后二月晦,宜依元嘉十九年制,释素即吉。”由此可见,刘宋时期的心丧制度在不断完善之中。嗣后,齐梁陈三代皆因循之,陈文帝天嘉元年八月,尚书仪曹请今月晦皇太后服安吉君禫除仪注,沈洙奏议:
谓至亲期断,加降故再期,而再周之丧,断二十五月。但重服不可顿除,故变之以纤缟,创巨不可便愈,故称之以祥禫。禫者,淡也,所以渐祛其情。至如父在为母出适后之子,则屈降之以期。期而除服,无复衰麻。缘情有本同之义,许以心制。心制既无杖绖可除,不容复改玄綅,既是心忧,则无所更淡其心也。且禫杖期者,十五月已有禫制。今申其免怀之感,故断以再周,止二十五月而已。(17)〔唐〕魏徵等:《隋书》卷八,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05页。
沈洙对心丧之期限、禫祭等制度进行了分析,对陈代的心丧制度提出了建议。他指出丧礼“缘情有本同之义,许以心制”。可见当时礼学以缘情本心为根本立足点与出发点。
再次,从南朝礼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来看,南朝五礼制度在排列顺序上体现出由内及外的体系模式与思维方式。五礼制度最早见于《周礼·春官》,但汉代实行的是《士礼》礼制,而非《周礼》制定的五礼制度。随着时代的发展,魏晋南北朝实行的是五礼制度,尤其是南朝统治者根据实际需要对五礼制度进行改革,形成了新的礼学体系,五礼的发展与完备标志着南朝礼学的发展与成熟。南朝五礼制度的排列顺序体现出明显的由内及外的等差主次之分,五礼依次分为吉、凶、宾、军、嘉五类礼制,其中吉礼主要是祭祀之礼,为五礼之首;凶礼即丧葬、丧服、哀吊及凶荒之礼;宾礼即朝见、聘问及会盟之礼;军礼主要是军事演习、出征仪式之礼;嘉礼主要是婚冠饮食、节令朝贺、抚慰臣下、尊贤敬老之礼。由五礼制度的主要内容可以看出,吉礼与凶礼主要是丧祭之礼,是指向家族内部的,以血缘亲疏关系定上下内外之别的礼仪制度,因而在五礼制度中居于前列核心部位,而宾礼主要是针对外藩使臣的接待之礼,军礼具有鲜明的对外的指向性,嘉礼则兼有内外两重向度,可见吉礼与凶礼主要是内向型的,宾、军、嘉三礼在总体上是外向型的,南朝五礼制度的排序恰恰体现出由内及外的思维形态。
要之,南朝礼学无论是整个理论体系,还是具体礼仪制度,抑或是礼学家的思想理念均体现出由内及外的思维方式,彰显出南朝礼学自身的学理特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我们将《文心雕龙》的结构体系与理论阐述方式与南朝礼学进行对比即可发现,二者有着极其惊人的内在相似之处,即彰显出由内及外的思维方式的异质同构性,二者均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由内及外、由里及表的思维方式,虽然相似性并不代表着渊源关系,但是如果我们对刘勰及其《文心雕龙》与南朝礼学的关系做一番梳理与探讨,即可发现,这种思维方式正是源于礼学。
三、刘勰《文心雕龙》的礼学蕴涵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运用了由内及外的思维方式,而如果追溯这种思维方式形成的内在机制,那么则不能不考虑在当时学界最为兴盛的礼学。《文心雕龙》对南朝礼学在思维方式上的绍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从整个理论体系来看,南朝礼学以三礼为经、为核心、为形而上的指导,五礼为纬、为具体的礼制、礼学内容之落实;《文心雕龙》则以前五篇为文之枢纽、总纲,从形而上与形而下两个方面探讨文章之本原,以此作为全文的理论指导,然后以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为羽翼,为具体的文体风格、写作原理、文学发展史之评述。通过两相对比即可发现,《文心雕龙》与南朝礼学在这种由内及外的思维方式层面具有天然的异质同构性,皆从形而上的理论本质的探赜向外延伸至具体的内容与实践经验的总结。其二,从重要组成部分来看,南朝礼学中最为发达的丧服礼也是最能彰显亲疏等差关系的礼制,而且五伦关系中以夫妇为核心向外衍生的礼制形态更加集中地体现出礼学由内及外的思维特质。而《文心雕龙》中作为文之枢纽的五篇总论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以居于最中心的《宗经》为核心,向外衍生扩展,这五篇总论的排序即是对由内及外的思维方式之运用。其三,从具体内容来看,《文心雕龙》的文体论、创作论等具体篇目在论述时也是按照由内及外的次序进行的,而南朝礼学的五礼制度的排列次序清晰地展现出由里及表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彰显出二者思维模式的内在一致性。其四,从对心的重视来看,《文心雕龙》将心列为文学创作的第一要义,而南朝礼学极重心丧礼,丧祭之礼首重重视内心情感的真诚,而其次考虑外在的礼仪形式。是以无论是《文心雕龙》还是南朝礼学均重视内心情感,也就是以内心情感为主,而以外在形式为次,这也是由内及外的思维方式之表现。
《文心雕龙》与南朝礼学思维方式的异质同构性彰显出这两类不同的学术思想体系在同一个历史文化场域中逐渐形成的集体无意识状态,礼学作为权力话语必然深深地浸润于南朝文论思想体系之中。而南朝文论深深地根植于以礼学为主的南朝儒学的土壤中,必然汲取礼学的思想话语特质,所以《文心雕龙》由内及外的思维方式与礼学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可以说正是礼学的思维方式感染了刘勰及其《文心雕龙》,遂展现出这种思维方式。那么礼学又是如何影响刘勰,换句话说刘勰又是如何接受礼学的呢?二者的渊源关系是如何成立的呢?这又是值得的探讨的,只有把这个问题弄清楚,才能有效合理地揭示出《文心雕龙》思维方式的形成因缘。要之,就刘勰及其《文心雕龙》与礼学的渊源关系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探讨。
一方面,就《文心雕龙》所彰显出的思想主旨与主要内容来看,《文心雕龙》的创作深受南朝礼学的影响。上文业已提及《文心雕龙》前五篇构成的文之枢纽的总论,以《宗经》为核心,向上下正负两个向度扩展。《宗经》篇指出各种文体均源于《五经》,文章如果能够宗经,就会有六种优点,即“文能宗经,体有六义”。在《宗经》篇中共有三处提到《礼经》,可见他对礼学是较为服膺的。
在《序志》篇中,刘勰先是叙述了自己的两个梦,即“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也!乃小子之垂梦欤!”第一个梦中的“彩云若锦”其实是暗喻文章之文采,这是南朝人惯常的用法,如钟嵘《诗品》卷中:“汤惠休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彩镂金。’”所以刘勰的第一个梦即是表明自己爱好文学。第二个梦颇耐人寻味,说自己梦见朱红色的礼器随孔子南行,醒来后大喜,即是表明自己极为推崇孔子,梦想自己列入孔门之中,他追随孔子表明自己是尊崇儒学的,而他手执礼器,则又表明自己推崇礼学,因为礼器既象征儒家文化,又代指礼学精神。刘勰借助这两个梦表达出自己对当时以礼学为代表的儒学的尊崇,因此这也是对《文心雕龙》与礼学密切关系的一个暗示。周勋初先生在《刘勰的两个梦》一文中说:“刘勰在这两个梦中寓有很深的用意:前者用以表明他自小与文学即有宿缘,后者用以表明他将宣扬儒家教义于南土。这两个梦不但与《序志》篇的内容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与《文心雕龙》全书总的精神也息息相通。它们不是书中可有可无的部分,而是理解全书的两把钥匙。”(18)周勋初:《文史探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9页。周先生指出这两个梦为理解全书的两把钥匙,即点明了《文心雕龙》崇儒的思想主旨,那么刘勰对儒学的哪一部分最为推崇呢?他在叙述两个梦后,说:“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文,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刘勰极力推尊圣人孔子,这在《征圣》篇中也有述及,因而在孔子的精神熏陶之下,他也燃起了注经的愿望,认为最能传承圣人之学的做法即是注经,但是理想是美好的,而现实是残酷的,当他考察学界现实即意识到自东汉以来的马融、郑玄诸位大儒早已遍注群经,建构了体大思精的经学体系,而自己如若注经则难以超越他们的成就,在这样的情形下,他转换思路,发现文章是经典的旁支,与经典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他列举了当时盛行的五礼制度与《周礼·太宰》中的治、教、礼、政、刑、事六典,认为五礼和六典皆借助文章以完成和施行,又进一步指出君臣的政绩、军国之大事皆靠文章来阐明,最后他得出结论:文章皆源于经典。这个结论与《征圣》《宗经》的主旨是一致的。正是在这个观念的引导下,刘勰认为自己只能通过“论文”以实现“敷赞圣旨”之愿望。
值得注意的是,刘勰在这短短的几句论述话语中,论述经学及经典与文章的渊源关系时,所举的例子皆与礼学有关。如东汉大儒马融有《三礼注》问世,其弟子郑玄更是三礼学之大家,郑玄以《三礼注》著称,以礼注经,成就极大,而其学之主流与核心即是礼学,所以孔颖达《礼记正义》云:“礼是郑学”。他列举马郑之学、礼学中的五礼与六典以及君臣政绩、军国大事等涉及的到礼仪制度的例子说明文章与礼学的关系,其实正是礼学在南朝极为发达的实际情况在其头脑中的反映。魏晋以降,统治阶级十分注重礼在治国安民方面的作用,是以礼学在南朝学术中处于核心地位,南朝礼学极为发达远远超越经学中的其他门类,《隋书·经籍志》著录的礼学典籍的数量远逾众经,这样的经学风尚自然影响到刘勰,刘勰也想研治礼学,所以才会举出以上与礼学相关的例子。
再看文体论,《文心雕龙·宗经》指出:“《礼》以立体,据事制范,章条纤曲,执而后显,采掇片言,莫非宝也。”“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刘勰强调礼经在建立体制规范的同时,也彰显出极高的文学价值,接下来他指出铭、诔、箴、祝这四种文体源于礼经。在具体的文体论中《明诗》与《乐府》自然是礼乐文化的产物,自不必赘言。《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十篇皆以礼学类文体为论述对象,其中颂、赞、祝、盟、封禅等文体属于吉礼的范畴,诔、碑、哀、吊等文体属于凶礼的范畴,诏、策、章、表、奏、启等文体属于宾礼(君臣之礼)的范畴,檄文则属于军礼的范畴。由是观之,刘勰根据当时礼制的具体情形进行礼学文体考论。陈戍国、陈冠梅《中国礼文学史》将《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檄移》《封禅》六篇归入礼文学作品,他们指出这些篇目“所讨论的对象或内容本身就在礼典礼仪之中,而作者在讨论相关的创作经验或应该把握的规律的时候,又写得美轮美奂,令人赞赏。”(19)陈戍国、陈冠梅:《中国礼学史(魏晋南北朝卷)》第二章,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48页。这几篇文体论既是文论,也是礼文学作品,由此可见刘勰的良苦用心。总的说来,文体论总共20篇,而关于礼学方面的即占一半以上,这些文体论既是文论作品,也是礼学批评,其中有一些还可以归为礼文学作品,可见,刘勰正是通过对这些礼学文体的批评以间接实现自己注经的梦想,以此“曲线救国”。
另一方面,从刘勰的立身行事来看,其与礼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刘勰早年“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20)〔唐〕姚思廉:《梁书》卷五十,第493页。他居于寺庙十余年,但并未落发为僧,主要利用寺庙的藏书以从事《文心雕龙》的创作,可见他是积极入世的,其在《文心雕龙·程器》篇中说:“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是以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发挥事业,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楩楠其质,豫章其干;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若此文人,应《梓材》之士矣。”可以看出,刘勰具有极其强烈的功名之心。所以《文心雕龙》成书之后,“未为时流所称。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21)〔唐〕姚思廉:《梁书》卷五十,第495页。沈约作为一代文宗,位高权重,刘勰取定于他的主要目的在于谋求仕进,所以他撰写《文心雕龙》的目的在于扬名于世,借以走上仕途。他于“天监初,起家奉朝请。中军临川王宏引兼记室,迁车骑仓曹参军。出为太末令,政有清绩。除仁威南康王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时七庙飨荐已用蔬果,而二郊农社犹有牺牲;勰乃表言二郊宜与七庙同改。诏付尚书议,依勰所陈。迁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22)〔唐〕姚思廉:《梁书》卷五十,第493页。在梁武帝天监年间,刘勰终于入仕,做了奉朝请兼临川王记室,又迁车骑仓曹参军、太末令、仁威南康王记室并兼东宫通事舍人,最后又迁步兵校尉。从他所从事的职业性质来看,都离不开对礼制的掌握与熟悉,尤其是两次做王府的记室,这需要有良好的礼学修养。而他因为当时的郊祭礼仍用牺牲,遂上表请求郊祭礼像七庙一样改用蔬果代替牺牲,并得到了批准,可见他具有实事求是的礼学精神,并具有正确的礼制判断。
值得注意的是,他兼职东宫通事舍人,深受昭明太子的爱接,这其中原因主要是他与萧统均有共同文学爱好,志趣相同。在文学主张方面,他们同属于梁代的折中一派。(23)周勋初:《梁代文论三派述要》,《文史探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8-99页;张仁青:《六朝唯美文学》第四章,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12年,第95页。但是他们的志趣相投远不止文学思想层面,还有一维重要的因素就是礼学思想的一致。《梁书·昭明太子传》记载因始兴王萧憺薨而牵涉到东宫丧礼的改定,萧统命刘孝绰议定此礼,并亲自评断了刘孝绰的意见,最后从礼学大师明山宾所议,萧统的礼论言简意赅,深入浅出,可以看出其有着深厚的礼学修养。而他编纂《文选》的标准“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也是在强调词采的前提下,以礼义为旨归,所以经他选录的文章未有不合礼义者。他在其母丁贵嫔的葬礼及丧礼中也是严格遵守礼制。曹道衡先生指出:“《梁书》本传云‘太子孝谨天至,每入朝,未五鼓便守城门开’这种做法,实即效法《礼记·文王世子》记周文王的做法。”(24)曹道衡:《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下编)第四章,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38页。可见,萧统具有浓厚的礼学思想,并始终严格遵守礼制,这固然与其性格有关,但主要还是在于他因储君的地位所接受到的儒家礼学教育有关。由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刘勰能兼职为东宫通事舍人,且受到萧统的爱接,除了文学方面的原因,应当还有礼学方面的因素。刘勰的礼学素养必定是得到了萧统的认可,甚至钦佩,是以能够得到其之礼遇,所以他们不仅属于文学思想的一系,也同属于礼学的信徒。
通过以上两个方面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刘勰尊崇礼学,并具有一定的礼学素养,《文心雕龙》的写作缘起与当时盛行的礼学也有密切的关系,如此一来,刘勰《文心雕龙》与南朝礼学在思维方式层面相通的内在原因即昭然若揭,正是刘勰因礼立义,所以《文心雕龙》在思想体系上效法南朝礼学,具有深厚的礼学蕴涵,以此形成了由内及外的思维方式。
四、结 语
学界对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的思想进行的探讨大多集中于玄学与道家思想的层面,虽然从儒学角度进行探析的理论成果也不少,但大抵将儒学作为一个整体文化形态进行探讨,而较少地从儒学的各个组成部分出发,进行分类讨论,虽然关于《周易》与《文心雕龙》的关系探讨的成果也较多,但也主要是从儒玄交汇的角度开展的。联系南朝的学术文化发展之实际形态,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玄佛合流成为一股明显的趋势,这表明玄学业已失去其在魏晋思想界的主导地位,而儒学随着皇权的复振而复兴,礼学更是因为其顺应时势的优点而得到社会上层的重视,遂发展至登峰造极之境。在这样的历史文化场域中,礼学作为权力话语自然会将意识形态、思维方式通过文论家这个媒介以注入文论作品中。《文心雕龙》的主旨思想、内容形态、思维方式皆浸润了礼学思想,彰显出深厚的礼学文化蕴涵,这是研究《文心雕龙》不可忽视的问题,明乎此,才能对《文心雕龙》思想体系的建构有一个更清晰的体认。因此,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出发,将研究视角深入到儒学内部,将研究尽量细化,方能发现以往不曾注意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