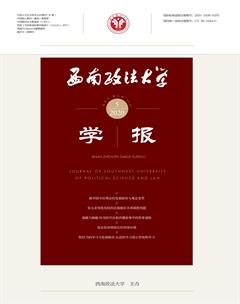论毒品重量与毒品纯度的复合立法模式
摘 要:《刑法》第357条第2款确立了以毒品重量认定毒品数量,而不以纯度折算含量的立法模式。该立法模式过度重视毒品重量,而忽视了毒品纯度在衡量毒品危害性方面的重要作用,不利于毒品案件的准确定罪量刑,是造成毒品犯罪重刑率普遍偏高的直接原因。为弥补重量认定型立法模式之不足,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刑事政策、指导意见、司法解释、案例指引等方式试图确立毒品纯度在毒品案件定罪量刑中的实际价值。司法补位措施对毒品犯罪正确定罪量刑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问题。鉴于此,应当在刑事立法上确立毒品纯度的法律地位,构建毒品重量和毒品纯度的复合立法模式,即将现行《刑法》规定的毒品数量认定标准,修改为以毒品总重量为基本标准,同时允许在部分案件中,以毒品纯度折算含量作为辅助标准。在立法上再进一步明确,毒品案件量刑时,应当考虑毒品的纯度,毒品纯度的高低,可以作为对被告人从轻、减轻或者从重处罰的依据。
关键词:毒品犯罪;毒品数量;毒品含量;毒品纯度;复合立法模式
中图分类号:DF62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20.05.08
一、问题的提出
(一)个案思考
案例1:宋某以120元的价格从上家处购买了1瓶美沙酮,然后,以150元的价格将其贩卖给左某,交易完成后被抓获。民警当场查获毒品美沙酮1瓶(净重212.3克、体积230毫升)、毒资150元。经检验,涉案毒品美沙酮溶液中盐酸美沙酮的含量为0.72mg/ml。一审法院认为,宋某贩卖毒品美沙酮212.3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第8项的规定,应认定为“贩卖其他毒品数量较大”,以贩卖毒品罪判处宋某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3000元。二审维持原判。[参见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2016)渝0109刑初154号刑事判决书、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渝01刑终379号刑事裁定书。]
该案事实清楚,判决所依据的法律及司法解释也较为明确,但涉案毒品美沙酮溶液中有效毒品成分的含量不到1‰,毒品价格只有150元,牟利数额也仅有30元,被告人宋某却被判处七年有期徒刑,量刑不可谓不重。那么,该案属于极端的特例还是普遍现象?带着疑问,笔者检索了相关类案。
(二)类案考察
1.样本选择
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随机检索了2014年到2019年间,全国法院审结的100件贩卖、运输美沙酮的案件。其中,贩卖毒品罪有87件,运输毒品罪有13件。这些案件涉及1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法院,具有相当程度的代表性。
2.考察内容
(1)涉案毒品的数量。涉案毒品美沙酮的数量在200克以下的案件有28件,200克以上的案件有72件;其中,涉案美沙酮的数量在200克以上的案件中,最低数量为201.1克,最高为2015.16克。
(2)涉案毒品的纯度。案件判决文书中明确载明毒品纯度的案件有22件。其中,纯度最高为0.94mg/ml,纯度最低为0.11mg/ml,平均纯度不到1‰。
(3)涉案毒品价格。案件判决文书明确载明毒品交易价格的案件有86件。其中,价格最高为1200元,最低仅为50元,平均价格为265元。
(4)案件的量刑。涉案毒品美沙酮的数量在200克以上的72个案件中,有70个案件的被告人被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重型率占比为97.22%,平均刑期约为七年六个月;有2件因按照毒品纯度折算了毒品数量,而判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余28个案件,因涉案毒品美沙酮溶液的重量在200克以下,被告人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
(三)类案量刑偏重
笔者认为上述类案量刑偏重,理由如下:
1.美沙酮对人体的危害性相对较低。美沙酮是二战期间德国人合成的一种镇痛药品。与吗啡比较,具有作用时间较长、不易产生耐受性、药物依赖性低的特点。“尽管被长期当作麻醉止痛药,但美沙酮却因其作为治疗海洛因毒瘾的有益药而著称。”[ [美]O·瑞、C·科塞:《毒品、社会与人的行为》,夏建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48页。]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沙酮在世界各国的戒毒机构中被广泛应用。临床实践证明,戒毒者长期服用美沙酮也会产生药物依赖性,形成瘾癖。故我国司法将美沙酮作为毒品予以规制。虽然美沙酮对人体有一定危害性,但其危害性与海洛因、甲基苯丙胺、鸦片等常见毒品的危害性不可同日而语。
2.美沙酮溶液中有效毒品成分的含量极低。任何毒品对人体的危害,均与毒品纯度成正比,纯度越大,危害越大。美沙酮也不例外。市面上经许可生产流通的盐酸美沙酮分为固体药片、注射液及口服溶液。其中,美沙酮片含盐酸美沙酮成分相对较高,而美沙酮注射液及口服溶液中盐酸美沙酮成分的含量均较低。替代治疗海洛因毒瘾的美沙酮溶液,其常见的生产规格为0.1mg/ml、0.2mg/ml、0.5mg/ml、1.0mg/ml。司法实践中查获的美沙酮,虽然来源不一,但均为液体,包含大量水分、糖分、色素等,有效成分盐酸美沙酮的含量极低,且在贩卖之前,犯罪分子在美沙酮溶液中再次加水的情况非常普遍,因此,实际查获的美沙酮溶液中盐酸美沙酮的含量往往只有1‰左右,其对人体的实际危害性被大大降低,不应科以重刑。
3.被告人牟利数额及涉案毒品价格均较小。牟利数额和毒品价格虽然不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等毒品犯罪的构成要件,但是,毒品犯罪是逐利型犯罪,毒品价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毒品在流通领域的价值,是衡量毒品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重要因素;牟利数额反映行为人犯罪的内在动因,表征了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一般而言,毒品犯罪的罪刑轻重与被告人的毒品交易价格和牟利数额存在高度关联性,毒品价格及牟利数额越高,罪刑越重,反之,则罪刑越轻。上述类案,被告人的牟利数额和毒品价格均较低,与科处的刑罚不相匹配。
二、重量认定型立法模式的反思
前述类案量刑偏重的现象,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司法裁量的尺度把握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刑法关于毒品数量认定的立法模式过于单一。
(一)毒品数量认定的立法模式
毒品数量认定的立法模式,当今世界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重量认定型立法模式和以英国为代表的纯度折算型立法模式。(1)美国的重量认定型立法模式。美国是世界上滥用毒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从1914年开始,美国陆续颁布了《哈里森麻醉品法》《化学品管制法》《预防和控制滥用毒品法》《反毒品滥用法》《反毒品走私法》等法律。2002年,美国联邦法院量刑指南第二章D部分第一节第一条列出了《毒品数量表》。该《毒品数量表》规定:“除非另有规定,表中所列的受管制物质重量是指任何混合物或物质的重量,此混合物或物质中含有可检测数量的受管制物质。如果混合物中含有一种以上的受管制物质,则整个混合物或物质的重量被指定归属于導致更大罪级的受管制物质”,“高纯度的受管制物质、复合物或混合物的交易可以成为加重责任的根据,除本指南本身对纯度已有规定的安非他明、苯环哌啶、甲基安非他明以外。”[ 魏春明:《英美两国毒品纯度与量刑分析》,载《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第36-37页。]简而言之,毒品数量不以纯度折算,除非该规定列举的安非他明、苯环哌啶、甲基安非他明等特定毒品折算成纯品量刑更重的,则应当以纯度折算;对于纯度高的毒品,量刑时可以从重或加重处罚。(2)英国的纯度折算型立法模式。英国滥用毒品的情况也十分严峻。英国现行有效的成文禁毒法律有两部,分别是1971年制定,1979年修正的《滥用毒品法》和1986年颁布的《贩毒罪法》。上述禁毒法律根据毒品的危害性不同,将毒品分为甲、乙、丙三个等级。其中,甲级毒品是包括海洛因、鸦片、可卡因等种类的硬毒品;乙级毒品是包括巴比妥类镇静剂、安非他明、大麻等种类的软毒品;丙级毒品是包括咖啡因、三唑仑等的精神药物。贩卖三种等级的毒品均以纯度折算含量后认定涉案毒品数量。英国刑事法院量刑指南和多个判例表明“输入(importation)海洛因数量是基于100%纯度的数量计算,输入500克以上海洛因,处10年以上监禁;5公斤以上海洛因,处14年以上监禁。与此相同,输入摇头丸、安非他明都是基于100%纯度的数量计算。众所周知,100%纯度的毒品在现实中几乎是不存在的,不纯的海洛因、摇头丸、安非他明需要折算成100%纯度的同样毒品,以折算后的数量定罪量刑”。[ 魏春明:《英美两国毒品纯度与量刑分析》,载《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第36-37页。]
(二)我国毒品数量认定的立法模式
1997年修订《刑法》时,关于毒品数量认定的立法模式究竟是采取重量认定型还是纯度折算型产生过争议。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刑法征求意见稿》第318条关于毒品数量不以纯度折算的规定有利于从严打击毒品犯罪。另一种意见认为,毒品的纯度不同,危害程度不同,量刑也应当不同。司法实践中缴获的毒品纯度是很悬殊的,如果仅规定以毒品的数量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而不看毒品的纯度,既不符合实际情况,也容易给实践中的执法工作造成失误,特别是一些涉及死刑的案件,故建议删除此款规定。立法机关最终采纳了第一种建议,在《刑法》第357条第2款规定:“毒品的数量以查证属实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的数量计算,不以纯度计算”。[ 高铭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诞生和发展完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80页。]
对该条文的理解,从文义解释角度,毒品数量的计算,原则上不考虑毒品中有效药物成分的占比、药理作用的程度、实际药效、药物依赖性、戒断性等因素,只要性质上属于毒品,就应当以查证属实的数量予以认定,而不能以纯度折算。从体系解释角度,(1)涉案毒品总重量是入罪标准。如非法持有毒品罪中,行为人持有鸦片200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10克即可入罪,而不论毒品纯度大小。(2)涉案毒品总重量是量刑标准。如《刑法》第347条规定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不同法定刑档次,均以涉案毒品重量作为最主要的区分标准。
由此可见,我国《刑法》关于毒品数量认定的规定与美国的立法模式类似,均采取的是重量认定型立法模式。该立法模式强调查证属实的毒品总重量是认定毒品数量的唯一标准。基于刑事立法的刚性规定,长期以来,在司法实践中,毒品数量一直是毒品案件定罪量刑的核心考量因素,与之密切相关的毒品纯度因素在定罪量刑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毒品纯度无论在毒品案件的定罪还是在量刑上的作用都显得微不足道。
(三)我国重量认定型立法模式的缺陷
1.导致毒品犯罪的定罪量刑“唯数量论”倾向
无须借助高深的化学知识,仅从常识上判断,相同种类,相同数量的毒品,如果纯度不同,其社会危害性当然不同,纯度高的毒品社会危害性大,纯度低的毒品社会危害性小,这是显而易见的。正因如此,刑事立法不能片面强调毒品重量的价值而忽略毒品纯度的价值。刑法确立的重量认定型的单一立法模式,导致毒品犯罪的定罪量刑存在“唯数量论”的倾向,毒品犯罪的量刑过程甚至蜕变为简单的数字运算,违背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精神。《刑法》第61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该规定要求刑罚裁量应当坚持罪责形式评价与实质评价的统一,反对唯单一情节论。在毒品犯罪中,毒品纯度和毒品重量均直接关乎毒品犯罪的社会危害性,都应当是最重要的实质评价标准。诚然,现行的重量认定型立法模式为从严打击毒品犯罪提供了效率保障,但无法兼顾毒品纯度与毒品危害性之间的正比例关系,这是个客观事实。一般而言,对于毒品纯度适中、既不显著偏高也不显著偏低的毒品,以毒品总重量衡量该毒品的危害性程度,基本符合实际情况。但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查获的掺杂掺假严重的毒品、有效毒品成分极低的液体毒品、混合毒品、法律无定罪量刑标准的新型毒品、国家定点企业按照标准规格生产的麻精药品流入社会的,往往毒品数量很大,且成分复杂、毒品纯度极低。同时,近年来,公安机关也查获了大量毒品纯度极高的毒品,危害性极大。无论是纯度极低还是极高的毒品,以“查证属实的毒品数量”认定涉案数量,都难以真实反映贩卖毒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从而导致具体案件的量刑失衡,背离罪责刑相适应的精神。特别是涉案的毒品数量达到死刑标准的,倘若不考虑毒品纯度,将严重背离我国“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死刑政策。
2.造成毒品犯罪的重刑化
无论是以美国为代表的重量认定型立法模式还是以英国为代表的纯度折算型的立法模式,均与两国关于毒品犯罪的刑罚相对轻缓相适应。在美国,非法制造、输入、输出或买卖100公斤海洛因,或500公斤可卡因或1.5公斤“快克”或每年贩卖毒品获利在50万美元以上的犯罪分子,才可能被判处20年监禁。在英国,毒品犯罪的法定最高刑为终身监禁,非法持有毒品罪的最高刑罚是7年监禁。生产、提供、进出口或意图提供而持有甲类毒品,根据毒品的数量,刑罚的幅度为10年以下监禁、10年以上监禁、14年以上监禁或不限金额的罚金。输入经纯度折算后5公斤以上的海洛因,才处14年以上监禁。正是基于英美两国毒品犯罪的刑罚相对轻缓,其单一型立法模式的弊端并没有那么突出。尽管如此,在两国国内,针对单一型立法模式造成量刑不准确问题的批评从未停息。
我国刑罚体系与英美两国截然不同。《刑法》针对毒品犯罪规定的刑罚相对英美两国要严苛得多,如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1000克以上海洛因或甲基苯丙胺50克以上,即应当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非法持有海洛因或甲基苯丙胺50克以上,即应当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同时,对于毒品犯罪的量刑规则,还在累犯的基础上,规定了毒品犯罪再犯,简化了累犯关于前罪必须是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和前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被赦免以后五年内再犯应当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严格限制条件,直接规定因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过刑,又犯毒品犯罪的,从重处罚。可见,我国《刑法》关于毒品犯罪的刑罚配置及量刑规则相当严厉。如果毒品犯罪案件办理当中不将毒品重量与毒品纯度综合考虑,势必造成毒品案件整体量刑偏重。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全国毒品犯罪的量刑数据。2012年到2016年,全国毒品犯罪案件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重刑率为21.91%,各年度的重刑率平均高于全部刑事案件总体重刑率约12个百分点。在毒品犯罪高发的云南省,2012年到2016年毒品犯罪的重刑率高达71.08%,高出全部刑事案件总体重刑率49.17个百分点。2017年,全国毒品犯罪案件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重刑率为21.93%,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高出全部刑事案件总体重刑率7.89个百分点。[ 以上数据详见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禁毒工作白皮书》(2012-2017)、《司法大数据专题分析报告之毒品犯罪》。]毋庸讳言,我国《刑法》确立的重量认定型立法模式是毒品犯罪重刑率过高的最直接原因。
三、毒品纯度对毒品案件定罪量刑的实际作用考察
为实现司法公正,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刑事政策、指导意见、司法解释、案例指引等形式试图弥补重量认定型立法模式的不足,明确毒品纯度因素在毒品案件定罪量刑上的应然价值。
(一)毒品纯度的司法补位梳理
1.特定涉案毒品直接以含量折算数量
司法实践中经常查获具有药用价值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被用于毒品犯罪,如医用杜冷丁、盐酸二氢埃托啡等。这类“药品中水分、淀粉、糖分、色素等成分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有效药物成分的含量较低,如果根据药品的总重量认定涉案毒品数量,势必同毒品成分的实际数量有明显差距,难以体现罚当其罪。”[ 叶晓颖、马岩、方文军、李静然:《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法》2016年第13期,第22页。]故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颁布的《关于审理毒品案件定罪量刑标准有关问题的解释》,“以括号标注的方式规定,对医用杜冷丁、盐酸二氢埃托啡针剂及片剂,要求按照药品中该类毒品成分的含量认定涉案毒品数量。”[ 叶晓颖、马岩、方文军、李静然:《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法》2016年第13期,第22页。]后来,又“考虑到其他由定点企业生产但流入非法渠道的麻精药品,也应当采用这种毒品数量认定方法”,[ 叶晓颖、马岩、方文军、李静然:《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法》2016年第13期,第22页。]故2016年颁布的《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6年毒品解释》)第1条第2款明确规定:“国家定点生产企业按照标准规格生产的麻醉药品或者精神药品被用于毒品犯罪的,根据药品中毒品成分的含量认定涉案毒品数量”。这种对特定毒品采取纯度折算含量的方式计算毒品数量的解释方法属于拉伦茨所说的“目的论的限缩”,即“法定规则—违反其字义—依法律目的应予限制,而法律文本并未包含此项限制,添加合乎意义要求的限制。借此,因字义过宽而适用范围过大的法定规则,将被限制仅适用于依法律目的或意义脉络宜于适用的范围。”[ [德]卡尔·拉伦茨:《法律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67页。]这种解释虽然可以使案件的裁判结果达致公正的目的,但无疑牺牲了法律条文文義的刚性约束。
2.死刑案件定罪量刑必须考虑毒品纯度
毒品纯度问题直接关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如果毒品数量达到判处死刑的标准,但毒品纯度低的,能否判处死刑,各地法院曾经有过争议。为统一该问题的认识,2000年《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南宁会议纪要》)规定:“掺假之后毒品的数量才达到判处死刑标准的,对被告人可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2007年,“两高一部”联合出台的《关于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2007年毒品意见》)规定:“可能判处死刑的毒品犯罪案件,毒品鉴定结论中应有含量鉴定的结论。”2008年,《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大连会议纪要》)重申上述意见。系列指导意见是全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探索形成的共识。第一,明确掺杂掺假之后的毒品即使达到了死刑数量标准,也可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本质上是对毒品纯度价值的确认,认可纯度低的毒品危害性达不到罪行极其严重的程度。第二,对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涉案毒品进行含量鉴定,明确了毒品纯度对死刑适用具有重要制约作用。这是对重量认定型立法模式的创新和突破。实践证明,该系列指导意见对限制和控制毒品案件的死刑适用作用明显。
3.掺杂掺假或成分复杂及未查获实物的毒品案件的量刑考量
《南宁会议纪要》规定:“对于查获的毒品有证据证明大量掺假,经鉴定查明毒品纯度极少,却有大量掺假成分的,在处刑时应酌情考虑”。《大连会议纪要》进一步规定:“对涉案毒品可能大量掺假或者系成分复杂的新类型毒品的,亦应当作出含量鉴定”。2015年《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武汉会议纪要》)进一步规定:“对于未查获实物的甲基苯丙胺片剂、MDMA片剂等混合毒品,可以根据在案证据证明的毒品粒数,参考本案或者本地区查获的同类毒品的平均重量计算出毒品数量”,且“涉案毒品纯度明显低于同类毒品的正常纯度的,量刑时可以酌情考虑”。以上规定均基于审判实践的现实需要采取的符合司法规律的务实措施。以走私海洛因为例:走私海洛因案件在实践中占比很高,一般而言,走私入境的海洛因纯度很高。但是近年来毒贩为谋取更高的利润,在海洛因中掺杂掺假现象越来越多,因此,实践中查获走私的海洛因纯度差别很大。这种情况下,如不做毒品含量鉴定,对纯度高的和纯度低的毒品在量刑时等同视之,看似发挥了严厉惩治毒品犯罪的作用,实际上显失公平。
4.混合毒品及法律法规未规定定罪量刑标准的毒品案件的定罪量刑考量
(1)涉及混合毒品的案件。《大连会议纪要》规定:“对于含有两种以上毒品成分的毒品混合物,应进一步作成分鉴定,确定所含的不同毒品成分及比例。对于毒品中含有海洛因、甲基苯丙胺的,应以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分别确定其毒品种类;不含海洛因、甲基苯丙胺的,应以其中毒性较大的毒品成分确定其毒品种类;如果毒性相当或者难以确定毒性大小的,以其中比例较大的毒品成分确定其毒品种类,并在量刑时综合考虑其他毒品成分、含量和全案所涉毒品数量”。以摇头丸类毒品案件为例。近年来,摇头丸类毒品案件较为常见。对查获的摇头丸的化学成分进行分析,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标准型,主要含有纯度较高的MDMA、MDA等若干苯丙胺类毒品、苯丙胺类衍生物以及其他化学物质相混合制成的片剂。第二类是混合型,化学成分很复杂,有甲基苯丙胺、大麻、海洛因、咖啡因、麻黄素、解热止痛药等成分。[ 高贵君主编:《毒品犯罪审判理论与实务》,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134页。]这种情况下,如果仅以其中一种化学成分认定毒品数量显失合理,必须在含量鉴定的前提下,考虑不同成分的毒性、种类占比等因素后确定。
(2)法律法规未规定定罪量刑标准的毒品案件。《大连会议纪要》规定:“对于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刑法、司法解释等尚未明确规定数量标准,也不具备折算条件的,应由有关专业部门确定涉案毒品毒效的大小、有效成分的多少、吸毒者对该毒品的依赖程度,综合考虑其致瘾癖性、戒断性、社会危害性等依法量刑。因条件限制不能确定的,可以参考涉案毒品非法交易的价格因素等,决定对被告人适用刑罚”。《武汉会议纪要》进一步规定:“对于既未规定定罪量刑标量标准,又不具备折算条件的毒品,综合考虑其致瘾癖性、社会危害性、数量、纯度等因素依法量刑”。
(二)司法补位难以解决毒品纯度立法缺失的问题
应当说,司法补位措施对于改善毒品重量认定型立法模式的弊端发挥了积极作用,对毒品案件正确定罪、准确量刑意义重大。但是,鉴于毒品纯度的立法缺失,司法补位措施的作用有限。
1.毒品案件办理中酌情考虑毒品纯度,缺乏刚性约束
对于涉及死刑的毒品犯罪案件,毒品纯度因素发挥了厘定生死界限的重大作用,对限制死刑适用的效果显著。但对于其他大部分非死刑案件而言,毒品纯度依旧未能有效发挥其制约定罪量刑的实际作用。尽管刑事司法政策一再要求在特定毒品案件量刑中酌情考虑毒品纯度,甚至综合考虑毒品的致瘾癖性、戒断性、社会危害性、价格等因素,但毒品纯度并无法律上的地位,无法以裁判规则的形式强制法官必须遵守。基于刑法规范在法律效力上的优位性,毒品总重量始终是毒品案件量刑考量的决定性因素。当毒品总重量已经确定,法官仅可以在与之对应的刑法条文规定的法定刑幅度内量刑。鉴于毒品案件涉案毒品数量往往较大,对应的基准刑本就偏高,即使考虑了毒品纯度低的因素,量刑仍会显著偏重,倘若被告人再有一个或多个从重处罚情节,就更不可能因毒品纯度低而从轻处罚。因此,司法实践中,毒品纯度对毒品犯罪的量刑轻重影响甚微,酌情考虑毒品纯度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毒品案件中量刑偏重的问题。
2.补位措施亦可能造成量刑分歧
以真实案件为例。案例2:被告人龙某系吸毒人员,其在戒毒中心接受免费美沙酮维持治疗过程中,借机将美沙酮带出。后龙某经电话联系,将多次积攒的1小瓶毒品美沙酮溶液贩卖给唐某。交易完成后,被民警抓获,当场查获疑似毒品美沙酮溶液1小瓶(净重211.55克、体积215毫升)、毒资300元。经检验,涉案毒品美沙酮溶液的含量为0.78mg/ml。一审以龙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二审维持原判。[参见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2015)碚法刑初字第00601号刑事判决书、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渝01刑初1号刑事裁定书。]
与案例1比较,两个案件犯罪性质相同,被告人宋某和龙某均无前科,贩卖毒品美沙酮溶液的体积及重量基本相同,涉案毒品中有效成分盐酸美沙酮的含量亦大致相同,危害后果相当,牟利数额都不大,犯罪主观方面一致。量刑显著差异的原因在于毒品数量认定标准不同。根據《2016年毒品解释》)第1条第2款的规定,同种成分且纯度相同的特定毒品,如果属于国家定点生产企业按照标准规格生产的麻精药品而被用于毒品犯罪的,应根据药品中毒品成分的含量认定涉案毒品的数量,反之,如果不是或没有证据证明是国家定点生产企业按照标准规格生产的麻精药品被用于毒品犯罪的,则应当按照毒品的总重量认定毒品数量。
在案例1中,因无证据证实被告人宋某贩卖的美沙酮溶液系定点企业按照标准规格生产流入非法渠道的,依据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精神,对宋某贩卖毒品数量的认定,应以查证属实的美沙酮溶液的重量计算,即宋某贩卖毒品美沙酮的数量是212.3克,应当认定为“贩卖其他毒品数量较大”。故一审法院根据刑法第347条第3款的规定判处宋某有期徒刑七年。而案例2中,因有证据证实龙某的毒品系从戒毒中心流出,属于国家定点企业按照标准规格生产的精神药品,根据《2016年毒品解释》第1条第2款的规定,毒品数量应当以涉案毒品中美沙酮成分的纯度予以折算。经计算,龙某贩卖毒品美沙酮的数量不足1克,再按照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颁布的《非法药物折算表》折算成海洛因后,数量更低,故一审法院依据《刑法》第347条第4款的规定,判处龙某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因毒品数量认定标准的差异,导致两个类似案件的量刑结果出现天壤之别。这种因填补规则漏洞而产生新的漏洞的情况,想必是补位措施出台前始料未及的。
3.高纯度毒品的从重处罚缺乏法律依据
根据前述刑事司法政策,毒品纯度显著偏低的,量刑时应考虑毒品纯度因素后酌情从轻处罚。但是,对于毒品纯度显著偏高的是否从重处罚,目前未有法律或司法解释作出明确规定。众所周知,近年来,随着化学工艺的进步,犯罪分子的制毒工艺也随之显著提升,司法实践中查获高纯度毒品司空见惯。相对于普通毒品,高纯度毒品的危害性显然更大,吸食高纯度毒品可能给吸食者造成致命伤害,吸食者单日吸食1克高纯度的海洛因或甲基苯丙胺就足以致死。[ 刘一亮、伍凌、戴粤:《毒品犯罪中的毒品纯度价值之提倡》,载《中国检察官》2014年第12期。]鉴于高纯度毒品的严重社会危害性,量刑时应当与普通毒品有所区分,予以从重处罚。但应当如何从重、从重的幅度以及是否可以加重处罚等操作层面的问题,都必须结合毒品纯度予以确定。因为毒品纯度的立法缺失,高纯度毒品的从重处罚等问题亦未有具体明确的法律依据。
4.超出刑法条文的文义射程,超越解释权限
毋庸讳言,司法解释及指导意见将特定毒品的数量以纯度折算的规定,实质上突破了刑法条文关于毒品数量认定的规定,创设了毒品数量认定的新标准。虽然从目的和效果上看,这种突破适应了审判实践的实际需要,符合实质公正的要求。但是,这些突破性规定超出了刑法的文义射程。“法律解释者都希望,在法律中寻求其时代问题的答案”。[ [德]卡尔·拉伦茨:《法律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99页。]寻求时代问题答案的途径往往是投向客观目的解释论的怀抱。“在刑法上,目的性论据经常是逾越文义的去限缩或扩大一个构成要件的适用范围”。[ [德]英格博格·普珀:《法学思维小学堂》,蔡圣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0页。]虽然客观目的解释结论能够使案件处理结论符合实质正义的诉求,但是,其对法的安定性的损害也是不可忽视的。笔者认为,任何解释结论必须谨守法律条文的文义范围。正如迈尔·海奥茨指出的“字义具有双重任务,它既是法官探寻意义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划定其解释活动的界限,字义可能范围外的说明,已经不再是解释,而是改变其意义”。[ [德]卡尔·拉伦茨:《法律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02页。]《刑法》第357条第2款的规定,查证属实的毒品数量是认定涉案毒品数量的唯一方法,即使适用该计算方法可能造成个案及类案的量刑不公,仍然不能逾越刑法的规定,如需突破,必须依照法定程序修改刑法条文。固守文义射程既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当然要求,也是司法解释的应然边界,亦符合立法法关于两高解释权限的限定。根据立法法的相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仅有权对审判和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作出解释,而增设新的毒品数量认定标准,则属于法律续造的范畴,应当由立法机关通过修改立法予以实现,司法解释无权作出规定。
四、破解:重构毒品数量认定的立法模式
前述问题的症结是刑事立法没有重视毒品纯度的应然价值,没有理顺毒品数量和毒品纯度之间的逻辑关系,因此,重构毒品数量认定的立法模式,确立毒品纯度在刑法上的价值势在必行。
(一)毒品纯度的立法价值
1.促进毒品犯罪的治理模式由粗疏转向精细
新中國成立以来,我国曾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无毒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边境开放,外资进入,境内外人员交往的频繁,境外贩毒集团乘机向我国渗透,受国际毒潮持续泛滥和国内开放等多种因素影响,我国毒潮再兴,毒品犯罪再发。有鉴于此,为遏制毒品犯罪快速蔓延,1990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关于禁毒的决定》,将查证属实的毒品数量作为毒品犯罪定罪量刑的核心依据予以规定,为从严打击毒品犯罪确立了简明有效的法律依据。该毒品数量认定标准被1997年《刑法》所吸收,一直沿用至今,在惩治毒品犯罪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见,现行从严从重从快的毒品犯罪治理模式,并非国家任意选择,而是基于特定社会治理需要和特殊社会环境及国家在特定时期的犯罪治理能力的现实抉择。
当前,我国的社会环境和犯罪治理能力显著改善,对于毒品犯罪的治理应当坚持从严惩处原则的同时,更加注重综合治理和精准打击,加大源头性毒品犯罪和严重毒品犯罪分子的惩处力度,注重个案的刑罚适用效果。众所周知,刑罚的威慑力取决于多种因素,刑罚的确定性是威慑力的基础,正如贝卡利亚所言“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 [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72页。]刑罚的确定性胜于严刑峻法。美国学者威尔逊和凯林提出的“破窗理论”证明,犯罪与秩序的失控有直接关系,控制犯罪的着力点应当是在铲除诱发犯罪的土壤基础上精准打击犯罪,提升案件侦破率,做到有罪必罚,提高犯罪成本,而不能仅仅倚重严苛刑罚的适用。因此,在毒品犯罪治理的目标转向的背景下,应当重新审视刑法关于毒品犯罪治理的具体规定。显然,《刑法》第357条第2款规定的毒品数量的单一型认定标准,已无法适应新的毒品犯罪治理目标以及精准打击毒品犯罪的现实需要。因此,从规则层面引入毒品纯度以弥补毒品数量认定标准之不足,力求实现精准量刑,乃刑事立法与司法由粗疏化向精细化转化的必然要求。
2.促使刑罚资源有效配置
法经济学认为,刑罚是一种稀缺的公共资源。“稀缺这一事实存在于经济学的核心之中。没有一个社会达到了一种无限供给的乌托邦。物品是有限的,而需求则似乎是无限的。”[ [美] 萨缪尔森:《经济学》,胡代光等译,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在现代国家,没有任何国家的刑罚资源达到了充分供给的程度。在刑罚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应当以最合理的刑罚成本投入获取最大限度的刑罚效益。一方面,从宏观的角度,刑罚资源在整个刑罚体系中应当配置合理,动态平衡。近五年来,我国毒品犯罪案件增幅很大,从2012年的76280件增长到2016年的117561件,增幅为54.12%,是全部刑事案件整体增幅的4.12倍。[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禁毒工作白皮书》(2012-2017年)。]在刑罚资源总量有限的前提下,毒品犯罪案件的过快增长,必然导致刑罚资源向毒品犯罪过度集聚,造成对其他犯罪的刑罚适用率降低;另一方面,从微观的角度,对任何犯罪行为适用刑罚,都应当在不违背处罚必要性、公正性和平等性原则的基础上,考虑量刑的成本与收益。“刑罚的目的既不是要摧残折磨一个感知者,也不是要消除业已犯下的罪行”,“只要刑罚的恶果大于犯罪带来的好处,刑罚就可以收到它的效果,这种大于好处的恶果中应该包含的,一是刑罚的坚定性,二是犯罪既得利益的丧失。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是多余的,因而也是蛮横的”。[ [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52页。]数据显示,“2010年至2015年,毒品犯罪的重刑率每年均高于全部刑事案件平均重刑率10个百分点以上,其中,2013年至2015年,毒品犯罪的重刑率更是全部刑事案件平均重刑率的2倍”。[ 齐文远、魏汉涛:《毒品犯罪治理的困境与出路》,载《河南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第71页。]大面积适用重刑的情况必然导致刑罚资源整体配比失衡,造成刑罚资源浪费与配比不足同时出现,显然与刑罚的效益性要求背道而驰。因此,调整毒品犯罪的治理规则,在刑事立法上增设毒品纯度作为衡量毒品社会危害性的标准,促使刑罚资源在毒品犯罪及整个犯罪治理体系中合理有效配置,是发挥刑罚惩罚与预防犯罪的基本功能的必然要求。
3.有利于将司法经验转化为立法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刑事政策、指导意见、司法解释、案例指引等形式对毒品纯度应然价值的探索与应用,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如前述死刑案件考虑毒品纯度因素,降低了死刑适用率;在特定毒品案件中以毒品纯度折算毒品含量,实现了实质公正等。但毋庸讳言,立法与司法的职权与定位不同,各有分工。按照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在精神,规定犯罪及其后果的法律只能由立法机关制定,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无权作出规定。[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49页。]为了理顺立法与司法的关系,有必要将司法实践中探索成熟的有关毒品纯度对定罪量刑实际作用的经验转化为立法。
(二)毒品数量认定模式的重构思路
1.继承:重量认定型立法模式历史合理性
任何立法模式的选择,既是对社会现实的回应,也是历史的抉择。回顾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自晚清以降,中华民族经历的苦难莫不与毒品泛滥存有关联。18世纪末,英国为了扭转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向中国走私鸦片,导致烟患泛滥。“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第一卷),第4页。]“食者愈众,几遍天下”。[ 梁思和整理:《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0页。]鸦片的大量输入,戕害人的健康,麻痹人的智力,摧毁人的意志,造成社会劳动力萎缩,军队丧失战斗力,官僚阶层更加堕落腐败,工商业凋敝,白银外流,清政府国库空虚,税赋日苛,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洋烟之为害乃今日之洪水猛兽也。然而殆有甚焉。洪水之害,不过九载,猛兽之害,不出殷都。洋烟之害,流毒百余年,蔓延二十二省,受其害者数十万万人,以后浸淫,尚未有艾”。[ 贺长龄、魏源编:《皇朝经世文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二十四卷第8页。] 鸦片问题动摇了清政府的国本。1839年,林则徐奉旨在广州虎门销烟,触动了英国的巨额非法利益。英国悍然发动鸦片战争。清政府乞和,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接受了英国割地赔款的全部要求,开启了中华民族屈辱史的序幕。此后一百年,国家内忧外患,社会动荡不安,政权频繁更迭,四海民不聊生。据不完全统计,1923年至1934年,全国吸毒人口约800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6.8%。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日军鼓励、纵容沦陷区民众吸毒,沦陷区内吸毒人口高达3200万,吸毒导致的沉沦使得中华民族险被亡国灭种。
新中国成立时,仍有2000余万的吸毒人口。新中国成立后,以史为鉴,我国开展了三年的禁烟禁毒运动,彻底铲除了毒品泛滥的根源,毒品一度绝迹。改革开放以后,毒品犯罪再次泛滥,官方统计数据显示,1982年我国吸毒人数不足千人,到1989年上升到7万人,1991年攀升到14.85万人,1995年跃升到52万,以后,每年以10%左右的增速递增。巨大的毒品需求导致毒品犯罪案件猛增。[参见苏智良:《中国毒品史》,上海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版,第398页。]1988年,公安机关破获毒品案件268起,到1992年已达69060起,四年猛增257倍,此后,更是节节攀升。[参见苏智良:《中国毒品史》,上海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毒品犯罪的现实威胁,国仇家恨的历史记忆,对民族危亡的忧虑,对国家未来的关切,无不左右著立法者的立法抉择。于是,1997年《刑法》修订时,延续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正式确立毒品数量的重量认定型立法模式。该立法模式简单好用,多年来为从严从快打击毒品犯罪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虽然随着我国犯罪治理能力的显著提升,重量认定型立法模式的弊端日益突出,但是必须清楚地看到,当前我国毒品犯罪的形势仍然十分严峻。第一,现阶段的毒品犯罪率上升的趋势没有得到显著遏制;第二,我国吸毒人数仍然增长迅速;第三,境外毒品输入的压力有增无减;禁毒斗争之路仍然任重道远。在这种背景之下,不能武断地将现有重量认定型立法模式推倒重来,而应当在继承现有立法模式合理成分的基础上进行适度修正,以兼顾打击毒品犯罪的效率性与公正性的双重目标。
2. 创新:增加毒品纯度规定,构建毒品重量与毒品纯度的复合立法模式
尽管我国禁毒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但是禁毒工作成效突出,禁毒的社会防控体系已经形成,毒品犯罪的审判专业化水平显著改善,毒品犯罪的精细化治理理念已经扎根,毒品犯罪的治理能力明显提升。在此背景下,重量认定型立法模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毒品犯罪治理的现代化需要。故对毒品数量认定的立法模式进行创新和重构势在必行。笔者主张,对毒品数量立法模式修正的比较务实的路径是,将现行《刑法》第357条第2款关于毒品数量以重量认定型的单一认定方式,修订以毒品总重量作为基本标准,同时允许在部分特殊案件中,以毒品纯度折算含量作为辅助标准。
就毒品纯度的折算而言,查获的毒品均应作毒品含量鉴定,根据毒品纯度的不同,分情况区别处理:第一,对于大部分涉案毒品纯度适中(5%-85%)的毒品案件,以查证属实的毒品总重量计算毒品数量,定罪量刑中不考虑毒品纯度因素的影响,从而保障惩治毒品犯罪的效率和效果;第二,对于涉案毒品纯度显著偏高(85%-100%)的毒品案件,量刑时应当从重处罚;第三,对于涉案毒品的纯度较低(1%-5%)的毒品案件,量刑时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第四,涉案毒品纯度极低的(1%以下)毒品案件,按照涉案毒品中该类毒品成分的纯度折算毒品含量,以折算后的毒品含量定罪量刑,对于以毒品纯度折算后,毒品含量极低的,综合考虑毒品纯度、主观恶性、犯罪情节后予以出罪。第五,毒品重量达到死刑标准,但是毒品纯度低的,可不判处死刑。
就折算基准而言,应当按照“同类折算,异类从重”的原则。根据《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列管办法》等法规的规定,我国列入管制的麻醉药品有121种,精神药品有149种,非药用类麻精药品156种,共计426种管制毒品。这其中大部分毒品没有明确的定罪量刑标准。对于没有定罪量刑标准的毒品,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以2004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台的《非法药物折算表》为标准,以海洛因为基准进行折算,将涉案毒品折算为海洛因的数量进行定罪量刑,但这种折算方法忽视了毒品纯度和毒品的实际毒性。以走私芬太尼为例,按照《非法药物折算表》规定的标准,1克芬太尼相当于40克海洛因,走私10克纯品海洛因和10克纯度为1%的芬太尼入境被查获,均构成走私毒品罪。按照前述折算标准,10克芬太尼相当于400克海洛因,行为人可能被判处十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但是10克纯品海洛因的法定刑是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如果考虑纯度后再折算成海洛因,10克纯度为1%的芬太尼只相当于4克纯品海洛因,应当在三年有期徒刑以下量刑。现有折算标准因未考虑纯度将导致量刑的差异过大。因此,根据前述折算规则,涉案毒品进行纯度折算之后,再通过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从《非法药物折算表》中规定的阿片类、苯丙胺类、可卡因类、大麻类、其他兴奋剂类、苯二氮卓类镇静安眠药、巴比妥类以及其他类镇静安眠药八种毒品类型中选出一个基准毒品,譬如将阿片类毒品的基准药品确定为海洛因,所有阿片类毒品犯罪的数量认定,都统一折算为海洛因;苯丙胺类毒品的基准药品确定为甲基苯丙胺,所有苯丙胺类毒品犯罪的数量认定,都统一折算为甲基苯丙胺。按照基准毒品的法定定罪量刑标准定罪处罚,不再一律折算成海洛因,基准毒品没有法定定罪量刑标准的或定罪量刑标准模糊的,通过司法解释明确规定,此即“同类折算”的原则。对于涉案毒品包含两种或者两种以上毒品的,根据纯度折算后,确定不同种类毒品的具体数量,从重处罚,此即“异类从重”的原则。
(三)具体的立法建议
建议将《刑法》第357条第2款修改为“毒品的数量以查证属实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的数量计算,必要时,毒品数量的计算可以以毒品的纯度折算”;增加以下内容作为该条第3款:“对于查获的毒品,都应作定性、定量鉴定。在量刑时,应当考虑毒品的纯度。毒品纯度的高低,可以作为对被告人从轻、减轻或者从重处罚的依据。”
五、结语
毒品数量的立法模式问题是决定毒品犯罪定罪量刑是否公正的根本问题,重量型立法模式的弊端显而易见,以毒品重量和毒品纯度复合立法模式取代重量型立法模式能从根本上改变毒品犯罪治理模式的粗疏化,改变毒品犯罪整体量刑偏重,刑罚资源配置不均衡的局面,但是,毒品重量和毒品纯度复合立法模式的设计是否符合毒品犯罪治理的实际需要,还需司法实践的验证。
Proposition for a Combined Weight-Purity Bill for
Narcotic Drug Amount Calculation
——Based on a Methadone Trafficking and Distribution Case
HUANG Xu
(Chongqing No.1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Chongqing 401147, China)Abstract:The article 357(2) of Criminal Law establishes the legislation model that the amount of drug shall be measured in pursuant to its weight, excluding any converted estimations of its purity. This legislation overemphasizes the weight of drugs, while ignoring the significant role of its purity when judging its harmfulness, thereby undermining the accuracy of the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which directly leads to the generally high rate of heavy penalty in drug crimes. In order to make up for the deficiency of the weight-based legislative model, the Supreme Court tried to establish the actual value of drug purity in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of drug cases by means of criminal policy, guidanc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and case guidance. Judicial supplementary measures have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the accuracy of the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but it also leads new problems. In view of this, the legal status of drug purity should be established in criminal legislations, and the composite legislation model of both drug weight and purity should be structured. that is to amend measure criteria of drug quantity in the current Criminal Law, taking the total drug weight as the basic standard and allowing any converted drug purity to content as an auxiliary standard in some cases. Legislations should further provid that drug purity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when sentencing for drug cases. The purity of drug can be used as a basis for a lighter, mitigated, or heavier punishment to defendants.
Key Words: drug crime; drug quantity; drug content; drug purity; mode of combined legislation
本文責任编辑:周玉芹
青年学术编辑:张永强
收稿日期:2020-08-26
基金项目:西南政法大学国家毒品问题治理研究中心(毒品犯罪与对策研究中心)研究项目“毒品含量鉴定问题研究”(DR2019J004)
作者简介:
黄旭(1967),男,四川省南部县人,重庆市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协同创新团队“国家毒品问题治理研究创新团队”成员,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