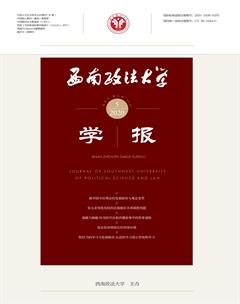新中国守法理论的发展脉络与观念变革
陆幸福 郭秉贵
摘 要:守法是法的实施的基本方式,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守法理论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阶级性法本质的影响下,形成了以守法义务为核心的传统守法理论;改革开放新时期,在对传统守法理论进行反思和检视的过程中,转向了对守法基础理论的正面建树,以法律主体性为基点的守法基础理论获得较大发展;法治建设新时代,全民守法的提出为守法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创新驱动,通过对其运行逻辑的阐释形成了以认同和肯定现行法的价值为导向的全民守法理论。与此同时,三种守法理论背后分别蕴含着消极守法、积极守法和尊法守法的守法观,两条主线交织中勾勒出新中国守法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脉络。立足当前,仍需要在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的图景中推动守法理论的发展,妥善处理守法与改革的关系、强化法治认同的根基、完善守法社会的理论构建等成为守法理论需要进一步关注的命题。
关键词:新中国;守法理论;守法观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20.05.01
引言
人们为何守法?如何守法?这是建设法治社会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也是法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等学科长期关注的问题。就我国目前的法治实践来看,立法技术日益成熟,执法和司法活动也不断加强和规范,但对于什么是促成全民自愿践行法律的内在力量和动员机制,现有的理论和具体对策方面的积累尚显不足。①鉴于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守法何以实现”。对新中国守法理论的发展历程与观念变革进行梳理,是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前提。新中国守法理论的发展作为贯穿法学学术研究的一条重要线索,与中国法理学从初步奠基到恢复发展再到不断完善的发展历程大体相似,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依据中国法学70年发展历程的主流时间段的划分,本文将新中国守法理论70年的发展也划分为新中国成立前30年(1949年—1978年)、改革开放新时期(1979年—2011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2年—至今)三个发展阶段,对应新中国成立前30年的传统守法理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守法基础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全民守法理论。]:新中国成立的前三十年,守法理论实现了初步奠基,在获得短暂发展后陷入停滞状态;改革开放新时期,守法理论逐步恢复发展,开启了守法现代化的研究进程;进入法治发展新时代,守法理论坚持守正创新,立足于全民守法及法治社会建设进一步丰富与发展。纵观这一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守法理论并非单纯为理论自发演进的过程,同时也体现出较强的制度依赖性,在与守法实践的互动中不断反思前行。因此,需要在理论——实践双向互动的图景中综合考察不同时期守法理论呈现出的特点和旨趣。整体来看,相较于对立法、司法和执法的研究,学界对守法的研究较为薄弱,这一研究现状不仅不利于守法理论本身的发展,而且还可能对守法实践的推进产生不利影响。当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我国法学界不再仅仅满足于法律法规在种类和数量上的完备,开始重点关注、思考和研究立法之后法律的实际运行,即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等问题[ 参见姚建宗:《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国法学———理论进步、形象塑造与发展动因(二)》,载《河南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第48页。],守法理论供给不足的现状正在逐渐改观。在此背景下,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守法理论的沿革,反思当前守法理论可能有哪些新的转向与突破成为本文的研究重点。
一、不同时期的守法理论及其所蕴含的守法观
(一)守法理论的初步发展时期
“废旧立新”是新中国法学面临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命题。1949年2月,党中央依据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的经验,发布了《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废除了国民党的六法全书。阶级本质的不同决定了党领导人民所建设的社会主义法制不同于旧政权下的法制,通过法律变革废除“伪法统”建立社会主义法制有其现实需要。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认了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成果,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有遵守法律的义务。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据统计,从1949年到1966年,政协会议、中央人民政府、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定法律、法令、决议及法律问题的决定127件。[ 参见许安标:《新中国70年立法的成就与经验》,载《中国人大》2019年第21期,第21页。]这一时期的立法工作,为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探索和发展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基础,为遵守宪法法律提供了明确依据。然而在具体实践中,虽然有相关的法律规定,但其内容较为原则,尚需在探索中不断具体化。各种民主改革与粉碎旧秩序的斗争,与其说是根据法律,还不如说是依靠群众的直接行动。[ 如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运动等,尽管若干法律支持了群众运动,或者说是在总结群众运动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但是它所规定的形式和内容,都还是纲领性的,甚至是大纲性的东西。参见浅井敦:《中国现代化与法律学——回顾新中国法学三十年的历史》,载《国外法学》1981年第1期,第4页。]与这一时期的立法活动及守法实践相对应,守法理论很大程度上仅关注法律规范中的守法,强调遵守宪法法律是我国人民的光荣义务。[ 参见思进:《论守法》,载《政法研究》1962年第4期,第5页。]
1.阶级性法本质下的传统守法理论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巩固政权和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发展的双重任务,守法理论肩负着为其提供保障的使命。受階级性法本质思维定式的影响,守法理论亦遵循明显的阶级斗争范式,即强迫敌人守法,说服教育公民自觉守法。守法理论中体现出“人民—敌人”的区分,人民严格遵守法律,就能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加强人民内部团结,更有力地进行对敌斗争。[ 参见柴钟麟:《关于我国过渡时期法权的性质和作用问题》,载《政法研究》1962年第3期,第29页。]只有遵守国家法律,遵守革命秩序,才不致给敌人以利用的漏洞,也才有利于孤立和打击敌人。[ 参见杨玉清:《论遵守法律》,载《政法研究》1954年第3期,第34-35页。]对于敌人,国家用强制压服的方法,强迫其服从,如果违反法律,予以坚决打击制裁。人民守法则是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觉悟越高,就越能自觉遵守法律。当然,法在人民内部也具有强制作用,但这与对敌专政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强制作用。[ 参见谦益:《关于我国过渡时期法权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方面的两点意见——与柴钟麟同志商榷》,载《政法研究》1962年第3期,第35页。]简言之,法的强制性普遍存在,只不过对于人民内部的强制在性质及方法上不同于对敌专政,人民越是自觉守法则受到这种强制力的约束和限制越小,如果人民违法犯罪,这种强制性也会体现为制裁。但这同说服教育的方法并不抵触,而是相辅相成,这种制裁只是说服教育的一种辅助手段。
2.以义务为核心的消积守法
守法是光荣、重大的任务和神圣的义务成为这一时期守法理论中的主要基调。五四宪法颁布前后,遵守宪法法律一度成为守法研究的核心主题。守法理论中体现出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将遵守宪法法律赋予崇高的使命感,遵守宪法法律成为我国公民的神圣义务。[ 参见吴家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载《教学与研究》1954年第7期,第15-16页。]为保障宪法的实施,严格地遵守宪法、法律,也是每个公民的重大任务。这种使命感的形成以社会主义法律本质上代表广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为出发点,推导出社会主义法律被接受的普遍性,具体体现为个人意志和利益自觉服从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以守法使命感的内在驱动力号召公民自觉守法。为强化这种使命感,法制发挥着说服教育的作用,成为统一人民思想和行动的工具——告诉人们这样做是符合人民利益和社会主义利益的,那样做是不符合人民利益和社会主义利益的。[ 参见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国家与法权理论教研室:《论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民主法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66—176页。]集体意志和利益驱动下的守法,将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法律只是一种管制和束缚的工具,人民对于法律的享有和运用,只能通过外部的灌输,法律要求他们关心的只是社会和集体的利益。”[ 孔小红:《中国法学四十年略论》,载《法学研究》1989年第2期,第49页。]使命感驱使下的守法难以体现出公民守法的主体性意识,也忽略了个人意志和利益与集体意志和利益之间不可避免的差异。以“义务”为核心的守法,本质上是一种消极守法,将法律规范视为外在的约束力量,只注重遵守法的词句而忽略其精神,认为法律中的“善”就是“服从”。[ 参见胡旭晟:《守法论纲——法理学与伦理学的考察》,载《比较法研究》1994年第1期,第11页。]
(二)守法理论的恢复与快速发展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历史新时期,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重新步入发展正轨。1979年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七部重要法律,拉开了新时期立法工作大幕。[ 1979年6月18日至7月1日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七部重要的法律。]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现行宪法,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此后,为满足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立法工作全面推进。为顺应改革开放和法制现代化潮流,守法观念也必须更新,只有观念的更新、变革,才能从根本上形成以改革为动力、为出发点和归宿的自觉守法观念。要真正使法制迸发出强大的力量,仅凭以不违法犯罪为底线的消极守法是难以实现的,需要一种更为积极的守法观,敢于、善于为改革而与一切違法犯罪现象作坚决斗争。[ 参见倪正茂:《论改革时期精神文明建设的法制需求》,载《法学》1986年第11期,第9页。]以改革之精神,转变守法之观念,由消极守法到积极守法成为新时期守法理论发展的重要转向。思想解放积极助推着这一转向,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开启了反思、怀疑和批判的新风,引发了对传统守法理论的检视与反思;“法本位”讨论引起法学界的关注,逐渐明晰了以权利和义务重构法学理论体系的途径和方向,亦为守法理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守法不仅意味着承担义务,享有权利也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伴随着观念的转变,学界逐步转向了对守法基础理论的正面建树。
1.守法基础理论研究
新时期的守法理论研究伴随着对传统守法理论的反思与检视而展开。以义务为核心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守法的传统守法理论逐渐遭到挑战,原因在于该理论仅仅把守法个体视为法律治理的客体,也即法律义务主体而非权利主体[ 参见黄竹胜:《对我国守法理论研究的方法论检讨》,载《法律方法》2002年第1期,第443页。],这一理念不利于充分调动守法主体的积极性,难以适应改革、发展的需求。面临为改革开放及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保障的现实需求,亟待探寻适合社会发展的守法理论。在对传统守法理论进行反思与检视的过程中,学界开始系统地阐释守法的概念、范畴、原理等基础理论。守法的概念内涵方面,既包括履行义务,也包括行使权利。尽管这一时期对守法的概念仍有各种不同的定义,但至少在两层含义上达成基本共识:一是依法享有权利并行使权利,二是依法承担义务并履行义务。守法的主体方面,既要求公民守法,也要求执政党和政府守法。执政党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对法的实施具有重要作用,对于法的实现也具有重要意义[ 参见童之伟:《执政党模范守法是实现法治之关键》,载《法学》2000年第7期,第2页。]。相较于公民守法,政府守法更为本质、也更为关键。政府守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消极不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二是积极排除一切阻碍法的实施的因素,保障守法主体的权利得以实现。守法的范围方面,随着各级立法机关积极开展立法工作,守法范围不断扩展。守法范围取决于一国的法律渊源,除此之外,一些非规范性文件,如有权国家机关依照法律程序依法制作的判决书、裁定书及合法有效的契约也属于守法的范围。[ 参见李龙:《法理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49页。]当正式的法律渊源不能满足社会的现实需求或与社会成员、社会群体的普遍观念脱节时,也会产生实际遵守习惯法、道德原则、公共政策等的“隐性守法”。[ 参见胡旭晟:《守法论纲——法理学与伦理学的考察》,载《比较法研究》1994年第1期,第2-3页。]随着守法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跨学科研究成果也开始显现。守法的经济学分析认为守法的内在动因是一套经济学逻辑,降低守法成本提高违法成本成为法律得以普遍遵守的一个维度。[ 参见游劝荣:《守法与守法成本间的“反比例关系”研究》,载《福建法学》2006年第3期,第2页。]守法的社会学分析关注社会关系中影响守法的具体因素,强调综合法律规范和各种社会力量保障守法。[ 参见封曰贤:《守法社会学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载《法学》1988年第12期,第11-13页。]守法的心理学分析通过研究守法行为的心理因素、结构等,寻求预防、控制和减少违法犯罪的措施。[ 参见王晓烁、刘庆顺:《守法行为的心理因素分析》,载《河北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第73页。]守法的伦理学分析将守法与道德紧密联系起来,从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相转换的视角来研究守法问题。[ 参见陈巧玲:《试论道德是法运行的重要保障》,载《学术界》1997年第5期,第57页。]总之,在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中,守法理论的系统性、综合性、包容性不断增强。
2.以主体性为基点的积极守法
传统守法理论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来观察社会成员的守法过程,因而忽视了守法个体接受法律过程的主体性。法律在社会实际生活中要得以实施,除需要以国家强制力作为保障之外,同样需要在守法主体中内生出自觉守法的力量,也即守法主体基于自身的意志、要求和利益,主动、自觉地守法。正是在此意义上,有学者将公民守法的过程视为一个法律主体性意识的建构过程,强调以人的主体性为基点来构建守法理论。[ 参见黄竹胜:《对我国守法理论研究的方法论检讨》,载《法律方法》2002年第1期,第448页。]这种过程论的视角是将公民作为法律主体而论的,而非法律的客体。主体性意识驱动下的守法,不仅要求守法主体遵循法律规范并将其作为行为准则,更强调对人的主体性的彰显,对法律规范内在精神的把握也不仅是外在力量灌输下单方面的被动接受,更多的是一个主动吸取与接纳的过程。[ 参见刘同君:《论和谐社会语境下公民守法的道德机制》,载《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6期,第107-108页。]以主体性为基点的守法,为守法理论回应社会实践提供了新的动力源泉。从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基础理论出发,守法不仅要求履行义务,也强调积极行使权利,主体性因素不断增强。具体而言,积极守法主要体现在“用法”和“护法”两个层面,这种语境下的守法已超越了“遵守”的字面含义,而要求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来对待法律。“公民用法”反映的是一种法治理念,意味着公民与法进入了一种新的关系形式,这种新的关系形式的本质在于公民与法的融合,公民精神与法律精神的一体化。[ 参见关保英:《公民用法问题研究》,载《东方法学》2010年第5期,第9页。]公民用法的过程中,其作为法律主体的主动性也贯穿于始终。“护法”是对守法更深层次的要求,既包括遵守法律、维护法律等基本意蕴[ 参见冯粤:《论积极守法》,载《伦理学研究》2008年第3期,第11-12页。],亦有促进法律不断完善之期冀。
(三)守法理论的创新与深入发展时期
全民守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础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开启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新时代。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正式把“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确认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当遵循的“新十六字方针”。全民守法的提出,是对守法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如何深入阐释全民守法的基本理论并作出相应的制度回应,是推进法治社会建设的关键所在。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从更加全局和系统的角度出发,全民守法基本理论阐释呈现出主体——客体——运行——保障的逻辑进路,法治认同成为其基本的理论内涵。在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的过程中,公民对制定良好的法律普遍地认可和接受,是推动法律体系向法治体系转变的内在支撑。这种认可和接受不是被动地服从,而是实现公民与法的互动,即法律符合民众的价值期待、满足民众的现实需求,民众从而认可法律、尊重法律、服从法律。
1.全民守法基本理论阐释
厘清守法的主體层次是理解全民守法的逻辑起点。全民守法要求全社会都要守法,中国共产党是守法的带头者和模范示范者,行使国家公权力的各级机关和公务人员是守法的重要力量,普通民众是守法的最广泛主体。[ 参见杨春福:《全民守法的法理阐释》,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年第5期,第66页。]首先,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带头尊崇法治、敬畏法律。其次,政府守法和领导干部守法是全民守法的关键。政府守法要求政府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践行法治并促进守法,政府守法最终要落实到个人的行动上,领导干部作为重要组织者、推动者、实践者,是法治动力体系中的“关键少数”,其法治自觉程度直接影响到法价值的实现程度[ 参见钟慧容、陈宗波:《“关键少数”的法治自觉及其成长路径》,载《社会科学家》2018年第5期,第109页。],需要把对法治的尊崇、对法律的敬畏真正转化成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最后,普通民众是守法的最广泛主体,公民个体守法是全民守法的基础和前提,法治社会的建设离不开具有守法意识的每一个公民。厘清守法的主体层次,为不同守法主体提供了明确的角色定位和行动指南。
明确守法的客体要求是推动全民守法的基本前提。良法是守法之前提,关于良法标准的界定主要有两条进路:形式法治观下的良法注重其合法性的正当来源和形式,实质法治观下的良法强调对法律内容(价值)的要求。但这二者的区分并非是绝对的,形式良法往往也有实质的意涵,实质良法也有形式要求。尽管对良法的标准和内涵的认识不尽相同,但对于全民所守之法为良法已是基本共识。即使承认全民都有遵守良法的义务,全民守法仍有可能遭遇困境,原因在于很难保证所有法律及法律中的所有条款都是优良的。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在法律可能出现不公的情况下,公民是否可以不服从。对此,学者们持审慎态度。如果因为不符合道德,某项规则即使是国家通过立法程序制定的也可以不加遵守,可能导致无政府主义的结果。[ 参见胡玉鸿:《全民守法何以可能?》,载《苏州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第59页。]为防止作出草率判断,应在坚定服从的基础上进行批判,尽最大限度的努力去弥补法律之不足,
并为法律的实质性转化付出自己的真实行动,从而实现对法律的批判。[ 参见郑智航、张笑:《守法论要》,载《当代法学》2003年第10期,第16页。]
探索守法的实现路径是落实全民守法的重要举措。法治的实施离不开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相互配合的运行机制,需要将全民守法置于法律实施全过程进行考察。信任立法是全民守法的基本前提,配合执法是全民守法的内在要求,倚赖司法是全民守法的重要方式,自觉守法是全民守法的核心要义[ 参见李林:《建设法治社会应推进全民守法》,载《法学杂志》2017年第8期,第4-5页。],在此意义上,实现全民守法必然要求同步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此外,普法教育是推进全民守法的重要措施。当前,普法内容需从注重形式向提升实效转变[ 参见陈甦、刘小妹:《以创新精神推进普法提质增效》,载《人民论坛》2019年第18期,第98页。];普法方式需以媒介融合发展为契机,积极探索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结合的普法模式[ 参见林凌:《新媒体普法传播模式创新研究》,载《当代传播》2018年第5期,第85-87页。];普法目标亦需从秩序维护转向法治观念的塑造,优化推动普法的良善发展。[ 参见付子堂、肖武:《普法的逻辑展开——基于30年普法活动的反思与展望》,载《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6期,第204页。]守法利益诱导机制是实现全民守法的关键举措。完善全民守法激励和惩戒机制,鼓励守法诚信行为,约束违法失信行为,是全民守法的基本导向。[ 参见单颖华:《当代中国全民守法的困境与出路》,载《中州学刊》2015年第7期,第51页。]
培育守法精神为形成全民守法氛围提供内在保障。只有当全社会的人们都具有普遍的守法精神或守法意识时,才能营造出全民守法的良好氛围。正如日本学者川岛武宜认为,近代化的法不同于其他各个历史时期所有的法律,它尤其不可缺少的条件是一定的意识性、精神性的因素。[ 参见川岛武宜:《现代化与法》,王志安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2页。]现代法治之所以呈现一种内在自觉、普遍有效的理性秩序,除了法律制度的内在价值与公民意识的合理性、合法性要求相吻合之外,另一种重要的因素就是它离不开公民积极守法精神的支撑。[ 参见马长山:《法治社会的根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4页。]因此,守法精神的培育至关重要。关于如何培育公民守法精神,除强化公民对国家法律制度合法性的认同、揭示法律之于社会发展和个人幸福的价值、培育具有“内在观点”的公民[ 参见魏治勋、刘一泽:《法治的根基在于培育具有“内在观点”的公民》,载《学习与探索》2019年第7期,第64页。]、加强普法宣传教育等基础研究之外,另外一条不同的进路主张进行实证研究[ 参见杨春福:《全民守法的法理阐释》,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年第5期,第68页。],例如加强与全民守法相关的概念及其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通过鲜活的素材和令人信服的理论让全民知晓法律、遵守法律。
2.以价值目标为导向的尊法守法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使尊法守法成为全体人民共同追求和自觉行动”,“尊法守法”成为新的要求。“尊法守法”不同于“遵法守法”,虽只有一字之差,但两者含义有很大的差别。遵法守法,意味着公民必须遵守法律,可以是被动的,也可以是主动的,但总体上它是一种社会倡导的行为准则,法律仍然是外在于守法主体的规则体系。“尊法守法”则是源于尊重法律的基本价值观和一种内心的崇尚坚守,不仅是在思想感情上主动接受,同时也内化为一种生活方式与行为自觉。正如美国学者昂格尔所指出的那样,人们遵守法律的主要原因在于,集体成员在信念上接受了这些法律,并且能够在行为上体现这些法律所表达的价值观。[ 参见[美]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周汉华译,译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9 页。] 伴随着法治现代化的推进,多元参与治理格局的形成为以价值目标为导向的尊法守法提供了动力。国家治理过程中,公权力主体不再是简单的单向管理者,公民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实现自身价值的机会和渠道更加多元。公民守法不再是屈于管制之下的服从,而是一种自觉行为,这种自觉的主观心理状态以“信念”为核心,它是守法主体与客体、文化环境的最佳协和,也是守法主体对客体和文化环境的超越,并因而充分显示出人的主体性。[ 参见胡旭晟:《守法论纲——法理学与伦理学的考察》,载《比较法研究》1994年第1期,第11页。]价值目标导向下的尊法守法,不仅体现出对法律规则的认同和尊重,更是对其背后所蕴含的价值理念和治理逻辑的尊重,民众在理解和接受的基础上形成稳定的心理状态和一以贯之的行为自觉。
二、新中国守法理论的总结与评述
守法理论的初步发展时期,在阶级性法本质的影响下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体现为“人民——敌人”相区分的守法形态,形成了集体意志和利益驱动下以义务为核心的传统守法理论。服务于当时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守法成为一项重大、光荣的任务,以崇高的使命感号召人民主动、自觉地守法,在有力地进行对敌斗争的同时,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胜利。传统守法理论是对当时社会实际和守法实践的深刻反映,紧密结合巩固新生政权、确立新的社会秩序的现实需求,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和各项改造的推进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发挥了积极作用。一方面,号召提高人民内部的觉悟,加快建设速率;另一方面,防止敌人的破坏,保障建设顺利进行。但也应当看到,这一时期对守法的理解和认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守法理论中蕴含的“人民—敌人”相区分的守法观念,法律未能成为人们社会生活所普遍仰仗的理性形式。[ 参见胡水君:《〈法学研究〉三十年:法理学》,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6期,第52页。]集体利益和意志驱动下以义务为核心的守法,本质上仍然体现为被动的、消极的守法,这种国家主义本位法律观下的守法理论,忽略了守法个体的主体性和守法权利保障的意涵。
改革开放新時期的守法理论,在对传统守法理论进行反思的过程中,转向了对自身基础理论的正面建树和探讨。在系统阐释守法的概念、范畴、原理等基础理论的同时,积极回应改革发展的需要,以改革之精神,推动守法观念之转变。受以权利和义务重构法学理论体系思潮的影响,守法权利观逐渐兴起,依法享有权利并行使权利成为守法理论的应有内涵,行使法律权利既是遵守法律的具体表现,更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动力。[ 参见夏华:《守法与权利的享用》,载《法学》1990年第9期,第13页。]守法权利观注重激发守法主体的自主性、能动性,在遵守法律之外延伸出公民用法和护法的内容,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以人的主体性为基点的积极守法理论。积极守法鼓励公民把法律作为维护自己合法权利的工具,为了自己权利的实现和利益的维护而自觉地遵守法律。尽管在这一时期,守法已突破消极履行法律义务的藩篱,获得积极行使权利的内涵,但是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若缺少社会心理基础和前提——公众的法治认同,仍然会遭遇强大的阻力而举步维艰。[ 参见李春明、张玉梅:《当代中国的法治认同:意义、内容及形成机制》,载《山东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第132页。]基于此,守法理论仍需作出进一步回应,关注影响守法自觉性、主动性的法治认同问题,为法治社会建设提供稳定的社会心理支撑。
法治建设新时代,全民守法的提出为守法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创新驱动,通过对全民守法基础理论的阐释使其基本的运行机理得以清晰展现。这一时期的守法理论关注守法主体内心对规则本身的尊重和认同,致力于实现让尊法守法成为全体人民共同追求和自觉行动的目标。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征程中,法治成为国家和社会治理所必须依托的重要方式,全民守法作为法治中国的基石,与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目标紧密地联系起来,使得守法理论得以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场域中展开。多元参与的治理模式为守法理论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守法主体之间交互性的增强,使法律规范由侧重于约束消极行为发展到重在激发积极行为,从而把法律要实现的价值目标转化为守法主体自己的价值目标,并通过积极行使法定权利、忠实履行法定义务参与到守法社会建设的进程中。作为社会治理的“参与者”,守法主体在信念上尊重和认同规则背后的法律精神及其基本价值理念,并将其转化为主动守法的行为自觉。但是这种以价值目标为导向的守法理论仍可能遭遇一定的困境。法的价值是主体内心确立并确信的绝对超越指向[ 参见卓泽渊:《论法的价值》,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6期,第4页。],正是由于价值世界的超越性,这也意味着人们所能作出的实际努力,与彻底实现法的价值对人们提出的要求总有或多或少的距离。同时,面对价值多元的冲击,探索整合多元价值的途径和对策,加强法治认同和守法社会建设的重要性不断凸显。
三、新时代守法理论的发展面向
新中国守法理论的发展烙印着明显的时代特色,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稳步前行。从传统守法理论到守法基础理论的演进,为守法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守法基础理论到全民守法理论的展开,为守法理论进一步跨越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之相对应,其背后蕴含着消极守法、积极守法、尊法守法的守法观也呈现出不同的内涵,理论和观念两条主线的交织勾勒出新中国守法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脉络。立足当前,仍然需要在理论——实践双向互动的图景中,直面转型时期改革与法治之间存在的张力、价值多元对守法带来的冲击、全民守法与守法社会建设面临一定阻力等现实挑战,在不断回应实践的过程中实现守法理论的渐进发展。
妥善处理改革与守法之间的关系。改革的核心是创新突破,强调“破”和“变”,而法治的核心是规则秩序,强调“立”和“定”,深层次、全方位的变革,必将引发法律体系、法律制度、法律实施等各方面的深刻调整与变化。[ 参见吴洁:《在法治下推进改革 在改革中完善法治》,载《红旗文稿》2019年第5期,第34页。]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当二者之间存在张力时,如何妥善处理改革与守法的关系。当前,改革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确立的目标及规则所架构的法治秩序下进行,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已成为基本共识,但哪些改革事项需要通过试验来积累经验,哪些改革事项应当直接全面推行,如何实现改革与守法的互动协调等尚处于探索阶段。以合法性授权为例,尽管《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重大改革于法有据”,但“实践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要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这一规定一定程度上为改革试验提供了合法性依据,但授权制度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除授权主体、授权事项、授权程序等有待进一步明确之外,改革试验仍面临着试验路径与方法不确定、改革试验参与者权利与义务不明晰、改革试验的合宪(法)性审查等问题。改革过程中既可能出现无法可依的困境,又存在违反现行法律的风险。消弭改革与守法之间的张力,既需要实现推进改革与遵守宪法法律的有机结合,又需要立足社会变革实际,把握法律修改与法律稳定性、权威性之间的关系[ 参见解永照、何晓斌:《“改革于法有据”的争论及其破解——基于良性违宪的思考》,载《理论探索》2015年第4期,第113页。],现有守法理论亟需在理论与实践的融贯中渐进突破,为这一难题的破解提供理论支撑。
强化法治认同的根基。法治认同作为社会认同的一种,需要社会公众在社会交往和社会实践中形成对于法治的理性认知和情感,并把这种理性认知和情感转化为自身的行为选择和具体行动。[ 参见尹奎杰:《法治认同培育的理性逻辑》,载《北方法学》2016年第3期,第113页。]法治认同对于守法而言尤其重要,因为社会公众一般价值判断通常呈现出松散的、弹性的样态,集个性与共性、理性与非理性因素于一身。因此,对于不同的法律是否具有道德正当性,人们的看法可能会有所不同,进而选择性遵守。众多复杂因素交互作用下的多元价值将会对守法价值共识的形成产生阻力,亟需以法治认同凝聚共识。守法不是静态的,守法过程将守法主体和守法客体贯穿起来了,形成立法者——普通民众——司法、执法者的三层结构,由于知识技能、思维方式的差别,法律职业群体能够根据专业的法律知识开展工作,而普通民众大多凭借日常生活经验和对法律的直觉行事。这种对法律的理解和运作能力的差距,导致对普通民众进行单方面守法灌输往往收效甚微。为此,必须以过程论的视角结合守法主体的守法体验来重新审视。美国学者泰勒通过一系列实证研究表明,在人们评价法律当局时,程序是否公正的问题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特别是,如果人们对法律和法律当局的总体看法是他们通过總结自己的某一次具体的个人经历而得出的,程序正义就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参见[美]泰勒:《人们为什么遵守法律》,黄永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142页。]基于此,守法理论在强调价值目标认同时,需要从实质和程序两个方面强化其根基,既要努力制定良法,也要保障立法、司法、执法遵循确定、公开的程序,使得普通民众能够参与其中,以广泛听取和吸纳公众意见强化认同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在守法过程中,立法、执法、司法也要接受人们对其合法性的评价,也即在守法互动中允许人们根据自己的道德价值观进行相应的解读和评判。
完善守法社会的理论构建。全民守法要求在建设法治社会的整体场域中把握守法,守法社会的建设应当成为全民守法的“高级目标”。虽然既有研究已经涉及影响和塑造守法社会建设的许多关键要素,例如守法主体、守法客体、守法运行、守法状态、守法精神等,但尚未形成一套有机整合各个要素的守法社会构建理论。当前,无论是以法治社会和社会治理为核心范畴的理论研究的兴起,还是全民守法和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的展开,都绕不开守法社会建设这一主题。从法治社会建设的整体性视角来看,守法并非孤立的社会现象或形态,而是渗透于立法、执法、司法、护法等各个环节。各环节之间既具有独立职能又相互联系,统一于法治社会建设的系统工程之中。如果将守法社会建设看作一个有机整体,守法不仅要求守法主体独善其身,而且要以积极作为、自觉守法的态度和建设主体的角色积极参与到建设守法社会的进程中。因此,有必要将关于守法问题的探讨从守法本身拓展到法律实施甚至法律实现的全过程,结合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实际对守法理论自身做出调适,系统地发展出有关守法社会建设的法学理论。无疑,守法社会的建设将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把守法主体、守法客体、守法环境等分散的要素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贯穿于法律制定、法律实施、法律实现的全过程之中,进而发展出关于守法社会建设的综合性、整体性理论。当然,守法社会的建设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予以推进,理论的发展不能脱离实践而存在,如果在理论上首先假设了个别法规的正确性,同时又假设大部分人都可以理解其正确性而守法,因而忽略了法律实践层次的问题,将是不切实际的。[ 参见卢敏超:《中国法律改革的现实层次》,载《法学评论》1992年第2期,第61页。]
结语
回顾新中国守法理论的发展历程,其发展脉络及与制度实践相互动的图景得以展现:新中国成立初期,伴随着“废旧立新”的法律变革,守法理论逐渐开始起步,在巩固新生政权及保障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时代背景中,呈现出以强调守法义务为核心的消极守法样态;改革开放新时期,守法理论逐渐复苏,与经济社会恢复发展及立法供给快速增加的实践相对应,在守法权利观的影响下,以法律主体性为基点的积极守法图景逐渐明晰;法治建设新时代,在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时代主旋律中,全民守法的提出为守法理论创新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价值目标导向下的尊法守法成为新的追求。这种演进发展既是个体守法境界的提升,又反映整个社会的守法状态的变迁。个体守法境界的提升虽然深受客观物质条件的影响,但人的主体性在其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社会整体守法状态的改变则受制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文明进步程度及法治的实现程度等。立足当前,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期,进一步深化改革,需要处理好改革与法治的关系,坚持重大改革于法有据;面对价值多元的冲击,需要从实质和程序两个方面强化法治认同的根基;推进守法社会建设,需要将影响和塑造守法社会的要素进行有机整合,并从社会系统运行层面综合考察不同要素之间的联系,进而获得体现守法社会运行机理的整体性理论。面向未来,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不断深入,在理论与实践的交织中将会产生更多的知识增长点,助推守法理论不断向前发展。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Law-Obedience
Theory and Concep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U Xing-fu, GUO Bing-gui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Abstract:
Law-obedience is the basic method of law enforcement, and the basic requirement of socialist rule of law. The law-obedience the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gone through three main stages. The first stage has begun since the countrys inception. Influenced by the class nature of law, the law-obedience concept was in the form of the distinguishment between people and enemy centering on law-obedience obligation. The second stage is in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eriod, in the process of introspection and refle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theory, the law-obedience theory turned to the basic and original theory, which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based on the legal subject. The third stage is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rule of law period, the proposal of obedience of law by every citizen provides an innov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w-obedience theory.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its operation, the law-obedience by every citizen theory oriented towards the recognition the value of the law is formed. At the same time, the three stages are supported by the ideas of negative law-obedience, active law-abiding and respecting and obedience of the law respectively. The intervening of the ideas outlined the development of law-obedience in theory and in practice. At present, it is still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law-obedience theory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hand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w-obedience and reform, strengthening the recogni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mproving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law-obedience society and other points related to the law-obedience theory.
Key Words: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aw-obedience theory; law-obedience concept
本文責任编辑:董彦斌
收稿日期:2020-07-0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法理学研究70年回理与评析”(19AFX002);重庆市人文社科项目“搜索引擎链接提供中的权利平衡研究”(17SKG147)
作者简介:
陆幸福(1974),男,江苏溧水人,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郭秉贵(1993),女,甘肃白银人,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 参见李娜:《守法社会的建设:内涵、机理与路径探讨》,载《法学家》2018年第5期,第17-18页。